107·特稿|阴阳有知否,哀敬处几何? ——殡葬改革下的冲突与和解


全文共4889个字,阅读大约需要8分钟· 《礼记》中记载:“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丧礼和祭礼作为传统礼制的一部分,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燃烧随葬品带来的隐患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厚葬的习俗,正在被时代重新考量。· 北京民政局的官网上,介绍了骨灰自然葬、海葬、立体安葬等较为新型的节地生态安葬方式。· 并非所有的殡葬从业者都能适应这种调整。位于八宝山后的上庄东街曾被称为“殡葬一条街”,街上曾有30多家售卖丧葬用品、提供殡葬一套龙服务的商家。·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同年级的大部分同学虽是无神论的观点,对死亡也有各种解读,但大部分都倾向于相信“逝者有灵”,相信人死之后有其他的归处。本文原刊于《107调查》第五十二期第六版
记者丨周雨卉 宛禹町 刘畅 张佳 赵晟萱
文编丨许露颖 易艳鑫 李鑫
农历十月初一,寒衣节。这天夜幕早早降临,寒风肆虐。
薛甲和母亲准备好纸袄和冥币,走到西便门附近的路口。他用粉笔画一个大圈,向着东北的方向留一个开口,那正是外公外婆沉眠之地的大致方位。
母亲拿着长棍翻动着燃烧的黄纸,灼烧的热气混着纸灰飘散,她喃喃道:“爸爸妈妈,在那边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有什么事托梦给我。”
同在这个寒冷的夜里,出租车司机王军开足了暖气,望着远方染上灰度的天幕打了个喷嚏。据他说,今天北京市七成以上的路口都有人在烧纸,“都是封建迷信”,他不以为意。
《礼记》中记载:“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丧礼和祭礼作为传统礼制的一部分,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慎终追远 厚葬长殡
唐微哲对爷爷奶奶的过世印象深刻。
她的老家在京郊农村,一直较为“传统”。初中时,爷爷在家中过世,爸爸和叔叔用干净的毛巾蘸着温水,一点一点为爷爷擦干身体,然后换上寿衣。沉默地看着老人平静的面孔,唐微哲觉得,死亡和普通的午睡没什么不同,却又有说不出来的异样。
接下来,她在遗体旁守了两天灵。各位亲友前来吊唁的情态她已记不太清,只记得守灵时和母亲、婶婶、堂弟一起戴着被称作“孝”的纯黑色袖套。“孝”的顶端还缝了一个红色的线团,表明孙子辈的身份。
一年后,奶奶随爷爷去了。那是大年初三,亲戚们陆续赶到病房。姑奶奶从一进门就开始哭嚎,她跪在床边,哑着嗓子喊道:“我的姐姐啊——你怎么就走了呢——” 一旁的二婶也发出嘶哑的呜咽声,由于在医院而刻意压低了音量。情绪的自然宣泄之外,她们都遵守着传统习惯中“哭丧”的需要。等亲友们都来见过最后一面,殡仪馆接走了老人的遗体,两天后火化并下葬。
正月初五,唐微哲和母亲先到殡仪馆,一起在焚烧炉处烧了些黄纸。等亲友差不多聚齐,简短的追悼会在殡仪馆的大厅进行,司仪引导着大家做最后的告别。她和其他人一起绕遗体一周,然后作为直系亲属,恭敬地磕了三个头。礼毕,她目送老人的遗体被送进火化炉。
火化结束之后,殡仪馆提供了一台轿子,把骨灰盒送到唐微哲家的车上。堂弟作为长孙,一路手捧着骨灰盒。堂姐的丈夫拿着两串“天圆地方”的方孔圆形纸钱,一路上断续地将钱撒出车窗外。
回到村里,墓穴已经开好。大家纷纷把手臂上的黑色袖套摘下扔进墓底,再将奶奶的骨灰放在里面,和爷爷并排,而后封好墓室。长子长媳分别头顶着一床被子下跪,配合完成封土规章中的仪式礼法。
唐微哲已经记不清是否有哀乐,只有姑奶奶那声“我的姐姐啊”的哀吟混合着沙土、冷风与飘飞的火星回荡在她脑海中。
之前买好的纸牛纸马纸轿子,这时被抬过来。先是分别砍断牛、马的一条腿,断了这些牲畜“逃跑”的后路,然后一把火烧净,希望能把这些东西送到亡者手中。
唐家的仪式已经是精简过的了。
曾经,在火葬前一晚,家人们在守灵之外,还需要敲锣打鼓游行,称之为“大席”,并烧些纸钱,让风把一张纸帽或其他的什么吹起来,所有人跑着追逐它,希望追到之后能被亡灵附身,听逝者再回来交代几句,再和亲人说说话。
在办丧事的几天里,家里人在路上遇到认识的长者,要依辈分关系行单膝跪地或双膝跪地之礼,报上自家老人的死讯。
这些仪式如今已被淡忘,但是唐微哲一家和叔叔一家作为直系亲属,仍恪守着“三年居丧期间,正月里不串门”的传统——若是串门,会给对方带来霉运。每年大年初三、清明、中元、忌日、寒衣节等祭拜时日,还要和爷爷兄弟家里的代表一起去坟前奉上果盘和糕点,烧些纸钱祭扫,聊表哀思。
关于爷爷奶奶的厚葬,唐微哲倒不是太相信“灵魂不灭”或“天堂地府”的那一套说法,只是宁愿想着“他们还在某个地方看着自己”,让自己更容易接受他们的离开。唐微哲也感慨“这么繁琐,太累了”,不过,经历了守灵、出殡、下葬等仪式,目睹“安眠”的老人已经化成洁白的骨灰,只剩下眼前的黄土堆后,她终于清楚地认识到了亲属的死亡。而最初脑中的空洞、不知所措,也转化成悲伤,并在仪式中得到了冲淡和疏解。“我也愿意用最长的时间,和最爱的人告别。”
葬礼传统的沿承之外,现代化的急速发展致使土地资源越发紧缺,处在北京市五环以里的八宝山人民公墓六七年来都没有建过新坟,海淀区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也早已饱和。燃烧随葬品带来的隐患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厚葬的习俗,正在被时代重新考量。
葬之有节 祭奠从简
北京民政局的官网上,介绍了骨灰自然葬、海葬、立体安葬等较为新型的节地生态安葬方式。
骨灰自然葬,是指使用可降解容器或直接将骨灰藏纳土中,并在周围种树种花,不建墓碑和硬质墓穴。骨灰海葬,是在北京市殡仪服务中心的组织下,到天津渤海湾,将亡者的骨灰撒入大海,并放飞和平鸽。立体安葬则是指骨灰盒并不入土,而放入占地较小的立体骨灰墙。
八宝山人民公墓的怀思阁是一处古式塔形建筑群,已经设立20余年,专门用于封存式集体深葬(逝者的骨灰按顺序放于怀思阁中,而后亲属不能进入,将逝者姓名雕刻在外墙上以便祭祀),这也是八宝山“老墓改造”计划的一部分。

(八宝山人民公墓服务厅前空地,水池里是残荷枯叶,围墙后有隐约的墓碑林立。 周雨卉 摄)
每位逝者的骨灰在怀思阁中的安置费用为500元,如果是本在八宝山人民公墓园内的老墓,家属若自愿迁入怀思阁深葬,则安置费用降为400元。而传统的建造墓穴和墓碑、入土安葬的方式则平均需花费四、五万元。怀思阁共有12座深葬塔,共计有五、六万处骨灰深葬位。而据倪主任介绍,建阁20余年来,仅仅售出4000处。
2015年10月19日,北京市民政局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绿色生态殡葬建设的意见》,倡导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遗体处理无害化,提高祭祀文明程度,应用环保型殡葬用品;要求有墓地的区县建设一处绿色生态墓地示范园。
为响应政策,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八宝山殡仪馆在2016年3月停掉了曾经用于焚烧黄纸或其他殡葬用品的焚化炉,在葬礼上烧纸钱、烧贡品的行为也随之被明令禁止。殡仪馆旁的八宝山人民公墓里,“文明祭扫”“鲜花送亲人”“严禁烧纸、燃放炮竹”等横幅标语十分醒目。

(八宝山人民公墓内标牌。 周雨卉 摄)
八宝山人民公墓历来是不设焚化炉的,据宣传处负责人倪主任介绍,前几年还有在园区内偷偷烧纸的行为,现在已经基本绝迹。取而代之地,公墓中的一些墓碑上搁着一束鲜花。不过,“墓碑上的花其实都是我们发的。”倪主任摊手说道。
万安公墓的焚化炉目前可以正常使用,但在园区内,同样严禁在炉外烧纸,四处打着“违者罚款500元”的标语。公墓花店的生意倒更加兴隆,寒衣节当天上午,花店老板忙着给前来扫墓的家属准备鲜花或花篮,基本没有空闲。
并非所有的殡葬从业者都能适应这种调整。位于八宝山后的上庄东街曾被称为“殡葬一条街”,街上曾有30多家售卖丧葬用品、提供殡葬一套龙服务的商家。这些从事殡仪服务的商贩除了要获得工商部门的许可证,还需得到民政局的资格认定。
3月,北京市启动“殡葬服务提升年”活动,3家存在违法行为的殡葬用品销售商店受到了处罚,被收缴非法宣传牌匾6块、冥币等丧葬用品15公斤。今年清明节,上庄东街被民政局突击检查,冥币、纸牛纸马等物品是重点查收对象。8月份,街上大部分商铺被拆除,只留下了两家骨灰盒商铺,以及一家提供各种丧葬用品和“殡葬一条龙”服务的商铺。
在人民公墓前后门口,一些小贩在地上简单摆几个花篮铺几沓纸钱,或削细树枝继续手工编花篮,或摆个小桌打牌、玩手机,时不时抬起头四处张望,警惕着随时可能出现的城管。
谈到上庄东街商铺拆除的原因,倪主任则表示,“殡葬一条街”的商贩和殡仪馆存在一定的商业竞争。而殡仪馆工作方面的负责人李主任表示,殡仪馆服务的价格都是统一的,依据政府有指导价和定价,“都是由发改委制定,定完就是死的。我们是价格合适服务周到,不像后街不规范的小店存在谋取暴利的情况。”
“瑞景祥”是一家原位于上庄东街的从事殡葬一条龙服务的商铺,在东街的商铺拆除行动后,而今已搬到了山上人民公墓的后门。在“瑞景祥”店员肖督看来,诸如殡仪馆为逝者遗体净身时所做的“沐浴”(即为遗体洗澡)仪式,其实就是并不必要的服务,只需“用酒精和毛巾为逝者擦拭身体”即可,所谓“沐浴”这种仪式,对逝者家属来说,只会加重其费用负担。“蒙人的事我们不做。”肖督说,“都说殡葬黑,但我们干好(的标准)不是挣多少钱,而是把活干好。我们干这行,主要就是方便家属。而且我们的价格比殡仪馆低,从服务(好)到价格(低)。”
“瑞景祥”的客户主要来自朋友、熟人或者曾经的客户介绍,生意受影响较小。肖督反倒觉得一条街拆了好,“因为很多小型的店铺不守规矩”。他称“不宣传迷信”,对于想要偷烧纸牛纸马的家属,他告诉对方“别信这些”。“为了环境,绿色,文明殡葬,很多都省略了。”
他觉得家属可以理解。

封建迷信抑或公序良俗?
由于爷爷的过世,大学生刘德森在高中时生发了一个想法:做一个关于“生死观”的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同年级的大部分同学虽持有无神论的观点,对死亡也有各种解读,但大部分都倾向于相信“逝者有灵”,相信人死之后有其他的归处。刘德森据此认为,这是人们细腻而感伤的自我安慰的表现,是无论如何都应该被尊重的。而令他无法接受的是,他的指导老师很干脆地告诉他:“你的结论一定要是‘这说明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唯物主义的教育,拒绝封建迷信’”。
丧葬之礼,究竟是封建迷信还是公序良俗?
“这谁都不好说。”倪主任摆摆手,有些为难。他认为这些礼节既承担着一定的社会作用,又加持着一部分封建迷信渲染。
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人类学方向的康敏副教授解释道:“中国的祖先崇拜有两个层面,就是葬礼和祭祀。祖先崇拜是一个应对社会危机的策略,人已经死亡了,社会成员已经消失了,改变死亡带来的负面影响的一种方法是假设死者继续存在,以此来减轻可能出现的悲伤和颓废消极,不让这种社会危机爆发。同时因为葬礼是一个家族都来参加,它又加强了社会和家族的凝聚。”
传统的儒家思想十分重视丧礼和祭礼,但却在主张“厚葬”的同时反对鬼神崇拜。《论语》中写道,“丧致乎哀而止”,而孔子本人也强调“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与之相对,宣扬“节葬”的墨家却认同鬼神崇拜。《墨子》中记载“棺三尺,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却同时赞成“天志”和“明鬼”。
但无论是厚葬还是节葬,正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所言,祭礼的缘起是相信鬼神的存在,但能演变出近乎礼法的祭祀习俗,则是出于朴素的哀思,出于对先祖的感情。
社会飞速发展,但死亡仍是敏感禁忌话题。年轻一代和老一辈之间,在“白事”“烧纸”等事情上有观念的差异。刘德森本人心中有一套转世观,他认为人会转世,既然逝者已经转世,烧的纸钱纸衣实际上就都无法收到。虽然会在清明节一起和家人烧纸,但他相信,只要人活着时尽了孝道,心意在了,仪式便不再重要。“如果我自己走了之后,我希望家人把我往海里一撒,烧不烧纸的都无所谓。”
每年都在寒衣节烧纸祭拜的许大爷觉得,这并不是一个相不相信死后有知的问题,而是传统,爷爷、父亲都是这样祭拜祖先,自己也习惯于这样的方式,至于儿子将来如何,他并不会强求。
“怀念、追忆、哀思,都是重要的传统美德,不能忘本。”寒衣节的路口,另一位在烧纸祭祀的张奶奶笑着说,“但如果这些形式没有了也可以,重要的是心意。我知道一些年轻人也有什么网上寄哀思的形式,不过对我们来说,有点跟不上。没有出来烧纸的话,心里头总有点什么别扭着。”她在路口画下两个粉笔圈,不同的开口朝向,分别祭拜自己的父亲母亲和公公婆婆。
李主任说道,“烧纸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把心里悲伤的情绪发泄出来,你要给他一个出口吧。我们也在下大力气筹建生命文化教育基地。”他认为殡葬改革不是对之前的全盘否定,只是逐步地去做目前能够做的事情。
但是康敏老师认为,从土葬到火葬的变化、丧葬仪式的简化,这些殡葬改革已经“和我们的传统差了太多”。 “但它仍是人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过渡仪式,肯定不能简单判定为封建迷信而加以取缔。仪式有其社会功能和象征意义。”
刘德森有时会回想起,在爷爷过世后,他曾戴着“孝”上学,当时沉浸在悲伤心情中的他,甚至没有留意过同学们曾对他投去或怪异或担忧的目光。如今再想起当时的心情,他的感慨也一如他当年问卷调查的结果:“大部分同学都不相信死亡即是终结,我也一样,我愿意对(爷爷)死后(所去)的世界怀有期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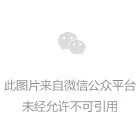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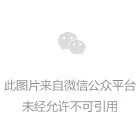
(除康敏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手记
第一次带题写稿,有很多的困难,文章也有很多的缺点,不过总算能顺利见报,感谢组里的大家和易推拉三位文编,也感谢能看到这里的各位读者。
我很喜欢《哈利波特》对夜琪的设定。面对过死亡之后,会想到一些哀伤而严肃的论调,开始看到巨大的灵兽在透明的虚无中奔跑,原来一直以为很遥远的事物,实际上就在自己身边。对生活的思考会发生一些变化,对生活的态度也是。所以我才会想,人们怎么看待死,影响着人们怎么看待生。
而为了逝者所做的一切事情,实际上都是为了还活着的人吧。故去的亲友就像星球边的暗物质,纵使不能相见,你的引力仍在。不知道烧一撮纸,点一炷香,祭一篮花,或在网上点一蜡烛,怎么样才能离你更近一点。
自身能力有限,我的稿件没有办法展现殡葬业的全貌,也不能为殡葬改革指明清晰的道路。只是听过了火葬场里男人的哭嚎,见过了黄纸灰旁老人的笑泪,对这些难以忘怀。



点击 关键词 查看往期内容
民大西路整改 | 北外后街故事 | 曼彻斯特爆炸 | 性教育 | 地下租客 | 艺考| 盲目放生| 视障群体 | 战地记者 | 小众服饰 | 素食主义 | 共享单车 | 医院挂号难 | Live House | 网络平台Up主 | 电子竞技 | 数字音乐| 曾海若 | 配音演员 | 大鱼海棠 | 独立纪录片 | 中医药 | 低龄留学 | 知识分享经济 | 北京地铁工作者 | VR体验站 | 瓶内画 | 三联韬奋书店 | 北外零点后 | 大栅栏 | 法医 | 北京小剧场 | 网络文学 | 相声“新生代” | 京剧 | 北理工足球 | 抑郁症 | 海淀城中村 | 北京站流浪人员 | 大学生微信公号 | MH370失联两周年 | 诗歌巴别塔 | 网络课程 | 网络主播 | 脱口秀 | 传销 | 线上支付 | 独立出版 | 性少数派 | 外研书店 | 斗狗产业链 | 尘肺病 | 皮村纪实 | 裸模 | 飙车族 | 人大东门假学生证 | 广东“麻风村” | Cosplay ️| 粉丝应援 | 导盲犬 |宋庄画家村 | 跨性别者 | 中关村乱象 | 高校博物馆 | 唐家岭 | 癌症村 | 青旅义工 | 打字员兼职
美编 | 赵曼婕
阅读原文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