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D新院长Sarah Whiting谈建筑的“物性”



学生们仍沉溺于盲目模仿,既不研究也不分析,鲜有鞭辟入里的观察,全然只顾生搬硬套。这暴露了我们的现状:建筑不断妥协,濒临失败,甚至整个studio还以这种现状为荣,庆祝狂欢。
一个广泛的共识正在缓缓地、不容置辩地浮出水面:“侧重建筑的物性和形式就是缺乏社会关怀,是建筑圈的大忌”。
我既不期许单体建筑可以具备扭转社会的能量,也不可能盲目犬儒式地追随商业风潮,我只是看腻了不少学生前赴后继地在设计中提出“评论”,而非用设计项目本身去回应“评论”。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99篇讲座。
本文整理自2015年2月7日由哈佛GSD新任院长Sarah Whiting于新西兰建筑师学会主讲的题为“I Object”的讲座。讲座由东南大学孙志健记录整理,由莱斯大学曾师从于Sarah的黎乐源校对并推荐。
记录者:孙志健

被怀疑在某宝找枪手的文字工作者
推荐人:黎乐源

南京大学建筑学学士,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建筑学硕士,曾任职于OMA, SOM等事务所
主讲人:萨拉·怀汀
(Sarah Whiting)

耶鲁大学文学学士,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硕士,麻省理工学院哲学博士,WW Architecture联合创始人兼合伙人。担任莱斯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直至2019年4月17日受任哈佛大学设计学院院长,1999-2005年于GSD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设计评论家,2005-200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助理教授,曾任教于IIT、肯塔基大学和佛罗里达大学,曾担任建筑杂志Assemblage编委会成员,并任职于Peter Eisenman和OMA等事务所。
正文共10894字74图,阅读完需要12分钟
推荐语
本篇讲座由Rice University硕士黎乐源推荐
萨拉•怀汀(Sarah Whiting) 是一个雷厉风行,却又极具亲和力的院长。
莱斯建筑学院规模很小,学生与教授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与交流,而萨拉正是这些交流的践行者,她记得学院里所有学生的名字,记住他/她的优点与缺点,循循善诱。她是一个风趣幽默、思维极其敏捷的理论家,也是一个态度明晰、行事干练的实践家。从她身上,我领会到建筑师在这个怪诞的社会面前所该秉持的态度。
有幸在萨拉临走前,上了萨拉和斯科特•科尔曼(Scott Colman)关于当代建筑实践的研讨课。在课上,萨拉屡屡强调当代建筑所面临的迫切难题(urgency),建筑语境里的观众(audience),建筑师的姿态(position),以及其力所能及的贡献(contribution)。于她而言,从过分强调指向性(indexicality)与自治性(autonomy)的批判主义(criticality),到到充斥着虚无主义(nihilism)的当代建筑理论,建筑变得越来越沉重且亦步亦趋。在“一切皆为建筑”(Architecture is everything)的共识间,建筑丧失了独特性,而在越发盘根错节的学科之间难以呼吸。然而,也正因为建筑作为一个通识学科,萨拉希望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当代建筑师与建筑评论家所面临的危机,以一种主动,敏捷,且明确的姿态入世。
下文中提到的《关于“多普勒效应”的笔记与现代主义的其它状态》一文,正是萨拉和罗伯特•索默尔(Robert Somol)在当代主导的范式(paradigm)面前——对于批判性(criticality)的过分追崇——所采取的态度。她与索默尔另辟蹊径,提出一套“投射性的”(projective)模型——相比于通过建立自治性以区别其它学科的辩证法,多普勒建筑强调表达(performance)与实践(practice),强调建筑学科与生俱来的多样性所产生的效果即其间的互换(例如材料,图解,协作,技术等等),强调文脉、建筑、使用者之间主体与客体间的多重交集与相互影响,从而触发使用者对于建筑的不同领会。对于萨拉而言,这套理论并不在于批判或否认当下的批判性(criticality),而是希望通过一种质问的姿态,反思建筑沉重的自主性,以一系列不完整的回应,为建筑论述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最后,回想过去的两年,萨拉总强调我们要有自己的论点(argument),无论是设计还是理论。批判别人是简单的,但有自己明确且坚定的立场却是最艰难的。谢谢萨拉在过去的两年里,耐心地为我们点亮了一盏拨开迷雾的明灯。
讲座正文
很荣幸来到新西兰建筑师学会,感谢组织者John和Charles的陪同和关照,感谢来自新西兰的两位挚友Mike Austin和Jill Matthewson的引见,这是我第三次在此演讲。我将从当今建筑文化体系中所见的现状展开来谈,这些思考时刻羁绊着我,当然听起来有点像说教(didactic),不过这也是我作为院长、历史学者、作家的本职工作。然后我会讲到我们自己的作品,所以如果你们对前半段的叙述兴致寥寥,请少安毋躁,最后我会讲到实际项目。

最近我被一个怪诞的共识激起了讨论的兴致,这个所谓“实体是罪恶的(object is bad)”的共识不仅遍布建筑评论界,甚至渗透进了广义的建筑思考领域,这似乎与自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以来“实体是现代性的重复(object is a refrain of modernity)”的理论危机稍有差别,我们迫在眉睫的危机更像是一种对实体的回避(shunning)。第二种共识在建筑讨论中是更普遍的潮流,那就是对理论的回避。焦虑、危机、灾难(apocalypses)……我们有无数类似的批判性主题作为早间新闻的不竭素材,但我并不认为我们有必要用这些负面词汇去夸大建筑的野心。
与此同时,我也赞同“共识”不应被人们忽略,当大家从纷繁复杂的观点中归纳共识,抑或是从上述两种主题中找寻关联时,得出的结论总是耐人寻味,所以我往往会对它们作出回应,有时帮忙出出主意(tweak)——我呼吁的“参与性自治(engaged autonomy)”或许有助于缓解(deflect)这些流行风潮造成的毁灭性影响,它是解读建筑、理解实践的不二法门。所以我们正处于对学院派和实践派的建筑思考都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由于我的双重身份故而能深切感受到这种变革,这是既振奋人心(exhilarating)又危机四伏的时刻——建筑正丧失与文化产业的相关性,逐步沦为纯粹的服务业。因此,是否保持前者的相关性,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行动。

约一年前,美国建筑杂志《Architect》刊登了一篇内德·克莱默(Ned Kramer)的评论(editorial),他是我熟识的莱斯大学校友,当时这瞬间引起我的关注,因为我不得不承认他在我印象中并非顶尖学生,克莱默声称自己“从不擅长建筑理论”,此后渐渐触类旁通。

Ned Kramer,《Architect》
他认为社会关联(social relevance),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和建筑性能(building performance)已经取代了“理论”在前沿实践者和学者们华而不实的修辞学(rhetoric)中的地位,我当然不能说他是错的,但值此全面变革的时刻,这种言论明显是在闪烁其词,回避讨论(theorize)建筑界正在发生的某些重要趋向。

在这个简短的演讲里,我想首先更深入地剖析关于“责任”的说辞与践行,其次再谈谈为何这种“责任”似乎总是不得不弃掷(shed )“理论”。其实在经济萧条之前,“责任”的说法在对于建筑术语界定的评论中已经初露端倪了,正如你们看到的这张2007年由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Lincoln Institute for Land Policy)赞助的圆桌会议的海报,是关于城市设计的论坛,只是到了2010年,经济滑坡带来的凋敝萧条(downturn)的颓势完全主导了所有人的思考。

《新闻周刊》(Newsweek)杂志通过一篇文章指出“建筑之死(death of architecture)”,将奢侈享乐主义(extravagance)的终结与更微妙的新兴美学的崛起进行对比,主流价值取向也随之变动——从“追求完成度”到“更高效的功能主义(functional)建筑”。那篇周刊文章中最吸引我眼球的就是引用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城市项目系主任Ricky Burdette的名言,他说:“随着学科之间的边界逐渐暧昧不明(blurring),你便开始意识到仅通过实体,建筑是无法解决当下问题的”。
“万物皆存在于城市文脉(context)之中”——这个关于“实体建筑”的论点在迈克尔·基莫尔曼(Michael Kimmelman)接替《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建筑评论人职位时再次横空出世,其实这个评论员职位我从13岁至今一直无比“觊觎(coveted)”,所以我说的话可能不会那么客观公正。但是基莫尔曼刻意避免写到单体建筑,而是通过集中笔墨描写住宅、项目和城市规划给文章重新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re- politicizing)。

Michael Kimmelman,《纽约时报》建筑评论人
正如他自己阐释的:“我做了20年艺术评论人,写了不少关于雕塑和艺术家的文章,当我谈论建筑时,我总理所当然地认为和审视雕塑的方法如出一辙”,但这也属于观察建筑的视角的“贫乏(impoverishment)”——我们要思考建筑的形体、寿命和使用者。这位建筑评论家在《纽约时报》的观点首先是建筑审美与雕塑异曲同工(identical),进一步说,同时探讨建筑的美学和本体是几乎不可能的。

最后一个案例颇为新颖,是Ron Witte和我(简称WW)在芝加哥美术馆(Chicago Art Institute)参加的小型展览项目“芝加哥主义(Chicagoisms)”,图中展示的这块展区名叫“乐观主义胜于规划(Optimism Trumps Planning)”,这个拥有奇特名号的单体建筑充满了整个街区,从几何学衍生出建筑内部的秩序和建筑与环境的关系。我们仅有150字篇幅来阐述项目,所以充分利用有限篇幅来谈“实体能够且应该成为‘发动器’(object can and should be a generator)”,这也是我讲座标题的灵感。

Optimism Trumps Planning展区,Chicagoisms,芝加哥美术馆
《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建筑评论家布莱尔·卡明(Blair Kamin)观展后点名批评了三个项目,其中就包括我们的作品,我们听到他批评(condemnation)道:“其它模型例如休斯顿的Ron Witte和Sarah Whiting做的‘I Object’傲慢地(arrogant)将建筑物化,极其缺乏(bereft)对城市环境的关怀和节能环保的关注”。所以布莱尔无比轻松地定了基调:我们对实体的关注意味着完全忽视(disregard)建筑环境,这只是浩如烟海的现代主义建筑中表达“物性(Objecthood)”的例子的冰山一角,我将建筑单体与雕塑、意象(iconicity)与明星建筑进行联想,注重实体似乎就意味着对社会环境、城市元素和公序良俗的不负责任(irresponsibility)。

“I Object”, Ron Witte & Sarah Whiting
另一方面,责任与道德义务(moral obligation)看起来和“实体”风马牛不相及,因为责任似乎是与关系、本质、文脉休戚相关的,但实体与责任之间的一线之隔几乎没有给实践者和评论家们留下多少可行空间(Running Room),一个广泛的共识正在缓缓地、不容置辩地浮出水面:“侧重建筑的物性和形式就是不负责任,是建筑圈的大忌(taboo)”。

这种“反对物性”的语境导致了奇怪的现状,即建筑师和学生们总试图“设计建筑而非设计建筑物(design architecture without designing a building)”,例如这张位于纽约曼哈顿的某匿名建筑学院的课程设计作业,暂且称为“116号街某学校”,课题是在皇后区的滨水(waterfront)场地上设计一座生产食物的复合养耕共生系统(aquaponics system),从图的深度可以看出这是最终答辩的成图,研究富含omega-3脂肪酸的食物的生产成了学生们推进设计的主要切入点。
至于建筑,大家都能看到,并没有多少工作量,更多的图幅是在详细讲述“养鱼”的故事而非任何建筑空间的设想。如今所有人都知道建筑是通识学科(generalist discipline),但如果连我们都不教学生如何设计建筑,谁会教他们呢?世界上许多科学家都知道养耕共生复合农场的诀窍,我们的职责是与他们合作而非试图成为他们,要通过设计与他们协作,诚然我们需要储备一定的基础知识便于与其它专业的专家沟通,但当务之急是要保持“设计”在行业中的核心地位。

曼哈顿116号街某建筑学院Studio学生作业
强调“设计”并不意味着建筑师要变成第三产业的服务提供者,我不得不指出这个前提,早在1947年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aszlo Moholy-Nagy,20世纪最杰出的前卫艺术家之一,曾任教于早期的包豪斯)就已宣称:“设计不是一个专业,而是一种整合和创造资源的态度”。当前的设计行为早已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被公众理解,但基本的观点不可动摇:设计是对于实体的形式与功能的一种表达模式,通过绘画、模型和建造表现出来,此处所谓“实体”可以象征任何尺度:小至服饰和家具,大到街区和城市。
简而言之,正如建筑历史学者约翰·赫斯科特(Keskett J.)曾诙谐地(facetiously)说过一个严肃的观点:设计就是去设计一个能创造新设计的设计(design is to design a design to produce a design),“设计”就是我们区别于其它领域的得天独厚的看家本领,但须知这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Keskett J.,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曾提出设计师有三层价值——设计师作为修饰者、区分者和驱动者
当然这并不是建筑文化圈第一次将目光聚焦在“非建筑”上,建筑师们极其谙熟地解读“非建筑”对建筑的影响,甚至成了他们的必备技能。Moma美术馆1964年举办了伯纳德·鲁多夫斯基(Bernard Rudovsky)的名为“没有建筑师的建筑(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的展览,同年他的同名书籍出版,其中记录了不少本土(vernacular)和公共(communal)建筑的优秀案例,所以说建筑不是由所谓“专家和大师”创造的,而是由拥有相同物质基础的一群人自发(spontaneous)持续的行为活动产生的。Rudovsky说展览和书籍都侧重本土风格的持续性(durability),然而讽刺的是,在展览40周年纪念日有评论批判他过度关注这些项目的美学要素,但并未对这些公共形式背后的(underlay)复杂社会经济现象给予同等重视和认可。因此,如果说60年代和如今的方法论间存在什么关键差异,那一定是由于其它复杂社会现象已完全主导审美取向,“实体”已被归入“缺乏社会关怀”的范畴。

《没有建筑师的建筑》,Bernard Rudovsky
同时我们也应铭记“物性”在我们学科漫长的体系中有它自身的历史沿革、支持者(champions)和反对派(opponents),艺术评论家和艺术史学者迈克尔·弗里德(Michael Fried)在1967年发表了一篇名噪一时的(explosive)评论极简主义(minimalism)的短篇论文《艺术与物性》(Art and Objecthood),他将“艺术作品的正统(formal)理解”与“宏观语境下对作品的解读”进行了深刻对比(pitted)。
论文里第二条重要的辩证性观点更值得深思,就是将艺术作品本身与观赏作品的主观经验联系起来,弗里德赞成将“实体”在它本身所在范围(spectrum)进行探讨,谴责了极简主义者用作品的观赏性和戏剧性(theatricality)凌驾于(overwhelm)作品本身的行为。如今弗里德的评论已获得超出他与旁人预期的影响力,其实我了解他的兴趣并不在于轻描淡写地谴责“戏剧性”,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研究“作品的观赏性”与“艺术作品的自治性”之间的矛盾(tension),正如他写道:“评论家们必须时刻牢记的公理(formulas)就是他所执著追寻的物性只不过是相对的(no more than relative)概念”。讽刺的是,他的论述源于(stemming)对艺术和物性的辩证对比(dialectic contrast),这种解读却掩盖(seal)了全文语境中“物性”看似自相矛盾(incompatible)的命运,所以这是对我们的重大警示:二元论(binaries)确实是个颇棘手的难题。

《艺术与物性》,迈克尔·弗里德,美国当代杰出艺术批评家,他的评论构成了晚期现代主义的核心文本,开启了批判美国极简主义艺术的大门
让我们回到今天对“实体”的讨论,如果说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在1968年将“实体”的危机与历史学的没落(eclipse)联系起来,那如今与之相关的就是“理论的黯然失色”。

《建筑理论与历史》,曼弗雷多·塔夫里,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批评家与历史学者,威尼斯建筑学派领导人物
十年前,罗伯特·索莫尔(Robert Somol)与我在Perspecta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多普勒效应”的笔记和现代主义的其它状态》(Notes Around the Doppler Effect and Other Moods of Modernism)的小短文:执迷于(stranglehold)照搬二元论以及辩证法——更明确地说是“运用辩证法简化某些理论关系”的趋势,正是我们在小论文中批判的重点(instigators)。我们既不期许单体建筑可以具备扭转社会的能量,也不可能盲目犬儒式地追随商业风潮,我们只是看腻了不少学生前赴后继地在设计中提出“评论”,而非用设计项目本身去回应“评论”。

《关于“多普勒效应”的笔记和现代主义的其它状态》,Perspecta
这种批判性项目的典型案例就是1991年Diller Scofidio 在沃克艺术中心(Walker Art Center)展览的“旅行箱研究(Tourisms Suitcase Study)”,它直观揭露了旅游业与其它社会层面的复杂关系。

Tourisms Suitcase Study,装置中每只旅行箱都是对美国50个州中某州的名胜古迹的调研,并通过图像与文字进行分析
但就在这个声名鹊起的装置问世十年后,也就是我们写小论文那年,学生们仍沉溺于盲目模仿(mimick)这个项目,既不研究也不分析,鲜有鞭辟入里的观察,全然只顾生搬硬套。这暴露了我们面临的现状:建筑不断妥协退让,濒临失败,甚至整个studio还以这种现状为荣,庆祝狂欢。

我们写的“多普勒效应”的小短文是基于当年在学科中发现的两个问题,请注意这是十年前的事,首先是二元论的束缚,它将本该深奥的讨论过度简化(caricature),第二点就是建筑被其它学科的逐渐取代(displacement),我们提出的方略是在坚持“跨学科交流(inter-disciplinarity)”的前提下重新强调“建筑”的重要性——建筑是大家都无比熟悉的,如今它已是通识学科了。但是我们要警惕,绝不能迷失在普适性中,不能将“通识(generalities)”误认作终极奥义。我们作为建筑师的天职是综合(synthetically)化用各种领域(landscape)的知识来接近“普适性”,只有设计才能整合所有资源。我提倡从“批判(critical)”向“投射(projective属于“后批评”理论范畴,指的建筑师主体意识在实践场中的投射)”的转变,所以我们应该优先(advanced)植入一个设计,这个设计不是仅有分析而已,而是要有“论点(propositions)”。

我的小论文的主旨被误读为对“后批评(post criticality)”的倡导,甚至有人说我主张“反批评(anti criticality)”,认为我反对理论。言归正传,让我们回到今天的现状——理论似乎已从我们的学科销声匿迹了,当然这不是我和Robert的错,我俩从未用过“后批评”、“后理论”等术语,所谓“反批评”的立场(stance)更是子虚乌有。我们唏嘘感喟(lamented)的只是这种“评论就像磨损的‘黑胶唱片’(scratched LP,指重复播放相同声调的黑胶唱片)”的现状,恐怕这个说法也是陈词滥调了,但事实上它就像黑胶唱片一样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相同论调(chord):批评应该作为一种产生新论点的理论工具,再回过头来淘汰旧论点。
这种说法是很合情合理,但它使我们陷入了皓首穷经地“生产(pose)”评论的无尽怪圈(loop)。对批判性项目的迷恋、对二元论的过分重视(overemphasis)和对建筑图像(icon)的谴责错综交织,扼杀(stymie)了不少建筑的新命题。但我想说,尽管这些阻碍力量很强大,但如今一种全新的建筑产品也正在萌芽,慢慢取代旧秩序。换言之,尽管理论家们正试图让建筑“高高在上”地摆脱其物性,但我仍乐观地看到日渐深入人心的建筑“实践”已经开始动摇这种偏见(bias),我们要时刻关注这种动向并巧妙利用它。

去年秋天我主持了由三位年轻明星建筑师组成的圆桌会议——比亚克·英格尔斯(Bjarke Ingels)、重松象平(Shohei Shigematsu,OMA合伙人,纽约办公室总监)和纳德·泰兰尼(Nader Tehrani,曾任MIT建筑与规划学院系主任,Cooper Union查宁建筑学院院长),通过深入交流我发现他们对从前建筑师未全面关注的独特领域都了然于胸、如数家珍——生态与经济责任、本土化转变、全球资源、社会责任和材料创新,所有这些在三位实践者看来是作为建筑师必须掌握和理解的。
我们往往囫囵吞枣地理解这三位建筑师,轻易地将他们归入“明星建筑师”之列,不假思索地给他们贴上标签,这绝没有恭维(compliment)的意思——OMA的作品随处可见,库哈斯就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明星建筑师之一。但我想强调的是,这三位建筑师都尽到了克莱默所说的三条责任——社会关联、可持续性和建筑性能。总之,他们的建筑与理论因为直截了当和易于理解而更为人所熟知,三位建筑师都是才华横溢的形体操控大师,通过分析环境、文脉、地域特色来呈现设计作品,都是出于对逻辑的思考,而非生搬硬套某条理论或幻想。所以令我震惊的是,这三位的作品显然是基于形式去积极回应文脉的,创造了建筑“实体”,但他们却以其它方式展示建筑,避而不谈建筑的“物性”。

左:Nader Tehrani,中:Shohei Shigematsu,右:Bjarke Ingels
德国文化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在20世纪20年代做柏林前线(Berlin Correspondent)记者时经常撰写文化评论,让人们以可视化方式阅读周遭世界,如果没有他对演讲说辞和侦探小说的深刻观察,我们将无法获得这样清晰易读且富有文化意蕴的精神食粮。这些创作经历为克拉考尔打开了一条更广阔的思路,正是通过这个方式,他让更多人意识到他们所处的环境正以无法想象的方式悄然影响着他们,这意味着建筑师和建筑写作者们放弃了为建筑学阐明方向,此处的建筑学概念是广义的——包括城市学、风景园林、建筑史等领域。

建筑的影响力必然离不开“物性”,“形式”也势必离不开功能(program)、组织、技术、经济、政治和文化。显而易见,在克莱默和基莫尔曼等一些建筑学者的论调的引导下,建筑的话语场正在切断建筑学这颗大树上我们赖以栖身(perched)的枝条和躯干,逐渐扑灭关于“形式”和“实体”的讨论,建筑的文化影响力更是无从谈起。

“I Object”, Ron Witte & Sarah Whiting,2014-2015
建筑学的“跨学科”潮流在过去25年间呈指数性扩张,然而我们追求“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新目标似乎一夜之间遏制了这种潮流。评判一座建筑成功与否的标准不能沦为“指标(metrics)”的计量,而要包含场地文脉、建筑自治等因素,重建对建筑实体与话语场的广泛尊重,这绝非缺乏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而是加深我们对建筑之外的潜在影响力的理解的必由之路。那么建筑不仅是“有求必应”地为世界服务的,它更是能让世界变得更好的,这才是我们的责任。因此,那些具有高度自治性的项目不仅能吻合我们学科的内在秩序,同时还能对时代背景下的物质环境、历史文脉、社会、政治、经济、形式、组织、功能条件进行回应。

“参与性自治”
现在我要从历史作品开始谈我们做过的项目,就是上次历史学者们邀请我来新西兰参加会议时展示过的作品。这是我在芝加哥的伊利诺伊理工学院(IIT)时做的,众所周知,密斯·凡·德·罗曾于1937年来到IIT执掌Armour技术学院,它包含校园边缘的两座砖石建筑,密斯的设计水平毋庸置疑。IIT校长Henry T. Heald非常有手腕,通过资本运作,从1937年到约1958年IIT逐渐成为占地100英亩的大校园,购置的资产都在受托人们(trustees)的名下,所以我们看不到单一的(consolidated)土地占有权,这就是如何在高密度环境下获取100英亩土地的秘诀。
所以提到IIT大家总是想到这张图,它就像一个完全自治的小世界,校园坐落在芝加哥南部,在当时被看作是北美最大的贫民窟(slum)。因此密斯的设计并不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现代主义中所有建筑都是遵循网格排布的,但校园的布局明显有所偏移(leaker),如果你翻阅这个项目的历史档案,就会发现设计过程中涉及了大量的两点透视的研究:空间总是在开阔场地中流动,引导你的视线在建筑间穿越,IIT校园就是在30年代后期到50年代被设计的。

IIT校园规划
另一个重要项目是迈克尔·里斯医院(Michael Reese Hospital),在密斯入职IIT五年后开工,它的城市层面由雷金纳德·伊萨克斯(Reginald Isaacs)操刀,建筑部分由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设计。

迈克尔·里斯医院,Michael Reese Hospital
迈克尔·里斯医院和IIT校园以及芝加哥的其它组织合称“Near South Side Plan”,它存在于1945至1960年之间,吸纳了教堂神职人员、社区领袖、《芝加哥卫报》(Chicago Defender,美国创办时间最久、影响力最大的黑人报刊,盛行于美国南部)的编辑和芝加哥商业圈的一些金融大鳄。

“Near South Side Plan”,1945-1960
从这张组织的照片中你能看到Henry T. Heald校长和密斯,Henry眼眶下的黑眼圈颇具辨识度,这就告诉我们一定要远离学院领导的职位,最近我也一直有黑眼圈——所以这是一条金科玉律。

他们的组织对芝加哥片区做的规划堪称全美首次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实践,对这个项目所做的调研分析也将成为我今后写作的素材和灵感。我还会讲我们事务所的四个项目——两个城市尺度的、兼顾自治性和文脉的项目,还有两个建筑项目。


全美首次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尝试的实践

首先是位于中国长沙的项目Many Worlds: Xingsha,我们要研究某街区内正在施工的12座高层建筑的立面,这是个很奇怪的任务。长沙就像中国很多其它新兴崛起的城市一样,建筑物像山峦般反复堆叠,在这种环境下置入任何新建筑都是无法辨识的(illegible),所有建筑都无法脱颖而出。

湖南省长沙市天际线
想要在长沙做一座建筑就像往水中添加水一样悄无声息,不留痕迹,我们主要研究了建筑立面,因为立面是建筑与城市发生关系的过渡元素,在垂直方向从基座(plinth)到屋顶都充满意趣。

既然这些高层都在施工,我们几乎没有余地去做新设计,现存的结构体系也无法改动——这12座建筑有居住、办公、商业等多种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再盖12座新房子。


我们用相似的手法通过光滑的(slipped)立面使这些建筑产生联系,只是轻微改动了立面的秩序,就使它们形成了充满共性的组团和群落,丝毫不影响建筑本身的功能性,它们依然是自治的。当然这个项目最后没有被实施,就像我们许多其它作品一样,大家都懂的。


鸟瞰渲染图
另一个城市项目尺度更大,它不仅展示了“参与性自治”的策略,产生了极大的自治性,同时还体现了“依附性(dependency)”,这是我们为位于台湾的海上(maritime)流行音乐中心竞赛做的设计。

CIRCULAR LOGIC: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The Ambient Whole
当初这个项目的功能瞬间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因为音乐是一个奇妙的概念:当你戴上耳机时,音乐是私人的;当你置身大型音乐会现场时,音乐是集体的。我们一贯的思路就是利用做竞赛的契机来调研平常感兴趣的议题,所以这次也不例外。




我们研究了建筑中圆形所触发的几何问题,因为在一个更大尺度的城市文脉中使用圆形似乎是一个很粗暴的举措,因为圆形本身似乎就是最粗暴的几何形体。是否存在一种制圆的方式,可以实实在在地融入一个更大的文脉之中。我认为这个项目位于海湾附近,本身属于人造土地,所以我们可以创造自己独特的城市片区,图中黄色的圆圈就是我们的设计。

总平面图

左:场地功能分析,右:场地景观分析
因此这个项目中所有建筑都是圆形的,通过带状景观与周边环境相连。我们很喜欢研究平面,尝试不同的方式让圆这个几何形成变成一个建筑制造器(Architectural generator),然后通过一条路径把它们联系起来,融入一个更大尺度的景观中,正如你在图中所看到的。

圆形建筑类型学研究

圆形体量与景观步道
我们对这些渲染图很不满意,这也是我们输掉竞赛的硬伤,后来想起这个项目又重新绘制了图纸,这时我们才领悟到原来“表达(representation)”也是设计的一部分。通过重新绘制,我们尝试把这些实体和城市文脉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因此,我们意识到,原图中渲染的黄色,是一种过于人工的方式,将这些物体从城市文脉中剥离开来。我并不认为研究圆形体量与文脉的关系是为了画出绚丽的图纸,它们是调研的重点,建筑材质如何通过颜色去表现当然也是其中的环节。


“差强人意”的渲染效果图


后期重新绘制总图

最后是两个建筑项目,首先是休斯顿的住宅,休斯顿如今是全美第四的巨型城市,仅次于我的故乡芝加哥。休斯顿是一个极为分散的城市,但有如其余的城市,其城市内部的密度也在渐渐地增加。我认为奥克兰也面临着一样的问题,正尝试着增加其城市中心的密度。大家都知道休斯顿是没有zoning区划的,所以任何东西都能见缝插针地建在空地上,当然这种说法有些夸张,因为具体到到小型区划时还是有规定限制的,但这座城市缺乏控制,你很难找到建筑与环境的明确关系,正因如此,建筑数量也随着城市扩张而不断攀升。

休斯顿城市密度分布图
这是马萨诸塞州的萨默维尔(Somerville),美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小城市之一,高密度的住宅布满地面,几乎没有私密的活动空间,邻里之间摩肩接踵,这也是高密度城市的必然现象,邻居之间缺乏交流与了解,所以我对庭院(courtyard)的类型(typology)进行研究,这也适用于休斯顿冬暖夏凉的宜人气候。

萨默维尔市坐落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米德尔塞克斯县,波士顿以北,为新英格兰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
庭院是一种形式感很强的操作,我们依然执著于“圆形”,从一个圆形的庭院出发,开放空间可以穿透建筑物的体量、墙壁、房间产生抽象的联系,就像你们做城市规划时让建筑物产生联系一样,从平面上可以看到起居室、餐厅、厨房,室外门廊(porch)也有入口能进入物品寄存室(mudroom)。





所以这座住宅有一个洞,但洞口变幻莫测,斗折蛇行,穿过楼层,表皮上却是在体量上切出简单的几何形,在同一个项目中创造出不同的关系。目前项目还在施工,拟定用砖材建造。

体量分析——洞口变化

施工过程照片
由于这些洞口的多种可能性和灵活性,我们可以在静态的轴线网格中创造瞬息万变的关系,依据使用者在住宅中所处位置的变化而产生千差万别的空间体验,所以这个项目通过建筑感知来探讨了主体与实体之间的关系。

平面轴线网格中产生的千变万化的视线关系

窗间的视线关系

视野的变化可以让人感受到空间的开阔,也是使房间之间产生联系的关键,所以“窗户”是项目中营造这些联系的重要工具。最终我们在建筑立面上共只使用了三种尺寸的窗,对窗户的研究已成为我们设计的重要环节,因为即便你做了再多的房间,终归要使它们在体量中流动串联,创造奇异的空间。砖墙的弧形表皮与圆形洞口的施工也是颇耗心血的,感谢施工人员,只是他们似乎对我们的“异形窗户”感到很头疼。


窗户的研究与建造


这个项目与我们在芝加哥做的展览项目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是对一个简单的体块进行操作,生成了洞口。

“I Object”模型,芝加哥美术馆
最后位于中国长沙的商业中心项目,正如这些字幕显示,设计过程中场地多次更改,原本是个位于有机茶园(tea orchards)的优美的场地,服务于商务出行和旅游的人群。设计初衷是开放的,希望与周边的美景发生视线联系,然而此后场地迁移到了很丑陋的环境,我们又做了内向性(internal)的建筑。我们面临的困境不只是场地,还有功能——原本功能是被严格限定的,必须包括客人留宿的空间和会议室,后来女业主说:“既然场地环境这么差,也不会有人愿意在这过夜的”,于是取消了住宿和旅馆的功能。

其实我们都对如何这个丑陋的场地一头雾水,但18个月来,业主从始至终都对项目保持着极大的热情。场地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空白,但空白也未必是坏事,让我们的思路回到几何、体块、方框,在建筑内部创造一个新文脉,所以我们引入了三个洞,沿着平面的布局改变窄缝的方向和形态,这些洞口可以容纳不同的使用者和不确定的事件与活动的发生。



这里有小空间、方形的更小空间、矩形的中等空间和更大空间,这些空间通过窄缝进行联结,这些形式的串联增强了空间的灵活性,有收有放,虚实相生。我意识到这个设计中的平面形式可以衍生出100种新的类型,每个平面图有100种使用方式,我们把这个想法告诉业主,说我们有100种方案。

100种平面变化类型的使用方式

洞口形体分析

长条形“窄缝”效果图

圆形庭院效果图
整个项目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孔洞、庭院和窄缝,如果施工过程中没有精确的控制和打磨,很容易和预期的建造效果相差甚远,所以我们花了不少时间研究构造细部,绘制了很多详图。尽管项目的全过程看似复杂,但只要把握规律,实际上是可以化繁为简的,很多问题会迎刃而解。

弧形细部构造详图

结语
就在昨天我们又收到了场地更改的消息,又换成了一个美丽的场地,设计当然也会继续随之变化。近期我在加州做讲座分享这个项目时收到学生的提问,问我们是用什么算法(algorithm)生成的设计,用了什么数学公式做出了平面图。
我从来毫不避讳地设计形体、推敲形式、研究功能来创造或推动新的“关系”,深化主体与客体的理论、社会理论和当代公共领域的理论,但这些都是通过“设计”而非“数学公式(mathematical formula)”实现的,此处的“设计”是指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具体的“设计”。如果说今天讲座能留给你们什么烙印的话,那就是要永远珍视建筑实体推动文化传统的价值,感谢大家。

讲座原址:
https://youtu.be/f2IendQBv7w
推荐文献
1. 《Notes around the Doppler Effect and Other Moods of Modernism》, Robert Somol and Sarah Whiting,Perspecta 33 (2002): 72–77.
2. Constructing a New Agenda: Architectural Theory 1993-2009, ed. Krista Sykes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2010), 190-203.
3. Sarah Whiting, “Means and Ends,” in The Building, ed. José Aragüez (Princeton: Princet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 Columbia Graduat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Planning and Preservation; London: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Zürich: Lars Müller Publishers, 2016), 392-396.
4. "Critical Reflections." ,Sarah Whiting,Assemblage, No. 41, 88–89. April 2000.
5. "Spot Check: A Conversation between Rem Koolhaas and Sarah Whiting." ,Rem Koolhaas, Sarah Whiting,Assemblage, No. 40, 36–55. December 1999.

知识星期,一周即焚

公众号后台回复“Sarah”,获取部分推荐文献电子版~知识星期每周不定时更新,一周即焚,获取知识请勤奋!

推荐人介绍


黎乐源
南京大学建筑学学士,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建筑学硕士,曾任职于OMA,SOM等事务所。
个人作品

1. Nature + (individual project, instructor:xdga)
项目通过对虚实关系(solid and void)的研究,探讨自然环境与建筑物的辩证关系

2. book cloud (individual project, instructor:ajay mathripragada)
项目通过对实体(objecthood)内在关系的思考,探索如何运动空间操作创作有趣的公共空间

3. Stair Game(合作者:Neha Sahai,instructor: Troy Schaum)
以质疑高层微型住宅的典型设计方法为出发点,探索raum plan创造公共性的意义,以此作为设计的出发点。

雷锋福利

欢迎添加“全球知识雷锋机器人”,邀请您加入哈佛知识雷锋粉丝群,由哈佛大牛作者坐镇,会热心答疑解惑、学习讨论,快来加入组织吧”(•̀ᴗ•́)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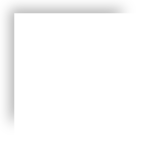
往期回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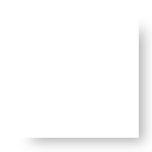
讲座专栏
北美讲座
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康奈尔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Paola Antonelli《人类终将灭绝,而设计师能给人类一个优雅结局?》
Germane Barnes:《要怎样做才能拯救一个城市?》
Herman Hertzberger:《他坚持设计为人,却被年轻一代忽略:赫曼·赫兹伯格讲他的结构主义》
哥伦比亚大学:
Cooper Union:
纽约州立大学:
伯克利大学:
莱斯大学:
迈阿密大学:
Neil Brenner:《星球城市指南 | 为什么外星人入侵地球总是失败》
宾夕法尼亚大学:
Dream The Combine:《梦境结合:虚虚实实的镜中景观》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麦吉尔大学:
德克萨斯A&M大学:
欧洲讲座
代尔夫特大学:
米兰理工大学:
佛罗伦萨大学:
伦敦大学UCL:
Adrian Forty:《失望:一种羞耻的建筑享受》
AA:
泰特美术馆:
英国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
英国皇家美术学院RA:
剑桥大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Sharon Zukin:《“原真性”城市场所的死与生》
谢菲尔德大学:
Richard Murphy:《“伪建筑师”斯卡帕》
阿尔托大学:
ETH:
门德里西奥建筑学院:
Valerio Olgiati:《“非参照”——你听说过却从未理解的Olgiati》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KTH:
马拉盖建筑学院:
Patrik Schumacher:《后扎哈时代的舒马赫宣言(上)》
Patrik Schumacher:《后扎哈时代的舒马赫宣言(下)》
巴黎建筑与遗产城:
国立里昂第三大学:
Jean-Philippe Pierron:《人类世时代的大都市化进程》
慕尼黑工业大学:
Ferdinand Ludwig《你一定没见过的活体建筑》
James Corner:《詹姆斯·科纳:从美墨边境到雄安要走多远?》
博洛尼亚大学:
Massimo Montanari《吃货的中世纪》
亚洲讲座
东京大学:
早稻田大学:
京都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清华大学:
MVRDV《MVRDV能把城市带到多远?》
中央美术学院:
澳洲讲座
墨尔本大学:
悉尼大学:
展览透视
“新知视野”专栏
珍贵文献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Sarah Whiting的WW Architecture网站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