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的幽灵:重新审视后现代



“我们与其将视线投向建筑的外部,看向城市和世界,不如到我们建筑噩梦的深处去寻找这些乌托邦原型式的出口。建筑本身隐藏着的地板门将会通往另一个可能的世界,而不是落入唯我论的陷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被永远囚困。”
“乌托邦的幽灵虽然在不同的案例中表现形式不一,但它已经从‘无处可在’变成了‘无处不在’。”
“历史本身远没有走到尽头,它会以类似反馈循环的形式归来,在这个稍有偏移的周期性中,我们将要去的地方从来不会和我们去过的地方完全一样。”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65篇讲座,
本次讲座于2009年2月2日在莱斯大学建筑学院举行,由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教授Reinhold Martin主讲,题为Utopia’s Ghost: Postmodernism Reconsidered,由华南理工大学张艺菡根据视频总结整理,由耶鲁建筑学院史论博士生翁佳校注并推荐。
记录者:张艺菡

华南理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本科三年级在读
推荐人:翁佳

清华07级,耶鲁建筑学院史论博士生,KPF建筑师,国际竞赛一等奖,现于耶鲁开设研讨课。
Reinhold Martin,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教授。集中研究空间的历史、权力和审美想象,以及技术基础设施对其产生的影响。他的研究方向还包括建筑学和认识论、全球化与城市以及传媒史。著有 The Organizational Complex: Architecture, Media, and CorporateSpace(2003)等书。

主讲人:
Reinhold Martin
文章全长18,170字,阅读完需要40分钟
(建议PC端观看)
推荐语
本篇讲座由耶鲁建筑学院史论博士生翁佳推荐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共产主义宣言
《乌托邦的幽灵》出版于2010年。夹在全球经济危机与世界末日预言之间的2010年似乎也并无大事可叙。早已破碎的建筑范式仍然支离,美国也还没有从金融海啸的废墟中重新醒来。那么,为什么要在2010年重新讨论后现代?难道三十余年间,文丘里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埃森曼的形式分析与建筑自主和库哈斯的恐慌批判法(Paranoid Critical Method)还没将后现代说尽?
后现代不仅仅是一个建筑与艺术形式的概念,也是资本环球化的产物——它首先是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詹克斯宣告现代建筑死亡的公案我们耳熟能详——在1972年7月15日,后现代主义随着普鲁伊特-伊戈住宅区的拆除将现代主义杀死。所谓乌托邦的幽灵,也即是现代主义精神的幽灵——带着千年主义天启使命的建筑理论,用乌托邦的空间等待第二次审判。现代主义的乌托邦想象孕育了对于笛卡尔理性、发展以及终极状态的信仰。而普遍认为的后现代则意味着这些信仰的消亡。
对于马丁来说,乌托邦的信仰却并没有消亡。它们只是从不存于世变得无处不在,如若不然,我们或许就不会在查尔斯·穆尔破碎的家中觉得无所适从,不会在斯特林的斯图加特国立美术馆中没有尽头的通道上若有所失,也不会在翁格斯的德国建筑博物馆层叠的幽闭空间中感到焦虑。与科林·罗的拼贴城市一样,对于马丁来说,翁格斯与库哈斯的柏林群岛不仅仅是一个空想项目,更是乌托邦的招魂阵。
然而马丁的写作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丰富早已纷繁的后现代建筑理论。在美国次贷危机的背景下,他借由乌托邦的幽灵,思考的是公共住宅的可能。詹克斯之后,现代主义与公共住宅被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我们无法区分建筑形式与政治主张的关联。或许对于Pruitt-Igoe来说,有问题的并不是建筑形式本身,而是支持这种建筑形式的政治的消亡。公共住宅在美国建筑与城市领域,已经成为了禁忌语;而马丁认为建筑应该学会与幽灵相处——公共住宅在此时此刻,不应该被规避,而应该继续讨论——毕竟“我们未曾现代过”又何谈后现代呢。

(明天中午12:00,雷锋将准时推送本文超详细+超清晰版本结构导图,敬请期待!)
讲座正文
Reinhold Martin

我首先想要提醒你们的是,为什么今天会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个词?它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处在历史化的进程中,所以,我们谈论这件事情的时机要么太早,要么已经太迟。
今天我要讲的内容是一个框架,可能会有些混乱和脱节,就像幽灵出现在了它们本不该出现的地方一样。
过去的几年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一个关于这个主题的研讨班。加拿大建筑中心(CCA, the Canadian Centre of Architecture)几乎是一个后现代主义建筑的档案馆,去年,我们和他们合作组织了一个展览,并在各地展出,包括蒙特利尔和纽约。在这个名为“乌托邦的幽灵”(Utopia’s Ghost)的展览*中,我们试图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中辨清乌托邦所没有意识到的事情。
*关于这个展览,后文有详细叙述。
这个展览是和我的学生们合作完成的,在和这些像你们一样的年轻人的谈话中,我学到了很多。你们没有在这些作品中长大,也没有被这样或那样的东西定型;在过去,你总是会站队,这就很容易产生摩擦。
在现代城市的语境中讨论这个问题会更加直接,在这里,我说的并不是全球城市或者图中这样的城市。

DLF-Plaza Tower, AHC, Gurgaon. (Image©AHC)
这是由上世纪七十年代毕业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哈费斯·康特拉克托(Hafeez Contractor)所设计的建筑。作为印度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他基本上设计建造了整个古尔冈城(Gurgaon)。在和我谈话时,他承认这些和七十年代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所做的建筑相差不大。所以,那个年代塑造的建筑师的作品今天仍然在各个地方被建造着。
在一些项目中,后现代城市被普遍认为是散布开来且令人不辨方向的地方。我们想要做的不只是弄清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中处理的问题是什么,更是要寻求一种处理问题时批判性的思考策略。
首先,我要为接下来比较密集的理论开篇道歉,在摘自《乌托邦的幽灵》(Utopia’s Ghost)这本书的理论介绍之后,我们会看一些建筑。
不可思之思
(Think the Unthinkable)

托马斯·J·沃森,是一名美国商人,在1914-1956年间出任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第1任首席执行官,带领IBM在1920-1950年代发展成国际知名的商业机构。(source: Wikipedia)
这是托马斯·J·沃森(Thomas J. Watson)。“Think”这个词在1915年就已经是这个公司的命令了,到了1940年,它成为了IBM的官方标语。这个词语的使用宣告着1970年代早期被称作非物质生产或后工业化生产的形成,服务经济崩塌,最终消亡。在1997年,对于人文精神合作的认同感姗姗来迟,换句话说,人类思想的合作本身就是促进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经济的高效引擎。这样的要求被IBM的竞争者苹果公司翻译为了“Think Different”(不同凡想)。

Think Different是广告公司TBWA\Chiat\Day纽约分支办公室于1997年起为苹果公司创作的广告口号,曾用于知名的电视广告、数个广告印刷品以及数个苹果公司产品的电视广告与广告印刷品中。苹果公司在2002年的Switch广告活动开始后停止使用这个口号。“Think Different”亦回应了IBM的长期口号“Think”。(source: Wikipedia)
事实上,这表明机器被人类所取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转折。这个状况的出现需要提到几个名字: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1973年乐观地将其描述为“正在到来的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在1980年代末,吉尔·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称之为“社会控制(the society of control)”;更近一些,哲学家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提出这是自革命与拿破仑之后的第二次回归;麦克·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则把它称作“帝国(Empire)”。
无论是作为一种症状、结果还是先驱,这些术语和理论仍然困扰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诸如让-弗郎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我想要回顾建筑学中的后现代主义。我并非要重新阐述其之后的命运,也不是在提倡一场后现代主义的复兴,而是重新思考后现代主义最初的一些假设。在这场讲座中提到的建筑并不是在描述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而是基于后现代的一些主要主题的历史事实的再理论化和再阐释(re-theoriza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这将是对于“什么是适当的建筑思想”的思考,从而在各种迅速出现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博士论文和基础性历史研究中理清各种论述和过程。我将不会重新定义什么是后现代建筑,在传统意义上,我们理所当然地将我们接下来会谈到的建筑划分出来。
今天讲座的背景中将会包含着关于历史时期划分、各学科知识的交叉和历史变迁问题——这些都是技术上的历史问题。这些历史问题在不断延伸和不断被挑战的参考系中变得更为复杂,从而越发显得迫在眉睫。这个参考系正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虽然在建筑学中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它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是后现代理论中最基础的假说之一了。我们所说的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或者说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是同时发生的,只是使用着不同的表述而已。
你们或许会想起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以及他在早期试图描绘其轮廓的一些尝试,其中就包含着对后现代建筑出现的前提和假定,它们所体现的特性常被看作文化后现代主义(cultural post-modernism)的范式和模型。
回看这些论述的概念和术语遗存意味着建筑不只是后现代艺术形式中的一个症状。但这并不是说所谓的后现代建筑并不存在,而是使其解释变得不那么使我们熟悉、不出于其本意地重新解读这些论述,或者说,故意曲解它的含义;当然,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复兴这种建筑,而是为了召唤出后现代主义认为早已被其杀死的幽灵。这个在历史过程中被反复争论的名词,我们仍然称之为“乌托邦”。
与诸如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对于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式分析不同,我所秉持的理论角度——生物政治学(biopolitical)——并不那么符合传统。我将建筑学的后现代主义理解为一种福柯式的话语*,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是风格。这种话语与其他话语相互影响、相互映射,集合成为异源矩阵(heterogeneous matrix),从而达到福柯所说的自我关照(the care of the self),或者说是作为知识与实践范畴的生命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life)。这是对于在人文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回归中发生的一切的一种总结方式,回归到生命作为问题本身的范畴来。
*Foucauldian Discourse Analysis,福柯式的话语分析,着重于通过语言和实践表达的社会中的权力关系。
在后现代主义中,这一点作为新人文主义(neo-humanism)*的形式贯穿始终,而建筑在各个层面均参与其中。今晚我想要涉及的层面包括随之产生的对于设想一种更美好生活的无力,也就是产生一种恰当的乌托邦思想的无力。如果说要给当代建筑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它们在本质上都无法想象一种乌托邦——它意味着一种与他人相处的更好、更公正的方式,而不仅仅是永久地保持现状和固有的暴力问题。这种可能性中包含的一些要素在各种不同的现代乌托邦思想中都有所描述,比如著名的反人文主义思潮(anti-humanist current)以及他们在如今新自由主义共识(neoliberal consensus)中所持的中立态度。
*新人文主义(neo-humanism)是一个整体性的哲学理论,旨在推动个人和集体的进步,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在其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它主张将人文主义(humanism)提升到普世主义的高度上,不再有任何“群体”(group)的意图。
*Anti-humanism,反人文主义。对于康德这样的自由主义人文主义者来说,普遍的理性将人从任何暴政中解放出来。但是,认为人文主义过于理想化的批判从19世纪就已经开始。尼采认为,人文主义只是有神论的一个世俗版本。马克思认为人权实际上是一个非人性化的产物,资本主义使人以自己的方式行事,从而产生经常性的冲突,人们需要权利来保护自己。他认为,真正的解放只能通过共产主义来实现,需要废除一切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弗洛伊德质疑人类理性自主的观点,认为人由潜意识驱动。海德格尔认为人文主义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它把人类赋予了一种普遍的本质,并把它凌驾于一切其他存在形式之上。在海德格尔看来,人本主义把意识作为哲学的范型,使之成为一种必须避免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从而拒绝了康德的自治理念,指出人是社会和历史的存在
在我的分析中,乌托邦的形象不同于影响塔夫里(Mafredo Tafuri)的意识形态幻象(ideological phantasm),而是一种话语建构,一种看起来被后现代主义的转变抛弃了的技术发明(technical invention)。因此,“乌托邦的幽灵”是我给这种建构在历史中的来世(historical afterlife)所起的名字,恰恰是在幽灵的这种半生半死的状态中,或者说没有人性(inhumanity)的状态中,我尝试用生命政治学的角度来理解它。

Vanna Venturi House, 1959, Robert Venturi
往日重现
(Presence of the Past)

Il Teatro del Mondo,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最引人注目的项目之一,它 1979年于威尼斯落成,是1980年威尼斯双年展上的装置之一。这座剧院建在一个驳船上的泻湖小港盆地里,然后被拖到威尼斯,并停泊在大运河上的圣马可广场前面。剧院可容纳多达400名观众。1981年,这个建筑被拆除。2004年,作为“热那亚欧洲文化之都”庆典的装置之一,剧院被重建。(source: Wikipedia)
我们从1980年的威尼斯开始。
意大利建筑师和评论家保罗·波尔托盖西(Paolo Portoghesi)出版了他关于后现代主义和建筑的书籍。“一个幽灵,后现代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A specter is roaming through Europe, the postmodern),这句话作为开篇首句出现在书中,书的副标题是“后工业社会的建筑”(the architecture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这本书在1982年出版了意大利语版本,次年翻译成英语出版。波尔托盖西给这句介绍性的话语加上了双引号,因为这实际上是他在一份法国报纸上发表的关于 “新街”(La Strada Novissima/the newest street)的巡回展览的文章标题。
*书的全名为 Postmodern :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Paolo Portoghesi

1980年,第一届威尼斯双年展开幕,策展人保罗·波尔托盖西将主题定为“过去的存在“(The Present of the Past)。其中的主要展品”主街“(La Strada Novissima)由二十个7×9.5米大小的建筑立面的人工布景组成,每个立面由一个建筑师设计。受邀参加的建筑师包括盖里、库哈斯、文丘里、汉斯·霍莱茵、波菲尔等。(Image ©domus)

La Strada Novissima在旧金山的巡回展览
the Fort Mason Art Center,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1982
(source:https://seek.rs/)
这个作品在后现代想象的产生过程中是一个重要记录。它是一个原尺寸、多建筑师参与的“街道”,其中充满了历史的引述。在1980年第一届威尼斯双年展中,保罗·波尔托盖西担任主策展人,“新街”作为双年展的主展品,在巴黎和旧金山进行了巡回展览。
当然,这篇刊登在法国报纸上的文章标题本身也是一句引用,或者说是一句改写,原句出自现代主义所产生的最重要的文稿中最重要的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共产主义宣言》的开篇。
作为1980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过去的存在”(the Presence of the Past)希望唤起大西洋两岸甚至日本的建筑师们对于历史的强烈兴趣和积极引用。

汉斯·霍莱茵(Hans Hollein)设计的立面。
(Source: Domus)
在1950年代早期,国际性的现代主义以诸如功能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占据了支配地位,将学院派(beaux-arts)和古典主义(classicism)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到了1980年代,就像曾经发生过的故事一样,现代主义被扔进了同一个垃圾桶里,它乌托邦的一面衰减为对于历史的好奇心,恍若一场浮士德式的梦靥。所以,在“过去的存在”中,建筑师们想要清理历史垃圾桶,试图清除过时的建筑语言和风格。他们时而认真时而随意,却总是反对现代主义者强制执行的各种禁令和教条。
无论是“新街”还是其他关于这种趋势的宣言,都成功地在建筑的范畴中将已成历史的过去恢复成为了完整的现实存在。许多声明虽然以“重回过去的建筑”(return to past architecture)的名义提出,但这些建筑并不是一堆复制品,而是为了直面由诸如功能主义的刻板教条给城市形态和市政表现(civic representation)带来的创伤。
1980年双年展中的历史主义并没有着重强调历史风格的简单复兴,而是给参观者们呈现了稍显刺目的假场景、假修复和假复兴(pseudo-events, pseudo-restoration and pseudo-revival),就像是一副拼凑画(pastiche)。

Venturi,Rauch & Scott Brown设计的立面。
(Source: Domus)
在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于1991年出版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重要著作中,他将包括建筑和文学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拼凑”(pastiche)称为“一场使用死去的语言的演讲(a speech in a dead language)”。这场“演讲”剥离了现代主义拙劣模仿的生命力,讽刺的是,这样的批判精神在诸如达达主义(Dada)的运动中流传了下来。
但是,在死去的语言中仍然存在着幽灵,特别是当这场死亡发生在威尼斯的时候。一个幽灵确实在欧洲出没。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句著名的话同时也给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1994*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幽灵》(Specters of Marx)提供了潜台词。在这本书中,德里达召唤出了长期萦绕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中的德国唯心主义(German idealism)的精神,同时,他在1989年后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中召唤出了其认为已被清除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幽灵。本质上来说,浏览这一段历史就像是在回溯左派(the Left)的经历。
*《马克思主义的幽灵》一书法文原版出版于1993年,英语译本出版于1994年。


左:《马克思主义的幽灵》 ;右:雅克·德里达
德里达通过“幽灵”的形象,对尤其是在欧洲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作出解释。他将这种“闹鬼”的逻辑(logic of haunting)称作幽灵缠绕论(Hauntology)*,与传统的本体论(Ontology)做出区分。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一点,德里达开始对《哈姆雷特》进行解读,但他的重点并未放在人物性格上,而是关注舞台道具。
*幽灵缠绕论(Hauntology),语出德里达《马克思主义的幽灵》(Specters of Marx)。它指的是时间、历史和本体论的一种分离,其中明显的存在(presence of being)被一种推迟的非起源(non-origin)所取代,被“既不存在也不缺席、非生非死的鬼魂形象”所表现。
剧中,哈姆雷特父亲的亡灵在一套铠甲里出现,或者说看起来在舞台上出现了,幽灵的脸被面甲(visor)所遮挡,德里达称之为“面甲效应”(visor effect)——幽灵在面甲(一个舞台道具)的遮蔽下间接出现并且望向观众。就像我们听说的一样,幽灵通常不会直接出现,你不会直接看到它,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看到”。
这种舞台布景方式将双年展中“新街”的一些特质带到了我们眼前,这些立面实际上是在意大利电影梦工场Cinecittà中制作的。今晚我想要做的就是在建筑的后现代主义的面甲之下,让乌托邦的幽灵显现。

Cinecittà鸟瞰图 (source:Wikipedia)

Cinecittà电视剧《罗马》(Rome)的布景(source:Wikipedia)
Cinecittà Studio位于罗马,是意大利的一家大型电影制片厂,建立于法西斯年代的1937年。在1980年,Cinecittà的舞台布景设计师“协助”参加“新街”展览的建筑师们完成立面建造。库哈斯(Rem Koolhaas)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作为建筑师所建造的立面和布景师设计的立面完全不同,他们甚至没有用Cinecittà的技师,但是Cinecittà在这届双年展中扮演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色,在这样一个早期的年代里就宣告着建筑是多么的虚幻(unsubstantial)。[1] 而里昂·克里尔(Leon Krier)则直接拒绝了布景师,坚持使用真实材料建造这个平面的大厦。

“新街”中库哈斯的提案。(Source: Domus)
现代建筑之“死”
(the Death of Modern Architecture)
在杀死种种形式的现代主义的同时,后现代主义建筑将历史的尾声纳入其中,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也终于可以销声匿迹。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ks)认为自己已有资格为此画上句号,塔夫里(Manfredo Tafuri)所说的先锋派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the avant-garde)也至此终结。詹克斯甚至给(现代主义)的终结标示出了一个确切的时间——1972年7月15日下午3时32分。这是在世贸中心被摧毁的三十年前,山崎实(Minoru Yamasaki)的另一个作品被炸毁,这个事件标示着一整个历史事件的落幕。讽刺的是,在普鲁伊特-伊戈住宅区(Pruitt-Igoe Apartment)被摧毁的同时,山崎实正在完成他的世贸中心设计方案。

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普鲁伊特-伊戈住宅区(Pruitt-Igoe Apartment)由美籍日裔建筑师山崎实(Minoru Yamasaki)设计,建成于1956年,在建成后即开始衰落。到1960年,这个住宅区以贫穷、犯罪和种族隔离而臭名昭著。1971年十二月,联邦和州政府做出了摧毁该住宅区的决定。1972年7月15日下午3时32分,第一阶段的拆除完成。(source: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左:2001年3月的世贸中心;右: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source:Wikipedia)
山崎实同时是纽约世贸中心的设计者。在1972年后大约三十年(2001)的9·11事件中,被恐怖分子摧毁。
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在这里讲的是关于生与死的问题。在詹克斯(Charles Jenks)1977年出版的著作《后现代建筑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中,他把普鲁伊特-伊戈住宅区的拆除作为了“现代主义的死亡”的标志。你们对这样的叙述和这些图片都非常的熟悉,它们在各个领域里传播。这些被记录在詹克斯和波尔托盖西书中的建筑事件在诸如1980年威尼斯双年展的地方被展示,随后,批评家们将它们引述为与艺术的发展同时发生的事件。
我今天想关注的一种叙述所宣称的是:随着像普鲁伊特-伊戈住宅区一样的项目的拆除,现代主义中对于公共住宅的乌托邦幻想和住宅中的暴力冲突也一并被永久消除了。这是新人文主义者(neo-humanist)的一种元叙事(meta-narrative)*,它永久地存在于诸如Katrina飓风侵袭后的新奥尔良的立法委任权(legislative mandate)中*。换句话说,我所关注的就是这些住宅项目。
*在Hurricane Katrina后,新奥尔良的大型公共住宅项目,曾经或被喜爱或被憎恶,都被夷为平地,被混合收入的社区所取代。
*元叙事(meta-narration),通常被叫做“大叙事”,就是无所不包的叙述,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这一术语是由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在1979年首次提出的。根据利奥塔的解释,元叙事或大叙事,确切地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文艺理论批评中,经常使用这个词语。史学借用这个词语,是受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一术语在批判理论,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理论中,指的是完整解释,即对历史的意义、经历和知识的叙述。它通过预期实现,对一个主导思想赋予社会合法性。

飓风Katrina过去十年后,新奥尔良的租金和收入变化。绿色部分租金和家庭收入均上涨,黄色部分租金上涨但收入降低。(Image©NYT)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问的是,即使在受到官方最大程度支持的示威运动中,是否能够看到乌托邦的幽灵在其中徘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此时此刻,我们越来越不可能从被称作全球化的“镜宫(Hall of Mirrors)”中脱离出来。跨国公司、霸权国家(empire-building nations)和非政府慈善组织都在他们的实践中推动着全球化的进程。学会如何与乌托邦相处成为了我们最为紧迫的任务,用德里达的话就是“如何与乌托邦的幽灵相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确切了解并重新思考在新的社会运动口号中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总是提醒我们:在后现代主义最为普遍的特质中,都未能想象出一种激进历史变革的可能性,更不要说去实现它。从勒杜(Claude-Nicolas Ledoux)到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大多数早期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建筑的乌托邦提案都需要描绘出一幅理想世界的图景,一个被投射到未来的项目。奇怪的是,使这样的图景成为现实同时标志着在一种持续进行的历史辩证法和过程中历史天启式的终结。当乌托邦真正实现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抓住它的幽灵。
因此,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都和历史的尾声共享着一种密切的关系,虽然殊途,但却同归。现代主义通过的是经常带有毁灭性的、以救世主自居的、带有赎罪色彩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其他;而后现代主义则是通过这些叙述的衰竭(exhaustion of narratives),将其打破为数不清的小故事。
来看一下这张表。

Evolutionary Tree of Architecture, Charles Jenks, 2000
这是某种“假的”历史时间线,詹克斯(Charles Jenks)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在重新制作这个表格——无论以什么形式,他出版的每一本书里都有这么一张图。上方这张出自《后现代建筑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
现代主义先锋派中“从这里到那里”的目的论叙述(teleological narratives),黑格尔派所说“时代精神”(Hegelian Zeitgeist),都被这样一种没有特殊指向性的建筑历史图表所取代了。詹克斯称之为建筑风格进化树(evolutionary tree)无意义的、生态学意义上的分支。你们可能看不清图上的字,但是其中包含着你们能想到的所有建筑风格。进化树图表是通过一系列基于图像的反馈环路(feedback loops)组织起来的,从而产生了一种被詹克斯称为“激进折衷主义(radical eclecticism)”的熵(entropy)。在这种多元论的平衡状态中,所有的东西都互不相同,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样的。对此,我有不一样的想法。
直到今天,詹克斯仍然坚持认为,如果把传媒生态学(media ecology)比作一碗混沌的浓汤,会有可识别的规律以次生形成(secondary formation)或集合的形式出现。但这些都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它们从这碗汤中出现,最终也只会消泯于其中,被另一种毫无意义的集合所取代。它们将永远处于一种动态的、漩涡状的停滞状态中,反反复复。
没有终点的路
(Roads to Nowhere)
所以,如何在各种决定性的历史变革中找寻到乌托邦精神,而不是作为一个个毫不相关的小故事存在于各种风格之中?为了探索这个问题从而召唤出乌托邦的幽灵,我想更近地看一看后现代主义本身,在其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现代主义乌托邦的踪迹。这至少可以分为五种建筑特征,这也正是我们在“乌托邦的幽灵”这一展览* 中所做的,分出了五种类型的乌托邦。
*Utopia's Ghost: Postmodernism Reconsidered是由Reinhold Martin策展,在加拿大建筑中心(CCA)于2008年举办的展览,分为Babble/Babel, Islands, Roads to Nowhere, (In)human Scale, Worlds within Worlds五个部分。下图是展览中的部分展品。

Portland Public Office Building, Portland, Oregon: Elevation,Michael Graves,1979,CCA Collection
(©Estate Of Michael Graves)

Derby Civic Center Entrance, James Frazer Stirling, 1970。在“乌托邦的幽灵”展览中,它被放在 Roads to Nowhere 的部分。
我想从展览中“没有终点的道路(Roads to Nowhere)”这个部分开始。这是斯特林(James Frazer Stirling)的德比市政中心(Derby Civic Center)项目。
我一直提到的是一种“哪都不去”的感觉,或者说一种被耗尽的活力。我尽可能的从文字形式的方向去追溯源头。在CIAM那里,他们简单地把它称为流线(circulation)。在这里,我想提醒你们关注柯布西耶提出的建筑漫步(promenade)及这一类型建筑的扮演的重要角色。

Villa Savoye: Section. Le Corbusier, 1928
比如说,在萨伏伊别墅(Villa Savoye)中,穿过建筑的通道并不出于从下至上的纯粹功能主义设计,而是曲折上升的具有电影效果的斜坡,它抓住的正是一个我一直在回避的历史进步。这条通道在别墅中穿梭上行,经过各个功能区域,最终充满戏剧性地抵达屋顶。
这是别墅的二层,在这里,使用者得以欣赏柯布西耶特意呈现出来的田园生活的框景。

Villa Savoye:Intermediate Level. Le Corbusier, 1928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个斜坡简单地总结了柯布西耶的一种目的论,一个“从这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过程。这种时空向量(space-time vector)的形式不可阻挡地指引柯布西耶在同时期绘制了一个机械化且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城市总平面。
现在,我希望你们将这种带有目的性的线性流线系统——或者说经典的柯布西耶建筑漫步——和斯特林1983年建成的斯图加特美术馆进行一个比较。这是加拿大建筑中心收藏的斯特林的一张小草图。

斯图加特国立美术馆(Staatsgalerie)平面草图。James Frazer Stirling,1977,CCA Collection.(©CCA)

斯图加特国立美术馆实景(source:Architravel.com)
作为后现代主义重要里程碑的建筑,斯图加特国立美术馆是为了推动这座后工业城市的旅游业发展而建造的,可以算作是盖里(Frank Gehry)在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先驱。
当时的斯图加特仍属于西德,斯特林事务所赢得的这个美术馆竞赛项目必须含有一条“民主路径(democratic path)”,以满足其地缘政治需求。在上图中你所看到的就是这条“民主路径”的入口。这样的“民主路径”,或者叫做“公共通道(public passage)”在西德的很多市政建筑中都被要求建造。在冷战逐渐缓和的日子里,这些路径并不需要将行人引到某个特定的地方,而是把他们引向一种模糊的、民主的关于西德的意象中去。所以说,斯特林体系中容纳着这些路径的存在性、可使用性和可达性,宣告着西德与东德的公共建筑在被描述时截然不同。这些场所中暗含着当权者们的言外之意。

斯图加特国立美术馆(Staatsgalerie)平面,James Frazer Stirling,1977
跟随着斯特林建筑的这些路径,我们将会去向何方?曲折地穿过几个层次(layers)之后,在整个行进过程中并没有高潮部分,而是一个没有尽头的通道,只是从这头到那头,没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地。经过前院后,另一条轴线建立起来,绕过一片形而上学的(metaphysical)的中心空地(见下图),在建筑的后面“流淌”而出,最终以其切线在靠近建筑前部的地方回归到博物馆中来。

斯图加特国立美术馆的中心空地(source: staatgalarie.de)

美术馆真正的入口(source: heinze.de)
博物馆的入口序列具有一种非正式性(informality),这只是斯特林在这座美术馆中布置的许多有趣并置(juxtaposition)中的一个。美术馆中有许多按照十九世纪方式排布的不连续房间,这与二十世纪许多美术馆内部布置方式并不相同。我们可以看到,美术馆流线的布置显得随意,而房间却以一种整饬的方式被组织起来。

Staatgalerie内部(source: The Architectural Review)
斯特林在斯图加特设计的这栋建筑中出现的这种模糊的、反高潮的(anti-climax)的漫步形式可以和1975年的西德另一城市科隆的博物馆做一个比较,虽然科隆的博物馆竞赛设计方案最终并未建成。这是奥斯瓦尔德·马蒂亚斯·翁格斯(Oswald Mathias Ungers)在竞赛中的方案,斯特林同样参与了这个项目的竞标。
翁格斯的方案选址于河边,临近大教堂,侧面则挨着火车站。你可以在图中看到这几个元素。为了将这些各不相干的元素协调在一起,翁格斯插入了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基础构造矩阵(matrix of infrastructure)。在平面中你可以看到,博物馆中的各个部分都像从地下的方格网中出现的一样,入口流线也被嵌入到格网中,以线性轴线的形式从环绕大教堂的广场开始,延伸至更高一层的平台,最终下降到河边的码头上。

O.M. Ungers, Museum and Commercial Center, Cologne, Germany, 1975(source:pinterest)
这条轴线从公共广场到达公共滨水空间,是“民主路径(democratic path)”的又一实例,却又与之完全不同。三个建筑场景被相继放置在轴线上,每一个场景都和前一个一样具有不确定性。这是三张场景的透视图。

图A

图B

图C
Perspective. O.M. Ungers, Museum and Commercial Center, Cologne, Germany, 1975
在翁格斯的这三张透视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超现实主义中以马格里特(René Magritte)为代表的形而上绘画(metaphysical painting)的美学影响。图A展现了一个空旷的前院,其中有着人体尺度模型和球状树;图B表现的是一个从空旷街道上行的斜坡,两边是图解式的建筑立面(diagrammatic façade),有着作为博物馆格网状前厅(antechambers)的方形的柱廊;图C则是被称作“雕塑花园”(sculpture garden)的场景,立方体树按照格网排布,大比例的雕塑被放置在两边的壁龛里。
我想要提醒你们注意平面中的一个小细节,它在这几张透视图中被放大了:中心轴线被图中的小飞艇标记出来,延伸出一条空间的通道;在第三张图中,它收缩成一条线,漂浮的格网中,中心的一排树把它显现了出来 。
图A中,带黑帽的男人形象从旁进入,在图B中走上了中轴线上的斜坡,在图C中却被毫不退让的树格网挤到了旁边,落入一个卑下的境地。


左:The Son of Man. René Magritte,1964
右:René Magritte
我对此进行强调的原因是:翁格斯本可以种四排树而不是三排树,这样就可以使中心通道一以贯之。这些格网当然带有着强烈的修辞色彩(rhetorical),但翁格斯却不这么认为,并且通过小飞艇在内的各种画面细节强调了这个观点。翁格斯虽然特意强调方案中的“场所营造”(place making),最终却以带黑礼帽男人的形象(这个形象也代表着建筑师本人)向我们呈现出一个神秘的、寓言式的历史主体(subject of history)——在这个建筑幻梦中,人的中心性(centrality)被一种过时的、关于自然与文化的系统化辩证法所取代了,树、格网和小飞艇均参与其中。
在这三张图的对比中,无论翁格斯方案中的对称形式参考了怎样的经典先例,人都从一开始的中心角色降级为了一个配角。在这些格网中,翁格斯拓展了以密斯、格罗皮乌斯、希尔伯海姆为代表的功能主义者(functionalist)的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t)趋势,而不是中断了它。翁格斯并没有采用一种更人性化、更合乎尺度的、等级明晰的古典主义来反对现代主义中各种不确定的几何图形以及其抽象性,而是与之一道将这种反人性(inhuman)的逻辑延伸至对古典主义本身的长期坚持中去了——这体现在博物馆的基础构造格网里出现的伪古典的反轴线(pseudo classical anti-axis)中。所以,这仍然是一个机器,无论它看上去多么人性化。
道路通往何方?
(Roads to Where)
为了防止你们觉得我所讲的东西漫无边际,现在我想让大家来看看这座房子,它的设计者及其作品中所体现的人性已经被广泛地认可了。他就是查尔斯·穆尔(Charles Moore)。

Moore-Rogger-Hofflander Condominium, Los Angeles. Charles Moore. 1978
穆尔自认为是一个“场所营造者(maker of place)”,以此来反对现代主义的“非场所(non-place)”。他所创造的是一个目的地、一个避难所,甚至是一个家,就像是一剂治疗现代性崛起中超验的、无家可归之感的解药。
在这里我想要介绍的房子是穆尔1978年在洛杉矶为他自己和两个朋友设计的独立公寓。用现在的话来说,它坚定地倒向了作为后现代主义特征的一种折衷风格:一种由当地特色(vernacular)、地域特色(regional)和大量现代主义引用结合而成的、古怪的折衷主义拼凑(eclectic pastiche)。
但是,这三个单元在内部通过一系列不同寻常的楼梯自发地相互交织、相互分隔。空间的碎片沿着楼梯两边在左右和上下方向上排布。这在平面上就可以看出来。

Moore-Rogger-Hofflander Condominium. 平面
(source:讲座视频截图)

左:二层内景与楼梯;右:二层楼梯
Moore-Rogger-Hofflander Condominium. From Charles W. Moore, Charles Moore Buildings and Projects 1949-1986,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86). Courtesy Tim Street-Porter
再一次,我们会问:这些楼梯都通往哪里呢?它们并不特别的通往什么地方,却有着惊人的精确性(precision)。不要低估了查尔斯·穆尔。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穆尔对他所说的“渗漏空间”(leaky space)的偏爱。这样的内部空间通过非系统的方法被打破,让光线经由规整的缝隙或对角线的视图照射进来,并且增加功能上的联系。穆尔的这些房子虽然尺度比较小,但它们都被称作是皮拉内西式的(Piranesian)*。第一眼看上去,穆尔房子中惯用的古色古香的装饰和甲壳动物摆设适于家庭生活,但皮拉内西式的庄严仍保留其中。这一点并不是通过其破碎的空间表现出来的,而是蕴藏在各式各样片段化的、四处穿越从而令人感到无力的走廊之中——它们并不能相互联系成为一条认知透明的(cognitively transparent)路径。这就像皮拉内西关于监狱的蚀刻画中不知通往何方的路和桥一样。
*Piranesian,源于意大利艺术家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通常指一种奇异的、阴沉的新古典主义风格。

乔瓦尼·皮拉内西,《桥》、《想象的监狱》系列,1745
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 Tavola VII (The Bridge), from The Imaginary Prisons series, 1745
在二十世纪,皮拉内西的作品关于人类本性的噩梦和无限的神秘性对博尔赫斯、卡夫卡等作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为理论家的皮拉内西在他的时代中亟需摆脱传统艺术语言中单一风格的奴役,从而提高创造力。过去的风格要素转变成了他的想象力,并成为了现实的形式。在《想象的监狱》(The Imaginary Prisons / Carceri d’invenzione)这一系列作品中,他绘制了一些想象中的地牢。画面被巨大的拱门、桥梁、通道等构筑物所统治,这些对于他来说都是来自古代世界的遗物。这个监狱的迷宫并不能用理性去理解,也不能绘制出地图,它甚至不是精神上的。为了避免发疯,监狱里的“居民”必须四处摸索以重塑现实。而作为一个精神实验,外部观察者的焦点会脱离连续性,却又不得不去执行这种连续性。[3]

客厅内景
Moore-Rogger-Hofflander Condominium. From Kevin P. Keim, An Architectural Life: Memoirs & Memories of Charles W. Moore, (Bulfinch Press Book/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Unites States of America). Courtesy Tim Street-Porter
与翁格斯的博物馆中的一场公民戏剧(civic drama)不同,房子里的流线没有一定要通往哪里的原因。同样的,我们可以确信穆尔在设计这栋房子的时候就非常了解有关建筑漫步的历史,对柯布西耶在诸如萨伏伊别墅的住宅建筑中重复使用的手段也十分熟悉。与我们刚才在斯特林和翁格斯的建筑中遇到的情况不同,穆尔不同寻常的楼梯和通道在这不确定的建筑叙述中并不与离散的事件相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是一个接一个的“纯粹事件”(pure events),不是建筑风格的拼凑画,而是在表现历史进程的概念本身,它们看起来像是要到某个地方去。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围合的体量所指向的各种建筑历史,穆尔的家庭住宅中的小插曲和事件才得以在时间与空间之外发生。
所以,在建筑学的范畴里,这些例子中对于历史元素糟糕的复制并及不上他们被组合起来的方式。特别是在穆尔的例子中,他企图制造出随意并置(casual juxtaposition)的效果,换句话说,就是拼凑(pastiche)本身。在斯特林、翁格斯和穆尔的三个案例中,他们都是通过“流线”(circulation)这一建筑元素来实现这样的效果的。本应伴随着路径的叙述却未曾诉说建筑与其自身历史的关系,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这似乎确实意味着这些建筑将现代主义中乌托邦式的宏大叙事(master narrative)转向了许多不确定的、片段的、无明确意义的微叙事(micro narrative),它们即使相加起来也同样毫无意义。
但是,如果事情其实恰好相反呢?如果在与后现代主义建筑领导者的声明、各个方面的辩论的直接对立中,存在着关于这种无法相加(failure to add-up)的某种特别的、无所依凭(helplessly)的乌托邦呢?
我所说的并不是一种调和的多元主义(conciliatory pluralism)——各个相互竞争的微叙述和各个相互竞争的风格被给予了同等的时间和空间,就像摆在超市货架上一样——这是詹克斯(Charles Jenks)的模型。我所说的是一种拒绝呈现出项目形式(the form of a project)的项目,它是一种间接出现的、无意中产生的项目,是被抑制的东西(the repressed)几乎无法被辨识的归来。
如果我们真正并完全进入了后现代主义,我们在面对内置的建筑叙述无法叠加的问题时,就不会感到一丝刺痛或挫折。但是我们会产生这种挫败感,或者说我认为我们有这样的感觉,我希望你们也有。为什么呢?因为在呈现不同形式的挫败和疲惫的时候,它们的对立面、永远被推迟着的到达的可能性、一段间隔、不可逆转甚至革命性的历史变革也无法制止地产生了。

拱廊街。(Image© Charles Lansiaux/DHAAP, Courtesy The Image Works)
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令人挫败的通道可以看作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十九世纪探索的欧洲拱廊街的鬼魂,在这些拱廊中可能还存在着本雅明所说的“微弱的弥赛亚力量”(a weak messianic power)。它们宣告的变革和我们可能想象的并不一样,我们不再能在其中辨认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历史。

奥斯曼时期的巴黎,老佛爷(Galeries Lafayette)内景。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文学家。1927年,本雅明开始为期十三年的“拱廊街计划”(Arcades Project),直至辞世,研究并没有完成。在19世纪的巴黎,拱廊街是奢侈品的聚集处,是现代商业步行街的前身。在以资本主义商业利益为目的的拱廊街中,出现了“闲逛者”,本雅明认为他们是第一批现代人。

《拱廊街计划》(Arcades Project)英译本目录
在这里,请允许我冒昧地下一个结论:如果我们要给世界历史变革幽灵般的表现一个名字,它被驱使也驱使着可能不再意味着“人”的人文主义,那么这个名字就是建筑(architecture),或者说建筑学(Architecture)。
如果说这些令人挫败的通道真的通向某个地方的话,那将是回到舞台布景中去,回到面甲效应(visor effect)里去。这就是说,它们回头指向了建筑的内在,也仅仅指向了建筑而已,或者就像塔夫里忧伤的描述那样,是“一座语言学游戏的皮拉内西监狱,像这样的不可救赎的、自主的(autonomous)的建筑从那时起就已被定罪”。这就是当原路折返回到建筑之时所发生的事情。


“房中房”
(House Within House)
看一下这个例子。这是翁格斯的另一个博物馆项目,这一次,这是一个关于建筑本身的博物馆,位于德国法兰克福,1984年开始开放。在这里,翁格斯把他小小的类型形式(type form)放置在了一个已经存在的十九世纪别墅中。
与他在科隆的博物馆设计中对格网矩阵的强调不同,翁格斯在这里放置了比喻性的(figural)亭子,一个房子套房子的“瀑布”,建筑中的建筑。

O. M. Ungers: 德国建筑博物馆(设计方案),法兰克福,
Oswald Mathias Ungers: Deutsches Architektur Museum, Frankfurt, 1983
下图是最终建成方案的剖切图。在我看来,原版的设计方案更加的令人兴奋。

O. M. Ungers: 德国建筑博物馆(建成方案),法兰克福,
Oswald Mathias Ungers: Deutsches Architektur Museum, Frankfurt, 1983
到1980年代中期,由文丘里(Robert Venturi)1964年在母亲住宅中所提出的住宅形式原型已经成为了类似建筑的一种“暗号”,用穆尔的话来说,像是瀑布(cascade)或深渊(abyss)。
这是穆尔在1962年设计的自宅。在图中可以看到房子中的房子,一个套一个。

Charles Moore自宅,加利福尼亚,美国,1962.
Moore House, Orinda, California, 1962. Image Courtesy of Morley Baer


Moore House, Orinda, California, 1962
所以说,翁格斯在一个建筑博物馆里把房子的形式作为展品是完全合适的;他甚至在楼下的展览中使用了脚手架。

内景。O. M. Ungers: 德国建筑博物馆,法兰克福,1983(source:DAM)
翁格斯在之前设计的实际建筑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它的中心是住房原型本身和它多次重复的幽灵。它可能和文丘里1976年在费城为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做的博物馆有着遥远的联系。

Robert Venturi:Franklin Court,Philadelphia,1976
(image source:worldarchitecturemap.org)
在严格意义上来说,翁格斯的博物馆确是被幽灵缠绕着的。
首先,它在传统意义上被幽灵缠绕着。这或许可以归因于罗西(Aldo Rossi)1965年在意大利赛格拉特(Segrate)做的纪念碑。在这个方案中,罗西以挤出抽象的山墙的形式彻底地运用了三角形的原型。

Aldo Rossi:Redevelopment of the square before the town hall and monumental fountain, Segrate (Italy), 1965
和所有的博物馆一样,翁格斯的博物馆有一种纪念性,就像大家认为罗西的作品并不专注于建筑本身,而是其记忆。
但是,翁格斯的建筑博物馆还在一个更为复杂的意义上被鬼魂缠绕着。在翁格斯为原版方案绘制的透视图中,它被它所拒绝的城市所缠绕,甚至将自己归还于城市。正如在其自我参照的空虚(self-referential emptiness)中宣告的一样,这栋建筑铭记着、哀悼着共同的未来(collective future),从中整个组合(assemblage)退缩成一种向内的眼光,而非向外望去。

O. M. Ungers: 德国建筑博物馆透视图,法兰克福,1983
Oswald Mathias Ungers: Deutsches Architektur Museum, Frankfurt, 1983
这样的“幽闭恐惧症”(claustrophobia)在翁格斯的其他项目中重复出现,包括他在1980年代做的柏林酒店竞赛(hotel berlin entry competition),这在内部体现为“建筑物中的建筑物”的序列在中庭的小玻璃房子处暂停,在外部则体现为典型德国街坊建筑(perimeter architecture)。
酒店设计中嵌套的拓扑关系让我们想起来波特曼(John Portman)的博纳文特酒店(Westin Bonaventure Hotel)令人迷失方向的、嵌入的室内景观。在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著名的解读中,这完全就是后现代空间的一个图解。

Oswald Matthias Ungers. Hotel Berlin, 1977

John Portman & Assocs. Westin Bonaventure Hotel, Los Angeles, 1974-76
(Image©Richard Anderson)
为了回应这种方向感的迷失,詹明信认为需要有一种新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以在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的迷宫中辨清方向——他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同样需要新形式的预测(projection),以引导我们离开这样的空间。我们与其将视线投向建筑的外部,看向城市和世界,不如到我们建筑噩梦的深处去寻找这些乌托邦原型式的出口(proto utopian exit)。像面甲一样的、建筑本身内置的、隐藏着的地板门将会通往另一个可能的世界,而不是通往一个更加唯我论的(solipsistic)牢房,像俄罗斯套娃一样被永远囚困。
从不存于世到无处不在
(From Nowhere to Everywhere)
于是,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翁格斯和包括库哈斯(Rem Koolhaas)、汉斯·科尔霍夫(Hans Kollhoff)在内的一群康奈尔大学学生开始进行合作,尝试在1977年重新组织西柏林的一个项目中尝试他拓扑学的级联模型(topological cascade)。在那个时候,西柏林就已经是一个在萎缩(shrinking)的城市了。

A manifesto (1977) by Oswald Mathias Ungers and Rem Koolhaas. THE CITY IN THE CITY——BERLIN: A GREEN ARCHIPELAGO
(source:Lars Müller Publishers)

Diagram,THE CITY IN THE CITY——BERLIN: A GREEN ARCHIPELAGO
(source:Lars Müller Publishers)
在这个名为“城市中的城市”(The City in the City)的项目中,它们提出了“绿色群岛”(a green archipelago)的概念。这些像绿色群岛一样的公园从现有的城市肌理中被提取出来,以应对城市中人口的减少。这样的安排被一些同等意义的已建成的“岛屿”打断。他们的设计基于的是从放射性平面(radial plan)到线性城市(linear city)的各式各样先例。
为了协调单体建筑和插入的城市尺度建筑物,也为了应对居民持续存在的对独立式住房(individual house)个人性的喜好和大型公寓大厦中存在的匿名性(anonymity),他们提出了“城市别墅”(urban villa)的住宅建筑原型。这是一种由四到八个单元组合而成的分离式集合住宅(detached collective dwelling)。在翁格斯和库哈斯各自的作品中,他们都开始讨论这个议题。


住宅建筑图表,THE CITY IN THE CITY——BERLIN: A GREEN ARCHIPELAGO
(Image source:Lars Müller Publishers)
库哈斯把曼哈顿的格网(Manhattan Grid)解读为支持个体在各个街块(block)中实现表达的基础设施。他的同事Zoe Zenghelis在1972年所绘制的图表将其表现为了在城市中的建筑历史博物馆。

Rem Koolhaas, Madelon Vriesendorp:The City of the Captive Globe Project, New York, New York, Axonometric. 1972 (图片来源:MoMA)

THE CITY IN THE CITY——BERLIN: A GREEN ARCHIPELAGO(source:Lars Müller Publishers)
在其多中心城市组织的层面上,“城市中的城市”(或者在这个西德的项目中是“岛屿中的岛屿”)的模型试图重新强调大西洋两岸北部后工业城市中某些正在消失的特征,以回应郊区化(suburbanization)带来的去中心化的压力。
最终的“群岛”试图在其各个部分中维持下去,尽可能覆盖更广的建筑范围。它并没有给出一个乌托邦,而是一个调和式的反乌托邦,或者正如其作者所说的那样,这是对现状的改进。
在此之前,许多乌托邦现代主义者提出要为客观问题找到科学的解决方式。这个项目在发表时就伴随着以下来自库哈斯、翁格斯和他们的同伴的一些评论。他们说:“我们没有必要创造出一个新的乌托邦,而是去创造一个更好的现实。”
有趣的是,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同样认为,联邦式群岛(federated archipelago)的政治模型或许可以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处理许多后现代主义乃至全球化中的多重错位。他举了尤纳·弗里德曼(Yona Friedman)1975年的“可实现的乌托邦”(Utopia Realizable)作为例子。在他的提案中,有着众多互不沟通的社区,或者说是由自动的岛屿组成的群岛,它们包围着地球并通过共享的基础设施相连。生活在其中的居民能够自由地离开他们的故土,迁徙到另外一个岛屿上——这是他们不可分割的权利。
尤纳的这个设想和翁格斯、库哈斯对柏林提出的方案似乎首先具备了了解其服务对象多样的、相互冲突的身份和欲望的优点,在此之前,西柏林这个都市里的人们长期被建筑师和规划师当作标准化、模式化的对象来对待。从本质上来说,这些被称作乌托邦的“小岛”被折射到了许多的小乌托邦里去,有了许多的“小岛”而非只有一个。

草图。THE CITY IN THE CITY——BERLIN: A GREEN ARCHIPELAGO.(source:Lars Müller Publishers)
乌托邦的幽灵几乎没有被所谓的现实主义平面(realism plan)所驱散,而是增加了、进入到了这些封闭社区中去。然而,这种增加(multiplicity),这种将幽灵分散成为幽灵集群(ghostly multitude)的方式并不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如果没有“城市别墅”这种半集合性质的权宜之计,那么它终于向后工业消费主义分裂的、碎片化的景观(landscape)让位了。它通过想象一系列个人的未来(individual future)以取代一个单一的、全体的未来(single collective one)。
在另一个可能的方向上,它尝试通过多样性的、迅速聚集的成为社区的飞地或有机的、当地的、最终成为封闭社区的逻辑来尝试取代过去指导建造千篇一律的集合体的模块化国际主义(modular universalism)。
即使被折射、被分散,乌托邦的幽灵仍然保持了它的一些世俗性(worldliness)。虽然在不同的案例中表现形式不一,它已经从“无处可在”变成了“无处不在”。
乌托邦再临
(Utopia Once Again)
为了得到结论,请允许我介绍一个反例,我尝试原路返回到这些事情的积极结果中去。在1970年代后期这个时间段里,我们刚刚讨论的建筑正在被设计或建造,与此同时,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卢森堡三个城市被看作是欧盟的“议会席位”,1979年欧盟第一次直接选举将在其中的一个城市进行。全球化又一次盘旋在我们的背景中。

罗杰·塔里伯特(Roger Tallibert)的欧洲议会大厦方案,卢森堡,1977 [4]
卢森堡委任法国建筑师罗杰·塔里伯特(Roger Taillibert)做一个设计,将这个新机构整合到城市中心里去。这个项目的名字叫做“中心300”(Center 300),它在1978年向公众公示,并迅速获得通过,以期在1979年能够建成。这大概就像是卢森堡向欧盟的一次投标。
这个方案中有一个仿若巴西利亚的平台,这座新的纪念碑将坐落其上。它的姿态就像一个巨大的抽象雕塑,已经准备好迎接欧洲立法机构这个庞大身躯中的各个器官。
同样在1978年,卢森堡建筑师里昂·克里尔(Léon Krier)准备了一个相对的项目作为回应。在这里,“城市中的城市”的群岛模型又出现了,里昂·克里尔把这一形式形成的城市称为“地区的联邦”(federation of quarters)。

克里尔规划的卢森堡作为“欧洲首都”的平面,1979
正如图中所能看到的,重新建造的街道构成了步行尺度的邻里单元,它们的侧面则布置着假装具有当地特色的低层、混合使用的城市肌理。这样的城市肌理不时被新古典主义的纪念碑式建筑打断。下图是克里尔欧洲议会大厦的设计方案。

克里尔为欧盟设计的议会大厦。
Léon Krier:New Parliament Building, Luxembourg, 1979
(source: Architectural Design, 49(1), 1979)
这个规划理想的设计对象既不是工业时代的工人们,也不是后工业时代的经理们,而是前工业时代的、严格意义上的工匠们(artisans);换句话说,他的设计对象正是“人”,他们就住在工作地点旁边的另一个街区里。在很多方面,克里尔都是被认定为后现代主义建筑师的一群人中在严格意义上最具有乌托邦精神的那一个。
我想要提出的一点是,克里尔提出的“一个无中介的乌托邦主义”(an unmediated utopianism),看起来很纯粹,但是对于我们在该时期其他作品中所追寻到的鬼魂,这些作品更像在除魔,而非一种召唤。他提出“石头之城”(a city of stone)的想法,以对抗混凝土、钢与玻璃建造的城市中刻意的人造感(artificiality)。克里尔这个除魔者(exorcist)试图使人性(humanity)复活,欧洲要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必然伴随着其他部分的死亡。对于现代主义完全丢失的“家”(home),或者说“故土”(homeland)的乡愁,在这个特定的时间里成为了新欧洲去疆界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后殖民时期移民现象(post-colonial migration)。
这样的神话在他的建筑中走得很深,甚至可以和建筑师阿尔伯特·斯皮尔(Albert Speer)对于并不存在的过去的荣光疯狂怀念的建筑相对比。克里尔对恢复这位建筑师的名誉异常坚持。


阿尔伯特·斯皮尔(Albert Speer)设计但未建成的人民大厅(Volkshalle),希特勒柏林规划的顶端就是人民大厅的巨大穹顶,凯旋门位于人民大厅前的街道上。(source:Wikipedia)
与齐美尔(Georg Simmel)所说的“都市陌生人”(metropolitan strangers)不同,鬼魂实际上是没有家的,也就是说,其他的场所。它以鬼魂的方式出没,却不与城市环境调和。
在这里,旧欧洲的心脏为了回应全球化而开始重新组织自己。克里尔这个仇外的(xenophobic)方案将问题放在了最突出的地方——选择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还是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是向陌生人开放,还是选择被净化的、欧洲的人性,用石头来建造?

德里达说:“学会和鬼魂一起生活。”这句话同样为试图寻找出路的自陷僵局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指派了任务。像这样被幽灵缠绕着的城市岛屿(urban islands)还有很多其他例子,比如罗西的圣卡塔尔多公墓(San Cataldo Cemetery)和海杜克(John Hejduk)在柏林、汉诺威和兰卡斯特的假面住宅项目(Berlin Masque,Hanover Masque and Lancaster Masque)。

Aldo Rossi:San Cataldo Cemetery,Modena,Italy,1971.
(source:MoMA)

Aldo Rossi:San Cataldo Cemetery,Modena,Italy,1971.
(source:MoMA)

John Hejduk , Berlin Masque, Maquette, 1982
抛开这些项目中他们为了重建意义的、虚伪的人文主义尝试不谈,他们可能终于给“将建筑与城市联系起来,从而将建筑与社会联系起来”的一系列行为画上了句号。这种联系被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的格言漂亮地总结为:城市就像是一个大的建筑,而建筑就像是小的城市。
但这些建筑却像是从城市中切割出来,成为了一条被遗弃的街道上与世隔绝的岛屿,这些房子仅仅向建筑学(Architecture)靠拢。

Aldo Rossi:San Cataldo Cemetery,Modena,Italy,1971.
(Image©Laurian Ghinitoiu)
但是在内部,我们惊讶地发现,同样的一条街指向了同样的一栋房子。总而言之,整个城市、整个世界都在最微小的细节中体现出来,可能在一个转角,也可能是模块化的网格。这些物体就像是建造了一个没有出口的镜宫(Hall of Mirrors),但在其领域中,实体化的精神(materialized spirit)埋伏在了实现一种新项目的潜力中,其中的幽灵终于从欧洲徘徊到了全世界。

Oswald Mathias Ungers: Deutsches Architektur Museum, Frankfurt, 1983
(Image source:frankfurt-tourismus.de)
在这个案例中,我所指的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建筑项目,其建筑思想形式既不自我陶醉地渲染建筑本身的历史,也不哀悼已逝之物,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尚未降临的未来。它向自身幽闭的内部探寻,向自己的历史中探寻,不是为了打败它,而是在寻找一种拓扑学上的反转——越往里走得远,也越往外走得远(the further inside you go, the further outside you get)。
于是,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反转:历史本身远没有走到尽头,它会以类似反馈循环(feedback loop)的形式归来,在这个稍有偏移的周期性中,我们将要去的地方从来不会和我们去过的地方完全一样。生活在这样的循环(loop)中,我们或许最终会意识到,如果“后现代主义”的“后”意味着什么,那就是要学会和幽灵共存。这些幽灵来自过去、现在和未来,来自活着的和死去的他者,也来自我们自身。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我们要学会思考什么叫做“乌托邦再临”(utopia once again)。
谢谢。
讲座原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mTeMpmDO1c
参考文献:
[1] Translucent oppositions. OMA’s proposal for the 1980 Venice Architecture Biennale, Léa-Catherine Szacka in conversation with Rem Koolhaas and Stefano de Martino. OASE Journal #94, 2015
[2] 10 Years After Katrina, Campbell Robertson and Richard Fausset, New York Times. Aug. 28, 2015
[3] The Imaginary Prisons. An Exercise of Freedom from 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 to Vik Muniz. Paola Paleari, 2017
[4] The Capital of Europe: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for the European Union. Carola Hein.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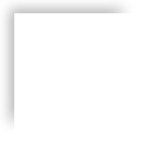
推荐书目



左: Utopia’s Ghost: Architecture and Postmodernism, Again, Reinhold Martin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右: The Organizational Complex:Architecture, Media, and Corporate Space , Reinhold Martin, The MIT Press, 2003


左:David Harvey -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_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Wiley-Blackwell,1991
右: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 Empir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左: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Fredric Jameson,Rizzoli, 1991
右: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Charles Jencks, Rizzoli, 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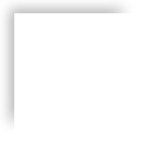
知识星期,一周即焚

公众号后台回复“后现代主义”,获取大部分推荐书目的电子版以及Martin教授的六篇论文~知识星期每周不定时更新,一周即焚,获取知识请勤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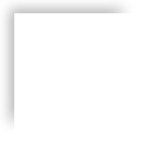
作者介绍


张艺菡
华南理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本科三年级在读。关注“社会住宅”,关注特别喜欢“主义”和特别不喜欢“主义”的建筑师。
艺菡在知识雷锋的其他文章
《忧虑的异托邦——被占领的空间:纽约、伊斯坦布尔和五月风暴》
《放逐柯布的奇幻城堡——里卡多·波菲尔与永生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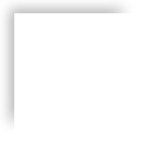
雷锋福利

欢迎添加“全球知识雷锋机器人”,邀请您加入欧洲知识雷锋粉丝群,由欧洲大牛作者坐镇,会热心答疑解惑、学习讨论,快来加入组织吧”(•̀ᴗ•́)و ̑̑


配乐:耶鲁大学 翁佳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由艺菡整理的Vidler讲座 “忧虑的异托邦——被占领的空间:纽约、伊斯坦布尔和五月风暴”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