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桥:说文解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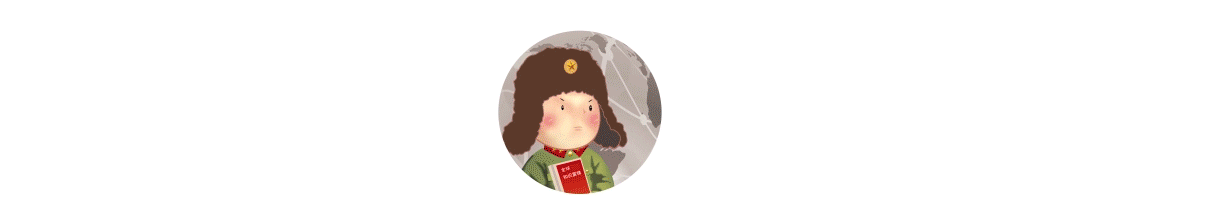
“在罗马建筑中,文字往往被镌刻在石材上与建筑合而为一,但在这里汉字却被作为独立的一层附加物与建筑分离。”
“对紫禁城来说,它的气势和权力象征也不仅是建筑物数量与规模形成的,而是由物体、物象、文字构成的系统共同建构的。”
“或许这也提供了挖掘世界第二大语言体系潜力的新途径,我们是否可以从不一样的角度重新思考这个世界,发现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并改善这个世界的秩序?”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96篇讲座。
本文整理自2017年3月6日于AA建筑学院举行的Evening Lecture,讲座原题为 The Empire of Figures,由弗吉尼亚大学建筑学院威登亚洲建筑教授(WEEDON PROFESSOR IN ASIAN ARCHITECTURE)李士桥教授主讲。讲座由东南大学秦瑜总结整理,由AA建筑联盟学院历史与批判性思考方向硕士乔沙维推荐,尤其感谢李士桥教授亲自审阅文章并进行细致的批注校对。
记录者:秦瑜

东南大学建筑学大四在读,企图跳出建筑自治的圈子,关注1:10000和1:1尺度的设计对象,喜爱怪诞的当代艺术
推荐人:乔沙维

华南理工建筑学院学士,AA建筑联盟学院历史与批判性思考方向硕士获Distinction
主讲人:李士桥

弗吉尼亚大学建筑学院威登亚洲建筑教授,主要研究当代亚洲建筑思想的独立性及其影响,其理论著作发表于世界知名权威刊物,曾受邀担任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会长奖章国际评审,全球受邀及特邀讲座70余场
正文共12443字89图,阅读完需要15分钟
推荐语
本讲座由AA建筑联盟学院历史与批判性思考方向硕士乔沙维推荐
李士桥教授的讲座主要有三个部分:基于语言学的引子,汉语背景下的文字和建筑城市,乃至最后讲座的核心——物质秩序。
我有幸在AA亲临教授的讲座现场,观察到现场的反响。对于中国听众和读者,第二部分是很容易理解的,这源自一种本能式的文化浸润。而对于西方听众,这恰恰是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或许正是因为大部分西方学者,即使通晓数门语言,也多是在印欧语系范畴内。他们对于汉语文化乃至语素文字,往往抱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却难以展开实质性的研究和讨论。而语言不仅仅是工具,如讲座中提到,语言对应哲学,是一种文明形式和思想途径。非常有趣的是,如今讲座被翻译成中文,面对中国读者,反而可以更多地探讨一下中国读者相对不那么熟悉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
在文明史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声音与图像间存在巨大分裂。[1]基于印欧语系的大量语言学研究,奠定了口说语言相对于文字的巨大优势。语音中心主义有它相对应的一系列哲学,伦理,和美学标准。西方哲学史主流观点认为,拼音文字是所有文明的归属,语素文字是相对古老而落后的。鉴于印欧语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字母系统的巨大影响,教授感慨,所以他作为一个母语汉语的人,却使用英语做此演讲。这种感触,我相信有这样经历的人会感同身受,用英文讨论或写作关于中国文化或和汉语相关的文章时。相反,在某些西方语境的话题下,使用英文反而比汉语更容易,不仅省去了翻译的麻烦,而且在于,如果使用汉语,有些讨论根本不会发生。
教授发问,那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语音偏见”吗?如德里达,虽然意识到说与书写一样存在很多问题,但其解构主义思想仍未脱离语音中心主义。在象形文字框架里,语音也许不是理解语言的最重要的环节。在这里,语言是声学和图像的结合。李士桥教授认为,表音文字和语素文字是两种不同记录语言和理解物理世界的途径:前者使用声音,而后者主要使用图像;前者的方式在与模仿(Mimesis),而后者在与变形(Modification)。这个变形过程是指解读,提炼,抽象化,并处理元素之间的关系。
在谈及汉语系统的时候,李士桥教授采用了 “造像(Figuration)” 这个词,他认为这个词适合表达中国文字如何通过某种力量创造图像,并同时创造物体的过程。从具体的物像到汉字的提炼过程,与从日常物像中提取整理归置而形成建筑和城市的过程本就相似。汉字和中国建筑城市不是由从天而降的想法产生,都是给予对人们观察到的事物以合理的方式总结形成。
与李教授身份相似的冯继仁先生曾对中国古代木建筑的基本元素斗拱进行考究。以营造法式为依据,他对“華拱”和“杪拱”进行了讨论。暗示着斗拱的建造方式与汉字书写有着种种隐秘的关联。[2] 在国内,中国比较文学的学者也多有对中国城市建筑群与章回小说的类比,比如“偏旁-汉字-词语-句子-文章”的层级,与中国古建筑从“斗拱-开间-建筑-院落-城市”的组织方式非常相似。[3] 以此探讨文字是思维的跳板,中国人在构思任何人造物品时,不自觉地遵循与文字体系类似的组织原则。虽然,从物理因素上讲,建筑材料的选择与建造技术手段对中国建筑城市有着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中国建筑城市也反映着中国人主观意识中自然而然使用的组织方式。中国园林讲求的“如画”意境,中国山水画中元素的位置经营在园林中同样重要,而这种组织方式又类似文本写作。教授在讲座中提到作为现代城市案例的杭州中心商务区,也有着相似的规律。
如果以上是汉语第一重“造像”的意思。那么第二重,如果还以最易理解的中国园林为例,这种对建筑,园林,城市组织创作的过程,本身就参考着文本的意境,以达到文本意境为上,甚至就是为着营造某种文本意境而产生的。这里可以略引一点中国画论作为补充。黄公望在山水画论中特别强调:论一张山水画的好坏,最要紧是要有一个能点题破题的名字。取名即是发问,也是点醒。园林里因仰慕前人贤者而创作的例子就太多了。那些伟大的文本,诗经楚辞、王维、陶渊明等对后世园林建筑城市的影响之深远,简直无法估量。
汉语之第三重“造像”或许借助了文字本身的虚构性。虚构fictional这个词,著名建筑理论家Adrian Forty* 有过一段精彩论述,旨在说明正由于语言文字的虚构性,其与图像一样,对建筑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4] 在汉语语境中,不同与表音语言,文字本身有着图像的属性。虚构性这个关键词,也是王澍理论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清人邹一桂,在《小山画谱》卷下中,有论述认为“书”是为“济画之不足”才出现的。[5] 通过物理空间中的亭台楼阁植物等元素不能实现的,园林用楹联匾额等文字载体作为补充,借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中国建筑中,文字也起到彰显权威等多种作用。李士桥喜爱用黄鹤楼的例子给西方学者细致解释,中国人并非主要通过黄鹤楼的物体实体去认识黄鹤楼,而是以近乎想象的方式在文字和画中认识黄鹤楼的形象。中国城市亦然,扬州苏州西安等等也不仅仅是现在的这一个,同样借助着文本的虚构性存在于两千年的文化记忆里。
* 拓展阅读:Adrian Forty《失望:一种羞耻的建筑享受》
AA有门课叫做 Design by Words(用字设计),是建筑历史与批判性思考专业最重要的一门。我想这似乎暗示着words(字)乃是此专业立身之本而非language(语言)?如果此处的words突破印欧语系的范畴,我们可展开的研究应当可以更全面,更有价值。在讲座的最后,李士桥教授批判,我们还在不加思考地延续语音中心论的理想,在摧毁全球环境的基础上实施无数的乌托邦,特别是今天涉及大数据的科技型乌托邦。如今,国际交流已成常态,我们无意割裂西方与东方,甚至这些词语的自身的定义就是模糊的。然而,即使致力于掌握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我们似乎仍然陷于Eurocentrism(欧洲中心主义)的魔咒中。某些先锋尝试,就像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字改革者曾主张以纯粹拼音文字代替汉语一样,未免局限。然而,语音中心主义以及在其基础上的哲学和思维方式,仅是认知世界的一种途径而已。弥合语言的天然鸿沟,搭建巴别塔,则需更多学者的身体力行。
[1]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and Edward Allen McCormick, Laocoon: An Essay upon The Limits of Painting And Poet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2]Jiren Feng,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Metaphor: Song Culture In The Yingzao Fashi Building Manual, 1st ed.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2): 160
[3]Diyong Long, "Chinese Architectural Space and Narrative Tradi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4, no. 97 (2014): 36-38.
[4]Adrian Forty, Mark Cousins et al., Architecture Studies, 01: Words, Buildings & Drawings, 1st ed.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Press, 2011): 12
[5]Yigui Zou, Xiaoshan Huapu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1936).
开场白
毕加索说,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去“写”我的画,而不会去“画”我的画。我不太确定徐冰的“天书”是否直接回应了毕加索,但徐冰的作品确实是对毕加索的明确回应。首先我想和大家介绍一下传统中国画中会涉及到的三个关于绘画的三个词汇。

徐冰: Landscript, 2004
* 徐冰, 中国当代艺术家,从事的艺术创作大多与文字有关, 譬如《天书》及“新英文书法”
第一个被称为“皴法”。它其实是一种通过毛笔的运行方式来创造不同脉络纹理,然后去表现不同现实物体的技法。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是,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传统中国画师,你是通过“文本”(也就是当时的画谱)来学习绘画技法的,而不是通过直接去描绘一个真实景象或者一个静物、人物。当年最有名的一本画谱叫做《芥子园画谱》,所有在练习中国画的人都听说过它。徐冰说他在练完了这本画谱后才明白,原来“皴法”是一种书写方式。

左:皴法;右上:《芥子园画谱》, 1679
第二个词汇是“写生”,似乎绘画是“书写”图像和景象。如果皴法是书写方式的话,那通过皴法“书写”出来的图像和景象似乎可以被看成是写生。写生似乎表达了绘画的真实方法,即通过皴法来表达“自然”。

文徵明(1470-1559): 潇湘八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第三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叫做“如画”。也就是说在中国,当你面对一片自然风光时,首先感受到的是图画一般的意境。这也反映了中国自有将风景视为书写作品的深刻传统意识。

网师园, 苏州
了解完这些词汇后,当看到这幅中国画时,你会认为它是一幅画作还是一幅写作?

又或者像这张照片,你怎么看待它到底是一座园林还是一场空间写作?

拙政园, 苏州
我们来迅速浏览更多的照片,其中的一些很有历史性。比如这几张拍的是中国著名文化风景区杭州西湖,你们要是去过那里就会明白历史是如何通过这种人为构造的景观联系起来的。

西湖, 杭州
这张照片可能和前面的有所不同,我们要怎样去看待图里的这种体验呢?你们当中一些人可能已经看出这是在上海城市规划馆里一个360°上海城市建设动态全景视频,这是一种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真实体验。这种体验不受时间限制,从而传递给我一个放大的、被增强的上海城市意象。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所看到的动态影像里的城市发展,从空间书写开始进而变成空间描绘再转向场景的建构或者真实的建造……

上海城市规划馆360°全景影像
城市是被书写的。这便是我想在讲座一开始讨论的问题:中国人书写他们的城市吗?我将会分为三个部分去讲述,很抱歉要以这样略带生硬的方式去划分讲座内容,但我想这会帮助我更清楚地阐述这些内容。
首先在第一部分我们需要先后退一步,去思考“写作”以及一个甚至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的概念——将语言视为声音或者是图像之间的巨大差异。二十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是结构主义,而结构主义是建立在语言作为语音的基础上。这是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语言学里的一个插图,展示出语言和交流与写作无关。对于索绪尔 来说,语言学的对象应该是口说的语言而非书写的文字,这显然否定了文字也是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并且他认为汉字书写是另外一种体系,语言学的研究是关于“听”“说”(也就是所谓的口耳相传)的研究,而无关乎“写”。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瑞士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奠基人,哲学流派结构主义开创者:
“Language is a well-defined object in the heterogeneous mass of speec acts.”
“In setting up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within the overall study of speech, I have also ouotlined the whole of linguistics.”

结构主义: 非书写!
我想借由此刻让大家反思一些更大层面的议题。一般而言,历史比较语言学是从对印欧语系的具体语言进行大量研究中产生的,它在很多方面都强调了口说语言较书写文字的优势。对于没有深厚专业知识的人来说,印度古老诗歌集《梨俱吠陀》(Rig Veda)读起来会有些不可思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对于音步音节、格律颂体的巨大贡献。你们可以看到诗歌集中收录的大量宇宙神鬼的诗歌神曲,以及它们所体现的音量节奏的平衡能力,及其所暗示的不通过文字而通过语音来思考、传授的能力。
柏拉图(Plato)在《斐德罗》(Phaedrus)* 里通过埃及国王阐述了书写的地位;柏拉图的埃及国王说,书写的发明实际上是“提醒”(Reminding)的发明,而并不是记忆。当然,这个典故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人也提到。从这个意义上看,书写把思想从身体转移到身体之外的物质,把思想外在化。通过书写,学生可以假装已经获得知识,而实际上真正的知识只能通过演说表达出来。
*Plato, Phaedrus: Thamus King of Egypt telling Theuth, inventor og writing:“so you have discovered an elixir not of memory but of reminding”.
**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法国哲学家、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哲学流派解构主义开创者
语音与文字的形式我认为这是思想传统的基础;这里,对语音的重视体现了基于拼音文字上的文明形式。字母不是一种图像,而是一种记录声音的方式,非常自然又很抽象。拼音文字是文明史中的一个最成功的故事。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图表,是历史语言学家大卫·安东尼(David Anthony)用来描述印欧语系如何从现在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扩展到南欧、伊朗、印度以及最终到达中国边境。所有印欧语系的语言来源于古印欧语,是历史语言学家假想重构的原始拼音语言。但没有人真正清楚古印欧语言是否曾以这种形式出现过。这一切都非常引人入胜!这张地图说明了印欧语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字母系统的巨大影响,以及为什么我作为一个母语是汉语的人却会站在这里讲英语。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实。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拼音语言是所有文明的归属吗?

大卫·安东尼: The Horse,the Wheel,and Language, 2007
*大卫·安东尼(David Anthony), 美国人类学教授,专攻印欧语言历史
通读过西方哲学史的话,你就会清楚地了解伟大思想家们的主流观点是,拼音语言是所有文明的归属。譬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将象形文字和字母的关系类比成譬喻和论据的关系,也就是从早期较为原始阶段的人类思考演变到后期的理性论据;黑格尔(G.W.F.Hegel)** 明确表示汉语并不是为科学而创造,因为它缺乏精确性。
* Fransic Bacon,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05): As hieroglyphics were before letters, so parables were before arguments.
** G.W.F.Hegel,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1837): The nature of their Written Language is at the outset a great hindr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s. Rather, conversly, because a true scientific interest does not exit, the Chinese have acquired no better instrument for representing and imparting thought.
近代德国学者,理论家瓦尔特·翁(Walter Ong)* 在《口承和书写》(Orality and Literacy)中坚信汉字将会被罗马字母所替代,虽然这会对文学造成巨大损失。这个发展只是时间问题,但一定终将会发生。威廉·汉纳斯(William Hannas)** 在《汉字困境》(Asia’s Orthographic Dilemma)一书中提出,汉字的困境是其不必要的复杂性;为维持这种复杂语言的社会结构是强制性的,不但产生了相应的政治形式,也遏制了年轻人的创造性。他认为汉字作为亚洲语言体系中的突出案例完全是一种有缺陷的语音系统,它们必定会被语言系统取代。
* Walter Ong, Orality and Literacy(1982):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characters will be replaced by the roman alphabet,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loss to literature will be enormous.
** William Hannas, Asia’s Orthographic Dilemma(1997): Nothing but an imperfect phonetic system, an obstacle to creativity.
那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语音偏见”吗?德里达在《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中批判了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语音中心主义有它相对应的一系列哲学,伦理,和美学的标准。他试图通过他的解构主义思想(deconstruction)证明言说与书写一样存在很多问题,但我认为其解构主义的基本精神没能离开语音中心主义。因此令我深有感触的是,语音中心主义哲学所关注的不只是语言和哲学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文明形式和思想途径。我不知道在没有完整一个学期的情况下要怎样将它阐释清楚 ……
这个思想途径的第一个关键概念是“摒弃”(Renunciation),伴随而来的是苦行生活、神圣空间(对比于世俗空间)以及圣徒与秩序的磨练;其次是从多神论到一神论到禁欲主义再到修道院的净化行为(Reduction);最后引导你去深度理解并实施乌托邦的过程(Imprint)。
我想强调,在文明史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声音与图像间存在巨大分裂。印欧语无疑是世界上的主导语系,占比高达45.72%;汉藏语系大约有1/5-1/4的世界人口在使用。如果只用单一语言来衡量,汉语应该是世界第一大语言。但如果我们包括所有语系的话,印欧语的发展绝对是非常非常繁荣的。公元前4000至公元前1000年之间,世界语言分化出两个非常不同的方向——声音与图象。象形文字包括古安那托利亚文字(Anatolian Hieroglyphics and Sumerian Cuneiform, 1900-900 BCE)、埃及文字(Egyptian Hieroglyphics, 3200 BCE-400 CE)和玛雅语文字(Maya Hieroglyphics, 1500 BCE-1600s),当然还有汉字。在象形文字框架里,语言是以物象来呈现,而不是纯粹的声音。这里,语言既是声学交流,也是视觉交流;语言是语音符号与物体图象的结合。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西方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破译语言的关键环节是破译语音密码:简·弗朗索斯·项博利安(Jean-Francois Champollion)破解埃及象形文字,或者大卫·斯图尔特(David Stuart)解读玛雅文字,语音解读是精通一门语言的最终环节。我却想说这些只是语音中心论的表现;象形文字里,语音也许不是理解语言的最重要的环节。

德累斯顿法典(Dreston Codex)
第二点与象形文字有关的是它的写作价值级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安那托利亚象形文字(大约有500个物象)实际上大部分使用于纪念性建筑或场合,雕刻在山上等等。

Dick Osseman 摄
我不想在这一点上赘述过多,就举一个国王印章的例子。印章使用了两种形式的文字,一种是在外圈使用的楔形文字,另一种实际上就是在中央的代表“国王”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的诞生本质上是为了易于书写,人们可以使用尖头的器物在湿黏土上作出三角形的楔形图样,这种快速的书写方式也是作为一种便利的工具而被创造的。但在国王印章上,物象的中心性以及它所关联的王者权威是对文字等级的有利证明,它暗示着什么是重要的什么不是。

国王印章, 乌加里特(Ugrit), 刻有希泰(Hittite)国王 Mursil 二世之名
同样,埃及象形文字中也有一些其它形式的文字使得书写更加便利,譬如古埃及僧侣体文字(hieratic)和通俗体文字(demotic)。但在我的印象里,象形文字毫无疑问是埃及语言体系中最重要的图象语言。试想那些在墓穴或是其他一些地方用于纪念死者的碑文,埃及国王的名字常常是被铭刻在卷边形牌匾中的。这些被铭刻的文字音形一致,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其发音,我们能推测出国王的名字可能叫作拉美西斯(Ramses),也可能不是。象形文字中涉及的事物的图象很重要,非常值得做更深层次的探索。

象形文字下的拉美西斯二世
我想说的第三点是,汉字书写同时具有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的特征及优点,它将象形文字与用毛笔书写的方式进行整合,形成一种更像是改良后的楔形文字。这里有些统计资料记录了汉字数量之庞大,这可能也是汉语或者汉字书写体系拥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并能被长久使用下去的原因。当然也有一些像是地域障碍因素存在,这就使得“汉语如何实现自身延续”成为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

国会图书馆
汉字没有分化出次级使用文字,同时汉字在文化中的地位是很高的。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罗马建筑中,文字往往被镌刻在石材上与建筑合而为一,但在这里汉字却被作为独立的一层附加物与建筑分离,这也是十分常见的现象。

Prestige: Demandig Its Own Layer

Power: Land as Medium of Writing
人们来到中国就会发现像这样的“刻字”不会被视为简单的平面涂鸦,而是人文景观中的一种重要元素。而像这位技艺精湛的老先生用一筐水和一杆毛笔在砖石路面上临帖,也是公园中一种很常见的消遣形式。这种行为在我看来就是毕加索“像书写一样绘画”的一刻。

中国文化在文字上的巨大的“投资”是很明显的。威廉·汉纳斯对汉字重要性的理解还是对的,虽然他的结论有很大的问题。下面展示的是一副极其著名的书法作品《兰亭序》,堪称4世纪书法巅峰的代表。如同学习绘画需要先临摹画册临本,学习书法也必然需要临摹像这样的文本。当代中国艺术家邱志杰以此为灵感花费多年时间创作出这样一件作品,期间在同一张纸面上临摹《兰亭序》共计1000次。

王羲之, 兰亭序, 353;冯承素, 部分摹本, 627-650
每一次临摹他都略微偏移纸面,所以50次以后文字已然消失墨迹层叠成为黑纸,然后不断重复这番操作。这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作品,它不仅仅传达出磨练书法技巧与建设汉语文化的艰辛,更是通过1000次复制行为创造的充满未知的墨色给读者带来震撼。艺术家还原并再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文本的价值及文化建设的意义,这使得《临摹兰亭集序1000次》充满吸引力。

邱志杰, 临摹兰亭集序1000次, 1990-1997
《天书》这具汉字书写体系的魅影对文化建构的本质产生巨大冲击,徐冰也甚至因为其作品动摇了整个书写体系的建立而暂时离开中国。《天书》遭受了诸多非议,但它的确是一次伟大的实践。徐冰说这只能算是一个人,花了四年的时间,做了一件什么都没说的事情。这仿佛在语音意义上便是以下所呈现的达达主义诗歌,一种源自发声而没有具体内容意义的文学创作。

徐冰, 天书, 1987-1991

Hugo Ball & Kurt Schwitters, 达达主义诗歌
第二部分我想探讨一下汉语的子系统,但我可能找不到比“造象”(Figuration)更好的词去切入了。这个词叙述着中国文字如何通过某种力量创造图像,并同时创造物体的过程。这里有几张简单的图表比较直观地展示了表音文字(Phonogram)和语素文字(Logogram)的区别,表音文字是印欧语使用声音来记录语言和理解物理世界的媒介,而形象的语素文字是另一种用物体图象来记录的媒介。并且两种媒介各自有不同的语言记录过程,印欧语的“模仿”(Mimesis)过程可以类比于文艺复兴对西方传统艺术科学的沿袭。而汉语的“造象”过程是一种过滤性的解读,基于一整套被变形事物、物体图象以及汉字而形成的系统。我认为这种对象事物的变形(Modification)非常重要,但这个过程具体如何发生?

表音文字与语素文字的区别
或许关键在于如何解读那些现存的文人园林。我们可以去苏州拜访众多美丽的园林,它们绝对是传统文人士子构建出的非凡场所。而真正令人赞叹不已的是园林中的每一样元素绝不仅仅就是你所看到的流水、山石、草木、亭榭本身,它们由于呈现出某种意象而被作为有价值的策展对象甄选出来,非常类似于我之前提到过的基于对象构建的写作方式。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西方传统珍奇柜的模式,珍奇柜的陈列对象因为其使用价值或者其可带给人们的知识而被珍藏;但园林与此完全不同,具有象征性的各种元素被组合到一起构成了一种诗意的写作表达。

文人园林的对象构建
这张照片所呈现的是由被抽象变形过的山石草木要素构建成的园林一角,这在园林中很常见。但这种改造并不如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我们可以对比西方园艺传统中的灌木修剪。在文人园林里,改造是极为缓慢的过程,如同邱志杰临摹兰亭序1000次那样。它甚至可以被称为一种“慢暴力”,而西方园艺中的灌木修剪更像是一种“快暴力”。




“慢暴力”
接下来又有一些跳跃了,这张图是杭州某处中心商务区,你们从中看到了什么?其中一些建筑物是西方建筑师设计的,剩下大多数都是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它们似乎都具有表现几何图形的形式。汉语“造象”中对对象物体抽象变形的操作在潜意识下影响着设计和建造过程,设计与建造的结果即为某种物象,譬如建筑,物象以此传达某种语义学内涵(Semantic Content),而正是这种内涵支持了其自身的传播。

杭州中心商务区
再一次回到文人园林,人们当然可以只是欣赏其中的山水草木,但园林里还有一种大量存在的艺术要素就是文字(Text)。 如果人们没有发现这些暗藏的文字,自然也会错过很多信息。文人园林里有多种文字营造的手段(题景、楹联、匾额等等),它们很多都用来暗示典故,你不仔细玩味的话可能无法领会那一处的景(Space-time Dislocation),当然这样的历史借喻需要多花些时间去解读。接下来展示的一些图片都将说明书写在造园中的重要作用,其余的诸多元素也都是书写的派生物,园林被视作书面对象来营造。



园林中的文字营造
以下是三种表现园林的方式,图上所示描绘的是同一座园林: 拙政园。十六世纪人们崇尚诗意解读自然与社会,园林精神和意象被诗意化地表达;而受二十世纪西方绘图法的影响,中国开始尝试如图中间这样的平面投影表达,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平面图。然而园林的意境难以通过平面投影去体现,因为园林中的文字要素都无法再现了。因此我尝试了一下第三种表达方式,它在体现西方绘图法的精确性的同时对东方园林书写的重要性也有所保留,如此人们或许可以体会到文字在中国古典园林里的重要性。

园林的三种表现方式
抛开文人士子的传统,如果我们放眼到商业文化,你依旧可以看到园林中的影子,就像图上这种常见的在建筑物上张贴文字的表现形式。你知道什么是主体吗,建筑还是文字?因此文字的永恒性不仅体现在园林里,也体现在建筑和中国城市里。


商业文化: 建筑还是文字作为主体?
接着我们继续讨论有关汉字书写的第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称它为“权力行为”(The Power Function)。当汉字被用在某些特殊场合,它们暗示着权力。

尺度, 向心, 深度, 完整
当人们望向紫禁城最重要的建筑之一太和殿时,会注意到刻有太和殿三个大字的匾额被挂在十分显眼的位置,而建筑似乎仅仅成为了匾额上文字的背景。

太和殿匾额
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胜利时,天安门广场上的文字张贴得极其醒目。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文字都将发挥其作用。毛泽东主席的书法如何在二十世纪成为他地位的有力象征,写书法为获取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党权利的象征,还有书写对象的一种权利象征。


天安门广场的文字张贴

毛泽东, 书法作品
在中国各地旅行的时候,我去到过一些把自己包装成重要大都市的小城市,它们给自己建了宏伟的市政厅,并且在外墙贴了这些文字来宣示内部重要的机构。

小城市市政厅
这种在中国较为普遍的现象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例证。所以对紫禁城来说,它的气势和权力象征也不仅是建筑物数量与规模形成的,而是由物体、物象、文字构成的系统共同建构的。

紫禁城
再回到二十世纪的城市建设,比如上海。或许这些构筑物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对象物体,谁设计了它、它有多高、它的外形什么样等等这些问题都建立在一个系统中,因此这个书写系统用独有的方式为这些对象创造了价值。

书写系统下的“造象”力量
汉字体系或其“造象”的最后一个特征和遗产(Heritage)有关,在我讨论中国城市时,中国遗产尤其城市建设遗产总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中国的遗产不一定是建立在保留遗迹的基础上,遗产经常会被拆除。但在这需要指明的一点是保留记忆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中国文字体系具有保留遗产的功能,记忆将被保留在文字中而非物件或是遗迹中(fetish of the text)。而这种情况在西方恰恰相反,所有的东西都被保留了下来,就如同《威尼斯宪章》(Pilgrimage, Venice Charter)提倡的那样是一种对遗迹的朝圣与信仰(fetish of the relic),它认为物质才是真正保存记忆的方式。
但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记忆并不总是与物共存的,它也存活在文字之中。中国自古有一项称作“考证”的传统,即通过研究来证实文献的准确性。(fetish of the text)二十世纪初期,古建筑家、中国近代政治家朱启钤偶然发现了《营造法式》于十六世纪的抄本。他对此异常兴奋,但朱启钤等人立即意识到抄本存在诸多问题。后来他又在图书馆发现了十二世纪出版的《营造法式》残缺的一页,当机立断通过十六世纪抄本来重制全书。屏幕上最右边的即为1925年朱启钤等人译注校对出版的《营造法式》,它在当时看起来至少与十二世纪的版本并无二致。

邱志杰, 《营造法式》重制版, 1925

不同时代对应《营造法式》版本
所以这是一件很吸引人的事,十六世纪的抄本被发现然后校勘重制成新版本,你能看到两个版本之间的绘图风格存在细微差别。不仅如此,朱启钤还增设了新的内容图示,并且把书装订成传统样式。1925版的《营造法式》的确是一本很出色的出版物,尽管在西方观点下它依旧是赝品。但在朱启钤看来,他倾注了大量心血重制的新版本,其文本自身的正确性就足以说明其原始性。

1925版再版
这对于我们理解那些处于重点文物保护建筑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耸立于长江边的黄鹤楼就是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屡建屡毁的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而其名称来历和营建之事也衍生出了很多传说。关于黄鹤楼各朝形制,很多画作都有所记录表现。中间这张图上是它最后留存的形制,是十九世纪人们根据古老传说重建的样式,但最终还是毁于火灾。1985年,黄鹤楼重建而成,虽和始建形制大体相似但还是有诸多不同之处。原样式为三层而现黄鹤楼有五层,原结构为木作结构而现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并且还加装了空调系统和电梯。但是你会发现来这里参观的游客并不会在意这些改变,因为原有的氛围和对黄鹤楼的记忆依旧稳固地存在。

黄鹤楼, 1868-1884, 毁于大火
左: 3世纪;右: 15世纪, 安政文绘

重建, 1985
那么这种记忆的稳固性是从何而来的呢?我认为它与诗歌密切相关。黄鹤楼是诗歌中的一种文化标志,像毛泽东、李白等很多诗人都曾描写过它。但这种文化的标志性并不根植于建筑的物质本体,而更体现在书写和文字中;这往往是西方学者最易忽视的一点,因为他们本能地会被建筑的非原真性所干扰,从而没有意识到稳固性(Stability)与原真性(Nature)的关系可能不完全适用于这种语境。

我在香港工作了很长时间,发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香港的中央码头(Central Pier)始建于1912年,原属英皇爱德华时期古典风格建筑(Edwardian blding),后改建为现代主义风格建筑,又在2006年改回了原有的爱德华样式。

中央码头, 香港, 1912;1957;2006
所以现在和码头和始建的码头之间也只存在着微弱的联系,它更像是一种爱德华式建筑的即兴创作,而新址也迁离原址约350m。在范围更大的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远远看到那座即兴创作的爱德华式建筑,由于原址要进行现代化公路建设,原来的建筑不得不迁址让位。

迁址前后的码头
这是从同一高处俯瞰的香港景象,纵观其八十年的发展,这前后两幅景象差别很大,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承载了不同的记忆。


如同前面所举几个具体的例子,这些不同的记忆体现在秩序中,尽管建筑的形式显然是大为不同的。
最后一点是从我之前所讲述过的所有内容中提炼出来的核心,也就是所谓物质秩序(Material Order)的概念。我们曾谈论到一种从对象物体快速转变成最终秩序“乌托邦”的理性进程(Intellectualization),但这种对象物体与乌托邦秩序间的生硬关联理应可以通过中间产物来调和,就像是初始秩序与最终秩序间的中级秩序。最终秩序可以是科学,可以是信仰,也可以是真理与正义……而中级秩序则与我们今天所探讨的物象与文字的作用息息相关,它给予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去配合全球生态来适应世界发展的状态。因为如今我们可能正面临着一个危机,我们建立了过多与世界发展不相容的“乌托邦”,而这种改造世界的理念与心态似乎显得有一点傲慢而自我了。
我想进一步描述原始物质秩序(Proto Material Orders),并且能在黑格尔、培根之后,有机会站在语音中心主义的对立面再一次去探究命名、思考和说话的行为。一些钻研汉学的优秀学者像是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曾深入探讨过在汉文化“物体化”(Immanence)的哲理下,真理并不产生于最终秩序而来源于中级秩序。这就好比你要说服某人,你的说辞应该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言自明。真理蕴藏于事物自身。这正是黑格尔所严厉抨击的,他认为思辨是一种非物质性的行为。

原始物质秩序: 命名、思考和说话的关系
在半个世纪前,反感天主教的葛兰言认为象征最终秩序的上帝和法律不能作为思辨的制约与最终的结果,整个过程应该像是在儒家哲学中去寻求真理与美德。另一位出色而睿智的汉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在“势”(Propensity)这个概念上做了更深一步的研究,在知道什么是秩序、秩序如何运作之后,他尝试从“迂回与进入”(Detour and Acccess)的不同倾向及效用而非事物因果关系来切入,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看待事物的方式。现在幻灯片上列出的是各种西方哲学思想中对语音中心主义的批评。

印欧语系智性传播方式的四种批判
约翰·韦布(John Webb)是尼克尔·琼斯(Nicole Jones)的女婿,同时也是一名建筑师。他曾著书猜测,中国人是挪亚(Noah)的后裔,他们将人类原始语言保留下来,即为现在的汉语。今天的我们仍然觉得这种堪称国学奇闻的猜测充满趣味,这里汉语被作为另类文明的象征。但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似乎以更为严肃的态度探寻着一种普遍语言(True Charater),尽管他提出汉字可能并不完全就是这种普遍语言,但研究汉字构造发现它具有普遍语言的特征。而关键在于,普遍语言的字词与事物间应存在直接而紧密的对应关系,而非通过符号获取概念再去关联到事物的这种间接关系,是通过两个步骤而非三个步骤来获得真正的哲学知识。在此我还想很快再提一下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十七世纪皇家学会里的奇人。胡克与牛顿曾发生过长期的争执,胡克坚持事物发展有着“经验证据”(Empirical Evidece)般的中级秩序,而不是像牛顿所关注的,实现从解释事物如何运作到普遍科学命题般的最终原因的快速跳转。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经验主义而非科学担负起了印欧语系的智性传播的重要角色。基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贡献和不足,拉康(Jacque Lacan)曾断言:“无意识的结构类似语言结构”(structure like a language)。在我看来,他所提到的并不是语言的语音结构,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在语音中心主义下图像的角色被“清除”(purge)了。这与黑格尔、瓦尔特·翁与威廉·汉纳斯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语言中被清除的图像(dismissal of the figure)通过无意识又回到现实之中。深受东方哲学影响的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曾试图重新思考西方思想传统,这个思路被哲学家布鲁诺·拉托尔(Bruno Latour)所继承发展。拉托尔想要回归客体本身,而不认可停留在无尽的抽象与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
最终我想提出的是对乌托邦的批评。乌托邦是逼真的(模拟状态下)但终究不是真实的,这是种很有意思的反思。物质秩序未必更加逼真,甚至在表现形式上不逼真的关系网。这个批评是对经常在建筑评论出现乌托邦、反托邦和异托邦三种状态同时出现的批评。对于最后一张幻灯片我想说的是,中级秩序的道德与美学或许应该作为是物质秩序的依据。与其在现有标准下重复“摒弃-精华-实施”(Renunciation-Reduction-Imprint)过程的无限循环,不如思考如何实践一种全新的经验主义。

乌托邦的批判
或许这也提供了挖掘世界第二大语言体系潜力的新途径,我们是否可以从不一样的角度重新思考这个世界,发现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并改善这个世界的秩序?但目前我们也许还并没有投入足够的研究;我们还在不加思考地延续语音中心论的理想,在摧毁全球环境的基础上实施无数的乌托邦,特别是今天涉及大数据的科技型乌托邦。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观看地址:
https://v.qq.com/x/page/r0815a0g85a.html
讲座原址:
https://youtu.be/gklOwOeh_vU
文中使用的图片来自讲座截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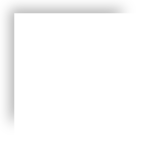
推荐观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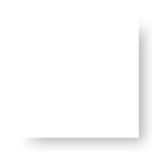


左: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City, 李士桥;
右: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Zygmunt Bauman

左:Benjamin, Walter.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 translated by Harry Zohn, edited by Lawrence Venuti,; 右:Cousins, Mark, Wei Chen, Xin Ruan, and Adrian Forty. Architecture Studies, 01 : Words, Buildings & Drawings.


左:Derrida, Jacques.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Lawrence Venuti; 右:Feng, Jiren.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Metaphor: Song Culture in The Yingzao Fashi Building Manual.


左:Guo, Qinghua.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Ideas, Methods, Techniques.右: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and Edward Allen McCormick. Laocoon: An Essay upon The Limits of Painting and Poetry.
另推荐:Fu, Baoshi, and Zonghao Ye. Fu Bao's Essays Collection on Painting Art.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House, 2003.
以及Goodman, Nelson. Languages of Art. New York: Hackett, 1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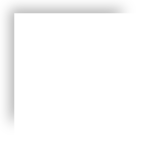
知识星期,一周即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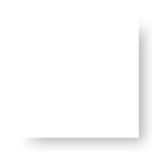
公众号后台回复“李士桥”,获取部分推荐书籍~知识星期每周不定时更新,一周即焚,获取知识请勤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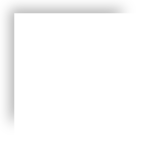
作者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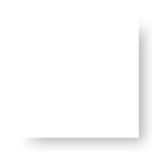

秦瑜
东南大学建筑学大四在读,企图跳出建筑自治的圈子,关注1:10000和1:1尺度的设计对象,喜爱怪诞的当代艺术。个人公众号:半两鱼,欢迎关注!
“半两鱼”的文章
《林屋叠嶂 Lost in Lod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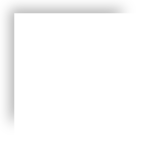
推荐人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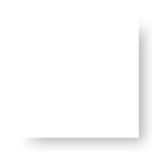

乔沙维
AA建筑联盟学院硕士,华南理工建筑学院学士
获AA HCT 专业 Distinction
三磊设计公司Design Director
乔沙维在雷锋推荐的其他文章
《后扎哈时代的舒马赫宣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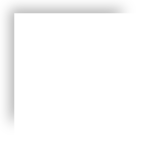
雷锋福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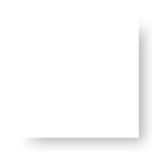
欢迎添加“全球知识雷锋机器人”,邀请您加入英国知识雷锋粉丝群,英国群由AA drl硕士王子乾主持,邀请到多位AA、UCL、谢菲等英国名校大牛同学坐镇,前沿科技、跨界研究与历史理论并重。大家会热心答疑解惑、学习讨论,快来加入组织吧”(•̀ᴗ•́)و ̑̑


配乐:秦瑜
排版:艺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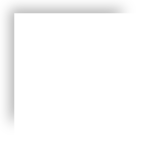
往期回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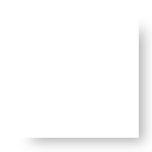
讲座专栏
北美讲座
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康奈尔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Paola Antonelli《人类终将灭绝,而设计师能给人类一个优雅结局?》
Germane Barnes:《要怎样做才能拯救一个城市?》
Herman Hertzberger:《他坚持设计为人,却被年轻一代忽略:赫曼·赫兹伯格讲他的结构主义》
哥伦比亚大学:
Cooper Union:
纽约州立大学:
伯克利大学:
莱斯大学:
迈阿密大学:
Neil Brenner:《星球城市指南 | 为什么外星人入侵地球总是失败》
宾夕法尼亚大学:
Dream The Combine:《梦境结合:虚虚实实的镜中景观》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麦吉尔大学:
德克萨斯A&M大学:
欧洲讲座
代尔夫特大学:
米兰理工大学:
佛罗伦萨大学:
伦敦大学UCL:
Adrian Forty:《失望:一种羞耻的建筑享受》
AA:
英国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
英国皇家美术学院RA:
剑桥大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Sharon Zukin:《“原真性”城市场所的死与生》
谢菲尔德大学:
Richard Murphy:《“伪建筑师”斯卡帕》
阿尔托大学:
ETH:
门德里西奥建筑学院:
Valerio Olgiati:《“非参照”——你听说过却从未理解的Olgiati》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KTH:
马拉盖建筑学院:
Patrik Schumacher:《后扎哈时代的舒马赫宣言(上)》
Patrik Schumacher:《后扎哈时代的舒马赫宣言(下)》
巴黎建筑与遗产城:
国立里昂第三大学:
Jean-Philippe Pierron:《人类世时代的大都市化进程》
慕尼黑工业大学:
Ferdinand Ludwig《你一定没见过的活体建筑》
James Corner:《詹姆斯·科纳:从美墨边境到雄安要走多远?》
博洛尼亚大学:
Massimo Montanari《吃货的中世纪》
亚洲讲座
东京大学:
京都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清华大学:
MVRDV《MVRDV能把城市带到多远?》
中央美术学院:
澳洲讲座
墨尔本大学:
悉尼大学:
展览透视
“新知视野”专栏
珍贵文献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雷锋第75篇讲座《后扎哈时代的舒马赫宣言(下)》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