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时代的大都市化进程



“城市的建立不仅依靠它的围墙,还依靠徜徉在那里的所有生命发出的喃喃絮语——这些生命的坚持、抵抗、对彼此共同生存空间的维护,构成了城市持久、顽强的生命力。”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81篇讲座。
本文是上海大学-法国里昂让·穆兰大学伦理学与可持续发展硕士研究生项目的课程之一,“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概念以及相关的哲学思考”,主讲人为法国里昂让·穆兰大学哲学博士生院院长让-菲利普·皮耶洪(Jean-Philippe Pierron)教授。讲座分两部分:Agriculture et alimentation 农业与食品问题 / Architecture et urbanisme soutenable 建筑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为讲座的第二部分,由曲晓蕊推荐并翻译。
记录者:曲晓蕊

法国里昂让•穆兰大学哲学系现象学与当代美学方向博士研究生。
主讲人:让-菲利普·皮耶洪(Jean-Philippe Pierron)教授

法国里昂让·穆兰大学哲学博士生院院长,IRPHIL里昂哲学研究所·法国高校联盟阐释学、图像学和符号学研究所·Labex IMU智能城市卓越研究院学术委员,研究方向:从阐释学、存在主义出发,对现代生活的道德哲学思考,尤其关注环境、医药与与家庭方面的问题。
文章全长16869字,阅读完需要40分钟
正文
在人类世(Anthropocène)时代对超大城市发展的思考[1] 提醒我们,城市的发展始终是一个矛盾综合体:自然与人工、社交纽带与疏离孤独、文明与野蛮、宅在家中闭门不出的安全感与出行的焦虑、日益膨胀的消费狂热与审慎节制-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梦想、划地而居-巷陌井然的安定生活与大量人口流动迁徙带来的灵活住行方式……在城市化大规模发展与被地质科学和社会科学称为“人类世”的时代影响下,这些矛盾都日益显著地表现出来。(“人类世”这一概念因其人类中心主义与殖民主义倾向、及其秘而不宣的“种族世”本质而引起了诸多争论;而将生态问题以地质区间原则重新划分的方式也是另一讨论焦点。 )诸多矛盾指向的核心,就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这里,应不应该把可持续发展视为矛盾多义的政策的体现?

法国地理学家米歇尔·吕索(Michel LUSSAULT)著,《超级地点:全球化语境下的新地理学描述》 (Hyper-lieux. Les nouvelles géographies de la mondialisation, Seuil, 2017)。
作为一种全新的宏大叙事,人类世[2]着眼于全球发展,对人与自然的联系做出了全新阐释,揭示出人类对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自然与社会系统之间交织错杂的深层联系。从联系的视角重新认识城市作为重要参与者,促进或削弱人与自然之间的经济、社会、生态与政治联系的作用。城市的“生态足迹”[3]就是重要例证。生态足迹是衡量自然资本与人类需求的关系的计量指标。通过估算用来满足人类需求的土地面积,它能够有效反映出人类活动为自然带来的压力。将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与维持这种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地表面积的比率以公顷数表达出来,这让我们看到,如果所有人都享有同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显然是无法持续的,例如,如果要全球人口都能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我们需要三个半地球的资源供给。更广泛地说,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启发我们从宜居性的角度重新思考城市在整个人类版图中的位置。除了作为地理位置(topos,处所)和行政区域,城市还是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chora,场域),其中包含了各种复杂的社会、环境关系。对自然的实际关怀总是隐身幕后。这些复杂的关系往往被隐藏在它们借助的手段、即技术管理系统之下
(饮用水或污水处理系统、垃圾管理系统、交通运输保障、风力空气净化手段、城市照明对黑夜与白天的分割及其对城市宇宙的展示) 。探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依然是在对人类活动的矛盾后果进行权衡,考察我们当前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和损害。这为我们打开了对城市发展在人与地球的关系中具有的伦理、政治和人类学意义的思考。

亚历山大·费德罗( Alexander FEDEREAU)著,《人类世哲学》( Pour une philosophie de l’anthropocène, 2017)。
在人类世时代,以关怀的视角来反思城市化,也将同时改变我们对空间的认识,令其中的关系发生改变:安全的城市让位于给人以安全感的城市;信息化控制(监控录像、数字化、人流设计、智能城市)让位于关系维护(可持续的城市、慢节奏、过渡、强调关联和协作的城市活动、“城市罗宾汉” * 等),促进对城市规划和改造工程的伦理监督,促进城市-农业的交互发展。设计以关系维护为核心的新型文化、实践活动:本地供给、永续农业,这些尝试既维护了传统农业、近郊农业,又促进了生态多样性以及城市中的自然[4]。如此一来,“给养城市”在充满关怀的“栖居”中重新建立联系,从而摆脱了传统城市“吸血鬼”式的、狼吞虎咽饕餮无度的妖魔化形象(如左拉《巴黎之腹》)。通过乡村的城市化(城郊结合部)、城市农业(共享花园)等形式,重建城市与自然之间的纽带。如果我们转变看法,以“依存”(vivre de)而不是“以…为生”(vivre sur)的角度看待食物,我们思考社会契约的方式也会随之转变。“依存”关系有着重要的伦理、政治学意义,其中包含了对于联系脆弱性的清醒认识,不再以控制、主导的方式通过不间断的操控来保证“城市食品和健康安全”,而是充分照顾到各因素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这正是城市这个人造环境时常令我们遗忘的一点。城市生态思想因此在城市空间中逐步重生。城市-花园、低碳出行、共享经济、重划领土的本地货币、乡土导游推荐或城市果园等都体现了这一点。在这个栖息地失落、城市沦为“居住机器”的时代,强调以栖居作为创建世界的基础,将引导我们反思究竟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来构建共同世界。
* 译者注:“城市罗宾汉” Robins des villes 是1997年成立于法国里昂的一个致力于维护城市公共空间、促进公众教育的协会,由来自各领域的志愿者组成。目前办公地点已扩展到马赛和巴黎,活动遍布全法。参见协会网站http://www.robinsdesvilles.org/index.html
生态转型对于建筑与城市发展的意义,就在于追问以怎样的建筑方式,才能够重现栖息地;建立怎样的城市,才能保护特定时空中共存的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感应、维系两者间的感性联系。
如果说城市始终处于城市(urbs)和城邦(polis)两种模式的交互影响之下,带有城市性与市民性双重特征,我们也不能忽略其中包含的身体联系——凭借身体存在于城市之中的体验,以及将我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昂希·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谈到的“城市权利”这一问题。不是有人群聚集在一起就能形成集体,仅有人的集合也还不足以构成共同体。事实上,如果说城市形成了一种凝聚力,真正在各部分之间起到粘着作用的,是成员对彼此的关注、城市的组织结构、以及他们为抵抗疏离感的离心作用而建立的共同发展计划。处于同一地理空间的事实联系还不足以形成团结一致的发展计划,后者意味着
分享相同的政治理念及一种更为深层的地缘诗学。

左:昂希·列斐伏尔著, Toward an Architecture of Enjoyment (Vers une architecture de la jouissance, R. Bononno译,2014);
右:昂希·列斐伏尔著,《城市权》( Le Droit à la ville, 1968)。
对城市发展现象的内在关系和生态意义的反思,不仅突出了感性、诗性及理性各因素在其中的交织,也对柏拉图在《政治学》中提出的城市隐喻以及政治家在其中扮演的织工角色做出了全新思考:
谈及对人类社会整体上的关怀,没有任何其他艺术形式能够在这一皇家艺术面前自称先导或鼻祖,因为这关怀正是它的本职,它就是统治全人类的艺术[5].
不过更准确地说,政治艺术应该是一门编织的艺术[6],它面对的不是一个固定、僵化的现实——棋盘一样稳固的城市平面图——而是精心设计的关系和以此织就的联系网,我们的城市生活就在此基础上展开,层层递推:私密的家,门口的小巷、街道、区和市……其间不断与自然产生关联(植物、动物,也包括水、光、土、风等自然元素)。因此,城市不仅由文本、也由纹理构成。巴西艺术家莉吉雅·帕佩(Lygia Pape)1968年的行为艺术作品 Divisor(因子)就是对这一理念的凝练和诗意表达 。

巴西艺术家Lygia Pape1968年的行为艺术作品Divisor。
她邀请里约各阶层的市民参与到作品之中,共同披上一张巨大的白色床单。由织物覆盖的空间代表了城市的肌理,以脆弱织物为代表的开放友好的关系网取代了分隔各个街区的铜墙铁壁,这是以雅典集会广场(Agora)模式为参照对城市空间的重塑。近来人们对城市生态多样性的关注;对恶劣城市环境中城市树木的养护;不再将垃圾视为废物,而是建立回收和再循环系统;不再将水资源视为威胁、以不透水模式设计城市排水系统,而是建构以动态水资源体系为特征的海绵城市;设计以参与模式为主导的生态街区,这些都是新型网络关系模式的集中体现。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在重申,城市不仅是其外观的建筑,还体现为集中流动的各种关系,它邀请、也要求着人们从伦理和政治关系角度重新思考城市的包容和开放性。这种关系和感性因素是城市的基础。它抵制了将居所简化为解决住房、安全和出行问题的“居住的机器”的功能主义倾向。它崇尚流动的形式,能以更为灵活开放的方式激发各种可能的关系; 把城市想象成一个漂浮的世界。视觉艺术家、空间设计师与城市规划师的角色就是为城市设计包容友好的面貌,重建诗意的栖居、以开放的空间促进日常轨迹之外的意外和邂逅的发生,重新接纳生活中积极的“偶然性”因素;而这样的设计正体现出关怀“此在”的政治视野,以一种地缘诗学来对抗地缘逻辑——前者将栖居理解为各种伦理关系;而后者关注的仅仅是技术效能。


左:Divisor在2017年第14届里昂当代艺术双年展上展出。右:Divisor在2013年“香港故事”展览中的重现。
谁又看不出,构建一个关注他人、体贴、无私、包容接纳的空间,而不是坚持地缘逻辑、一味追求效率和力量,会带来怎样不同的效果?[7]
2017年第14届“漂浮的世界”里昂当代艺术双年展期间,艺术家菲利普·盖斯纳(Philippe Quesne)以充满诗意的作品《洞穴》(
Welcome to Caveland,2016)重新定义了持久的栖居。这件装置作品将一件巨大的黑塑料袋用鼓风机吹起,膨胀充塞在糖厂大厅建筑框架的一隅。

Philippe Quesne的作品Welcome to Caveland (2016)在2017年第14届里昂当代艺术双年展期间展出。
这是一个反-岩洞。它的外形令人联想到史前人类在岩石之下寻得的栖身之所,而实质上却毫无岩洞的稳固,仅靠鼓风机不间断的运转来支撑其内部空间。这个矛盾的洞穴本该如磐石般坚固可靠,其实际存在却仅靠风的吹动,鼓风机若停止运转,洞穴也就潸然坍塌。它提醒了我们城市——人类极不稳定的栖居之所——这顶帐篷的脆弱,尤其是当我们想到,大量涌入城市的避难者,只能凭运气,在这飘摇屋檐下寻得接济招待。菲利普·盖斯纳说,自己在这件作品中“设计了近似于风景或景观公园一般的场景……这件作品不仅是脆弱的庇护之所,当我们步入其中,仿佛走进了一个生物的内部、走进一只搁浅在展览场地的忧郁的蓝鲸的肚腹”[8]。

Welcome to Caveland内部。
但我们是不是真能喊出“欢迎来到洞穴”?菲利普·盖斯纳的作品《洞穴》指出了作为传统藏身之地的洞穴、以及城市的脆弱性。在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城市社会,住所的首要作用就是满足安全需求,即使那些避难所无法确然保证其接待功能。一种新的斗争正在兴起,地理学家米歇尔·卢索尔(Michel Lussault)称之为“争地运动”。这个塑料作品是一个漂浮的居所,它集中体现了我们所处时代的主要特征,即不确定性——我们已不知自己应存身何处。它是今天各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生动隐喻。这就是今天人们寻求长居久安、而非追求在一成不变的不朽中永存的愿望的意义所在。我们不能把城市的建设问题简单归结为技术上的生态-建构(推崇低能耗建筑、追求由技术发展带来的满足感、对“高环保性能”建筑的向往)——这正是地缘逻辑主义所宣扬的理念。这一立场忽视了生态-社会-建构这一必要维度。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漂浮的世界。图像、信息和噪音的泛滥、物质的增殖扩张、社交网络的蓬勃发展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令现代城市演化为迅速移动的世界。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物资、信息和人口的加速流动为城市的发展增添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因素,令其难以维持稳固形式。没有什么比岩洞更稳固,而构成这洞穴的质料却纤薄脆弱,系于一息之间。没有什么比城市更确实,扎根于四面高墙铁壁之间,但实际构成城市的,却是其内部的彼此关联和悄声耳语,是它们日复一日织就了城市之网。艺术家、空间设计师与城市规划师所面临的挑战,正是要既关注这些流动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又要创造适当的空间形式来应对这些流动,与之相适应、合作,而不是焦虑担忧。不仅要保证安全(sécurisé / secured),还要给人以安全感 (sécurisant / securing , reassuring)。
在政治建构开始之前,在城市建筑方面的思考因此成为了创建联系的有力中介。它让我们看到,
与推行民主参与制、鼓励居民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改变不够环保的生活方式等目标比起来,生态建构的技术手段和高环保性能建筑其实是最容易达成的目标。轻飘飘的
技术至上口号其实是城市机器的乌托邦梦想的延续。它还以不间断的监控报告替代了对周边环境的悉心关怀。栖身于数字化系统构成的环境之中
(数字水表、电表、控制温度的数字仪表板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 数字城市仍然体现出一种理性乌托邦思想, 因为它的控制是为了抑制无序、事故和不完善, 力图达到最理想的标准化状态。数据收集和管理功能是与整体理性化的乌托邦理念相一致的, 它们的最终目标就是令智能城市与极权城市相结合, 一切都被识别、记录、转存, 就像边沁的圆形监狱[9]* 。
* 译者注:圆形监狱(Panoptikon)理论,是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1795年根据可视性原则设计的圆环状建筑,在其中央造一个塔楼,面对圆环的内侧开很大观察窗,四周是一系列按层次划分的牢房。每个牢房中有两个窗户:一个让光线照进来,另一个面对塔楼,塔楼通过大观察窗可以对牢房内部进行监视。于是牢房“变成了一个小剧院,每个演员都是单独的,即被完全个体化,又是时时可见的”。犯人对监视者来说是可见的,但无法看到监视者。这种建筑如此完善,以至于在监视者不存在的情况下其监督机制仍能有效地运作。“犯人看不见监视者是否在塔楼里,因此犯人必须循规蹈矩——仿佛监视是永久性和总体性的。如果犯人不能肯定他是被监视的,他就变成了自己的监视者。”边沁声称他的这个发现是一个“哥伦布之蛋”,因为他找到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们一直寻找的东西——权力技术。内容来自网络。
在计算机控制之下的可持续城市就是这一模式的最新化身。它伴随的风险就是忽视市民的实践创新能力、忽略社会结构、破坏本地居民在长期合作、分享、团结互助中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即“社会纽带”。漫画家恩基·比拉(Enki Bilal)在他的最新作品《BUG》[10]中描述了一幅未来图景,从反面揭示、预言了城市的无形关怀的力量 。



Enki Bilal作品《BUG》(2017)。
想象一个数字化管理的城市,突然间因为一个巨大的系统Bug瞬间失去了所有存储的数据,此时,人们发现这个硕大的城市竟无法重建其原有的社会和生态联系,因为建立在海量数据基础上的虚拟现实已经令人们完全失去了对这些联系的感受力或注意力。所有的关系都被信息和数据连接所取代。Bug 的出现唤醒了人们沉睡的意识、让人们看到支撑彼此存在的基础:在庞大的计算机内存背后被唤起的微弱回忆、机械任务之下残存的个体感知、在机器人助手协助下一如既往地施展专业准确的操作技能、结构井然的程序化生活中依然闪现的意外的相遇……
从关怀的角度思考城市现象,可以抵制机械的“居住机器”思想。它鼓励人们对规则标准做出诗意的修补、法制之下的大胆越矩行为,这些做法虽然颠覆了城市设立的安全规条,却是为了真正令人在城市中获得安全感。公民身份不是从公民权的宣布开始生效,而是在默默伴随并支持我们的生活行为、且人人平等的城市权中获得。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斯篇》(Protagoras)中讲了普罗米修斯和厄庇墨透斯的故事,以此说明在城邦中,所有人都同样具有克己心(pudeur)和正义感(justice)[11]。我们对正义感这个词并不陌生,而克己心出现在这里却让人有些意外。它强调联系的内在品质,而不仅仅是理性和标准化的衡量方法。克己是在社会和政治维度上具有的深度。它不仅是社交礼节,也是对社会的微妙本质的关注。相对于贯透身心的过度激情而言,克己是一种关怀,对自己、也是对他人——其中也包括非人类,它敞开了相遇的可能性。有了克己之心,城市性(urbanité)得以在偶发细节之上安枕,是关怀令这些意外插曲拥有了未来。社会学家阿维夏伊·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在《体面的社会》(La société décente)[12]一书中对柏拉图的分析做出了回应。

阿维沙伊·马加利特著,《体面社会》,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得体是对克己的另一种表达。一个体面的社会意味着所有公民都不会被羞辱,而是获得尊重。为此,马格利特对“文明社会”和“体面社会”做了区分。“文明社会”简化了克己的意义,往差了说是过于腼腆,往好了说是符合文明社会的行为规范。法律,即城邦的警卫,保证了权利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但仅有这些还不足以建立一个社会。在主体与主体间表面上形成的契约关系之下,还存在着一层关系公约。这是存在于社会中更为古老的、感性的和情感的联系。这种互相支持的关怀是“体面社会”的特征,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富于同情的语言不可或缺的成分。克制有度的关怀、把对他人的关心内在化,塑造了我们的社会联系。我们也可以称其为城市性。它容许每个人作为一个主体存在,并作为人类获得他人的尊重,而不被视而不见、视为低等或受到排斥。
这些微不足道的对世界的关怀构成了城市最终的样貌,并维护着我们共同的世界。从共享单车到共享花园,从自主打票到隔代合住,从对城市的感性认识(光、环境声音等)到社会互助、参与性活动,以及邻里关怀……城市活动的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方面,也在社会政治领域不断涌现。哲学家纪尧姆·勒布朗(Guillaume Le Blanc)在《微小生命的起义》(Insurrection des vies minuscules)[13]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种羞怯克己的城市政治形象。身影蹒跚却又步履不停,由于自身的弱小,他不仅任由命运的偶然性摆布,还张开双臂来拥抱这样的偶然。其中的典型人物就是查理·卓别林塑造的小丑形象。

纪尧姆·勒布朗著,《微小生命的起义》 (2014)
卓别林饰演的理发师的关怀来自脆弱的群居生活。这种相互关怀的哲学已被理性化的经济体制和机械化社会所无情摒弃。民主假说被世界主义假说所取代。人人的力量,是对这个没有国界划分的世界、这个与大地一体的世界中每个生命的关怀。“大地丰裕,能够养活所有人”。实际上,人类有着双重的手足情、连带心。有被排斥者、贫困者的手足情谊,他们因生活在同一个犹太区而彼此息息相关;也有现代生活的共生纽带,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飞机和汽车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14]。
可是,距离拉近了,不代表就此感觉亲密。如果把城市性的构建比喻成一条大船,卓别林塑造的人物形象就是船首的雕像,只不过这船首自身处在摇摆不定之中,它帮我们构建起这样一个共同世界,支持、强化了人类的个体独特性和集体性,人类与非人类的互动也包含其中。城市的建立不仅依靠它的围墙,还依靠在那里徜徉的所有生命发出的喃喃絮语——这些生命的坚持、抵抗、对彼此共同生存空间的维护,构成了城市持久、顽强的生命力。这就是构建可持续的、有生态责任的城市的另外一种角度。这就是它的世界主义也就是世界-政治(cosmo-politisme)理想。正因为清晰意识到与人类、与自身所在的特定环境之间的联系的脆弱性,并清楚知道未来即寓于其中,世界主义理念所支持的未来并非着眼于自身的眼前利益,而是首先向周围的其他生命敞开。
对身处环境的关怀,就是留意其中各种关系、重视相互依赖性。这就要求我们准确具体地去描述城市/家园中包含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从而进一步确认应采取的行动。以下两个例子可以让这一点更容易理解:城市灯光照明和城市公园。
我们迎来了灯光管理时代。我们不再是重复机械动作的机械主体 [16]。
被剥夺了黑夜的城市失去了与宇宙的联系。
但灯光为城市带来的意义不仅在技术或经济方面那么简单。它还具有审美意义,探询着身体在城市中的全部感性经验。从这一角度来看,城市灯光不但影响到城市与其所在的环境氛围的关系
(破坏了自然光氛围),还影响到所有生物以及城市“动物”,其中也包括人类。因此不能仅仅考虑节能,而应更多地致力于保护氛围,因为灯光使我们更加敏感、在夜的诗意中滋养我们的情绪和感情
(恐惧、夜晚的愉悦、隐匿于明暗交织之中的安全感、凝望星空)。灯光不只是光。它激发想象,令人在感性氛围中观照自身,它抵抗着仅从安全需要考虑为照明设置的唯一准入门槛。“夜晚的城市真美”——对城市的诗意描述因此令人对城市空间的光影色调更加敏感,并令其成为城市的一项品质:从星光灿烂的夜空到烟花盛放的节庆场景,从夜色深沉到明暗交替的光影游戏,从电力女神到微弱烛光的顽强不息。夜晚的审美让我们的感官更加敏锐,同时也加强了与宇宙的联系,令我们与天地相连、矗立于大地之上。以上这些是为了说明,在日夜交替的节奏中,自然与城市的联系获得了另一个维度,它为社会联系谱下基调,并提醒我们,即使在完全人工的环境中,我们仍与周边环境、与在地球上所处的位置以及地球的自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以严谨理性著称的哲学家康德,也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结尾处感叹到,当我们仰望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心中总会充溢着赞叹和敬畏,历久弥新。我们需要结合感性和形而上学的整体来理解这段璀璨星夜的冥思,从中发现作为本源的浩瀚夜空的深度。从对黑夜的恐惧到面向夜空的冥思,从明暗交织的模糊暗示带来的焦虑不安——“哪里暗影模糊,哪里就有狼”——到喀尔刻
(Circé希腊神话中能够控制黑暗的女神)式的徜徉在黑夜的暗影迷离中的欣喜,城市空间的色调为我们带来不同的情绪。它是城市的“生态传记”(éco-bio-graphie生态-绿色-书写)——也就是说城市的生活方式正寓于昼夜气氛引发的各种关系之中,来自于引发我们的恐惧惊骇的各种想象。白天与黑夜影响着我们的情绪,并为我们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定下基调
(人们对于夜间的工作有着各种想象,而守夜人代表了其中重要的守护者形象),有时是偏爱、期望或渴求,有时却是担心焦虑。这绝不偶然:
政治同时也是一种感性联系。在这一点上城市花园景观的发展就很具说明性。我们从古典时期继承下来的园艺理念是以几何形式来设计生物的样态——例如法式花园——在这一精神指导下,园艺只能是一门卑微的艺术,过于依赖感性关系和利害关系,令其审美价值和装饰价值都大打折扣(如康德所言)。不过,我们也可以把城市花园的休闲活动和园丁的工作看作是活跃的生命关系的组织者,而不只是对景观的规划。正是因此,园艺设计师吉尔·克莱芒(Gilles Clément)[17]的工作无疑带来了园艺理念的革命。

Gilles Clément的房子。


Gilles Clément作品,巴黎布朗利河岸博物馆。
园丁的工作并不是(用墨斗)做几何设计,而是(以筐篮)编扎组合。这意味着打破园艺的国界线,将花园的领域扩展至全球;不再从落地生根的稳定一面看待植物,而是从植物与环境形成的动态关系方面着眼,重新审视这些“流浪者”[18],消除对观赏植物和“野草”的区分,不再将城市中的自然看作一种入侵、斗争(或许可以从放弃“有害的”、“野草”、“划定界限”、“连根拔除”、“制定规范”……等常用词开始)。园艺不再是一门改造大自然的外形、赋予其秩序的艺术,而是对自然中各种关系的处理斡旋(重修人行道、有效利用落叶、道路防水层的去除、停止对农药和杀虫剂的使用、令城市与自然的边界模糊化、公共花园和绿地的对角线化等)。园艺因此成为对生态系统中各种关系的自由纽结、一个不断打破原有规划图纸的游戏、一项活的进程。


Gilles Clément园艺设计。
我们已经看到,关怀并不是对世界的重新阐释,而是一项改造,因此它并非本质主义、一成不变,而是要考虑特定背景。关注语境的特殊性,不仅依靠往日经验及反思,也要充分参考自然科学、人文科学领域的专家意见,这令我们看到,城市中的环境问题,以人类活动的重要影响为特征(例如城市中的生物多样性),与农业环境、花园、自然保护区或一般的自然空间中的环境问题有着极大差异。如果说在此之前自然环境一般被视为一项先天条件,现在我们看到它其实是人力的构建,是由政治、社会、司法方面的多重裁定和抉择、尤其是象征性决策所决定的。而我们应该对其后果保持清醒意识。
其首要后果是证明,人类世和人力改造活动的结果并不是要带来“自然”的终结。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指出,“即使在人类创造活动影响之下……自然的原始创造力依然持续发生着作用”[19]。即使在人力主宰、人类创造的环境中,原有的自然环境还维系着其中各生物之间的关系。自然环境所代表的不仅是一处避难所、或濒临消失的遗迹,而是一股顽强不竭的原始创造力。对环境的关注和关怀针对的不是某物,而是一种日渐脆弱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各式混杂的环境,例如动物园、城市绿地、城市绿色-蓝色基础设施等,我们应更准确地称之为生态重居 (réhabitation)[20],而不是生态重建。其重要性不在于修复人类活动带来的灾难后果,而是从源头上转变造成这些后果的行为模式,看人类如何能重新建立与自然的良性互利关系。这就像是在医学中,医药的作用并不是消除疾病,而是令生命体焕发维持健康的原始创造力,在环境方面,我们可以依靠这些相互依存的坚韧持久的联系,而不过多介入和干涉。这就是消极关怀的伦理学,与卢梭所说的消极教育相一致。这意味着克制自身的干预行动。环境保护计划应该主动禁止文化的过多干涉,将自然环境作为希望达到的理想目标的范本。可是,如果在环境保护方面,规定什么是错的比规定什么是对的要容易得多,我们又该如何判断呢?消极关怀可以体现为多种不同方式:在生态保护区中保护原始自然环境不受改变;在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地区,重新引入当地灭绝已久的原有物种,恢复其本来的生物多样性;在遭受严重污染的地区进行污染治理和恢复重建;或在日常行动中落实保护自然的举措。但在所有这些行动中,最关键的原则就是告别外部强加的空间部署方式,转而以管理、照料的方式维护环境中的各项关系及彼此关照。
随即而来的就是第二个后果:对环境脆弱性的关注也让人在对环境的关怀行动中始终能够对环境影响保持敏感意识。对地区保护实践的肯定和宣传能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些活动。这些举措的施行有赖于当地文化提供的技术、经济、社会活动等多种支持手段。自然环境无法脱离社会、以及人们为保护自然而做出的各种辛劳或欢喜的努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更倾向于用milieu这个词(有自然处所和社会环境双重意义,接近于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提出的“风土”- fudô概念)[21]。对纯粹原生或野性的强调恰恰是一种人为的放大,自然与人类对自然的维护行为是不可分割的,这种维护是双向的——当然,这样说不是有意地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的紧张时刻、那些灾害或悲剧,自然并不总能把事情做得很好(疾病,瘟疫,海啸,地震等)。这些关注和关怀还牵涉到地质或地理现状,因为要考虑到气候、水域或地形等多种因素。呵护气候和呵护某一流域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些措施强调的是关系,那么关怀呵护的视角就不是与周遭环境的直接联系——感同身受、共同的痛苦——而是要通过制度措施来落实这一关怀。可以说,我们目前所处的生态时刻已经进入了关怀力的时代,此前在各个文明、社会和行为惯例中潜藏已久、却因习以为常而被忽视的社会环保行为,今天已经引起了人们更明确也更自觉的注意。实际的关怀行动往往发生在幕后。在环境方面,甚至可以说这些努力经常都隐于无形。这就需要我们留意并细致描述这些致力于保护自然的行业。如公园门卫,森林消防队,植树护林人,林区导游或自然解说员,饮用集水井或净水中心的负责人,水警,地区水务局在某一流域指派的水情监察员、举报人(从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成员到反转基因产品协会的志愿者等)。我们把呵护自然栖息地的任务交给了这些既是见证人又是守卫的守护者们。关怀力时代意味着承认并感激那些守护着所有生命起源的环境的工作者们。因此,关怀力时代从现象学角度纠正了将我们眼中的自然(风景之美,生物的鲜活生命力等)与这一自然存在本身(生机盎然的自然环境)割裂的态度,让人充分意识到万物之间的关联和相互依赖。
最后,如果说关怀的视角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眼前现状的复杂性,对世间存在现象层面的经验则在对自然的种种阐释中体现无余,这些理解远比人们常常灌输的刻板理论要复杂得多。一些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区可以保持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与依靠自然进程自发调节的做法截然对立。这是生态系统不可替代的内在结构,其独特性也恰恰说明了生命样态的多元可能性。重视这些因素是抵制全球商品化带来的单一化、贫瘠化趋势的一种方法。
社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令世界成之为世界的脆弱复杂的关联之网的一部分,它令关怀具有了政治维度。它反对的恰恰是以技术-工业手段对自然的控制——农业生产体系的标准化,在领地、技术、行动方面达到一致,试图创造一个脱离土地的自然。我们可以绘制一幅环境关怀质监地图,列出所有薄弱区域,从而更好地维护生态多样性。欧洲的Natura 2000保护区由各地区的自然保护公园组成,相互勾连的绿色、蓝色基础设施就是这种理念最直接、感性化的表达。此外,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加入由不同地区的自然关照者——不管是专业人员还是志愿者——所提供的经验知识地图。
我们不是要“冻结”一种“野生”的自然环境、依靠人类的参与来保持其原始状态不受改变。与此相反,我们要保护的是当地原有的生态“进化能力”。这意味着维持原有实践;这意味着自然保护区的统一管理将充分平衡各地区根据本地特色制定的特定管理方式;这意味着对多样化空间所进行的复杂管理。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人类并不处于自然之外,而是自然中的一员,是自然之中活跃的一份子,如果人类采取明智的行动,对自然进行“合理的利用”,就能为自然带来益处。[22]
对自然环境多样性的充分重视也不能忽略文化的因素,甚至可以说,这一联系的存在恰恰是因为生存环境不仅指明了我们所在的位置,还规定了在此处存在的法则、在特定土地上栖居的方式。
[1] Michel LUSSAULT, Hyper-lieux. Les nouvelles géographies de la mondialisation, Seuil, 2017
[2] Alexander FEDEREAU, Pour une philosophie de l’anthropocène, PUF, 2017
[3] Aurélien BOUTAU, GONDRAN, L'empreinte écologique, La découverte, 2009.
[4] Annales de géographie : agricultures et villes : des articulations renouvelées, N° 712- 2016/- Armand colin.
[5] Le politique, trad. E. Chambry, Garnier-Flammarion, 1969, 276b-c, p. 196.
[6] Op. cit., 282 d, p. 207.
[7] LUSSAULT Michel, De la lutte des classes à la lutte des places, Grasset, Paris, 2009, p. 218.
[8] Moderne, Mondes Flottants, Editions Les presses du réel, 2017, p. 260.
[9] Jean-Jacques WUNENBURGER, « De l’utopie à la ville habitable » dans L’imagination géopoïétique. Espaces, images, sens, Editions Mimesis, 2016, p.225.
[10] Casterman, 2017
[11] PLATON, Protagoras, trad. A. Croiset, Belles Lettres, 1923, 322 d.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见《柏拉图全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322 d. 。此外,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有两段论述(771e-772b、841a-b)都是关于克己心问题。这里的克己心并不仅仅是社会文明规条的体现,而是一种特殊的美德,即对他人判断的内化。它影响到邻里关系、空间上的接近,以及今天城市生活熙熙攘攘中必不可少的经验(公共交通、大厅等)。在这里我要感谢Jean-François PRADEAU提醒了我这些文本的相关性。
[12]La société décente, ed. Climats, 1999.
[13] L’insurrection des vies minuscules, Bayard, collection Les révoltes philosophiques, 2014.
[14] L’insurrection des vies minuscules, op. cit., p.131.
[15] Hartmut ROSA, Accélération, Une critique sociale du temps, trad. Didier Renault, La découverte, 2005, p.105.
[16] Gaston BACHELARD, La flamme d’une chandelle [1961], Quadrige/PUF, 2008, p. 90.
[17] Thomas et le voyageur : esquisse d’un jardin planétaire, Albin Michel, 1997 ; Le jardin en mouvement, Pandore, 1991
[18] Eloge des vagabondes, Herbes, arbres et fleurs à la conquête du monde, ed. Nil, 2002.
[19] Merleau-Ponty, Maurice, La natur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95, p. 169
[20] Marion WALLER, Artefacts naturels. Nature, réparation, responsabilité, Editions de l'Eclat, 2016
[21] Tetsurô WATSUJI, Fûdo, le milieu humain, Commentaire et traduction par Augustin Berque, éditions du CNRS, 2011;和辻哲郎,《風土:人間學的考察》,东方出版社,2017年。
[22] Catherine et Raphaël LARRERE, Du bon usage de la nature, Pour une philosophie de l’environnement [1997], Champs/Flammarion, 2009, p. 289.
[23] Roland SHAER, Répondre du vivant, Paris, Le Pommier, 2013, p. 37.
文中使用的图片来自网络
END

推荐书目



左:《空间的诗学》【法】加斯东·巴什拉
右:《梦想的诗学》【法】加斯东·巴什拉

知识星期,一周即焚

公众号后台回复“人类世”,获取所有推荐书目的电子版~知识星期每周不定时更新,一周即焚,获取知识请勤奋!

作者介绍


曲晓蕊
法国里昂让•穆兰大学哲学系现象学与当代美学方向博士研究生。

雷锋福利

欢迎添加“全球知识雷锋机器人”,邀请您加入欧洲知识雷锋粉丝群,由欧洲大牛作者坐镇,会热心答疑解惑、学习讨论,快来加入组织吧”(•̀ᴗ•́)و ̑̑


配乐:曲晓蕊
排版:艺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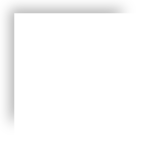
往期回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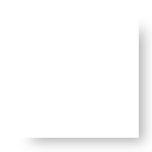
建筑专栏
北美讲座
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康奈尔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Paola Antonelli《人类终将灭绝,而设计师能给人类一个优雅结局?》
哥伦比亚大学:
Cooper Union:
纽约州立大学:
伯克利大学:
莱斯大学:
加拿大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麦吉尔大学:
欧洲讲座
代尔夫特大学:
米兰理工大学:
佛罗伦萨大学:
AA:
Ricardo Bofill《放逐柯布的奇幻城堡——里卡多·波菲尔与永生纪念碑》北欧阿尔托大学:
ETH:
门德里西奥建筑学院:
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
Pascal Flammer《探寻意义的筱原建筑——Flammer谈筱原一男》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KTH:
马拉盖建筑学院:
Patrik Schumacher《后扎哈时代的舒马赫宣言(上)》
Patrik Schumacher《后扎哈时代的舒马赫宣言(下)》
剑桥:
巴黎建筑与遗产城:
Juhani Pallasmaa《流水的网红建筑,铁打的阿尔托》
亚洲讲座
东京大学:
京都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清华大学:
MVRDV《MVRDV能把城市带到多远?》
中央美术学院:
Rem Koolhaas《普通乡村——库哈斯在央美究竟讲了什么?》
澳洲讲座
墨尔本大学:
悉尼大学:
Ferdinand Ludwig《你一定没见过的活体建筑》
Tom Leader《逝去的人、火车与码头,因他再一次停留》
哈佛大学:
博洛尼亚大学:
Massimo Montanari《吃货的中世纪》
未来专栏
伯克利大学:
Framelab研讨会: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雷锋第38篇文章:忧虑的异托邦 | 你不曾看到的社会空间真相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