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计》的变形计 | 土逗谈



作者 | 吴畅畅
编辑 | 耄耋
美编 | 黄山

《变形计》时隔2年后再次上演,只不过这次的播出平台从湖南卫视换成芒果TV。芒果TV复播的《变形计》3.0(已经播出四集),虽然保留原有的城乡少年互换生活的故事原型,但它与此前的1.0和2.0版本相比,农村女娃丽姐和南京顽劣少年陈新颖的“搞笑”言论,以及节目后期剪辑(尤其是花字和BGM背景音乐)的娱乐化,竟然成为节目在社交媒体上的宣传噱头。一档客观上曾经承载着记录中国城乡分裂与差别的准纪录片,如今改头换面,利用社交媒体与弹幕文化重新装点城乡少年互换生活的沉重故事,令人感慨!

变形计1.0:普通人的奇迹!
如果单纯从技术层面衡量,湖南卫视2006年4月首播的《变形计》与英国第4频道的《换妻》节目一样,同属生活互换类真人秀,侧重于不同个体与新的生活环境之间矛盾的铺展,而且在一种“可控的”结局的基础上展开“失控的”碰撞——这也正是此类节目引发关注的重要原因。在节目的后期剪辑过程中,每一集都是在已经全盘知晓结果、制作方事先设计或符合观众心理期待的前提下,完成剪接并按照戏剧化的程序引向最终结局。最终结局就是“互换成功”,而“互换成功”的标准是,一定要“拍到城里孩子内心有了改变”,只要“学会了感恩,就是成功”。
那么,为何要做好“长线作战的准备”,在城市孩子身上人为地制造“内心改变”,以制作一档凸显“质朴的人文关怀”的纪实类专题节目?2005年《超级女声》之后,湖南卫视高层有意识地计划“向高端受众转移”,以部分抵消因《超级女声》而形成的“低俗”、“低龄”的文化标签和公共形象。为此,湖南卫视启用前湖南经视制片人李泓荔,远赴英国筹备一年后推出《变形计》,试图用互换的形式“真真切切地”记录下存在于“我们身边的一个秘密社会”,进而打造“贫富差距日益增大”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影像版”的《变形记》。第一季四集节目原本包括母女、村官与村民、城乡教师互换等内容,不料,讲述城市网瘾少年魏程与青海农村娃高占喜的互换故事《网变》播出后竟然受到中宣部、公安部的电话表扬,并获得湖南卫视2006年一号宣传嘉奖令。宣传部门的肯定、收视率的压力以及原湖南卫视新闻中心多个团队的相继加入,推动《变形计》的重心从阶层、代际与官民的互换体验,逐渐偏移到城市与农村孩子的生活互换。《爸爸去哪儿》前总导演谢涤葵作为《变形计》早期的主力编导之一,曾撰文指出《变形计》是“我们在偏远山区挖到的一剂良药”,它应当承担“专门治疗让很多家长失去信心的城市独生子女病”的社会责任,使这些“娇生惯养、五谷不分、好逸恶劳、精神萎靡”的城市独生子女“内心有所触动” ,即便这样,节目“最受益的肯定还是农村孩子”。从“阶层的互动或流动”甚至“冲突”的“真实”记录“窄化”为直击城乡差别这一“社会现实”的“纪实节目”,随后“软化”为服务于相对富裕的城市中产阶层(“家庭条件一定要是中等偏上的”)的、“无害的”教育手段,节目目标的设立及其转变,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在既定的宣传口径之下,节目有些反直觉地向观众尝试“兜售”一种基于代际差异与城乡差异的移情,以努力由上至下地实现跨阶层沟通与理解这一“自赋的”社会干预(social intervention)任务。

变形计1.0:普通人的奇迹
从2006年第一季到2008年第五季,《变形计》在全台甚至整个电视业娱乐化的大环境下,始终没有放弃“原生态的”记录方式,坚持“粗剪”而非凭借综艺化的“字幕、画外音”的后期工作制造笑点,诚如担任前五季节目导演(制片)的梁书源始终拒绝《变形计》走《爸爸去哪儿》那样的娱乐大众路线。
第一季《网变》和第二季《成长之痛》两期节目,都“真实”记录了一个涉世未深的农村少年与一个网瘾深重、并拒绝与父母沟通的都市少年之间互换生活后所发生的各种情况。这从根本上奠定了节目的未来走向:1)叙事遵循了一种日常的戏剧化模式—— 凋敝的农村与光怪陆离的城市,以及通过快速镜头喧闹地展现了裹挟着欲望与享乐主义的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进而2)节目有意地在极度不发达的乡村地区与转型中的城市之间制造某种张力,而被人为局限在生活环境的变化网络与暂时交换的青春岁月中的两位少年,则成为了这种张力的再现客体;并且3)城市与农村少年的角色规定成型—— 来自乡村的孩子心智成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而成长于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少年却玩世不恭,亟待被规驯—— 贯穿至第十二季;由此4)节目经典的且充满“正能量的”戏剧情节关系(crisis structure)固定下来,即当城市少年遭遇到乡村地区贫穷的生活条件和设备简陋的教学设备时,心灵受到撞击,幡然醒悟,回家后缓和与家人的紧张关系并开始在学校发愤图强(例如第一季《网变》中魏程打工挣钱给青海家庭的爸爸,最后离别下跪叩谢;第二季《成长之痛》中胡耿和父亲最后冰释前嫌等)。
然而,这一明显迎合大多数拥有问题少年的城市家庭观众的需求与趣味的行为,仍然低调隐晦地“再现”了农民工与留守儿童这两个当代中国的底层群体真实的生活境况或工作条件。在此之前,他们要么长期在电视上处于隐形状态,要么在新闻与时事报道中享有严格框架的可见性。如今,这两个被迫隔离的社会群体所遭受的情感创伤与精神失调为这个无剧本真人秀节目准备了最原始的一手材料。至少,第一季至第五季的《变形计》向我们提供了观察乡村的另外一个视角:今天的乡村和城市是相互塑造的,我们无法离开乡村去理解城市,也无法离开城市去理解乡村。它的出现表明,在高层“热衷于将西方商业化模式本土化,并有意培养该集团在未来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媒体集团”的背景之下,湖南卫视新闻从业者“当中大多数人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还存在点铁肩担道义的激进,始终对弱势群体保持关注” ——这或许是对《变形计》2008年停播前的口号“普通人的奇迹”的最佳注解。

变形计2.0:勇敢者的游戏?
虽然2007年《变形计》在新加坡亚洲电视节上斩获“ 最佳真实电视节目奖”,它还是因故逐渐淡出荧屏。直到2012年,湖南卫视被禁止举办歌唱类真人秀节目、“限娱令”下发导致频道编排战略的整体变革,以及真人秀节目的日渐崛起,让湖南卫视高层决定《变形计》以周间日播类节目的形式回归,随之改变的,是节目的口号 ——“一份来自远山深处的力量”。2014年寒假第7季播出时,无论在网络点播量还是首播收视表现上开始呈现“火了”的态势。但这个讲述“王子与贫儿”的现代中国版故事在复播后的阶段(2012——2015)里1)常规化与娱乐化的制作流程,释放了一种“受娱乐冗余所负累”的媒体情怀;2)社交媒体的发展,以及互换主角特别是城市孩子的“表演”及其动机暴露了节目“形式上的严重僵化”。
一方面,《变形计》的数位编导在公开场合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前期寻找城市少年作为节目参与者的过程十分困难,“曾经有三个月到处去找人,都没找到一个适合节目的孩子”。不过,随着2014年节目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城市少年在了解该节目的流程与性质后“抱着想红的目的”报名《变形计》,希望“在参加节目以后利用高涨的影响力牟利”,节目客观上为城市“富二代”提供一条另类的成名途径。无论是第五季《少年何愁》的易虎臣,最引发争议的第七季《山路弯弯》李锦鉴还是《母爱的呼唤》里跋扈的施宁杰,甚至是第十二季《青春的方向》“星二代”林子濠,他们只需要在镜头面前表演出节目组和观众所期待的“浪子回头”的桥段,就能比同时参加互换的乡村“穷二代”更能赢得受众的好感。更何况他们善于经营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节目一旦播出以后,拥有的粉丝数量急剧上升,他们一跃成为具有社会知名度的青少年,潜在的商业效应也随后被全面激活。这与早期《变形计》的主人公在节目播出后所收获的关注度明显有别。

变形计2.0:勇敢者的游戏
另一方面,《变形计》的常规化播出给节目组带来巨大的生产和制作压力——如何在7天甚至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孕育”或“爆发”出城市少年应然的“内心改变”,而非实然的“平淡”进展,谢涤葵主张应当“设计任务、真实记录”,以符合湖南卫视高层所要求“真实剧(reality drama)的感觉”。从李锦鉴和施宁杰的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节目组在既定的戏剧情节关系的基础上“强行”叠加了一整套严丝合缝的叙述结构:“农村是一个田园牧歌般的存在……农村有许多城市不具备的人性之美,比如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对城市观众来说(它)无异于一个纯净心灵的乌托邦”。在这套逻辑的调教下,编导削足适履地制造和引导“有意义的”事件,捕捉和选择极致的情感表达的时刻:不仅凋敝、衰败、贫穷的农村被节目制作者喧宾夺主地征用为帮助城市少年获得“善的品性”或“德性”的镜像式的空间,他们更放任城市少年以内化的“东方主义”视角随心所欲地“体验”乡村;“农二代”或“穷二代”的“苦”非但没有透过媒体被完整地释放出来,他们的发声反而再次沦为城市中产阶级“三观”包裹下的社会向上流动的个人奋斗故事:几乎每位来到城市的乡村少年都会被刻意安排“体验”底层闯荡的艰辛生活。节目剪辑有意逢迎这样一种被结构化了的、不平衡的立场,从而使每一场生活互换显得更加具有目的论的色彩,更加刻板敷衍,却也更加化约易懂。
与之相对应,原本节目中客观再现的市场化机制下中国不可逆转的城乡分裂与贫富分化的图景,竟悄然返回到第一任导演李泓荔制作《变形计》时所期待记录的“秘密的社会”,即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收入差距与矛盾。只是,如果让城市里的“蚁族”青年、或遭受大规模无产阶级化的家庭的孩子而非富二代、星二代与乡村少年互换,是否更能暴露中国三十余年城市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对城市与乡村的双重破坏?

变形计3.0:网综化的城乡互换故事
2017年复播的《变形计》尽管仍然以城乡少年互换生活为原型,却在这前两期中采用了大量搞笑综艺的后期剪辑手法:从一剪梅的配乐,到张迪发脾气时的手游界面,从陈新颖进村时后期配上的“生命值”到“瞻前顾后式”、“自由落体式”、“自我鼓励式”等花字。这与90后一代进入节目后期剪辑队伍密不可分。这些年轻的后期制作者利用他们熟悉的网络词汇重新包装故事,增加该节目的不少笑料,顺理成章地成为节目的宣传卖点:例如节目组把陈新颖等人在镜头面前所表现的烧野草、撕棉被、偷钱抽烟等顽劣行径,视为节目的“笑点”;将陈新颖的不适应称为“变形吐槽大会”;非但没有批评张迪的粗鲁行为,反而配上“碾碎他们”的画外音,把它们与网络流行元素结合在一起,无形中使他们的行为变成了合理的玩闹。这一娱乐化与网综化的举措非但不是创新,制作者自作聪明地以此消解了节目原本的定位与诉求。
然而,看完前两集,笔者的疑问在于,如果《变形计》1.0的主角是城市问题少年,2.0的主角是城市富二代,那么3.0的主角是否存在变形的必要?特别是《变形计》真相版的推出,加深了笔者的这一认知。陈新颖的家庭固然不完整,但是第一集里他和妈妈的怒目相向甚至动手争执的画面,源自于妈妈阻止他联系爸爸的事实,所以到底是孩子需要变形,还是父母本身教育存在问题?

变形计3.0:变身网综
接下来的疑问是,2017年《变形计》究竟是城乡青年的生活互换变形,还是普通(而非问题)城市青年的乡村生活体验真人秀?作为城市青年芸芸众生的一员,陈新颖、张迪等城市青年对乡村的一无所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心理定式与认知框架,以及在遭遇乡村贫困生活时的抱怨与毫无耐性,无形中使他们成为了该节目网络受众的代言人,后者在与之同龄的后期剪辑组成员的“帮助”下,借助城市青年的眼睛,猎奇地观看与他们生活相去甚远的乡村生活,在产生通感效应的同时,强化了城市生活的正统性。
或许这么理解,《变形计》3.0在社交媒体上的走红,向我们展示了网络流行文化和城市青年代际文化遭遇乡村生活时的种种“变形”和“不适应”,但年轻和网综化的节目组,已经不愿意甚至无力、无法处理这一宏大的命题,不如投机取巧,淡而化之,这一看似软化实则激进的处理手法,它的欲求已不再着眼于未来,不再立基于守护乡村的姿态,而仅仅立足于当下,当下城市文化以及与之相连的新媒体技术对乡村生活的收编与改造。在此基础上,城市青年、网络受众与后期剪辑形成相对坚固的收视“同盟”。只是,这样“变形”的《变形计》还能走多远?
(龚蕾对本文最后一部分亦有贡献,在此感谢)

本文首发于土逗公社
转载请联系土逗获得内容授权
土逗谈
咦?有大事发生?有劲爆热点?
它从哪里来?它往何处去?和我们啥关系?
嗯…我们一块儿谈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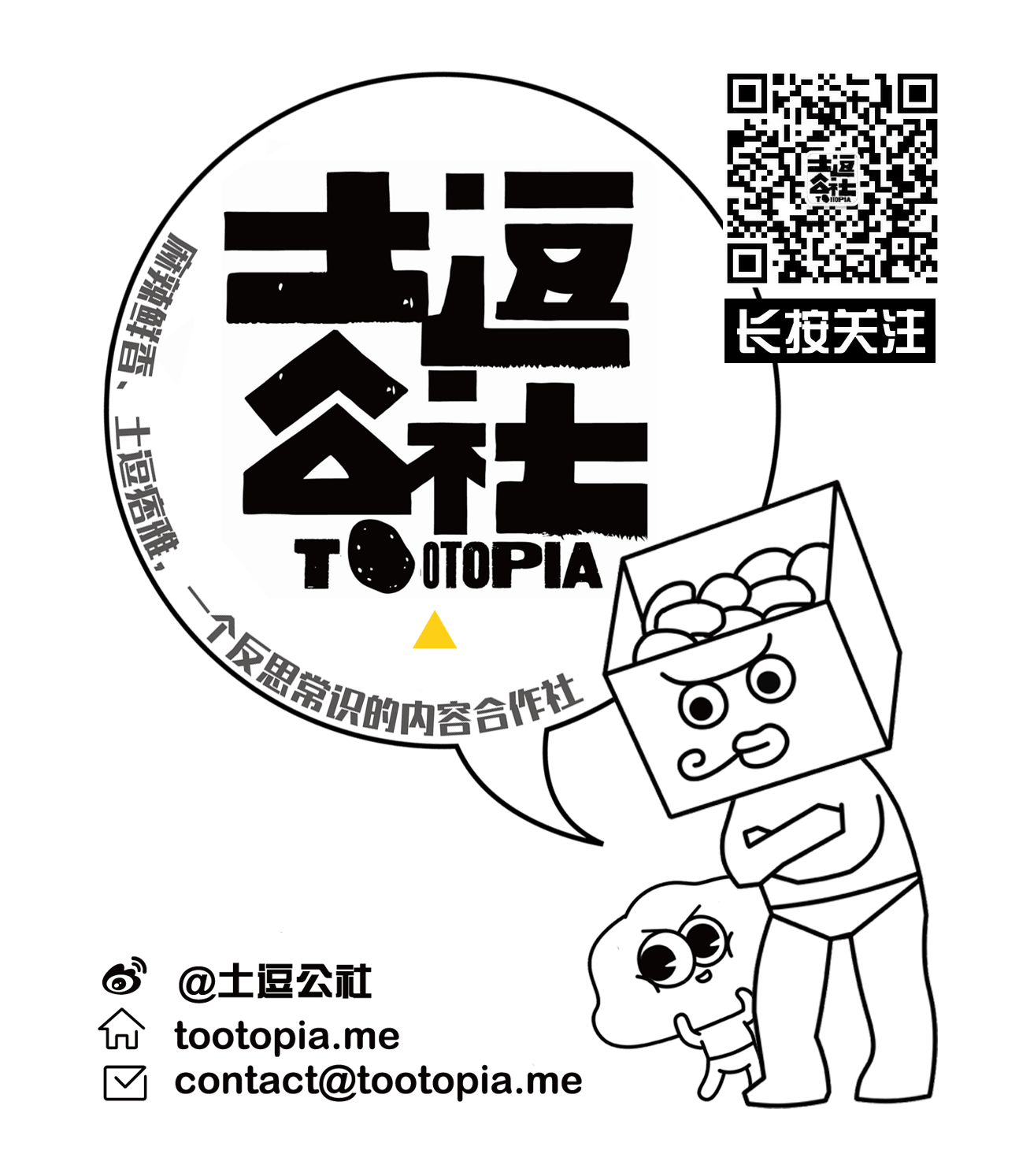
漫画:发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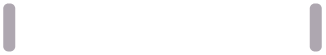
点击关键词查看更多
这里“阅读原文”,查看更多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