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葬礼上团聚 在生活中别离 | 土逗事



作者 | 杨猛
编辑 | 小蛮妖
美编 | 黄山


这一天终究没能和往常一样
“大娃,你爷爷吃不下东西了,看来这两天可能有点危险……”
挂了父亲的电话,我就联系朋友去家里给爷爷装食管,没过一会儿就接到堂弟的电话:“哥,爷爷走了……”
“嗯。”挂了电话,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妈妈与我连夜赶到家时,已经快凌晨4点了。父亲、弟弟和堂弟在轮流守灵。
灵堂中央布置着做法事的道场,爷爷的棺椁放在灵堂右侧的两张长条高凳上,下面的过河灯一直亮着,菜籽油在灯草芯上燃烧起淡黄的火苗微微摇曳着。棺椁前的桌子上摆放着一斗金黄而饱满的玉米粒,里面插着香蜡,三条细细的青烟轻柔的腾起,散开,淡去。棺椁与桌子间夹着一张木门,上面挂着爷爷的遗像,面容红润,溢着微笑。
“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晚了”,我们端庄的跪在爷爷的棺椁前上香烧纸钱,告诉他。开口的那一瞬间,谁也没能抑制住自己的情绪,路上小叔的叮嘱似乎从未发生过,任凭外面怎样咆哮。爷爷依然静静的躺在里面,一声不吭。也许依然面容红润,溢着微笑。
爷爷虽然86岁了,但身体还算硬朗,记忆力和视觉比很多年轻人还好,只是听力下降了,牙齿也快掉光了,行动也缓慢了。
今年三月的家乡和往年一样,春暖花开。11日早晨,爷爷准备和往常一样,缓缓起床,拄着拐杖迈着小碎步坐到门口的椅子上,用热水洗脸后泡脚,同时抽上一支烟,悠然的欣赏着屋外的风景和路过的行人,就这样开始他一天的生活。
可是,这一天终究没能和往常一样,甚至从此以后的每一天,都没再能和往常一样。就在爷爷从床上下来的那一刻,一个不小心没扶稳就摔倒在了床前,从此爷爷瘫痪在床,再没能站起来过。

“只要背睡破皮了,也就快了”
在爷爷的这一生中,还有一次卧床两年半的经历,那是在土地包产到户的第二年,从小帮地主家放牛的爷爷怎么也没料到,在自己步入老年时却被邻居家的老牛用头顶着从山坡上摔下来,伤得特别严重。
那时农村医疗条件很差,草药和药酒是最常见的药品,很多人都认为爷爷凶多吉少,可他瘦弱的身体居然战胜了病魔。爷爷的左膝盖下方留下了比巴掌还大的一块伤疤,像青花瓷上的花纹一样,每当卷起裤管,便格外抢眼。
在这个春天里,和爷爷一样不幸的还有两位老人,他们年龄都比爷爷小,都在摔倒卧床一周左右相继离去。农村医院不愿意收治高龄病人,农村空巢老人的特殊照顾,几乎都还是一片空白。

空巢老人 图片来源:网络
爷爷摔伤时堂妹正好在家休假,之后几天弟弟也从宁波赶回去了。堂妹一直从事老龄医务护理工作的堂妹,正好发挥了自己的专长,帮爷爷减轻了很多痛苦和心理包袱,渐渐增强他活下去的信心。
“爷爷刚睡着,这些天疼得他一直在呻吟,需要不停的给他捏腿才能舒服点,一晚到亮难得休息上这么一小会儿。”我和堂弟走进爷爷的房间时,坐在一旁的堂妹小声的告诉我们。
“吃东西了吗?”堂弟问。
“吃不了干的,刚给他冲了半碗奶粉,吃了两口就不吃了。”
爷爷耳背,我们这样的对话即便在他醒着的时候也根本听不见。他咧着嘴,微微偏着头,睡得很香,显然是被疼痛折磨得累坏了,当房间里静下来时,便回荡着若有若无的细细鼾声,分不清是从空旷的嘴里传出,还是从鼻孔里飘来。
“大娃,你回来了。”爷爷侧着脸,一双小眼睛出神的盯着我,神志清晰地问。
“嗯,我回来了,爷爷松点没(好点了没有)。”我有些意外,语无伦次地支吾着,但爷爷没反应,可能是没听到,我又凑近一点大声符了句:“您松点没有。”
“嗯……,好不起了”爷爷皱着眉苦着脸失望地看着我,迟缓地呻吟着回答。接着又问:“你姑娘(女朋友)呢?”
“她厂头忙走不开,二回再来看您。”虽然说的都是实话,身体却像被电击了一样,费了很大劲才把这句话说完。
我是他长孙,我的婚事也是他这些年最操心的事,每次回家,他都拉着我:“孙儿啊,晃不得(大意不得)了哦,你个人的家式(婚事)要打紧哦。”爷爷的手指像坚硬、冰凉的枯树枝一样,一节一节的散落在我的手心,敲击着连接心弦的每一根神经。他也会不厌其烦的在亲人面前念叨这件事,像是给他们下命令一样。
这是爷爷平生最大的心愿,我没能为他实现,但愿回到他爸爸妈妈身边时,祈祷他不会受到责备。
“给您冲点奶粉哈。”爷爷轻轻地摇了摇头示意我不用。
“他不吃,都是逼着喂才勉强吃两口。现在可以给他喝点水,一会儿再喂奶粉。”堂妹安排道。
谁都明白爷爷不吃东西是怎么回事,不只是大小便不能自理这么简单。偶尔,我们在屋外还能听到爷爷向奶奶絮叨:“久病床前无孝子,拖累年轻人啊。”“不知道还要熬多久。”
后来,他也会时不时问我们,“孙儿,你给我看看背破皮了没。”小时候,爷爷经常慢悠悠地给我们讲他照顾过的那些临终前老人的故事:“只要背睡破皮了,也就快了。”

图片来源:网络
给爷爷洗头很不方便,我们四兄妹就趁父亲不在时和爷爷商量着把头发给剃了,用我的剃须刀剃,我们一人拉着围布接头发,一人用手托着头,一人操刀剃发,花白的头发随着呲呲的声音被推下来。父亲觉得剃头一定得挑个吉利日子。我们觉得他这样太迷信。但在灾难面前,人们往往希望能在迷信里找到哪怕一丁点儿的慰藉。
堂弟点燃一支香烟,送到爷爷的嘴里,再抽出一张抽纸铺在爷爷的胸前,用来收集掉下来的烟灰,爷爷用左手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时而送到嘴里轻轻地吸上一小口。
他把剩下的半支烟伸过去,示意着不抽了,堂弟从案台上拿起一支铝制的钢笔帽,把烟头塞了进去,一会儿烟头就熄灭了,想抽的时候再取出来点着了接着抽。这个抽半支烟的习惯已经保持好几年了,那支笔帽里早也被熏得漆黑,并凝固了一层黏黏的烟油。
“爷爷,来,自己端着吃。”堂妹将小半碗饭菜和筷子递到爷爷的手里。
渐渐的,爷爷可以吃下一些饭了,堂妹便决定逐步帮助爷爷恢复一些简单的自理能力,这样可以增强爷爷的自信心。
虽然吃起饭来跟小孩一样嘴角和碗边都粘满了米粒,但看着他缓缓的蹒跚着筷子把饭一口口的送到嘴里时,内心是很欣慰的。因为他向你展现了生命中最坚强的一面,让你看到了希望。
喝水时也不再用勺子喂了,而是给他吸管自己慢慢喝,想喝水时自己就可以取到。每次只要能多吃上一小口,多完成一个小动作,我们都会拼命地表扬他、鼓励他再接再厉。
陪爷爷过完生日没多久,我和堂妹都相继回到了工作的城市,其它亲人也陆陆续续回家探望后又离开了,只有父亲、弟弟和堂弟继续陪伴和精心照顾着爷爷,直到爷爷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

也许爷爷正在思索着,让自己回到什么时候好呢
爷爷下葬的日子选在归西后第四天的早晨,这几天我主要负责守灵,按习俗灵堂内必须要一直有人守着,其实也没做什么,无非就是续香、烛、油灯,磕头这些事。
也许爷爷正在思索着,让自己回到什么时候好呢。
回到给地主家放牛的童年?白天放牛晚上磨面,推磨时在磨盘上插一柱香,借着香的微光干活,也用香的燃烧记工时。地主一家吃好的,自己却吃得很差。童年太苦还是不回去了吧。
那回到年轻力壮,正赶上国家大搞建设的年代?那时候爷爷应征参加公路建设,全靠人力在荒山野岭抬石头架桥垒路。没有工钱,哪天能吃上红薯土豆,就算是改善伙食了。但大伙都是冲着填饱肚子去的。

图片来源:网络
夏天蚊子多,冬天冻得只能靠拼命干活来取暖。晚上盖秧毡(用稻草做的被子)又扎又硬。虽然那段经历很苦,但幸运的是爷爷最终完好的回来了,还带着一本据说可以在六十岁时就能到民政局领钱的证件回来。可惜那证被淘气的小叔从箱子里翻出来玩耍弄丢了,后来也没有补办上……小时候,爷爷常常给我们讲这些故事,他常说:“屋头有粮,心头不慌。”
建议爷爷还是回到勤劳种田的时候吧,那时我已经开始记事了。虽然也很辛苦,但田间地头,总能看到爷爷一边勤恳种田,一边和乡亲们对着山歌的情景。每次和爷爷出行,他都会带着我一起,移走滚落在乡间小路上的每一块绊脚石,他说:“方便别人就是方便自己。”

你出门都一千零二十三天了
我喜欢家乡四季分明的气候,喜欢家乡的空气、溪流、鸟鸣、一草一木,更喜欢家乡纯朴的乡土人情、团结的家族文化和近乎自然规律的慢节奏生活。
在我走出高中的校门后,并没有像大多数同学一样,寻着父辈的脚步迅速混流到世界工厂的生产链上。但最终还是难逃厄运。因为家乡经济水平低,就业机会少,没关系也没经验,很难还上我上学时亲戚和族人支持的近一万元学费。在家折腾了一年多后,还是无奈地选择了进城打工。
我起初的计划很简单,就两个目标:一个是还债,另一个是攒点本钱回去开一个乡村主题的影像工作室。债是省吃俭用还上了,可本钱却怎么也攒不够,越到后来考虑的事情会越多,渐渐的也认识到创业并非易事,这事儿也就搁置了。
前几年我会时不时的在招聘网站上寻找返乡就业的机会,几次面试后,发现要么是别人对我不满意,要么是我对工作内容不喜欢。经过一次次折腾和碰壁,现在已经不再考虑回去的事了,而考虑更多的是怎么在城市留下来。
正殿(葬礼中接待宾客的日子)那天十分闷热。灵堂里燃烧着灯烛纸钱,温度更高,下午刮起了风,像是要下雨了,看样子应该会凉快些,远处传来似有似无的雷声,但我并没有察觉到,可能是被锣鼓声中和了。
婶子神情凝固,快步跨到灵堂前注视着我交待到:“大娃,快给爷爷打声招呼,响雷了,叫他别作怪啊。”我一脸茫然,惊愕地望着婶子,脑袋一片空白,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放心,现在有这个,没事的,在这儿趟上半个月也作不了怪了。”大伯指了下棺椁旁的制冷机,比划着手指向我们解说着:“现在里面至少有这么厚的冰。”
老家农村还沿用着土葬的习俗,棺椁一般用杉木制作,不能使用胶水、铁钉和油漆,通常会在棺椁外表刷上一层精炼的土漆。下葬的日子是通过死者子女的生辰八字推算出来,很是讲究。子女越多日子越难挑选,所以一周以上才下葬的情况非常普遍。

图片来源:网络
当遇上夏秋季节,身体一般都已经腐烂了。由于受到温度和湿度的大范围波动影响,尸水有时会通过棺椁的缝隙渗出来,特别是遇上雷电的震动时。以前,乡亲们就称这种现象叫“作怪”,所以需要在打雷时安慰亡灵。
离发丧还有两个多小时,终于可以开棺了。所有亲人都静静地围在爷爷的棺椁旁,凝视着爷爷安祥的遗容,为他做去往天堂路上的最后准备。两个椰子大小的陶瓷衣食罐里,装满了干粮和盘缠,还有各种新生活的必须品,用红布和麻线封系着,放进爷爷头上方的棺椁角落里。父亲揭下房上的三片老瓦,用纸钱擦净,一片横枕在爷爷的头下,两片竖排着各护在一边。
虽然大伯吩咐我在凌晨两点时就断电解了冻,但取走冷冻片时,被子上还是残留下不少坚强的小冰晶。爷爷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显得蜡白,被脸颊撑出一副枯瘦的轮廓。他那双现已经脱水内陷的小眼睛虚闭着,窥视着我用手指捻起的小冰晶,窥视着想要帮他合上张开的嘴巴的小叔,窥视着为他整理衣角及离行前每一个细节的亲人们。
我抚摸着爷爷冰冷的身体,就这样即将和他永别了,他的一生已经走完,他又将会到哪里去呢。我不知道,也许爷爷也不清楚他的人生留下了什么,但我知道,他为我留下了什么。

家——更像是一个临时驻足的客栈
爷爷下葬的第三个早晨,是第一次祭祀,称作“护山”。简单的仪式后,我们在坟上又夯了一些土,在坟头上各留下了一把花圈和花伞。其余的与抬棺椁的扛木,绳索,棺罩等一起清理到了一旁,用火点着。伴随着火势越响越烈,火苗窜起三米多高,热浪随风翻腾,散发着塑料烧焦的味道。

图片来源:网络
“大娃,你以后还是回来吧,尽量离家近点,好照看到家里。”小姑红肿着眼睛,眼泪蹭得满脸都是。每次哭丧后,她伤心又自责地找我商量,希望能在我身上挽回些她永远挽回不了的东西。
小姑和我同一个属相,刚好大我一轮,从小就特别疼爱我。她在90年代和父母去浙江打工,便留在当地结了婚。“嫁得太远了,即使再想家想亲人,也不可能随时想回来就回得来,回一趟家太不容易了。”
那几天,她一直自责在爷爷卧床后没能一直陪伴在身边,而我将来的家,也和她一样选择了一个同样遥远的地方。在小姑的内心深处,她不希望这种因为距离所造成的亲情的缺失,继续笼罩着这个家庭。但,这或许已经无法再挽回了。
次晨,我、小姑、小叔和婶子坐上了开住宜宾的汽车,他们订了傍晚发住杭州的火车,经过四十个小时的颠簸后,再中转几个小时的汽车就可以到达工作地了。而我订了下午发住广州的火车,三十六个半小时。再中转两个多小时就回到深圳了。
至此,家里只剩下五十多岁的父母,其他亲人都已陆续回到各自工作的城市。每次回家,就像是一次有待着完成的任务。家——更像是一个临时驻足的客栈。
汽车在高架上腾云驾雾,周围都是高耸林立的楼房。这座城池里,近四十年的开放史,也是我们跨省务工的流动史,足足两代人的青春奉献和骨肉分离。
在我外出务工的第三个年头,我第一次踏上与亲人团聚的回乡路,那是11年的元旦。
“大娃,从你起身那天算起到今天,你出门都一千零二十三天了。”爷爷不紧不慢地比划着手指微笑着看着我。我们一家人除爷爷外,都有过外出的经历,但我们谁也没在意过自己离开家多久了。只有爷爷守在家里扳着手指头天天盼着亲人的平安归来。

本文首发于土逗公社
转载请联系土逗获得内容授权
土逗事
故事从来不只是发生在聚光灯下,
茫茫时间流过,遥遥路途走过,谁不是有故事的人?
狂放的笑,纵情的歌,奔涌的泪;
刻骨铭心的爱,怒发冲冠的恨;棰心的痛苦,难言的悲愁,幼稚的相信,单纯的盼望;一夜白头的苦闷,付之杯酒的隐忍,千回百转的纠结,走投无路的绝境;抑或是平静的孤独的似乎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一天又一天⋯⋯在这里,土逗等待分享你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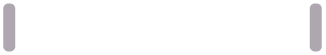
点击关键词查看更多
这里“阅读原文”,查看更多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