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网民,还是被剥削的“数字家庭主妇”? | 土逗思



作者 | 虞小欢
编辑 | Catherine
美编 | 黄山

每天早上醒来,相信很多人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登录各种社交软件打卡:打开朋友圈点赞好友的状态,浏览公众号转发10万+文章,刷微博看新闻参与讨论社会热点。然而忙得不亦乐乎的你可曾想过,每一个“赞”、每一次订阅、每一条搜索都是你作为免费数字劳工(digital labor)被互联网公司悄悄剥削的剩余价值。当然,你可能觉得这种上纲上线的论断和现实生活差距太大,毕竟你觉得自己的网络生活乐趣无穷。

点赞,图片来源:网络
《女性主义,劳工和数字媒体:数字家庭主妇》一书有助于破除以上迷思,在这本书中,贾勒特•贾勒特(Kylie Jarrett)细致梳理了围绕数字媒体研究的各种理论分歧,考察了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被资本吸收的过程。基于女性主义的范式,透过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的视角,她提出一种思考消费者劳动力(consumer labor)的新模型:非物质商品的生产间接地剥削了用户的剩余价值。“数字家庭主妇”一词在书中不仅是用来形容以数字媒体用户为代表的情感劳工(affect labor)的修辞手法,更彰显了此书旨在建立马克思主义女权思想和自治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间的对话。

《女性主义,劳工和数字媒体:数字家庭主妇》,图片来源:网络

上网就像做家务,都是免费劳动
在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人们在虚拟网络中留下的痕迹都被各大商业公司采集成为用户数据。公司通过出售和交易这些数据来获取收益。你每次“谷歌一下”都是在训练网站的算法,告诉它你的口味和兴趣,帮助它建立个人和群体层面的消费者需求地图,以便于它更好地服务你,也更好地服务那些想要向你推销产品的广告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达拉斯•史密斯(Dallas Smythe)就颇有洞见地提出了“观众商品”(audience-commodity)的概念:媒体产业的主要动力来自出售观众给广告商[1]。 在Web 2.0时代,互联网经济同样高度依赖广告产业,商业媒介公司更加强化了对数字化观众商品(digital audience commodity)数据的搜罗,细致到网民的一举一动都能被即时准确地捕捉到。
然而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表示,这些在劳动合同之外的“劳动”、没有正式工资关系的“劳动”都不符合严格的劳动定义:网上劳动不具有生产力,因为它并没有把自然资源转换成商品。用户点击广告并没有改变广告的性质。
研究家庭劳动的女权学者并不赞同用“能否有报偿”作为判断是否算作“劳动”的标准,那些有薪酬的工作不过是家长制社会关系的产物。网民免费生产内容和家庭主妇的劳作是类似的:家庭劳动者生产的劳动力(labor-power)比其在薪资市场上的交换价值要高的多,同样用户在网上发布的内容所具有的价值也远超其出售给广告商的价格:它们都是一种无价的支持资本主义的工具,为后者提供稳定的、有效的劳动力。
点击广告可能并不会改变广告,但它对潜在的数据结构产生了影响。这种结构转变会推动生产过程的转化,进而实现用户数据变现。 贾勒特就此分析道:“数字媒体消费者和家务劳动者同资本间的关系非常相似。 他们都参与到看似自愿又有社会价值的工作中,发挥着相近的经济功能——即刻或长期地减少劳动成本”[2]。 由于他们的劳动是无价的,包含在其劳动产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无形中缩短了,商品的成本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差距随之拉大。他们贡献给资本的几乎完全是剩余价值 ,“数字家庭主妇被深深地剥削了”[3],贾勒特批判道。与此同时,数字媒体用户也被异化了:用户生产的数据被网站采集、管理和使用,而这些过程是完全没有用户参与,也不受用户控制的。

网民的能动性
但是在另外一边,比如文化研究学者和极端的女性研究者,他们并不赞同把互联网用户视为被资本主义剥削的对象或把消费者劳动力生产看作异化的产物,他们认为这些论断过于简单粗暴:“把在instagram上发早餐照片,在buzzfeed上测验你和哪个星际迷航角色更像,或是转发明星的最新自拍都看作是关乎你生计的事, 真的非常难以想象”,贾勒特写道,“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把脸书用户视为奴隶——等同于血钻劳工、巴格达的服装厂工人或是苹果在亚洲外包工厂的技工,显得既不敏感也很夸张” [4]。
这些学者没有从经济效果的角度切入,而是采用人类学研究和用户研究的方法探究数字媒体消费者,把关注点侧重在个人能动性上。研究表明消费者劳动对用户而言相当有趣,和他们的兴趣紧密相关,很多时候是她们社会能动性的源头,毫无剥削可言。有些精明的参与者,比如网络游戏的玩家会积极地反抗游戏公司并协商他们的“工作”安排。因此除了观众商品,消费者劳动力也同样生产了非异化的使用价值(inalienable use-values),包括情感,愉悦,社会连带关系,能动性和普遍智能。这些有利于自我实现的工具表明了用户并没有被数字媒体产业普遍异化。

非物质产物:情感
在综述异化和能动理论之争的过程中,贾勒特并没有站队单边学派。她受到了堂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人机合体理论中“混合体”观点的启发[5],认为消费者劳动和家庭劳动一样处于异化和能动之间。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模型来理解这类工作是如何同时产生使用价值,比如情感和可计量的交换价值的,以及这两种价值如何彼此结合。这种理论上的“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非常重要,它能使研究者不再纠结于消费者劳动机制是不是剥削的,有生产力的,或是异化的,而是更多地认知工作的经济和社会功能,更好地理解劳动产出的不是只有商品,还有非异化的使用价值。

ins上晒出的早餐,图片来源:网络
在进一步讨论新模型前,贾勒特引入了哈特和奈格里(Hardt & Negri)的“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概念。这类人类交流和互动的劳动是有形的,但它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是非物质的,比如放松、舒适、满足、兴奋、激情等感觉,目的在于创造和操控情感强度(affective intensity)。在后福特工作(post-fordist)中,这种情感劳动被去性别化,不再局限于家庭范围。
当代媒体工作,尤其是消费者劳动的重要产物就是情感强度 。2014年一名脸书科学家和康奈尔大学两位教授合作发表的一篇文章引发了巨大争议,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脸书是否控制了用户的情感 [6]。这次大规模实验中的重要一环就是利用计算机算法来操控英语用户的脸书推送,比如改变推送内容的正面和负面的情绪信息。用户的反馈则被用于检测他们的情绪是否受到了脸书内容的影响。不少学者纷纷质疑这项研究的伦理问题,这也侧面反映了情感在数字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情感强度对网站的重要性。连那位脸书科学家也承认,该项研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观察用户粘性和情感间的关系。虽然可以就此推测操控情感是脸书公司的核心业务之一,但情感对用户而言“本质上是非异化的,用马克思的话语来说,只能作为使用价值被消费。” [7]
为了探究非异化情感和抽象商品化两种特质同时存在于同一物体,或同一交换过程的情况,贾勒特认为需要动态地、分阶段地去分析。物品在不同的状态间穿梭,其劳动性质和价值形式也不断发生变化。要研究一件混杂产品(hybrid product),尤其是家务劳动和数字媒体产品,就要分析在其文化/经济生命周期中,环境、参与因素和经济功能的特殊性。
贾勒特多次在书中提到 Fortunati,这位首先提出了再造家庭劳动生产性的意大利学者给了她很大的启发。Fortunati认为再生产领域的工作被资本吸收需要经过两个阶段:首先转换家务活的生产方式,把它变成可以被男性工人直接消费的使用价值,然后再将使用价值转换为劳动力[8]。
这一观点对研究消费者劳动有非常大的理论价值。在数字经济中,非物质商品,例如社交网站上的点赞,虽然没有可以量化的交换价值, 但它仍然参与了剩余价值的生产。点“赞”最开始肯定是情感驱使,是消费使用价值后的生产和再生产,然而“赞”一旦被浏览就即刻被物化进入网站的后端数据库,最终变成了观众商品:网民不知不觉就“被共享”给其他数字媒体供应商,“被出卖”给广告商。与此同时,用户无偿生产的内容,比如免费给脸书和微信贡献的表情包,它们的版权和使用权都并不完全为制作者拥有和控制——这正是消费者劳动力的异化。面对这种新瓶装旧酒式的剩余价值剥削,贾勒特呼吁已深深嵌入在数字媒体中的我们务必提高警惕。
注释:
[1] Smythe, Dallas W. 2014.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I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in a Digital Age: Revisiting a Critical Theory of Commercial Media, edited by Lee McGuigan and Vincent Manzerolle, 29–53. New York: Peter Lang. Originally published 1977.
[2] Jarrett, Kylie. Feminism, Labour and Digital Media: The Digital Housewife. Routledge Studies in New Media and Cyberculture. p. 87.
[3] 同上
[4] Jarrett, Kylie. Feminism, Labour and Digital Media: The Digital Housewife. Routledge Studies in New Media and Cyberculture. p. 95
[5] Haraway, Donna J.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6] Kramer, Adam D. I., Jamie E. Guillory and Jeffrey T. Hancock. 2014. “Experimental Evidence of Massive-scale Emotional Contagion Through Net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1 (24). http://www.pnas.org/content/111/24/8788.full.
[7] Jarrett, Kylie. Feminism, Labour and Digital Media: The Digital Housewife. Routledge Studies in New Media and Cyberculture. p.121
[8] Fortunati, Leopoldina. 1995. The Arcane of Reproduction: Housework, Prostitution, Labour and Capital. Translated by Hilary Creek. New York: Autonomedia.

本文首发于土逗公社
转载请联系土逗获得内容授权
土逗思
为热点事件注入冷静思考,
向思想先哲撷取智慧精华,
关注新书、新文化、新趋势……
土逗思期待与你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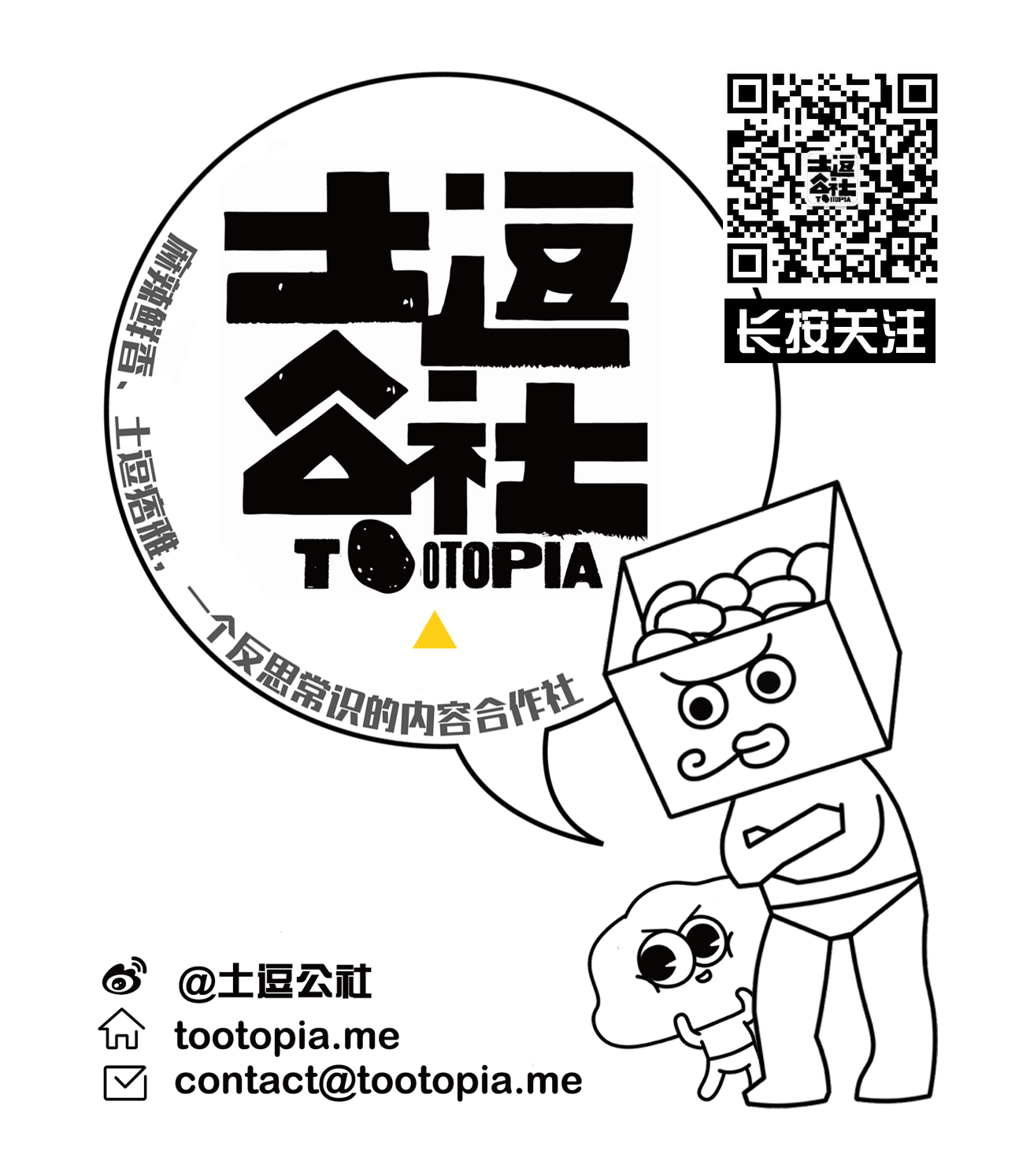
漫画:发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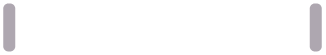
点击关键词查看更多
这里“阅读原文”,查看更多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