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民谣介入台湾:《菊花夜行军》十五年 | 土逗思



作者 | 许振华
编辑 | Catherine
美编 | 黄山

来台湾交换前,我从未想过我能碰上林生祥的演出,更不要说是《菊花夜行军》十五周年的纪念演唱会。
《菊花夜行军》是台湾音乐史上最特别的专辑之一。独立于流行音乐工业之外的它,录制于高雄美浓客家农庄的烟房,被戏称是“手工业”录音。专辑一共十首歌曲,具有完整的概念性,以客家话演唱,带来超越语言/族群的感动。
知名乐评人马世芳评论说,这张专辑能让“城里知青、美浓老农和远嫁的南洋姊妹”都闻之落泪,既能在社运现场点燃热血、又能像发烧唱片一样在音响店用来测试器材。
十五年前,交工乐队凭借这张专辑以黑马姿态获得金曲奖最佳乐队。主唱、月琴手林生祥的获奖致辞说,引领他们的是罗大佑和崔健影响下的“在地摇滚路线”,是陈达告诉他们的“音乐要走入社会”。他们所要做的,是将作为麦克风的自己,递到农民和工人面前。
因此,他们在对现代摇滚乐乐理的深刻理解之下,引入唢呐、改造福佬传统月琴、对话大浦调等客家山歌,以客家话为主要唱词,以此为在地摇滚张目;音乐要走入社会,他们就直接投身到九十年代美浓反水库的运动中。
2003年,交工乐队突然解散。林生祥与“笔手”钟永丰继续创作,与新乐手形成新团队,精进音乐纵深;贝司陈冠宇、鼓手钟成达与唢呐郭进财则组成“好客乐队”,扩大议题关注面向。在地摇滚与走入社会的路线,仍然贯穿在乐队成员分别后的音乐实践。
“毋当来归毋当来归”(客家话“不如归乡、不如归乡”),是《风神125》中主角阿成的自白。
十五年后的五月二十号,台北国际会议中心,老交工终于回归。有幸亲临现场的我,想趁这个纪念节点,回溯《菊花夜行军》,与交工乐队的音乐创作。

图为乐队19晚排练照,图片来源:生祥乐队Facebook主页,摄影:钟圣雄

好山好水留子孙,好男好女反水库
“交工”二字,取自台湾美浓烟农在农忙时期,彼此“交换劳力”的习俗。1999年的《我等就来唱山歌》与2001年的《菊花夜行军》,是完整理解交工缺一不可的两张专辑。
谈到它们的起点,一定是美浓的反水库运动。美浓,是台湾高雄客家农庄,占地约120平方公里,属六堆客家文化区域。“卷首诗”《县道184》的歌词说,沿公路出美浓,就是不通语言的另一个山头。
1992年,美浓水库大坝的规划未经广泛咨询便着急上马,得知消息的乡亲义愤填膺。延续“解严”后台湾社会运动的能量、1988年“还我母语”运动后客家族群在台湾社会的“现身”,美浓的在地知识分子开始组织串联,反水库的八年抗争就此展开。
到了1998年,反水库运动情势急转直下,社会学背景的年轻知识分子钟永丰——日后与林生祥长期合作的“笔者”,三番两次地去请生祥回乡做运动音乐。他列举民谣-社运脉络下的Bob Dylan、布鲁斯·斯普林汀等摇滚要角,又搬出社会学知识叙说“音乐生产方式与社会意义的辨证关联”。四年前认识了生祥的他,写好了《夜行巴士》的歌词,讲述93、94年美浓乡民乘夜车北上抗议的公路旅程。

图为美浓风景,图片来源:途牛网
将信将疑的林生祥很快将字句转换成弹唱自如的新曲。林生祥原先就读于有深厚民歌传统的淡江大学,七十年代李双泽等人“唱自己的歌”的运动余韵,仍荡漾在校园文化中。
距离他最近、影响最直接的音乐创作思潮,则是“黑名单工作室”掀起的“母语歌”运动。他在淡江大学组建的观子音乐坑乐队,便努力走入社区,以普罗大众为表演对象。
1998年,他和改组的交工乐队回到美浓参加运动。村民提供灵感、永丰撰写歌词、交工完成音乐创作。“我等就来唱山歌” 、“好山好水留子孙,好男好女反水库”、“水库若做得、屎不也吃得”等等,都是在抗争现场响起的音乐语言。
这场运动的音乐成果便是《我等就来唱山歌》。2000年扁政府上台,正式宣告美浓水库工程暂停。在这之后,交工还要创作什么呢?
回到八十年代,要加入世贸组织的前身GATT,那么台湾烟草业势必遭受冲击,美浓老烟农就此转型,种起了菊花,人们的作息也随作物改变。构思专辑概念与写作歌词的返乡知识分子钟永丰,从那时起就决定,以后一定要写一个以《菊花夜行军》为名的东西。
钟永丰早已经有了题目,林生祥则在废弃烟房改造的录音室内对伙伴们预言,《唱山歌》之后,一定能做出“更叼的专辑”。
那当然就是专辑《菊花夜行军》。

图为《我等就来唱山歌》十五周年纪念演唱会宣传海报

重返县道184,把什么种回来?
“重返县道184,把自己种回来”,是纪念演唱会的宣传语。交工在专辑歌词本中说,县道184之于美浓人,“唇齿相依、爱恨交织”。它将美浓分割出来,为其输送外界的营养,也带来经济上的剥削。
《菊花夜行军》,以“阿成”为主角。阿成是台湾八十年代返乡青年的一员,因在城市找不到“头路”(台、客语“出路”之意),宁受父母责怪、同乡笑话,也要回家耕田,要沿着《县道184》的公路,骑着机车《风神125》回到美浓。
为提高生产,夜晚的菊花田,灯火通明。阿成感觉这景象如梦似幻,但他很快又要遭受挫折。经销商真的可以把菊花销往海外吗?一旦失败,所有经济损失都要由农人承担。点题曲《菊花夜行军》的第一段落,便以哀叹之声铺陈种菊人内心的不安。
何谓夜行军?“日光灯晕晕”,阿成畅想菊花海洋中的各个品种要来一起踢正步。此时铁牛车(拖拉机)的声音突然响起——置身菊花田,阿城仿佛在夜行军,所谓六万六千朵菊花都是听命于他的士卒:“一二,一二三四,全部都有,跑步走。”
钟永丰在十五周年的纪念短片里说,阿成是连接起来八十年代台湾返乡青年、无壳蜗牛运动和泡沫经济的缩影。林生祥则说,人生就是受尽煎熬,要不断面对失败。他们都将自己的人生经验,投身到创作中。

图为菊花夜行军专辑封面,图片来源:YOUTUBE
但这不只是阿成的故事。女性,也是专辑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面向。娶妻,是父母对男丁的期盼。然而台湾经济的剧变,使农村男青年的婚姻问题,不得不通过国际婚姻市场来解决。
《阿芬擐人》便以唢呐、铃鼓、三弦等传统乐器,展现南洋媳妇怀孕分娩的过程。一方面,她“无根无底”,另一方面,却要“像花生种土中”,让孩子生根又发芽。这欢乐的曲调,实际上改写自牵亡歌阵的三弦弹拨手法。往生,又迎接生命。欢乐,又哀愁。这是南洋-台湾婚姻中的国族与性别的张力,也是文化融合的希望。
在《报导者》的访问中,林生祥谈及他的父权记忆:家庭里没有人敢反抗男性长辈,只要反抗就是不孝。每次到台北领金曲奖,陪同的妈妈一路都会诉苦。讲出来了,她才有笑容。
由生祥妈妈亲自演唱的《愁上愁下》,运用客家传统山歌大埔调,讲述的正是女性的艰难:一面是压抑的婆媳关系、一面是对儿女的担忧。这些忧愁都藏在山歌中,也酿造了生祥妈妈等妇女天生的好嗓子。十五周年当晚,她盛装打扮,站在台上,一词一句都唱的中气十足。
十五周年纪念短片中,生祥回到了当年录音的烟房。因台湾加入WTO荒废的烟房,被他们改造成创作“手工业”音乐奇迹的录音房。那时候的音乐生产,自始至终都是“交工”的:农田与野猪就在隔壁,乡亲们热心地送来凤梨与芭乐,更参与录音;从录音、唢呐编排到词曲咬合,每个乐队成员都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在领导、每个人也都被领导。
十五年了,《风神125》和《菊花夜行军》继续传唱,感动每一个想家、欲归家与寻家而不得的人。十五年,交工的音乐养分与创作理念,支持了南洋台湾姐妹会等社区实践,哺育了诸如音乐、策展、戏剧等更多的文化作品。

“我们最基本的立场,就是社会主义”
大陆乐迷初听交工最惊喜的段落,应是《菊花夜行军》二、三段落之间的唢呐版《国际歌》独奏。那熟悉的旋律,是经历过社会主义的我们的知识背景。
然而比起亲切,更多的是错愕。不只国际歌,唢呐吹奏下响起的旁白,是刻意模仿蒋经国口音的广播:“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是我中华民国建设的基本策略”。三民主义与国际歌齐飞,戳破了“以农养工”的发展主义的虚伪。
钟永丰曾在2008年一篇与《南风窗》的对谈中说,他们介入公共议题多年不变的立场,就是“社会主义”。在他看来,台湾的资本主义发展,如果完全没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和主张,将会非常糟糕。
国际歌、社会主义、甚至是毛泽东,在对岸交工的音乐创作中有奇妙的漂流。2009年,钟永丰在广州的一场交流会直言毛泽东对他的影响——他对公益、对运动、对音乐与文化关系的理解,得益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如果希望人民能听得懂创作者的语言,就要保证三点:写的东西不让人讨厌;写的东西可以回到自己家门;即便由运动产生,也要让音乐可以在床边、在书桌听,才有意义。
后来又有人问起钟永丰“社会主义”的立场,他却说自己已经过了贴标签的年纪。而林生祥坦言,比起对理论的认知,他更在意的是人性与生活。比起意识形态的认定,更令人启发的,还是他们的创作方法。林生祥与交工的音乐功底已无需赘言。钟永丰的歌词、专辑理念与介入主义,同样有其丰富的脉络。
社会学调查,是钟永丰掌握“语言”的工具。为了每张专辑、每个议题、每个概念,他都会去做访谈、做田调。知识分子的出身,则让他可以发表论述,组织行动。
而文学与音乐素养,更是支撑他这么多年的歌词创作的支柱。
《杜诗详注》是钟永丰的床头书。钟永丰多次演讲,都会将杜甫和Bob Dylan串联在一起。乍听起来这有些奇怪,但在他看来,杜甫就是当年唐朝的朋克歌手。在钟永丰眼里,杜甫和迪伦一样,都是民歌大流在某个时间点的集大成者。杜甫的诗,以精准的节奏反映社会现实。这也启发他,以朋克摇滚来呈现2016年生祥乐队的专辑《围庄》。

图为《围庄》专辑封面,图片来源:网络
以Bob Dylan为代表的美国民谣/摇滚,则是另一大养分来源。民谣作为路径、民谣作为方法、民谣作为思想……这些题目,钟永丰总能讲很多很多。
在钟永丰看来,摇滚乐与民谣同源,都要不断与社会现实对话。它可以用来理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更能“通灵”——掌握到生活环境中人的情绪与心灵状态。尽管摇滚乐是西方的文化霸权,但它自身的反抗性、阶级性、运动性,在深层结构上可以让全人类都来欣赏。
他还特别看重创作中的“语言”与“劳动”的辩证关系。写作农村、劳动的东西,以现代或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很难产生对话。在劳动场合,语言一定是“竞争”出来的——节奏要强、语言要鲜活、比喻要够巧妙。惟如此,体力耗累的劳动者,才能愿意听创作者说话、唱歌。
所谓客家话,也只是生活语言,而非区隔、分化族群的标识。1988年的“还我母语”运动,让客家话有机会突破官方国语与“台语”的夹击。“四大族群”渐成官方论述,客家人似乎被正名,但族群边界也越来越清晰。林生祥与钟永丰选择有意识地超越族群区隔:交工深受福佬民间音乐人陈达影响,也创作过台语歌、国语歌;到后来,林生祥甚至因坚持音乐类型才是划分奖项的依据,而拒绝领取金曲奖“最佳客家乐队/专辑”。

回不去的县道184,种不回的自己
比对大陆的音乐创作,若谈与工人、农民的连结,新工人艺术团、重D音等都是实打实的草根实践;若以摇滚、乡土、方言、地方、批判等等为关键词,我们能列举出万能青年旅店、腰、苏阳、野孩子、舌头、五条人、顶楼马戏团等一大票乐队名字。
但论及音乐概念的完整性、录音的创意、音乐的生产方式以及介入运动……他们与交工、与《菊花夜行军》又太不一样;面临的社会条件,更大不相同。
这样的音乐创作,即使在台湾也很难再寻得——热血、集体讨论、扎根地方、“手工业”录音、与村民共同生产/创作——这是名副其实的“交工”,是好几条时代脉络汇流下的“奇迹”。
五月二十号,我们回到县道184了吗?这是林生祥第一次尝试大场馆,三千人,全座席。这个确证经典的时刻,多少有些尴尬:固定、安稳的位置,与旋律引起的律动完全逆反;期待林生祥继续突破自我的死忠乐迷,大概也会失望于现场表演的保守编排。
这种制造经典时刻的尴尬,在正式演奏《菊花夜行军》前的热身中多少消解。大家自愿站起来随音乐摇摆,在“晚点名”的经典桥段化身菊花大声喊“有”,与生祥一唱一和地呼喊“菊花夜行军”。
歌迷制作的《菊花夜行军》动画视频,导演:小花(钟熠能)
这一幕多少令人想起“交工舞”。当时还在社区与社区间巡回的他们,为让演出真的面向大众,真的能让大家都参与进来,特地编排了“交工舞”,好让所有人都能感受音乐律动与身体的共振。
或许就如大陆乐评人剑烧所说,交工的前成员都已经有了不错的生活,他们无法、也不需要把自己“种回来”。这一晚的林生祥,以“音乐上的尴尬”平衡怀旧与创新的矛盾,“把自己置身于失位的音乐人与一代人宴会司仪的分裂角色”。
可为着十五年,为着音乐本身的经典,为着这反省的契机,我也选择“谅解”这位苦心的司仪。
县道184,早已变成“台28线”;那个众志成城反水库的美浓,也许永远都回不去了;我们大陆的听众,更难以代入那个“南台湾”的乡愁。
然而面向生活、面向社会、面向公众的思考与创作,还将继续。社会和音乐的关系是什么?在何种脉络下,两者才有可能完美结合、并创造出隽永的作品?
十五年前的《菊花夜行军》,在今天继续拷问着我们。

本文首发于土逗公社
转载请联系土逗获得内容授权
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土逗怕哪天联系不到你,请大家让自己身边有土逗气质的亲朋好友加管理员微信吧!
微信管理员id:tootopialee
微信管理员二维码

欢迎通过以下各种途径关注“土逗公社”
微博:@土逗公社
豆瓣:土逗公社
知乎:土逗君
土逗思
为热点事件注入冷静思考,
向思想先哲撷取智慧精华,
关注新书、新文化、新趋势……
土逗思期待与你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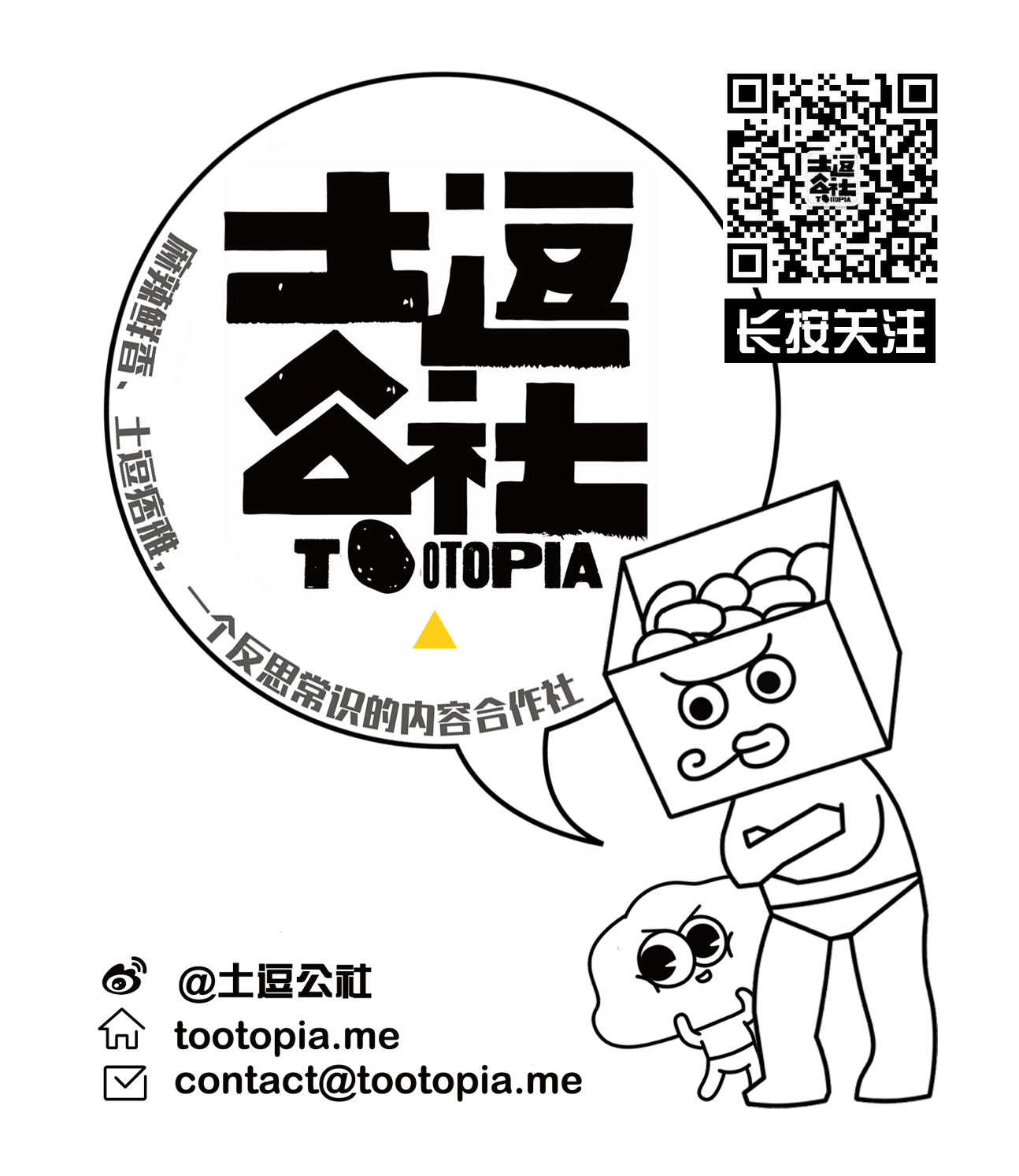
漫画:发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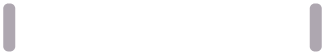
点击关键词查看更多
这里“阅读原文”,查看更多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