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医生的建筑师 | Beatriz Colomina:X光建筑

译者:尼基塔



讲座栏目主持人:陈柏旭
全球知识雷锋联合创始人、UCA优思建筑事务所创始人
阴差阳错下诞生的x光、挥之不去的战争阴霾、技术与观念的革命、被文青和权贵青睐的避世生活...著名建筑学者科伦米娜从医学话语和成像技术的角度探入宛若一团乱麻的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思潮,领一众西方名流客串出演,为读者献上《X光建筑之“是躺平生活哲学带我们走向了现代化”》。
阿道夫·卢斯也是一名受虐癖学生......你们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有点神经过敏的人,瞧瞧他那双手的姿势,整个人都紧张兮兮的。
密斯收藏X光片,勒·柯布西耶也收藏X光片......现代建筑甚至开始从外表上就接近于医疗影像:有着透明的玻璃幕墙,并且把内部结构暴露出来。
白立方的形式跟精神和生理健康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已经非常强烈了,建筑的功能就好比某种有效的安慰剂一样。
现代建筑之所以现代,也有肺结核的功劳。这并不是因为现代建筑师设计了现代的疗养院,而是疗养院使得建筑师走向现代化(modernized)。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176篇讲座。
本文整理自2019年4月30日在
墨尔本大学设计学院举办的讲座,讲座原题为
BE—150 Dean's Lecture - Beatriz Colomina: X-Ray Architecture, 由Beatriz Colomina教授主讲。讲座尼基塔记录,由菜菜、Eileen.W校编。
记录者:尼基塔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硕士,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访问研究学者(技术哲学与伦理方向)
主持人:茱莉·威利斯(Julie Willis)

澳大利亚建筑史学家和学者,墨尔本大学建筑学教授,建筑、建造与规划学院院长
主讲人:
贝奥特利兹·科伦米娜(Beatriz Colomina)

普林斯顿建筑学院研究生导师,著名建筑理论家、历史学家、作家,普林斯顿大学“媒体与现代性”跨学科课程的创立与指导者之一。她的研究涉及建筑学与艺术、技术、性学、媒体的交叉领域,对建筑学之外的纸媒、摄影、广告、影视等方向也颇有涉猎。知名出版著作包括《性与空间》1993,《私密性与公开性》1995,《我们是人类吗?关于设计的考古学》2016,《X光建筑》2019,等。
正文共19936字118图,阅读完需要30分钟
开场白

(图1:讲座PPT标题页)
各位朋友,老师们,同学们,以及所有到场的来宾们:
欢迎各位来听院长系列讲座。本系列讲座特邀建成环境领域的国际著名专家及领导者来主讲。我是茱莉·威利斯(Julie Willis),建筑、建造与规划学院的院长。今晚的讲座邀请到一位世界一流的建筑史家、理论家、研究学者、策展人及写作者来建成环境学院主讲。

(图2:茱莉·威利斯院长开场介绍)
贝奥特利兹·科伦米娜(Beatriz Colomina)是普林斯顿大学建筑系建筑史专业霍华德·克罗斯比·巴特勒(Howard Crosby Butler)讲席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建筑系研究生课程主任,她在普林斯顿大学指导并开创了“媒体与现代性(media and modernity)”跨学科课程。她是柏林高等研究院(Berli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2018-2019年度访问研究学者,这次她也是专程从那儿过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图3:墨尔本设计学院大楼外观)
贝奥特利兹在建筑、艺术、技术、性学与媒体的交叉领域著述广泛。她的著作以超过25种语言出版。其中两本书——《性与空间(Sexuality & Space)》(1993)和《私密性与公开性(Privacy and Publicity)》(1993)曾获美国建筑学会国际图书奖。


(图5、6:《性与空间》书籍封面 /左;《私密性与公开性》书籍封面/右)
她曾策划过众多国际展览,包括近期作为2016年伊斯坦布尔设计双年展的联合策展人——展览主题为“我们是人类吗?物种设计(Are We Human? The Design of the Species)”。2017年她参加首届首尔建筑与城市主义双年展并展出一件装置。
在西班牙完成学业之后,贝奥特利兹于80年代以访问研究学者的身份来到纽约人文研究院(New York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在那里她接触了沃尔夫冈·施菲尔布施(Wolfgang Schivelbusch)*、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苏桑·桑塔格(Susan Sontag)等人的作品,并深受他们的跨学科思想的启发和影响。




(图6、7、8、9: 沃尔夫冈·施菲尔布*施肖像/左1;《铁路之旅》书籍封面/左2;卡尔·休斯克*肖像/左3;《世纪之末维也纳》书籍第一版封面,插图来自古斯塔夫·克林姆特( Gustav Klimt)的画作“Pallas Athene”初稿/左4)
注*:沃尔夫冈·施菲尔布施(Wolfgang Schivelbusch,1941-),德国文化研究学者、历史学家和作者,著有书籍《铁路之旅:十九世纪的工业化时空(The Railway Journey: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ime and Spa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2014)等。
注*:卡尔·休斯克(Carl Emil Schorske, 1915-2015),美国文化史家,曾以著作《世纪之末的维也纳:政治与文化(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1980)获普利策非虚构文学奖,该书对现代欧洲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于1958年出版,给贝奥特利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开始透过各种真实的以及臆想中的疾病,透过病理学的关系角度来梳理现代建筑,包括:广场恐惧症(agoraphobia)、幽闭恐惧症(claustrophobia)、肺结核(tuberculosis)、卫生、细菌和新鲜空气。她的这一兴趣持续了几十年,期间创作出许多论文以及书的章节,最终这些成果都收录于近期出版的《X光建筑(X-Ray Architecture)》这本书。


(图10、11:《X光建筑》书籍封面/左;密斯的弗里德里希大街摩天楼北立面透视,1921年建筑师手稿/右)
这本书也是今晚讲座的主题。书中探讨了
医学话语和成像技术如何影响了二十世纪建筑的形成、表现形式和概念吸收。书中所论述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对现代建筑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二十世纪建筑师,如密斯·凡·德罗,喜欢把建筑的内部暴露在公众的视野,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1919年的透明的弗里德里希大街摩天楼(Friedrichstrasse Skyscraper )。
那个时代的主流医疗风尚,包括一些重要的医疗诊断工具,X光等,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并且在多大程度上对现代建筑产生了影响呢?这是一个十分令人着迷的问题。我非常期待贝奥特利兹在讲座中与我们分享她的探索。请大家和我一起掌声欢迎贝奥特利兹·科伦米娜教授!
讲座正文

(图12:贝奥特利兹·科伦米娜教授演讲)
非常感谢院长的慷慨介绍以及邀请。生日快乐!150周年,哇,真令人感动!当然,还要感谢唐纳德•贝茨*(Donald Bates)以及其它朋友们的接待——家庭拜访、参观校园等等。还有,同学们也都非常棒!感谢你们在这些天里跟我分享你们的作品。我们在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
*唐纳德•贝茨(Donald Bates),墨尔本设计学院副院长。

(图13:《X光建筑》插图之一,西班牙语《国家建筑杂志》1952年第126期封面)
如院长所言,这本书的写作陪伴我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下面我从书的引言部分摘取一些内容。实际上,建筑和疾病之间的纽带,可以说是我最长时间专注和研究的东西。就像刚才院长所说的,可以一直追溯到我初来纽约时,也就是1980年。彼时我刚完成在巴塞罗那的学业。我的运气出奇的好——坦白讲,我靠的真的是运气——我在纽约的人文研究所担任访问研究员。在那里,我遇到了许多杰出的学者,其中包括苏桑·桑塔格。

(图14:苏桑·桑塔格 ,1933-2004,摄于1972年11月3日)
那时桑塔格的书《疾病的隐喻》刚出版不久,从中我深受启发,并开始从各种病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建筑。这些疾病有真实的,也有臆造的,如广场恐惧、幽闭恐惧症、神经衰弱,等等;其中最为显著的是肺结核病。同时我也对卫生、细菌、新鲜空气这些东西痴迷。我心想:这是个很棒的题目,可以拿来做一篇毕业论文。当时我身处纽约,沉醉于一种狂热状态之中,洋洋洒洒地写了几百页。
但是,在那个年代,建筑学领域还没有出现所谓的跨学科研究。在我念博士的巴塞罗那没有,在后来我做访问学者的哥伦比亚大学那里也不存在。所以,最后我就做了现代建筑和大众传媒的研究课题——摄影、杂志、电影,等等。这项研究后来发展成了《私密性与公开性》这本书。但有趣的是,现在回头看,当时建筑领域甚至还没准备好接纳跟大众媒体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在80年代讨论建筑中的媒体简直就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听起来像是在攻击建筑,或者是揭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甚至人们把媒体本身也视为疾病般的存在,讳莫如深。

(图15:《疾病的隐喻》书籍封面)
那么,回到有关肺结核和现代建筑这个课题上,对于我而言,它就有点像是一种被压抑已久的能量释放。尽管这股被压抑的欲望一直潜伏在那里,像是病毒一样会时不时出没,以散文或会议论文的形式出现,但是它一直没能够被正大光明地开展。实际上,我不得不对自己写过的文章做一个统计,结果我发现已经写了超过12篇了。而当我真正坐下来着手写这本书时,我才意识到其实这本书的一半篇幅都已完成,只是我本人毫无察觉。
因此,最后我利用了我的学术年假来完成这本书的写作。那年我在柏林的美国学院(American Academy in Berlin)*做研究,起初我准备要做的是另外一个完全不相干的课题,但是在我来到柏林的研究院时,我发现万湖(Wannsee)这个地方有好多肺结核疗养院,空气也比柏林的其它地区要干净很多,有很多人专程从其它地区来到万湖治疗肺结核。
注*:柏林美国学院是柏林的一家私人的、独立的、无党派的研究和文化机构,致力于维持和加强美德之间的长期智力、文化和政治联系。每年,学院的独立搜索委员会都会从数百名申请者中提名大约20位研究员,前往位于万湖湖畔的历史悠久的别墅汉斯·阿恩霍尔德中心(Hans Arnhold Center)进行为期一个学期的研究项目。
于是我决定要换一个研究课题,亦或说这是命运的安排——我的意思是说,在我人生中有很多事情都是在无意中发生的。于是就重新回到我已经陆续思考了很长时间的这个问题。我立马开始想象自己就身在万湖的一个类似于肺结核疗养院的地方,周围从事学术研究的同仁也都成了我的病友。后面你们将会看到,其实这也是围绕着肺结核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
在这之前,我先给大家补充一点背景知识,下面我会讲一点《x光建筑》中第一章里面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健康与建筑之间的关联。实际上呢,这并不仅仅是有关肺结核的问题。这本书里提出的理论旨在论证建筑和医学之间一直都存在着紧密的相互关联。古典时期关于希腊城邦的理论指出,希腊城市的建设遵照的是四体液学说*,而在当代,人们对于健康的认识也恰恰是设计理论的组织架构来源,也就是说,这个做法一直持续至今。因此,建筑学话语本身就是在同身体和大脑相关的理论当中编织出来的;在它的构建模式中,建筑师类似于医生,而客户则是患者。
例如,维特鲁威在公元一世纪提出来的西方建筑学理论,强调建筑师必须要同时接受医学的训练。因此,今天你们要是觉得光学建筑学的知识还不够,那么不妨想象一下,假如现在大家还被要求必须上医学课,那该怎么办。
注*:四体液学说、四体液说,或称体液学说(Humorism,Humoralism或Humorae theory),起源于古希腊的医学理论,认为人体是由四种体液构成-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这四种体液对应到四种元素、四种气质,四种体液在人体内失去平衡就会造成疾病。这个学说在希腊化时代广泛传至地中海区,受希波克拉底著作影响,古罗马医学、波斯医学、伊斯兰医学、维吾尔医学都以古希腊的体液学说为理论基础。印度医学受古希腊医学影响,也采用四体液学说。

(图16:维特鲁威《建筑十书》)
这是维特鲁威说的。实际上,他在《建筑十书(Ten Books on Architecture)》*里花了大量笔触去探讨健康的问题,对城市选址是否符合健康标准的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他认为,城市选址要参考古代动物献祭的方法,要通过解剖来检验当地的动物肝脏是否“健康”;假如是健康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就适合建造城市。同样道理,在为房屋选址的健康标准上,他也用到古希腊的四体液说,并强调风和太阳的方向。反过来他也讲到,假如一个人患病了,那么建筑设计可以怎样来帮助患者快速康复。这是维特鲁威的思想的一个方面。我们在建筑学院里大家都有读过维特鲁威,但是几乎没有人去关注他对于健康方面的理论探讨。例如,他讲到的建筑怎样才能帮助一个患者,这些饱受疾病摧残的患者中也包括了肺结核患者。
注*:建筑十书 (De architectura)由古罗马建筑师和军事工程师维特鲁威著。全书分为十卷,是现存最古老且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学专著。内容涉及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基本原理、建筑构图原理、西方古典建筑型制、建筑环境控制、建筑材料、市政设施、建筑师的培养等。

(图17:切萨雷·切萨拉诺绘制的维特鲁威人,1521年)
接着我们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是意大利建筑师切萨雷·切萨拉诺(Cesare Cesariano,1475–1543 )绘制的维特鲁威人。尽管依然用身体作为分析策略,但是你们看,健康问题在此时不再是以四体液说和一个整全的身体*来作为参照,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具经过解剖、切割和分析的身体。
文艺复兴时期的设计学院习惯建在医学院的边上,在很多方面,它们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医学院的问题是:如何征得教会的同意来获取医学解剖研究用的尸体,也就是说,尸体非常难弄到。建筑学院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怎样把一栋建筑整到另一栋建筑内部,从而对这栋建筑进行研究呢?于是,他们想到一个办法。建筑学院开始把建筑的局部构造做成石膏,这个做法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这是麻省理工学院,美国第一所建筑学院,它里面还存放有很多这样的石膏模型。
注*:1490年达芬奇绘制了初版《维特鲁威人》,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嵌入了一个圆形和一个矩形当中。

(图18:MIT建筑学院的石膏模型)

(图19:伦敦外科医生约翰·巴尼斯特[John Banister]在巴伯·外科医生会堂[Barber-Surgeons' Hall] 上医学解剖课,图像来自马特奥·里尔多·科伦坡[Matteo Realdo Colombo] 的《论解剖物/De re anatonomica》卷头插画,绘制于约1580年)
那么,文艺复兴时期的学院一边开始做石膏模型,一边也开始做解剖研究了,对吧?实际上,在第一所设计学院,也就是1563年由瓦萨里(Giorgio Vasari)*创建的佛罗伦萨设计艺术学院(Academia delle Arti del Disegno),学校就要求所有学生在当地附近的圣塔·玛丽亚·诺瓦医院(Ospedale di Santa Maria Nuova)观摩尸体解剖。这是组成建筑学生专业训练的组成部分,学生还要把人体的各个结构部位画出来。哪怕尸体腐烂发臭,导致学生甚至教授都病倒了,学生还是得继续呆在里面对着已经分解的尸体画画。
医生发现可以通过解剖来探究人体的内部损伤,通过切割和解剖来观察这些躯体内部的秘密,同理,建筑师也试图通过把建筑切开、解剖开来从而揭示建筑内部的秘密。
注*: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和建筑师,以传记《艺苑名人传(Lives of the Most Excellent Painters, Sculptors, and Architects)》留名后世,为艺术史作品的出版先驱。


(图20:达芬奇手稿:《子宫中的胚胎/Embryo in the Womb》, 约1510年/左;《头盖骨解剖图/View of Skull》,约1489年/右)
例如,在达芬奇的草稿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建筑内部的各种剖面图。这些剖面图跟医学解剖图形成了并排对照。他在描述大脑和子宫的内部结构时用的也是建筑学的语汇。他说这些围合的结构需要被切割开来才能看清里面的秘密。下面是一些医学和建筑的例子。


(图21:维奥莱·勒·杜克的《十一至十六世纪法国建筑的理性词典》/左; 哥特式建筑拱柱基石[Tas-de-charge]解剖分析图/右,1854-1868年)
快速进入到19世纪中期,你们看到像维奥莱·勒·杜克(Viollet-le-Duc)*这样的建筑师,他在《十一至十六世纪法国建筑的理性词典(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architecture française du XI au XVI siecle )》中用剖透视来处理中世纪的建筑,看起来也是一种解剖手法。他其实深受乔治·居维叶(George Cuvier)*的比较解剖学(Leçons d'anatomie comparée,1800-1805)的影响,把中世纪的建筑当作是人体来进行分析。他直接谈到,需要通过像解剖“动物”一样来理解建筑是如何运作的。这幅建筑插图也是来自维奥莱·勒·杜克。
注*:欧仁·埃马纽埃尔·维奥莱-勒-杜克(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1814-1879)为法国建筑师与理论家,最有名的成就为修复中世纪建筑。法国哥德复兴建筑的中心人物,并启发了现代建筑。出生于巴黎;在瑞士洛桑过世。
注*:乔治·利奥波德·克雷蒂安·弗列德里克·达戈贝尔·居维叶男爵(Baron Georges Léopold Chrétien Frédéric Dagobert Cuvier,1769-1832) ,简称乔治·居维叶,法国博物学家、比较解剖学家与动物学家,也被称为“古生物学之父”。 为博物学家弗列德利克·居维叶之兄。 19世纪早期的巴黎科学界名人,是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领域的开山鼻祖。

(图22:乔治·居维叶的《比较解剖学》/左;居维叶在巴黎植物园[ Jardin des Plantes of Paris]上解剖课,约1800年)

(图23:X射线发现者威廉·伦琴[Wilhelm Conrad Rontgen]/左;维克多-伦琴支架模型3的广告[ Victor Roentgen Stand. Model 3],1920年 /右)
下面我们很快进入到20世纪。因为医学成像技术的变化,建筑再现手法也相应发生了更迭。在20世纪,出现了X光的广泛应用,这个发明使得一种新的建筑思维方式产生了。


(图24:X光片,拍摄对象是俄国阿历山德拉女皇的手和手腕, 约1898年/左;密斯·凡·德罗的柏林玻璃摩天大楼模型,1922年/右)
现代建筑甚至开始从外表上就接近于医疗影像:有着透明的玻璃幕墙,并且把内部结构暴露出来。我这么说听起来好像没什么,这些图像流传了这么多年,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就是一直没什么人特别加以留意。实际上,像密斯和柯布西耶这一代建筑师,他们不仅仅对X光着迷,他们还收藏X光片呢。密斯收藏X光片,勒·柯布西耶也收藏X光片。他们在各自出版的书中都用到这些图像。然后你们再看这些建筑,突然间好像目光可以穿透它们。你们可以穿透建筑表层的皮肤,看到建筑内部的结构和骨架。实际上,密斯把他的建筑叫作“表皮和筋骨建筑(architecture of skin and bones)”。
由于今天时间有限,我就把重点放在肺结核这个话题上。事实上,就肺结核对20世纪建筑所产生的影响而言,可以专门写成一本书,一整部百科全书了。这要从建筑师与医生之间的积极合作开始谈起。

(图25:阿尔瓦·阿尔托的帕伊米奥疗养院设计手稿,场地平面图)
现在我们不再跟医生合作来设计建筑了,但是在20世纪早期,这样的合作发生在肺结核疗养院的设计中,例如,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和艾诺·阿尔托(Aino Aalto)所设计的芬兰帕伊米奥疗养院(Paimio Sanatorium)。

(图26:帕伊米奥疗养院的外观,照片摄于1934年左右)

(图27:帕伊米奥疗养院的阳台,照片摄于1934年左右)
帕伊米奥疗养院的阳台在空中看起来很有戏剧张力。这张照片里,它的轮廓造型看起来跟X光胸透影像有一种诡异的相似性。整洁有序的卧房,不带任何装饰,这样的设计力图将容易积灰的表面最小化。即便是地板和窗台下方墙体的衔接都采用了曲面的做法,你们看这张图,这是刻意为了要避免成为藏污纳垢的死角。


(图28、29:帕伊米奥疗养院的病房实景照片和阿尔托的设计草图——窗和地板间的衔接曲面,草图创作于1929年)
房间里地各式各样的洁具、部件也都是由建筑师设计的,包括躺椅。椅背特别设计了一个弯曲的角度,目的是促进呼吸和咳痰。洗手池的设计考虑到减少水花飞溅,还有痰盂的设计也是考虑到尽量压低声音。同样,门把也是精心设计的,注意不要勾到医生的白大褂。不过,这栋建筑的主要设施还是它的顶楼阳台。




(图30、31:帕伊米奥疗养院的病房实景照片;消音洗手池草图,创作于1932年;门把手细节设计)

(图32:帕伊米奥疗养院的顶层阳台,病人在接受新鲜空气疗法,照片摄于1933年)

(图33:帕伊米奥疗养院的顶层阳台)
顶楼阳台距离地面的森林景观有七层楼高。护士们推着轮椅把病人送到阳台上,让他们有规律地呼吸到清新空气,晒晒太阳。他们躺在这些躺椅里面,这些椅子是由艾诺·阿尔托设计的。

(图34:帕伊米奥疗养院专用的由艾诺·阿尔托设计的躺椅草图,创作于1932年)

(图35:艾诺·阿尔托躺在自己设计的躺椅上,1934年)
在这张照片里,你们看设计师躺在自己设计的躺椅里。你们看,建筑师本人就是疗养院的病人。最终,这个阳台不得不弃用,因为绝望的病人会趁着护士一不留神就从阳台上纵身跃下,防不胜防。

(图36:帕伊米奥疗养院的阳台,病人接受阳光空气疗法)
所以,在这里,治疗的安排是这样的:每天早晨很早开始,一直到晚上,病人们都会躺在这里,呼吸清新空气。但是同时,这种疗法还变成了一种辅助性自杀,因为他们(病人)会在护士们稍不留意的间隙试图跳楼自杀。1943年人们发现链霉素的作用,这便动摇了空气和阳光疗法的科学依据,甚至可以说它促成了帕伊米奥疗养院终止营业。
现代建筑之所以现代,实际上也有肺结核的功劳。这并不是因为现代建筑师设计了现代的疗养院,而是疗养院使得建筑师走向现代化(modernized)。举个例子,阿尔瓦·阿尔托在他“皈依现代建筑(功能主义)”之前其实是一个新古典主义建筑师。这一转折发生在他参与芬兰Kinkomaa的一个肺结核疗养院的设计竞赛后。阿尔托没有赢得竞赛,但他的参赛方案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预见了帕伊米奥疗养院。

(图37:阿尔瓦·阿尔托参加芬兰Kinkomaa肺结核疗养院设计竞赛的方案,透视图,创作于1927年,未实现)
对于阿尔瓦·阿尔托而言,疗养院并非提供医疗服务的建筑,而是医学自身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是作为一种医疗方式的装置设计。他写道:“建筑的用途就是作为一个医学工具……房间的设计是……因此建筑本身即是一项医疗工具。”你们瞧,这些是他说的,对吧?
房间的设计要从饱受疾病摧残的卧床病患的实际需求出发。这儿有一点背景信息很重要,那就是阿尔托本人在参与这个项目竞赛的时候生病了。他自己声称,他对设计问题的理解以及当中最关键的灵感得益于卧床的那段漫长时光。


(图38、39:帕伊米奥疗养院病房的热环境分析图/左 ;阿尔瓦·阿尔托为一个“直立的人”设计的普通房间和为帕伊米奥疗养院“躺平的病人”设计的房间,作为插图出现在建筑师撰写于1940年的文章《建筑的人性化(Humanizing of Architecture)》中的插图,创作于1940年11月/右)
他写道:“建筑常常是为直立的人而设想的,但现在的情况所面对的客户是永远躺平的状态。房间的整个设计都要发生变动,整个建筑也都需要随之调整。光源不能固定在天花板上,因为它对卧榻的患者而言太过刺眼。天花板这块区域刚好是他们的视线活动范围,因此这一块区域对于他们而言至关重要,相当于一种新的立面。透过窗户向外望见的森林景色也同样需要从躺平的患者的视角出发来考量。”

(图40:帕伊米奥疗养院长长的阳台走廊,低矮的栏杆和纤细的扶手)
阳台上,低矮的栏杆和纤细的扶手,都要避开躺平的患者的视线,要让病人看到远方的森林上空。色彩对于房间布置来说也非常重要。他谈到,使用“安静的、暗色系的”蓝色来装饰天花板。他还谈到,明亮的淡黄色适合用于入口的接待柜台、大堂的油毡地毯,楼梯还有走廊,要“在即便是阴冷的天气里也能够唤起一种晴天的乐观朝气” *。这些都是引述他的话。
注*:《帕伊米奥疗养院色彩研究》(阿尔瓦·阿尔多基金会),见推荐阅读。https://issuu.com/alvaraaltopublications/docs/appendices_cmp___colour_research_pa

(图41:帕伊米奥疗养院的主楼道)
心理学因素当然也在细致考量的范畴。阿尔托写道:“长时间的禁闭生活对于卧床的病人而言是非常压抑的。肺结核疗养院的设计必须有很多敞开的窗户。”反过来说,就是医院要设计得像是住房,而住房也要设计得类似于疗养院。这是阿尔托说的,这话里透露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转折点。“我发现病人的特殊生理和心理反应,也为普通住宅的设计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点……如要考察人们对形式、建造作出怎样的反应,非常管用的一个做法是拿特别敏感的人群——比如疗养院中的肺结核病人来作先行试验。”


(图42:帕伊米奥疗养院的休息活动室和悬臂式山毛榉木躺椅,左图摄于1933年)
因此,病人的身体和心理的敏感性被用在了建筑的校准实验中。即便是专门为帕伊米奥设计的一些特殊的家具也成为了普通人家里的家具。这种悬臂式的山毛榉木躺椅,最初是设计给帕伊米奥疗养院里用的,它能够“帮助病人打开胸腔,促进呼吸”。这是阿尔托的原话。但是很快的,这种椅子就走进了千家万户,直到今天你只要花个一两千美元就能买到。这一点很有趣。他说:疗养院需要的家具是轻盈的、灵活的,容易清洁打理,等等。在做了很多实验之后,他们想出了这样一个灵活的系统,用于家具生产。这非常适用于长期忍受折磨的疗养院生活。

(图43:赫尔辛基的Artek商店,摄于1939年)
于是,阿尔瓦和艾诺阿尔托就在疗养院边上设立了这个工作坊,所有的家具都是在这个工作坊中生产的。但是,就在帕伊米奥疗养院建成后不到两年光景,这个工作坊就变成了一个家具公司,名叫Artek。这些原先设计用于疗养院的家具最后都进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图44:帕伊米奥疗养院病房的热环境分析图)
阿尔托的参照对象显然是身患重疾的病人。他声称:“建筑师要设计……” ;这一点在你们今天思考各式新鲜兴趣话题时非常重要,而在残疾研究(disability studies)中这一要素也是显而易见的。那正是说明,肺结核病人成为了现代建筑师的参照对象。建筑师要从身体状态最虚弱的人的角度出发来做设计。所以在这儿,我们不是谈论那些身体非常健壮的人,而是要为身体最虚弱的人做设计。

(图45:医学显微镜下的肺结核杆菌,根据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医生绘制的手稿创作的雕刻,图像显示肺结核病人肺部的鲜活杆菌/左;医学显微镜下的肺结核杆菌,根据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医生绘制的手稿创作的雕刻,图像显示在培养皿中培养两周后的肺结核杆菌)


(图46、47: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他在维也纳的诊所/左;维克多-伦琴支架模型3[ Victor Roentgen Stand. Model 3]的广告,1920年/右)
接下去我要讲一讲“现代建筑的隐形业主”。 实际上,你们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X光,还有跟疾病相关的细菌学和细菌理论,几乎全部是同时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出现的,而它们全都关注内部(inside),承认看不见的东西的存在:无意识,骷髅,细菌的微观元素,肺结核杆菌,等等。
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5),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他生于奥地利弗莱堡的一个犹太家庭,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维也纳工作,后因躲避纳粹,迁居英国伦敦。


(图48:X光片,显示威廉·伦琴妻子安娜·贝尔塔·路德维希[Anna Bertha Ludwig]戴着结婚戒指的左手,拍摄于1895年12月22日/左;X光片,拍摄俄国亚历山德拉女皇的手及手腕,约1898年/右)
这一点非常有趣。世界上第一个X光片拍的是威廉·伦琴*(Wilhelm Röntgen)的妻子的一只手。伦琴显然当时很担心被自己的同事发现他在偷偷研究这个,于是就拉着自己的妻子——顺便说一下,妻俩当时喝得醉醺醺的——来到实验室,拍下了这一张X光片,也就是历史上的第一张X光影像。接着忽然之间,很多贵族们也竞相效仿,想要拍一张自己的肖像,顺便在手上戴个戒指。于是,手的X光片就这样流行开来,成为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风靡一时的一种新型亲密肖像照。
不管怎么说,这个时期盛行的趋势是向内看,建筑也把内部结构往外翻。威胁不再是来自于外部的,而是隐藏在内部,深入到细菌和肺结核杆菌的微观层面。细菌的微观层面成为了某种设计参照,例如,在这件家具的设计中,设计师关注到耐脏问题。他们设计了这件非常令人赞叹的家具,也包括我们的住房和城市:从微观到宏观,从细菌到城市。突然之间,人们眼里的城市像是布满了看不见的居住者,某种意义上,这些隐形的居住者成为了现代建筑和都市主义的新业主。这些微生物也就是新的业主。
注*:威廉·康拉德·伦琴(Wilhelm Conrad Röntgen,1845-1923),德国物理学家。 1895年11月8日,时为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校长的他在进行阴极射线的实验时,观察到放在射线管附近涂有氰亚铂酸钡的屏上发出的微光,最后他确信这是一种尚未为人所知的新射线。有人提议将他发现的新射线定名为“伦琴射线”,伦琴却坚持用“X射线”这一名称,产生X射线的机器叫做X射线机。

(图49:耐脏躺椅设计,表面光洁,易于打理)
建筑师和医生这两种职业的结合产生了某种类型的细菌学家。这一结合所生成的设计原则也相应地脱胎于实验室中对微生物的细致研究。建筑本身成为了带有细菌学研究特征的产物。柯布西耶曾将这一点表达得恰如其分。他说:“1922年我试图在实验室中做一些研究,把我的微生物隔离开来。”这句话出现在柯布西耶写的非常著名的一本书里*,但是鲜有人留意。“我观察它的演变。”“我的微生物学说清晰透彻,无可争议,确凿无疑。”“诊断...”诸如此类。接着,他又开始谈论现代建筑和规划,也是采用这些细菌和微生物相关的术语。这些微生物从字面意义和隐喻层面上,构成了一种新建筑和城市主义的基础。自相矛盾的是,现代建筑必须要将这种新的隐形秩序展现出来,它采用了透明的图像,以一种视觉卫生来传递干净整洁、清透、健康的理念。
注*:书名为《论建筑与城市规划之现状(Precis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图50:乔治·柯克[George Keck],玻璃房[Crystal House],1933-1934年, 于1934年芝加哥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上展出, 车库里停着一辆由巴克明斯特·富勒[R. Buckminster Fuller]设计的动态最大张力车[Dymaxion car])

(图51:约瑟夫·霍夫曼设计的普克斯多夫疗养院,创作原稿西立面,1903年)

(图52:瑞士建筑师奥托·普雷格哈特[Otto Pfleghard]和马克思·赫菲力[Max Haefeli]与工程师罗伯特·麦拉特[Robert Maillart]合作设计的亚历山德拉女王疗养院,1907年)
事实上,现代建筑史中记载的疗养院不计其数。我们可以想到的有:例如,约瑟夫·霍夫曼(Josef Hoffmann)设计的位于维也纳郊外的普克斯多夫疗养院(Purkersdorf, 1903);奥托·瓦格纳的设计的维也纳斯坦恩霍夫疗养院(Steinhof, 1907);瑞士达沃斯的亚历山德拉女王疗养院(Queen Alexandra Sanatorium, 1907),也是由建筑师和医生以及工程师合作完成的,体现了当时最尖端的建筑工程技术和医疗技术。

(图53:印有荷兰希佛萨姆的阳光疗养院的明信片,1927年)

(图54理查德·多克设计的魏布林根疗养院,1926-1968年)
此外,还有杨·杜伊柯(Jan Duiker)和伯纳德·毕吉特(Bernard Bijvoet)设计的位于荷兰希佛萨姆(Hilversum)的阳光疗养院(Zonnestraal, 1925-1928);理查德·多克(Richard Docker)设计的魏布林根疗养院(Waiblingen, 1926-1968);约瑟·路易·泽特(Josep Lluis Sert)设计的巴塞罗那抗肺结核疗养院(Despensario Antituberculoso, 1934)和山坡疗养院项目。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图片是威廉·冈斯特(William Ganster )和威廉·佩雷拉(William Pereira)所设计的莱克县肺结核疗养院(Lake County Tuberculosis Sanatorium, 1931),位于伊利诺伊州的沃基根(Waukegan)。


(图55:西班牙《国家建筑/Revista Nacional de Arquitectura》杂志封面,第126期,1952年6月,显示莱克县肺结核疗养院的照片叠加在一张肺部X光片上/左;伊利诺伊州沃基根莱克县肺结核疗养院,1939年/右)
案例真的数不胜数。许多建筑师都做过疗养院的设计,某种程度上,这些疗养院也定义了他们。疗养院成为了新的建造材料和技术的试验平台,而且经常是建筑师、工程师和医生的实验性合作。

(图56:维纳·黑贝布莱德[Werner Hebebrand]和威廉·克莱内茨[Wilhelm Kleinertz]设计的德国马尔堡“阳光之景/Sonnenblick”疗养院,1929-1931年)

(图57:荷兰希佛萨姆阳光疗养院鸟瞰,印在1931年的一张明信片上/右)
这些疗养院的一个很典型的特点是:地处偏远,像一艘艘远洋邮轮一样漂浮在山坡上,森林里,或者是湖畔和海滨地带。它们的阳台也是一排一排的,打造成一个个小沙滩一样,有些是人工雕琢的沙滩,有些时候就设置在建筑内部,比如前面这张图片里的这个疗养院,它里面设置了一个人工沙滩给小孩子们使用;更有甚者,在建筑外部便配备自然沙滩。这样的设计看起来像是建筑本身在接受治疗。

(图58:杰克建筑师哈罗米尔·克雷查[Jaromir Krejcar)设计的特伦钦温泉镇[Trencianske Teplice] 马赫纳奇[Machnac]疗养院, 1929-1932年)

(图59:法国艾克斯莱班[Aix-Les-Bains]的人工沙滩)

(图60: G·卢巴斯基[G. Lubarskij],俄罗斯奥德萨[Odessa]附近的肺结核疗养院,1930年)
你们看这些建筑,它们像是阳光设备一样,会根据太阳的角度来自动调节。有些时候它们会按照一个非常陡的角度这样堆叠上去,比如左边这张图片上显示的马塞尔·布罗伊尔(Marcel Breuer)设计的这个建筑,它是1930年的一个疗养院,可容纳1100张床位。还有比这个更倾斜的角度,这是尼古拉·维森塔(Nicola Visontai)为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设计的疗养院,这斜坡后面安装了一个升降梯,可以沿着这么陡的一个角度上上下下来载客。

(图61:布罗伊尔和古斯塔夫·哈森弗卢格[Gustav Hassenpflug]设计的“1100张床位”疗养院,1930年/左;维森塔设计的阿尔卑斯山疗养院项目,1934年/右)

(图62:萨伊德曼和珐尔德合作的法国艾克斯莱班[Aix-les-Bains]旋转疗养院,1930年)
还有更为极端的例子,比如这个由放射科医师琼·萨伊德曼(Jean Saidman)和建筑师安德烈·珐尔德(Andre Farde)一起合作完成的项目,长25米,能够在离地16米的空中旋转,确保肺结核病人总能够面朝阳光。

(图63:印度占姆纳格旋转疗养院,1934年)

(图64:法国Aix-les-Bains旋转疗养院,1930年)


(图65:法国Aix-les-Bains旋转疗养院可倾斜病床)
接着他们又在印度的占姆纳格(Jamnagar )造了一个类似的疗养院。这个建筑里有这些不可思议的精密设备,例如可伸缩的玻璃墙,还有专门聚焦的仪器,能够增大太阳照射面积。即便是这个床,你们瞧瞧,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金属框架来悬空,上下滑动,调整角度,以保持跟这些仪器以及太阳的角度一致。

(图66:普克斯多夫疗养院主厅)
疗养院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实验室,孵化出了对于形式和空间组织的新态度。假如我们再回过头去看20世纪的第一所疗养院,约瑟夫·霍夫曼的普克斯多夫疗养院展现出了:纯白的表面,激烈鲜明的线条,还有方正的家具。此外,建筑师还首次采用了埃纳比克钢筋混凝土施工,又首次采用了玻璃和电。电在当时也被视为清洁卫生的能源形式,它比天然气要清洁。当然更重要的是,电被用于各种各样的实验疗法当中,比如试图用来增强神经功能的电动桑拿机器,电动沐浴,还有电椅等等。他们谈到用电来增强神经,打造了这种“酷刑机器(torture machine)”。

(图67:普克斯多夫疗养院的机械诊疗室,1905-1906年)
在普克斯多夫疗养院刚建立那会儿,批评家路德维希·希维西(Ludwig Hevesi)形容它是“赤裸的霍夫曼建筑(the naked Hoffmann building)”:墙上贴着白瓷砖,刷成白色或者是贴了白瓷砖的“可清洗的病房(washable warld)”。希维西非常急切地想要自己亲身体验一把疗养院里的各种诊疗设备,这些设备主要放在所谓的“机械诊疗室(mechano-therapy room)”内:“在这个优雅的白色大厅里,摆满了各种人造设备,我很快就熟悉了它们的操作性能,包括电动桑拿机器——一切都是用电来驱动的。”

(图68:理查德·艾彬的两本书《论健康的和患病的神经》和《性心理疾病》的封面,以及他和妻子玛丽·路易斯[Marie Luise]的合影)
这个建筑实际上是在原先由神经心理医师理查德·冯·克拉夫特·艾彬(Richard von Krafft-Ebing)所成立的一所疗养院的基础上加盖的。这幅图片上你们看到的是他和他的妻子。普克斯多夫疗养院还未建成时,艾彬就去世了,但是他的思想理念却渗透到了这个建筑中。克拉夫特·艾彬甚至争辩道:“现代大都会正在破坏居民的神经,而空气、光、自然,以及简洁性,这些是最为有效的疗法。”他写了一本书,题目是《论健康的和患病的神经(Uber gesunde und kranke Nerven)》(1885年),一年后他又写了另外一本书,名叫《性心理疾病(Psychopatia Sexualis)》。他还造了一个新词叫“受虐狂* (masochism)”同样因为他而得以流传开来的另外一个词是“施虐狂( sadism)”。
普克斯多夫疗养院接待过的病人包括很多社会名流。你们看左上方这里,这个人是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 还有设计了普克斯多夫疗养院家具的科罗曼·莫泽*(Koloman Moser)以及其他人。甚至建筑师约瑟夫·霍夫曼本人也都是这个疗养院的常客。显然,建筑师霍夫曼本人也饱受神经紊乱的折磨,这发生在普克斯多夫疗养院项目的委任设计之前,霍夫曼对克拉夫特·艾彬的理念表示感同身受。依照霍夫曼的传记作者爱德华·赛勒克(Eduard Sekler)的研究,霍夫曼正是因为当时自己所承受的神经紊乱的病痛折磨才不打算接受这个委约。这里顺便一提,普克斯多夫疗养院接待的病人得的病涵盖面很广,包括神经紊乱、神经衰弱症、饮食失调、药物滥用、歇斯底里症,等等。
注*:masochism这个词衍生自作家利奥波德·冯·萨赫-马索克(Leopold von Sacher-Masoch)的姓氏。

(图69:普克斯多夫疗养院接待过的名人肖像:马勒[左上一]、勋伯格[左上二]、霍夫曼史塔[左下一]、莫泽[左下二]、霍夫曼[右])
注*: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 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是19世纪德奥传统和20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音乐之间承前启后的桥梁。马勒之后,十二音和无调性音乐等先锋理念崛起,传统调性音乐的辉煌时代走向终结。
注*: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 1874-1951),奥地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作家,画家。 勋伯格的方法,无论是在和声还是发展方面,都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音乐理念之一。有三代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作曲家接受并发展了他的理念,但同时他的理论也激起了许多人的强烈反对。
注*:胡戈·劳伦斯·奥古斯特·霍夫曼·冯·霍夫曼史塔(Hugo von Hofmannsthal, 1874-1929),或译作霍夫曼斯塔尔。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诗人、评论家。
注*:科罗曼·莫泽(Koloman Moser, 1868-1918),奥地利艺术家,对20世纪的平面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是维也纳分离派运动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也是WienerWerkstätte的共同创始人。莫泽设计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包括从邮票到杂志小玻璃瓶的书籍和图形作品。
所以说,有人可能是因为得了肺结核去那儿治疗,也有人可能是因为得了各种莫名其妙的疑难杂症。只要你说自己有病就没人反对你住进去。也有可能你住院前得的是神经紊乱症,出院之后发现自己染上了肺结核。不过反正也没人仔细往这上面去想。反正就是这样,我也很不解,不过无所谓了就这么着吧。
说到这儿,情况就很清楚了:这个疗养院被视为当时维也纳的上流阶层和知识分子们的一种新型社交场所。他们都喜欢到那里住一住。这位是科罗曼·莫泽,疗养院里的家具是他设计的,他也时不时在里面住上一阵子。我不太清楚他得的什么病,就是他设计了普克斯多夫的这些方方正正的家具,他跟霍夫曼一样都是疗养院的常客。记者兼艺术批评家贝莎·扎克哈康德尔(Bertha Zuckerhakandl)在当时为《维纳公共报(Wiener Allgemeine Zeitung)》写的一篇文章中形容普克斯多夫是现代酒店和现代康养中心两者的交集。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则用了更加尖酸的口气形容它是一个“疗愈诈骗机构(healing-swindle-institution)”。
注*: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 1874-1936),二十世纪早期最著名的奥地利作家之一,也是记者、讽刺作家、诗人、剧作家、格言作家、语言与文化评论家,生于奥匈帝国基钦,死于奥地利维也纳。



(图70、71、72:科罗曼·莫泽/左;记者兼艺术批评家贝莎·扎克哈康德尔/中;卡尔·克劳斯肖像及其作品《火炬(Die Fackel)》/右)

(图73:普克斯多夫疗养院的餐厅)

(图74:普克斯多夫疗养院的病房)
评论家们向这栋建筑内在所包含的清晰和真理致敬。实际上,普克斯多夫疗养院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建筑的现代性。“现代”成为了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群体中的一种新的复杂品位,这些人在普克斯多夫疗养院里规规矩矩地围着一张纯白的桌子,煞有介事地接受治疗,睡在当时被认为是非常整洁亮丽的白色房间里,然后还要让自己顺服于白色空间里的种种治疗安排,就像之前你们看到的那些张照片里所显示的那样。白立方的形式跟精神和生理健康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已经非常强烈了,建筑的功能就好比某种有效的安慰剂一样。

(图75:托马斯·曼和他的短篇小说《崔斯坦(Tristan)》)
这个理念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非常清晰的表达。以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为例,你们可能读到过他的短篇小说《崔斯坦(Tristan)》。故事发生在1903年,同年普克斯多夫疗养院刚建成。小说的背景设定在一处虚构的疗养院,名叫“爱茵弗里德(Einfried)”。托马斯·曼作了如下描述:“一栋长长的,白色长方形的建筑”,“热心推荐给肺病患者,以及其它各类疾病患者。”这里的情况跟在普克斯多夫疗养院差不多:有肠胃紊乱的病人,有心脏方面问题的人,中风的,风湿病患者,神经疾病以及各种内脏间歇性闹病的患者。其中一名患者——她是小说中科罗特杨先生(Herr Kloterjahn)的妻子,问另外一个人时说道:“说真的,您为什么留在爱茵弗里德呢?……斯宾奈尔先生,您来这儿是为了做什么治疗?”
“治疗?哦,我只稍微电疗一下。不,不值一提。我会告诉您我来这儿的真正原因,尊贵的夫人,我是为了赶时髦……显然,人们对于柔软而舒适、骄奢淫逸的家具的感受是一回事,对于这些桌子、椅子和地毯的笔直线条又是另一种感受。这明亮和硬朗的感觉,冰冷的、质朴的简洁,克制的力量,尊贵的夫人,毫无疑问,它最终会荡涤我的心灵,使得我获得重生。”
注*:保罗·托马斯·曼(Paul Thomas Mann ,1875-1955), 德国作家,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著名小说如《魂断威尼斯(Death in Venice)》曾被翻拍成电影。

(图76:引用自小说《崔斯坦(Tristan)》中的一段对话)
好吧,那么这里就很清楚了,用托马斯·曼的话说,不管斯宾奈尔先生得的什么病,时髦才是他真正的解药。顺便一提,根据小说中的描写,斯宾奈尔先生“穿着一身白色的夹克,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住在这栋纯白的建筑里——完全由白雪覆盖的纯洁无暇的区域,摆设着白色的搪瓷扶手椅,白色的折叠门,白色的画廊,包裹着病人们白色的面孔和白色的手,以及他们在白色掩盖之下的激情和欲望。”白色(whiteness)是这栋建筑,这里的景观,乃至于这里的病人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最具一致性的特征。


(图77、78:卡米洛·希泰和他的《遵循艺术原则的城市设计》创作手稿,1889年)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主题,讲讲“施虐与受虐”。克拉夫特·艾彬的理念在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中间也不乏影响力。举个例子,我们来看下卡米洛·希泰(Camillo Sitte)对于现代城市设计的批判。在他看来,现代城市引发了广场恐惧症和其它一些神经疾病。在他的著作《遵循艺术原则的城市设计(Der Städtebau nach seinen künstlerischen Grundsätzen)》中,他提倡要回归到亲密的城市空间,像在中世纪时候一样,这种空间对居住者实施庇护。
阿道夫·卢斯(Adolf Loos)也是一名受虐癖学生。你们感兴趣的话,卢斯的著作中有很多关于受虐癖的参考资料,只是没人注意到这一点。卢斯认为具有现代神经的人类已经对装饰忍无可忍。1926年他在巴黎索邦做过一个(系列)讲座,加起来一共是4个讲座,以德语进行,主题都是在讨论具有现代神经的人类( Der Mensch mit den modernen Nerven)。关于神经的主题占据了卢斯的一生,浸润着他从世纪之交开始的所有写作。

(图79:阿道夫·卢斯和他于1926年在巴黎索邦做的四场以德语进行的讲座)
对于卢斯而言,消除装饰并非仅仅是一种美学上的选择,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思索。但是当我阅读了更多相关资料之后,我更多地意识到,对于他而言,这是一种神经学上的、而非出于麻醉目的的选择。根据卢斯的观点,现代人已经不具备那种神经来适应过去几个世纪的吃、穿和装饰习惯。
在《装饰与罪恶(Ornament and Crime)》这本书中,我相信大家都读过这本书,里头他确切地谈到,他看着经一番装点后被展示在餐桌上的动物着实感到毛骨悚然,尤其是当他或许不得不吃下某道用馅料填入动物体内的菜肴时。他接着说:“我只吃烤牛肉。”不论是食物还是建筑,过度繁复的装饰都让他感到恶心。我们的神经已经变得不一样了,那样的装饰让我们感到不适,是因为我们不再拥有同样的神经,而并不是说我们更喜欢这样的简洁。

(图80:阿道夫·卢斯的《装饰与罪恶》德语版/左;餐桌上的填充动物展示/右)

(图81: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奥斯卡·柯克西卡[Oscar Kokoschka]画的阿道夫·卢斯肖像)
但是呢,实际上这种迷恋——当你们看到这张由柯克西卡画的卢斯本人的画像时,你们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有点神经过敏的人,瞧瞧他那双手的姿势,整个人都紧张兮兮的。这种对于神经的迷恋,就像我之前说的,并非仅仅是一种维也纳人独享的烦恼。

(图82:保罗·希尔巴特肖像,摄于1897年,以及他的《玻璃建筑》德文版封面,柏林,1914年)

(图83:引用书中文字片段)
在他的《玻璃建筑(Glasarchitektur)》(1914)中,保罗·希尔巴特*(Paul Scheerbart)写道——这句话也很有趣——“疗养院将会想要变成玻璃建筑;光彩照人的玻璃建筑对于神经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没有什么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他不过是沉浸在卫生的观念里,要把灰尘、花粉、昆虫等等这些东西都去除,要干净到一尘不染。他写了一部非常令人赞叹的电报中篇小说(telegram novella),名叫《治疗花粉病的海上疗养院(The Oceanic Sanatorium for Hay Fever)》。在这篇小说中,他天马行空地想象道:“漂浮的小岛,微风轻拂,多彩的亭阁……”她说:“每个人,在美国都得了花粉病…….所以在花朵盛开的季节,我们一定要到海上去居住......我们的海上疗养院花粉病协会(Oceanic Sanatorium Society for Hay Fever )就是为此而成立的:漂浮的小岛与干燥的陆地和天然小岛剥离,漂移出几百英里远。在我们的岛上,灰尘是不存在的。”
注*:保罗·卡尔·威廉·希尔巴特(Paul Karl Wilhelm Scheerbart, 1863-1915),德国推测小说文学和绘画作者。他还以化名KunoKüfer出版,最出名的是《玻璃建筑( Glasarchitektur)》一书。舍尔巴特与表现主义建筑有关,其主要支持者之一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


(图84、85:希尔巴特刊登于《风暴/Der Sturm》文化艺术周刊的文章内容赏析。《风暴》是一份德语艺文杂志,由赫沃思·瓦尔登[Herwarth Walden]创办,内容涵盖表现主义、立体派、达达和超现实主义等各项艺术运动。杂志活跃于1910年至1932年间。讲座中提到的卡尔·克劳斯、阿道夫·卢斯以及希尔巴特都是曾是该刊物的撰稿人。)


(图86、87:希尔巴特小说插图)
希尔巴特把现代技术一并视为疾病的诱因和治疗手段。他写道:“神经科医生应该把疗养院里彩色光线的镇定作用写进药方里。”早在1901年,他就设想“空中疗养院(air-sanatoria)”能够在空中飞翔,治疗由于现代城市引发的各种神经紊乱病症。航空技术在希尔巴特的所有乌托邦小说中都居于核心,它既是治疗手段,也是罪魁祸首。在战前的1914年写就的一份反战宣言中,他预见空战作为现代机器的缩影将会产生“全面的癫狂(general insanity)”:“只稍用脑子想想,”他写道,“这些军事技术就会对人们的神经产生有害作用。”
对于他而言,至少这是一种先知般的预言。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他精神崩溃。1915年他死于饥饿,据说是为了抗议而绝食。既然他都没有上过前线,看起来好像也真的是“想想”就要了他的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建筑疗愈”这个主题。瑞士达沃斯,也就是托马斯·曼的著名小说《魔山(Der Zauberberg)》的故事情节展开的背景。达沃斯是现代疗愈现象的一个典型缩影,早在1910年代就已经有了差不多26座疗养院。例如,这座谢茨阿尔卑疗养院(Schatzalp)*,建于1899年和1900年间,也是托马斯·曼在《魔山》中唯一指名道姓提到的疗养院。
注*:此疗养院现在是瑞士达沃斯谢茨阿尔卑酒店:https://www.schatzalp.ch/en/htl/history/

(图88:瑞士达沃斯Waldsanatorium疗养院1911年宣传册)

(图89:印有谢茨阿尔卑疗养院照片的明信片,约1900年)
如前所述,这座疗养院可称得上是跨界合作的典范,合作者是卢修斯·斯宾格勒(Lucius Spengler)医生和两位来自苏黎世的年轻建筑师——奥托·弗列格哈特(Otto Pfleghard)和 马克思·赫菲力(Max Haefeli),以及工程师罗伯特·玛依拉特(Robert Maillart)。玛依拉特曾在法国的弗朗索瓦·埃纳比克*(Francois Hennebique)公司工作。这是瑞士第一座以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建筑,也因此它成了疗养院的经典案例。在这个建筑里面大家看到最尖端的医疗手段跟建筑中最先进的技术很巧合地发生了交汇。
注*:弗朗索瓦·埃纳比克(François Hennebique),法国工程师,自学成才,于1892年为其开创性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系统申请了专利,将柱和梁等独立的建筑元素整合到一个整体元素中。埃纳比克(Hennebique)体系是现代钢筋混凝土施工方法的首次出现。
谢茨阿尔卑疗养院的建筑形式现在看来非常粗野。
它的水平性和抽象性看过去相当粗野,立面横向跨度有100米长,设置了无尽的看不到头的走廊,像一艘茫茫大海中的远洋班轮。阳台的设置是出于治疗空间需求的考虑,以满足病人们能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躺在阳台上特殊设计的躺椅上晒太阳,接受这样的治疗,不管冬天还是夏天都是如此。

(图90:“躺平疗法[Liegekur]”,达沃斯Villa Pravenda,疗养院阳台上的病人,照片摄于约1900年)

(图91:躺平疗法,达沃斯,约1910年的明信片)
于是你们看,这张经典照片上显示的,天气特别好的时候会有人在照看这些病人。另外这张照片上,病人躺着排成一排,每个人都裹着一条毯子,上面覆盖着皑皑白雪,他们好像被遗弃在这个角落,边上扔了一只扫帚在这里陪伴他们。有趣的是,右边这张图上面的病人看起来反倒乐呵呵的,而左边的这张图片上的病人看起来则一脸怨气。我想他们可能心里头还在期待,看看是不是会有奇迹发生吧,然而,并没有,什么也没有发生。然后再对照这张,这些病人就好像生无可恋样子,好吧,就这样吧,随它去吧。

(图92:托马斯·曼和他的小说《魔山》德语版封面)

(图93:瑞士达沃斯瓦尔德疗养院)

(图94:在“活力[Lebendige Kraft]”疗养院接受水疗的肺结核病人,由疗养院的创建者马克西米利安·伯奇·布伦纳[Maximilian Bircher Brenner]医生将其全身包裹成白色,照片摄于苏黎世,1910年)
托马斯·曼喜欢捕捉敏锐的建筑细节,假如你们读过《魔山》的话就会知道,里面充斥着大量的对于现代建筑的细节刻画:这是什么样的建筑啦,诸如此类。对于疗养院的躺椅,他也耗费了大量笔墨去精心刻画,烘托出一种“躺平”的边缘生活哲学。
这种水平视角的疗愈策略也是瓦尔德疗养院(Wald)的核心。瓦尔德疗养院也位于达沃斯。卡提亚·曼(Katia Mann)——托马斯·曼的妻子就曾经在那里住过,托马斯·曼创作《魔山》的灵感也正是来源于此。曼的小说对这座现代建筑中的社交生活进行了生动描绘:一切都裹在白色中,甚至是病人在接受水疗时,也都裹成一身白色。


(图95、96:托马斯曼的妻子卡提亚·曼及其与孩子们的合影[莫妮卡、格洛、迈克尔、克劳斯、伊丽莎白、艾瑞卡],约1920年)
卡提亚·曼实际上是这坐疗养院新落成后的第一批患者之一。她于1912年开始患病,也就是在生下第四个孩子之后的一年。她母亲坚持认为她得的不是肺结核,而是由于生育所造成的虚脱。短短四年里,她一共生了四个孩子,两次流产,操持一大家子的事务,同时据说还要用打字机帮丈夫把创作手稿打出来。顺便一提,卡提亚曾攻读数学,并在X射线的发明者威廉·伦琴门下学习实验物理学,但是她母亲坚持要她放弃高等教育的机会,为了让她在21岁时嫁给了托马斯·曼。不管她得的是什么病,反正她在多个疗养院里进进出出,一直待到1914年才回家,接着又生了两个孩子。

(图97:瑞士达沃斯瓦尔德疗养院的餐厅)
肺结核总是跟各种神经紊乱疾病牵扯上关系,而它所导致的那种忧郁也意味着医生对病人采取的是一种心理疗法。疗养院提供了某种逃离城市的机会,但这是逃离正常的家庭生活,投向一种相对舒适、稳定而令人心猿意马的环境,在那里可以结交新的朋友,同时也必须服从严格的日常管控。这些经过高度严格设计的诊所空间,甚至代表了一种新的优雅的家庭生活形式。卡提亚·曼曾经说过,这段经历使得她变得更加坚强,从而使得她能够禁受住后来生活中的种种磨难。想想她也真的是命途多舛:二战,逃亡到美国,最疼爱的孩子克劳斯自杀了,接着第二个孩子迈克尔也自杀了。她究竟是如何熬过来的,我们不得而知。

(图98:荷兰希佛萨姆阳光疗养院明信片)
不管怎样,这原本属于富贵阶层的现代远洋班轮最终通过像阳光疗养院(Zonnestraal,1925-1928)这样的建筑得以民主化。这座疗养院位于荷兰的希佛萨姆(Hilversum),距离阿姆斯特丹有20英里。“Zonnestraal”这个词在荷兰语中的意思是“阳光”。这座建筑是由杨·杜伊柯(Jan Duiker)和伯纳德·毕吉特(Bernard Bijvoet)两人为荷兰钻石工人总工会(General Diamond Workers’Union)所设计的。这又是一座白色混凝土建筑,它的医疗属性再次被发挥到了极致,近乎成了一种宣言。阳光疗养院是一部健康机器,一个生产制造健康身体的工厂。

(图99:希佛萨姆阳光疗养院的阳台外观/左;1928年海报上的宣传标语:引入光线、空气和阳光/右)
这是它的宣传标语:引入光线、空气和阳光。因此,它在很多方面有点像是现代建筑的宣言。住在这里的病人也是推着轮椅直接从各自的房间里出来,到阳台上晒太阳,不过这里的阳台不再是一种社交空间,这一点跟之前提到的疗养院有所不同。因为在这儿,病人之间很少有互动。从这张照片上看,他们都是把头埋在各自的房间里,或者是埋在自己手上的书中。和他们真正有互动的是阳光、机器——这些非常复杂的呼吸诊疗设备。
我想,单间病房的设置看似是工人阶层疗养院的一种进步表现。但是,当我再次读到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的小说……他的小说对我理解疗养院帮助很大,因为他自己也是断断续续在疗养院里呆过,所以作为一名肺结核患者的这些经历也都渗透到了他的写作中。当再次读完他的小说之后,我开始意识到,在一座疗养院里一旦一个病人被转移到一个单独的房间,意味着最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这种可能性只有一个。
注*:托马斯·伯恩哈德(Nicolaas Thomas Bernhard,1931-1989,http://www.thomasbernhard.org/),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诗人。伯恩哈德的作品被誉为“二战以来最重要的文学成就”。他被认为是战后最重要的德语作者之一。

(图100:希佛萨姆阳光疗养院的病人在使用呼吸机,约1928年)

(图101:单人病房)

(图102:谢茨阿尔卑疗养院的选址)

(图103:小说《崔斯坦》中对于死亡的描述片段)

(图104:奥托·瓦格纳在《大城市》中提出的维也纳第二十二城区规划构想,1911年)
你们可能想要知道,可能马上要问,干嘛这么着急把棺材里的死者尸体从经过特殊设计的停尸房运到郊区的遥远墓地?他说,一座大城市,很快就要限制在火车上运送尸体了,因此在每个住区必须要设立一个停尸房站点,专门用来清运尸体。当然你们还可以想到巴西利亚,它在城市两翼最靠近边缘的地方设立医院,也是不让人看到尸体。我们不想看到死人。


(图105:罗伯特·穆齐尔,1880-1942/左;小说《没有个性的人》第一版封面,1943年)

(图106:奥托·瓦格纳设计的环形大街维也纳酒店,双人间渲染图,1910年)
于是在二十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你们瞧瞧,这些建筑师们都非常着迷于健康的观念。接下来我要快速地从这里直接跳过去了。不过,还有一点值得讲一下。实际上,最后每一栋建筑都搞得很像疗养院。例如,拿阿姆斯特丹的健康儿童户外学校*(Open Air School for Healthy Children)来说,它是在阳光疗养院建成后的两年建的,也是由同样的两位设计师操刀设计:杨·杜伊柯(Jan Duiker)和伯纳德·毕吉特(Bernard Bijvoet)。
他们把光线、空气和阳光的原则引入其中,只是这一次他们设计的时候考虑的建筑使用者是儿童。儿童被弄到这些玻璃机器里面,甚至还要求他们坐到这个屋顶上面,在上面呼吸新鲜空气并晒着太阳。所以这个建筑被构想成一种光设备,跟1930年代的光疗很像,在那些阳光不太充足的地方采用这种阳光疗法。就像这幅宣传照上显示的,孩子们在学校里要接受各种各样的机器治疗,也没人去想会不会得皮肤癌之类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下一代人的问题了。它生发出这样的一些疑问:“这东西真的好用吗?这都是真的吗?要不我来试一下这个看看。”所以你们瞧,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沉迷和迷恋的对象。
注*:Open Air School “户外学校”是一战后专门为儿童打造的露天教育设施,旨在预防肺结核。该类学校多数建在城郊或乡下地区,具有良好的通风设施和户外教学环境。

(图107:杨·杜伊柯和伯纳德·毕吉特设计的阿姆斯特丹健康儿童户外学校,1927-1930)

(图108:阿姆斯特丹健康儿童户外学校,1927-1930)

(图109:法国孩童在接受室内日光浴疗法,1937年)
好吧,那么,我在讲座结束之前再讲点什么好呢?不如,我最后再给大家快速地讲一个可能你们都会感兴趣的故事。这是关于图根哈特住宅(Tugendhat House)的故事。因为不仅现代建筑师们强调健康和锻炼的重要性,在对抗疾病的威胁时,疾病成为了参照对象;实际上,建筑也在无意中被人们视为健康身体的等价物。

(图110:图根哈特住宅,从花园侧观望)


(图111、112:《现代建筑》画册封面及《国际风格》杂志封底的图根哈特住宅)
我对此感兴趣的是:这所房子在德国占领捷克之后遭到废弃,再后来落到了共产党官僚的手上,他们就琢磨着:“我们拿这个建筑怎么办好呢?它可以用来干什么用呢?好吧,不如就把它当作一个医院,为那些身体有缺陷的儿童提供骨科矫正治疗服务。”

(图113:图根哈特住宅的起居室变更为儿童康复中心,1966年)


(图114、115:图根哈特住宅的起居室被重新用于青少年体育活动室)

(图116:图根哈特住宅变更为Karla Hladka舞蹈学校体育研究所,阳台被重新用于儿童体育活动室)
当时的捷克共产党官僚没有意识到,其实在早些年的时候,这房子已经留下了照片,老照片上的房子也具有同样的气质。在1930年代的照片里看过去,图根哈特住宅里也有小孩在阳台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玩耍。这个照片跟前面那张50年代的照片非常巧合地呈现了相同的内容。

(图117:图根哈特住宅的顶层阳台上裸晒的小孩)
图根哈特住宅的业主可能也把建筑当作是一种健康机器来理解。建筑评论家尤斯图斯·比尔(Justus Bier)曾在一本建筑杂志撰文并以一种善辩的口吻质疑道:“图根哈特住宅真的能住人吗?”弗里茨·图根哈特(Fritz Tugendhat)很有代表性地把达沃斯的疗养院拿出来作比较,实际上没有人问及疗养院的问题,但是他却作了如下回应:“这房子我住了快一年了,可以毫不犹豫地向您保证,从技术上考察,它可谓五脏俱全,满足了一个现代人所能渴望的一切……在万里无云的霜天,可以把窗户放下来,坐在太阳底下享受白茫茫一片的大地雪景,跟在达沃斯一样。”跟在达沃斯一样,跟在达沃斯的疗养院里一样。
于是,在冬天的时候呢,根据他本人描述,全家人会在起居室里靠在大块的玻璃窗前围坐下来。这些玻璃窗可以整块放下来一直降到地面的高度,使得窗外的景致一览无余。全家人围坐在窗边,享受日光浴和清新空气,望着窗外美丽的雪景,生活就跟在达沃斯的疗养院里一样。这些照片上可以看到他们家的孩子们在花园里光着身子嬉戏玩闹。这场景不禁令人想到生活改革运动* (Lebensreform )。
注*:生活改革(Lebensreform)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20世纪初的德意志帝国和瑞士的一场社会运动,倡导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强调保健食品/生食/有机食品,素食主义,裸体主义,性解放,替代医学,和宗教改革,同时促进了戒酒,戒烟,戒毒和禁打疫苗。
我在做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弗里茨·图根哈特本人在委约这个项目设计时,健康状况不佳,密斯回忆道:“他是个谨小慎微的人,而且身体不太好。他不相信一个医生说的话,而是同时找了好几个医生给他看病。”这里有意思的是,密斯似乎也没有意识到,实际上这样的情形在当时再寻常不过了。因为二十世纪早期的新兴科学/医学还存在着不确定性,所以通常资产阶级和有钱人会咨询不同的医生和其它行医者,以听取不同的医疗建议。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建筑师好像也成了一种新的备选医疗顾问。
我的讲座到此就结束了。非常感谢!

(图118:科伦米娜教授/左;威利斯院长/右)
讲座原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EcbsttGmr0&t=214s
图片来源 / 参考资料:
图1:讲座视频截图
图2:讲座视频截图
图3:https://msd.unimelb.edu.au/explore
图4:https://www.amazon.com/Sexuality-Space-Princeton-Papers-Architecture/dp/1878271083
图5:https://mitpress.mit.edu/books/privacy-and-publicity
图6:https://www.doppiozero.com/rubriche/3/201804/wolfgang-schivelbusch-trump-merkel-e-litalia-provinciale
图7:https://www.amazon.com/Railway-Journey-Industrialization-Nineteenth-Century/dp/0520282264
图8:https://www.nytimes.com/2015/09/18/arts/carl-e-schorske-cultural-historian-dies-at-100.html
图9:https://www.amazon.com/Fin-Siecle-Vienna-Politics-Culture/dp/0394744780
图10:https://www.lars-mueller-publishers.com/x-ray-architecture
图11:https://www.moma.org/collection/works/787
图12:讲座视频截图 原杂志链接
https://www.coam.org/es/fundacion/biblioteca/revista-arquitectura-100-anios/etapa-1946-1958/revista-nacional-arquitectura-n126-Junio-1952
图12:讲座视频截图
图13:https://lh3.googleusercontent.com/proxy/tQpeWVBVtGhaLRHzQhxeAywgQ4wBlbJYpQA8ExPPDc4LR63GCm9esrqPaF_IdiPKytANkl_ZVKaQPGOO1Gu-eIVZQxeXfETR6UZy1E9E94qBQJ8bfY3pwgSpWk4kFCxjK4PLJFEsgJb2Hus_QqoWBs_Gz0Li9Z_q3exdy4q22AgEnYckKumgt5E
原杂志链接
https://www.coam.org/es/fundacion/biblioteca/revista-arquitectura-100-anios/etapa-1946-1958/revista-nacional-arquitectura-n126-Junio-1952
图14: https://www.frieze.com/tags/susan-sontag
图15:https://www.amazon.co.uk/Illness-As-Metaphor-Susan-Sontag/dp/0374520739
图16:讲座视频截图
图17:https://www.researchgate.net/figure/truvian-man-Cesariano-1521-f-49r_fig1_323523814
图18:讲座视频截图
图19:讲座视频截图;https://www.gettyimages.com.au/detail/news-photo/john-banister-giving-an-anatomical-lesson-at-the-barber-news-photo/593279676
图20:左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6/63/Leonardo_da_Vinci_-_Studies_of_the_foetus_in_the_womb.jpg; 右https://www.rct.uk/sites/default/files/collection-online/3/d/262841-1333033283.jpg
图21:左 https://covers.openlibrary.org/b/id/7186784-L.jpg; 右 https://blogs.3ds.com/perspectives/authorship-transformation-aec/
图22:讲座视频截图
图23:讲座视频截图
图24:左 https://www.theromanovfamily.com/wp-content/uploads/2015/09/xray.jpg 右https://en.wikiarquitectura.com/wpcontent/uploads/2017/01/Rascacielos_de_vidrio.jpg
图25:https://www.mdpi.com/arts/arts-07-00078/article_deploy/html/images/arts-07-00078-g001.png
图26:讲座视频截图
图27:https://static.frieze.com/files/inline-images/xraymain3.jpeg
图28:https://www.mdpi.com/arts/arts-07-00078/article_deploy/html/images/arts-07-00078-g008.png
图29:讲座视频截图
图30:左上http://kvadratinterwoven.com/paimio-sanatorium 左下http://solarhousehistory.com/blog/2014/4/30/alvar-aalto-and-solar-geometry 右https://www.architectural-review.com/buildings/revisit-aaltos-paimio-sanatorium-continues-to-radiate-a-profound-sense-of-human-empathy
图31:讲座视频截图
图32:https://archeyes.com/paimio-sanatorium-alvar-aalto/alvar-aalto-paimio-sanatorium-archeyes-terrace/
图33:https://assets-maharam-prod.s3.amazonaws.com/images/story_images/large/1043/stories_muraben_01_05.jpg?1544125496
图34:讲座视频截图
图35:http://blogs.getty.edu/iris/files/2016/04/image005r.jpg?x45884
图36:https://daniellaondesign.com/wp-content/uploads/2021/01/50-003-267_1_orig.jpg
图37:讲座视频截图
图38:讲座视频截图
图39:讲座视频截图
图40:讲座视频截图
图41:https://divisare-res.cloudinary.com/images/c_limit,f_auto,h_2000,q_auto,w_3000/v1526912400/l2ex8hhm1cbyrgxsytbn/alvar-aalto-fabrice-fouillet-paimio-sanatorium.jpg
图42:左https://cdnassets.hw.net/3e/e2/08e2e9444b63be3a08cc6ccbbed4/paimio-aalto-chairs-hero.jpg 右https://d2mpxrrcad19ou.cloudfront.net/item_images/867979/10311802_fullsize.jpg
图43:https://d32dm0rphc51dk.cloudfront.net/jGy2idxxc3b1TpwyDjY50g/large.jpg
图44:讲座视频截图
图45:讲座视频截图
图46:讲座视频截图
图47:讲座视频截图
图48:左https://www.phaidon.com/resource/124-rontgen.jpg;右https://www.theromanovfamily.com/wp-content/uploads/2015/09/xray.jpg
图49:讲座视频截图
图50:讲座视频截图
图51:https://www.woka.com/files/content/gallery/Purkersdorf-Zeichnung-1220.jpg
图52:https://i.pinimg.com/originals/23/80/fc/2380fc53db03094492162601c3575b5f.jpg
图53:讲座视频截图
图54:讲座视频截图
图55:左https://lh3.googleusercontent.com/proxy/tQpeWVBVtGhaLRHzQhxeAywgQ4wBlbJYpQA8ExPPDc4LR63GCm9esrqPaF_IdiPKytANkl_ZVKaQPGOO1Gu-eIVZQxeXfETR6UZy1E9E94qBQJ8bfY3pwgSpWk4kFCxjK4PLJFEsgJb2Hus_QqoWBs_Gz0Li9Z_q3exdy4q22AgEnYckKumgt5E
; 右https://explore.chicagocollections.org/image/uic/59/bz61c7x/
图56:讲座视频截图
图57:讲座视频截图
图58:https://jaromirkrejcar.com/wp-content/uploads/2020/05/12-1024x835.jpg
图59:讲座视频截图
图60:讲座视频截图
图61:讲座视频截图
图62:https://1.bp.blogspot.com/-jbvwD23v8ro/XTV7W3vTKhI/AAAAAAAAglI/M7yDGtqo6IQLbpcL-TajynGaG6NY3ZzXwCLcBGAs/s1600/solarium-saidman-2.jpg
图63:https://3.bp.blogspot.com/--Lbs334H11Y/XTV7YESLoxI/AAAAAAAAglQ/bICyjjCPrugqmA4flFkIsMfF9KhOCvtWwCLcBGAs/s1600/solarium-saidman-4.jpg
图64:讲座视频截图
图65:左https://pbs.twimg.com/media/D_1P5I8XoAAF9lz.jpg ;右https://static.messynessychic.com/wp-content/uploads/2019/07/solarium-saidman-8.jpg
图66:https://i.pinimg.com/originals/81/b2/c5/81b2c543cefafdc7791320615389fb9d.jpg
图67:讲座视频截图
图68:讲座视频截图
图69:讲座视频截图
图70:https://cdn.galleriesnow.net/wp-content/uploads/2018/09/Koloman-Moser-MAK.jpg
图71:https://arielehoffmanculturalcritic.files.wordpress.com/2013/02/berta-zuckerkandl.jpg
图72:讲座视频截图
图73:https://en.wikiarquitectura.com/wp-content/uploads/2017/07/Sanatoriumpurkersdorf-18.jpg
图74:https://d3i71xaburhd42.cloudfront.net/bbd74c5598ec6979eddea0e4841c94114ce0315b/14-Figure18-1.png
图75:讲座视频截图
图76:讲座视频截图
图77:讲座视频截图
图78:讲座视频截图
图79:讲座视频截图
图80:讲座视频截图
图81:https://uploads2.wikiart.org/images/oskar-kokoschka/adolf-loos-1909.jpg!Large.jpg
图82:讲座视频截图
图83:讲座视频截图
图84:讲座视频截图
图85:讲座视频截图
图86:https://nguptacouk.files.wordpress.com/2018/09/scheerbart-nusi-pusi-1912.jpg
图87:https://payload.cargocollective.com/1/2/88505/4547917/Lesabendio-art2-Scheerbart.jpg
图88:https://thinkbelt.org/media/pages/shows/interstitial/x-ray-architecture-beatriz-colomina/3658740091-1588757703/s.87.jpg
图89: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de/a/a1/Sanatorium_Schatzalp%2C_Davos_1900.jpg
图90:https://static2.abitare.it/wp-content/uploads/2019/09/X-RAY-ARCHITECTURE-page088-fig052-en.jpg?v=391875
图91:https://www.swissinfo.ch/resource/image/7863722/landscape_ratio16x9/1920/1080/d70c8fe8e9b6db64ea1483291eab33a1/48A874A189540703CF34DA9ABAFB0234/davos-7874356.jpg
图92:讲座视频截图
图93:https://i.pinimg.com/originals/74/43/08/7443084b8b341b0739004191c85a4a9f.jpg
图94:https://i2.wp.com/we-make-money-not-art.com/wp-content/uploads/2019/03/X-RAY-ARCHITECTURE-page035-fig040.jpg?resize=700%2C507
图95:https://i.pinimg.com/originals/f6/83/7c/f6837cf6c0c9ed9b5018767b9fb46ad4.jpg
图96:http://panathinaeos.files.wordpress.com/2011/07/katja_mann_mit_ihren_sechs_kindern_um_1925.jpg
图97:https://i0.wp.com/www.discoveroutloud.com/wp-content/uploads/2018/12/big_77.jpg?ssl=1
图98:https://en.wikiarquitectura.com/wp-content/uploads/2019/11/Sanatorium-Zonnestraal-arch-4.jpg
图99:讲座视频截图
图100:讲座视频截图
图101:讲座视频截图
图102:讲座视频截图
图103:讲座视频截图
图104:https://lh3.googleusercontent.com/proxy/X9K-IGOf8_KGySgtCztn9KKH_7dDpmBfY0OgzWx_4o5rGdzSUE5jQ_liw4WojoNzhQzFwOfb1OzYEQURKfOqcDbpxiaIowi6qxUzwkkGyDR6k0fFNEmL7m0JNg1zanJA2x0akNlfyn3HeGJUdG4rQA
图105:左 tumblr_m9jb16j4em1qlapqpo1_12801.jpg;https://images.venator-hanstein.de/142_58129_1_l.jpg
图106:https://i.pinimg.com/originals/6c/7c/04/6c7c04619e4d2e49046aa1c63be5e567.jpg图107:https://external-preview.redd.it/n5DMv74GAOK7Cvg8gBrCyHxId3xsvJtaWFaUrEVGf7U.jpg?auto=webp&s=82fa41b7ad038b5fe61e94e41c7383118c0b7ae3
图108:讲座视频截图
图109:https://i0.wp.com/we-make-money-not-art.com/wp-content/uploads/2019/03/X-RAY-ARCHITECTURE-page098-fig066.jpg?resize=700%2C463
图110:https://en.wikiarquitectura.com/wp-content/uploads/2017/01/MansiC3B3n_Tugendhat5.jpg
图111:https://modernism101.com/wp-content/uploads/2015/07/moma_modern_architecture_1932_00.jpg
图112:https://d3525k1ryd2155.cloudfront.net/h/643/096/1035096643.0.x.jpgs
图113:讲座视频截图
图114:讲座视频截图
图115:讲座视频截图
图116:https://xenotheka.caad.arch.ethz.ch/wp-content/uploads/2020/11/image.imageformat.fullwidth.1330505735-850x489.jpg
图117:讲座视频截图
图118:讲座视频截图
*如无特殊说明,本文图片注释来自《X-Ray Architecture》一书,
其它文本注释来自维基百科。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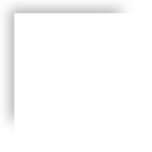
推荐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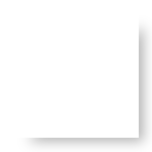
雷锋记录的Beatriz Colomina讲座
现代建筑是冗长的肥皂剧
1953-1979——《花花公子》与现代设计相濡以沫的26年

《X光建筑》(X-RAY ARCHITECTURE),
贝奥特利兹·科伦米娜(Beatriz Colomina)著,2018
https://www.lars-mueller-publishers.com/x-ray-architecture

《帕伊米奥疗养院色彩研究》,阿尔瓦·阿尔多基金会,2015 https://issuu.com/alvaraaltopublications/docs/appendices_cmp___colour_research_pa

马勒第五交响曲。这首曲子是电影《魂断威尼斯(Death in Venice)》的配乐,电影由托马斯·曼的同名小说改编。马勒和曼都是本次讲座中提及的二十世纪“肺结核文化社交圈”的重要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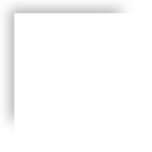
知识星期,一周即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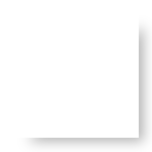
公众号后台回复“X-Ray”,获取部分推荐资料电子版~ 知识星期不定时更新,一周即焚,获取知识请勤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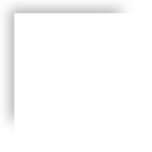
作者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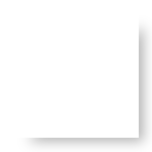

尼基塔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硕士,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访问研究学者(技术哲学与伦理方向)
尼基塔在知识雷锋的其他文章
媒体考古学 |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新事物是如何产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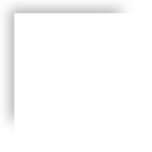
雷锋福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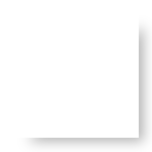
添加小雷锋,邀请您加入“技术时代语言研究所”,由Nikita、翁佳、竞飞等优秀作者坐镇,欢迎分享讨论最新学术资讯,快来加入组织吧~




点击进入小雷锋后台“往期盘点”
2021年,雷锋继续陪你温故知新



关键词
疗养院
医学
疾病
建筑师
医生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