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考古学 |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新事物是如何产生的?

译者:尼基塔



讲座栏目主持人:陈柏旭
全球知识雷锋联合创始人、UCA优思建筑事务所创始人
齐林斯基教授从学生时代起便醉心于媒体研究。他生长于二战结束不久后的欧洲,在百废待兴的大环境中窥到了媒体蕴藏的力量。他通过媒体研究洞鉴古今,又从其广大的涉猎范围中抽取一粟,向台下的学生们揭示事物诞生背后的奥秘。齐林斯基教授是风趣而率真的学者,年少时对探寻事物发展的“执拗”奠定了他一生对媒体研究的热忱。他道:“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媒体研究并非仅仅研究高端文化。我们研究摇滚乐,研究工人剧场,研究各种各样的地下媒体实践,因为这对于思考“媒体究竟为何物”这个问题是极为重要的。
未来和过去不是“事实空间”,而是“潜在空间”
现在回想起来,我后来所从事的全部工作,包括大量的机构、研究、教学工作,以及担任两所大学的校长等等这些工作,和我在最早期所做的这些具有开创性的事情相比,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170篇讲座。
本文整理自2019年11月29日在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举办的讲座,讲座原题为How Does the New Come into the World?Self-Portrait of a Variantologist and an Archaeologist of Art & Media
由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教授主讲。讲座由尼基塔记录整理,由Eileen.W校编。
记录者:尼基塔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硕士
荷兰网络文化研究所(INC)研究员
主讲人: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
(Siegfried Zielinski)

现任瑞士欧洲研究院媒体考古学与技术文化专题米歇尔·福柯讲席教授。2020年受邀在同济大学任客座教授。他曾担任德国柏林艺术大学媒体理论系主任、维勒穆·傅拉瑟文献库主任(至2016年)、德国科隆媒体艺术学院创始院长(1994年-2000年)、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与设计大学校长(2016年-2018年)。
主持人:李麟学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麟和建筑工作室ATELIER L+ 主持建筑师,能量与热力学建筑中心CETA主持人,《时代建筑》专栏主持人
正文共18426字60图,阅读完需要30分钟
译者序

图一: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 摄影 © MONO KROM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教授出生于1951年,属于在二战之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欧洲年轻人。他们困惑、反叛,带着无解的愤怒。他们好像被莫名地塞进一道发生了错位、扭曲和偏离的时空夹层里——面对历史,战争才结束不久,法西斯政权所犯下的疯狂罪行还历历在目;面对此刻,他们正双脚踩在第三帝国的废墟上;而更重要是往后的三四十年,他们将在冷战的政治阴影中度过少年、青年与中年。他们的选择会是什么?1961年8月13日,全长155公里的柏林墙计划将东德与西德分开。这期间,记者出身的库哈斯出于职业敏感,决定前往柏林考察这座具有独特历史和政治意义的“建筑”。库哈斯对柏林墙的调研结果呈现在1972年提交给AA建筑学院的一篇论文中。论文题为《逃离,或者成为建筑自愿的囚徒》(Exodus, or the Voluntary Prisoners of Architecture*),其中写道:“这堵墙是一件杰作。起初不过是用一些可怜巴巴的带刺铁丝网划出一道想象的边界线,然而与这物理的外表比起来,它的心理及象征性效应却是不可估量的……这绝望的感觉是巨大的。建筑是制造绝望的负罪工具,它在人类历史的过往中并不乏先例。”
*注: http://socks-studio.com/2011/03/19/exodus-or-the-voluntary-prisoners-of-architecture/



图二、三、四:库哈斯《逃离,或者成为建筑自愿的囚徒》作品方案部分绘图
1970年,出生于波兰的犹太裔建筑师丹尼尔·李伯斯金从纽约库伯联盟获得了职业建筑师学位,而距离他赢得柏林犹太人博物馆的竞赛还有十九年——1989年,柏林墙倒,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图五、六:由丹尼尔·李伯斯金设计的柏林犹太人博物馆
无线电等通讯技术发明以及密码学等信息情报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尤其是它们在二战中充当纳粹宣传工具这一角色,引起了战后年轻人的关注和批判。“纳粹究竟是如何赢得人心的?”他们一边追问,一边动手拆解和分析这些“理性”工具背后的运作逻辑,由此诞生了“媒体研究”。齐林斯基教授将1970-1980间的活动和经历概括为自己人生中最为宝贵的十年,也是他从事最具有开创性意义工作的十年。这些早年的活动和经历为其后来的媒体理论研究奠定了关键性的基础。1972年他离开马尔堡前往柏林求学,直至1989年在柏林工大取得哲学教授资格后离开。在这前后差不多十七年的时间里,他在柏林工大的全部活动和经历几乎都无法绕开从城市中心穿过去的那堵围墙,而更值得留意的是,他坚决拒绝不加思索地接受以这堵墙为代表的许多既定现实,包括那些人为酿造的历史。
在一次以“城市空间和异托邦场所”为主题的演讲*中,他这样描述道:“1970和1980年代的柏林曾经是最为令人向往的艺术中心,聚集了大批的音乐家、剧场工作者、舞蹈团体、设计师等;在将东德和西德分开的柏林墙的阴影之下,涌现了大量异托邦的驻地、工作室、画廊、场馆,吸引了很多杰出而疯狂的艺术家,他们可以在柏林这座城市试验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
*注:2020年12月12日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在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主办的城市传播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异托邦场所,或曰邂逅的物质主义”。视频观看链接:https://m.bilibili.com/video/BV1Tt4y1k7sb

图七:齐林斯基教授演讲视频截图
1990年代初,齐林斯基教授参与创建德国科隆媒体艺术学院并担任院长。千禧年之后,媒体技术和媒体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和移动通讯设备的普及,媒体已经司空见惯。“媒体已经变成了一个系统,成为了日常性基础设施。”这个时候媒体对于艺术家和艺术创作而言还有什么新奇的启发和意义吗?个体如何在这样的系统性媒体条件下过着高强度的线上线下两栖生活(存在)而不至于产生心理变异和精神分裂?这些问题和思考在2006年出版的《[…媒体之后]》([…After the Media])这本书中得到了具体的阐述,而书的末尾章节中所提出的二十三项宣言则可被视为某种意义上抵抗被媒体系统彻底异化的思想和行动指南。与此同时,齐林斯基教授的研究视角转向了地质学中的“深层时间”,提出了探讨科学、技术与艺术之间深层互动关系的方法学和思想路径,其中包括“变体学”、“媒体时间机器”、“前瞻考古学”等概念和实践方法。
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他所编纂的变体学研究系列丛书的第三卷专门探讨中国的艺术、科学和技术存在于深层时间中的互动关系。在2006年翻译出版的《媒体考古学》(Archäologie Der Medien)的中文版序言中,他为自己未能掌握中文,无法读取中国早期媒体历史的源代码而感到遗憾。序言开头引用了布莱希特1927年的一篇短文中的一段带有修辞色彩的话,以揭示新事物与深层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我记起了一个古老的故事,据说有人向一个中国人夸耀西方文化的优越性。那中国人问道:‘你们有些什么呢?’那人对他说:‘我们有铁路、汽车、电话。’那位中国人很客气地回答他说:‘这些东西,我们倒是已经又给忘记掉了。’说到无线电,我立刻又出现这样一个可怕的印象,似乎它是一个陈旧的装置,是那时由于大洪水的降临而遭到遗忘的东西。”


图八、九:[…After the Media]英文版以及《媒体考古学》中文版封面
我初次见到齐林斯基教授是在他担任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与设计大学校长期间。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博物馆紧邻这座大学,建筑的前身建于1915-1918年间,是当时最大和最先进的工业建筑。厂房在二战结束后转为民用,到了1970年代又被彻底弃用。1997年大楼改造完成,由当时新成立的艺术与媒体博物馆正式入驻并使用至今。 2015年,为纪念建筑的百年诞辰,博物馆在举办展览时拆除了所有白盒子的分区隔墙,将原始粗糙的预制混凝土骨架完全暴露出来。其中1号和2号中庭用于展示艺术家池田亮司基于数据生成的多媒体装置《微观|宏观》(micro|macro),将这座百年工业建筑转变成了一个当下的数据空间,换句话说,这也意味着赖特在二十世纪所提出的“机器、材料和人”的关系,在二十一世纪的技术条件下重新被解读为“媒体、数据和人”的关系。


图十、十一: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博物馆建筑改造前与改造后
(右为池田亮司作品《微观|宏观》展览现场)
齐林斯基教授思维敏捷,精力充沛,对待事物总抱着积极和好奇的心态。我常讶异于他是如何做到的。在我的记忆中,他回信从不拖沓,用词讲究精炼,回答问题条理清晰。他基本不用手机,坚持使用纸和笔进行大量记录、构思和写作。他的父母都是音乐家,他年轻的时候也曾参加过各种动手的实践和劳动。他的经历也佐证了本次讲座中他反复强调的一个理念,即“媒体思想和媒体实践是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在看待“新事物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上,他认为先锋的态度“是在旧事物中发现新东西,而不是在新事物中一味证实旧有的东西”。这句话背后的主题其实也对应着他在媒体考古学中发展起来的方法学所蕴含的借鉴和关联,用他自己的话是这样来概括的:“不要徒劳地去搜寻,而要幸运地去发现(Geglücktes Finden anstatt vergeblicher Suche)”。


图十二、十三:齐林斯基教授2017年在卡尔斯鲁厄艺术与设计大学毕业展开幕仪式上讲话以及现场照片
开场白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还有各位到场的嘉宾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教授来学院做这个讲座。他今天的演讲题目是“新事物是如何产生的?”在他演讲完之后还会有一个嘉宾座谈的环节。下面请允许我先对齐林斯基教授做一个简单介绍。
齐林斯基教授现任瑞士欧洲研究院媒体考古学与技术文化专题米歇尔·福柯讲席教授。他曾担任德国柏林艺术大学媒体理论系主任、维勒穆·傅拉瑟文献库主任(至2016年)、德国科隆媒体艺术学院创始院长(1994年-2000年)、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与设计大学校长(2016年-2018年)。同时,他也出版了大量书籍与论文著述。他的考古学及变体学研究专注于探索艺术与媒介二者之间的关系。他与著名媒体艺术先驱彼得·维贝尔(Peter Weibel)一起策划过许多大型展览。这些项目先后在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博物馆展出,其中包括:《维勒穆·傅拉瑟与艺术》(2015年)、《阿拉的自动机器》(2015年)、《对话——拉蒙·柳利与组合艺术》(2018年)、《运动中的艺术——百件媒体艺术杰作》(2018年)。此外,齐林斯基教授还是布达佩斯艺术大学的荣誉博士和教授,以及柏林艺术学院、北莱茵河-韦斯特伐利亚科学与艺术学院的院士。
现在,有请齐林斯基教授上台演讲。大家欢迎!

图十四:齐林斯基教授同济讲座现场照片
讲座正文

图十五:讲座标题“新事物是如何产生的”
媒体思想是一个很综合的学科,其研究者的背景不尽相同、视角迥异,但我们都怀着共同的兴趣和激情,以媒体为研究对象,并通过媒体来开展创造性工作。我希望今天的演讲不至于令各位感到枯燥,与此同时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因此我想采用“自画像”这一艺术形式,与大家分享过去五十年以来,我在媒体考古学领域所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一些方法论以及理论性的原则。透过这个“自画像”,大家将会看到,五十年前那个与你们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最初是如何开启自己在媒体和艺术领域的思考与实践的,以及后来如何成为了一名国际媒体理论学者。尽管这些成就并不令我引以为傲,但是当我回想我的一生都在从事探索新奇事物,我一直挺开心。
请允许我引用一小段文字来开始今天的演讲。几个月前,也就是2018年,北京的歌德学院邀请我就一个问题作出回应。这个问题恰好也就是今天我演讲的题目:什么是新事物?亦或更确切地说:新事物是如何产生的?以下是我针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回应*:
“我不认为新事物是一个存在论上的事件,面对它,我们得惊诧或雀跃。与我而言,新事物是一种界面,介于两者之间,一边是文化记录下来的过往当下,另一边是尚未存档,尚未成为历史遗产,和作为被管理的自身。界面朝两个方向开放,内居其间的是对艺术、知识和媒体的感觉,它们是我关切的核心。”
后面我会对这段文字作一些解释。请允许我接着再念一小段:
“我将思考潜在未来的新事物理解为一次思想实验的邀请。我认为构筑未来,就是成为艺术和媒体的考古学者兼变体学者(Variantologe),意味着寻找艺术、科学和技术中(另类的)深层时间关系。这些现象的源头引发我灼热的兴趣,一再驱使我重新思考,从中汲取意料之外的变体。在艺术、知识、媒体及其之间相互作用的领域中,先锋从未无中生有地创造世界,更不曾将世界在存有中重新发明。相反,先锋从已经过去的当下穿梭而过,行至未来可能的当下。这个运动的前提,是一种与好奇心有关的态度,它想要的是在旧事物中发现新东西,而不是在新事物中一味证实旧有的东西。”
*注:此处中文翻译来自于歌德学院网站https://www.goethe.de/ins/cn/zh/kul/fok/zkt/21423277.html

图十六:“我们寻找感觉与惊喜”
1960s-1980s:
从马尔堡到柏林
上面这段照着稿子念是多么令人感到乏味,实际上我在演讲时从不这么做。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正式进入主题。

图十七:齐林斯基简历的部分内容
这里我给大家看一眼我的简历,它看起来可能有点奇怪。这上面添加了我学生时期的经历,而正是这些早期的工作和活动,对于往后乃至我一生的职业生涯都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我特意提起这一段经历,也与今天这场讲座所在地(同济大学)的理工科背景有关。回想1960年代末,那时我刚上大学,我开始对电影和无线电这些媒体产生兴趣。但是那个时候的德国大学还没有开设这样的专业,所以不可能有机会学习这些东西。完全不可能。我那时就读于德国马尔堡大学*,他们没有媒体研究这个专业。可我们对媒体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于是,我们便尝试自己来“发明”亦或说是创造出一个新的专业。我用的“发明”这个词并非虚妄。我们没有去找教授。我们决定自己着手创建。这个逻辑很简单:假如你们(大学)不能够提供这样的机会,那么我们(学生)就自发地来创造它。在媒体实践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创办了自己的报纸、杂志、无线电台。我们没有去找教授,打算自己来筹办。我们在学校里上的研讨课涉及面很广,涵盖哲学、考古学、政治科学、语言学、文字学,等等。但是,在媒体研究和媒体实践方面,我们是利用自由时间来开展的,我们大约90%的时间都花在自己的研究上,自己去开创。这一点十分重要。
在这段时间,也就是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早期的这段时间里,我所从事的这项课余活动奠定了我整个职业生涯的基础。它的重要性几乎盖过了后来我在整个学术生涯中所从事的全部工作。当你需要自己动手来完成一项前所未有的事情时,你需要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倾注你所有的激情和好奇心。因为没有教授给你指导,所以你必须分外努力,比所有人都努力很多倍,也因此你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的收获和进步。
*注:历史上的马尔堡大学专注于人文科学领域,二战后一度以哲学与神学研究著称,二十世纪有多位著名神学家如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 1884-1976)和卡尔·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曾在此求学与任教,今天在谷歌地图上搜索马尔堡大学则会看到“其生命科学系最知名”这一标记。


图十八、十九:历史上的马尔堡大学(1891年)和她今天在谷德地图上的标记
1970年代早期我去往柏林深造,当时柏林的大学里已经有了媒体研究这个专业。再后来,我们几个学生和一两个教授一起正式创建了第一个关于媒体研究的研究生课程。这是1980年代早期,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十年。课程名称是“媒体研究与媒体咨询”,而我们的课程就设立在柏林工大的校园中心。
现在回想起来,我后来所从事的全部工作,包括大量的机构、研究、教学工作,以及担任两所大学的校长等等这些工作,和我在最早期所做的这些具有开创性的事情相比,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从1970年到1980年,这期间是我最宝贵的十年。后来在1990年代,我有幸能够在德国创建了第一所艺术和媒体学院,也就是科隆媒体艺术学院,并且创办了很多艺术节。我们在1995年创办了第一个数字媒体艺术节,叫DIGITALE。我们有一个专门为数字声音而举行的艺术节,叫PER_SON*。那时候是两千年初,1990年代下半段,我们还有短片电影节,等等。
*[后期采访补充]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我是在1995年的时候创立DIGITALE艺术节。这个艺术节每年举办一次,场地就在科隆路德维希美术馆的电影档案馆。我们当时关注的是,像电影这样的户外活动在数字条件下能够怎样运作。它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电影艺术节,因为除了电影之外,我们还举办演出、音乐会以及各种各样的户外实践活动。我们是一开始做的DIGITALE艺术节,之后发展成了PER_SON艺术节,后者更多聚焦于声响、声音和音乐方面的实践。PER_SON艺术节一直持续发生到2004年。
媒体思想与媒体实践的
相互关系
回到开头,这里非常重要。屏幕上大家看到的是1970年代的柏林,这大概是1972年的样子。右图右上角的这座大楼是我们成立的研究所,叫作“技术时代语言研究所”。后面我会再讲。这座大楼靠近柏林动物园地铁站。在它后面还有这些建筑,这些公司来自第三帝国*,他们为德国法西斯政府生产制造无线电、电子产品和电视机等设备,它们强大到几乎挟持了整座城市。而我们就身处在这样的权力结构当中,试图开展我们的工作,试图发展出我们自己的媒体实践和思想。
*[后期采访补充]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这家公司的名字是TELEFUNKEN,主要是为纳粹政权生产和制造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它也就是后来的TELECOM的前身。

图二十:印有第三帝国无线电装备厂商公司大楼(右上角)的明信片
对于我们而言,媒体思想和媒体实践一直都是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媒体思想对于我而言,一直是交叉话语(interdiscursive)的实践。从这一点来看,我想同济大学会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可以尝试开创这样的交叉学科实践。“交叉话语”意味着,媒体研究不可能单纯从媒体本身中发展出来,也不能由单一某个学科中发展而来。媒体研究这个领域,总是有各式各样的不同学科,它们相互穿插、重叠,原因是媒体本身就包含了“交叉话语”的属性,也就是跨学科的属性。

图二十一:齐林斯基的写作手稿
在我当时读书的地方,以及1990年代初我所在的大学,已经有电子音乐这个专业。我知道你们这里也有音乐专业,此处我特指声音工程专业。而早在1960年代的柏林工大,我们就创建了战后的第一个声音工程专业。此外,还有语言学,尤其是计算机语言学,以及后来出现的很有影响力的符号学研究,包括研究科学的科学(研究科学的世界观等问题)、实验诗歌、实验剧场和电影等。

图二十二:“媒体思想作为交叉学科的实践”
我在前两天的西岸教育博览会论坛上提到过这些历史,不妨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成立于1961年的研究所,它的名字听起来有点古怪,叫“技术时代语言研究所” *。它的成立牢牢地扎根于各式各样的实践活动中:声音,电子,实验……有关声音、无线电、剧场等多样化的实验。它是游走在边缘的点,处在各种不同话语交汇的中心。
*[后期采访补充]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这所机构的名字叫“技术时代语言研究所(Institute of Language in a Technical Age)”。它是由当时在柏林工大的一些诗人、作家以及文学系的教授们发起的。我在这里提到的这个领域叫“自动语言翻译(automatische Spachübersetzung)”。它是早期的一种智能机器(DENKMASCHINEN)应用。这里涉及到一个实用的场景,就是在1960年代,当时大量的科学论文文献都是用英文写成的,所以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动机。自动翻译要为翻译建立一些例行的规则。其实,当时在俄国也有人在开展相应的一些项目,因为当时的苏联社会使用很多种不同的语言,所以就很有必要有这样一部自动机器来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和沟通。

图二十三:技术时代语言研究所(1961-1972)
大家知道1961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可能在座的各位年轻人不太理解,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对于德国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个背景。1961年,柏林墙把东德和西德分开。因此,成立于1961年的“技术时代语言研究所”,它的背后有着一个特殊的原因。当时有一帮教授和年轻人(学生们)希望给机器一个机会,看看机器是否可以比人类做得更好。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背景。现在你们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在这个研究所后面,矗立着来自第三帝国法西斯政权的标志性建筑,而在我们前方则是一道新筑的围墙,它从整个城市的中心穿过。这一切,或多或少,都是人为的。因此,一个乌托邦的想法就这样诞生了:让我们试试看机器是不是可以做的更好?让我们试试看机器是不是能够写诗?让我们试试看机器是不是会拍电影?当然我们知道机器是拍电影的工具,但是它们懂得艺术性创造吗?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
先锋艺术实验
以上我讲述了这个研究所成立的背景和初衷。对于现在的你们,大概会觉得很难想象。这个研究所成立之后具体开展什么研究呢?其中一个领域是自动翻译:文字和语言的相互转换,语言和无线电之间的转译,等等。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发生在1961年的事情,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实际上,在当时的东德以及东欧,并不止我们这帮人在从事这些探索性活动。在当时的南斯拉夫,尤其是捷克,先锋的实验运动发展十分蓬勃。他们也开始研究计算机,探索计算机在艺术创造中的潜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早在1961年就已经有了计算机艺术和自动翻译研究了。这本杂志是捷克那边的运动中发起的。《比特一》,《比特二》。《比特》是杂志的名称。这个项目的名字叫《新趋势》。他们还组织表演、展览、研讨会等。这是1962年,也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


图二十四、二十五:《比特一》、《比特二》杂志
我在前面提到过,这是身处一所理工科大学的优势,媒体研究可以得到工程技术类学科的支持。在我那时就读的大学里,工程师和技术专家们都非常支持我们,他们马上就意识到:“没错!这些孩子需要用到机器。他们要做实验,没错,那就要给他们一些机器!”于是,我们就有了当时最早期的一些机器。我们最老的录像机——用于录制图像和声音的机器——来自于1964年,半个多世纪以前。有了这些机器,我们就可以动手做实验了。我们还有录音机等等各种各样的设备。我们还得到了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等科学家们的支持。他们也一拍即合:“没错!这些孩子需要机器。他们要做实验。”因此,我的媒体研究和实践最初是从实验室里的动手操作开始的。实验本身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媒介和过程,我们通过实验来获得知识,开发知识,发展新的思想。因此,媒体思想和媒体实践,从一开始就深深烙印在我们所从事的研究活动中。我们注重发展自己的思想,然后通过制作展览等活动,让媒体实践发展出异质多元的形式和方式。

图二十六:《热和冷:1945-69》展览海报
这是我们在1970年代做的一个项目,它由三个大型展览组成,探讨的是东西方世界的冷战,分为三个阶段:40年代、50年代、60年代。你们看到这里有个毛泽东的头像。在那个年代,毛泽东对于我们就像是一个流行文化明星,在他边上的是鲍勃·迪伦,中间还有其它一些摇滚明星。展览中也有部分与毛泽东相关的内容,毕竟那是60年代。我们那时候制作了很大的画册,里面有大量的照片和图像。另外,我们在展览中运用了大量各种不同的媒介和材料,还围绕着我们的研究举办了音乐会和演出等。
这是我在1972年做的一张海报。我呼吁,要从物质的层面去研究媒体。呼吁的提出,意味着当时的德国还没有这样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因此,我们又需要自己动手来创造了。马塞拉*可能发现了,在这里我们其实受到了在巴黎的法国五月革命的影响,我们把他们的图像挪用过来,放到了自己的语境里面*。我记得那时候我二十一岁。我们写了很多文章,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始终贯彻着一种思想,那就是媒体实践和媒体思考始终相互紧密依存。
*注:这里指的是马塞拉·里斯塔(Marcella List)女士,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新媒体部策展人,也是当晚讲座的论坛嘉宾之一。
*[后期采访补充]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那个时候我们利用各种形式的印刷媒介。我在这里展示的这张海报(指涉68年的巴黎五月风暴运动)用的是丝网印刷。无线电在那时候是很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介。在意大利、德国和其它一些国家当时有一个非常激进的自由广播运动(他们广播的大部分内容在当时被列为是非法的)。当我1972年/1973年去到柏林,录像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媒介,在鼓动宣传和视听研究方面。幸运的是,当时在柏林工大我们有一些半职业性质的机器设备,可以供我们做一些实验。

图二十七:二十一岁时的齐林斯基做的一张海报
这些都是我们在非常早期发起的前卫艺术。我们开始研究计算机,开始思考网络计算机的可能性。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的《仙纳都计划》(Project Xanadu)是在1960年代发起的,到了1974年他又出版了关于仙纳都共和国的一本书。尼尔森的作品中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宣言式口号:“现在你能够而且必须了解计算机(You can and must understand computers now)”。这张图像上面有一个朝上的指向天空的拳头。和我们当时在柏林工大时的情况一样,这件作品里的计算机也被尼尔森视作一种自由和解放的象征:计算机也会是一种潜在的空间,可以创造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在我们发展媒体理论、媒体实践以及媒体艺术实践的那起初的十年时间里,这种乌托邦式的想象非常重要。

图二十八:泰德·尼尔森《仙纳都计划》经典标语和拳头的符号
与此同时,我们在哲学方面,尤其是在文化批判理论方面,也受到过很强的训练。霍克海默、本雅明、阿多诺——这些名字你们可能听起来很陌生,但是他们在我那个时代是批判理论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们阅读了很多这些批判理论家们的著作,尤其是与媒体相关的文章和论述,并且试图把这些理论运用到实际的创作中。对大众媒体的文化批判在我们的作品和工作中影响尤为深刻。

图二十九:“文化批判理论”
这是媒体艺术史上非常早期的一个录像作品,今天被视为杰作。这是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和卡罗塔·舒尔曼(Carlota Schoolman)创作于1973年的一件作品,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标题,叫《电视传递大众》(Television Delivers People)。假如我们把“电视”替换成“互联网”,就变成了“互联网传递大众” (Internet Delivers People)。理查德·塞拉在作品中提示:“消费者才是被消费的。你才是那件产品。你是电视的消费品。你被传送到广告商那里,而广告商才是客户。”这件作品把我们惯常所接受的现实给颠倒了过来,让我们看到当时很火的商业电视,尤其是美国商业电视节目,它们背后的运作逻辑是什么,就是把观众传递到消费产业去。

图三十:作品《电视传递大众》
这种批判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当时的批判性理论的影响,我们把它运用到了我们的创作活动中。对于我们当时这帮生活在德国的年轻人,批判法西斯媒体政权传统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年轻时的我花了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好几年的时间,反复地去搜索和研究纳粹工厂生产出的电影,然后分析它们,试图去弄明白那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纳粹的宣传机器究竟是怎样建造出来的,他们究竟是如何成功地给民众洗脑的?

图三十一:纳粹反犹宣传电影《犹太人苏斯》(Jud Süß)剧照
这部电影是1940年代最为重要的一部反犹电影之一,我大概反复看了75次。我们做了很多分析,写了很多文章,然后把这些分析拿出去分享,做成自己的一个项目。这是一部1979年的美国电视剧,讲述的是犹太人大屠杀事件。这本书来自1982年,我们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制作了电影和录像。我们去到了美国,展示我们的研究,跟美国的观众见面和交流。之后我们又回到德国,根据这些经验和话语又生成了大量的媒体创作和活动。

图三十二:齐林斯基对犹太大屠杀的纳粹宣传所作的研究之一
我们也对摇滚乐和流行文化展开了大量研究,因为在那个年代这些东西渗透在了日常生活中,但是跟历史的关系又是暧昧不明的。这张图片上是性手枪乐队(Sex Pistols)的席德维瑟斯(Sid Vicious),他的本名叫约翰·利奇(John Richie)。大家看到,这张照片里的他穿着印有纳粹万字符设计的T恤。当时有各种各样的音乐,各种各样的乐队,都在处理这个主题。这样的题材也是我们在媒体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媒体研究并非仅仅研究高端文化。我们研究摇滚乐,研究工人剧场,研究各种各样的地下媒体实践,因为这对于思考“媒体究竟为何物”这个问题是极为重要的。
*[后期采访补充]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1970年代青年文化的这种表达,呈现为用一种轻浮的方式来使用法西斯的象征性符号,这种态度主要源于想要对资产阶级那些人进行挑衅。针对这种现象我所做的研究和批判其实还牵涉到更大的背景,更大的一个项目,那就是德国社会对于犹太人大屠杀的反应和接受,因为在当时右翼势力还很强,战争也才刚刚结束不久。

图三十三:身穿印有纳粹万字符T恤的性手枪成员席德维瑟斯
下面我讲一讲人与机器的互动关系(non-trivial relationship*)。实验室,或者说具有实验性的实践,贯穿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在我的个人履历中扮演重要角色。不要轻易接受看待人机关系的任何敷衍的说法,不要轻易接受这样的论点:“没错,就是机器的问题”,或者,“好吧,是我太蠢了”,又或者,“哦,我太懒了。”或者索性反过来,“这都是人的问题。”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它是一种相互关联的过程。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方式去验证这种关联性。
*注:关于 non-trivial relationship也有译作“非平凡关系”,可能会让人想到高等数学的“非平凡解”或二阶控制论中的某些概念。此处我依照讲者的解释译作“人机互动关系”,希望去掉多余的晦涩修辞,从而更为直接地指向一个基本问题和事实,那就是人与机器之间不存在单向度(one dimensional)的作用,它们之间不是依照非此即彼(either/or)或者“是与否”判断而生成的单一线性逻辑关系。齐林斯基在这里强调一个动态的交互过程。

图三十四:人与机器的互动关系
从这种动态关系中,我们自己发展出了一个概念并称之为“界面启发法(interface heuristics)”。这个概念不算太旧,这是我们最近几年才发展的一个概念。“界面启发法” 的核心概念是说,机器可以像人类一样,被视为一种主体。机器主体和人类主体可以建立起一种相互的关系,二者相互碰撞、交流、对话并不断加深这种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思想和行为当中可以被形式化(formalizable)的部分,与机器的形式功能建立起了对应的联系,这个部分是可以不断创造出交流和交互关系的。媒体人和媒体机器之间的连结是动态的,它是一种相互的连结。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发展出大量的各式各样的界面和复杂的综合体。由于时间关系,这里我不能够更多地展开。

图三十五:“界面多重性”的演示图表
我们再回到历史。我想给大家看一个例子。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一部机器, 当时的录像机。这是可以录制电子图像的机器。我在1985年发表了相关论文。图片上这台录像机器是当时最早的一部录像机,看起来非常复杂而且很笨重。我当时在一所理工科大学的哲学系里写博士论文。当时很多哲学系教授都还不知道录像机是什么,而我的论文偏偏要研究这个机器的历史,于是我把他们弄得很不高兴。所以我不得不去大学里找了一位工程师,这样我的毕业论文导师就有两位:一位是工程师,一位是哲学家。这是在1984年到1985年之间。后来,很快地,录像机就更新换代了,变成手持式,可以随身携带,只不过体积会比现在的大一些。
图三十六:最早的录像机
人与机器的动态关系为我们打开全新的可能性:和机器一起行动,操作媒体机器。当然这也引发了很多有关的思考,比如在性方面的讨论,在更大的社会影响层面去思考人和机器之间的关系,诸如此类。

图三十七:技术移动性与一种关于人机/身体与性关系的新意识
这里有一个比较简短的例子。我想请大家特别留意,这是1980年代的作品,也就是40年前,你们大多数人在那时候还未出生。在柏林,我跟我的学生们一起,用录像机器做了这件作品。我们用了两台录像机,一个用于播放,一个用于记录。这是蒙太奇拼贴剪辑工具套装。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辅助工具。学生们需要一帧一帧地把素材拼贴到一起。他们需要花好几个小时来研究这些素材,电视和电影的内容,然后构建自己的内容材料。他们没有摄像机,因为摄像机太贵了。他们就自己从电视台或者其它渠道买来一些现成的视觉素材,然后把他们编排到这个短片里。下面我给大家播放一小段影片,让你们感受一下80年代柏林学生的作品。这是Einstürzende Neubauten(字面翻译:倒塌的新建筑),他们是来自柏林的非常重要的一支工业朋克乐队*。
*[后期采访补充]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这件学生作品当时没有正式记录下来存档。它的音乐是 Einstuerzende Neubauten创作的,叫作“HALBER MENSCH(半人)”。Einstuerzende Neubauten这支工业乐队在1980年代对我们的身份认同影响非常大。

图三十八:1980年代学生手动加工的录像作品《Feed My Ego》截屏
艺术不
ART MUST NOT
几年前,艺术家阿希姆·莫内(Achim Mohné)在做一个项目,他邀请我来发明三个单词,或者是一个词组。我把这几个单词写在我们学院大楼的屋顶上。现在这几个字都还在柏林艺术大学其中一幢楼的屋顶上,谷歌摄像头会拍到它们。这是大学的其中一幢楼,这栋楼很大,是当时的媒体艺术系所在的大楼。你们可以看到屋顶上几个字:KUNST MUSS NICHT,意思是“艺术不(ART MUST NOT)”。

图三十九:柏林艺术大学屋顶上的“艺术不(ART MUST NOT)”这三个字
在跟技术或者先进技术/高度标准化的技术打交道的时候,艺术处在历史性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之所以说是一个危险的位置,是因为艺术很容易被用于点缀社会,让后者看起来更好看或者更美好一点。这意味着艺术成为了一种社会服务。这是危险的。“艺术不”的意图就是要阐明这一点:
艺术提倡自由,表达的自由,某种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包容梦想,这些都不必要被语法或者秩序所捆绑。这几个字现在还在大楼的屋顶上。明确地说,学校的校长很不喜欢这件作品。但是它现在还在那儿,因为他也不敢就这么上去把它给抹掉。
前两天我在西岸的论坛中提到,1990年代我有幸能够亲手创建科隆媒体艺术学院,成为欧洲第一所艺术与媒体学院的创始校长。这是一件令我感到非常欣喜的事,因为那是在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所以拥有很多自由和自主的空间去发挥。我们有非常棒的团队。布丽吉塔(Brigitta Zics)*是当时加入学院的一名学生。她今晚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她的经验。当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机器和设备,可以做实验和创作。
*注:布丽吉塔·齐克斯(Brigitta Zics),艺术家,当晚讲座的论坛嘉宾之一。

图四十:1990年代初创建的科隆媒体艺术学院是当时欧洲第一所艺术与媒体学院
这是1970年代我画的一幅草图,上面是一部电视机,一位绅士拿着一把伞,戴着一顶帽子的形象。当时在科隆艺术媒体学院创校初期,教学团队中有两位艺术家,他们看到我的这幅草图,产生了一个灵感,后来创作了一场舞蹈演出。这是在1993-94年的时候呈现的演出。我给大家播放一到两分钟的视频,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件1993年和94年的作品可以被看作是对今天的移动媒体的一种预告。这是意大利录像艺术家法布里齐奥·普莱西(Fabrizio Plessi)和 弗雷德里克·弗拉芒(Frédéric Flamand),后者是一名编舞艺术家。

图四十一:1978年齐林斯基1978年画的一幅素描

图四十二:1994年法布里齐奥·普莱西和弗雷德里克·弗拉芒合作的表演“EX MACHINA”
在一些作品中,艺术家采用了界面(interface)来创造具有表演性的情景。关于这些情景中所使用的新技术以及它们对于人和社会的影响,我们并不是要去验证,而是想要展开来进行实验和讨论。在学院创建后的第一年,我们非常重视和强调这个理念。这是1993年和94年,念本硕课程的学生们创作的其中一件作品。它的名字叫《赛博性(Cyber Sex)》。它通过ISDN连接协议把不同的人的身体连上网。这件作品提出一个问题:假设两个人一个在巴黎,一个在科隆,他们之间可以通过机器而产生互相之间的吸引吗?学生们找来设计师一起设计出这套服装,上面嵌入了电子传感器。穿戴这些电子传感器的身体可以通过ISDN进行交流,这不是以虚拟的方式而是以非常直接的物理方式跟另一个身体进行接触。这件作品引发了很多争议和讨论,另外它也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界面的构建和设计,当时在1990年代还没有专门针对这些东西的研究和开发。所以,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由一群艺术家引发了这些讨论,他们贡献了政治、文化和美学的讨论。
*[后期采访补充]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关于“Cyber Sex”这件作品,我在《AUDIOVISIONS》(英文于1990年翻译出版)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有作过一点讨论。在2004年的时候我还把这件作品带到中国,当时准备参加清华大学的一个展览,可惜的是内容审查没有过,所以最后没能展出来。作品当时用的是ISDN(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network)连接技术,是一种能够高速传送声音信号、图像等的系统。它还用了当时非常昂贵的由Silicon Graphics所生产的计算机,还有早期的3D软件。

图四十三:作品《赛博性(Cyber Sex)》海报
这是一项合作软件项目。在1990年代也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研究,通过这样的圆形物件,以虚拟的方式来完成的。你可以穿梭在非常复杂的信息和文字的海洋中,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用的是著名媒体哲学家维兰·弗拉瑟(Vilém Flusser)的文献档案。你可以对档案中所存储的不同片段进行自由组合,包括声音和文本。

图四十四:作品《合作软件界面》(右)
这是一个录像游戏,非常原始的录像/电脑游戏。你们可能都知道,它曾经是街机游戏。这件作品名字叫“Pain Station”,和电脑游戏史有些渊源,也属于桌面电子游戏。这一组学生用了这样的一种界面,把它打造出一种戏剧化的场景。它的基本设定是这样的:有两个玩家,当其中一个快要输掉,或者是比较慢的那个,就会受到惩罚。这是机器通过电子传感器来感应和判断,然后自动做出的一种物理性惩罚,惩罚的部位是手。这个场面充满了戏剧性张力。我下面给大家播放一段。学生们构建这个戏剧性场景的意图是希望探讨人和机器之间的关系,例如,我们在跟机器进行交互和以娱乐为目的时,到底可以走到多远?这件作品把“酷刑惩罚”的装置放进来讨论。这是机器自发的一种惩罚机制。这件作品做出来也可以是一项公共活动,一个戏剧表演。我把它称作是“界面的戏剧化”。

图四十五:玩家在玩《Pain Station》时输掉的一方接受惩罚的情景
媒体之后
After the Media
2000年初,我转向思考“媒体之后的艺术”这个问题。因为我越来越认识到,媒体已经系统化了。媒体变成了一个系统。它们已经变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基础设施的一个部分。这一点意味着对于艺术创作而言,媒体已经不再那么有趣了。那么,后面打算怎么做呢?这是大学的义务。大学需要为年轻人,为年轻的学生们提出具有前瞻性的策略,要让创作者站在前沿的角度。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难给出答案。
2005年的时候,我看到这样一幅拍摄于科隆梅拉顿-弗里德霍夫墓园(Melatten-Friedhof)的照片。照片上这块墓碑长得就是一副移动电话的样子。我的解释是,这意味着媒体的巅峰时刻已经过去了。这是一座为已逝媒体而立的纪念碑。我们需要思考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当然,这块墓碑本身用意完全不是这个概念,可能他们所设想的是通过这块长得像移动电话的石头,让死者跟上帝之间交流起来更方便。

图四十六:出现在科隆梅拉顿-弗里德霍夫墓园里的一块长得像移动电话的墓碑
从那时开始,我转向了对于“深层时间”的思考:深层时间的媒体历史和发展。我完全确信的是,我们通过深层时间的运行,透过层叠的深时媒体,可以穿越现在,进入潜在未来。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艰深的哲学问题。我希望把这个问题简化一下,在这里激发大家一起来思考。这意味着,
未来和过去不是“事实空间”,而是“潜在空间”。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处理,也可以那样来处理;你可以提出这样的公式,也可以提出那样的构想。未来和过去的开放性是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能够来讨论“媒体时间机器”,以及艺术、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
下面我给大家看几个例子,解释一下这个概念是怎样运作的。我所思考的,我的方法和理论概念中,这部时间机器有两个时间箭头,其中一个箭头是指向未来的,另外一个箭头指向过去。当这两个箭头在想象的事物中相遇,惊奇(surprise)就会发生。这样一个惊奇的发生空间,也就是在大学里面不同学科之间产生碰撞的空间。跨学科,或者是惊奇发生器(gnerators of surprise),也就是过去和未来的潜在空间。

图四十七:“媒体时间机器”的概念演示
深层时间:
科学、技术与艺术之关联
在我着手开展媒体深层时间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的时候,做了一个关于中国的项目,探讨中国的深层时间。我邀请了中国的科学家和科学史专家戴念祖。他是一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他在数学、物理学,以及科学、声学和电学历史等方面都有专门研究。参加这个工作坊的还有一位他的学生,来自安徽合肥的徐飞*。徐飞是位考古学家、音乐历史与理论的研究专家、同时也是计算机科学家。我们组织了整整一个星期的工作坊,探讨中国文化的深层时间,考察科学、技术、艺术之间的关系。
*注:徐飞,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哲学系,其会议论文发表于《变体学3》,题为《中国古代乐律声学探究及其成就》(The Exploration and Achievements of Acoustics of Yue-Lu in Ancient China)。

图四十八:《变体学》第三卷封面与封底
在这个工作坊的交流中,我们碰撞出了一个“惊奇”,它是一个表演,是一部会下象棋的自动机器,它来自元朝。这是在公元前二世纪,你们可以把这个叫做早期的象棋自动机。棋盘上这些棋子是用金属和雄鸡血制作的,棋盘用的是磁敏材料,会把棋子吸住,让棋子在棋盘上不断移动,并且不受人的控制。因此,这个自动机械装置的运动其实是脱离人为控制的,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动机。中国的专家们把这个人造物件挖掘出来,然后放入到现在的这个时空中,让年轻的学生们以及那些玩计算机游戏的人都大为惊叹。

图四十九:考古发现的会自主下象棋的机械装置
我们尝试深入到中国和希腊文明的传统中去探索科学、技术与艺术之间的深层互动。在这个案例中,主要是中国的传统,涉及乐器的调律系统。这里展示的调律系统构造跟器乐主要是笛子和丝弦乐器。这个乐器叫做骨笛,也是来自公元前。这个调律系统,它所涉及的技术,以及这个乐器出现在那时候的中国,都可以说是非常先进的,我们反倒对此没有感到特别惊讶。徐飞在工作坊中演奏了一段用骨笛吹出的音乐。根据考古记载,这个乐器大概有七千到八千年的历史,它可以吹奏出完整的八音。多年前徐飞在贾湖挖掘到的这个骨笛能演奏出现代音乐的完整音程。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什么是进步?什么是技术的进步?


图五十、五十一:考古发现的骨笛和吹笛子的人像雕塑
这些都是我们在思考的一些根本问题,包括艺术与科学在演算方面所产生的关系。比如,音乐的调律系统,它需要非常强大的计算工具。算盘当然是最早期的一个计算工具,能够以数学的方法演算出调律系统。当一个算盘不够用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好几个算法来搭建更为复杂的演算工具,可以有平行的演算系统,很有效也很可靠。

图五十二:中国古代的平行演算系统
以上我们谈的是千年前的文化,科学文化。大约又过了五六百年,早期的欧洲文艺复兴,也可以说是是欧洲现代早期,出现了这种盒子。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把它叫做“数字柜(Cassetta mathematica)”,现在我们把它叫做个人计算机。机器上方是菜单栏,在垂直面你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数学应用,还有数学公式,按照这些公式可以搭建出非常复杂的数学演算工具。基歇尔把这个转译成一个音乐的世界,并且在17世纪的中叶制作出历史上的第一支编曲机器,即音序器。这个物件名字叫“音乐方舟(Arc Musarithmica)”。它是一部简易作曲机器,用于制作和声音乐。可以把这些不同的板抽出来,这些竖向排列的板,然后把他们组合成不同的形式,然后就可以生成一些简单的音乐结构了。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说,它能够创作出多么复杂的音乐,而是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部机器是1650年的时候发明的。而且,它跟现代的作曲机器没有特别大的差别,只是现在人们用的技术以及硬件方面发生了改变,而核心的软件,核心的思想和概念,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图五十三:基歇尔的“数字柜”

图五十四:基歇尔的音乐方舟”
前瞻考古学
Pro-spective Archaeologies
最后我想要讲一点可能对大家而言比较感兴趣的东西,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在这个大学,最近的十年时间里,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前瞻考古学(Pro-spective Archaeologies)”。“前瞻考古学”到底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简单来讲,它是关于如何透过思辨推理(speculative reasoning)来完成从过去到未来的穿越。在这里,我在前面所提到的时间机器又出现了,但是这一次是形式非常具体的机器。我们在这个项目中所做的是,重新发现过去那些非常复杂的机器装置和艺术装置,换句话说,也就是好几个世纪以前的媒体艺术。我们把这些东西挖掘出来,对它们进行分析研究,再重新把它们构造出来,跟学生一起重新制作这些古老的装置。通过这样的再造方式,通过这些机器,我们可以发现通往潜在未来的思想。
这件作品名叫《自动音乐装置(Music Automaton)》,它的原型来自于9世纪巴格达的智慧宫,它最早是在公元850年被发明和打造出来的。这部机器可以录制音乐,比如说笛子吹出来的音乐。同时在机器的另一边还可以演奏,通过这个程序来演奏。这个程序的机关就在这个鼓这里,它会旋转,上面有不同的孔,有的深一点,有的浅一点,诸如此类。这些孔在转动的机械部件上,然后通过这些孔的开口,这个笛子便可以开始演奏了*。项目的参与者包括一位在机械电子方面非常有才华的中国学生,他打造了机械传动装置部分。还有一名俄罗斯的学生,他做了动画的部分。
*注:这个机器的运作原理是在旋转的部件上打深浅不一的洞来控制机器的按压程度,从而模仿手指在笛子孔洞上的按压以达到演奏效果。

图五十五:《自动音乐装置(Music Automaton)》
我想顺便提一下,在同济你们有很棒的动画系,这已经让我们十分羡慕。上面展示的这件作品其实就是一件动画作品,它使用到木料、金属还有一点其它的材料,然后学生们把它打造成了一件基于时间的动力装置。这就是我所说的“扩展动画”(expanded animation)的概念。今年一月份在深圳有一个艺术节,他们邀请我写了一篇文章,阐述“扩展动画”的概念。他们还有一本书,以及一些其它文本材料,都是以中文出版的,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
说到这儿其实我的演讲大概差不多快要结束了。我最近策划的一个项目是一个大型展览,同时也是一个大型出版项目,主题是关于拉蒙·柳利(Ramon Lull)和他的思想机器(thinking machine)。这张图上你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纸质计算机,它们可以被称为思想机器。这些纸质机器是可以生成讯息和文本的,就像是思考机器一样地运作。你可以对机器提一个简单的问题,让机器来回答。在这个例子里面,这些问题有关于上帝的,关于宗教的,还有关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机器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一个修道士僧侣、哲学家发明的,他的名字叫拉蒙·柳利。这本书的印刷出现在后来稍微晚一点的时候,它的手稿则创作于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请大家留意,这是在七百年前的发明,它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由于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就不多展开了。

图五十六:拉蒙·柳利的组合艺术
在这里,拉蒙·柳利的出发点非常简单:基督徒、犹太教徒、穆斯林教徒,虽然他们相互之间无法理解对方,但我们不能就这么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个现象。我们可以从这一刻开始构想,这三种宗教各自都有一本典籍——《圣经》、《可兰经》(al-qurʾān)和《希伯来圣经》(Tanakh)。这三种宗教都基于同一个理念,那就是信奉一个神,只是他们分别采用了三种不同的语言。我们可以发明一种符号语言来促成三种语言间的交流,也可以发展出名叫“组合艺术(Ars Magna Combinatoria)”的具体方法,然后通过这三种不同的步骤来创造出一部思想机器,它可以帮助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进行相互交流和理解。

图五十七:拉蒙·柳利的思想机器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想法,它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启发了很多欧洲的思想家,其中包括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 )在1666年所撰写的《有关组合艺术的论文》(Dissertatio de arte combinatoria )。左边的这本书是莱布尼茨撰写的,右边是莱布尼茨翻译了中国的《易经》,把它转译成了包含0和1两个符号的二进制系统。易经中包含了许多长线、短线、和它们的组合,这是欧洲二进制代码发展的先驱。除了莱布尼茨,当然还有其它人对此展开研究,比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他们发展出了不同的方向。但是,莱布尼茨是在17世纪发明了二进制代码,在当时可以说这是非常具有先锋意义的。莱布尼茨所知道的这些来自中国的知识,是通过当时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带回去的一些器物而获得的,比如这个碟子,上面就有《易经》的符号,这启发了他。基歇尔在他的著作《科学的艺术》(The Art of Science)中也提到了许多关于组合系统的内容,这里我就不深入探讨了。

图五十八:莱布尼茨《有关组合艺术的论文》和他根据《易经》发明的二进制系统
在“前瞻考古学”这个项目中我们所做的这种“重建”工作,范围也涉及到20世纪的早期计算机,早期软件和硬件,等等。我在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博物馆创立了一个特别项目,叫“文献研究驻场项目(Archivists in Residence)”。这个项目就是为了培训专门的人才来从事这种重建工作的。最近我也希望可以在深圳或者上海来开展这一类项目,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契机。
2017年我们在捷克布鲁日重新制作了一场在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电子音乐会,叫《汽笛交响曲》(Symphony of Sirens),也叫《工厂汽笛交响曲》(Symphony of Factory Sirens)。这场音乐会在历史上只演出过两次,一次是1922年在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另外一次是1923年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它很可能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一场电子音乐演出。在这场由人和机器协作完成的户外集体演奏中,作曲家和指挥家阿尔谢尼·埃弗拉莫夫(Arseny Avraamov)把两座城市(巴库和莫斯科)变成了一件庞大的乐器。由于演奏会的演奏家和演奏机器分布在城市空间的不同角落,乐曲的现场指挥埃弗拉莫夫不得不爬到一座高楼的屋顶,站在上面奋力挥舞着手中的旗子。参与整场演出的除了有两千人组成的合唱团,还有各式各样的机器:枪、大炮、飞机、火车头,等等。

图五十九:齐林斯基指挥的《汽笛交响曲》(2017年)
你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部分的乐器。我站在前面这里,扮演的是埃弗拉莫夫的角色,后来我又跑到了屋顶上来指挥这场演出。我们动用了各种机械的枪支和大炮、火车头、摩托车、以及汽车和各种机器设备作为乐器。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无穷的乐趣。有很多人加入我们,他们有来自冰球队的、足球队的、合唱团的,来自捷克全国上下的不同地方。这是非常难忘的有趣经历。
最后,我想对我的演讲内容作一个简单总结。当我回顾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媒体思想和媒体实践所在的文化和现实对于我而言是世界的(mondial),而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它是具有普适性的,同时也富含着多重性和多样性(multifarious);它是关乎宇宙的(cosmic),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anthropocentric);它是多线性的和动态变化着的(multi-linear and dynamic ),而非单线性的(mono linear)。当我愈深入到时间中,就愈发要不断地将不同文化和动态系统纳入到我的思考和实践体系。以此为基础,我想我们可以开拓出具有不同可能性的未来。

图六十:讲座最后总结的要点
讲座来源:尼基塔现场录音
图片来源 / 参考资料:
文章开头gif:截取自《汽笛交响曲》(2017)https://www.br.de/mediathek/video/hoerspiel-live-auffuehrung-in-bruenn-tschechien-symphonie-der-sirenen-av:5b56d871b1689c0018e176c7
图一:由讲者惠允
图二、三、四:http://socks-studio.com/2011/03/19/exodus-or-the-voluntary-prisoners-of-architecture/
图五、六:https://www.archdaily.cn/cn/928617/adjing-dian-bo-lin-you-tai-ren-bo-wu-guan-studio-libeskind?ad_source=search&ad_medium=search_result_all
图七:https://m.bilibili.com/video/BV1Tt4y1k7sb
图八、九:讲座PPT演示稿
图十、十一:https://zkm.de/en/about-the-zkm/entstehung-philosophie/architecture
图十二、十三:尼基塔私人档案库藏
图十四:尼基塔私人档案库藏
图十五:讲座PPT演示稿
图十六:讲座PPT演示稿
图十七:讲座PPT演示稿
图十八、十九: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arburg_old_university_post-1891.jpg;谷歌地图搜索截图
图二十:讲座PPT演示稿
图二十一:讲座PPT演示稿
图二十二:讲座PPT演示稿
图二十三:讲座PPT演示稿
图二十四、二十五:讲座PPT演示稿
图二十六:讲座PPT演示稿
图二十七:讲座PPT演示稿
图二十八:讲座PPT演示稿
图二十九:讲座PPT演示稿
图三十:讲座PPT演示稿
图三十一:讲座PPT演示稿
图三十二:讲座PPT演示稿
图三十三:讲座PPT演示稿
图三十四:讲座PPT演示稿
图三十五:讲座PPT演示稿
图三十六:讲座PPT演示稿
图三十七:讲座PPT演示稿
图三十八:讲座PPT演示稿
图三十九:讲座PPT演示稿
图四十:讲座PPT演示稿
图四十一、四十二:讲座PPT演示稿
图四十三:讲座PPT演示稿
图四十四:讲座PPT演示稿
图四十五:讲座PPT演示稿
图四十六:讲座PPT演示稿
图四十七:讲座PPT演示稿
图四十八:讲座PPT演示稿
图四十九:讲座PPT演示稿
图五十、五十一:讲座PPT演示稿
图五十二:讲座PPT演示稿
图五十三、五十四:讲座PPT演示稿
图五十五:©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博物馆
图五十六:讲座PPT演示稿
图五十七:讲座PPT演示稿
图五十八:讲座PPT演示稿
图五十九:讲座PPT演示稿
图六十:讲座PPT演示稿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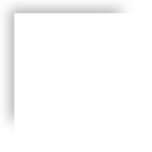
推荐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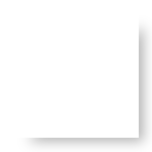

[...After the Media] (2013), Siegfried Zielinski

齐林斯基教授和FM Einheit合作的电台
网址:https://musicaeterna.org/media/radio/fm-module-21-expendi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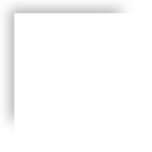
作者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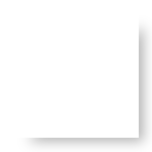

尼基塔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硕士,荷兰网络文化研究所(INC)研究员。[email protect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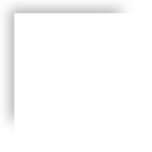
雷锋福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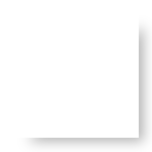
欢迎添加“唠嗑小雷锋”,邀请您加入英国知识雷锋粉丝群,由英国大牛作者坐镇,会热心答疑解惑、学习讨论,快来加入组织吧”(•̀ᴗ•́)و ̑̑



点击进入小雷锋后台“往期盘点”
2021年,雷锋继续陪你温故知新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