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玮 | 《约伯记》与中国人的认识论(一)


作者 | 施玮博士
文章来源 | 香柏原创
周姿研授权香柏
正文 TEXT↘
当代中国文化思潮多元而纷杂,但仔细分析,一部分是传统文化贴了新标签;一部分是概念、口号式的,并无具体、实质性的内容;还有一些是东西方文化表层、初步碰撞的产物。我认为后二者目前对民众思想根基的影响并不大,而传统中国文化以及它在今天的渐变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目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传统儒家思想,以及借着新儒学思潮表现出来的,传统中国文化和当下民众生活、思想、情感的互动与发展趋向。

随着世界进入地球村、E世代,从表面上看,资讯极为发达,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似乎已经很接近,但实质上现象背后的文化根源仍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西方神学教义类的书藉翻译很多,但实质上基督教思想仍没有真正深入地与中国文化对话。这正是文化宣教以及中色神学建立所要面对的具体问题。
人心思意念中,最深的渴望和困境,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核心问题是世界观、价值观问题。本文试图借助对《约伯记》表现的人对世界和人生、上帝和真理的认识及方法与途径的分析,来对照剖析中国人的上帝观和人生观,尝试了解中国人在认识上帝与真理途径中的阻碍。
对真理的追寻与求问,西方追问存在,中国追求审美;西方讲求结果,中国推崇过程。对上帝的认识,西方讲求的是存在与否(抽象观念),中国讲求的是他与我的关系(具体关系);对信仰、教义,西方追求的是严密性,中国追求的是实用性。在秋痕编写的《论中国现代新儒家》一文中,就引述了梁漱溟先生的观点作为新儒学思想的代表。“东方人讲哲学都是想求得一个生命,西方人只想求得知识,…中国哲学的方法为直觉,着眼研究者在‘生’。…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流畅的去生发。”
从中国人常问的问题中就可以有此感受。若上帝存在,为何好人无好报,恶人反倒昌盛?灾难临到是上帝的惩罚吗?伴君如伴虎,从旧约看上帝不也是喜怒无常?对神明,敬而只能远之。人和神的关系怎能亲近?如何亲近?有道德的人、历史中的圣贤在天堂还是地狱?因此,我觉得以神学教义来对话,不如以《圣经》中的人物与故事来启发。

《约伯记》中约伯作为一位非以色列民族的贤者,全书借着他的故事与思想和辩论,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探索上帝的形象,以及人与上帝的关系,并由此看人生命存在的本质。中国人在认识上帝、接受信仰中遇到的问题、存在的偏差,此书卷中大都有相应的探讨;而作为最古老的诗剧,其结构与语言上的优美生动和场景的简化抽象,也相当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借着人物和故事呈现哲理的寓言式文体也是中国人熟悉的。因此,笔者选择《约伯记》来探讨中国文化中的认识论。
第一 自我判断与善恶报应
在《约伯记》第一句中就说出了人类文化中的“义人”概念,也相当于中国人的“好人”、“君子”、“圣贤”等。
“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三个词描述了作为“好人”的三个方面:品格、信仰、行为。品格是关于个人所是的问题;而信仰与行为,是关于个人所为的方面:一是与神、天地的关系,一是与人的关系;一是内在的,一是外显的。
虽然在后现代,或是所谓后—后现代文化中,模糊、挑战了“好人”“坏人”的界定,更强调人性中善恶同存的相对性与滑动性。例如“北京好人”这部2010年11月刚刚在北京首轮上演,就获得关注与好评的实验话剧。但仔细一想,这与传统“好人”“坏人”定义并无分别,只是二者同在一体,有二个“我”而已。

《约伯记》以一个圣贤的好人为例,就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因人自身的缺点而遭至正当的惩罚。中国人在谈论得救问题时也一样,会以孔子、雷锋、等“好人”、“君子”为例,在我们面对“孔子得不得救?”“某某这样的好人也都下地狱?”这类问题时,问话对象其实关心的不是孔子或别的什么人是否得救,他们所关心的是自我完善的价值,与祸福奖惩的公平性。《约伯记》以这样一个完全的贤者为例,正是回应了人最本质的思虑。
对祸福奖惩公平性的诉求,也就是通常认为“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才是天理,才是老天当有的公平。而这个诉求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提出来的,因为它是由人自己判断好与恶的标准,又要求神按照人的奖惩原则来降祸降福。这也是构建起功德、福祸、奖惩等宗教和人文思想的基础。《约伯记》中的辩论,特别是最后神亲自的显现与讲论,就回应了这个问题,我将在下文一步步分析。
《约伯记》第一章中,第二、三节就讲了约伯的蒙福:“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这里所讲的就是人类文化中普遍的“蒙福”观:儿女、家产、地位。这两节与第一节相联,就形成了表面上的因果关系,但这个因果关系并非是上帝所定的,而是人的认为。传统思想和经验主义都是建立在人对事物表面的观察,并受到人善恶判断与趋向的影响,人却将这种判断,这种因果关系,看成是必然的,是上帝的律,或者准确的说是一个高于上帝的律,是上帝也必需遵行的律。

当耶和华问撒但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记》1:8)时,神并没有说约伯在地上的儿女、财产、地位,是因他的义而得的奖赏。神欣赏、夸奖约伯的所是、所为,而撒但挑战的是约伯为义的目的。若约伯是为了积功德而蒙祝福,那么他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与一般人无二。就像不信的人常说:“神若祝福我…我也会信的。”;“神那么祝福他,给他…他当然爱主。”
有些教会的传道人迎合这种自我中心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企图以“成功神学”来引导人“信主、爱主”,这是对神不认识的“瞎子”行为。而耶稣说过:“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 在《约伯记》第一、二章中,上帝耶和华二次允许撒但攻击约伯的所有,就是要断开人的行善与神的祝福之间的因果关系,强调神奖惩的主权,也是为了将人的眼目从地上的祸福、物质的得失,转向对神的永能与神性的追求和认识。
人对苦难的感受,不仅仅是物质的得失,更是心理上的委曲与不平,苦难破坏了人心中的自我判断系统。每个人的心中虽不敢认定自己圣贤,是完全人,但都认为自己是趋善的。按照善蒙福、恶降祸的自我判断系统,就产生了各种不平:我的善,得到相当的祝福了吗?我的恶,大到与所降的祸相当吗?与我同样程度善恶的人福祸如何?
而一旦,我所看到并感受的福祸与我所判定自己的善恶不相当时,我痛苦是因为我失去了自己作为判定者的存在性。在此,人判断自己以及他人的善恶标准,都是自己的判定。即便在儒家思想中,善与诚的概念虽然强调的是顺“天命”、“自然”,而这个“顺”仍是顺自我(包括自然所接受的文化)的标准。

谢文郁在《<中庸>君子论:困境和出路》一文中指出:
《中庸》从‘率性之谓道’出发,展现了这样一种君子生存:适当地按照天命所赋的本性为人处事。…于是,问题似乎就转变为一个认识论问题:人的本性是什么?……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生存中的每时每刻都是在一定的自我本性认识的引导下进行判断选择,率性而动。…人如何能打破自己的一弊之见,完善对自我本性的认识?
“基督教的罪人概念要强调的是,人无法依靠自己来遵循神的旨意,我们这样看,对于基督教来说,好的生存是在神的旨意中的生存。”信仰者能够战胜苦难的原因,正是我们交出了自己的判断权,降服与神的主权,神的主权与神的判断构成了我们存在的基石,我们只是个领受者和跟随者。因此,苦难就无法破坏我们里面的判断系统。
成功神学表面上可以吸引人来羡慕基督徒生活,来爱主。但实质上,成功神学吸引来的羡慕,不是羡慕基督徒里面基督的生命,而是羡慕一些“有荣耀”的基督徒外显的物质上的蒙福。本质上说,基督生命的内住,与符合社会价值观的“成功”,并没有本质上必然的联系。成功神学只是加强了人在罪性中原有的自我判断系统,并没有一个从人本主义到神本主义的主权交接过程。于是,这样的“信徒”所爱的“神”,只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判断系统的“神”,一旦神所做的事超出了他们自己的判断框架,他们就会怀疑、愤怒、恐慌、并进入更大的苦难。
刘清虔先生说:
在约伯的心中,上帝作为的标准是“德福一致”,也就是说,有德者必能蒙福,上帝的赏赐乃是临在于有德者,“有德”即是对上帝忠诚。约伯因为敬畏上帝,故为人正直,并远离恶事;他深怕稍有恶念而得罪上帝,甚至致使上帝收回对他的祝福;他也深怕他的儿子得罪上帝,故要他的儿子自洁并亲自为他们献祭。在约伯的观念里,只要敬畏上帝,上帝必能保住他的产业且不止息地赐福他,而只要做到“无可指谪”,上帝就无降祸的理由。

在《约伯记》一、二章中,耶和华允许撒旦的攻击,就是挑战并打破了人的这个判断系统,以启示上帝之道中的“善”。
第2节 人对上帝的原始认知
中国人对“天”的概念中,就如《中庸》开篇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是有位格的,有喜怒哀乐,给了人本性,但祂不再管理人间,而是高高在上。而对于有可能与人的生活发生关系的“鬼神”,就是灵界的生物,则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因此儒家的关注点是人与人的关系,而非人与天的关系。以至王阳明弟子问他,“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渊泉如渊’地位时,先生曰:‘人心是天,渊。’”中国文化中淡化了天道的外在于人的实存性,而强调人里面对天道认知,并甚而认为天道就在人里面,也只在人里面。这也是造成新儒学学者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物的关系”的偏差与误读,外在于人的真实存在,并非只有物,更有造物也造人的上帝。
在中国历史中的各种祭祀活动中,敬畏的成份是主要的。在中国文化中大都回避对神的探讨,若说有一定成份对上帝的认知,也仅限于他是位降祸降福的审判者。

约伯起初对上帝的认知,也与中国文化中一样,主要在“敬畏”上。不仅在开始对约伯的描述里,还是在上帝口中向撒但的夸赞里,都反复说到他“敬畏神”的品质。并且,我们在第五节中看到约伯为儿女献祭。“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约伯这样行,并非是因为他得到了上帝的什么旨意,也不是知道儿女犯了得罪上帝的过犯,只是出于“敬畏”,不要让上帝有降祸的理由。同时,他并不认为需要更多地认识上帝,而只需要敬畏,就可以让上帝喜悦,降福于他,并保守他的福。而后来,当他落在苦难中时,第三章里,他求出生的那日灭没,“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于其上。”(《约伯记》3:1-4)其实,这与他后来不断求神的眼目不要看他、放过他,是一样的心态,就像亚当、夏娃犯罪后所做的--自我隐藏、躲避神的面。这两种反映,所表现出来的他对神的认知是一样的,那就是神是一位审判者。这也是中国人对神、对天的原始认知。
在对中国文化的历代宣教中,甚至在中国人信主后的成长中、中色神学的研究发展中,我们都会遇到这个原始认知的不同表现形式。
例如,在宣教、传福音过程中,底层民众容易倾向信神迹、求神迹,为自己的实际生活需求来“信”上帝,一旦成为信徒后,他们也不渴望更多知道上帝的属性。对于这群“信”神,而不在乎认识信的是一位怎样的神的人。一般正面的观点是:这是简单的信心,很好!负面的观点是:功利主义、拜偶像的心态等。但我认为,若联系到人类对上帝的原始认知,和中国文化来看这个现象,就会发现不正确的“敬畏”之心,产生了他们心理上对神的隐藏。只有更多诠释并强调上帝的各种属性--神的名,并指出中国人心中原始上帝观的偏差,才可以事半功倍。为以后信徒与神建立个人性的关系、灵性成熟打下基础,也才能避免信徒和教会被异教邪说侵扰、破坏,使得我们的宣教是有根基的、果效长存的。

向老年知识分子宣教时,我们常遇到他们的回避。他们因为受儒学影响,对神迹奇事视为怪力乱神而不谈论。对造物主上帝,他们视不言为敬。因此,看到基督徒表现出来的与上帝亲近和同在,他们会认为是不敬。
对中青年知识分子宣教时,他们最多提到的就是旧约中上帝的“可怕”、“残暴”,与新约中“爱”的神不统一。表面上看,他们是无法接受旧约里的神,其实这个神的样式是他们潜意识中上帝的样子,他们要躲避。而新约里的耶稣基督是良友、是良人、是爱,因此在新约福音书中也很少有关上帝全部属性的描述,而单单偏重爱与陪伴。这时,他们不再逃避,但他们不逃避的不是三位一体的神,而是被取圣诞老公公般的“天父”,他们内心中仍然逃避了那位可敬畏的、审判的主。
同样,在华人教会中的反智倾向,虽然起因很多,但究其根本,也是受到了这种错误“敬畏”观的影响。
《约伯记》中接下来三轮关于罪与苦难的探讨,都是建立在这个对上帝的原始认知上,人与上帝的关系只剩“敬畏”。而这个敬畏却又是出于上一章所说的,人的认识论中“德福一至”、“祸福奖惩”规则上的。因此,这种“敬畏”,是人本的,而非神本的。

——战善战 尽程途 守主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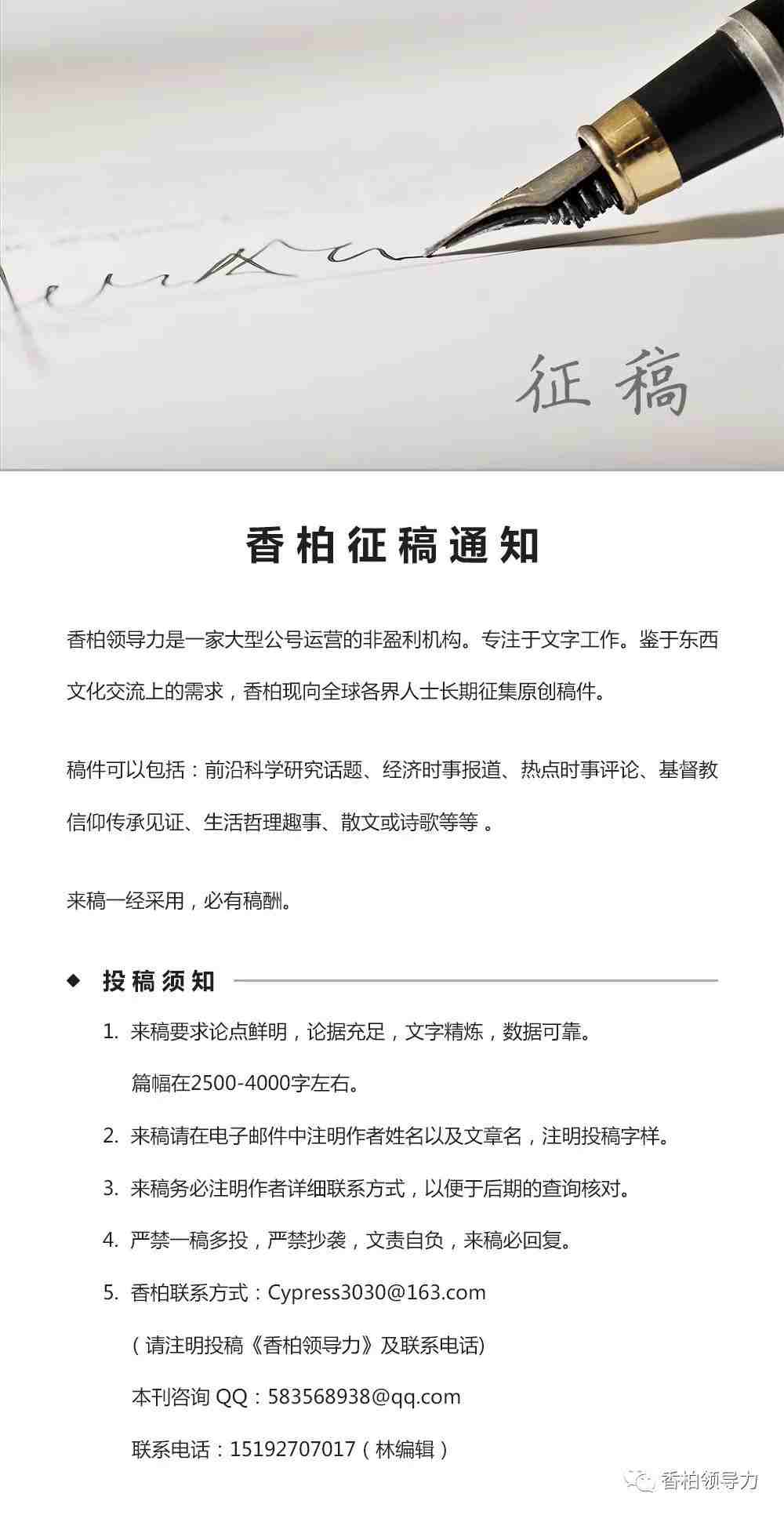
执行编辑:ChengSun
校对: Deborah
配图: Niuben
美编:Deborah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