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劭恺教授 | 宗教对人生或社会的意义(下)


作者 | 曾劭恺教授,浙大哲学系
文章来源 | 香柏原创
宗教于社会和人生的意义,自古以来就是哲学范畴的议题。每一种宗教都其固定的历史存在价值和意义。作者建议在对每个宗教进行价值判断之前,要真的去了解那个宗教。
作者在本文中从西方字源学语境中的“宗教”开始谈起,谈到西方的”宗教“基本上是被定义为基督教,由此看到真正的宗教乃是对三一真神的敬拜。随着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浪漫主义的时代发展,哲学家们对”宗教“的理解从纯粹理性上的knowing,进而发展到实践理性上的doing。康德对此提出了更完整、更成熟的宗教哲学。作者还谈到了近代艺术家,画家,思想家,哲学家们备受影响的feeling,已经跨出”宗教“界,他们崇尚人性中超然性的部分,是对上帝绝对依靠的那一份敬虔。因此现代很多基督徒认为基督教不是一门宗教,而是人与神的关系、人对神的认识。究竟如何看待宗教及其对现代的影响和支配?
请继续阅读曾教授在2017年3月9日,应台湾大学的邀请进行台大哲学桂冠讲座文稿的第二部分,他授权香柏推出此文,或许读者在反思与判断的过程当中,对自己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也会有所修正。深度好文,共飨大家。

正文 TEXT↘
事实上,在西方,“宗教”一词的含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英文religion一词源自于拉丁文religio。这个字可能来自于relegere,意思是“重复阅读”,指“反覆地研读”。但多数学者比较接受的解释是,religio这个字,源于religare,是“约束”的意思。不过,字源学的讨论对于我们今天思考的课题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在漫长的希腊罗马以及基督教历史当中,这个字的含意已经跟可能的字源没有直接关系了。
在基督教成为欧洲大一统的思想体系以后,“宗教”一词基本上就与“基督教”划上了等号,这个字所指的是对三一真神的敬畏。在这语境中,只有基督教是真宗教,意思是,只有基督教以真神为敬畏的对象。到了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神学家加尔文那部深深影响整个欧美文化的巨著,就在这含意上被命名为institutio christianae religionis──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到了十八世纪,在启蒙运动的影响底下,人们对传统基督教的教义有愈来愈多质疑,他们对“宗教”的定义也因此有所改变。我在《牛津指南》系列当中的Oxford Handbook of Nineteenth-Century Christian Thought一书当中指出:传统上,不论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不论正统派、敬虔派,“宗教”一词的含意必然包含人对神的认识,而这预设神对人的自我彰显。换言之,“宗教”主要关乎知识--对神的知识、对神真理的知识。但笛卡儿的方法论怀疑主义使得后来的欧陆理性主义愈来愈排除“天启”的信仰,采取一种自然神论的哲学进路来论述关于神的事情。在英伦的经验主义学派当中,虽然洛克、柏克莱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尽管洛克在神学上采取了基督教的异端),但经验论的集大成者休膜宣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不可行性,也进而令欧陆理性主义的理性神学(rational theology)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康德读到了休膜的著作,形容自己“从哲学教义的睡梦中被敲醒”。在《纯粹理性批判》当中,康德宣告理性神学是行不通的,人不可能在纯粹理性的范围内建构对神的知识。在这范围当中,神只是一个拟想,一个Postulat,是所谓的regulative principle,也就是作为拟想,被用以解释一些现象,但不是人类感知到而确知的对象。然而,康德并没有扬弃宗教。在《实践理性批判》第二版的序言当中,康德说,当我们离开纯粹理性进入实践理性的范畴,也就是道德的范畴的时候,“神”就不再是一个拟想,不是regulative principle,而成为一个constitutive principle,意思是,藉由道德的超然性,the moral sublime,“神”成为人确实感知的对象,而这也是他整个道德哲学体系的出发点与基础。在更晚期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当中,康德提出了更完整、更成熟的宗教哲学。在他而言,宗教并不关乎纯粹理性上的knowing,而是关乎实践理性上的doing。

在康德之后,十九世纪主流欧陆思想对于“宗教“的论述,基本上都在他的影子底下。例如,基督教神学家士莱马赫在《宗教演讲录》一书中,对当时普鲁士那些藐视基督教的文化人解释说,其实宗教并不关乎教义、不关乎对神的知识。不过,士莱马赫否定了康德所否定的,却没有肯定康德所肯定的。对康德而言,宗教关乎doing,但对士莱马赫而言,宗教关乎feeling,一种对上帝绝对依靠的敬虔感。士莱马赫早期的论述采取了一种浪漫主义的进路,他认为,古罗马的多神宗教比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理性宗教,是更加敬虔、更具有宗教性的;而那些不上教会的文化人,其实都有深刻的宗教性。士莱马赫在早期著作当中主张,我们都是有限者,而宇宙是无限的,但那位无限者并非绝对超越、远在天边的上帝。反之,每个有限者都是无限者的一部分,而每个有限者里面都有无限者。这跟陆象山讲的“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很类似。士莱马赫说,当我们观察这宇宙,又探索我们的内心,在这种天人合一的状态中感受对无限者的绝对依靠,这就是“真宗教”了。到了晚期,士莱马赫会说,只有基督教能够提供救赎,但士莱马赫早期关于宗教的论述,更能代表当时欧陆的宗教观。这种观念认为,基督教只是“真宗教”的一种形式,而“真宗教”也可以藉由其它的institutional religions表达出来,甚至美术、文学、音乐,都可以成为“真宗教”。
例如,诗人席勒一反康德关于“美与超然性”的论述。康德认为艺术只能表达the beautiful,却不能表达我们在浩瀚星空还有内在道德良知当中所认知到的 the sublime。这是因为康德接受了基督教神学,特别是宗教改革神学对于上帝超越性的强调。席勒则用一种类似于史宾诺沙及士莱马赫的方式,将“神性”与“人性”划上等号。于是,艺术家就能够像先知一样,表达属神的超然性:每个人里面都有神性。在席勒著名的《欢乐颂》当中,他把Freude称为Götterfunken--人性当中的sparkle of divinity。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的终乐章,采取了很多宗教音乐的元素,包括合唱,还有德国赞美诗的音乐体裁,歌颂的却不是传统基督教的上帝,而是席勒笔下,人性当中那神圣的超然性。席勒说,这种超然性会带来狂喜的感觉,而这也体现在贝多芬的音乐当中。再后来,浪漫主义的美术家、音乐家、文学家、思想家,也用类似的进路,建构所谓的Kunstreligion,也就是所谓的“艺术宗教”,把宗教艺术化,又把艺术宗教化。对他们而言,不论是教会的赞美诗,或是华格纳的歌剧,所要表达的都是类似于士莱马赫在《宗教演讲录》里面所说的那种“宗教情操”。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许多强调教会教义真理的基督教神学家纷纷宣称,基督教并不是一门宗教,而是对神的认识。荷兰的巴文克、瑞士的卡尔.巴特,都在这语境中强调基督教并不是宗教。巴特在早期的《罗马书注释》当中,借用祁克果关于“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辩证论述,宣称宗教是“人类可能性的最高峰”,但神的行动所产生的信仰却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发现,很多英国基督徒也强调,基督教不是一门宗教,而是人与神的关系、人对神的认识。事实上,在这种近代、现代西方语境以及汉语语境当中,不少佛学家也会说,佛法并非这种定义下的宗教。
不论基督教、佛教是不是这语境中所定义的“宗教”,也不论在座每个人的价值体系有什么差异,我想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假如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将我们的社会“去宗教化”、“去魔化”(disenchant),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关于这问题,清末民初的中国启蒙思想家严复先生有精辟的见解,在今天仍值得我们思考。大家如果想更深入研究,可以参考中研院黄克武先生的作品。严复先生有些思想非常耐人寻味。他早年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支持民主、科学,是近代中国启蒙的先驱,但是他后来又批判五四运动,支持“孔教会”、“宗圣会”,甚至认同“上海灵学会”关于神鬼、灵魂的说法。关于这种吊诡,学者有不同的解释,而我认为,黄克武先生的解释相当具有说服力。他指出,严复先生并不是改变立场或自相矛盾,而是在他的“现代性方案与终极关怀之间具有内在凝聚性与一致性”。
严复先生绝不是反对德先生、赛先生,他反对的是五四那种试图抹杀宗教、抹杀传统的激进现代化运动。他是近代中国引进西方科学的先驱,但他认为,把科学当成信仰、迷信科学万能、高喊“科学救国”的那种科学主义以及爱国主义,对于人类而言是具有毁灭性的。黄克武先生引用严复论及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句诗:“何期(期待的期)科学精(专精的精),转把斯民蹂(蹂躏的蹂)。君看四年战,兹事那可又”。黄先生解释到:严复以及梁启超等人“看到西方物质文明的过度发展,导致毁灭性的战争”,他们“批判西方科学畸形发展、爱国主义与种族之争所导致的残酷战争”。也就是在这里,他们看见中国传统以及宗教的重要性。
严复先生有一次读到一则新闻:有个英国女性医护人员在一战期间被德军抓到,判了死刑,在枪决之前留下遗言,说:“站在上帝与永恒之前,我了解到爱国主义是不够的,我必须对每个人都没有憎恨与酷烈。”这让严复先生有感而发,写下一段话:“爱国一言,殊未足以增进人道也。”爱国是好的,但狂热的爱国主义,如果没有更高的宗教信仰所带来的人道精神去平衡,那么结果是非常危险的。严复先生在近代西方语境当中,用真宗教、宗教情操这些概念来解释中国的传统,而他的思想绝不是反现代化的。事实上,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主流思想家,包括康德、黑格尔、士莱马赫、祁克果,都用了很大的力气,在现代社会当中为宗教的意义辩护。

当然,如果你是金正恩的支持者,你不会因严复或康德关于宗教的论述,就认为宗教有意义,反而你可能更加认为宗教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是这样,我个人会希望你价值判断的标准有所改变。
最后,我还想提出一个论点,作为我们的结论。我们今天探讨的“宗教”一词,如果是近代、现代西方语境以及中文语境中的“宗教“,那么不但是巴文克、巴特这样的神学家,许多佛学家也会说,他们的信仰并不是这样的“宗教“。
事实上,每个宗教都有它的独特性。“宗教对人生或社会有意义吗?”这问题,不能代替“基督教对人生或社会有意义吗?”或“佛教对人生或社会有意义吗?”我们不能把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回教、道教等统称为同样含意上的“宗教”,简单粗暴地以为“宗教都是劝人向善”,或者“宗教都是迷信”,或者“宗教带来暴力”。对于人生与社会而言,不论正面或负面的意义,每个宗教是不一样的。印度教能使人民知足常乐,也能减轻底层人民的痛苦感;马克斯.韦伯指出,基督新教使人民勤奋工作,并乐于分享财富,造就了均富的社会。这些影响有意义、无意义,意义正面或负面,都取决于每个人的价值观。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者,你不会认为印度教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你不会认同十七世纪基督新教的社会价值。
但重点是,我希望各位在对每个宗教进行价值判断之前,要真的去了解那个宗教。蒋勋先生是佛教徒,但他讨论林布兰、维米尔、梵谷这些荷兰画家的作品的时候,指出加尔文的基督新教信仰对荷兰文化深刻而正面的意义,我们如果真的研究过这一派的神学思想,我们会发现,蒋勋先生的观察非常深入,也非常正确。加尔文的一生当中,的确有些不光彩的事迹;基督教的历史上,的确有许多污点;所有的宗教都在历史上留下过令人不齿的劣迹;但这不代表这些宗教本身的信仰必然是鼓励这类行为的。
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加尔文认同日内瓦市议会判处赛尔维图火刑,是出于他神学上的矛盾,而他的后人已经修正了这矛盾,采取了他神学上更核心的原则。蒋梦麟先生说耶稣是乘着炮弹来到中国的,许多人也把基督教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联想在一起,但很多人不知道,当年在中国的英国宣教士为了废止大英帝国的鸦片交易,大批大批地付上了鲜血与生命的代价。我们对于个别宗教的教义与历史不够了解的时候,往往会人云亦云地对那些宗教产生误解。如果我们真的有兴趣了解个别的宗教对于人生或社会的意义,我们就必须客观、谦卑地去研究、认识那个宗教,而不是看到了一些令人不快的现象,就直接否定那个宗教对于人生或社会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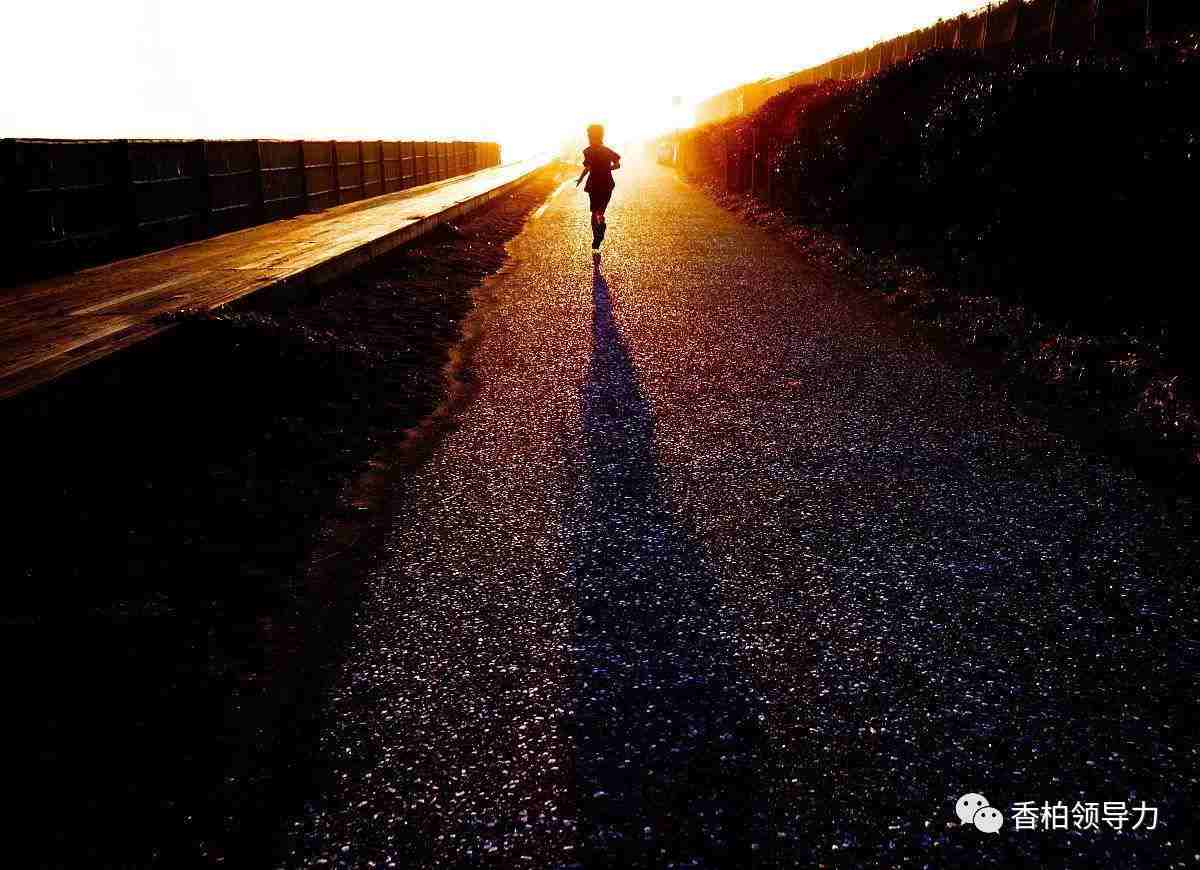

——战善战 尽程途 守主道 ——


编辑:ChengSun
初编:青云
校对: Deborah
配图: Ashine
美编:Deborah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