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劭恺教授 | 人无信不立 (上)


作者 | 曾劭恺教授
文章来源 | 香柏原创
Deborah
2018.02.09

相约香柏,认识生命,传递信仰
香柏的读者们,新年好!
2017年,香柏讲座进行了一整年的时间,香柏读者沙龙群由原来的两三个人逐渐增至到如今的一万人,是上帝把异象放在赵晓教授的里面,是圣灵把诸多的感动放在特邀嘉宾的里面,吸引我们相聚在香柏。
我们万分感恩上帝丰盛的恩典和丰富的预备。感谢神。
香柏全心服事读者们,每一周六将近40位香柏同工一同出列,默默奉献,用心付出,以不同的职分守望在每一个香柏群,一直坚持两个小时的服事;特邀嘉宾们甘心献上自己的研究成果,以敬畏上帝的心尽心、尽意、尽力地传递、传播,传送给千万读者。都把香柏当作“家”,感谢神!
冯雪薇律师说,这是一种大众传播,全民教育。非常重要!
异象告诉我们:只管把粮食洒在水面上,运行到感动您的地方,那里就生根发芽,从生命的活水里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来!
香柏读者们凡是以感恩的心面对每一次的讲座,在年终之际他们都收获了福杯满溢。

这都为中国新千年文明的转型起到了更好的架构作用。
进入2018,正值新年开年万家团圆的此刻,今晚香柏进行第一次讲座,上帝又为我们预备了海内外知名哲学教授曾劭恺。

浙大教授曾劭恺 :
加拿大籍,出生于中国台湾,2017年入选浙江大学文科百人计划,担任哲学系 宗教学 研究所 研究员,具博士及硕士 研究生 招生资格。
本科就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B.S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双主修物理及德文。
大学毕业后转入基督教研究专业,先后获加拿大维真学院、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硕士学位,以及英国牛津大学研修硕士与哲学博士学位(MSt, DPhil, University of Oxford)。
兼任学术期刊《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A&HCI、Scopus等)编辑委员。
著有英文专著Karl Barth's Infralapsarian Theology (IVP Academic, 2016)、《牛津手册》系列之The Oxford Handbook of Nineteenth-Century Christian Thought 专书论文等。主要学科为基督教思想研究,工作研究领域包括巴特研究、汉语神学、近现代基督教思想史、浪漫主义、克尔凯郭尔研究、黑格尔研究、加尔文研究、宗教改革思想研究、奥古斯丁研究等。
若说社会价值,一定要探讨人生的意义。若要从意义引发的DOING,才能让人深知自己的BEING。
你的所是才带来你的所为!
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中,我们如何理解人的存在,曾教授今晚借助西方语言学溯源“宗教”一词的来源以及人遇到上帝位格时所能形成的敬畏意识,进一步探讨宗教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宗教所标明的社会意义。

我们现在有请曾教授!

曾劭恺
浙大教授
各位朋友,大家好,在这里先跟大家拜个年,祝各位新年快乐。也感谢香柏的团队给我这个机会,跟各位分享专题。今天的题目是“人无信不立”,这个标题是赵晓教授知道了我要分享的内容以后提议分享的。
我一听,就拍案叫好。这句话出自《论语·颜渊》。
子贡问孔子:“治理国家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
孔子提出了三点:“足兵、足食、民信。”
子贡又问:“如果这三者必须去除一项,那么应该先去除哪一项?”
孔子说:“这里面最不重要的就是军事武力,所以‘去兵’。”
子贡又问:“如果还要再去掉一项,那么孔子会选择何者?”
孔子回答:“去食。”粮食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
孔子接着解释:“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这意思是,自古以来,人都是会死的,但是如果当政者没有在社会上建立“信”的价值,以致人民能够信任当政者、信任社会、信任邻舍,像当年鲁国能够夜不闭户,如果没有这样的“信”,那么国家就不成立了。“民无信不立”。

这样一套论述就暗示,社会的诚信、朋友有“信”、以至人民对国家社会、对当政者的信任,并不取决于富国强兵、丰衣足食。在我们中国儒家的传统当中,“富强”并不是立国之本,它不应该是一个国家首要的核心价值。有些东西,比经济、军事上的强大更加重要。我们可以这样想:一个流氓没有钱、没有力量,就只是个小流氓。一个流氓富裕了,强大了,他就变成土豪劣绅。教育、文化或许能提高人民的素质,但这也不是立国之本。一个土豪劣绅顶多就是欺压乡亲父老,但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果对苍天不怀敬畏之心,却可以贪赃枉法、烧杀掳掠,而长久逍遥法外。一个伟大的国家或民族之所以伟大,并不取决于她多么富裕强大。鲁国不是大国,但有信,民则立。在儒家的价值观当中,“信”才是立国立民之本。
我们今天讲“人无信不立”,取的是双关语,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是宗教信仰的“信”。事实上,在汉语及西方的语境当中,“信实”、“诚信”、“信仰”、“信任”都是相通的概念,都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中文是“信”,英文是faith,拉丁文fide,希腊文pistews。新约圣经里面,pistews这个字被翻译为“信”,它可以指神的信实,也可以指人对神的信心。这是相通的,而如果我们可以从一个现代西方概念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信”,那么这概念非“宗教”莫属。如何定义“宗教”,是个复杂的课题,我们稍后会花时间来探讨。

今天要讨论的是宗教信仰对人生与社会的意义。这是将近一年前,我受邀担任台湾大学哲学系“哲学桂冠讲座”的讲员主讲的题目。这题目是当时主办单位确定的。今天的内容,我会基于那次的演讲展开,会铺陈得比较广,讲得比较深。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不是特定的宗教,而是广泛意义上的宗教。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开宗明义地强调,终极而言,每个宗教都是独特的,每个宗教对于人生与社会的意义都不一样。
今天是大年初二,我们刚步入戊戌年。120年前,晚清的维新人士发动了戊戌变法,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带领我们国家进入现代化过程的重要事件。当时年轻的维新领袖梁启超先生,后来对中国的现代化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提到梁启超,我们可能立刻会想到他晚年发动五四运动,倡导新文化。这是他用生命最后十多年的光阴所作出的贡献。但我们可能不知道,他在世的最后这十年间,在思想上有一个重要的转变,也就是他对宗教的看法。当代最著名的女性汉学家之一,法国的巴斯蒂先生(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指出,梁启超对宗教的观点,对其一生的学思路程,具有主导性的影响。

我们今天讲的“宗教”,其实是十九世纪欧陆文化的产物,对古代中国文化完全陌生,当时对梁启超而言,也是个新概念。我们等一下会解释这个概念在历史上的发展。总之,梁启超早年认为,宗教信仰是救国的关键。但是到了孙中山先生革命前后的那个时期,也就是1905-1918年,梁启超却主张,政治本身就具有宗教性,政治可以取代宗教,成为人民的信仰。有趣的是,1918-1929年,也就是1916年发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倡导新文化的那最后十年,梁启超先生却重新认识到宗教对人生与社会的意义。稍早提到那位法国学者巴斯蒂写道:“在他的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梁启超的宗教,无论就其功能而言,还是就其实质而言,都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宗教不再是对一种政治理想的支撑物,也不再是梁氏希望自己和每一个人都放弃自私自利而为之完全献身的终极目的──救国──的支撑物,宗教替代了政治理想,或者毋宁说宗教超越了政治理想。宗教肯定了人性的个人及其自由的至高无上。只有实现了人性的个人及其自由才是一种定局。政治的、社会的形式或指令只不过是过渡性的、经验性的、永远不完善的手段。”
今天我们的国家富强了,这是从晚清列强侵略的羞辱之后,中国人一直在追求的。我们想超英赶美,是想要比他们更强大、更富裕。但梁启超先生在当年已经认识到,真正伟大的国家民族,并不在乎富裕与强大。富强并不是立国之本。他深刻地认识到“民无信不立”的道理,而他透过西学的洞见,明白了宗教对于个人及国家社会的意义。当然,梁启超的时代过去了。戊戌变法过去了二甲子,中国已经是富强的世界大国。但这是否意味,宗教信仰在今天,对于我们的人生与社会,就不再具有意义了呢?

在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厘清“宗教”跟“意义”这两个词汇。所谓“意义”,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方面就是denotation、connotation。当我们问“What do you mean?”,这里的meaning是指“意思”、“含义”、“指涉”。我们今天不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意义”。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意义”,是指“价值”与“目的”。例如,有个著名的问题,the meaning of life,人生的意义。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在一本英文书籍里面写道,“we can realize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life in ordinary human existence”(“我们唯有在日常的人类实存当中,才有可能实现人生的终极意义”)。在这里,“意义”一词的使用比较宽泛,同时指涉“价值”与“目的”。
在传统形而上学的“目的论”(teleology)、“终极因”(final cause)的范畴里面,“意义”是指“目的”。譬如,一间房子的存在,有许多因。有质料因:它是用钢筋水泥、用木头做的;有形式因:不论是上海的老洋房或是传统的四合院,我们一看就知道是房子,因为它有房子之为房子的形式。但质料因、形式因本身,并不赋予房子存在的意义。它不是平白无故就存在的,它被盖起来,是有目的的,这叫“终极因”。在这个目的论的含义上,我现在所处的这栋建筑,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住在里面的人遮风挡雨,提供一个物质意义上的家、一个归宿。这个目的,就是形而上学里面所谓的“终极因”,final cause。当我们在这层含义上问,“宗教对人生或社会有什么意义”,就是在问“宗教在人生或社会中的存在,目的何在”?终极因的问题,是自然科学不去触碰的。有些社会学家可能会说,宗教是统治阶级的手段、是社会稳定的因素等等,因此具有目的性的意义。基督教的牧师可能会说,他所信仰的宗教,目的在于认识神;有些会说是为了得永生;有些会说是为了得钻石。

除了形而上学以外,“价值学”(axiology)是哲学另一大分科,它也讨论“意义”的问题,而在这里,“意义”是指“价值”。在这层含义上,我们今天的课题可以理解为:“宗教对人生或社会有什么价值?”当然,这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每个人的世界观,以及对“价值”的定义。譬如,唯物主义者费尔巴赫(Ludwig Feuerbach)会说,宗教的价值就是将人性当中的无限性投射出来,让人类间接意识到自身物种的无限性,而到了十九世纪,宗教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已经不再具有价值了。实用主义者威廉.詹姆士则会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肯定宗教对于社会的价值,这价值是工具性的价值。对于纵欲主义者而言,可能像佛教这样的禁欲宗教是不具有社会价值或人生价值的。
所以,宗教对于人生或社会有什么意义?这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怎么理解“目的”与“价值”。假如我今天花些时间,说服各位说基督教的改革宗神学在十七世纪产生了“法治”这样的概念与词汇,这不必然意味在座各位因此会认为这套神学对社会有正面意义。譬如,假如我们中间有金正恩的支持者,那么他大概会认为,为社会带来法治的宗教,只有负面的意义。
对另一些人而言,“意义”的问题本身就是没意义的。几年前,我们家请了一位浙江东阳的木雕师傅来替我们做家具。他手艺非常精湛,收入也非常可观,远远超过像我这样的大学教授。所以他根本没有把我们这些搞学术的人放在眼里,特别是这些研究“意义”问题的人。对他来说,赚钱就是人生的意义,不赚钱的事业,就是没意义的。

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尔(Heinrich Böll)写过一篇很有名的短篇故事。有个城里的商人到渔村去,需要坐船到他的目的地,但是没找到船夫,只见到一名渔夫,大白天的躺在渔船上晒太阳、睡午觉。那名商人出钱要渔夫载他出行,渔夫却不肯,坚持要睡他的午觉。
商人不以为然,说:“你如果天天把睡午觉的时间拿来捕鱼、载客,能够多赚多少钱,你知道吗?”
渔夫没算过,所以表示不知道。精打细算的商人算给他看,那名渔夫却不为所动,问道:“我赚那么多钱有什么意义?”
商人就替他分析:“你赚了钱,可以再买一艘渔船,雇一些人来,捕更多的鱼,赚更多的钱,最后买下一整批的渔船,再买几个货柜车,把渔获载到城里去卖,你就成了大富翁了。”
渔夫还是不明白这样赚钱意义何在,追问:“那我变成大富翁以后,可以干嘛?”
商人像是看笨蛋一样看着他,说:“你成为大富翁,就可以付钱让别人替你干活,你就可以买一艘船,不用工作,天天躺在上面晒太阳、睡午觉了啊!”
各位,我们每个人的追求不同,价值判断的标准不同,世界观不同。除非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致的价值判断标准、一致的哲学世界观,否则讨论“宗教对人生或社会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很难具有意义的,只能鸡同鸭讲。对我个人来说,把赚钱当成人生意义的人,活的是很没有意义的。但是对很多人来说,探讨“意义”这件事,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这不只是那些本身就不爱思考的人的观点。很多哲学家追寻意义,追寻到最后,却断定说人类对意义的追寻,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今天不是来传教的,我不是要来改变各位的价值观、世界观。我只是想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厘清一些问题。所以我今天能够作的比较有意义的事,不是来探讨宗教对人生或社会有什么意义,而是解释什么是“宗教”,排除一些人们对宗教可能带有的误解,然后让各位自己慢慢去反思、判断宗教对于人生与社会的价值。而可能我们在这反思与判断的过程当中,对自己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也有会有所修正。
所以,什么是宗教?中文的“宗”与“教”两个字,在古代本来是不连用的。晚清史学家刘锦藻在《皇朝续文献通考》里面写道:“古无所谓『宗教』也,自释氏入中国,其道自别为宗,于是六朝后有此说。”在已发现的汉文文献当中,最早连用“宗”、“教”二字的,乃是出自六朝,也就是魏晋南北时期在南方的六个朝代,大概在公元五世纪左右。但一直到隋唐,“宗教”这个词汇都还不是很普遍的术语。到了南宋,“宗教”一词才成为佛门的惯常用语。不过,早在北宋,日本的佛教就已经普遍地使用了“宗教”一词,而这很可能是从中国引进的,所以我们可以推论,中文的“宗教”一词是在北宋佛教当中成形的用语。

“宗”这个字是汉传佛教借自汉文的用语,譬如禅家在唐代分成南北二宗,南宗强调“顿误”,北宗强调“渐误”。而“教”这个字则是沿用周人的观念。《易经》有云:“圣人以神道设教,使天下服矣。”这里讲的“教”,不完全是我们今天所讲的education、teaching,也不完全是religion,而是结合了两者。其实,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跟今天讲的“教育”也有差异。我们可以借用明代徐上瀛的一段话来理解“教”的概念。徐上瀛在这里是讨论古琴演奏的目的与价值。他写道:“稽古至圣,心通造化,德协神人,理一身之性情,以理天下人之性情。”(明.徐上瀛)所以古代的至圣制琴,目的在于教化。在这里,“教”这个概念,是涉及天、天理、天道、神道的,是使人心及宇宙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是一种“上施下效”的概念。佛教借用了这样的概念,在宋代发明了“宗教”一词,并且主张以“教”来分“宗”。
在这古代用语的含义上,我们也可以称儒家为“宗教”意义上的“儒教”。我们甚至可以把艺术看作一门宗教。明代大家董其昌是人文艺术美学的宗师,他以南北禅宗比喻两种艺术,写道:“禅家有南北二宗,于唐时分,画家亦有南北二宗,亦于唐时分。”艺术、音乐,在这种含义上都可以被称为“宗教”。当然,这跟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的“艺术宗教”(Kunstreligion)是不一样的概念。而且,“宗教”在古代是佛门用语,所以儒道两家也不会称自家学说为“宗教”。

我们今天使用“宗教”一词,已经不是古代的佛门用语了,而是近代西方,特别是十九世纪以后所说的religion。所有宗教学的学者都知道,或者说至少他们应该知道,现代中文在这个含义上使用“宗教”一词,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引进西学,而中国很多现代西学的概念跟词汇,都是采用日本汉字的翻译。
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岔题讨论一下西学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重大意义。今天我们国家有所谓的“宗教事务局”,有国务院发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中国艺术史学家会研究所谓的宗教艺术。其实,我们都是在用西方这个“宗教”的概念在看世界。
我跟我太太经常讨论国学与西学,讨论中国艺术史。我们始终认为,不应该用对立的眼光看待国学跟西学。现在很多人推崇国学,贬低西学,对于西方的东西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却已经带着一种既自卑又自大的敌意。譬如我时不时会听一些人说,研究汉学的西方学者,根本不懂中国;研究中国艺术史的西方学者,根本不懂中国艺术史。事实上,这样的说法,本身已经预设了一些西学的概念,是中国古代没有的。

譬如“中国艺术”这个词预设了“中国”的概念。今天我们说自己是“中国”人,把自己跟西方人区分开来,这种区分的背后,其实是十九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的概念,nation-state。今天我们理所当然、无远弗届地使用这个西方的概念。我们今天都会说孔子是中国人。曾经有韩国学者提出,孔子是韩国人,中国网友就怒了,我们都认为,孔子理所当然是中国人。但是在孔子的年代,并没有“中国”这个概念。当然,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孔子是中国人,就像我们可以说黑格尔是德国哲学家。但是黑格尔那个时代,德国还不是一个国家,就像在孔子的时代,中国还不是一个国家是一样的处境。孔子并不会说自己是中国人。古代的鲁国、齐国,跟我们今天讲的中国,并不是同一个含义上的“国”。把state的政治实体以及nation的民族文化实体结合起来,才有了“中国”、“美国”这些“民族国家”的概念,这是近代西方的概念。State的概念,跟nation的概念,其实并没有必然的联系,nation-state的复杂概念,是近代西方产生出来的。而只有在我们接受了这个西方的概念以后,我们才有可能界定历史上哪些东西、哪些人物、哪些现象是“中国的”,然后我们才有可能讨论所谓的“中国艺术史”。
而我们会发现、吸收、学习和引进这个西方的概念,并不会让我们失去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特点。反而,这个西方的概念,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认识我们自己为中国人。所以我认为,把西方的东西都想成是侵略、殖民、同化的手段,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我们刚才提到中国艺术史。事实上,“历史”这个概念,也是从西方来的。当代中国史学泰斗、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先生经常强调,在中国古代的观念当中,“历”是“历”,“史”是“史”,这两个字在古代文献当中很少连用。“历”这个字,指的是时间的先后次序,是英文的chronology,类似希腊人chronos的概念。譬如我们有日历、年历,有计算黄道吉日的黄历,这是时间次序的概念。“史”则是指事件、故事。所谓“历史”,是把“时间”与“事件”两个概念结合起来,不是一个简单概念(simple idea),而是一个复杂概念(complex idea)。古代的中国人,并没有注意到,或者说并不强调“历”与“史”中间的联系。
强调“历”跟“史”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是西方人的史观。维新以后的日本学者,取了“历”跟“史”两个汉字,连缀成词,用来翻译西方的history、historiography。特别是日本在现代化过程当中受到德国的影响,德文的“历史”有两个字,Geschichte跟Historie。Geschichte是指“发生过的事”,也有“故事”的意思,接近中国人讲的“史”。十九世纪德国历史主义兴起以后,则用另一个字,特指史学家研究的历史,这个字就是Historie,也就是时间与事件所结合起来而形成的进程。在这个进程当中,事件与事件之间有强烈的因果联系,是有目的的,且有一套公例或公理让我们能够明白古今之间的类比,而时间则是承载这个进程的媒介。

西方人的时间观与史观,简单来说,可以描述为“线性”的观点。历史是一条直线,朝着一个目的在进行,因此是一个进程。这是基督教特有的观点,虽然说希伯来《圣经》有这样的论述,但是清楚地阐述这种时间观与史观,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找到的,而真正把这样的历史观发扬光大,影响西方文明,一般学者会归功于奥古斯丁。奥古斯丁目睹西罗马帝国被蛮族侵略以至颠覆,而他把这重大的历史事件与上帝的救赎历史以及将来要降临的上帝之城联系起来,又提出了“上帝创造时间”的观点,结果这就产生了西方文明的线性史观。基督教相信历史是有目的的、有意义的,朝着一个终极的目标在进展,这就是基督教的末世论。在基督教开始主导西方文化以前,西方的史观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循环的,跟中国的史观类似。当然,批判性、分析性的历史研究,在西方要等到十九世纪才会成形。
中国人的时间观与史观是循环的。举例说明,西方文明受基督教影响,年历是历年递增的,今年公元2018年,明年就是2019。中国不是。在中国,今年是狗年,十二年后又是狗年。今年戊戌,二甲子前也是戊戌,发生了戊戌政变。这是中国的时间观。这里讲的是“历史”里面的“历”。

讲到“历史”里面的“史”,中国古代的史观,也是循环的。孔子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开宗立派的宗师,他想作的,不外乎回归三皇五帝的黄金年代。西方汉学家把宋代理学称为Neo-Confucianism,如果直译,就是“新孔子主义”。但朱熹并不认为自己在创新。他重新诠释四书,是意图回归古代圣贤的天下。道家思想的循环史观更加明显。《道德经》说大道“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
这样的史观也就意味,“进程”或“进步”的观念,跟“历”或“史”是无法联系在一起的。这不是说中国人不求进步,但是中国人过去的观念里面,“进步”与“历史”没有必然或强烈的关联。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天道、道统的一个循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革命”与“历史进程”联系起来的,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这种联系,背后有基督教在西方强大的影响。

去发现、研究“史”跟“历”,也就是事件在时间当中演进的轨迹,正是现代西方历史学的学术方法。而这种“历史”的意识,对于各个学科都带来深刻的影响。西方人文学术方法的核心,就是所谓的“历史分析法”(historical-analytical method)或“历史批判法”(historical-critical method)。中国古代是没有这种史学的。史记、资治通鉴,在现代史学的标准下,都只能当成“史料”,而不能算作“历史”著作。
在今天,我们会把一个人物的思想、作品,放在历史进程的轨迹、历史的通例当中去研究,这是西学,而这种诠释方法背后乃是基督教的文明。今天我们研究中国艺术史,也会使用这样的方法,这在古代是没有的。古人当然也会辨别不同时代的作品有不同的特征。北宋郭若虚注意到,“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但郭若虚没有办法从思想史的脉络去分析、解释宋代文化当中的格物精神,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文化处境中形成的,而这又如何影响了宋代的花鸟画,以及画院的写实画风。

我讲这些,并不是在吹捧西学,而是在说,我们不要重蹈百年前错误的覆辙,不要一味地以为中国的东西比西方好,一味地以为西方人不懂中国、西方汉学家不明白中国文化、西方的中国艺术史学家不懂中国艺术。我发现一件事,就是那些一味抗拒西方元素的国学爱好者、爱国人士,因为没有虚心去了解西方的东西,所以他们想事情其实往往都戴着西方的眼镜,却不自知。

——战善战 尽程途 守主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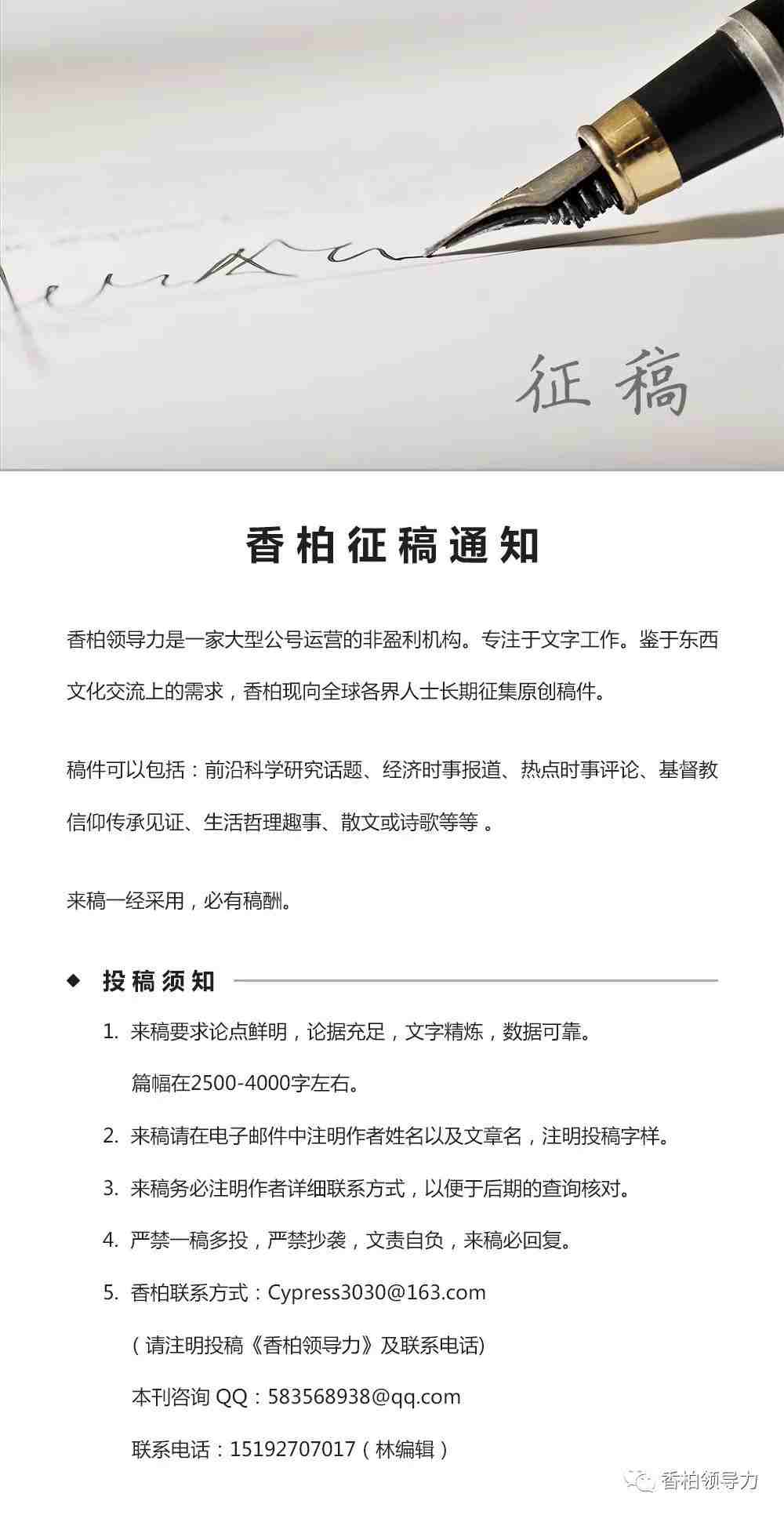
执行编辑:ChengSun
校对: Jack
配图:Niuben
美编:Deborah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