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到国外,我一步步学会独立生存|征文大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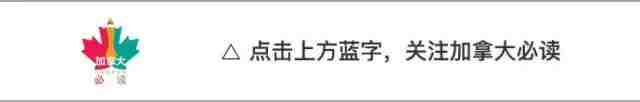
去年年底开始,加拿大必读与西洋参考一起联合举办了“分享出国心路,赢取万元大奖”有奖征文活动。在长达2个多月的征稿中,我们陆续收到了大量来稿。我们会陆续将投稿一一展现出来。
新的房间除了一个入墙式衣柜什么家具都没有。现在正在世界某个角落做生态调查的室友已经提早把我零碎的家当从学校宿舍都搬了过来,到的第一天一打开房间门就看到集中在房间某一角的我的锅碗瓢盆、书和文件。
贴心的室友还帮我准备好了气垫床、被子等等。然而气垫床旧了总是充不满气,虽然室友也贴心地留了修补漏气的胶带,可一躺下去的感觉就是漫入波涛汹涌的水中,随便动动就能造成气垫床的局部坍塌,很不安稳地睡过一夜之后,我决定在找到合适的床之前还是先睡在地板上:把先前买来打包东西的防水布铺在地上,再把室友留下的床单铺上,一个简易的床板就做好了。
这样又睡了两个晚上后,在网上二手交易小组找到了一个合适又可以帮忙免费送上门的床,要知道二手交易小组通常都是只能自取的,只能说太及时雨太及时雨,接着又搜罗到了一个二手书柜,开学季打折的书桌,房间三大件就此搞定。

差不多去年的这个时候,第一次出国的我入住的是提前申请好的学校宿舍,出了机场找到接送的人,司机就会把你先送到宿管处拿钥匙再把你送到宿舍。仍然记得当时机场到学校的半个多小时车程里,我在渐暗的天色中看着道路两旁空旷的田野,和不时闪现的牛羊,心头突然升起的恐惧和无助,到达渐有人烟的市区时的张望和好奇,走进如花园别墅一般的宿管处时的惊艳和震撼。
当时的我,三十岁第一次走出国门的我,要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未知的世界,一路所见的前所未见之物,一路所遇的前所未见之人,都足以让只在一个国家长期以一种语言生活过的我慌乱地调动所有感官去感受。每天,生活和学习的无数细节因为语言让人格外沮丧,累的时候也会怀疑自己到底选择了什么,但在其实也没有退路的日子里,当也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耽于自己的失败和情绪,只能每天醒来打开房门硬着头皮继续磕磕绊绊地面对。
后知后觉地,听不懂老师上课、在图书馆哭、一遍遍重复抄写叶绿体线粒体的英语、实验课的手足无措等等等等,这些去年才发生的事,现在回头看竟然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去年一月初,学生签证终于下来,我可以订机票收拾行李的时候,没有犹豫地带上了那本《来自民间的叛逆》,三年多前去深圳后来又跑去北京的时候也毫不犹豫地带上了,当时不嫌重也要带上的理由,除了很感兴趣的民歌内容外,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书名,来自民间的叛逆,听着就像一种宣示,自我认知认同以后进而就有一种来自吉祥物的陪伴之类的心理暗示,我就是来自民间的叛逆啊。

这次出国的前一天,跟家人一起吃饭时,爸爸突然说:“你看窗外的树长红色叶子了,这么多年第一次见,我们家今年会好的。”我听完转头看了一下那棵在我房间也能看到的树,那棵从我中学开始就一直站在那儿的树,鼻头突然一酸。
从决定转行开始,从注销律师证,从福州到深圳,从深圳到北京,从北京到新西兰,每次都是两个行李箱,一张动车或者飞机票,在当地不认识任何人,不去想太多以后的情况下,就这么出发了。
但每次运气也都很好,在深圳住了三天青旅就找到了一个合租单元房里的小次卧,又在几周后找到了一个互联网文字策划的工作,后来远程投了北京一个出版社的简历,飞去面试通过就订了青旅直接过去上班,一边上班一边网上找房子,到北京的第一个周末就找到了一个刚好短期出租一个多月可以用来过渡的次卧。
那时是冬天,住进去的前几天要上班也没顾得上买被子,晚上拿几件厚衣服盖一下就睡着了,也没觉得有什么,倒是人生第一次经历了北方有暖气的夜晚,觉得很有意思。再后来,在北京发生了很多事,在涵芬楼听了很多自然科学类的讲座,就决定孤注一掷重返校园再当一次本科生学习植物学了。
过去的这一年,一个不可避免又有些麻烦的事情是向别人介绍自己的专业,就像以前学法律总会被问你们是不是要背很多法条啊,现在的专业误会就是别人总以为你应当知道很多植物的名字。

其实植物学是生物下的一个分支学科,研究的范围从形态到分类到病理到药用价值等等无所不包,要知道我们人类社会整个外部物质世界的衣食住行,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建立在植物的贡献上的,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植物内部的生命原理,以及它们与微生物的依存关系,但目前的一年所学并不足以让我对某个领域特别了解,只是刚刚开始建立一种比较规范的系统性分析的思考能力。
比如一年多前看刘华杰老师的《檀岛花事》,并不太理解入侵物种的影响以及全书中贯彻始终的对外来物种的鄙弃,现在终于明白了他阐述立场的原因。
另外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是向别人解释为什么三十岁了又回来念本科,又为什么这回念的是植物学。因为植物是美和科学的结合啊,无论是纯粹的美的直观的感受还是理性的有价值的研究,都是会给人生带来无穷无尽乐趣和满足的东西,这就是我真实的想法,至于学了以后要做什么,我其实是没有或者说不敢多想的,只是抱着所热爱的事物一定会再给你启示的天真先去做了。
同学们大部分都是 17 岁到 21岁,大部分都是第一次上大学,也有少部分像我一样因为各种原因重返校园的大龄学生,当少数派出现在了大多数里,某些场合下的解释就变得必要,但解释并不是为了用年龄去严格地分出某种对立的界限,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各自的经历和背景,而我自己从一次次地跟人介绍自己中也更加了解和接受了自己。
重新念本科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大概是,我可以同时拥有两种视角,17 岁的视角和 30 岁的视角,好像有两个自己同时在这个身体里成长,17 的岁的我又从记忆里醒来,热切地观察着周围新鲜的一切跃跃欲试,30 岁的自己则好笑地注视着这样的心情,纵容着这份好奇,但总适时地提醒她人生是不能重来的,应该善用时间和精力做该做的事。
新西兰的本科课程挺紧,每个学期除开考试周严格算来就三个月左右,夏去春来的,第一学年就结束了。

回国的时候,以为自己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准备“要回家了”这件事,特地选了坐六个多小时的大巴到基督城转机而不是一个多小时的飞机,结果一路上完全没有想象中的不平静或是对往事的浮想和总结。
我看着窗外不断经过的植被、羊群和农田,只是像寻找灵感一样,想着要怎么在知识、能力和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和作用点,让自己接下来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独立地生存下去。
很难说出变化是在哪一个具体的时刻发生的,当察觉到的时候开始,身体里好像已经有了一股新的力量,人应该在什么事情上跟外界妥协又在什么时候一定要顺从自己的心,已经不会再为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惑了。
回国后第二次过来新西兰,一路都很顺畅,自然而然,我不再是一个连自己要念的学校的名字都说不清楚的初闯入者了,我不再需要在心里练习确认很多遍单词和语序才敢开口和人说话了,在不同口音的人群中走过也能基本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了,所有用英语写成的标识都始对我显现更多的善意。
我可以开始心中有数地选择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最佳交通方案,可以放下行李不用手机搜索就跑去一个地方。我的脸上大概也没有了那种最初的迷茫,走在街上竟然开始有人向我问路。这个不预期到达的新世界对我来说终于不再是一团巨大的一无所知了,尽管我站在那道被时间打开的小小缺口前,仍然不知道前面等待我的会是什么,但是好像没有什么能再让我害怕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时间邪恶,也只能这样了。

“诗酒趁年华,他乡亦故乡。”这是那天一个人在惠灵顿植物园暴走的时候在一张捐赠的椅子上看到的话,落款是一个杨姓老先生。自从离开了中国,我对所有迁徙漂泊的行为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在惠灵顿蒂帕帕国立博物馆名为“护照”的早期移民故事展里,我仔细地读着那些从不同国家出发最后漂洋过海来到新西兰的迁移者的故事,不管是难民也好,淘金者也好,躲避战争也好,追求更好的生活也好,人们最后是要停下来才能去生活的。
每个个体的经历不一样,但在相似的出发和到达里,有一些过程,有一些夜晚和早晨,都是一样的。而我,当然还是幸运的,可以暂时逃离了家乡关于女性、婚姻和年龄的固化价值观,得以再一次地,去伸手触碰另一种可能。
本文系征文活动投稿,作者陈十一
欣赏更多比赛征文:
为了磨练自己,我选择了出国留学|征文大赛
【魁北克、安省欢迎你】
我们魁北克、安省移民留学交流群
已经陆续先后开启
添加加拿大必读小编个人微信(ID:yiqijianada)
通过人工验证后,即可加入我们的交流群哦~
你还可以关注这些: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