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肃造一座罗马古城,弘扬佛法 | 土逗事
平均阅读时长为 4分钟



作者 | 嘻咪ཞི་མི།
编辑 | 小蛮妖
美编 | 黄山


她被鬼附体了,这个鬼魂是古罗马人
“你相信鬼魂么?我信。”
窗外,下午四点的冬日余晖斜射进接待处的玻璃窗,惨淡的夕阳照在那尊菩萨身上,甲居士迫不及待地跟我讲起当地妇女李金兰的故事。
李金兰大概是结婚生子后方才察觉自己的与众不同,她的梦境里经常闪现出一群踏过铁马冰河的异族武士,轰轰烈烈辨不清是鲜血还是泥土的战场,哪怕是自己清醒的时候,耳朵里也隐约传来一个陌生男子的低沉哭泣。
村里人当然知道她那些奇奇怪怪的言语举止,便怕她三分:前一秒这个女子还跟着他们开心谈笑,后一秒却变得低沉沧桑,浑身冒汗,大声嚎叫当地人完全听不懂的语言。
大概李金兰本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新社会长大的孩子从小都是无神论的熏陶,也不会相信自己被鬼魂附了体。直到有一天,她在家里做饭时又犯了病,浑身蜷缩满目痛苦地喊出了救命,忽然晕倒。醒来后,李金兰大概想明白了一件事,她被鬼附体了,这个鬼魂是古罗马人,而且非同常人,那是凯撒三王子的魂魄。
凯撒三王子的魂魄给李金兰提出了一个不请之情,他和他的将士们两千年前奉命东征,一路前行于此,不料在这里中了西汉军队的埋伏,葬身戈壁,成了孤魂野鬼,后来无意中接触了佛法,便附身到李金兰身上,只求能借着她的身体,找到菩萨,超度轮回。

《天将雄狮》讲述了古罗马人流落中国西域的故事
“所以,我们在这里建金山寺和骊靬罗马城,把这里当作道场,不仅是因为慈悲心的齐老菩萨广种福田,更是超度这里的鬼魂呐。”甲居士叹了口气,眼望着窗外的祁连山,白雪连绵。
这位女居士体形削瘦,江浙方言口音,看起来六十多岁。我试着去相信她的话,尽管我并非一个无神论者,但听到这一番“神话传说”还是觉得荒诞和不可思议,哪怕凯撒大帝真的要东征,彼时的罗马军队怎么能坦坦荡荡穿过安息和贵霜帝国的国境,能直抵中原王朝统治下的河西走廊呢?
甲居士看着我不可思议的表情,端了一杯热茶给我,又望向窗外金碧辉宏罗马式的大雄宝殿。她拍了拍我的肩,叫我安心,说这里的大部分鬼魂都已超度,剩下的恶鬼也被镇压在大雄宝殿之下,而李金兰本人此后再无异常,很久以前就离开骊靬村了。“真要感谢齐老菩萨来到此地,种下的福田,求得一地安详。”她说。
当我还没来得及追问齐老菩萨究竟是谁的时候,接待室的大门忽然被撞开,亦是一名穿着素色居士服的女居士兴冲冲地嚷道:“甲居士,你看,又出现佛光了。”
我跟随她们来到户外,举头望向夕阳的方向,彩虹一般的弧圈伴着落日,甲居士边拿起手机拍照,边口念阿弥陀佛。在她看来,这就是神迹。
而我目光所及之处,罗马式的穹顶,仿古的城墙院落,还有远方正在施工的脚手架,这片沉寂的戈壁滩在经历让人难以想象的外在改变。或许他们不仅在建造罗马,也在重塑自己的历史,文化与认同。
“对了,你是要挂单在这里住几天吧?”甲居士问。我迟疑片刻,点了点头。

骊靬罗马城的建设是弘扬佛法和广种福田
1994年,永昌县政府在县城南街立起了二男一女的三尊人物雕像,高鼻梁,卷头发,眉目纵深,目光望向今天骊靬古城所在的方位。这三座人物雕像是当地政府雄心勃勃的旅游建设蓝图的开始,但直到今时今日,这片夹在金张掖和银武威之间的河西走廊县域,却依然鲜为人知。

能让当地政府对发展旅游业抱有很大希冀的原因在于上世纪80年代一场历史学界的学术争论:永昌县骊靬村得名是否跟古罗马军团有关?永昌县境内有没有可能有古罗马人的后裔?
尽管这样大胆的学术假设在清朝道光年间就有学者提出,但真正让此问题引发公众关注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澳大利亚和一些国内学者从史料里“小心求证”了一些线索,加上永昌县境内确实有着外貌体质跟当地人大不相同的居民,这些学者便推测永昌境内存在古罗马兵团的后裔,这些后裔可能还居住于今天骊靬村周边。
1989年的《人民日报》关于骊靬的报道让本该是学术讨论变成了一次公共新闻,该报道里声称:西汉元帝时代设置的骊靬城是用作安置罗马战俘的,这一发现解开了公元前53年,一支6000多人的古罗马军队在卡尔莱战役中被安息(帕提亚,今伊朗高原)军队打败突围溃逃,不知下落的历史之谜。
而此后史料的匮乏让这场纷争鉴于沉寂,随后新世纪的学术发现对于想蹭着“罗马”发展经济的当地政府无异于当头一棒:史料里发现骊靬县的设置其实远早于古罗马军队的征战时间,而2005年兰州大学利用遗传技术给当地人的生物遗传检测也证明,当地人基因里并没有发现跟欧洲人种相关联。

长相酷似罗马雕像的骊靬人
不过政府依然没有放弃历史“罗马化”的企图,先后成立了骊靬文化研究会,发表了《骊靬探丛》的论文集,并召集部分学者,多次组织召开了骊靬文化学术研讨会。政府推动上述学术研究活动背后的目的显而易见:为了旅游业和骊靬古城的开发。
2011年,骊靬古城的招商引资终于有了进展,在相继打造了净土宗浙江东天目山和山东海岛金山寺后,皈依佛门的齐素萍居士,也被佛门子弟唤作的齐老菩萨,在这片戈壁滩上投入巨资,计划建造出一座罗马城出来,这座新城以仿罗马万神殿的金山寺为中心,包括了商业街,高档住宅区,罗马大道等项目……当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骊靬古城的工程也浩浩荡荡持续至今。
我试图去询问金山寺的居士僧人如何看待佛教力量主导了骊靬古城浩浩荡荡的开发时,他们的回复很坦然:骊靬罗马城的建设是弘扬佛法和广种福田,你看,将来所有永昌人不都会受益么?
只是每次望着眼前这片崭新的古城,我心里总会惴惴不安。探究历史,或许从来都不是历史学家的事情。

我妈希望在寺院里学到些知识将来能考上大学
金山寺仿佛是浮在戈壁滩上的禁闭岛,南面祁连山麓,荒凉到不长任何野草,向北望去是河西走廊典型的冲积扇绿洲,因为比县城海拔要高,从骊靬古城可俯瞰到县城。除了罗马式的大雄宝殿,寺院本身是一座缺乏亮点且令人压抑的仿古城池,四面厚重的中式城墙,缺了瓮城也依然气势逼人。寺院里的其他建筑皆为中式,而大部分僧房和公共空间,都巧妙地修在厚实的城墙体内,在城墙内侧留有门窗,仿若黄土高原上的窑洞。

骊靬古城金山寺
甲居士给我安排的僧房就在这样的“窑洞”内,房间里五六张上下床铺,形似青旅,颇为简单。进房间的时候人皆不在,我挑了张空闲床铺,安顿行李后,她带领我去食堂吃斋饭。
寺院的修行有自己的规矩,甲居士一路提醒我粮食蔬菜皆是捐赠或寺院种植而来,万不可浪费,粮食不可轻易掉在地方,否则要从地上拾起再吃下去,为了吃掉碗里的食物残渣,要拿开水吞服下去才算妥当。
饭后整个寺院便陷入夜晚荒凉的死寂,借着门窗透出来昏黄灯光,我回到床位,几位室友都在。靠近门边的男子看起来接近不惑之年,头发是秃顶还是剃短,在浑浊的灯光下分辨不清,他安静地坐在床边,床头柜上摆放着几部佛教经书,页脚卷起,暗示已看过很多遍。他被其他人称作师兄,似乎住在这里很久,却不知祖籍身世,不寒喧人情冷暖。
每天早课前他第一个起床,开灯,洗漱,随后去大雄宝殿里修持念经。路上遇到其他人往往点头微笑,至多简单地打声招呼。但即便如此温润的佛教徒也曾对他人“妄语”过,因几名游客用几句粗话抱怨住宿条件的简陋,师兄急冲冲顶撞了一句:这里简陋你可以滚回家去!
最里面的床铺属于一位皮肤黝黑、皱纹深刻的当地农民——老丁。他平时也不怎么说话,但话少不是因为“禁语”,纯粹是因为老实。他说来这里一个月有余,隔几天抽空回家一趟取点吃的,边说边从床下面取出一大袋子,掰了一大块馍馍给我。老丁叹息,自己皈依佛门完全是因为齐老菩萨让他的老婆子(妻子)往生了。那年妻子罹患乳腺癌,临死前曾去东天目山见过齐老菩萨,临走前最后几日躺在床上,不吃任何食物,静卧念佛,终日房间佛教绕梁,安详而去。
老婆子往生后,不像其他人的僵硬,而是柔软的,见此状老丁也决定皈依了佛门。来金山寺念佛,一来也觉得自己了无牵挂,更重要的是给老婆子还愿:“两个娃娃考大学都跑出去了,结婚都在外地,我一个人在家等死,不如在寺院里大家过得还相互有个照应,小伙子你说是不是?”
老丁憨憨地笑,我想他是希望我能理解一位农村空巢老人的寂寞。

骊靬古城金山寺
小丙是唯一住在这里的孩子,一个高中生,睡在我上铺,比起其他人的沧桑沉稳,显然多了一些稚嫩朝气。他来到这边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母亲让他过来的,而他内心或许还跟其他孩子一样,不太适应寺院的生活。好在我遇见小丙以后,寺庙生活多了些现代人的世俗气,比如小丙会告诉我哪里可以蹭wifi,如何爬上城墙,而每天凌晨四点开始的晨课,小丙和我会因为前一晚手机玩得太晚而醒不来。
我在和小丙的接触中大概能猜到他的家庭环境:不曾谈及父亲,母亲一手带大;而他念高中的学校和他的举止谈吐,亦说明生活的懒散或学习的怠慢。母亲将改造小丙的重任托付于寺庙生活之上,正如小丙自己说:我妈希望我在寺院里学到些知识将来能考上大学。
我会每天跟随者小丙去寺院上课,给小丙教授唯识论的师傅,看起来是眉目清秀的南方人,精神抖擞,冬日里单薄僧衣,看不出一丝畏寒的体态。小丙的师傅或许是从我们最熟知的那类顿悟空门之人,在深圳打拼多年,事业小有起色,但终觉俗世灯红酒绿生活的厌恶,偶然接触到佛门,便坦然放下了一切,先是在东天目山出家,后来金山寺建成,义无反顾来此。如今金山寺的僧人居士,十有二三跟他的经历相同。
“接待你的甲居士曾经是上海戏剧界的著名演员,可别小看了她,她变卖了家业和房产,没打算再回上海去。”小丙的师傅说,继而长叹一声,放在桌上的iPhone亮起,闪过一条微信通知。下课临近中午,天色却黯淡下来。我望望窗外,祁连山上浮着一层阴云积雪。
“看来要下雪了,这里的雪通常很大。”小丙说得格外激动。

“你相信你是罗马人吗?”“我觉得是。”石居士说。
雪霁,中午暖阳,骊靬的雪渐渐融化,地面因为化雪而变得泥泞不堪。石居士跳过大大小小的泥淖,终于走到了人工湖边。他摘下帽子,络腮胡和凌乱的头发融为一体,鼻梁高挺,一张西域面孔。我赶上石居士的脚步有些困难,他人高马大,健步如飞。

甘肃骊靬古城
石居士其实并不是骊靬村的人,家在永昌的另一个乡上,只不过因为念佛的缘故在骊靬村租了房子,平常住在村子里,白天去金山寺给僧侣做饭,成了金山寺唯一一位“罗马人”。
金山寺与骊靬村之间隔着一大片人工湖,僧人们认为这亦是齐老菩萨的福田,湖水改善了当地的气候,也给农民提供了灌溉水源。而现在整个湖周围着一圈扎扎实实的铁丝网。石居士说夏天金山寺那边放生,这边的农民就等在岸边捞鱼,后来寺院索性把整个湖围了起来,跟村子隔绝了往来。此举让住在村上的石居士往来非常不便,于是他偷偷在剪开了一个铁丝网的角落,这事儿寺院里还不知道。
我跟着石居士钻过小洞,与湖对岸的金山寺和规划雄心勃勃的罗马城规划相比,骊靬村与西北农村别无二致,稀稀拉拉的土房子无规则的聚集到一起,房院的墙壁全都用的是夯土和稻草。索性这里雨水不多,还不曾听说房屋垮掉的例子。
石居士租了靠近路边的小屋子。他带我进屋,继而取煤、点炉子、烧水,动作一气呵成,没多久递我一杯热茶。房间与其他农民房丝毫无分别,只是桌上多了基本佛教书籍。我上下打望,见墙上众多照片里有一张他跟外国人的合影。
石居士引我去看旁边的那一张,这是几年前政府将所有的“骊靬人”召集起来,大约二十多人,一起拍摄的合影。那次是因为外国人来拍电视,当地政府把县里面长得像“外国”的人全部拉到了骊靬村,让他们穿上罗马人的铠甲,照猫画虎地学着电视里罗马士兵的排兵布阵,折腾了四五天后才回去。之后地方政府设想把他们整体搬到骊靬村住下来,每天给游客展演。

当地人身穿罗马铠甲
“这根本不现实。”石居士说,“没有那么多游客,政府的招商引资也那么难,很多年轻的小伙子,都外出打工了。”
我试着邀请石居士照一张全身像,他答应地很果断。室外,光线充足,石居士抬头挺胸,咄咄逼人的样子,仿佛身上已穿着罗马士兵的铠甲,就像膝跳反射一样自然。我猜,这样的表演场景在他人生中经历过许多次了。
“你相信你是罗马人吗?”
“我觉得是。”石居士说。

罗马城圈占了不少农田,赔款很长时间没有落实
金山寺的僧人居士或许认为,骊靬古城的建设是对当地经济特别是骊靬村的帮扶。不过骊靬村的村民大概不能同意。如果骊靬古城是要重建罗马的话,那么骊靬村仿佛亘古荒凉的北非村落,让他们产生隔阂的不是人工湖,而是包围起人工湖和寺院的铁丝网。
下雪后的骊靬村异常宁静,然而这种寂静让人不能想起任何描述田园村庄的美好词汇,它是中国几乎每一座村庄正在经历的那种可怕但无奈的转变,老龄化和城市化进程让骊靬村加速凋零:在村庄绕了一圈后,只发现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以及在街边围坐在一起晒太阳的老头儿。他们冷漠、疏远甚至警惕盯视每一个不曾见过的陌生人,显然还不习惯于游客的踏访。
我像一个闯入者,围观村庄生活的日常。那几个晒太阳的老头警惕地盯着我,寸步不离。我随口问他们是否了解当地历史,老头们摇了摇头,只是言语含糊的叫我离开,又似乎在隐瞒什么。忽然有个老头指着前方的土房子,说那户人家有个老汉对骊靬村的过去很熟悉,你不妨去问问。
我沿着他指引的方向敲了房门,三十多岁的女子开了门,说明了来意后,女子示意我进客厅稍等,不一会儿,推着轮椅上的老汉出来了。他所回答的跟我预期一致,在“罗马”出现以前,骊靬村和周边的村庄一样,毫无特别之处。只是在答谢告辞时,老汉忽然又叫住我:“小伙子,你是外地的记者么?我看你像,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把这件事报道出去。”
老汉说这村庄的颓废都是庙里的齐老婆子(金山寺的僧人居士称呼的齐老菩萨)有关。金山寺和罗马城的开发建设圈占了不少农田,这些农田对于绿洲上的农民来说就是命根子,之后赔偿款又很长时间没有落实,去年底的时候老头子的儿子带着几个人去告状,没想到就莫名其妙失踪,后来进了局子,过完年都没放出来。
临走前,老头子再三请我为他多拍几张像,他说自己已经不在乎性命保全,只是希望儿子能尽早出来。

甘肃骊靬古城
不过村长给我描绘了骊靬村的美好蓝图,其貌不扬的小村庄正在想方设法融入骊靬古城的建设当中:县政府在县城建了居民楼,村民可以选择搬到城里居住;而眼前这些和“罗马城”格格不入的土房子,将来要建成罗马风格的别墅,留在这里的人可以不用种田,可以靠罗马武士的表演和农家乐赚钱,品尝当地的特色食物,比如披萨饼、意大利面……
“披萨饼是这里特色的食物么?”我问。
村长尴尬的微笑摇头:“不,不,那个饼子我还是吃不太习惯。”

一算命先生告诉他,你的孩子中了魔
我打算离开骊靬古城的前一天下午,甲居士问我为何没见我上早课?我想了很多理由,但最终选择诚实告诉她早上起不来,不过已和小丙约定好明早必要去早课的。
那晚房间里多了一对父子,河北人,早上匆匆忙忙的火车赶到兰州,又坐长途汽车赶到永昌,一路大雪,高速公路封闭,耽误了不少时间。孩子睡到床上,已是昏昏沉沉。
河北男子只为了孩子而来,说起儿子他眉头紧锁。九岁的孩子调皮多动,成绩糟糕,他请过保姆、家教,送到武校,但都不能改变孩子“恶劣”的品行。直到有一天,一算命先生告诉他,你的孩子中了魔!男子按照算命的建议,带着孩子奔波去全国各地的道观和寺庙,只为了解除魔障,或者能收留孩子的地方。
在山西的某座寺院拒绝后,金山寺是他们来的第二站。尽管金山寺有专门的儿童佛学培训班,但学费高昂,录取挑剔,孩子依然被拒之门外。
河北汉子不顾戒律,抽烟消愁,絮叨着生意的辛苦和顽童的罪行,每一句都会带上些骂人的几个脏字。修行最久的大师兄道出了真话:真看不出孩子什么问题,这当爹的倒是问题一大堆。

甘肃骊靬古城
离开那日凌晨三点,小丙唤醒了我,洗漱、换服,跟随他向罗马万神殿的大雄宝殿走去。经历一系列今日我早已忘得干净的仪礼,只记得插进男众的队伍里,口念阿弥陀佛四字,持续两个小时。
七点多,金山寺的罗马金顶迎来第一缕阳光,众人在离开殿堂,换服、饮食。
九点,起身离开。僧侣、居士以及向我这样的游客,在冰天雪地中等待最早去县城的班车。僧众们显然是去县城为了采购,骊靬古城生活的不便,让去一趟县城仿佛短暂的宣告回到尘世,换来暂时的自由。
同一班车上还有河北父子,父亲上车前抢了前排座位,拉开窗户,仰头,仿佛把一路上所有的不快集中于喉咙:呸!
痰化于雪地,了无痕迹。

本文首发于土逗公社
转载请联系土逗获得内容授权
土逗事
故事从来不只是发生在聚光灯下,
茫茫时间流过,遥遥路途走过,谁不是有故事的人?
狂放的笑,纵情的歌,奔涌的泪;
刻骨铭心的爱,怒发冲冠的恨;棰心的痛苦,难言的悲愁,幼稚的相信,单纯的盼望;一夜白头的苦闷,付之杯酒的隐忍,千回百转的纠结,走投无路的绝境;抑或是平静的孤独的似乎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一天又一天⋯⋯在这里,土逗等待分享你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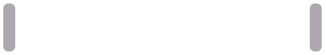
点击关键词查看更多
这里“阅读原文”,查看更多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