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剪纸里的求救

你知道吗?
“太阳其实是个大闺女。
因为她手攥一把针,谁敢正眼看她就扎他眼睛。
而月亮则是个男人。
胆子大不怕黑,夜里也出来陪人下地干活。”
不是摘自什么文学或童话名著。
这是一位年迈的陕西农妇,对自己剪纸的解释。
一轮烈日,一轮明月,照着花房里的一位姑娘。或许是我近年见过最浪漫,也最震撼的作品——
库淑兰最钟爱的题材《剪花娘子》
它的作者叫库淑兰。
自出生起,她用了65年时间,让自己的剪纸从窑洞挂到了国内外艺术馆展厅。
联合国都要为她戴上桂冠,称她一句“先生”。
纪录片《一梦大千世界,一剪锦簇繁花》
在她去世后,我们又用了18年的时间重新发现这位民间艺术家。
陕西省美术博物馆最近的一场回顾展《花间世界》,让库淑兰的纸花在微博的数万转发里绽放。
面对着那张她跪着切菜的背影相片,人们惊呼:
“这是苦难里开出的花朵!”
我自然也是为她的作品及故事落泪的人之一。
自打第一眼看见,就对她的传奇无比心醉神迷。
但对很多人的这套“苦难美学”,我感到不适与困惑。
库淑兰的剪刀仿佛可以创造整个世界。
同时,她也恰恰在讲述着这个世界的,关于苦难的真理。
第一次刷到库淑兰在窑洞里和她作品的合影时,我的反应蛮奇怪的——
上海美影厂。
不是本美影厂脑残粉又在瞎YY。
同样取材佛教文化,同样深得民间艺术影响,同样质朴又华丽。
库淑兰的剪纸和国产动画美学顶峰《九色鹿》,确有异曲同工的妙处。
只是,这两幅瑰丽画卷的源头虽相似,展示的却又是不同的内核。
它们恰好对应了佛教的两大侧面——
《九色鹿》对应的是远高于人性的神迹。
《剪花娘子》对应的,则是人性造就的苦难。
库淑兰的路一直很难走。
1920年,她出生在咸阳一个农民家庭里,一睁眼便是在逃荒乞讨的年代。
按当时看,其实她胎投得不算差。
家境不愁温饱,童年自由自在,甚至上过几年新式学堂。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她的作品里总有种热烈的童稚。
比如《空空树》。
她哼着自己编的歌谣,“空空树,树空空,空空树里一窝蜂”。
苍凉的黄土高原,被她剪成了繁茂梦幻的奇观。
我看到的时候很震惊:这是大人配拥有的想象力吗?
然而在九岁时,库淑兰的童年却戛然而止——
她能上树能趟河的双足,被母亲亲手捆成了小脚。
她的身体再也跟不上自己的思维,在向往自由的同时更不得不习惯跪着干活。
缠足恰如一个象征。
她再也没能逃离当时绝大多数底层人民的命运。
巧合的是,库淑兰的前60年,恰好重合着历史动荡的60年。
但如今回头看,压在她身上的,是大时代,也是小家庭。
她的丈夫是个庄稼汉子,祖上阔过,但到自己这辈只剩下使唤人的脾气了。
因此自17岁出嫁,库淑兰就再没过过清闲日子。
她得跪在地里收麦子,迈着一双小脚上山挖草药,还要替人绣花缝补,乃至看病驱邪。
以此才勉强撑起这个穷苦的家。
她的乡亲提起她最深的记忆便是,她从睁眼就干活到天黑。
但即便如此,夫家还是对她动辄打骂,甚至直接拿起干农活的铁叉插进她皮肉里。
库淑兰是幻想过婚姻的美好的。
她的剪纸作品里时常出现两小无猜的美好,配的是“江娃拿哩花鞭子,打了梅香脚尖子”,打情骂俏的歌谣。
但在现实里,“情”与“俏”都不曾存在过,只有让人绝望的暴力。
最讽刺的是,要不是库淑兰有这么多绮丽的幻想,还能将其变成手艺卖钱。
她在家里的处境,可能只会更加痛苦。
老头也高兴了
比过去干活挣的钱要多了
不过,对于生活在封建时代余晖的女人来说,这种生活其实是常态。
千千万万个库淑兰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她本人也未必觉得苦。
真正痛在她心尖的,还是骨肉亲情。
自嫁人后的十年里,库淑兰一连生下了13个孩子。
其中有10个在艰苦的岁月里相继夭折,成了她心中无法治愈的伤痛。
她的剪刀下时常出现孩子的群像。
但在一片热闹的色彩与图形之下隐藏着的,又是沉重的哀思。
可人生的奇妙也就在这里了。
库淑兰一生的基调注定是苦难
。
但真正让她区别于万千苦难众生的,又是一场神迹——
85年的冬天,她冒雪出门替乡里人的孩子看病。
回程却失足摔下了一条深沟,陷入了昏迷。
在那个时代,这个地界,这就可以直接准备身后事了。
但四十多天后,库淑兰居然奇迹般地苏醒,复原,回到艰辛的人世。
而且,还没能下地便拿起剪刀开始创作。
自此,风格大变。
她原本生动拙朴的民俗剪纸,变成了巨幅的华美画卷,像唐卡般震撼。
库淑兰说,有个叫“剪花娘子”的神仙救了她,还在昏迷时教授了她高超的技艺。
再到后来,她开始称自己就是“剪花娘子”。
不太信鬼神的我,却莫名对这个故事深深着迷。
跟迷信无关。
而是,我很爱其中所暗含的一种浪漫——
在我们听多了的外国神话里,人们总在等待一个仙子,一个上帝的救扶。
但在库淑兰的传奇里,她就是那个救自己于疾苦的神。
孤身一人,造出了自己的莫高窟。
库淑兰在2022年的再度走红,让我想起前不久的另一个“网红”——
二舅。
两者区别是库淑兰有更耀眼的成就。
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拥有一项为人称道的天赋——
绝对坚韧地忍受痛苦,甚至能在绝地开出花。
自然,库淑兰的作品有一种极致的美,二舅的故事也有动人的力量。
但在一大波“二舅营销”之后,我却谨慎多了。
我不会再把她的作品解读为“苦难中的希望”。
咱不急着展开探讨,先接着看点艺术。
2003年,纪录片导演沙青到陕西拍摄新作。
他认识了这样一位农民——
老母瘫痪,妻子在外打工,两个孩子还有一个是脑瘫。
可让人惊异的是,这位农民却能伴着屋外黄沙的呼啸,一边看着两个孩子,一边手拿剪刀。
上下翻飞,纸张不多时便化作了灵动的蝴蝶。
《在一起的时光》
他本名叫雷祥生,但他更愿意称自己为西亚蝶。
既因为他一直在剪蝴蝶,也因为他向往蝴蝶的自由。
在很难称作窗户的窗户上,他的剪纸和一片塑料膜布一同抵御着寒风。
也为西亚蝶圈出了逼仄生活中最珍贵的一隅平静。
这部纪录片有个乍一看很温暖的标题,《在一起的时光》。
但它展现的只有绝望和沉默。
孩子痛苦得难以忍受,家庭艰难到难以为继。
西亚蝶在镜头前常一言不发地呆坐、出神。
为数不多开口的时候,不是在安慰儿子,就是在跟医院“讨价还价”。
是的,对于足够穷苦的人,连救命的手术都是要商量着少花点钱的。
但看到作为艺术家的西亚蝶的作品时,那种挣扎无助,瞬间又只剩让人动容的平静。
军官和爱人在火车上热吻,动物和鲜花将一对恋人盛情包围。
这是在传统艺术里少见的对爱的渴望。
一位少年带着灿烂的笑容,长出双翅从轮椅上起飞。
这是他献给患有脑瘫的儿子最浪漫的祝福。
再到他最钟爱的蝴蝶题材。
这张剪得其实相对简单很多——
一对恋人相拥在蛹中,却终于生出蝶翼振翅而飞。
这是他献予自己愿想。
在婚姻与爱情无关的世界里,他和妻子没有感情,却又被谁逼着似的一直过着。
直到后来他才正视到,自己其实恐惧这段婚姻。
而且,他其实也不喜欢异性。
在儿子离世,和妻子分开后,他依旧困惑且痛苦。
西亚蝶曾拿过奖,当时他的领奖词是这样说的——
花是美好的,鸟是自由的,月亮是我的平台,今天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就是我期盼的月亮。来源:《GS乐点》
但恰如月亮只在黑暗中显得美丽,他的人生,也并未因艺术这轮明月,褪去孤苦的底色。
纪录片中有这样一个画面。
西亚蝶在贫瘠的黄土中种出了娇艳的月季,他小心翼翼地剪下、插瓶、摆弄。
随后小心地摆在了熟睡的儿子枕边。
这是昏暗的电影里,极少数的一抹亮色。
恰如库淑兰一样,他也在极力用美装点晦暗的生活。
但你能说这是黑夜中的希望吗?
明月本身就是黑夜的一部分,它只能聊慰人心,不能消灾减祸。
库淑兰的人生映照着无数个女性,西亚蝶也是少数群体的一个缩影。
他们并没有因容忍或“化痛苦为艺术”,跃出生命的压抑。
希望,确实能给人走出苦难的力量。
但不是所有在苦难中的挣扎和自救,都能被美化为希望。
这种歌颂带着无耻。
它不单削减了苦难的重量,还把承受苦难作为一种美好品质。
你瞧,她不单忍受住了,还在绝望中创造了伟大的艺术,多牛X啊!
这是对库淑兰和西亚蝶们彻头彻尾的误读。
他们忍受苦难,是因为没得选择,命运已经把重担压在了他们身上。
而之于他们的艺术。
我们该看到的不是“苦难的土壤开出了花”。
而是在被花朵惊艳的同时,去回望那片被我们忽视已久的土地。
其实我很懂大家为什么热爱库淑兰、二舅式的叙事。
他们的故事像一个柳暗花明的寓言,告诉我们生活很操蛋,但我们依旧可以乐观承受,搞不好还能创造什么奇迹。
但如果故事中的人是你。
你真觉得自己会相信“柳暗花明”吗?
库淑兰在歌谣里分明唱的是——
前天吃搅团
昨天吃搅团
今天咋还吃搅团?
这是一场无尽的循环。
成为剪纸大师的库淑兰救不了那个15岁就被逼着退学嫁人的小女孩。
在国外办展的西亚蝶弥补不了错误的婚姻和病逝的孩子。
二舅也没办法扔掉拐杖重过天才的一生。
我倒觉得他们真正动人之处,恰如《在一起的时光》所呈现的——
平静。
他们就端坐在苦难里,把绝望稀释到咽得下口的程度,再点缀一点灵光与花色。
然后静待一生过去。
他们从来没想过用过来人的身份给你一个答案。
只用一个承受着苦难的佝偻背影,展示着普通人的历史。
历史预言不了未来,时来运转从来都不在计划里。
但同为普通人,他们的苦和我们的苦,本就存在不需道明的共振。
“希望”对于很多人而言其实是奢侈品。
很多人不会有库淑兰的运气。
且你怎么说得出口,她有什么所谓“运气”?
百忍成金的慰藉往往很虚伪,是种居高临下的隔靴搔痒。
它的可恶之处在于,无脑推崇苦行精神,无视真正沉默的大多数,甚至开始蔑视出声叫苦者。
但鲁迅写出祥林嫂,是为了让我们嘲笑她不断重复着自己受的磨难吗?
他说的分明是,无论反抗还是顺从,生活在吃人时是不会挑剔的。
无数的“库淑兰”,在生活里可能真的望不到光芒。
他们始终在苦海浮沉,也平静地接受着这日子。
他们的希望太沉重,沉重到不能被随便用来贩售。
今年我最喜欢的国产电影之一,《隐入尘烟》。
很好笑的是,这部作品同时招惹上了两帮人的狙击——
一方骂它美化苦难,一方骂它贩卖苦难。
所以这是个怎样的故事?
黄沙包围的一个村子里,老光棍马有铁被家里安排娶了身患隐疾的曹贵英。
这是一对被全世界抛弃的陌生夫妻。
却最终在穷苦和摧折中提炼出了甘美的爱。
骂它美化苦难的,无非是指斥它太过浪漫。
多数农村女性比起曹贵英,肯定更接近库淑兰。
这么拍难道不是在掩饰女性的困境?
诚然,在穷困中描绘一段纯洁的爱,这是蛮不“现实主义”的手笔。
但宠妻无底线的马有铁,并不是失真的假人。
在生存面前,他的粗鄙和鲁莽仍然留存,不至于完美到脱离现实。
他们不是富足到拥有爱,而是赤贫到只剩下爱。
流离失所,被富人当血库一样抽血,一次次失去家园,最终落得阴阳两隔。
这能叫“美化苦难”吗?
与其指责这电影用浪漫稀释了绝望,倒不如说它用这点浪漫把人间疾苦反衬到了极致。
再谈“贩卖苦难”。
有人说《隐入尘烟》故意展示农村不堪的一面,是为了博眼球,甚至涉嫌迎合外国对中国的刻板想象。
求求这些人睁开眼吧。
前些日子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问题——
现在还有穷人吗?
有一个回答是,他们就在电商平台200元山寨电视机的买家秀里。
这也是虚构出的穷困吗?
相比起来,《隐入尘烟》的镜头甚至还算得上整洁干净了。
我喜爱《隐入尘烟》的理由,不在于它对苦难描绘的写实程度。
而是它忠实呈现的,俗世人对苦难的态度。
平静,沉默,倔强,恰如庄稼一样努力生长过,随后静待死神的收割。
电影中,夫妻二人用麦粒压出的梅花印赚足了网友的泪水。
这盛开在皮肤上的花朵,也恰如库淑兰和西亚蝶华美的剪纸。
它们超越不了命运,但却能衬出命运真正的底色。
苦难的唯一真理是,承认它。
不捂住眼装看不见,也不把它视作绽放希望的花田。
而是理解,它就是我们忽略已久的,芸芸众生的原本样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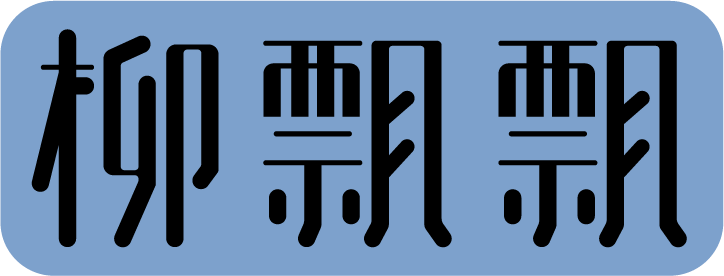
承认普通人的痛,很难吗?
↘↘↘
阅读原文 关键词
库淑兰
剪纸
苦难
就是
这是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