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札记



· 这是第4359篇原创首发文章 字数 6k+·
· 贾铭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回家过年,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一件事。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而事实上,刚迈进腊月,很多同事就期待着回家。比如,食堂吃饭的时候,总有同事交流疫情进展、地方防疫政策和离返京经验。还突出表现在:1月6日15:30,行政办公室邮件群发了离京审批政策通知:“原则上倡议春节假期期间非必要不出京”“离京必须严格执行报备审批”。仅仅5分钟后(15:35),办公室又群发了春运抢票日历和攻略,提醒大家及时购票。
盼望着、盼望着,假期终于到了。可倏忽又走了,给人的感觉是它虽然来了,但又好像没有来过一样……
2022年1月30日—2022年2月5日,我返乡5天。所见所思所想,散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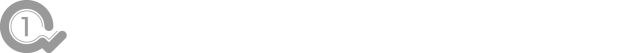
临近年关,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准备返乡过节的群众,都绷紧了神经。大家共同的愿望就是:不要有本土传播病例。但可惜,西安暴发了一波疫情,各地也有零星散发。
1月15日,北京海淀疾控公布新增一例阳性病例。此后,海淀、丰台、房山、朝阳、西城,都陆续有确诊病例。海淀、丰台,也陆续出现中风险地区。
北京,既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又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表率。城市治理能力,自然排在全国前列。所以,尽管北京有中风险地区,但疫情防控依然相对精准,并没有对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特别大的影响。
1月20日,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某县长在会上说:“你只要返回,先隔离再拘留。”
“恶意返乡”成了2022年的第一个热词。1月21日,北京新增10例本土确诊和6例无症状感染者。1月23日,丰台全区开展核酸检测。陆续又有其他区开展全区核酸检测,我们这些在京工作的非京户籍人口,心凉了半截。
自1月23日开始,我就多次给家乡的社区打电话(各个街道和社区的电话在当地政府公号有多次推送,网上也很容易查到),询问当地最新的疫情防控政策。22日的时候,我在微信群看到有人说,只要从有中风险地区的县/区返乡,就要集中隔离7天、居家隔离7天,再自主健康监测7天,也就是“14+7”。这是典型的层层加码。
但我致电询问时,接线员却告诉我,只要不是中风险地区返乡,就只需要提前与社区报备,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抵达当地后,再自主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即可。23日、25日、27日,我三次致电,回复都一样,且态度都很友好平和。返乡过程非常顺利,虽然我提前做了核酸,也没有人查验我的核酸检测证明。抵家次日,我又主动到当地医院,补查了一次核酸检测,免费。
从这个角度来说,持续的疫情或许还是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或者说,至少提升了部分地区的政策执行方式。
就说我们市,2020年返乡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说起来啰嗦,但有点好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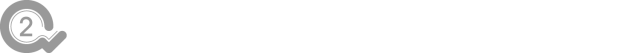
故事1:
2020年的时候,尽管疫情已经发生了一年,可我们事前仍然很难获取当地责任部门的咨询电话。但当我们顺利抵达当地高铁站的时候,专门有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在出口等待。并不说明意图,只是喊:北京来的来这里集合!
乘客们聚拢到两名工作人员身边后,两人就要求我们上交身份证,也不告知身份和用途。
待该次列车乘客出站完毕后,“制服”大手一挥:都上车!也不告知去向。现在回想一下,我们一群人,并未问明去向,就敢上车,一方面是由于对方身穿制服,代表公权力;另一方面,怕也是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作祟:反正这么多人,别人都上,我也上呗。
上车以后,司机与乘客间有塑料薄膜隔开,算是一种“物理隔离”的手段。全程,司机跟我们没有任何交谈。最有意思的是下面这一幕,给我们现场演绎了恐慌、谣言是如何产生和传播的。
首先是大婶A给家里打电话,说是被拉上了一辆大巴车,不知道咋回事儿。家里人说,估计是防疫要求,可能要隔离。
接着是大婶B给家里打电话,说是可能要被隔离了,去哪儿隔离还不知道,反正让集中上了一辆大巴车。
这时候,整车人都有点乱哄哄的。
接着是大叔C给家里打电话,中气十足似又故作轻松还有点洋洋得意地说:“完了,回不去了,要隔离7天哈。”
接着又有很多人给家里通报,说是要被隔离。即使我们这些“沉得住气”没有给家里打电话的人,不得不说,内心其实也做好了被隔离的准备。你看,事实上,我们没有获取任何可靠消息,但我们几乎每个人都笃定:我们会被隔离。
所以,有时候,并不需要事前策划和幕后黑手,一个群体,就会基于一些非常有限的线索,推测、演绎出一个故事,并且不断补足这个杜撰出来的故事的细节,最终,大部分人都笃定,故事就是事实。
这种群体现象,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乌合之众》,写得非常清楚,感兴趣可以找来看。
故事2:
事实上,我们最终并没有被隔离。
乘客先是听从工作人员的指示,老老实实上了车。尽管经历了短暂的慌乱,但当所有人都笃定会被隔离后,车内反而又安静了下来,只有少数乘客偶尔翻找东西带来的“窸窸窣窣”和车辆偶尔颠簸一下的“咣当声”。总之,这辆不知道将要把我们载向何处的车,与我们日常搭乘的其他的车,似乎没有任何不同。
车辆行进一个半小时以后,我们到达了我们熟悉的,当地的一家酒店后院。有两个身穿白大褂、戴着口罩的医护人员在门口等我们。
我们下车后,“白大褂”喊:都来我这领身份证、登记。
一群人,乱哄哄地围着“白大褂”领身份证。我心想,如果真的有感染者,即使在车上没感染,此刻基本也都“全军覆没”了。期间,由于戴着口罩喊名字不清楚,“白大褂”,还把口罩拉到了下巴。
很快,我们进入酒店,每人一个房间。但是,酒店的这栋楼明显并没有被投入使用,床品不脏,但明显没有更换过;有的空调是坏的,有的遥控器没有电池;洗手间的自来水初放也是浑浊的,没有热水。
得,又没人理我们了。没有人通知我们,隔离后要做什么,要隔离多久。
大概十五分钟后,有两个“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穿着隔离服,来给我们咽拭子核酸采样。
到我的时候,我赫然发现,给我们采样的这俩人,就是刚刚在门口给我们登记的俩人……登记的时候,两个人的防护十分稀松,一个人还摘下了口罩……此时,又全副武装……
核酸检测当晚八点,就出了结果,所有人就都可以回家了。但每个人支付了80元的隔离费用(只入住了4小时,该酒店正式房间1天的房费为114元),收款账户显示是酒店。我当然对收费是有质疑的。但又能如何呢?预想中的隔离7天没有发生,就算万幸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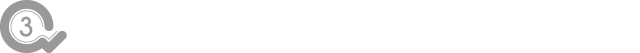
与上一个春节相比,这一个春节的疫情防控,尽管节奏依然很紧张,但在执行方式上,大部分地区,确实更加温和。比如,去年的时候,外地返乡后,当地社区防疫人员到户访谈,详细登记从哪儿来,仔细叮咛少出门。今年,没有实地跟进。但在大年初一、大年初二,县级、街道,两级防疫办公室,分别给我致电,再次进行流调登记。
两次接电话的时候,我都询问了对方,春节是否放假。答曰,春节期间全员当值,节后可以调休。
其实,不仅是因为疫情,基层工作人员才比较辛苦,很多时候都辛苦。事实上,很多老百姓对公务员存在误解,一直把“公务员”等同于“铁饭碗”。工作稳定不假,但铁饭碗里的饭却不一定那么香。绝大部分基层公务员的日常工作并不轻松,甚至非常辛苦,收入并不高,上升空间更是极为有限。
第一,相对来说,福利不错,但也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好,绝对不是高薪。
公务员工资主要由基本工资(职务职级工资)和津补贴组成。职务工资根据不同行政级别划定,职级工资由学历、工作年限确定,这两部分相对固定,全国标准统一。而津补贴部分较为灵活,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财政水平确定。
比如,某县级市工作7年的公务员,工资构成如下:职务工资380元,职级工资408元,职岗津贴245元,地区工作补贴290元,综合补贴170元,医补6元,差旅费200元。此外,煤贴、误餐、通讯费、交通补贴等共1210元,实发2909元。另外,我询问了我们当地的公务员,答曰,第一年月薪实发到手不到4600元,工作五年后,实发月薪不到5500元。
当然,公务员确实有一些福利待遇,比如免费食堂、医疗补助等等。
第二,上升空间极为有限,大部分公务员能在副科级退休就不错,少部分人可以熬到正科,也有少部分人一辈子科员。
道理很简单,一个萝卜一个坑。
举个例子,一个中等规模的县级市,正式有编制的公务员人数,大概在2000~3000人左右,正副处级干部总共有30~60人左右,正副科级干部大概280人~560人左右。正常来讲,新入职的为科员,工作满4年,第五年时才有资格升副科。有资格不意味着一定能上。
所以,为了缓解这种正常晋升序列的拥堵,地方又有一些创新,在科员-科级,科级-处级,再分一些职级,这就复杂了。
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写过一篇博士论文叫《中县干部》,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一部分基层官场生态,感兴趣可以看看。
我想说什么呢?
年年考公热,但要不要考公,首先要对公务员的工作有清醒的认知,其次再看自己是否适合,是否喜欢。我盲目从众上个车,最多被隔离7天,如果盲目从众考公务员,考不上浪费时间,考上了发现不喜欢,再转行,又浪费时间,动辄就是浪费三五年。要慎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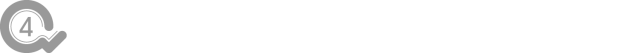
北大周其仁教授鼓励大家除了书本中的经济学,还要学习“真实世界经济学”,确实,生活中处处有经济学。
大概十年前,我们那边的乡村就陆续开始修水泥路。村庄出一部分钱,上级政府还会补贴一部分。有的村庄比较富裕,村庄部分,村委会全资承担。有的村庄财务情况差一点,采用村民集资的形式,可以出钱,也可以出工。这里面有什么经济学现象呢?
首先,公共品供给问题。村里修路,是典型的公共品。由于存在“搭便车”问题,如果没有其他的约束或者激励措施,村民很难自发地集资出钱把路修成。所以,地方政府出一部分钱,村干部再游说、激励富户或者乡贤出一部分,剩下的再村民集资,村民就有意愿有能力把路修成。
其次,迷你版以工代赈。有的村修路的时候,优先雇佣本村村民,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应聘”。这样,本村村民在务农收入之外,还增加了务工收入。修路的过程,既增加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又增加了村民收入,相应的,村民收入上升,又利于消费。这不就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施行的以工代赈吗?
最后,产业转移、规划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有点牵强,但也蛮有意思。我老舅家是个体户,主营业务是服装加工。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就把工厂从城郊搬到了农村(产业转移)。而去我老舅家有路线A和路线B可以选,都是上文提到的十年前修建的水泥路,路宽4米,且都是穿村路。
不同的是,路线A全程都是4米宽,没有错车道。路线B途经的村庄村干部比较有远见,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会修建一段5~6米宽,长度几米十几米不等的路段作为错车道(规划问题)。久而久之,选路线B的人更多,于是,沿途村庄临街的地方,就多了几个小卖部。有意思的是,路线A和路线B几乎是同时修建的,所以如果当时各村之间的信息传递再通畅一些,说不定路线A也会预留错车道(信息不对称问题)。
后来,我查了一下,交通运输主管部门2019年发布的《小交通量农村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规定农村道路无大型、重载型车辆时,按照四级公路标准建设,3.5米宽的单行道,每公里不应少于3处错车道。不知道更早的时候,有没有相关技术标准,如果有的话,为什么A路线没有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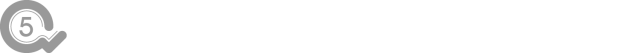
外甥(姐姐的儿子)今年10岁,来我家吃饭。吃草莓的时候专心致志用牙签给草莓“剔籽”,这要是二十几年前我在亲戚家饭桌上用牙签剔草莓籽,我爸的大嗓门早就扯起来了:干什么!好好吃!但是我姐怎么说的呢?我姐说:对,好好剔,以后有女朋友,就得给她这么剔哈,吃火龙果也得剔!
培养暖男,从娃娃抓起,有读者家有适龄女儿吗?哈哈!
结果小朋友脸都红了,赶紧把草莓塞嘴里吃掉了。
其实,小孩子给草莓剔籽,只是一时好玩罢了,即使不管他,他也不会真的每次吃草莓都剔籽——那还不得累死。我姐跟我爸,反映出两种教育方式。一柔一刚。
那我是不是应该批判下老爸的粗暴的教育方式?其实也不是。不同的教育方式可能跟人所处的性格、年代、社会背景、受教育程度都有关系。很多人都说我独立,抗压能力强。所以,到底是老爸的“坏脾气”使我的内心更加强大,还是我的内心本来就足够强大,所以抵御了老爸的“坏脾气”,这个也很难说清楚。
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有自己自由的意志和权利,不是父母的附属品,也不是成年人实现自己当年未竟理想的工具。如果你愿意把小孩子当平等的朋友对待,多一点尊重,少一点控制,教育小孩就不会变得那么复杂。
比如,我认识的一个年轻妈妈,允许自己读中学的儿子2022年第一天,自己一个人骑行几十公里,穿越小半个南京城。而班里其他同学的妈妈都不允许自家孩子这么做。难道这个妈妈不担心孩子安全吗?可谁年轻的时候没有个奇思妙想呢?我读大学的时候,也自己买了自行车,经常在成都的大街小巷骑行。本计划骑行川藏,后来车被偷了,只能作罢。
马尔克斯说:“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生命重在体验,什么年龄做什么样的事情,有些事情,错过了那个年纪,可能一生都不会再有那个想法。
说到教育,又不得不提2021年热议的“普职分流”。
2021年3月,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坚持职普比例大体相当。这将意味着,中考结束,仅有一半的学生可以走向普通高中,而另一半将走进职业教育的大门。事实上,职普五五分流并非新政,几十年前就提出来了,2021年只是再次强调了这个原则。
很多专家建议“取消职普分流”。比如,2022年1月,北京大学国发院院长姚洋在媒体采访时就表示:“教育制度要进行系统性改革,根本是要转变思路,但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认为可以从升学制度来入手,首先应该取消中考分流。对比来看,城市里的孩子被分流的可能性很小,被分流的更多是郊区和农村的孩子,这就造成了一种教育不公。”
当然,也有专家“支持职普分流”。
我个人观察,中国的职业教育改革,应该是想借鉴德国“双元制”教育的成功经验。关于中国的职业教育和德国的双元制,水姐在《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一文中有清晰的介绍,这里不展开。
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讲,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高质量技术人才。年轻人选择职业教育路径的前途或许也并非想象中那么黯淡。
但我想说的是,与德国相比,我们现阶段的国情,或许还难以为职校毕业的学生提供公平平等的社会环境,也会出现姚洋院长担忧的城乡教育不公的问题。
当然,教育部已经出台了包括双减在内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效如何,还需要子弹飞一会儿。
总体上,我认为,教育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缩小城乡间的教育差距。而另有一些问题,比如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问题,可能不仅是教育改革面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教育改革之外的问题,应该全社会采取措施,合力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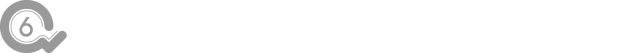
互联网时代,每到春节前后网上总会出现一个热门话题:现在年味儿变淡了。
迈入腊月,一直盼望着回家,但过年前两天,还不能最终确定是否可以回家的时候,忽然脑子就有点懵:如果不回家,在北京我该做点什么?过年要自己做饭吗?要不要打扫卫生、装饰房间?这7天假期要怎么过?茫然、慌乱、紧迫油然而生。当最终坐上返乡的高铁,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景色,一下子,心就安了。
或许真的是年味儿淡了,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长大了,或者变老了。刚满月时候我还抱过的婴儿,现在已经小学二年级了。今年我刚教会叫“舅舅”的外甥女,可能一眨眼,又该上幼儿园了。
时序更替,新故相推。
曾几何时,我们熟悉故乡的大街小巷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可恍然间,我们漂泊在外的游子们和故乡,又成了彼此熟悉的陌生人。我们错过了故乡的很多人和事儿,可我慢慢感觉到,这种小遗憾或许也是美好的一种证明。

- 作者:贾铭,青年经济学者、自由撰稿人。研究领域为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关注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政商关系、博弈论。
「 图片 | 视觉中国 」


内容合作、投稿交流:[email protected]
阅读原文 关键词
疫情防控
核酸检测
1月
北京
村民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