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的鸡听见她的名字都闻风丧胆,这个被严重低估的女演员,才是真正的文艺女神| 专访


这是司马推送的第 741 个与众不同的人
她是中国唯一一位满贯入选欧洲三大电影节的80后女演员,却热衷走完光鲜的红毯后,一头钻进厨房煮火锅,做口水鸡,“戛纳的鸡听见她的名字都闻风丧胆”。
国际电影节上,各国导演们互相以“黄璐的导演”的身份打招呼,在参加《演员的诞生》前,这个名字却无人知晓。
真人秀播出后,认识她的人多了,她挺开心,却也不是太在意,“喜欢的自然会喜欢,不喜欢的怎么也不会喜欢,还不如自己开心一点。”

5月8日,又一年戛纳电影节开幕。这个星球金字塔尖上的导演、演员、制片人们,只有这时候才甘愿躬身俯首,如鱼滑溜入网,等待在这个法国渔村大放异彩。
网红、毯星、新出炉的火热偶像,霸占国内媒体的往往是另一番花团锦簇。没有作品也厚着脸皮在红毯上赖足6分钟,类似的滑稽闹剧层出不穷。
而她习惯了被官方邀请携作品出席,红毯上松弛自如;暂别镜头后,钻进当地公寓全神对待一只口水鸡。如果有一本《戛纳别记》,抖落掉那些滑稽剧,黄璐这样有趣的轶闻该是记上一笔的。


前一秒在电影殿堂,下一秒就在厨房~
不只戛纳,世界顶尖的电影节像是游乐场,被她玩了个遍。大四准备毕业论文时,她接到了组委会邀请,随即凭借李扬导演的《盲山》第一次来到戛纳。之后,带着《世界之间》和娄烨的《推拿》,她分别登场威尼斯和柏林国际电影节。国内80后女演员里,她第一个全满贯了欧洲三大电影节。
挑剔而神经质的法国媒体赞她,演绎细腻而动人,没有太大起伏的东方面孔,却蕴含了惊人的爆发力。
导演们都偏爱她,知道用了她,片子几乎一定是能拿奖的。有回釜山电影节,来自中国、英国、斯里兰卡的导演们扎堆儿聊天,聊着聊着,发现虽然各自国家的经纬度天差地别,竟然都是黄璐的导演。从此,“黄璐的导演”成为电影圈打招呼的新方式。

黄璐《推拿》
然而这张面孔出现在银幕上时,“黄璐”就消失了,浮现出的一个个角色,个个被她拿捏得极为得当,好似本色出演。
讲述女大学生被拐入深山的《盲山》,这些年每每有类似的热点事件,是一定会提及的。有人看过电影,甚至担心她现实中过得好不好。

这倒也不是个例。
所有见过黄璐本人的人,
都要花费一些时间,
才能把“两个她”对上号。
银幕上的她,
是汗流浃背寻路无门的绝望母亲。
一个闭眼,让人心碎。

新加坡社会底层的妓女,
笑得天真畅快,
角色的立体和丰富,
瞬间出来了。

没有调动太多面部神经,
一个俯仰,一次吞吐,
没有说话,却让人想探究,想一看再看。

银幕下的她,
同时做着化妆、和“有束光”聊天、签名三件事,
还不紧不慢,手上签名不停。
用成都人软软绵绵的好听声音说:
“我在画画儿呢。”
一下子,
采访前沉淀的所有“严肃、文艺、深沉”的印象,
都被软软地打破了。

这种反差的张力,她与生俱来。
比如她是“文艺片女神”和导演们的缪斯,比如她出生在成都的一个研究核物理的知识分子家庭。
“我觉得越是离得远,越是有兴趣。”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小黄璐关上门,拉上窗帘,悄悄把翻录的影碟放进笨重而巨大的LD放录机。文艺片《情人》,被她当黄片看,还奇怪这黄片怎么这么闷。看得高兴了就自己在家一个人演,手舞足蹈。

LD放录机是个迷人的黑盒子,黄璐那根理科生的神经在其中翻滚,渐渐锤炼得纤细而有韧性,足以让她伸出触角,去自己尝试成为银幕上的人。
机缘巧合下,她出演了杜琪峰《百年好合》中的一个龙套,演古天乐的一个峨嵋小师妹。这也是她第一次尝到表演带来的一点点甜头。
她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那时候的她已经在四川一所高校读大一,没有意外的话,会顺利毕业,成为玻璃幕墙的高耸写字楼中,一名普通的上班族,在一把办公椅上度过24小时×5天的人生。
父亲以为她只是去玩玩,“肯定考不上的”。
没想到一考即中。
从传统高校退学,放弃了一眼看到头的生活,黄璐半只脚迈进了电影表演的殿堂。

没想到这金光灿灿的殿堂,一开始就给她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2003年的北电表演系,高手如云,随便揪个人出来,都是一抬脚脚尖能碰到额头的练家子。半路出家的黄璐,此前十几年都是和物理公式、几何模型打交道。形体课、舞蹈课上,她格格不入。
一直到现在,黄璐都不是人群中肢体最协调的那个。少年时她身形就像个竹竿儿,早恋的小男朋友,说,你什么都好,就是太瘦了。为了这一句话,黄璐做梦都想增肥,甚至强撑着吃到狂吐。

青春期常见的苦闷,在电影学院的环境中,百倍千倍地放大了。当时的北电表演系,每天早上要出晨功,一人迟到,全班受罚。每个北京异乡的深夜,黄璐都不敢睡觉,担心因为自己连累全班。
最糟糕的时候,她几乎一个月都没睡踏实。
十几年前,抑郁症还不为人知,整天待在宿舍的黄璐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只知道自己不敢见人,也害怕出门。
不知道未来在何方,躲在舒适区不肯出来,对舒适区外的世界越来越陌生。对很多低落抑郁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死循环。

大学时的黄璐和妈妈
转机出现在2005年。
当时的宣传栏上,贴了一则小广告,说是研究生毕业作品,招一名会游泳的女演员。因为是学生作业,黄璐觉得自己游泳还不错,就报了个名试试。
去了现场才知道,并不是什么研究生作业,这是章明导演的新片《结果》,搭戏的是香港资深演员,黄光亮。

这个意外,让黄璐发现,自己很适应拍摄现场。此前在形体课上的努力,好像都没有找对方向。走出几十平米的四方教室,在实打实的拍摄中,她舒展了曾经笨拙的肢体,奇迹般地找回了自信。
“感谢当初虎头虎脑的我。”她心有余悸。
像是一个从黑暗里走出来的人,小心翼翼地向光走出第一步,从此,就停不下来了。拍摄《盲山》的李扬导演,正是看了黄璐在《结果》中的表演,决定用她。之后的一部部片子,像一块块连着的多米诺骨牌,推着黄璐游遍了世界各地。

斯里兰卡,迪拜,
英国,新加坡……
借着拍片的机会,
黄璐从一个国界线走向另一个。
笑称自己,是主业旅游,副业拍电影。

就连旅游,她也和别人不太一样。
片方给她安排住宿时,
相比于五星级酒店,
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民宿,
为了更好地体验当地人的生活。

CBD和富丽的商场,
她视而不见。
一头扎进旁边乱糟糟的跳蚤市场和菜市场,
因为——“有人味”。

在外拍戏时,
黄渤给她寄了一套环保餐具,
因为她说自己,
“不喜欢一次性餐具。”

她还想过出一本书,叫《没头脑走天下》:“天知道我这个连门都不会开,鞋带也永远系不紧,筷子永远拿不对,并且永远分不清东南西北的人是怎么可以安全回到家的。”
知乎一个“你认为有哪些内地女星格调较高”的提问中,一个回答获得了五千个网友的点赞:
“她的长相并非绝美,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她的戏路与发展。但是出道10多年,浸淫在这个有些浮华的圈子里,依然保持自己的态度和初心,着实不易。”

他说的,就是黄璐。更奇妙的是,看到了这个回答的黄璐,在柏林电影节的交流环节,一下子就认出了这位网友,双方还约了一场采访。
网友是第一次采访,本来紧张得不行,却没有想到黄璐和丈夫,坐着公交车就来到了约定的地点。
提起这段2016年的轶事,黄璐乐了,秒速叫出了网友的名字,还不太在意地解释说,自己只是想体验一下德国的交通,“真的一秒都不差。”

黄璐和丈夫范玮
毕竟黄璐,一直乐于做一个隐藏在角色背后的人。有人开玩笑,说她适合做一个间谍。今年年初落幕的《演员的诞生》,她登场三次,场场不同。
第一次,是无奈将孩子归还的农村母亲。她看过原版,但不想和原版演得一样。在她的诠释里,这个角色除了悲情还多了一些理直气壮。

观众说她演得遭人恨,她不太在乎,“我是故意的,毕竟在农村,不能生育真的就是一件大事。”
第二次,是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不甘人下的雁儿,戏份不多,但是在别人敲锣开演时,她眼梢嘴角的戏,一丝也没有落下。

第三次,本来是要演铁道工人的妻子。
黄璐和导师宋丹丹说了半天,终于饰演了一个城市女青年,轻轻巧巧,眼神里初为人母的动情就有了。
”我也想演甜甜的爱情片呀。”文艺片女神的包袱,她好像从来就没有背上。

有人演戏,不管演谁都好像在演自己;黄璐演戏,很容易就让人忘记了黄璐。
观众说,这种演技,是黄璐高级的地方。
她却好像并不在意什么是低什么是高,表演在她那里,从来不是比赛。“如果大家想去了解我,我就多说一点;如果大家只想看我的作品的话,我就做一个神隐在银幕后的人,这样也挺好,平时会有很多自由。”

这种自由与放松,是黄璐十年修炼得来的。
从普通高校的学生,到电影学院;
从大银幕、电影节,到国内更多观众的视野内。
如同升级打怪,有的人越成长,
会给自己戴上越坚硬的铠甲,越厚的面具。
黄璐却完全相反,
拥有越多,
她越不怕失去,
反而想要把身外之物,一件一件脱干净。

“和当初相比,我不再需要特别去讨好谁。以前烦恼,怎么能做到大家都喜欢我?现在觉得,喜欢的自然会喜欢,不喜欢的怎么也不会喜欢,还不如自己开心一点。”
十年前,她大四的时候,没有多少收入。第一次随《盲山》剧组去戛纳,愣头愣脑,自费找设计师设计了礼服,首饰是爸爸在西藏买的银饰,高跟鞋临时买来充场面。穿着一身行头,嘴角牵出微笑,心头却都是忐忑。

“现在想想太傻了。”
如今的黄璐,全身上下,除了内衣,没有一件是自己买的。
她也不想用名牌包包装点自己。
“我的包都是朋友做的。”她的语气有些小骄傲。
不但不喜欢买买买,她还恨不得家里什么都没有。
东西少了,重要的东西才会显露出来。

演戏也是这样。
和黄轩合演《推拿》时,关在小屋子里,从清晨拍到黄昏,开拍和关机时的界限已经模糊了。很多演员,不习惯娄烨这样的拍摄方式,希望导演给予具体的指导,野蛮生长的黄璐,倒乐得自己发挥。

像水墨写意画的“留白”,这张常常在国际电影节出现的面孔,现在习惯每一条戏的情绪收敛一些,再收敛一些。如果每一条都太满,放在一起就会过火,如同响鼓重擂,观众反而感受不到角色一闪而过的细微情绪。留一点空白,反而刚刚好。
后来娄烨对她说,“你没有工业流水线上那些演员的影子,这是你身上最宝贵的特质。”

娄烨和黄璐
很多人觉得,演员啊,一定要“人戏合一”,演一个角色后久久沉浸其中,才够艺术。够专业。黄璐却觉得,这并不一定是专业的态度。
有回,导演看到黄璐在玩手机,气得说,“一会儿那场戏很重要,你要流着泪,哭着死,好好琢磨琢磨。”但是看到黄璐的表演,也只能说,好吧,就这样吧。
只要表演对了,感觉对了,效果对了,黄璐并不苛求使用什么方式。
上一秒还像个“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和导演在道具“尸体”边说说笑笑闹闹,下一秒开拍,她已不是“黄璐”。

“我不想把自己逼成抑郁症,和大学时一样。我觉得演员,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才能有更好的条件去演绎。”
她对过去也没有苛求。好多人说,回看当年的戏,会不会觉得可以做得更好。
“我没有”,黄璐说。
“你让我再去演盲山,肯定演不了那么好了。”

电影对黄璐来说最重要的意义,不是拿了多少奖,或者赚了多少钱,而是记录保留了时光片段中的自己。她说,自己是个对保留每段时光特别贪恋的人。
“每个人每段时间都是不同的状态,美或丑,都是自己的一部分。”

接受“有束光”专访中的黄璐
这样洒脱不羁的黄璐,是不是很“佛系”呢?
“在佛系这个词出来前,我已经很佛了。”提到这个词,黄璐又乐了。
不过她很快补充,朋友间偶尔开开玩笑可以,老是给自己贴“佛系”的标签,就“太跟风了”。

从新片《血十三》的首映礼上回到休息间,黄璐脱掉了十公分高跟的黑白格纹鞋子,过分束口的鞋帮,在脚踝上勒出深深浅浅的痕迹。
“这些鞋子啊,中看不中用。”说着又换回了自己轻巧的运动鞋。
她又要轻装上阵了。

图片来自@黄璐lulu
非常感谢黄璐接受有束光专访: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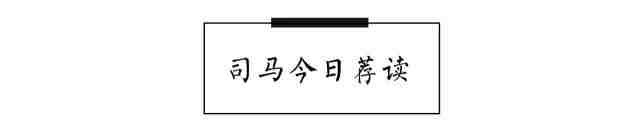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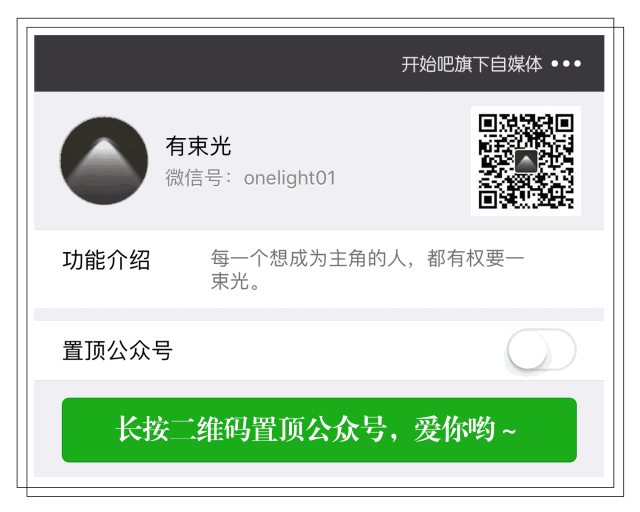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