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你们打水漂的样子,真丑陋…救了三万人的父亲和垒起纪念馆的儿子,他们不能被遗忘,三十万亡魂更不能


这是司马推送的第 735 个与众不同的人
打一个水漂,要一秒钟。
屠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平民,要十二秒。
纪念三十万陨落的亡魂,要十八年。
1937年12月13日,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发生了。炮火背后,有一个家族的两代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了这一座城池。
一为生,一为死。

五一劳动节,一则视频在微博上激起了巨大的愤怒。
阳光很好,十来个不满十岁的孩子,捡起地上的石子使劲向池中抛去,此起彼伏,欢笑尖叫,好似游乐场中的竞赛。如果这场景发生在别处,看到的人也只能笑一笑,说一声调皮。
然而,这里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画面中有成年人驻足,也有人经过,
却只是看了一看,就走过去了。
没有一个人,出面阻止。
没有一个人说:孩子,别这样,
你们扔的石头,每一块,都代表着一个,
在南京大屠杀里死去的人。

视频激起了一片哗然,
不仅仅因为嬉戏的行动破坏了馆内肃穆的气氛,
更因为,纪念馆本身,在建成之初,
就被称作是“一部石头垒成的史书”。
这里的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都仿佛是81年前那一天逝去的一个个无辜的生命。
当我们走在上面时,石子会发出“沙沙”的声音。
轻得好像遇难同胞临终前的一声叹息。

一位父亲,在南京大屠杀中,救回了三万同胞;
一个儿子,在和平年代,建造起这座纪念馆。
将近一个世纪,齐家两代人守护着这个城市,
尽管,大多数人,已经完全不记得他们。

时间从1937年12月13日,回拨回到几个月前,当时的中国第一大都会,五光十色的上海,沦陷了。
南京城前所未有地陷入危机,普通民众在熄灯睡觉前,都好像能听到炮火的轰鸣在一寸寸靠近。金陵大学的学生们坐不住了,没有粮草,没有子弹,他们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城市。
他们决定捐款建造一座旗杆。而且这座旗杆,高度一定要超过日本大使馆那根。
一位年轻的中国建筑师接下了这个任务,他叫齐兆昌。

当时的南京地区,几乎有一大半学校,都是齐兆昌一手带领修建的。有多处标志性建筑,都出自他手。
他的才能,不仅限于高校闻名,军阀冯玉祥甚至曾请他弃教从政,却被他婉言推辞了。
战时的修建不允许慢工细活,很快,新旗杆就竖了起来。当旗帜升起那天,老百姓看在眼里,心里,也好像多了一点底。

南京大学中古朴精致的小礼堂
可惜,如同螳臂当车,一根细瘦的旗杆,挡不住坦克一往无前的履带。
他决定把力量从“建筑”转移到“救人”。
齐兆昌和被称为“南京大屠杀中的保护神”的德国人拉贝,一手成立了难民营,难民营特意修成“十字架”的形状,为的是让空袭时的炮弹,避开这最后的留守地。

炮火和屠刀间,年轻建筑师和拉贝穿梭来去,救回了三万同胞,安顿在金陵大学这一块小小的地方。然而日军还是会进入难民营抓人,所有手上有老茧的,都会被无情拖走。
有回在汉口路,齐兆昌正在救难民时,来了两个日军,将枪顶在齐兆昌身上。虽然戴着红十字的袖章,但是日军并不相信。
这时正好走来一个同为救助难民的外国人林查理,生死关头,齐兆昌喊出名字,林查理骗日本兵,说齐兆昌是自己的仆人,这才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
1938年1月,齐兆昌向安全区通告,难民营还剩一万余人,多数是老人,妇女,儿童。他们也成为了后来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中,清晰可数的幸存者。

齐兆昌不知道,
在长达六周的浩劫中,
当时在他身边,每隔12秒,
就要陨落一个的三十万亡魂。
在四十七年后,
那三十万魂魄以另一种方式,
又一个个回到了这块土地——
因为当时他身边一个六岁的孩子,他的儿子,齐康。

1984年秋天,秋雨绵绵,已经接下纪念馆建筑设计的齐康,来到南京江东门的工地。
这时他和当年的齐兆昌一样,已经是个中年人了。
或许是苍天有眼,在奠基之时,地底下埋藏了半个世纪的累累白骨,终于重现天日。
“白骨刺得我眼睛发痛”,兵荒马乱的回忆重回齐康的脑海。

1937年,时年六岁的齐康,
在事变前夕,被齐兆康送回老家浙江天台。
时值春天,却没有万物复苏的感觉,
日复一日的轰炸摧毁了这个县城的春天。
小学是6点上课,8点放学,
避开轰炸的时间。

然而有一回日军提前轰炸,逃无可逃的小齐康,把自己缩到家里祖宗排位小小的佛龛下面,提心吊胆地等待头顶的摇晃结束。很多人都死于这一场轰炸,齐康因为佛龛的庇护,才捡回了一条命。
成年后的齐康,已经名满整个建筑界的泰斗,但是在他签名时,总是会在名字下面画一只孤零零的小舟。
他说,“这就是我的一生”。如同在大海中漂泊无依起起伏伏。
如同他十岁那年那一只从浙江开往南京的小船一样。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逃亡在外四年的齐康,和哥哥一起,坐一条小船,一路从天台漂流回南京。
只有十来岁的两个少年,夹杂在迎来送往的码头人流中,行李搬不动,只能沿着楼梯往下慢慢挪动。日军拿皮鞭抽着重回南京的人们,身上的衣服,被皮鞭撕裂成一条条碎布。
齐康他们拿眼睛在这幅人间地狱的景象里搜寻父亲的身影,口中不停地喊着“爸爸”。

“那个时候我还很小,日军命令我们过港时都要向日本兵低个头,我们不肯低就是弯着腰走过去。”
这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少年,能想到的仅有的反抗方式。
齐康的童年,就是在乡下、天台、南京来回折返,流离失所,直到一束光照到齐康身上,他才找到生而为人的一点点喜悦。
身为中学美术老师的姨母,常带一些画给齐康。有一回,齐康临摹了一张基督布道的画,得到了家里人的称赞,从此他更加用心,艺术的世界太奇妙了,和现实的冰冷是那么不一样。
终于在一次图画比赛中,他得到了第一名这个小小的褒奖。“这是我童年里最高兴的一天。”

齐兆昌见他爱画,也想把自己的建筑家学传下去,就找了个时间,教他用比例尺。他拿着父亲的测量工具,像找到了丈量这个世界的一把尺子,满世界蹦跶,把整个家测了个遍。
父亲抽屉里的那些建筑设计图,他渐渐可以看懂;南京老宅的一棵树,一块石头,一根木梁,一角飞檐,被他重新用一种新的目光打量。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同胞纪念馆的第一颗石子,在这一天落下,垒实。

1984年秋天。,站在纪念馆的奠基碑前,齐康头发凋零如秋草,耳朵也不大灵光,他整个人像是萧萧秋雨中摇曳的一只小舟。
从童年最高兴的那一天算起,这之后的这大半个世纪,对他来说并不平静。
凭借对建筑和艺术的热情、天分和家学,建国后,齐康考取了南京大学的建筑系。
杨廷宝、刘敦桢、童寯、张镛森、刘光华等……当时南大建筑系的师资,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建筑界的全明星队。

从左到右分别是童寯、杨廷宝、刘敦桢
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曾热情参与上山下乡的齐康,却始料未及地被打倒。批斗100多次,被抄家7次,造反派揪着他的头发,将他打到耳膜穿孔。曾经朝夕相对的朋友,见了他也把头偏过去,“齐康”两个字几乎和反动挂上了勾。
漩涡中心的齐康,在南京大学的厕所,一扫就是三年。
“运动一来,人人自危。人就像飘在漩涡中的落叶,让你搞不清怎么回事,常常是一会儿漂浮在水面,一会儿又被水卷下去,有的就这样看不见了,消失在另一世界。”
很多人就这样消失了,齐康却留了下来,不仅留下了,他还决定用自己这一艘历尽风雨的小舟,去渡三十万亡魂。
“30万可怜南京人的血肉生命,值得我呕心沥血去祭奠。”这一渡,就几乎是二十年。

方案尚未成形时,摆在齐康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复古而传统的,仅仅设计一座纪念建筑。另一条则是做整体性的环境设计。
没有多犹豫,尽管意味着困难,齐康选择了第二条少人走的路。
有了大方向,下一步就是搭好整个纪念馆的设计框架。
首先,是做减法。
传统纪念馆经常运用的对称、直线等元素,通通不要。因为齐康想要营造的,是整个有感觉的空间,而非中规中矩的“建筑作业”。
建筑物、场地、墙、树、坡道、雕塑,在建筑师手中奇妙地排兵布阵,让每个游历这里的人,都仿佛重回到历史的现场。

多余的色彩,不要。
杨廷宝和齐康说过,“一座经典的建筑,颜色绝不能超过三种。”
于是就有了我们见到的,灰白的沧桑墙体,肃黑的雕塑,土黄色的卵石。

奢侈靡费的建筑材料,不要。
所以地上铺的,都是开采黄砂的副产品——鹅卵石。为了避免像日本的枯山水,齐康选用了更为粗犷的卵石。
触目无数黄石,如同累累白骨,伏下去仿佛能听到无数亡魂在哭,和台阶上铺设的青草形成强烈对比,齐康想以此唤起“生与死”的感悟。

观念的束缚,不要。
设计灾难墙前的“十字碑”时,齐康踌躇了。因为十字架是基督教中标志性的元素,不知道运用于纪念馆是否合适?
当时旁人的一番话,让他下定决心。
“南京大屠杀是世界历史的浩劫之一,纪念馆是一扇窗,十字架造型更利于各国民众感知这段历史”。

十字碑上,
用凝重的黑色雕刻着“1937.12.13—1938.1”,
这六周,正是浩劫持续的六周。
十字碑伫立在这里,像一种沉默的守护。

去掉多余的,
剩下的每个角落,都耗尽齐康的心思。
入口处的墙上,
用中、英、日三种文字书写的“遇难者 300000”
触目惊心。

长达50米的浮雕墙,
像一个横截面,
复活了一个个被俘虏被束缚的无辜民众的形象。

担心群雕离得太远,不容易看清,
又担心单体雕塑意蕴不够丰富。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他最终选用了“体块错位”的手法,
雕刻出了苦苦挣扎不想被活埋的手。

整个面容痛苦地皱成一团的头颅,

看似简洁,却意蕴丰富的"和平大钟”:
三根柱子象征“3”,
顶端五个圆圈象征五个“0”,
悬挂大钟的梁如同一个倒下的“人字”
——这是“倒下的300000人敲响的和平大钟”。

三十万曾经鲜活,会欢笑,会哭泣的人
如今却变成了三十万封尘封的档案,
三十万个刻于墙上冰冷的名字,
甚至,有的是一家人的名字,
战火中失散,如今紧紧挨在一起。


在最艰难的时候,齐兆昌在金陵大学义务教课,分文不取。
从1984年到2002年,在设计纪念馆的二十年中,齐康同样没有收取一分钱,任何有需要他出现的场合,他随叫随到。
甚至齐康的学生,都知道一条默认的规定,谁收了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分钱,就不再是他的学生。
“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劫难的历史永远不会也不应磨灭。”齐康说。
纪念馆落成的那一天,如同沉重的记忆被拂去灰尘。但是对所有有意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清晨,阿姨开始一天的清扫,
甚至细致到了鹅卵石缝之间。

来自法国巴黎大学的志愿者山穆,
在南京的三伏天来到馆中,
却穿了一身西装。
因为在他心中,纪念馆是庄重严肃的地方,
要正式以待。

杨振宁参观纪念馆后,
临走时他突然请求带一套纪念馆的幻灯片回美国,
因为很多年轻人以为世界已经和平,
却不知道历史上曾经发生了怎样的浩劫。

很多来自以色列的参观者,
会在馆内徘徊,停驻,
此情此景,
让他们回想起以色列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眼泪忍不住缓缓落下。

中秋节,
如今零落寥寥的幸存者会重聚在这里,
因为 “纪念馆是幸存者们的第二个家”。

为了照顾盲人参观者,
馆内还会组织志愿者专门服务,
因为”纪念馆是石材累就的建筑群,
但我们的服务是有温度的。”

从小在南京长大的美籍华人鲁照宁,
十年如一日地在网上搜寻拍卖的文物,
自费买下捐赠给纪念馆。

2015年12月,又一个十年过去。
纪念馆的新一期,在接棒人何镜堂手中完成了。
作为齐康主持的一、二期警醒主题的补充,
这一次的主题,是和平。
鸟瞰纪念馆的整体形状,像一只和平之舟。

洁白象征着期许的雕塑下,
写着两个字
“和平”

同时落成的,
还有位于利济巷的慰安所旧址陈列馆。
墙上十三颗硕大的透明泪滴,
仿佛慰安妇心中无尽的痛苦。

陈列馆背部的照片,
有几位老人尚在否?

反对战争,祈愿和平,是全世界的事。纪念馆建立的目的,也从来不是煽动仇恨。
在日本熊本发生地震,很多网友冷眼旁观的时候,纪念馆的微博,却发出问候。
过去的二十年,熊本县的日中友好协会,每年都会坚持来纪念馆吊唁。

“打水漂”事件发生后,有人评价,战争中流淌的这么多血,不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孩子可以快乐地成长吗?
当然,你侬我侬的情侣、精神矍铄的老人、意气风发的青年、天真可喜的孩子,可以从和平大钟旁从容走过,不必像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无数受苦的人一样,命运不由人自主,颠沛流离,家破人亡。
这是所有人的期望。

但是,齐兆昌倾书生之力,博命一般,从鬼门关夺回近万条人命;齐康摇一叶小舟,渡三十万亡魂,以石头写史书。不是为了忘却。
历史学者余世存曾说:中国人缺少形式上宗教,但中国人不是没有超越的时刻,不是没有道德的坚守。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
我们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但我们相信有公正的历史。历史,是中国人的信仰。
我们可以宽恕罪行,但是不能遗忘历史。


本文图片和视频均源自网络,
版权属于版权方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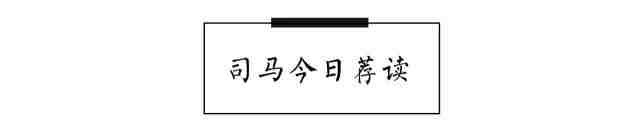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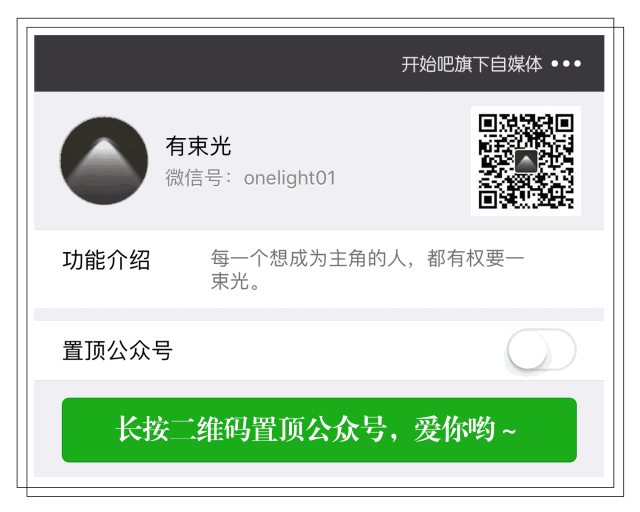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