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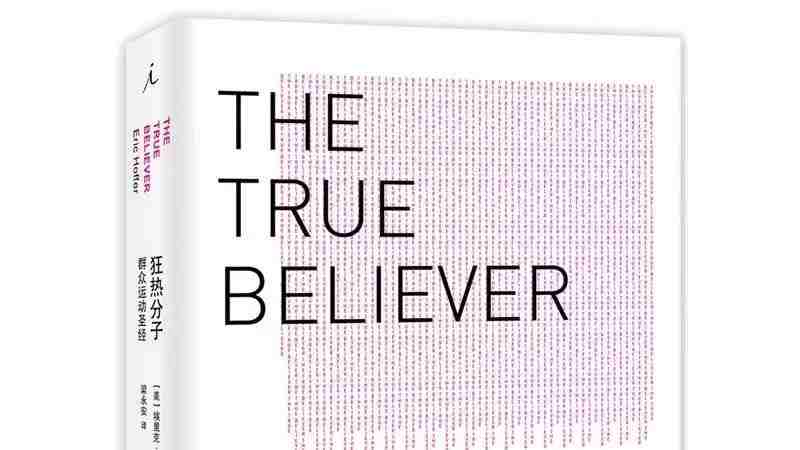

自我若是软弱无力,再多的自由又有何用?
奴隶都是贫穷的,但在奴隶制度普遍存在且行之有年的地方,发生群众运动的机会并不大。奴隶之间的绝对平等,以及奴隶区域之内紧密的团体生活,都让失意感不容易发生。在一个有奴隶制度的社会里,会闹事的不是新遭奴役的人就是刚获解放的奴隶。就后者而言,他们的不满来自自由带给他们的苦恼。
自由对失意感的加深作用不亚于舒缓作用。选择的自由让个人得把失败的责任也一起扛。自由鼓励多种多样的尝试,也无可避免会带来多种多样的失败于失意感。
一个人除非善于用脑子,否则自由就会成为他一种讨厌的负担。自我若是软弱无力,再多的自由又有何用?我们参加群众运动,是为了逃避个人责任或为了得到——用一个热情洋溢的年轻纳粹党员的话说——“免于自由的自由”。普通的纳粹党员会力辩他们并未犯下任何罪行,这并不是虚伪。他们认为自己受了骗,上了当,而且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又何来责任可言。他们会参加纳粹运动,不就是为了得到免于负责任的自由吗?
狂热者对自由的恐惧尤甚于迫害
群众运动虽然往往打着自由的旗号对抗高压秩序,但它们全速启动以后,却不会让个人自由有实现的余地。这是因为,当一个群众运动在与既有秩序作生死斗争,或是抵抗内外敌人以求自存时,它的首要之务是建立团结性和自我牺牲精神,而这两样东西都需要个人放弃其意志、判断与利益。罗伯斯庇尔说过,革命政府是“反抗暴政的专制政体”。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一个群众运动在其积极阶段会打压个人自由,但此举并未拂逆其追随者的意愿。法国历史学家勒南说过,狂热者对自由的恐惧尤甚于迫害。一个群众运动兴起时,其追随者尽管活在一种得严格遵守信条和命令的紧迫气氛中,仍然会有一种强烈的自由感。这种自由感来自他们逃离了他们厌憎、害怕的那个“自我”。这种逃离让他们感觉得到释放与救赎。另外,造就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变迁也带给他们自由之感,尽管这变迁是他们在严格纪律下执行的。只有当运动过了它的积极阶段,凝固为一些稳定的制度模式以后,个人自由才有抬头的机会。一个群众运动的积极阶段越短,人们越会觉得造就个人自由是运动本身而.不是运动的终结。另外,积极阶段越短,被群众运动推翻和取代的那个极权体制在人们的印象中就越暴虐。
最大声呼吁自由的人,往往是最不乐于住在自由社会的人
那些觉得自己生命败坏了和荒废掉的人,会渴望平等与博爱多于渴望自由。如果他们为追求自由奔走呼号,他们想要的只是一种建立平等与博爱的自由。对平等的激情是一种对匿名的激情 :想要成为构成一件外衣的众多丝线之 一,一根无别于其他丝线的丝线。这样,就没有人会把他指出来,与别人比较,让其低劣无所遁形。
那些最大声呼吁自由的人,往往是最不乐于住在目由社会里的人。 “失意者”因为受到自己的短处压迫,会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一于现有的种种限制。实际上,他们最深的渴望是终结“人人皆有自由”的现象。他们想要取消自由竞争,取消自由社会里人人都要经历的无情考验。
少数人的热望
在自由实际存在的地方,平等是大众的热望。
在平等实际存在的地方,自由是极少数人的热望。
有平等而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而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模式。
评论
现在的大家口中的白左,经常被称为liberal,其实早就脱离了自由的定义。简单地说,这些所谓的liberal,是70年代平权运动之后的Social liberal。Social liberal更强调结果平等,所以他们无条件支持LGBT、BLM或穆斯林,支持政府再分配,支持教育平权。
白左,现在自称为“自由主义者”,因为和“自由”这个词相关联而沾沾自喜。这个并不稀奇,早在一百多年前,他们自称为“左派”,因为和“右派”这个词关联而沾沾自喜。
人们期望最平等的社会,最后出来的却是奴隶社会。欧美的白左们,正在亲手打造一个现代化奴隶社会。
相关阅读
阅读原文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