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及其主体性:胡塞尔在《第一哲学》中对于笛卡尔的解释

“雅典学园”微信学习群已经度过了2年多的时光,哲友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胡塞尔哲学的学习。微信公号“哲学门”同步“雅典学园”群的学习内容,精选紧扣学习内容的文章发布。
点击以下图片关注“哲学门”
系统性学习哲学防失联
“我思”及其主体性
胡塞尔在《第一哲学》中对于笛卡尔的解释
吴增定
作者简介:吴增定,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
原文出处:哲学动态 2017 年 05 期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的是胡塞尔在《第一哲学》中对于笛卡尔哲学的解释和批评。胡塞尔高度肯定了笛卡尔哲学在哲学史中的转折性意义,认为正是笛卡尔使得哲学告别朴素的客观主义,转向一种先验的现代主体性哲学。同时胡塞尔也指出,笛卡尔虽然发现了“我思”或自我意识的绝对领域,却忽视了“我思”自身的意向性构造成就,将之视作一种同“物体”相对的精神实体,从而陷入了“自然主义”的谬误。通过对笛卡尔哲学的批评,胡塞尔不仅修正了他早年的“笛卡尔主义”倾向,而且开启了他后期对于生活世界的现象学思考。
关 键 词:我思 主体性 笛卡尔主义 意向性
作为1923至1924年间的一部讲稿,《第一哲学》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和哲学研究生涯中占有相当特殊和重要的地位。从时间上说,这部讲稿是连接胡塞尔的中期著作《观念I》、后期著作《笛卡尔式沉思:现象学的一个导论》和《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等之间的思想桥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认识空白,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他从静态的“构造现象学”到动态的“发生现象学”其间思想的深化和转变之轨迹。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第一次系统、完整地表达了胡塞尔对于哲学史的看法,纠正了此前对于他的某些误解,比如,认为他不关心哲学史问题,其现象学是一种非历史性的严格科学,等等。在《第一哲学》中,胡塞尔以一种类似黑格尔的方式,第一次清晰揭示了他的先验现象学与自柏拉图以来的整个哲学史的内在关联。在他看来,先验现象学代表了西方哲学最内在的思想动力和目标,是包括柏拉图、笛卡尔和康德等在内的哲学家们所一直追求但始终没能实现的目标:绝对的主体性。胡塞尔所谓“绝对的主体性”是指:自我或纯粹意识是一个绝对明见、自我负责、自我构造、自我理解的理性和先验主体,而一切客观性(文化、意义和价值等)都是“纯粹意识”的意向性构造之成就。正是出于这一理念,胡塞尔认为这个绝对的先验主体性就是一切意义和真理的本原:它不仅构成了西方哲学乃至西方文明的根本精神和内在目标,而且代表了人性本身的最高理想和目标——人通过哲学的理性生活成为一个自由、自我理解和自我负责的绝对主体。
对于哲学史,胡塞尔依然将哲学的真正开端定位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并将其哲学精神理解为克服智者学派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追求一种绝对的知识和真理。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胡塞尔认为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哲学仍然停留于一种素朴的客观主义态度(也就是胡塞尔在《观念I》中所说的“自然态度”),即他们将知识和真理本身看成一种自在和客观的实体,而没有看到它们都是意识的意向相关物和构造物,或者说都是主体性的成就。①在胡塞尔的心目中,恰恰是笛卡尔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将“我思”或“意识”作为一个绝对确定性的王国,不仅把它当成一个“阿基米德之点”,而且试图在其基础上建立一种“普遍科学”。正因为如此,笛卡尔在胡塞尔版本的哲学史中占据了十分核心的位置。正如黑格尔认为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意味着绝对精神开始返回自己的故乡,胡塞尔也把笛卡尔的“我思”看成现代主体性哲学和先验哲学的真正开端。
胡塞尔对于笛卡尔的这种理解和评价在他的很多著作中都有明确的表达。在《观念I》中,胡塞尔将他的“先验悬置”或“先验还原”方法同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方法相提并论。正如笛卡尔为了追求“确定、无疑”和“清楚、明白”的真理而将一切科学知识都视为“普遍怀疑”的对象,胡塞尔也将关于“超越物”甚至关于世界的“存在设定”或存在信念搁置起来,留下作为剩余物的绝对“内在性”领域,也就是“纯粹意识”。在《第一哲学》和《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胡塞尔都将这种“先验还原”的方法称作“笛卡尔的路径”,并且认为它所通向的正是一个绝对主体性的领域。他还说道:“事实上,笛卡尔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哲学:由于改变了哲学的整个风格,所以它呈现出一个彻底的转变——从素朴的客体主义到先验的主体主义。”②他不仅自始至终将笛卡尔看成是现代主体性哲学的真正开端,而且把自己的先验现象学也称为一种“新笛卡尔主义”。③然而,正是由于胡塞尔过分强调他与笛卡尔的亲缘性,其先验现象学才被很多同时代及后来的哲学家和学者视为一种典型的“笛卡尔主义”,并且因此受到各种批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批评来自海德格尔。早在《时间概念史导论》中海德格尔就指出:“胡塞尔最初所追问的完全不是关于意识的存在特性的问题,引导着他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思考:在根本上,意识如何能够成为一门绝对科学的可能的对象?引领着他的那个首要的东西是有关一门绝对科学的观念。意识应该是一门绝对科学的领域这个观念并不是简单发明出来的,毋宁说它正是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所一直拥有的观念。”④在《存在与时间》以及之后的著作中,海德格尔出于类似的理由将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视作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继承者。
海德格尔的这一看法不仅被伽达默尔、德里达、列维纳斯和马里翁(J.Marion)等所继承,而且也为珀格勒(O.Poeggler)和德雷福斯(H.L.Dreyfus)等学者所接受。对于这种“标准化”解读,不少学者都作出了批评和反驳。早在20世纪40年代,福尔同(J.S.Fulton)就明确地将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同笛卡尔的哲学以及所谓的“笛卡尔主义”划清界限。20世纪60年代,胡塞尔晚年的学生和助手兰德格雷贝(L.Landgrebe)在一篇题为《胡塞尔告别笛卡尔主义》的文章中明确否认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是一种笛卡尔主义。后来,大卫·卡尔(D.Carr)和威尔顿(D.Welton)都指出了胡塞尔与笛卡尔在哲学上的根本分歧。近年来,扎哈维(D.Zahavi)等学者更是特别强调,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与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所批评的笛卡尔式的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完全无关。
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及其哲学意义,我们有必要思考三个相关的问题:
首先,胡塞尔对笛卡尔的理解是否符合笛卡尔的原意?
其次,这种理解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先验现象学之理念?
最后,他的先验现象学同笛卡尔哲学的根本分歧究竟何在?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重新审视胡塞尔在《第一哲学》中对于笛卡尔哲学的具体解释。
正如《第一哲学》书名所显示的,该书一方面关系到胡塞尔对第一哲学的理解,另一方面又立足于其先验现象学视野。简单地说,胡塞尔对包括笛卡尔在内的整个哲学史的解释都基于一个前提:先验现象学不仅是真正的“第一哲学(first philosophy)”,而且是自柏拉图以来的整个哲学史的内在动力和最终目标。那么,他是在何种意义上将先验现象学看作真正的“第一哲学”呢?
按照艾伦(J.Allen)的总结,胡塞尔的“第一哲学”大致包含了三重规定。
首先,其“第一性”或“首要性”在于其地位和价值最优先,其他的哲学学科都是“第二哲学”。
其次,它包含了某种“目的论式的”科学理想,即它作为最高的知识和真理构成了其他科学的指导目标,并且使得其他科学的内在联系和统一成为可能。
最后,它是一种关于“真正开端(the beginning)”的科学或知识。⑤用胡塞尔本人的话说,“依此,这个入口,这个第一哲学的开端本身,也就是所有一般哲学的开端。因此,就从事哲学研究的主体,我们必须说,哲学的开始者,从真正意义上说,是那样一种人,他从哲学的开端起,真正地,因此是以绝对经受住检验的真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最彻底的洞察,形成第一哲学”⑥。
其中第三个规定即现象学是一种关于真正开端的科学或哲学,显然是最重要的。在胡塞尔看来,“第一哲学”所追求的开端必须达到彻底的“无前提性”,也就是说,这种开端必须是完全和彻底的“自身给予”或“自身显现”,而不是预设某种前提或原理。从这一标准看,传统哲学中被视为“第一哲学”同义词的形而上学显然没有达到真正的开端,因为它总是潜在地预设了某种终极实在、本体、“实体(ousia/substance)”或“第一原理”,如理念、上帝和精神等。在形而上学之中,这种终极实在、本体、实体或第一原理本身被当成是某种不言自明的前提和基础,整个体系由此得以被演绎和构造出来。因此,胡塞尔明确地否定形而上学是“第一哲学”。
在《观念I》中,胡塞尔将形而上学的这种“有前提性”理解为一种“自然态度”。所谓“自然态度”就是一种“直向”和“非反思”的思考方式,它总是不加反思地预设了某种“实体”或“存在物”的存在,并且将其视为思考和认识的前提和出发点。在终极的意义上,“自然态度”就是关于世界存在的一般设定或总体信仰,它不仅不言自明地假定了世界作为存在物整体的存在,而且把意识本身也看作世界的一部分。与这种“自然态度”相反的则是一种“反思的态度”或“先验的态度”,它并未预设某种对象或存在物的存在,而是首先回到进行认识和思考的“我思”或意识本身。
因为对于我思或意识来说,只有意识本身才是绝对地“自身给予”、“自身显现”或“明见地显现”,所以在胡塞尔看来,意识本身应该成为哲学的真正开端。
不仅如此,一切非意识的存在物都变成了意识的意向相关物。
因此,意识本身就成为具有意向性构造作用的先验主体,而世界则成为主体的意向性构造或意向性相关物。
如果说先验自我或主体性作为“自身给予”或“自身显现”成为哲学的真正开端,那么毫无疑问,以主体性为开端和目标的先验现象学才是胡塞尔心目中真正的“第一哲学”。
从作为“第一哲学”的先验现象学观念出发,胡塞尔对自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史进行了某种“价值重估”。对于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开端和代表的希腊哲学,胡塞尔同样给予高度的评价。在他看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首先是为了应对当时智者学派的挑战,克服后者所坚持的怀疑主义精神,以获得永恒和绝对的知识或真理。他们将科学或哲学所代表的理论沉思或理性生活同未加检验的意见区别开来,并且将前者看作人的最高价值和生活方式。他评价道:“由于柏拉图,这些纯粹的理念:真正的认识,真正的理论和科学,以及——包含着它们全部的——真正的哲学,才进入到人类的意识。”⑦在这一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发展出了逻辑学、各种具体科学和“第一哲学”的观念,大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希腊哲学的思想内容。
但同时,胡塞尔认为,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仍然停留在一种素朴和非反思的哲学思考态度之中,因其预设了某种客观自在的本原即理念或实体等,但并没有反思性地澄清这种所谓客观自在的本原与意识之间的关系。
尽管古希腊哲学家们也考察宽泛意义上的意识,也就是灵魂的各种活动,但在他们那里,意识或灵魂的活动也被看成某种客观自在的存在物,而不是具有意向性构造作用的纯粹意识或先验自我。⑧换言之,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没有反思性地澄清和“悬置”这种素朴的自然态度,都不言自明地设定了世界的“预先被给予性”。
正是在笛卡尔那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素朴的自然态度和客观主义立场第一次遭到了普遍的怀疑。
胡塞尔指出,在笛卡尔那里,一切传统的先入之见都被重新检验,一切看似客观自在的对象和客观有效的知识都受到怀疑。这种怀疑如此彻底以至于不仅客观自在的物理世界,而且包括柏拉图的客观理念世界、逻辑和数学的客观真理、一切自在有效的客观知识甚至上帝都无一幸免。
然而,恰恰通过这种“普遍怀疑”,怀疑本身作为一种“我思(cogito)”获得了无可怀疑的确定性。胡塞尔高度肯定了“我思”对于笛卡尔的哲学意义,他不仅把“我思”看成是笛卡尔哲学的“阿基米德之点”,而且视之为一切哲学的绝对开端:
真正的哲学应该在这种纯粹认识的绝对根据之上,通过一种在这种自身认识的范围内以绝对证明自身正当的方法实行的思想进程,作为内在的产物产生出来;正是作为绝对的开端并且在每一步上都绝对证明自身正当的行为产生出来。因此这个我思(ego cogito)是纯粹在自身之上建立的哲学的,普遍科学的第一的而且是唯一的基础。⑨
按照胡塞尔的分析,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而获得的“我思”不仅意味着哲学的真正开端,而且代表了哲学的全新转向。“我思”或“主体性”是一个独立、自足、封闭和绝对的领域,在其基础上可以建立一个真正的科学和知识大厦,实现普遍科学的理想。
但是,胡塞尔认为笛卡尔本人并没有认识到“我思”或主体性领域这一发现的伟大意义。就像哥伦布虽然“发现了新大陆,但对此毫无所知,而仅仅以为发现了一条通向古老印度的新海路”⑩。
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在论证了“我思”的确定性之后并未进一步探究“我思”的意向性构造之本质,而是借助“因果性”和“无限”等“内在观念”推出上帝的存在;通过上帝的“诚实性”,笛卡尔又推导出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有效性,并最终论证了外在世界的客观存在。
结果,笛卡尔的主体性哲学最终变成了一种同时肯定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的二元论哲学,“于是就建立起两个实体的学说,根据这种学说,具有最终哲学真理真正的客观世界上由物质实体和与它具有因果性联系的精神本质构成的,每一个精神本质都如同我的自我(ego)一样,是自在自为地绝对地存在着的。”(11)
当笛卡尔将“我思”变成一种与物质相对的精神实体时,他显然完全否定了“我思”作为主体性的革命性意义,重新退回到某种素朴、非反思和直向的“自然态度”。
这样一来,笛卡尔哲学就变成了一种与中世纪经院哲学类似的典型形而上学,在其中上帝是真正的实体,而精神和物质则变成两个互不相干的相对实体。
于是,笛卡尔哲学的核心问题不再是“我思”如何意向性地指向或构造“我思之物”,而变成了“我思”作为一种精神实体如何认识一个完全不同的外在物质实体。
后世哲学家和学者对笛卡尔主义的各种质疑和责难,如吉尔伯特·赖尔所批评的“机器中的幽灵”等,皆由此而来。因而最终,笛卡尔只能算是现代主体性哲学的“摩西”,并没有真正地进入主体性的“希望之乡”。

胡塞尔进一步指出,笛卡尔将“我思”理解为一种精神实体的做法,恰恰为洛克等后来哲学家的自然主义敞开了大门。在洛克等人那里,“我思”变成了一种心理观念或心理事件,同外在的物理事件和对象一样,都服从机械因果法则。自19世纪晚期至今所滥觞的各种自然主义思潮,如心理主义、实证主义、物理主义和生物主义等,从源头上都可以追溯到笛卡尔对于“我思”的客观主义理解。

从《观念I》和《笛卡尔式沉思:现象学的一个导论》来看,胡塞尔在《第一哲学》中批评笛卡尔的理由似乎更容易理解。
首先同时也最重要的是,胡塞尔认为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仍然不够彻底,并没有达到现象学意义的“先验悬置”或“先验还原”:前者是一种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意义的怀疑,它仅仅怀疑或否定相关事物的存在;怀疑和否定本身仍然是一种“存在设定”,尽管这是一种否定性的“存在设定”;然而作为一种“存在设定”,怀疑和否定依然是一种“自然态度”。看起来悖谬的是,笛卡尔恰恰是以怀疑和否定的方式设定了被怀疑物和被否定物的存在。换言之,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摆脱“自然态度”,没有摆脱关于世界的一般存在设定。对他来说,“我思”在进行怀疑之前就已经被看成是某个现成存在物,并且与其他的现成存在物一起处在作为整体的世界之中。
其次,
胡塞尔批评笛卡尔对于数学知识与方法的不合理使用。诚然,笛卡尔在进行“普遍怀疑”时排除了数学知识和方法,但当他在通过“普遍怀疑”方法获得了“我思”的确定性之后,他就不再怀疑数学知识的绝对有效性,不仅将它看成一切知识和真理的典范,而且通过数学式的演绎和推理建构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由此,胡塞尔总结说:“笛卡尔并没有成为建立与先验基础之上的、建立于我思之上的,因此是真正先验哲学的创始人,以至于
他仍然完全囿于客观主义的先入之见中。”(12)这里所说的“客观主义”,正是他在《观念I》中所说的“自然态度”。
在他看来,笛卡尔的“客观主义”谬误在于:
“我思”明明意味着彻底和纯粹的主体性(或主观性),却被当成某种客观自在的精神实体,并且和物质实体一道共同从属于最高和真正的实体上帝。
最后,胡塞尔认为笛卡尔忽视“我思”的“主体性”的真正原因在于,他没有认识到“我思”本身的意向性指向或构造作用。
事实上,“我思”或意识本身就具有某种意向的超越性,它能够超出自己的内在性意向地指向、把握或“构造”某个“客观”物。或者反过来说,包括上帝和外物在内的一切所谓客观自在的实体或对象等,都是意向地相对于“我思”而存在,都是“我思”的意向相关物。无论是最低层次的“我思”(如知觉和想象等),还是较高层次的“我思”(如判断和科学认识活动);无论是认知性的“我思”(“客体化行为”),还是情感意愿性的“我思”(“非客体化行为”),都意向性地指向或构造某种对象相关物,譬如物理自然世界、动物灵魂世界,乃至客观的文化、精神和价值世界。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世界就是“我思”或先验自我的意向性构造物或相关物。在胡塞尔看来,这才是“我思”的真正主体性,而这种主体性显然只有通过反思性的“先验悬置”或“先验还原”才能获得。
从胡塞尔对笛卡尔的解释和批评中可以看出,他对于笛卡尔哲学的态度基本可以概括为“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也就是说,他虽然在宏观层面肯定笛卡尔对于主体性的哲学发现,但在微观层面却拒绝了笛卡尔哲学的几乎所有具体观点,如笛卡尔的“简单性质(simple nature)”、“内在观念(innate ideas)”、实体学说,上帝存在的证明、心灵和物质二元论等,更不要说笛卡尔的激情学说。

对于胡塞尔来说,笛卡尔哲学的影响似乎仅限于一种哲学精神的感召,却几乎没有涉及任何具体的哲学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把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看成一种“笛卡尔主义”,还是将其视为一种笛卡尔式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似乎都是对于胡塞尔和笛卡尔的共同误解。就像奥斯本(A.D.Osborn)所说的,“在胡塞尔所乐于自称的新笛卡尔主义之中,根本没有什么笛卡尔的东西”(13)。 (老蝉注,这话也不完全对)
(老蝉注,这话也不完全对)

让我们暂时跳出胡塞尔的视野,将笛卡尔的哲学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作一个简要的对比。
站在笛卡尔的立场看,胡塞尔对于笛卡尔哲学的解释和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解的错位甚至误解。
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的“前言”中,笛卡尔早就清楚地指出其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证明上帝和灵魂的存在:
“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是应该用哲学的理由而不应该用神学的理由去论证的主要问题。”(14)或者更准确地说,其哲学意图在于,一方面澄清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并为之辩护,另一方面调和现代自然科学所隐含的反目的论或机械论的自然观与传统基督教的神学教义和道德学说。尽管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获得了“我思”的确定性,但他并没有将“我思”视为唯一的实体,更不是最高的实体。换言之,对于他而言“我思”仅仅是其哲学的开端而不是最终的目标,更不是哲学的全部。如列维纳斯和马里翁所见,笛卡尔恰恰认为,“我思”本身就是有限、有缺陷和不完美的,否则就不会犯错和受骗,所以他将“我思”视作一个有限者,并向作为无限者的上帝敞开。
但是在胡塞尔的哲学中,“我思”的地位则完全不同。对他来说,“我思”不仅意味着哲学的开端,而且构成了哲学的全部。他甚至将先验现象学和所谓的“先验自我学”等同起来,视之为真正的“第一哲学”。在其先验现象学视野之中,“我思”非但不是一个有限的实体,甚至根本不是实体,因为包括上帝、精神和物质在内的一切实体,都是“我思”的意向相关物,或者说都是“我思”的意向性构造成就。在这个意义上,“我思”是一个真正自足、自由、自律、自我构造、自我理解和自我负责的理性主体,既不需要论证上帝的存在,也不需要通过上帝去论证外物的存在。
这就是胡塞尔所说的“主体性”。在他的心目中,主体性不仅是包括笛卡尔在内的现代哲学的隐秘渴望,而且是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之内在动力和终极目标。
与胡塞尔相比,笛卡尔对于“我思”地位的肯定远远没有达到主体性的程度。对笛卡尔来说,“我思”仅仅是一种有限的精神实体,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独立、自在和无限的实体,也就是上帝。在笛卡尔的“我思”与上帝之间存在着一个绝对的鸿沟与界限。尽管笛卡尔被包括康德、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内的绝大多数哲学家看成现代哲学革命的发起者和奠基人,并且开启了现代主体性哲学之门,但是他在某些根本点上仍然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传统的继承者。对于笛卡尔来说,第一哲学仍然是探寻“什么是实体”或“何物存在”的形而上学,而不是胡塞尔式的先验现象学。就像胡塞尔所批评的那样,即使是在“普遍怀疑”中,笛卡尔仍然处在某种不言自明的“自然态度”之中,保持了一种素朴的“存在信念”。在胡塞尔等批评者看来,笛卡尔的这种态度显然过于保守,并不彻底,保留了太多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残余。但就笛卡尔本人来说,这毋宁是一种节制和谨慎。他既不希望也不相信他的哲学会与传统的宗教和道德教义发生冲突,所以他不可能将“我思”从一种有限的实体变成终极的主体性。
无论如何,笛卡尔毕竟把“我思”看成“第一哲学”的开端,并且由此推演出上帝和外在世界的存在。

 自笛卡尔之后,无论是以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为代表的所谓大陆理性主义哲学,还是以霍布斯、洛克和休谟等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都是以不同的方式推进笛卡尔的主体性哲学革命:前者试图打破“我思”、物体和上帝之间的绝对鸿沟,将它们看作同一个实体(斯宾诺莎)或无限多个实体(莱布尼兹);后者则深入到“我思”或心理世界内部,并且将包括心灵、外物和上帝在内的一切实体都视为心理观念的联想。而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无论是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还是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也都可以被视作对笛卡尔主体性哲学的继承和继续推进。
自笛卡尔之后,无论是以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为代表的所谓大陆理性主义哲学,还是以霍布斯、洛克和休谟等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都是以不同的方式推进笛卡尔的主体性哲学革命:前者试图打破“我思”、物体和上帝之间的绝对鸿沟,将它们看作同一个实体(斯宾诺莎)或无限多个实体(莱布尼兹);后者则深入到“我思”或心理世界内部,并且将包括心灵、外物和上帝在内的一切实体都视为心理观念的联想。而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无论是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还是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也都可以被视作对笛卡尔主体性哲学的继承和继续推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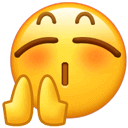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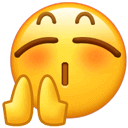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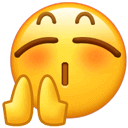

相比之下,胡塞尔显然将笛卡尔的主体性哲学革命推进得最为彻底。在他的“第一哲学”也就是先验现象学之中,“我思”就是一切,一切非“我思”之物都是“我思”的意向相关物或意向构造物。因此胡塞尔的第一哲学既不需要笛卡尔的上帝,也不需要康德的“物自身”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或许在主体性哲学的意义上,胡塞尔可被视为一个比笛卡尔更彻底的“笛卡尔主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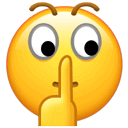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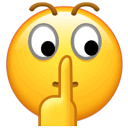
在《第一哲学》中,胡塞尔将他在《现象学的观念》和《观念I》中所发展出来的“先验还原”方法称为“笛卡尔的途径”。胡塞尔用一种类似笛卡尔“普遍怀疑”的方法将所有的“先入之见”,尤其是关于世界之客观存在的自然态度或信念搁置起来,“放在括号中”存而不论。这种笛卡尔式的“先验还原”所得到的“剩余物”就是“纯粹意识”。胡塞尔将其理解为笛卡尔的“我思”:“我思被笛卡尔如此广泛地理解,以至于它包含着‘我知觉、我记忆、我想象、我判断、我感觉、我渴望、我意愿’中的每一项,以及包括在无数流动的特殊形态中的一切类似的自我体验。”(15)此外,胡塞尔认为,“我思”作为“纯粹意识”的“纯粹性”就在于,它不再像在“自然态度”中那样被看成“实在世界的事物,正如动物生命中的体验一样”(16)。在《第一哲学》中,胡塞尔以类似的方式简要总结了笛卡尔式“先验还原”的两个要点:
一是从意识中排除任何关于世界存在的信念设定,
二是消除意识的“世间性”,即否定意识是世界中的自然物或现成存在物。
不过,这种“笛卡尔的途径”的“先验还原”隐含了两个可能的麻烦和误解。
第一,胡塞尔将通过“先验悬置”得到的“剩余物”也就是“纯粹意识”看作一个“内在性(Immenanz)”的领域,而把包括世界在内的所有“实在物(res)”都看作一个“超越性(Transcdenz)”的领域。两者的区别在于,作为“内在性”的“纯粹意识”是绝对的存在,而作为“超越性”的物,则是相对和偶然的存在。用胡塞尔本人的话说:“因此,内在的存在无疑在如下的意义上是绝对的存在,即它在本质上不需要任何‘物’的存在。另一方面,超验‘物’的世界完全是依赖于意识的,即并非依存于什么在逻辑上可设想的意识,而是依存于实显的意识的。”(17)
胡塞尔关于“纯粹意识”与“物”或“内在性”与“超越性”的区分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笛卡尔关于心灵(mind)和物体(body)的二元论。而且更严重的是,这种区分甚至导向一种贝克莱式的“主观观念论”——“存在就是被意识(Sein ist Bewusstsein)”。 尽管胡塞尔努力将他的先验现象学与贝克莱的“主观观念论”区别开来,但是,将“纯粹意识”看作一种“绝对的存在”难道不是一种典型的“自然态度”或存在设定吗?(18)换言之,他的先验现象学难道不是一种以“我思”或“纯粹意识”为终极存在或本原(ousia)的形而上学吗?事实上,海德格尔等批评者恰恰是根据这一理由将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理解为一种典型的笛卡尔主义,也就是“主体性形而上学”。
尽管胡塞尔努力将他的先验现象学与贝克莱的“主观观念论”区别开来,但是,将“纯粹意识”看作一种“绝对的存在”难道不是一种典型的“自然态度”或存在设定吗?(18)换言之,他的先验现象学难道不是一种以“我思”或“纯粹意识”为终极存在或本原(ousia)的形而上学吗?事实上,海德格尔等批评者恰恰是根据这一理由将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理解为一种典型的笛卡尔主义,也就是“主体性形而上学”。

第二,当胡塞尔将世界本身看作“现象”,或者说看作先验自我或纯粹意识的意向相关物(也就是意义)时,“先验自我”或“纯粹意识”似乎就变成了与世界相对的一个抽象“极点”,即所谓的“自我极”。在海德格尔等批评者看来,这又是一种“笛卡尔主义”的典型特征。因为这样一来,所谓的“先验自我”就变成了一个“无世界(weltlos)”的抽象主体,就好像笛卡尔形而上学中与“物体”相对的“心灵”实体。尽管胡塞尔的本意并非如此,但这至少表明,他的笛卡尔式“先验还原”不仅非常容易引起一种“笛卡尔主义”的误解,而且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世界是否仅仅是“先验自我”的意向相关物或构造物?
胡塞尔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在《观念I》中,胡塞尔就已经提出了另一种关于世界的看法。
世界不仅仅是先验自我的意向性相关物,而且是先验自我的终极视域。
在《第一哲学》(下卷)中,胡塞尔大大地发展了《观念I》时期提出的“视域(horizont)”概念。对他而言,“视域”概念具有两方面的决定性意义:
一方面,
“视域”概念极大地克服了“我思”或“先验自我”的抽象性,使之具有了
时间性和历史性,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和具体,
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极点”;
另一方面,“视域”概念也大大地拓展了“世界”的思想内涵,使得世界不再仅仅是先验自我的意向相关物或意向构造物,而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我思”或先验自我的意向性构造的根本。(19)
在后一种意义上,胡塞尔在《观念I》中所提出的笛卡尔式的“先验还原”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在《第一哲学》(下卷)中,胡塞尔就把这种“笛卡尔的途径”视为“通向先验还原的第一条道路”。考虑到这种“笛卡尔的途径”有导向一个抽象和“无世界”的先验主体的危险,胡塞尔提出了第二个先验还原的途径,也就是视域分析的途径。
视域分析的途径并不是对“笛卡尔的途径”的简单补充,而是对它的大大深化和拓展,甚至是某种程度的修正,即“证实了前面提出的论点:
先验主体性的揭示是同意识的视域的揭示是并行的”(20)。
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胡塞尔把第二个先验还原途径,即视域分析,更明确地称为“生活世界”的先验还原,并且批评了“笛卡尔的途径”的不足。用他的话说:“那条道路(即笛卡尔的途径)虽然通过一种跳跃就已经达到了先验自我,但是因为毕竟缺少任何先行的说明,这种先验自我看上去就完全是空无内容的;因此人们在最初就不知道,借助于这种悬搁会获得什么,甚至也不知道,如何从这里出发就会获得一种对哲学有决定性意义的全新的基础科学。”(21)
这样看来,在《第一哲学》(下卷)中,胡塞尔仅仅有限度地告别了《观念I》中笛卡尔式的先验还原路径,但并没有告别作为现代主体性哲学代名词的笛卡尔主义。因为他对于世界之视域的现象学分析,也是为了揭示出终极的主体性原则:“先验自我”是一个意向性地构造一切意义,自我理解、自我负责和自由独立的理性主体。
但问题在于,胡塞尔在《第一哲学》之后的“发生现象学”思考似乎显示了一个相反的事实:
对于“我思”或先验自我来说,世界本身是一个“预先被给予的”视域。
换言之,“我思”或先验自我之所以能够意向性地构造意义或相关物,恰恰是因为它已经“在世界中”。更为重要的是,世界作为“我思”或先验自我的终极视域本身不可能是先验自我的意向性构造成就,因为世界是“我思”或先验自我的具体意向性构造之前提。

这也意味着,“我思”或“先验自我”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成为胡塞尔意义的自由自足和自我负责的绝对主体性。



就这点而言,胡塞尔在《第一哲学》(下卷)和《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的“我思”或先验自我比《观念I》中的“我思”或先验自我更接近笛卡尔的“我思”——两者都是有限和不自足的,都不是绝对的主体性。这一解释或许不符合胡塞尔的主观意愿,但更符合“事情本身”。





“雅典学园”微信学习群已经度过了2年多的时光,哲友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胡塞尔哲学的学习。微信公号“哲学门”同步“雅典学园”群的学习内容,精选紧扣学习内容的文章发布。
点击以下图片关注“哲学门”
系统性学习哲学防失联
注释:
①⑥⑦⑧⑨⑩(11)(12)胡塞尔:《第一哲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6,第87页;第33~34页;第42页;第90页;第100页;第101页;第104页。
②③胡塞尔:《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张宪译,人民出版社,2008,第41页;第1页。
④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欧东明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143页。
⑤Jeffner Allen,"What is Husserl's First Philosophy?",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42(4),1982,p.610.
(13)转引自James Street Fulton,"The Cartesianism of Phenomenology",The Philosophical Review,49(3),1940,p.286。
(14)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6,第1页。另可参见该书第9页。
(15)(16)(17)(18)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卷,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102页;第100页;第134页;§55。
(19)Ludwig Landgrebe,"Husserl's Departure from Cartesianism",The Phenomenology of Husserl:Selected Critical Readings,edited,translated an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R.O.Elveton,Noesis Press,Ltd 2000,p.260、pp.266~268.
(20)Saulius Geniusas,The Origins of the Horizon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Springer,2012,p.116.
(21)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187~188页。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