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酒馆“读大学”,唱歌把评委逗笑,玩了13年音乐的脑洞歌手,还在写寓言


▼
▼
2019年,张若水参加《这!就是原创》音乐综艺时,把头发绑在脑后,露出一张干净年轻的脸,他弹着吉他,对着陈粒唱了首《小镇的天桥》。
歌词有趣,但像口水话;旋律特别,又有些不着调。但他闭着眼睛,咧着嘴角,无比沉醉。
对面的陈粒听了两句就被逗乐了,在一连唱出十几个“浪费”后,选手席里也爆发出一阵哄闹声。
“奇特”的旋律和粗暴的歌词,让人感到有意思,也让人摸不着头脑。
第一轮,张若水落选。
但在下一轮比赛,陈粒启用后悔装置,在台上喊:“名字叫张若水的小朋友,你到小陈老师这里来。”
从选手席中站起来,张若水有些愣然,脸上还有红晕。
但即便如此,三年后,张若水还是没有出名。
他在成都的街头边,喝着三块钱的汽水,学各种想学的乐器,藏在烟火之中,无名之中,以音乐的形式,去思考、表达城市文明与人的关系。
01 ▼
他的脑子里装着宇宙吗?
与2019年参加综艺的时候相比,张若水看起来,“老”了不少。 素面朝天,戴着金属眼镜,瘦削身材罩在宽松的牛仔外套和棉布裤里,长发中飘着两缕灰白——不是挑染,是真的白发。
我们把收音设备夹在他的衣服上,没有声音。反复试了几次,设备仍然失灵。
他神游在外的神情终于回到现实,揶揄道:“完了完了,我有问题,可能感冒了身体有电,感觉可以通过这个拓展一下,写篇博士论文——《论人体感冒时电流对收音设备产生的影响》,引用一下那个什么麦斯威尔的电磁理论。”张若水哈哈大笑起来。
最后验证是收音设备的问题后,他叹气:“看来不是我的问题了,我的博士论文写不出来咯。”
张若水来自四川达州一个小镇,到成都很长一段时间后,小镇仍然更有家的感觉。
但“家”的感觉变了,是什么时候?
成年后,张若水回去的时间越来越少,直到有一次,他陡然意识到小镇扩大了五六倍面积,很多陌生建筑拔地而起。涌现的新地名、新地标让人意识到它在蓄力发展,接轨时代,但3块钱打车费可以走遍整个小镇的岁月,同时一去不复返。
在写完《小镇的天桥》那刻后,他发现老家也不是家了,与此同时,家乡孕育出来的自尊与习惯,也像是浮萍。张若水没有了根。
如今,在成都生活了十二三年,他在这里正式走上音乐之路,结婚安家,终于摸到一些安放灵魂的归属感。
小镇青年融入新一线城市,迷茫困顿之外,也因距离感而得以抽离其中,带着更清醒的目光去观摩现代城市之下的种种。
他写城市生活,写城乡结合部,歌词简单直接,混杂幽默的四川方言,爱从朴实日常的物象中发散离奇想象,思考现代文明社会,及其消逝的东西。
他在歌里疑惑道,对于习惯没有斑马线的小镇居民来说,两秒钟穿过的马路,何必修个天桥折腾他们,这浪费时间、体力、感情、青春、人民币......
鱼缸里的四条鱼,有的双目失明,有的缺氧被埋在树下,有的被抛弃在臭水沟,但还有一条决绝地奔向大海,在大海中死去;
小时候农村娃娃随便捡个瓶瓶罐罐就能在村头zhua(踢)足球,但21世纪的一块空地,能变成足球场吗?还是修成了停车场、大商场、飞机场或商品房?
张若水天马行空,有很多离奇想象和从个人视角出发的幽默感。
生命是荒诞的,因为“生命有生命力,所以会在荒芜的地方诞生有趣的东西。”
人可能是麻木的,“因为蹲厕所蹲久了,脚也会麻木。”
地球想和木星说话,木星不搭理,所以地球让人类灵感一现造出火箭,“有点类似于我挖一坨耳屎给它弹过去,那个耳屎还在上面拍个照,传些信息回来,比较高级的耳屎。”
想象力像脱缰的野马,他滔滔不绝,又似乎只在自言自语。在严肃思考中,又用一个个玩笑去消解重量,平衡自我。一个已入而立之年的男人,一边手舞足蹈,一边凝视社会。
他的歌词常常有寓言的味道,简单却耐人寻味,陈粒曾在节目中说:“我发现张若水的作品,太难忘了。”
02 ▼
小酒馆把一个少年送上舞台
张若水初中一直是班上最矮小,最不起眼的男孩。青春的敏感自卑和反叛相撞,“人生有意义吗?什么东西都被固化了。”
他在英语课上听到后街男孩和西城男孩的歌,潜意识觉得那个东西很酷,可以以此彰显自我存在的价值。同样喜欢音乐的发小和他吹嘘:“你知道林肯公园吗?林肯公园是现在最牛的乐队!”
张若水心里纳闷,面上却云淡风轻,“是吗,那我去看下。”
从小镇的唱片店里买下一张林肯公园德州现场的磁带,装进步步高学习机里,“卧槽!这是啥啊,很吵啊!”
但第二天,张若水还是把它们带去了学校,下课也不上厕所,戴着耳机在座位上夸张地摇来摇去。发小凑过来问:“你今天在听啥子哦!?”
张若水把一只耳机塞给他,卖关子:“你听嘛。”
闹哄哄的声音从单音道耳机里传来,发小瞪大眼睛望着张若水,大叫道:“WC!这个难道就是林肯公园嘛?!”
张若水得意道:“就是!”
后来,“Rock Year”音乐网站给张若水打开了更广阔的摇滚世界,横跨几十年,所有风格的摇滚乐,都能在上面找到。那时候他梦想,要和发小组一个世界上最牛的乐队。
2009年,张若水高考。大学开学前一个月,他被介绍给成都一个乐队当吉他手。那时他什么都不懂,吉他弹得半斤二两,跟着乐队边玩边学。过了两个月,他就嚣张地和发小组起乐队,一起写歌,排练的时候幻想在演出。
当小酒馆舞台助理的机会递过来的时候,张若水二话不说抓下了。除了观看免费演出的吸引力,在十几岁的张若水心中,小酒馆是摇滚乐的圣地,是玩乐队的唯一途径。
他在小酒馆给乐队接线,接触各种风格迥异的乐队,从调音、正式演出,到演出结束,张若水近距离观察和参与了乐队的整个流程。
也在小酒馆,他见到过四五百人的现场演出的火热,也听到过只有10个观众的沉静。
第一次在小酒馆演出时,张若水的乐队是马赛克乐队的暖场嘉宾。底下四五百人,观众反响特别热烈,台上的张若水忍不住得意,觉得自己像个摇滚明星,帅到不行。
第一首歌结束后,吉他手欧文凑过来,“不行,我琴弦断了,没法演了。”
张若水说,“锤子哦,我们已经站在上面了,必须演。”
欧文摇头说,这没法演啊。张若水问,不弹这根弦不行吗?欧文说必须用这根,张若水又说,那换一根不行吗?
俩人在舞台上窃窃私语,热闹气氛突然暂停,底下观众也懵了。欧文尴尬地向观众解释说,不好意思,我的琴弦弹断了。底下发出一阵爆笑。
马赛克乐队的卓越看到这场“事故”后,把自己的吉他递上了舞台,演出继续。张若水和鼓手点头示意,脑海里反复告诉自己“演出就是排练,下面没得人在笑你。”
张若水带着饱满情绪,准备卡点进音乐,结果人都跳了起来,该吉他出声的点却没声。
他回头一看,傻在台上——换了把吉他,线接上了,音响没开。
鼓手也愣得停住了动作,好不容易起来的气氛再次垮掉。
尽管张若水回忆第一次的演出像场闹剧,但咫尺的梦想和青春的热烈,还是让他们发自肺腑地感慨,那个晚上特别好,自己也特别牛。
在这之后,他们有空就会去小酒馆演出。站上舞台演出是年少时埋下的种子,张若水期待太久,渴望太久,愿意为这场狂热的梦付出一切。
一周七天,他三四天和乐队排练,两天在小酒馆,逃了不少课,甚至想退学,多年后他笑称,自己大学读的是“小酒馆摇滚乐专业”。
这几年,张若水的微信头像一直是《海贼王》路飞,而对他来说,小酒馆则是《海贼王》里的罗格镇,是音乐梦想真正开始照进现实的地方,是地球上的他,够到“木星”的那支火箭。
03▼
▼
3块钱的汽水
不顾一切留下痕迹
在张若水以为乐队会越来越好的时候,乐队解散了。欧文要出国留学,打算回来后当个英语老师。张若水不能理解,也没法接受。
乐队解散后的好几年,张若水都没办法和欧文好好说话。两人一见面就吵架,互相以激烈的碰撞,来用力证明彼此当年的选择和坚持是对的。
如今剑拔弩张的气势已去,两人和气地聊天,偶尔一起玩乐器,他不再强求谁必须得为音乐梦想孤注一掷,现实生活让他理解了人生的无奈,也理解了队员当年的选择。
但张若水不再组乐队了。他一个人做音乐,偶尔和朋友合作,但那种关系像是牌友,松散自由,不背负责任的关联。“大家都长大了嘛”,他说。
参加综艺节目给他带去一些关注和名气,但也不算太多。三年过去,他大多活跃在成都和一些音乐节中,创作也不算高产,总而言之,还是一个不太出名的歌手。
他曾动过去北京的念头,但念头在脑海里转了一圈就丢掉了。他想慢慢学习和探索,也不想被任何东西捆绑住音乐和灵魂。在快速造星的流量时代,成都给他留有这个空间。
但他也没有太过焦虑,如果成名是最终的追求,“那我不如现在对着镜头脱裤子。”
当然,他也并非完全没有企图心,“我觉得我的东西真的挺好的,值得被多听几遍,也许你第一遍会因为我的口音劝退,但可不可以多给我一次机会?准确地说多给自己一次机会。”
在音乐里,他继续做少年,纯粹炙热地追求着自我和梦想,以及青春时期就渴望的世俗框定外的认可。
张若水相信音乐,大过相信语言。
语言被语法、词汇、发音、环境影响,轻易便与真实意义背道而驰,但音乐无法伪装。“以前有种说法是,如果你遇到外星人,是可以用音乐和外星人交流的。”
在某个音乐节的宣传中,他介绍自己的歌是“唱着椒盐的望天歌”。但事实上,他找不到一种现有风格去定义自己的音乐。
“唱片店里有各种各样的分类,民谣的、摇滚的、流行的...我觉得以后说不定还会有多一种分类,可能叫Single style之类的,张若水的就放在里面。”
但如果不是川东小镇和成都,没有小酒馆,也没有等待他学习与纵情自我的城市和听众,张若水还能成为张若水吗?
“橘子喜欢在南方酸性土壤里生长,丢到北方碱性土壤,它不是这个味道,但还是橘子,最后它会成为属于那个地方的东西。在哪既重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这个人。”他不定义音乐,也不定义自己。
他曾看到一个00后艺术家的自我描述:自己的人生像隔夜跑了气的可乐,不好喝也没那么难喝,没什么价值,又有一点价值。
这个有些丧气的形容戳中了张若水。他不爱喝水,爱喝小卖部里三块钱的汽水,自己的人生似乎也能用汽水来比喻:自由流动的汽水被摇晃后,气泡从水中密集上涌,喷发。即便爆发的瞬间如此短暂,但喷出来的汽水,还是会黏你一手。
不被阻碍的自由,有过爆炸般的惊鸿一刻,并留下痕迹,张若水觉得自己的音乐与人生,都应当如此。
04▼
▼
一千年后
当不会音乐的人听到我的声音
夜色渐晚,他抱着双腿坐在地上,伸手指了指矮墙外的居民楼,“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音乐,就是千家万户的音乐。”
对面那栋楼晚上九点居民洗澡哼的调子;路边的清洁工嘴里不自主发出的声音;公交站台边等车的人唱的歌......所有这些,真实原始,不修边幅,没有门槛,由心而发,不可复制。
张若水的音乐来源于具体至极的生活和物象,有时候,他觉得音乐不是自己创作出来的,而是本来存在于宇宙之中,只是他在灵感来临时及时抓住了那一瞬。
90%的创作,都不经刻意思考,灵感来了,歌词从脑海里往外蹦,他就掏出随身带的小本本写下来。
早几年,因为吉他弹得太初级,歌词写成流水账,张若水粗糙的音乐被称为“口水歌”,遭到不少非议。他坦承当年的吉他水平确实不太高,但至今,他依然坚持认为一个和弦也能写一首歌,粗糙简单的音乐也能好听。
“我比较反对别人动不动就说,这个吉他难不难哦,我可能不得行,我以前gao(试)过......”他认为艺术天赋,是每个人都有的艺术本能。
一千年以后,如果有人听到张若水的歌,他希望对方感慨:“哇!这种东西他都能做,我也能做!”
他想让自己的音乐带来认同和启发,而非被高高在上的歌颂,在音乐人专业门槛的傲慢下,不断画地为牢。
聊到最后,张若水被严肃的回答问累了,他开始打破深度,回到开头说要写篇博士论文的状态。
问他身上最大的特质是什么,他想了会儿,摇头说不知道,末了突然指着自己的脸,
“嗷!最大的特点是头发前面是白的,这里还有一颗牙,耳朵是这样飞起来的!”
我知道,他又想回到自己神游的宇宙中去了。
由此刻MOMENTS发起,新青年同行者与LOOKLIVE联合发起的音乐主题讲述计划。本次计划将由「系列人物报道」、「微纪录片」和「多嘉宾主题公益分享会线上直播」三部分组成。
我们邀请了 9 组成都音乐人/制作人作为微纪录片主角、公益分享会分享者,共同讲述成都音乐故事,感受安放于音乐之中的真实日常。
出品 | 益美传媒
作者 | 海吉
益美君开通视频号啦
此刻MOMENTS
寓言诗人张若水:
小酒馆的摇滚乐学生
音乐里永远的少年
快戳视频和益美君一起看看这个故事吧~
👇👇👇
- END -
从歌到人,都不被束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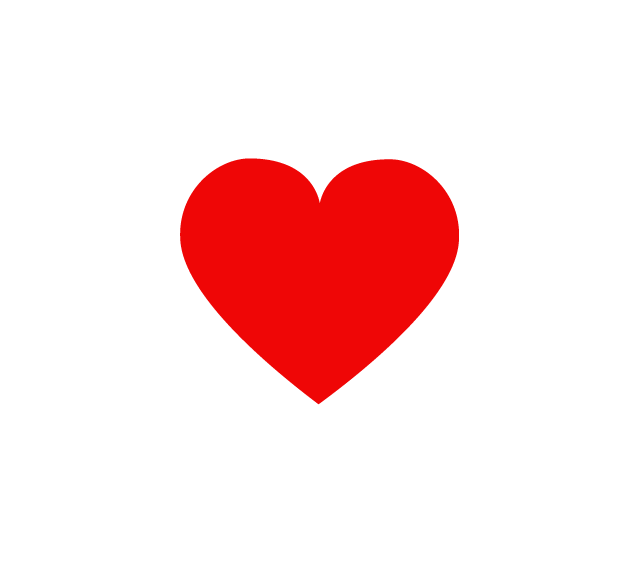
阅读原文 关键词
乐队
吉他
小酒馆
林肯公园
歌手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