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爆发!北京女孩辞职去战地,在炮火中接生婴儿,“即使不在前线,亦可参与救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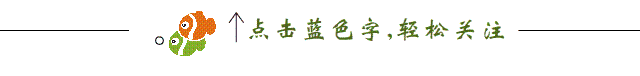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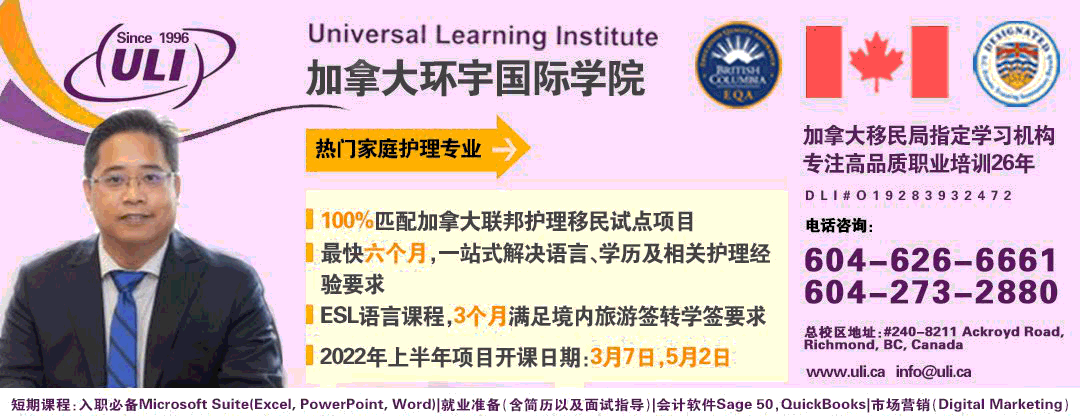

俄乌冲突的第五天,局势让各方关注。
基辅街头发生猛烈交火,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地区发生炮战。
当我们平静地开启新一周的日常生活时,世界的那个角落,被炮火和枪声洗刷。

26号,联合国难民署事务部表示,已有超36万乌克兰难民选择背井离乡,离开祖国。
最大的受害者,总是流离失所的百姓。
然而在人们彻夜逃离战火的时候,有一群天使,义无反顾地闯进死神的领地。
他们有个名字,叫“无国界医生”(MSF)。
每逢危难,他们总是亲身奔赴全球各大灾区、战区、疫区,向在最恶劣环境下挣扎着的人们,伸出援手。
中国无国界医生的故事,要从一个女人开始说起。
她叫屠铮,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

她是中国内地,第一位参与“无国界医生”海外志愿工作的医生。
在2007年4月,36岁的她远赴利比里亚的首都蒙罗维亚,为当地妇女提供妇产服务及外科手术。
那里刚结束长达14年的内战,上百万人流离失所,故乡成了一片焦土。
屠铮面对的,是不间断的武装冲突,和极其脆弱的医疗系统。
当年,利比里亚有325万人口。但注册医生,只有121人。
那里的孩子是按出生日取名,从星期一到星期日。
一周以后,孩子还活着,才会取一个正式的名字。

为了救人,屠铮曾连续工作36个小时。
经常被半夜叫醒,站上手术台。
她不怕外面的枪林弹雨,却怕自己的无能为力。
维生器械匮乏,6个月中,她眼睁睁送走6个孕妇,还有记不清数量的孩子——比她过去从医10年见证的死亡还要多。
高温雨季,医院没有能力给除了手术室之外的地方安装空调。
屠铮的手术服在汗水和潮湿中锈得扣不住,同事急得不行,屠铮冷静撕下一块胶布。
“别慌,贴上!赶紧手术!”
医院的救援项目上,有越来越多名为“Zheng”的小孩出生。
那是战火纷飞里,共同经历生死关头后,妈妈们为了记住这位美丽善良的医生,为孩子赋予的新生的意义。

屠铮在救援项目上工作 图源@MSF
屠铮之前,利比里亚的医院从没见过中国人。
屠铮来后,Benson医院的员工接连感叹:
“中国女人,真能干!”
2012年5月,做了几年无国界医生的屠铮,收到一封邮件。
发信人是她曾经的师妹,浙江妹子蒋励。
“屠老师,我想加入MSF。我已做好准备,来迎接这个重大的转折点。”
又一个中国姑娘,扛起炬火,做暗夜中的点灯人。

2013年,蒋励33岁,被指派到阿富汗霍斯特省。
医院就是一幢残破的平房,三间屋子。
一间手术室,一间病房,一间医生宿舍。
蒋励和另一位来自巴西的姑娘,就是这家医院仅有的两名妇产医生。

蒋励(右一)
阿富汗的春天,浸在战火里。
医院旁边就是警察局,经常遭到反对派的武装攻击。
蒋励和医生们的宿舍外墙砌着一圈砖,就是为了防止被流弹打穿。

关于阿富汗的新闻里,总是绕不开自杀式袭击、武装冲突、极端分子这样的字眼。
蒋励顾不上恐惧,因为无国界医生开办的医院全部免费,每天都会涌入大量的病患。
她面对是每个月1200到1300的分娩量,这是此前人民医院的四倍。
医院就像一个流水线,不断有孩子被生出来。
“待产室住不下,就在车上生、地上生。我进手术室的时候外面是一拨人,等我出来时看见的已经都是不同的面孔了。”
每隔一天,蒋励就要经历一次24小时的完全当值。
这24小时内,随时待命,没有阖眼休息的时间。

在这个不倡导女性接受教育的地方,母婴的死亡率很高,每天她都能遇到从没见过的疑难杂症。
很多妇女在小诊所接受了不正规的治疗,接受超大量催产素后导致子宫破裂。
在国内很少见的重度先兆子痫的胎盘早剥症状、合并症和并发症,在这里随处可见。
枪声也无处不在。
一天晚上,蒋励正在睡梦中,巨大的爆炸声让她从梦中惊醒。
她惊慌失措,不知道往哪里躲,害怕地给万里之外的未婚夫打电话,颤抖着诉说自己正在经历的恐袭。
未婚夫极力安慰她,给她发来马友友的大提琴协奏曲,希望用音乐安抚她的情绪。
蒋励就安慰自己。
“等天亮,就安全了。”

阿富汗受到攻击的医疗机构
危险如影随形,但蒋励仍恪尽职守。
原本在阿富汗,每十万例孕产妇里面,就有四五百例死亡。
但在蒋励值守阿富汗的3个月里,她接生了几千个新生婴儿。并且,没有发生过一例产妇死亡。
蒋励创造了一个奇迹。

做无国界医生,是没有工资的。
只有每个月922欧元的补助金,和只够生活成本的津贴。
按目前的汇率换算成人民币,6500块多点。
但选择加入的他们,谁在乎的是那几千块钱薪水。
他们放弃了和平和安稳,甘愿陷入危险和贫穷。
不过是医者仁心。
来自香港的赵卓邦,是一位护士主管。
他在2013年,辞掉了月薪30000港币的高薪工作,加入无国界医生。

赵卓邦 图源@MSF
工作地点,是也门的萨达。
当时,那是比伊拉克还接近地狱的战乱之地,几乎每天都受到联军的空袭。
不论昼夜,耳边都是战机、爆炸和空袭的声音。
有天凌晨6点,“轰”地一声巨响,炸弹直接轰毁他们基地旁边的一栋建筑物。
距离他的宿舍,近到只有700米。

可这些,他早就习以为常。
直到2015年的冬至。
一个男人走进医院帐篷,在床上放下一张毯子和一个袋子便离开了。
赵卓邦打开毯子,里面是一个小女孩的尸体。
“她的脸被烟熏黑,右边头部有大部分都不见了。其他护士告诉我,袋子里装的是人体残肢。”(来自MSF赵卓邦自述《也门:掠夺希望的残酷战争》)
恐惧和后怕在这一刻被放到最大,可眼前一个个求生的病患,让他迅速冷静下来。
他是唯一能给这些绝望之人带去希望的人。

另一个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故事,关于一个4岁的小男孩。
他每天都会跟随祖父,一起到医院来更换包扎敷料。
小男孩的所有家人都在一场空袭中丧生。
他自己的右臂,也在空袭中受创,需要截肢。
为了逗他开心,赵卓邦每次都会在他的绷带上画上一只手表。

可看着男孩天真烂漫的笑容时,他心里却隐隐作痛。
所有人都知道,他永远失去了在右手戴上手表的可能。
有时候,赵卓邦会拿香港和当地的孩子做比较。
“在香港,小朋友如果听到了飞机的声音会很开心,他们会喊‘长大我要做飞行员’。 但在也门,飞机带来的从来都不是希望。”

做无国界医生,最难的不会是工作,而是如何活下来。
西非埃博拉病毒爆发时,赵卓邦也在第一线。
一天,他穿好防护服准备前往高风险区。
同事叫住他,邀请他一起祈祷。
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手挽手围成一圈,虔诚地闭上眼。
祷告完,大家都会为对方送上一句“Be safe”。
每个人都说得很沉重。
走出门,谁也无法预知下一刻会面临怎样的危险。
全身而退是最重要的。

病毒通过血液和体液等传播,会经伤口感染。
那段时间,他不剃胡子,也不剪指甲。
只有一次,赵卓邦的手被纸划伤了。
平常不需要处理的伤口在那时的疫区,加剧了极大感染病毒的概率。
那是他最恐惧的一次。
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在那一刻一遍遍地拿消毒水洗,祈祷着千万不要感染,千万不要。
尽管如此,赵卓邦还是在疫区待了一个月。
那是执行埃博拉任务所允许的最长时限。

还有一位在刚果和南苏丹执行任务的姑娘,周吉芳。
她的任务地点在政府军、反政府军武装和部落武装长期冲突的地方,经常听到枪响。
她说:“最危险的一次是武装分子在半夜潜入了营地,他们应该是来抢劫的,有位医生从房间里出来,被劫匪打中了肩膀。
好在组织及时救治,并运到比利时治疗了很长时间。
(MSF)成立四十多年来,我们有医生被绑架,也有医生在执行任务中受伤和牺牲,意外是无法避免的,你要做好遭遇最坏情况的心理准备。”
他们知道此去征程漫漫,前路艰险,辛苦异常。
但穿上白大褂便是一身傲骨,一腔赤血。
行者无涯,医者无疆。
新疆医生阿依夏·那万在演讲中提到,
很多医生、后勤工作人员,在结束了当前的援助项目平安归家后,都会说:
“好,这是我最后一次去了,我要享受我的生活。”
可是每当他们从新闻或电视上看到这里在发生战争,那里在遭遇天灾的时候,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收拾行李,前往需要他们的地方。

阿依夏·那万
他们放弃了无数人最向往的钞票、房子、家庭和平安。
他们灰头土脸地跟死神对峙,用纱布、血袋、消毒水和手术刀,打着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至今在那些世界没人留意的角落,做着这些主流社会上不相关、遥远的事,从而去帮助那些陌生的,实实在在的人。”
他们在最危险的地方逆行,即使代价是自己的性命。
想起《鼠疫》里那个主人公医生,他尽其所能挽救病患的生命。
同事问他,“你为什么非要去?什么促使你这么奋不顾身?”
医生平静地说:“我从未对死亡习以为常。”
生命无常,不代表生命无力。
他们誓死,要为那些身陷囹圄的人,带去活下去的可能。
他们在捍卫每一个人,活着的权利。
他们见证了人间疾苦,然后努力地在苦难里,撑出希望。
印象里有一个小故事,是一位中国母亲的感慨。
她希望儿子能够从事金融类的“体面工作”,儿子却选择去非洲当无国界医生。
她说,大概是自己成长得太慢,没有跟上孩子的步伐。
她希望孩子有一个better life,但孩子已经想要一个better world了。
我想,此时的地球村,也大抵如此。
接下来的斗争,可能会更残酷。
铁拳和硝烟,凌驾在一个个头破血流的生命上方。
无尽的灾难中,无人可以独善其身。
希望冲突能够早日终结。
因为和平,从来就不只是一个梦想,而是需要每个人去践行的目标。
资料来源:
《中国青年说》:无国界医生战地实录
《中国新闻周刊》:来自中国的“无国界医生”
《澎湃新闻》:无国家医生蒋励,阿富汗战争中的天使
MSF无国界医生官网https://msf.org.cn
《一条》赵卓邦采访视频
大家都在看
大家都在看


关于我们

点分享

点收藏

点点赞

点在看
关键词
无国界医生
医生
医院
“无国界医生”
中国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