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精选摘自《收获》曾经的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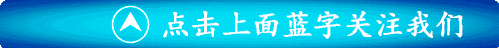
【留美学子】第2512期
8年国际视角精选文摘
教育·人文·名师·媒体生态圈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曾经的音乐》
文:沙石

原载自《收获》
经作者授权发表

那是夏日的一天。我从伦敦出发,坐了两个半小时的火车来到英国的海港城市利物浦。
火车的车皮是橘红色的,但就其结构而言,它与中国的绿皮火车相差无几。真难想象在中国高铁四通八达的今天,在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还能坐上这样几乎过时的老式火车。不过这倒符合英国人的怀旧情怀,凭我的观察,英美人喜欢复古,对他们来说东西越陈旧越好。

下车时天上飘着毛毛雨,云层很低,让人感到压抑。
我走出站台,立刻觉出这里的异国情调。红砖房,卵石街道,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这种欧式古典建筑风格都很少见。从人们漫不经心的步伐和不哭不笑的表情来看,这里真是甲壳虫音乐的故乡。我展开地图,装模作样地查看。其实我在出发前已经规划好了路线。接下来我要步行二十分钟到阿尔伯特码头,那是甲壳虫乐队故事博物馆的所在地。
从前我对利物浦这个城市认知甚少,只听说这里有一支英超足球劲旅,是出英国足球名将和足球流氓的地方。不过我这次不是为足球而来的。利物浦是现代摇滚乐的发源地,因为这里是甲壳虫乐队的故乡,每年有上百万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怀着朝拜的心理到此一游。我是众多朝拜者中的一个,带着探索和求证的心情而来。
我提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囊向阿尔伯特码头走去。参观甲壳虫乐队故事博物馆是我此行的目的,其实何止此行,在大半的人生旅程中我都在探寻甲壳虫音乐,只是有时热烈,有时不那么热烈而已。唯一让我担心的一件事是参观了博物馆,完成了自己的心愿,我的追求就到头了。当多年的梦想即将实现的时候,人总会觉得快要得到了什么,与此同时又要失去什么。人就是这样的动物。

对甲壳虫音乐的认识起初很模糊,充满了少儿时期的迷惘,还曾经闯入过误区,甚至还陷入一个不大不小的骗局。说到这里,就自然想起我的小学同学张一禾,一个古怪又疯狂的富家子弟。
对有钱人,特别是当下那些肥得流油的富豪,我有种天然的鄙视,觉得他们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在我看来,他们的生活太空虚,太乏味,不管他们怎么显摆自己的财富,他们的优越感还是很苍白。当然,我的这个认知可能有点偏激,甚至有欠公平。其实人有了钱还是可以享有许多东西的,比如说豪宅,豪车,游艇,还有小三、小四、小五等等。我对金钱的不屑多来自一个复杂的情结。
它大概与小时候过惯了清苦的生活有关。十二三岁时,我的最大心愿就是穿一双白回力,就是那种高腰的白球鞋,只有专业篮球队员才配穿在脚上。但也有列外,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张一禾,他不是篮球运动员,可也穿着白回力,只是因为他家里有钱。我对富人的成见就是从张一禾脚上的白回力转换而来的。不过对白回力的向往也给了我上进的动力。它让我有梦想,有追求,还有间歇的定力。假设没有对白回力的渴望,我的生活也会像有钱人那样无趣。
上小学时,体育自然是我最喜欢的科目,理由很简单,就是体育课上每做一个动作都让我感到白回力带给我的冲动。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改变了我的爱好取向,我转而从体育爱上了音乐。不过我对数学的厌恶是不可逆转的,是永久性的,这个心结一直延续至今。
我曾经认为数学家是一群自虐狂,他们狡猾,尖刻,专门出一些难题难为自己。记得数学课上教我们加减乘除的老师总是用生产队修筑猪圈作为例题。生产队修猪圈,长20尺,宽15尺,求猪圈的面积是多少?生产队修猪圈,挖地2尺,如果修五个同样大小的猪圈,总挖土量是多少?
当时我就想:难道生产队除了修猪圈就不会干点别的吗?没想到人对未来是有感应的,尽管现代科学还无法解释这个现象。许多年后,我下乡来到农村,生产队长第一眼看到我二话没说就派我到养猪场去喂猪。我的宿命好像是被事先安排好了一样 - 对数字的厌恶导致了我对数学课的排斥;对数学课的排斥让我不喜欢猪圈;因为不喜欢猪圈,我才被派去喂猪。我的人生大致可以这样解释。
起初,我对音乐课并不感兴趣,因为那是女生喜欢的玩意儿。可是这个意识在五年级第二个学期的第一天发生了变化。那天来了一位教音乐的新老师,是个二十几岁的女子。她一走进教室,全体同学都惊呆了,平时吵吵嚷嚷的我们安静得像一群绵羊,连一向不安分的张一禾都变成了一个听话的乖孩子。
是新老师的美丽把我们征服了。她太迷人了,虽然当时我们也说不清她到底什么地方迷人。多少年以后每当回想起少时的迷惘和惆怅,我才意识到她的迷人之处是她身上的女人味。这多少也解释了我为什么喜欢看她那双弹风琴的手和我拉大了嗓门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时她向我投来厌恶的一瞥所带给我的快感。
后来我又想出了一些鬼点子来引起女老师的注意,比如当大家都唱“王二小放牛郎”的时候,我故意趴在桌上睡大觉(其实是装睡),以便吸引女老师快步走到我的书桌前,用手指敲打我的后脑勺,说:“你上课睡觉,给我罚站10分钟。”听了她的话,我揉揉眼,伸伸腰,大大方方地站起来,表面上忿忿不平,而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得意。
所以说,我爱上音乐是女老师用手敲我后脑勺的结果。
不过我的音乐才华是很有限的,这一点我十分清楚。我唱歌除了嗓门大,其它方面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可是这一点也不影响我对音乐的喜爱。我不但喜欢唱歌,还喜欢听歌,当然更喜欢听美女老师弹奏出的每一个音符。
我开始潜心体会音乐带给人的感受,并很快学会了从不同的音符中体会出喜怒哀乐的情感。这种类似初恋的热情,充满了盲目的冲动和好奇。正当音乐即将把我从小河流水带入惊涛骇浪的时候,我注意到报纸上出现了批判“甲壳虫音乐”的文章。甲壳虫音乐?多么奇怪的名字。这是什么牛鬼蛇神?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许多年后,当我来到美国,才知道甲壳虫音乐的学名是“Beatles”,在港台和新加坡一带通常被称为“披头士”或者“披头四”,不过我还是觉得只有“甲壳虫音乐”这个名字才能让我的心绪插上遐想的翅膀。
没想到对甲壳虫音乐产生疑虑的还不止我一个。私下打听了一下,大部分同学以及他们的亲属,上至父母,下至兄弟姐妹,没有人听过甲壳虫音乐。那么问题就来了。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应该提出这样一个质疑:既然没人听过甲壳虫音乐,为什么要拿出来批判?一时间同学中间掀起了一个探讨甲壳虫乐队的热潮。一部分同学认为,甲壳虫最典型的代表是屎壳郎,因此说甲壳虫音乐一定又臭又甲,所以必须要批判。而另外一部分同学则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指出,甲壳虫并非一无是处,它们的存在给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所以它们或许值得称颂。
随着更多批判文章的出现,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深入,不久一个阴谋论诞生了。根据这个推论,很可能有人利用批判的武器来宣扬甲壳虫音乐,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什么遭到批判,什么东西就容易红火,就像当下的演艺界的明星,总要搞出点丑闻来才能走红。
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以音乐天才自居的张一禾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只是这次不是因为他脚上穿的白回力。
张一禾除了出身富裕家庭外,他还是个音乐狂热分子。他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不刷牙,不洗脸,但他一定要拉小提琴。不过尽管他拉琴拉得很投入,但这并不意味他拉得有多好,连我这个没有多少乐感的人都能听出他拉出的曲子颤音用得太多,铁丝声太重。好在张一禾的家境殷实,他有拉提琴的资本。张一禾的老爸是名教授,在大学教授英语。他的老妈曾是阔人家的小姐。富裕的生活足以让张一禾在同学中趾高气扬,也让他有一把意大利的虎纹小提琴,这自然引起许多同学的羡慕。他演奏小提琴时,总是半闭着眼,摇晃着他超大脑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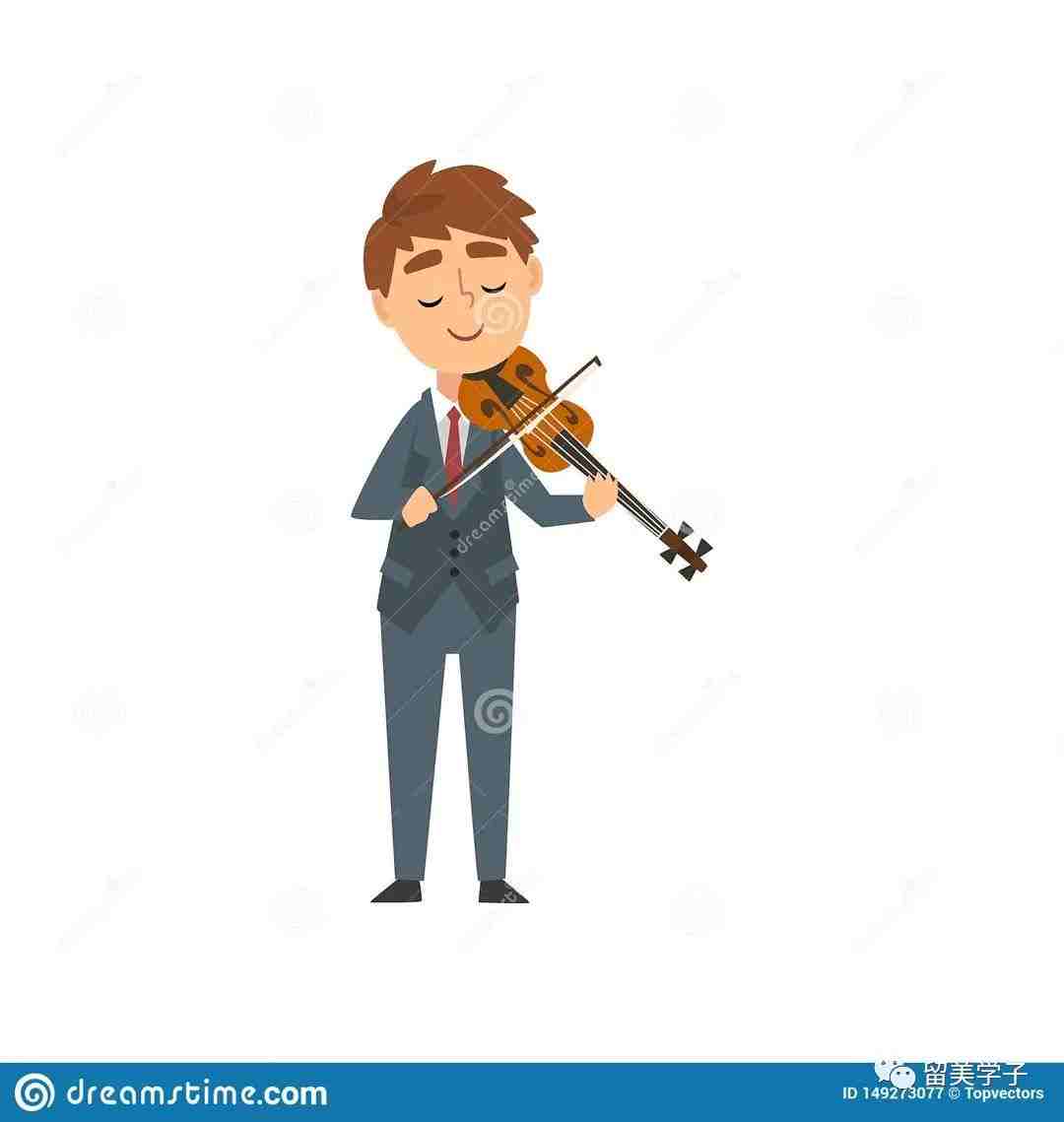
我经常听张一禾磕磕绊绊的演奏。他拉的《新疆之春》相当够味,足以让我倾倒,而西班牙作曲家萨拉萨蒂的名曲《流浪者之歌》却被他拉得像寡妇哭坟一样。没想到张一禾的大脑壳里装的净是些坏水。他利用我的好恶,定下一个规矩,只要我想听《新疆之春》,就要给他一毛钱,而相反的是,如果我不想听《流浪者之歌》,也要给他一毛钱。这样一来二去,他从我这赚了不少黑心钱。
“张一禾,你这狗日的。”一想起他的阴险,我就忍不住骂他一句。
虽然张一禾是教授的儿子,但他一点也不用功学习。他和我一样,喜欢上体育课,因为可以显摆他的白回力,也喜欢在音乐课身上表现他的音乐才华,不过他沾了数字也和我一样发懵。如果说我和张一禾之间有一丁点相同之处的话,那么厌恶数学是我们的唯一的共性。
张一禾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练琴上。他练琴最明显的标志是他左腮下一块明显的肿块。那是他长期用下巴架琴留下的活疤,之所以说是活疤是因为它永远红肿,而且带着血丝,像个烂透了的西红柿。这是张一禾拉琴的鉴证,也是他炫耀的资本,人前人后,特别是在女生面前,他总是扬着头,把鲜活的肿块暴露在众人的视线之下。
这天张一禾把一群同学召集到一起,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说他终于知道什么是甲壳虫音乐了。听到他的宣布,大家异常激动,都问他是不是像屎壳郎一样又臭又甲?张一禾摇摇头说不是,实际上听上去节奏感很强,是降E大调协奏曲。张一禾的话让大家肃然起敬。看看人家张一禾,还知道什么是降E大调,还知道什么是协奏曲,真不愧是小提琴家。这样的赞许自然让张一禾很是得意。他说他的话字字属实,绝不是空穴来风,因为他已经听过了唱片。这下大家更兴奋了。
既然他听了唱片,那他家就一定有留声机,这是明摆着的。我们中间绝大多数人都没听过唱片,更没见过留声机。可不可以让我们一饱眼福,同时亲耳聆听甲壳虫音乐到底是什么德行,求求你啦,行不行啊?有几个女生又是跳脚又是作揖地祈求张一禾。张一禾高高地仰起他的头,露出下巴上那块鲜灵的肿块。

我们一行七八个同学来到张一禾的家,围着那台留声机,前后左右地端详好一阵子。张一禾用英语告诉我们,这玩意儿叫Phonograph(留声机)。说着他从箱子里取出一张胶木唱片,黑盘,中间的红圈上印着金字。我们传看着这张唱片,上边印的全是外国字,谁都看不懂,只好把全部的信任寄托在张一禾身上。
人家至少有个教英语的老爸,对不?随着音乐从留声机中飘出,周围的空气发出美妙的震动。我们都像吃了激素一样兴奋。听完第一遍,彼此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说挺热闹的。原来这就是甲壳虫音乐。我们听了一遍又一遍,以致每个音符都在大脑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这么好听的东西不应该和屎壳郎扯上关系,一定是有人搞错了。这年头好东西被误认为坏东西,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
从此,我以为我听过了甲壳虫音乐了,也懂得了甲壳虫音乐,没想到我的自以为是,不过是自欺欺人,我和我的那些同伴被带进了一个误区,整个事件带着欺骗的色彩。
事情败露的时间是1986年7月5日这一天。
当天晚上,中央乐团上演了一场由李德伦指挥的交响乐。当电视实况转播里传出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多年前张一禾放给我们听的不是什么甲壳虫音乐,而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我这才意识到我们是被张一禾忽悠了。那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激怒了我,愤怒过后又感到有些委屈,复杂的心情至今难忘。
一连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到了第五天,情绪才渐渐稳定下来,我转而开始暴饮暴食,在床上贪睡不起。我开始四处打听张一禾的下落,但结果不尽令人失望。张一禾早就不拉提琴了。他已成功转身,开了公司,成了董事长,赚了数不清的钱。张一禾会赚钱,这一点也不让我吃惊,就凭当年他里外从我这赚钱的手段,就说明他有着非凡的商业头脑。
来自各方面的消息还显示,张一禾近年带着家眷,包括他的教授老爸和曾经是富家小姐的老妈,移民到了海外。听到这里,我更加沮丧,觉得张一禾做人不厚道,他欠我一个解释,他必须给我们这群人一个交待。我对有钱人的嫉妒因此转化成了嫉恨。
“张一禾,你个狗日的。”我暗自骂道。
不过人经受一些打击也不全是坏事。通过这件事,我对甲壳虫音乐的兴趣一点没有减弱,反而得到了提升。对它的期待就像一颗埋在干旱土壤里的种子,不但渴望着水分,更渴望着发芽。
不过初到美国时,我并没有把探索甲壳虫音乐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原因很简单,我是人,我要吃饭,要住房,有时还要满足对女色的需求。
来旧金山之初,为了谋生我在一家搬家公司作搬运工,这对一个年近中年的人来说,不但是身体上的挑战,也是心灵上的挑战。虽然先前养猪时也干过体力活,但那已是久远的往事。做搬运工带给我最深刻的感受是美国的家具特别沉重,总是压得我肩疼,腰疼,心也疼。
一天收工后,我穿着肮脏的工作服,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家走。路过一家酒吧,从里边传来一阵歌声,深沉而又缓慢,我忍不住驻足倾听。其实,吸引我的不是优美的节奏,也不是动听的旋律,它带给我更多的是一种的苍凉。那正是我当时的境遇:潦倒、穷困、孤独、思乡。难言的伤感涌上心头。不知不觉中,我已泪流满面。一段音乐让我如此动情,可见它的感染力。当年在张一禾家听到《英雄交响曲》的时候,我似乎也有过这个感受,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前后的心情一样又不一样。
我忍不住走进酒吧,问正在侍酒的酒保这是什么歌曲?怎么让我如此感伤?酒保用看外星人的目光看着我,说你难道不知道Beatles(甲壳虫乐队)?这是他们的名曲,曲名是《Yesterday》(昨天)。
就这样,从错把《英雄交响曲》当成甲壳虫音乐过去许多年之后,我终于认识了甲壳虫音乐,它再度闯入我的生活就如同二婚一样,虽然没有第一次的狂热,但相对的淡定反而能持续长久。原来,我光顾的是以甲壳虫音乐为主题的酒吧,名为 Light Rock (轻摇滚),在旧金山一带颇具盛名。
从此,我成了轻摇滚酒吧的常客,疲劳的时候,孤独的时候,想跳楼自杀的时候,我都会来到这里,点上一杯略苦略涩的葡萄酒,一边喝一边听那些打动了亿万人心的歌声。我渐渐走近了那四个来自英国利物浦的小子。约翰·列侬,保罗·麦卡特尼,乔治·哈里森和林格·斯塔尔,成了我不能忘怀的名字。他们与我很遥远,而又十分接近。几年下来,除了酒量大有长进之外,我还熟悉了甲壳虫乐队演奏的摇滚乐,总共有213首歌曲。

这些歌总是在悲伤的时候让我看到光明,在高兴得忘乎所以的时候让我冷静。它们让我百听不厌。《昨天》、《Let it Be》、《Something》、《嘿,朱迪》、《请取悦我》、《回去》、《穿越苍穹》、《太阳出来了》,当然还有成就了村上春树的同名小说的《挪威的森林》,这些歌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像我的朋友,像我的兄弟,像与我的情人。那些充满诗意的歌词带着些许神秘,是那么耐人寻味,而时常甜美时常苦涩的青春爱情,夹杂着失落和对生活的无奈。这不就是人生?
《昨天》的歌词总是能唱出我的心声:
昨天
我所有的烦恼似乎很遥远
现在看来,他们将留在这里
哦,我相信昨天
突然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一半了
有阴影笼罩着我
哦,昨天突然来了
她为什么要走,我不知道,她不会说
我说错了,现在我想昨天
昨天
爱情是如此简单易玩
现在我需要一个躲藏的地方
哦,我相信昨天
她为什么要走,我不知道,她不会说
我说错了,现在我想昨天
……
今天,我来到了利物浦。这里是诞生《昨天》的摇篮。一想到这里,我的心就莫名其妙地慌乱。
毛毛雨过后,天色变得更加阴沉。令我吃惊的是利物浦的夏天竟然和我老家一样,潮湿、闷热、多汗。从这样环境出来的人往往慵懒,颓废,喜欢用睡眠度过溽热的夏天。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曾经这样活过。
阿尔伯特码头不愧是个码头,它三面临海。被称为“甲壳虫乐队故事”的博物馆是一座临海的红砖四层楼房,除了正门上方挂着一个大型蓝色甲壳虫乐队的Logo(徽章)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装璜,更没有广告和宣传海报。后来进入展厅以后,我更发现博物馆的内部同样没有什么装饰,所有陈列的展品都是原件,十分陈旧,甚至显得破烂。狭长的走廊和一道道偏门,让我想起小时候住过的筒子楼。普通、不加掩饰、贴近大众生活,这不正是甲壳虫音乐带给人们的感受?
在博物馆门口,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走到我面前,满脸的胡须几乎遮盖住他白人的脸廓。他用生甲的中国话说:“你好!上帝保佑你。”我掏出一张印着女王头像的五英镑钞票递给他。他又连声用中文说“谢谢”。看起来到这里来参观的一定有不少中国人,连聪明的流浪汉都知道与时共进。不过流浪汉在欧美城市非常常见,没有什么稀奇,流浪汉是西方社会的标签。
我站在约翰·列侬的白色钢琴前,带着默哀的心情。当年的《昨天》就是用这架钢琴谱出曲来,后来被保罗·麦卡特尼演唱,一时风靡全球,成为被永久传唱的名曲。2000年,《滚石》杂志和MTV电视联合评出六十年代以来世界最伟大的流行歌曲,《昨天》名列第一。

眼前的一切让我百感交集。
如果当年报纸上没有出现批判甲壳虫音乐的文章,我们那群小屁孩怎么会知道甲壳虫乐队的存在?尽管张一禾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误导了我们,尽管他的做法的确有点卑劣,但这件事毕竟激发了我们对甲壳虫音乐的好奇和向往。看着展馆墙上成百上千的黑白照片,我陷入了沉思。虽然那些照片里绝对不会有我们那群小学生的身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存在其中。约翰·列侬的节奏吉他,保罗·麦卡特尼的贝斯键盘,乔治·哈里森主奏吉他和林格·斯塔尔的鼓架,都保持着直立的姿态展示在前来参观的观众面前,好像在告诉世人,他们的音乐永远不会倒下。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我来到博物馆最后的展厅,再走过一道门,我就要离开这个催生了现代摇滚乐的地方。这让我恋恋不舍。多年的渴望就要结束了。我有所得,但又似有所失,好像忘记了什么,好像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完成。不过这个感觉从我进了博物馆之前就存在我的意识里,岂止是进展览馆之前,缺憾感早在我来英国之前就有了,早在我在养猪场喂猪的时候就有了,甚至可以说早在我出生之前就有了。
这就是生活,永远不圆满,永远有缺憾,只有接受了缺憾,人生才能获得圆满。这就是我,喜欢搬弄哲理,喜欢自圆其说,可以让可怜变得悲壮,把丧事办成喜事,就是在丢了钱时候也能用“破财免灾”来勉励自己。

最后的展厅没有多少展品,正面墙上写着一大段致谢辞,不外乎感谢你的光临,感谢你的支持,感谢你的陪伴,对这些公式化的东西,我没有兴趣。倒是谢辞的结尾部分引起了我的注意。这里的文字主要是感谢那些为博物馆捐款的大户,而且在接下来的半面墙上还列出捐款大户的名字,每个名字上方还配着一张一英尺大小的照片。到了我这把年纪早就不把惊喜当作惊喜,即使遇到惊喜,也常常只惊不喜,但是这次有些例外。
当我的目光触及到Yi He Zhang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真的被惊到了,虽然喜的感觉是后来的事。为了验证最初的怀疑,我认真地查看了名字上方的照片。与四十多年前相比,张一禾老了,胖了,鬓角上的银发和紧绷的嘴唇显出一点霸气,不过那种吊儿郎当的音乐家气质还萦绕在眉宇之间。没错,是张一禾,是那个狂爱音乐厌恶数字的张一禾。
我特别留意了一下他左边的下巴,那个拉琴留下的疤痕还在,只是不再鲜活,也没有了血丝,从前的活疤已经变成了死疤。
也许是因为看到了张一禾的胖脸,或者是他鬓角上的白发,总之有一种东西让我释怀,长期的压抑感似乎在离我而去。虽然张一禾的捐款与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但它还是让我看到了他的另外一面。第一次,我开始认识到钱,如果能够上升到精神层面,还是挺可爱的,还是能够改变世界的。或许张一禾已经不欠我什么了,当然我从始至终都不欠他什么,唯一需要向他表示歉意的是我对有钱人持有的偏见。
我走出博物馆,天上又飘起了毛毛雨。被淋湿的卵石路面油光滑亮,让我想到过去看过的一些油画,所不同的是这次的感觉是置身于油画之中。我朝着火车站的方向走去,默默地想着心事。当年的张一禾是有意用《英雄交响曲》迷惑我们,还是他本人也蒙在鼓里?这是个问题。
周围不断有行人从身旁走过,来去匆匆的人们如同与我擦肩而过的人生。还有天上飞过的鸽子,噗啦啦地煽动着翅膀,像是与我道别。道别,这正是我此刻的心情,只要离开这里,我就会把过去远远地抛在身后,可是张一禾就像长在我身上的一个痦子一样和我不离不弃。
走出不到一个街口,就看见几个流浪汉在街角处游荡。我有意不与他们有眼神上的接触,只想匆匆走过去。但没走出几步,我却走不动了,双脚不由地立定在那里。是从身后传来的音乐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先是一愣,紧接着心又动了一下。
飘忽的音乐是我熟悉的甲壳虫经典之作《Let It Be 》(顺其自然)。这里是甲壳虫音乐的故乡,听到这类乐曲本没有什么稀奇,但是音乐中的什么东西触动了我,让我不能无动于衷。音乐是用小提琴演奏出来的,其中用了过多的颤音,还参杂着铁丝声。它唤醒了我的记忆。我的头皮一阵发麻,随即麻酥酥的感觉顺着脊背窜到脚跟上。
我转身回来,几乎和拉琴的人打了个照面。只见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身上穿的衣服很是破烂。他不但是个流浪汉,而且还是个中国人,他的脸型和眉眼的布局看上去还十分熟悉。我不能不为此吃惊。我的出现也把他吓了一跳。他先是呆滞地看着我,然后慢慢放下支在肩上的小提琴,这下我看到了他左腮下的疤痕。麻酥酥的感觉再次从头窜到脚。我认出了他是谁。
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遇见张一禾是我要命也没想到的。在博物馆,他是捐款大户,受到成千上万人的仰慕,而这会儿站在我眼前的是个穷困潦倒的流浪汉,二者之间的落差太大了,其中的故事肯定是部惊天地泣鬼神的肥皂剧。
张一禾直愣愣地看着我,我也愣愣地看着他。他脸上的某块肌肉在抽动,不知道他是想哭还是想笑。从他空洞的目光来看,他没有认出我是谁,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因为我不想伤害他的自尊。
我想说点什么,就凭积累了四十几年的牵挂,有好的,有坏的,我也应该说点什么,可是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塞住了,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好看着张一禾的脸在不规则地抽动。

过了一会儿,他重新架起提琴,继续他的演奏。老实说,《顺其自然》是首轻摇滚乐曲,不太适合用小提琴来演奏,但乐曲的情绪是对的,忧伤,无奈,却又怀揣着希望。瑟瑟的琴声告诉我,张一禾不是在演奏,而是在倾诉,他在用每个音符讲述关于他的肥皂剧。我不知道他在肥皂剧中发生了什么,也无法猜测是困苦选择了张一禾,还是张一禾选择了困苦,可如果把他生活的点点滴滴用一条线连接起来,就会发现其中的每个点都和甲壳虫音乐有关。
张一禾的面前放着一个铁罐,我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我掏出钱包,从里边取出一张五英镑的钞票,放在罐子里,可是一想不行,又放进一张五十英镑的钞票,又放了一张一百英镑的钞票,最后我干脆清干了我的钱包,连一个先令都没留下。最可气的是在这期间张一禾没有露出一丝一毫的谢意,他只是不慌不忙地拉琴,半闭着眼睛,摇晃着超大的脑壳。他还是这么孤傲,这么各色,当年的臭脾气一点都没改。

我离开了张一禾,把《顺其自然》的琴声留在了身后,不过它的歌词却伴随在我的心里:
……
耳语智慧之言,顺其自然
当生活在世界上心碎的人们同意时
会有答案,就这样吧
因为虽然他们可能会分开,但他们仍然有机会看到
……
悄悄地说智慧的话,让它成为,成为
当夜多云时,仍有一盏灯照在我身上
闪亮到明天,就这样吧
我在音乐声中醒来,玛丽妈妈来找我
顺其自然,顺其自然,顺其自然
……
我继续往前走,脚踩在潮湿的卵石上,发出私语般的声响。就在这时,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张一禾演奏的乐曲突然开始转调,由《顺其自然》变成了《新疆之春》,前者充满了忧伤,后者是满满的欢快,二者之间的转变没有过渡,生甲,且又唐突。张一禾拉的《新疆之春》曾经让我倾倒。我站立在原地,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张一禾,你这个狗日的。”我忍不住又骂了他一句。
(完)
2021年5月30日
修改于2021年7月11日

沙石
美籍华人作家。美国华文文学艺术协会(美华文协)荣誉会长,短篇小说《玻璃房子》选入中国小说排行榜,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玻璃房子》及长篇小说《情徒》。
从事文学创作以来,小说,散文,随笔等作品不断在海内外刊物上发表。
原籍中国天津,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英文系。90年代初毕业于美国内华达雷诺大学新闻系,曾在中美新闻媒体从事记者编辑工作达六年。目前在旧金山市政府担任公关专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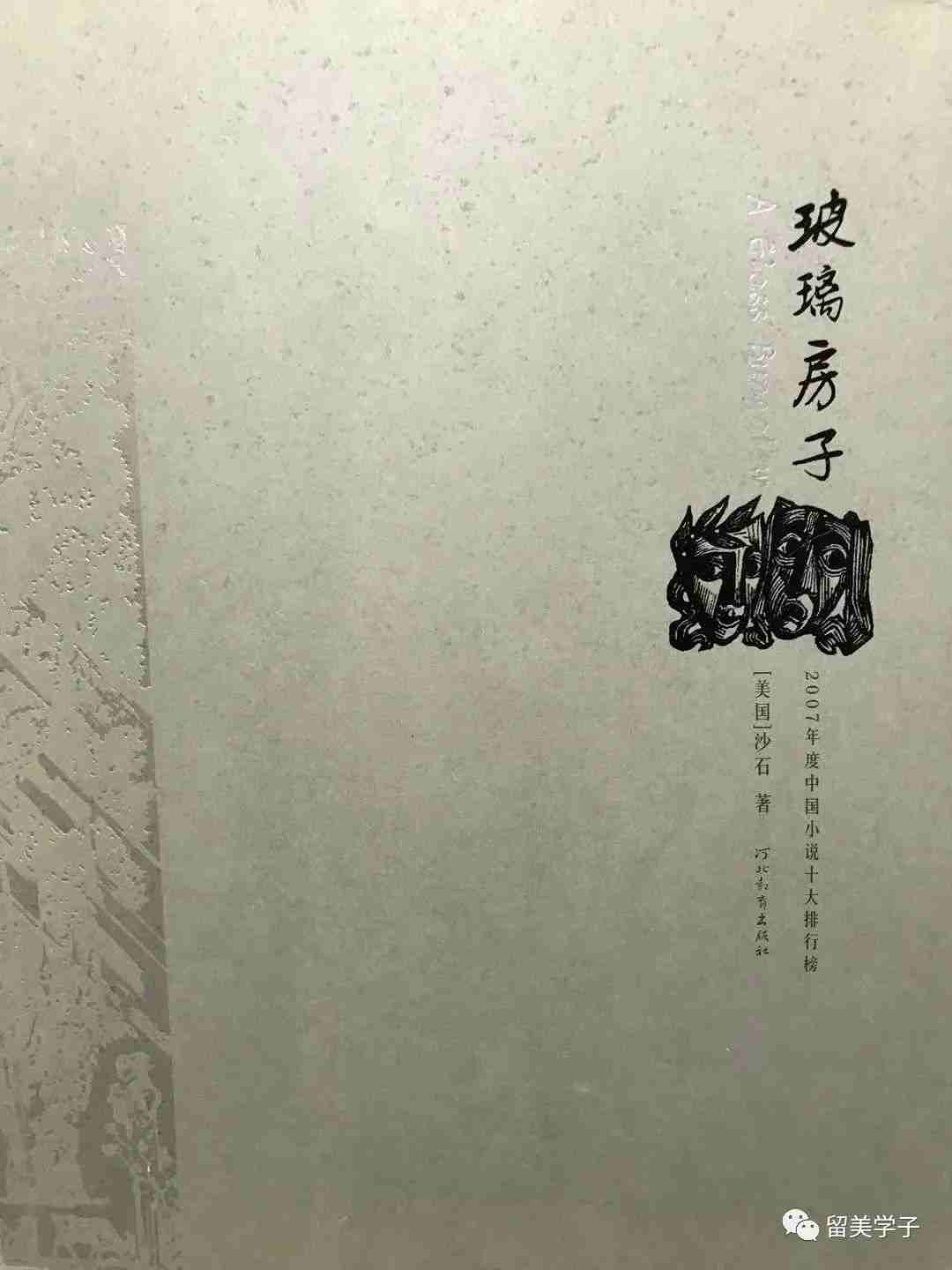
作家沙石部分作品
延伸阅读链接


【重要通知】
下周起白宫将免费提供新冠居家检测
美国人可以通过政府网站免费领取新冠居家快速检测,这些检测将被直接寄民众家中。
政府官网地址:https://www.covidtests.gov
只需输入姓名地址等基本信息就可领取检测,有5亿份检测供民众免费使用。
关于疫情参考
【留美学子】近期发表

喜欢就点“赞”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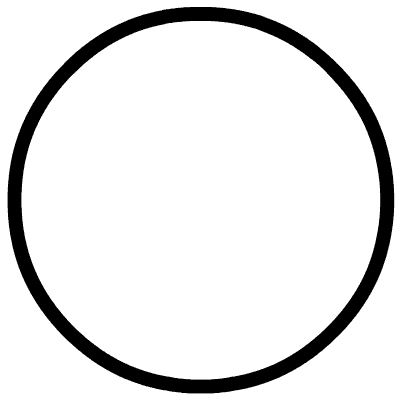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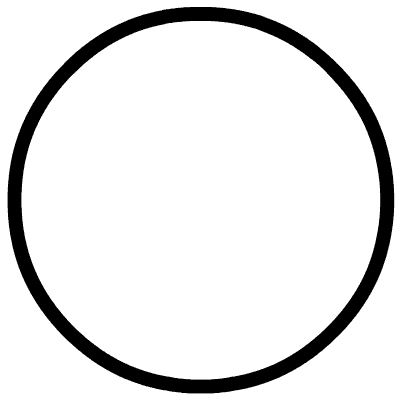
阅读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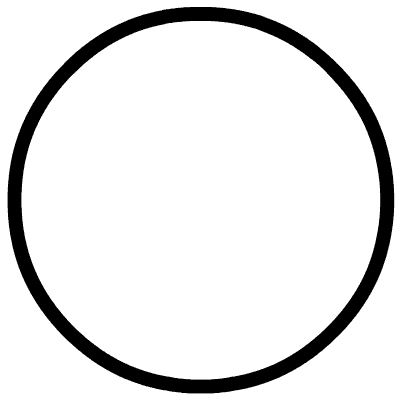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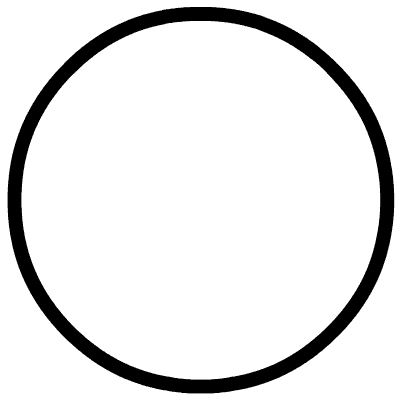
关键词
英国
音乐
就是
甲壳虫乐队
利物浦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