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发福比亚迪,还能朋克得起来吗?丨超级工厂·华南


编者按:36氪最近在深圳成立了第二总部,以内容先行的我们也开通了36氪华南公众号。这是第三篇文章,也是一个全新栏目——超级工厂。
之所以要做超级工厂栏目,就是因为最近三年,中国制造业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在下一个高端制造时代再立潮头,激发了行业从业者的思考。在此特殊转折点,36氪想通过这个栏目深入到中国最先进工厂一线,挖掘出中国供应链的独有价值。给所有投资人和创业者一个新思路参考,从而一起携手深耕供应链,助力中国创新!第一期选择企业为比亚迪,除了其股价在一年时间涨了5倍之外,更重要的是比亚迪背后有手机、汽车、半导体、光伏等复杂产业链,更能一窥全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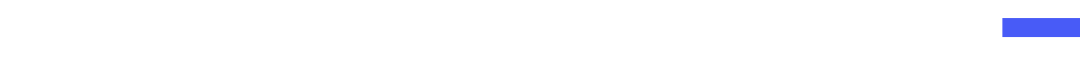
编辑 |彭孝秋
封面来源 | IC photo
2020年4月21日,《财富》杂志公布“全球最伟大25名抗疫领袖”榜单,其中共有3名中国人入选,分别是位列第1位的李文亮、第3位的马云、第19位的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
上榜的两位企业家中,马云被评上是因为他向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捐赠了逾1亿件物资,而王传福是因为他最先组织企业大规模生产抗疫物资。所以,《财富》杂志把王传福排在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前面。
去年疫情爆发之后,口罩、消毒水等防护物资一时成为紧缺产品。在那个无法正常复工的春节里,由于口罩供应链上游停产和需求量暴增的双重推动,“一罩难求”也拉高了疫情紧张气氛。比如口罩里重要组成部分的熔喷布,价格瞬间由2万元/吨飙涨至70万元/吨。
2020年1月31日凌晨,还在海外出差的王传福,就在高管群里宣布了两周内要实现口罩生产的决定。这项决定不仅让比亚迪免于遭受疫情后经济下行的重创,还带来了比亚迪电子2020年一季度同比增长69%盈利。

无独有偶,不管是出于道义还是生意,疫情之后跨界造口罩的车企不止比亚迪一家。比如广汽、陕汽、上汽通用五菱等也都纷纷加入了造口罩阵营。那么,为什么最后上榜的只有王传福一人呢?答案就藏在产能里。
按照比亚迪公开的口罩产线进程来看,比亚迪完成了3天出图纸、10天正式量产的速度,也调动了8万工程师。到了3月,比亚迪口罩日产可达500万只;5月,产量暴增至5000万只/天。在最终公开的数据中,比亚迪口罩日产能最高可达一亿只,而当时全国每天的产能只有2000多万只。
增长和迭代的速度肉眼可见,比亚迪方告诉36氪,在布列整齐的100多条口罩生产线中,前21条产线最为特殊,每一台都是一个新版本。对应的产能也从原先日产不足50万只,到逐渐保持每日30-50万只速度增长,进而仅用三个月时间,就从毫无经验变为全球最大口罩制造商。
不可否认,汽车行业本身就有“大制造业”优势,口罩生产需要的聚丙烯材料和无尘环境也和汽车生产的“涂装车间”相契合,这是车企可以造口罩的先天优势。但也有瓶颈存在,比如“汽车生产的部件是硬质的,而口罩则是软的”,处理软质的口罩材料需要很多细节,这就成为制约产量的瓶颈。
不过,从最终结果上看,如果说黑天鹅事件是对传统制造业的突击大考,那么比亚迪以传统车企身份,向自动化转型交出了一份具有自身特色答卷。而这份答卷背后,藏在比亚迪生产力中的奥秘是——在智能化、自动化、碳中和时代浪潮之中,比亚迪全方位、多元化、智能化“超级工厂”阵营,囊括了比亚迪长长的产业链,不断革新的自动化设备和传统制造业独有的匠人精神。
比如,一条口罩机生产线,涉及的各种齿轮、链条、滚轴、滚轮就需要1300个元器件,而其中90%都来自比亚迪自制。此外,比亚迪也是用加工高端精密产品的设备去加工口罩机,所以做出来的精度、质量各方面都远高于口罩本身要求。这自然就归功于比亚迪的几万个加工中心,有各种各样的磨床、模具等高精设备,以及从创立初期保持至今的制造积累。
如果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只能反映出当下“时间点”制造力,那么放到更宏观层面呢?也就是把“时间点”拉长成“时间线”,应该如何定义新时代的大国制造,比亚迪在用超级工厂给出自己的回答。


2007年,受大环境影响,比亚迪遭遇巨大压力,股价从70多港元一路下跌到7港元多,市值缩水10倍,PE(市盈率)也只有2倍。
投资人的大面积抛售情况直到2008年9月29日才发生转折,在那一天的香港新闻发布会上,曾被认为是巴菲特继承人的戴维·索科尔公开宣布,他们一直在跟踪中国优质项目,投资比亚迪是进军中国市场的开始。
这笔投资由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子公司中美能源控股承担,投资金额为2.3亿美元,占比10%。股神的背书震惊资资本市场,仅在三个交易日内,比亚迪股价涨幅就高达99%。自此,对于比亚迪的热议程度和股价关注度久居不下。
股神为什么要投资比亚迪?特别至今都未对比亚迪作任何减持动作。在外界看来,2003年才进军汽车行业的比亚迪无疑是个年轻中国车企,与国外的宝马、奥迪、奔驰、别克等百年车企相比,那时的中国汽车普遍被认为缺乏历史积淀和制造基础。
毕竟,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汽车就已有“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公司鼎立,欧洲厂商也以产品设计上的优越性出口美国市场,形成了欧美车企两霸并存的局面。而直到1984年,上海汽车和大众公司设立合作汽车厂,中国市场才开始生产轿车。
起步虽晚,但抵不住中国的高速发展。所以很快在20世纪初,就迎来了变量,中国车企也开始破局。
破局首先是得益于中国人均收入的增加,开始对个人汽车需求大增,全世界汽车新的增长点开始转向中国市场。也是在这个时候百花齐放,一方面是外资企业开始投资中国,设立合作汽车厂;另一方面是以奇瑞、吉利等民族资本为代表的厂家拔地而起。
其次是能源的影响。纵观整个汽车产业的发展历程,能源的多寡、价格高低牵动着汽车需求。比如在1973年、1979年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中,汽车需求就急速锐减,而日本生产的小型车也正是凭借着省油特点,受到国际市场欢迎。
事实上,在决定进军汽车之前,比亚迪只是一家电池厂商,但已占据了镍镉电池市场最大的份额。巴菲特在后来的一次采访时曾透露,比亚迪是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创新型公司,它在能源的使用上有自己见解。要知道,投资比亚迪时,巴菲特卖掉中石油不过一年。
股神没有判断错,比亚迪和同行差距正在不断被拉小。仅一年时间,比亚迪e6就问世,这也是中国第一台国产电动汽车。巧合的是,在新能源车发展初期,市场最主要的驱动力来自产业政策,B端市场是主要受益领域,这种优势一直持续到2019年。按照当时媒体报道,企业消费大约占新能源车销量的7成,私人消费贡献仅3成。
2010年2月26日,深圳巴士集团联手比亚迪,合作成立国内首个纯电动出租车公司——深圳市鹏程电动汽车出租车有限公司,深圳巴士占股55%,比亚迪占股45%。比亚迪e6的推出就直指出租车市场,不以盈利为目的,在深圳市作为出租车交付使用。
新能源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市场庞大的人口数量和率先在B端使用的商业化路径给了比亚迪更多尝试机会和产品打磨空间。所以,虽然特斯拉的王牌产品Model S、Model X要早于比亚迪投入市场,但直到2014年4月,特斯拉才正式进入中国市场。而那时的比亚迪,也开始逐步进入新能源车为主导的阶段,随后相继推出王牌产品王朝系列和e系列产品规划。
新能源车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后,比亚迪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品牌阵营,以2020年来说,比亚迪共有25款主要在售车型,覆盖了55个价位段。同时,以比亚迪汉为例,也有搭载了DM-i混动发动机和刀片电池现象级产品出现,在性能上也和特斯拉的拳头产品不相上下。
在今天的B端市场上,比亚迪早就提出了7+4战略(其中“7”为私家车、出租车、城市公交、道路客运、城市商品物流、城市建筑物流、环卫车;“4”为仓储、港口、机场、矿山专用车辆),印有BYD logo的出租车、公交车在深圳大街上随处可见;
C端市场也用数字说话,根据乘联会数据,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前三名为比亚迪、上汽通用五菱、特斯拉,市场份额分别为15.3%、14.7%和11.5%。
事实上,在“软件定义汽车”的大浪潮席卷中,传统车企更是被动的与者,而非主动出击者,这种被动状态显得有些萎靡不振。首先是疫情之后逐渐下行的车市表现:2020年,全球汽车销量同比降低13.8%至7797万辆,而新能源乘用车全球销量达到了312.48万辆,同比增长41%。
其次,一个底盘四个轮子上的汽车市场也正发生着一场传统车企与软件、互联网公司们的主权争夺战。当车变为“电脑”,作为大数据拥有者的互联网造车们就抓住了数据重资产,而传统车企只能通过合作的方式参与转型,沦为“互联网车”的工具人,眼看他人高楼起。
而同样作为传统车企的比亚迪则不同。一方面,它没有被后浪拍在沙滩上,成为自动驾驶玩家们的车架子;另一方面,它也并没手握数据来体现创新性。当消费者们谈及比亚迪新能源车的竞争力时,通常会提到混动发动机DM-i和刀片电池——这正是能源变革过程中最难攻克的技术环节。
所以,比亚迪创新仍在于制造技术本身的突破。
以比亚迪自主研发的混动DM系统为例,其最新的一代DM-i系统更新于今年1月,高性能取向向低油耗、强NVH(噪声、振动与声振粗糙度,是衡量汽车制造质量的一个综合性问题)方面转变。换句话说,可以在实现更高性能的同时降低能耗使用,这也被认为是整个混动技术的发展方向。
而早在2008年,第一代DM技术就已经发布,当时就可以实现百公里加速时间比同级别燃油车快2-3秒还节能的成绩。如今13年过去、该技术已迭代了四次。这种经过时间沉淀的技术积累和制造能力,就形成了比亚迪牢固护城河。
如果用出生年龄来做个区分的话,它比新势力们更年长一些,胜在底层建设稳固;又比传统车企们更年轻一些,胜在敢于面对挑战。
2020年6月,J.P.Morgan发布报告《BYD becoming more of a tech stock than an auto stock》称比亚迪正越来越像科技股,而不局限于汽车股。正如巴菲特所说,正值壮年的比亚迪是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创新型公司。


如果只用车来概述比亚迪,明显只说对了一半。
比亚迪2020年年报显示,汽车、汽车相关产品及其他产品收入占比为53%,另外47%的的营收来自手机部件、组装及其他产品业务和二次充电电池及光伏业务,其中分别对应占比39%和8%。
毫不夸张的说,比亚迪几乎什么都能造。
在汽车产业链上,垂直整合的方向通常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这是因为,越靠近产业链上游的厂商,往往掌握着更难以突破的技术,也就占据着更强话语权。但事实上,更大的利润和议价空间实际上在整车与消费者之间。
举例来说,在新能源汽车投入市场的早期阶段,什么样的车会热销主要看补贴政策,这也就更近一步决定了市场会使用什么样的动力电池产品。比如国产特斯拉Model 3必须搭载低价位的磷酸铁锂电池才能挤进30万元的补贴售价上限。在这个阶段,电池厂商的成本控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随着产业链逐步走向成熟,产品定价权就转移到了靠近C端的车企手中。按照2017年的数据,在传统汽油车产业链中,汽车企业的净利润几乎为零部件企业的4-5倍。所以,当下游厂商获得较为稳定的市场份额后,往往会对产业链上游高附加值的环节进行垂直整合。
比如,韩国现代集团在汽车业务发展10年后创立了从事汽车零部件业务的现代摩比斯,丰田旗下从事汽车零部件业务的电装及爱信精机比汽车业务晚来16年,特斯拉宣布自研自产4680电池、长城自研蜂巢电池等等,都是自下而上的整合。
但比亚迪是个特例。2003年1月23日,比亚迪以2.7亿元的价格收购了西安秦川汽车有限责任公司77%股份,正式进军汽车市场,成为继吉利之后的国内第二家民营轿车生产企业。而在此之前的八年中,比亚迪的主业一直都是电池,它因在镍镉电池上的制造能力被称为“电池大王”,直到2020年,比亚迪仍以14.9%的占比排在了全国动力电池装机量第二位。
站在今天回看,从电池延展到整车是个聪明的做法,它占据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的两个重头戏。但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秦川汽车除了执照,其实啥也没有。按王传福所说,当年为了进入汽车行业,比亚迪购买了50多辆全球二手车进行拆解。
就在决定进军汽车行业的前一年,比亚迪还全资收购了北京吉普的吉驰模具厂,也就是后来的比亚迪模具,开始生产用于汽车制造中必须的模具。同年,比亚迪电子公司的前身开始运营,主要为手机制造商制造和销售手机元件(主要包括手机外壳及手机键盘)及模组,以及提供组装服务(包括高水准组装服务及印刷电路板组装服务)。
可以说,从产业链上看,比亚迪在进军汽车行业之前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以,如果说宁德时代、特斯拉等是单项冠军,比亚迪更是全能选手。这种垂直整合能力一直延续到今天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中,上游的锂矿等初级材料供应链;中游的电池制造、电机、电控、IGBT等;下游的各种生产销售供应链等,比亚迪都有布局。

一句常被业内用来评价比亚迪垂直整合能力的原话是:“除了汽车轮胎和玻璃,比亚迪几乎具备所有核心零部件的自主研发生产能力。”王传福自己都曾公开表示:“既能做电池,又能做电机,还能做电控的车企,目前全球也就只有比亚迪。”
也就是说,在比亚迪长长的产业链上,几乎只要拥有原材料,比亚迪就都可以自己操作。这同时也意味着,在比亚迪的工厂中,产业链变的很短、供应链变得更加一站式,帮助比亚迪形成了具有持续生产质优价廉汽车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保证汽车产品原料价格低的情况下,也能比其他工厂更加高效。
但是,比整车制造更为重要的是,比亚迪能造的还更多。2018年起,比亚迪的各零部件业务从向母公司供货为主开始走向了开放的战略。据媒体报道,比亚迪先是打破垂直整合体系,拆分动力电池业务、让一些零部件、车载软件、模具等部门独立运营,也开始引进外部供应商。后在去年成立了五家”弗迪系“子公司,即弗迪电池、 弗迪视觉、弗迪科技、弗迪动力和弗迪模具,分别从事动力电池、车灯、半导体、底盘、模具等业务。此外,比亚迪半导体也启动了上市的进程。
尽管这些业务的最大客户仍是比亚迪母公司,但开放战略之后,来自比亚迪制造的覆盖面将变得越来越大。最新进展是来自竞争对手特斯拉,按照8月5日媒体报道,配有刀片电池的特斯拉车型已进入C样测试阶段。
今天,在比亚迪的工厂中,也加入了MES\AGV等先进技术赋能,但对于比亚迪大而全的制造底座来说,先进技术更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碳。超级制造的定义更在于经年累月不断积淀之后的自身底气,这种“什么都能造”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这才是任何工厂都难以直接抄的作业。


如果可以穿越回10年前的比亚迪工厂,感受就会是“很不现代化”。
当时的一则报道写道,很多人在参观了比亚迪的生产线之后,不以为然,“这太落后了,人家一汽、二汽,生产一辆汽车是以分钟算,可比亚迪却要按小时计算,压根不是一个层面的对手。”比如,在比亚迪一条600多米的生产线上,就有近百名工人忙碌,其中一些人的工作可能简单到仅仅是拧紧一个螺丝。
人海战术、逆向研发,看似是笨方法,实际上却是比亚迪能够在早期打通市场的关键。因为在当时环境下,低价一定是顾客购买力的敲门砖。如何降低成本?使用人力肯定比购买自动化设备低,并且人力不仅可以保证产品质量,还可以实现更低价格优势。
以电池产线为例,在逆向研发方式下,王传福通过拆解同行全自动电池产线,最后重建了一条由100多道工序组成的人工生产线,把原本上千万的生产线成本降低到不足100万。
但在今天,“人丁兴旺”并不一定意味着成本节约,因为人的价格越来越贵了。
这一方面是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物质需求增加的双重作用下,劳动力资源变得越来越紧俏;另一方面,在中国,随着政府对科研支持的加大,市场资金对创投领域的兴趣日益高涨以及居民教育水平提高。人口红利虽在下降,工程师红利却开始崛起,原来工厂里的蓝领也更愿意去研究所和实验室。
瑞银中国证券研究主管侯延琨就曾在采访中表示,“中国每年大学理工科的毕业生数量超过300万人,为美国的五倍,而与此同时,中国研发人员薪资仅为美国八分之一左右,这种‘工程师红利’可以弥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所带来的影响。”
这一趋势也将在制造业中有所体现,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指出,科技将对传统制造业进行赋能和改造,未来10-15年中高端制造布局逐渐显现,中国经济发展结构方向将迈向产业基础的高级化和产业链的现代化。
这样的趋势和比亚迪此前靠人力堆砌的生产方式几乎完全相反。从比亚迪如今的22多万员工数量来看,似乎并没有告别“人海战术”方法。相比之下,去年汽车总销量约为比亚迪4倍的吉利,员工人数仅约为比亚迪三分之一。
不过,做自动化并不是做“减法”,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加”。
在比亚迪深圳坪山工厂总装车间工作了11年的一名管理人员告诉36氪,从2015年开始,这条一直用来汽车总装的生产线开始配备MES/AGV/机械手等自动化设备,与之前没有自动化的产线相比,更大变动不是工人数量减少,而是增加了产线的效率和更能符合客户需求的定制化、灵活化效果。
同样,在自动化程度更高的比亚迪电子,其第一事业部总经理江向荣也表示了相似的观点:“自动化”最直观体现是在产值增加的同时,员工数量并没有增加。如今,比亚迪电子的车间内已经很少能见到工作人员身影,一个车间配有2500台CNC数控机台,755组机械手,每天可以加工10万片手机金属器件,无人驾驶的自动化小车(AGV小车)在承担着运输工作,并且车间联网率超过90%。2015年仅为200多亿的比亚迪电子产值,2018年已经达到了400多亿。
对于以比亚迪为代表的传统企业来说,自动化变动并不发生在朝夕之间,当“人丁兴旺”的比亚迪带着大而全的身躯奔向智能时代时,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其一,在自动化的趋势下,如何找到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去变革,做技术叠加,而不是技术赋能,才是保持创新性的根源问题。
其二,对于比亚迪来说,大而全的另一面是,当公司业务量变大,内部沟通成本通常会高于外部。那么,如何用新兴技术做好人员、资源、业务的整合管理也是新课题。
当然,这些问题的答题人并不只有比亚迪,还有中国供应链体系的构建者——一个个新兴或老派的超级工厂们。
20世纪初期,当科技的触手开始向各行各业蔓延时,曾有人用“向传统产业剥洋葱”来形容科技不断渗透的方法,即一步一步缓慢渗透,从单个客户开始,到最后占领所有客户,这就是“剥洋葱”全过程。这个过程也被认为是传统行业不得不被动接受变革的过程,想要不被加了“.COM"和".AI"的浪潮拍在沙滩上,主动拥抱科技变革是传统行业的必由之路。
但比亚迪似乎永远年轻,永远跑在前面。
2008年,比亚迪提出了“三大绿色梦想”,即光伏、电动车和储能,表达了“从能源获取、存储到应用,摆脱对化石能源依赖”的预期。这里面有个大背景是,据王传福透露,中国72.3%的石油依赖进口,其中的70%又从马六甲海峡海运回来。此外,交通用油占了70%。所以新能源发展迫在眉睫。
对于可能是人类未来储能大产业的光伏,早在2010年,比亚迪太阳能组件就被安装到美国土地上;还有对于轨道交通的畅想,可以不单独占用路面、建设在道路中央分隔带或狭窄街道上的云轨,早在2016年时比亚迪就已经开始规划设计。
如何定义年少?不一定是后起之秀,或更是在有了制造基石的沉淀之后,明确了解自身需求、并愿意接受技术赋能的创新派工匠精神。如果少年爱做梦的话,比亚迪恰巧有个梦工厂。在制造基石与前沿技术能够合二为一的工厂中,我们也可以肯定的称它为“超级工厂”。
聊了这么多,下方转场,跟我氪一起沉浸式体验比亚迪超级工厂

36氪旗下华南官方账号
真诚推荐你来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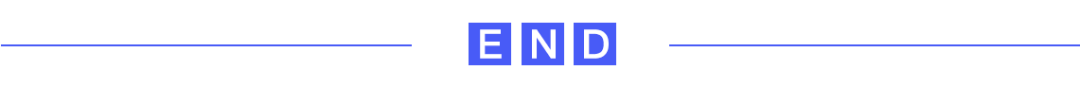


来个“分享、点赞、在看”👇
仅靠自动化炫技还称不上智能制造
阅读原文 关键词
比亚迪
电池
王传福
产品
特斯拉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