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竟然闯进了一个灵异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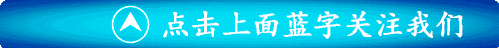
【留美学子】第2372期
7年国际视角精选文摘
教育·人文·名师·媒体生态圈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前言

农历七月,是我国民俗传说中的“鬼月”,特选1992年我在北京遇到的灵异事件。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许多读者讨论;然而还有后续的奇异事件发生…
直至2020年出版《戴小华文集》时才补上。感兴趣的朋友请慢慢看。

《闯进灵异世界》
作者 戴小华

罗素曾言,你知道的是什么?这是“科学”。你不知道的是什么?这是“哲学”。
我不晓得,自己遇上的“这件事”到底是什么“学”?
我相信唯物论,从不认为有所谓的“灵异世界”,但我却在这次旅途中遇到一件“诡异”的事,至今仍不明。
那年十月中旬,我刚游完长江三峡和四川峨嵋山,深秋,又回到北京。
走进预先订好的饭店,到柜台登记时,服务员面带笑容地说:“很抱歉,客房全满,只剩一间豪华房。我们安排你住进这间房,但不加房钱,请到10楼的服务台登记。”
上了10楼,办理好住房手续,服务员交给我一把钥匙,房号是1057。这号码依照广东人的发音,意头不太好,可我不信这些。
虽不信,一开门就不顺。任我如何转动门匙,始终打不开房门,最后服务员拿了 Master Key才将门打开。
待行李一送进房,我就迫不及待去古董市场寻宝。
在一间古董表店,见所有表只标价三四百人民币,惟独一只表标价人民币三千八。我惊讶道:“为何这么贵?”店主解释:“这是14K的欧米茄金表,所以特贵。要买,就买这只,才是最好的投资。”
我再三考虑,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终以人民币一千八成交,心想:如是仿冒,损失不算大,是真的,就捡到便宜货了。
回房后,人已疲倦万分,梳洗完毕,再检查一下门锁,确定安全,倒头就睡了。睡着睡着,“诡异的事”来了。我感觉到“身后有人!”随即,那人用手从我头部沿着脊椎骨婉蜒摸到腰部。我动也不敢动……叫也不敢叫……以免惊动他,使自己受到伤害。心想:“可能他在摸我身上有无佩带贵重饰物。”
那人在毫无所获下,“走”到落地窗前,侧身而立。这时,我才敢以眼角余光扫瞄。那男人朦朦胧胧,像是裹在雾气里的模糊人影,形象并不是十分清楚。他的表情木然,我无法由他脸上看出真正的意图所在。他身上的穿着却是六十年代的。
旋又细想:“不可能呀!房门反锁上了安全扣,窗是封闭的,这么高的楼,贼是绝对进不来的。”
那么进来的又是什么?
接着,脑电波似乎发出这样的讯息:“这是梦。既是梦,就得赶紧自梦中醒来。”
我想睁眼,但睁不开,想动,只觉得身上有千钧般沉重,丝毫无法动弹。
我挣扎了又挣扎,挣扎了又挣扎,努力一寸一分地使劲睁开似乎被胶水粘住的眼皮……终于,我睁开了眼。
往房内四望,空旷旷的,毫无一人。
我起身,移步窗前,打开窗帘,遥望下去,街上闪烁着零星的车灯。再检查屋内四周,一切正常,也就不多想“其他”,继续睡眠。
第二天出门前,先将护照及贵重物件(包括新买的旧表)放进饭店内的保险箱,才去探望萧乾夫妇。一年多不见,他俩仍是神采奕奕,目前正忙着翻译一本巨著,与他俩畅谈了一个多小时,即告辞。


在萧乾夫妇北京家中合影
下午到什刹海公园拍照。这里虽非观光点,但景色美得出奇。令我惊讶的是,池边垂柳尚在婆娑摇曳,满地却已压着一层金黄透明的落叶。几个孩子在收集落叶,我也情不自禁捡起几片。我喜欢秋天的绚丽灿烂,秋叶的美丽,和我所体验到的情味,使我不会为它的凋落而伤感,因为它们选择在生命最美好的时刻告别人世。
在我眼中,北国的秋叶,实在要比早些日子装点街头的上百万盆鲜花更有韵致和意境。

晚上,巧遇从美国来的平路。她来北京收集资料,准备写一本重要人物的传记。与她同进晚餐.并相约第二天共游香山公园。
早听说香山红叶是北京最浓最浓的秋色。每年雨季过后,进入凉爽的秋天,游人便如潮水般涌去观赏那“京华秋色好,香山叶正红”的美丽景致。
当晚,早早入睡,没有任何“状况”发生。

北京十刹海公园的秋叶
隔日清晨,赶赴香山。到了乘缆车登山处,已有许多比我们更早的游人在那儿大摆长龙。
坐上缆车,居高临下,俯瞰园内一片柿树,简直像一片火似的,红得煞是好看。
缆车缓缓往上滑动。朝西一望,山坡上满布红叶,半黄半红的,可惜还没红透,要是红透了,太阳一照,那颜色该有多浓。再往上就是香山最高峰“鬼见愁”。这里有两块大石,状如香炉,在阳光照射下,岚光袅袅,似有几位高香在燃烧,故此山称香山。

与台湾作家平路在香山最高峰“鬼见愁”的大石上合影
下山到香山饭店浏览,进入贝聿铭设计的一处富有明代情趣的小型庭园。园中心有个小池,池旁栽满了不知名的花木,它们经了秋阳的熏染,经了秋风的吹拂,呈现出各种色彩。有鲜明如玛瑙般的红,有娇艳如油菜花般的黄,也有青翠如玉石般的绿。总之,我们行走其间,已经不像现实的人,而变成了山水画中点缀的人物。
见时间还早,我们又去明十三陵。但我们去的不是游人如鲫的长陵和定陵,而是去已发现但还未修复的献陵。这里人迹罕至。当那一大片废墟呈现在眼底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历史忽然倒退到了明代。而在乱石衰草中间,仿佛浮现了一大群被鞭笞的奴隶,正在此赶建着明仁宗的陵墓。

献陵
我在这样一座废墟中徘徊,千思万绪兜上心来。自古以来,封建帝王就崇尚厚葬。秦陵出土的兵马俑,以及那座巨大的地宫坟山就是个证明。从明代起,还形成了这样一个传统:谁的权势越大,在位时间越长,就越是喜欢在生前早早为自己兴建陵墓,不惜劳民伤财。明前期四个皇帝;洪武、永乐、洪熙、宣德,甚至强迫后宫嫔妃、宫人太监殉葬,经营死后的安乐窝。野蛮至极!
现在我对着破墙残碑,怅然凝望。
风在树林中呼啸,忽高忽低,如泣如诉,仿佛对我说:过去皇帝抢了天下,把自己监禁在宫中,把一切宝物聚在身边,以为他是富甲天下。然而,过了一代又一代,到头来曾被列为禁地的陵墓,仍是被偷、被盗、被挖掘,最后依旧还诸天下,还落个死无宁日,这岂不是既可悲复可笑么?
返回饭店,取出保险箱的东西,理好行李,即上床就寝。
不多久,感觉有人进房。我眯着眼,借着昏暗灯光,模模糊糊看见“一男一女”,约莫三十多岁。“男的”仍是先前的那位,站在同样的位置,连表情、服装都与前晚一样。“女的”则站在床尾右侧角,中等身材,身着浅米色缀小红花的衣装,也是六十年代的服装款式。头发短又鬈曲,那脸……天啊!竟是张“阴阳脸”(面部中分,一边为黑,另一边为白)。“她”微微牵动着左半边脸的嘴角,似笑却又显出无限哀愁。“她”静静站在那儿,眼神望着落地窗前的“男人”。
我屏息凝气,像个偷窥的第三者。气氛就这样凝固着。
突然,门外有急促的打门声,接着是撞击的声音。声音愈来愈猛,门快被撞开了,这下,我慌了,赶紧跳下床,抓起电话,猛按“0”,对着总机大喊:“救命!”正喊着,门被撞开,一位五十多岁的矮胖妇人冲进来。危急中,突又想起:“不可能,门锁得好好的,绝不可能有人进得来,一定又是梦,得赶紧醒来……醒来……
又是一番挣扎,终于张开了眼。惊醒后,房内仍是空无一人。除了冷气机的响声,自己的心跳声,真可说是“万籁俱寂”。我想自己又做了场噩梦,当时也不在意,倒头又睡。
第二天一早搭机自北京飞往上海。到上海的那晚,王安忆、李子云、王小莺到我下榻的饭店房内聊天。我向她们叙述了北京所梦。
安忆首先发言:“我觉得你第三晚的梦是第一晚梦的延续。头晚‘男’的来寻找‘他’的爱人,结果发现你不是‘她’,就站在窗前静候。后来你醒了,梦也断了。”安忆的表情既严肃又认真。她续说:“第三晚的情节,让我感觉一桩惨案发生了。不是情杀就是殉情。不过真正让我不寒而栗的是那‘一男一女’的静默,还有那‘女人’露出的一抹悲凉的笑意。”

1992年拜访上海市作家协会与王安忆/李子云/王小鹰合影
“按理是日有所见,夜有所梦。但你偏偏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做这样的梦。”小莺寻思道。
“这房间一定不‘干净’。”安忆语气肯定。
“是呀!那是饭店最后的一间空房,可能以前的住客也有类似的经验,所以饭店只有在全满的情况下,才会将此房租出。”小莺接着说。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如人惨死,像自杀、车祸之类的,他的魂魄就会一直飘荡在出事的地方。”子云又说:“这种人就像判刑一样,天天都在原处死一次,永远都重复。”
“或许白天你去荒无人烟的陵墓,沾了些阴气,于是你的脑电波能与‘他们’感应,在梦中,就闯入了‘他们’的灵异世界了。”
“这就是处在同样的‘空间’,却跨越了不同的‘时间’,于是你就在梦中目睹着这场‘时空交错”的情节进行着。”
“可惜你急着醒来,不知后事如何?”
大家你一言我一句地猜测着,她们三位不愧为享誉中国文坛的名作家,极富想象和推理的能力。就接受她们所推论的理由,否则我还能找到什么更好的解释?
返回吉隆坡,将表拿到店里查验,顺便配条新表带。店主将表壳拆开,用十倍的放大镜细看。突然他说:“表内有一行刻得很细的字,字迹歪歪斜斜,定是那时的表主用细针自己刻上去的。”
“刻些什么?”我既兴奋又好奇地催问着。
“‘1965年10月14日洁?头200,表距今不止二十七年,中国解放后,不可能再有外国名表进口,照表的款式绝对是1949年前的产品。”店主又说:“1965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戴这种表的人,不被视为走资派,惨遭批斗才怪。难怪表主不敢送到表店用机器刻字。”
“‘文革’时惨死的人、自杀的人就成千上万。”我叹道。
“这样名贵的表,又刻上字,定是极心爱之物。既如此刻骨铭心,人死,有时‘魂魄仍在’。”店主摇摇头接着说:“我曾经有位顾客在一家古物店买了一只光泽极美的蓝宝石戒指,当他戴着那粒蓝宝石入睡时,晚上就有‘异样’发生,不戴,就没事。”
综合许多“事件联想”,我突然有了一个较清楚的轮廓:出现在我梦的“人”,不都是六十年代的装扮吗?第一天买了这只表,当晚“怪梦”就来了,第二天将表放进保险箱,没任何‘状况”发生,第三晚从保险箱拿出来,“怪梦”又来了!
表是否与梦有关?
可能答案一辈子也找不出来了。其实人世间只有问题,没有答案的事情很多。然我始终秉持一种想法,那就是人只要不做亏心事,世上没什么好怕的。只是当我戴着这只表时,始终有着一种挥之不去、招之即来的戚戚之情,总觉得自己像个掠夺别人心爱物件的人。如今表已随我漂洋过海,魂魄再难追随。
或许有一天我会戴着这只表再回到那间1057号房,续我未完的梦,解我想不透的谜。
(1992年完稿)

后续
自从《闯进灵异世界》一文在1992年发表后,引起很多朋友的好奇和议论。1993年第三届“海外华文女作家会议”在吉隆坡举办,世界各地来了许多女作家。会议结束后,旧金山来的女作家翔翎在我家留宿几天。
她非常好奇想看看这只亚米加金表,因自配好金表带,我就将表放在保险箱,从未带过。既然她想看,我遂将这只表自保险箱取出,当晚就带着表和她一起出席友人的乔迁之喜。
晚饭过后,她问我几点了?我将左手伸到她眼前,将表轻轻挪正,好让她看清时间,结果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表带突然断开,整只表摔在了地上。翔翎觉得这表有些邪,劝我以后别带。然我一向不信邪,认为可能是珠宝店没将新做的表带和表焊接好。第二天我将表拿到珠宝店修复。
店主将表重新拆开,这次用更高倍数的显微镜里外仔细检查一遍,突然告诉我,上次说表里刻的“200”,这两个0是写在2的右上方而且字体较小,那么,应该是时间符号,代表凌晨两点,而原先看不清楚的字“其实是“洁砍头”,也就是说拥有这只亚米加金表,叫“洁”的姑娘在1965年10月14日凌晨两点被砍头。他接着又说,因金表年代已久,表缘上的金已氧化,如再焊接,表可能会变形,他店里的师傅不具有这种精湛的手艺,只有等香港的师傅来时,请他处理。于是表就留在了珠宝店内保险箱内。
之后,我曾询问过几次,店主告知,来过的香港师傅都不敢处里,怕做不好要担负赔赏责任,于是表就一直留在珠宝店的保险箱里。
后来我因事物繁忙,忘了询问,直到三年后,我再打电话给店主,电话已停。我遂前往珠宝店,没想到,珠宝店大门紧闭,已被法院查封,店主也不知去向。当然那只金表也就下落不明了!
(2020年补续)

戴小华作品 延伸阅读


祖籍河北沧州,生在台湾台中,定居马来西亚吉隆坡。80年代中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工作,至今35年。在马、中、台结集出版的个人专著有《因为有情》、《忽如归》、《沙城》、《深情看世界》、《永结无情游》等25本;编辑出版《当代马华文存》、《马华文学大系》、《金蜘蛛丛书》、《海外华文女作家自选集》等65本。
她有许多作品被选入中国和马来西亚中学及大学的教科书内,并在马、中、台荣获许多重要文学奖。在马来西亚是一位具有国内和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界领导及作家。
戴小华曾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总会长,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长,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会长。现为世界华文文学联会副会长/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会副会长/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永久荣誉总会长/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务顾问/中国东盟协会文教发展委员会主席。


【留美学子】近期发表

喜欢就点个好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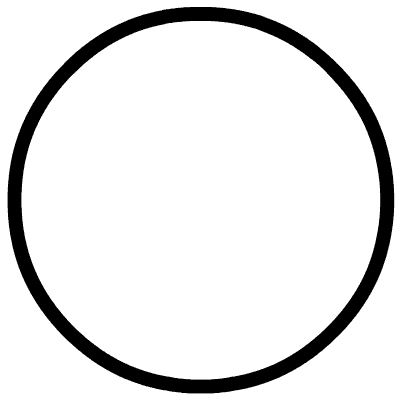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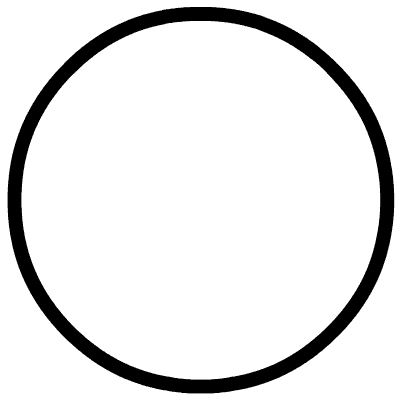
关键词
饭店
会长
华文
北京
保险箱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