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的双子星”:一段塑造现代文明内核的友谊



位于苏格兰高级法院大楼前的休谟雕像
“苏格兰的双子星”:
一段塑造现代文明内核的友谊
1776年夏天,当大卫·休谟病卧床榻行将离世时,特威德河两岸的很多英国公众都翘首等待他去世的消息。在之前的四十年里,休谟的著述时刻挑战着他们对哲学、政治,特别是宗教的信仰。在他走过的这几十年岁月里,虔信之徒们不断谩骂和攻讦他,苏格兰教会一致同意开除他的教籍,但是现在,他们拿他再也没有办法了。
每个人都想知道这个臭名昭著的异端分子如何面对生命的终结。他是否会悔恨,甚至放弃他对宗教信仰的质疑?他是否会在没有来世信仰的支撑中痛苦地死去?休谟去世这件事和他生前的种种一样,具有很强的幽默色彩,却毫无宗教色彩。他的离去平静而勇敢,他的好朋友亚当·斯密记录了这个过程。

无愧于神圣而可敬的友谊之名
仇恨和争吵总是比友谊更容易描绘:冲突具有戏剧效果,而友情则司空见惯。这或许正是休谟和斯密之间的友谊没有得到足够分析的原因。由此推论,关于哲学冲突的书比比皆是,而关于哲学友谊的书却少得可怜,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甚至于连休谟的传记作者都忽略了他和斯密的长期友谊,而去关注他和卢梭之间为时很短的疯狂争吵。说实话,这次争吵对休谟的生活和思想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哲学友谊经常被世人忽略,这不足为怪,但却是不幸的事。自哲学诞生之初,友谊就被认为是哲学和哲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只需草草翻阅一下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人们就可以明白这点。亚里士多德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一个人如果不能拥有友谊,那么即便他拥有其他一切,依然无法存活于世。
休谟和斯密明确表示认同这个论断。休谟认为“友谊是人类社会的主要乐趣”;斯密认为来自朋友的尊敬和喜爱,是“人类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休谟为此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来证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让自然的一切力量和元素共同服务和服从于一个人,”他说,“让太阳听从他的指挥升起和落下,大海和河流按照他的意愿流动,大地为他提供有用之物或他想要的一切。但他仍然会感到痛苦,直到有人愿意分享他的快乐为止。
哪怕只有一个人,他也能从这个人那里享受到敬重和友情。”颇让人意外的是,即便是在休谟的《英国史》中,友谊的概念也占有重要的分量。正如一位杰出的休谟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英国史》中,“友谊的能力……几乎是对一个人品性的决定性考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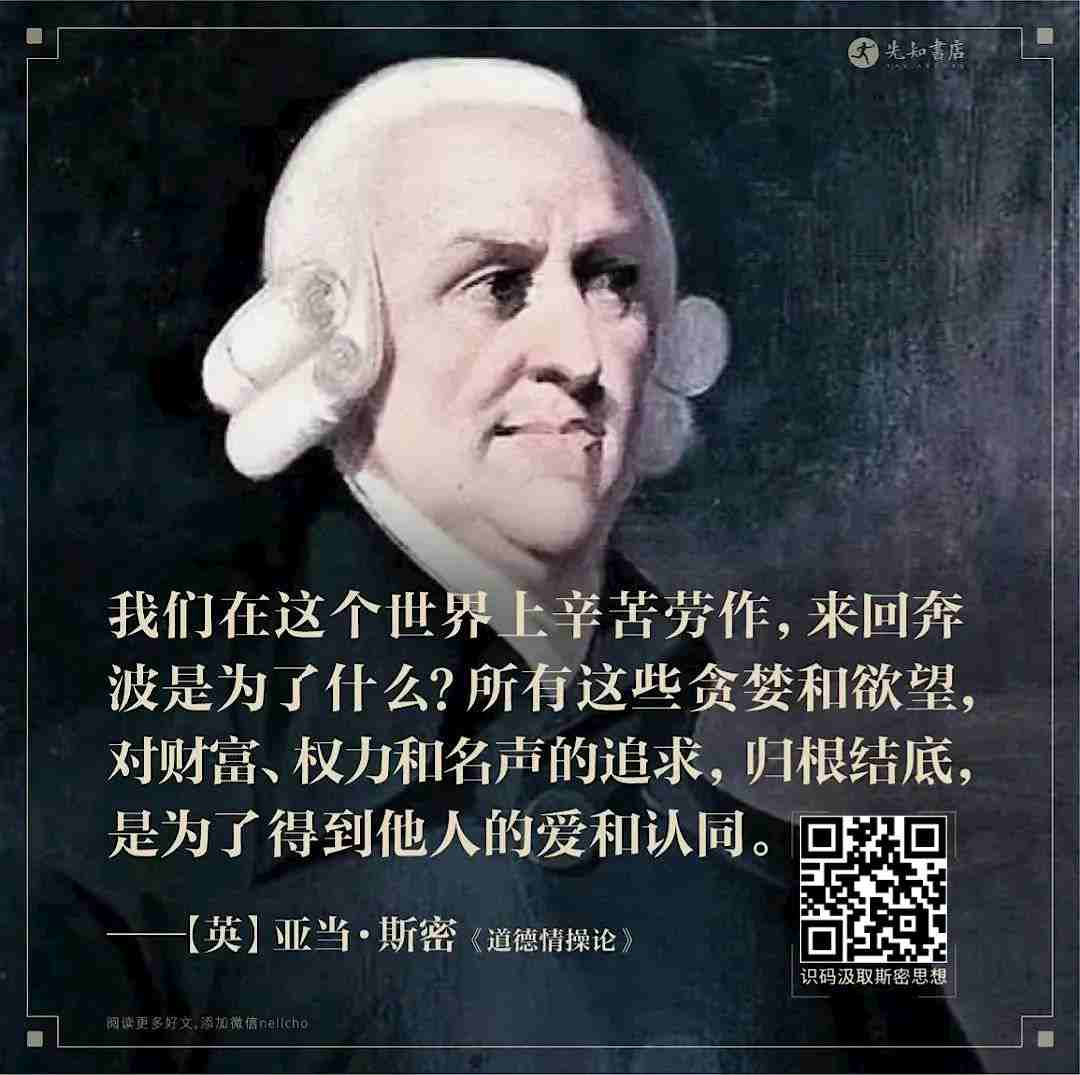
亚里士多德将友谊分为三类:出于功利的、乐趣的和美德的友谊,其中第三类是最高尚和弥足珍贵的。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他相信后者“无愧于神圣而可敬的友谊之名”。
斯密和休谟之间的友谊,堪称是对这样一种友谊的教科书式诠释:一种稳定、持久而互惠的纽带,不仅源于彼此的兴趣,或源于从对方的陪伴中得到的乐趣,也源于对崇高目标的共同追求,比如对哲学的探索。
研究休谟和斯密的私人情谊和学术关系,会让人们对友谊有不同的理解,超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米歇尔·德·蒙田和弗朗西斯·培根等人对友谊的论述。
这些哲学家通常对友谊进行抽象的概念分析,比如友谊的不同形式,它在人性中的根源,它同一个人的自身利益、同爱情,以及同正义之间的关系。然而,对休谟和斯密的考察,则会让我们看到最高层次的哲学友谊,这种友谊世间罕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研究案例。
事实上,回溯西方文化传统,再难找到更完美的哲学友谊的例子。如果挖空历史仔细翻查,也许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可以算作一对?但考虑到他们之间40岁的年龄差距,二人的关系更可能是师生关系,或者是导师和门徒的关系,这不能算是一种平等的友谊,更何况,他们之间的私人交流鲜有记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关系同样如此。
休谟和斯密的友谊产生的背景与他们的友谊本身同样出名。18世纪初,他们都出生在苏格兰。世代的贫穷、疾病、无知和迷信,以及持续不断的宗教冲突和间或的军事占领,曾经让这块土地饱受创伤。休谟曾经说,苏格兰一直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粗鄙、最贫穷、最动荡、最不安定的地区”。
但是,休谟和斯密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刚好是苏格兰经济和文化走向繁荣昌盛的转折期。那个时代生机勃勃的活力,甚至让当时的观察家也感到震惊。
休谟后来也感受到了苏格兰的变化,他在1757年对一位朋友说:“目前这个国家涌现出如此多的天才人物,真是让人佩服!”他说道:“在失去了我们的王子、议会和独立政府,甚至失去了我们的首要贵族之后,我们民气消沉。我们说着一种落后的方言,语调和发音奇怪而突兀。在这种艰难情形下,我们竟成为全欧洲在文学上最杰出的民族,这难道不值得世人惊奇吗?”

“那是个伟人辈出的时代”
19世纪初期,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在回首休谟、斯密及其同时代人时说:“那是个伟人辈出的时代。”注意到这一现象的不仅仅是苏格兰人自己,当时可以算得上最开明的英格兰人爱德华·吉本,也在1776年承认,他“总是怀着最诚挚的敬意,来看待不列颠岛的北部,品位和哲学似乎已经从这座充满烟雾和繁忙的都市退场,而走向了那里”。
苏格兰启蒙运动是思想的黄金时代,可以同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和文艺复兴后的意大利相提并论。
甚至有一本畅销书的书名就是《苏格兰人如何发明了现代世界》。苏格兰“文人”迥异于法国知识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思想并不激进,更不会同当局和权贵唇枪舌剑,在民众中享有良好的声誉,是社会活动的深度参与者。
他们多数就职于大学、法律、教会或医学等有较高学术要求的领域。部分是因为这些原因,他们的思想普遍缺乏颠覆性的锋芒,而后者正是巴黎哲学家们的鲜明特色。当然,苏格兰文人中也有少数例外,首当其冲的就是休谟。

在苏格兰文人的思想大多中庸温和的背景下,斯密和休谟思想中激进的一面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一个在18世纪初期还贫穷落后的国家,为何在18世纪中叶一跃而成为智识强国了呢?
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包括教区学校的创新体系,该体系使苏格兰成为世界上文化水平最高的社会之一,也包括现已成为欧洲一流大学的位于格拉斯哥的那些大学,爱丁堡大学、阿伯丁大学和圣安德鲁斯大学,还包括许多俱乐部和辩论社团的出现,繁荣的出版业,以及思想进步、最终领导苏格兰长老会的温和派教长。
当然,1707年缔造大不列颠的联合也同样重要。自1603年王室联合以来,苏格兰一直没有独立的君主政体。
但18世纪初,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议会合并,使得苏格兰与强大的英格兰关系更加紧密,这就为苏格兰的安全和稳定,以及进入英格兰及其殖民地的市场,提供了保证。
苏格兰在讨价还价时放弃了大部分的政治权力,在新组建的下议院中,苏格兰只占据558个席位中的45席,但对本国的法律、宗教和教育机构保留了很大的控制权。
虽然实现议会联合花费的时间超过了支持者们的预期,但是联合最终还是带来了经济的蓬勃发展,伴之而生的是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机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苏格兰人都对这个新秩序感到满意,1715年和1745年的雅各布派叛乱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苏格兰最杰出的文人们却很少质疑这个联合,尤其是休谟和斯密。对于英格兰人对苏格兰的各种偏见,他们均表示愤慨,但对联合二人持欢迎态度。总而言之,休谟和斯密的友谊诞生于英国政治稳定期间。
事实上,在这个时期之前和之后都是动荡不安的时代,而他们的友谊恰好出现在动荡之间的稳定期。他们在1749年首次相遇,也就是在最后一次雅各布派起义的几年之后。休谟在1776年去世,正值英国与美洲殖民地冲突升级的开端。

在这一稳定时期,能称得上政治动荡的也只有与法国的七年战争(1756—1763年)以及18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威尔克斯与自由”骚乱。后者曾经令休谟深深感到震惊。
然而,与18世纪两头的大事件——光荣革命与1707年联合,以及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相比,无论从什么意义上来说,这些政治动荡都只能算是温和的静水波澜。当时的宗教环境也是这份友谊的助推手。光荣革命之后的1690年,苏格兰长老会恢复为苏格兰的国教,而英格兰则保留了英格兰国教。然而,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苏格兰长老会本身的特点和做法导致严重冲突此起彼伏。

“截然”相反与“深刻”相似
休谟和斯密的观点,在如此多的方面,有着如此广泛而深刻的相似性。考虑到这一点,二人对虔信宗教的同时代人所采取的截然相反的立场,就愈加引人注目了。
休谟比斯密年长12岁,又早早地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在斯密开始发表作品之前,他几乎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著述。从这个角度来说,休谟对斯密思想的塑造程度,应该远远大于斯密对休谟思想的影响。
当然,除了密友休谟的影响之外,斯密还从许多思想家那里汲取营养,所以斯密也被称为“伟大的折中主义者”,然而绝大多数研究斯密的学者都认为,休谟的影响在斯密著述中无处不在。
例如,尼古拉斯·菲利普森在其撰写的斯密传记中,称斯密是“忠实的休谟派”,甚至是“完美的休谟派”,其“任务是发展休谟哲学的含义,并将其扩展到他自己创立的领域”。然而,这并不是说斯密全盘接受休谟的观点。
恰恰相反,我们会看到他几乎改良了他所触碰的一切。研究斯密的著名学者塞缪尔·弗莱沙克尔真切描述了他们在知识层面的关系:“斯密的思想围绕着休谟的思想展开。
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到处闪烁着休谟的思想光辉,尽管斯密几乎对休谟所有观点都不会完全赞同。”弗莱沙克尔在别处也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说:“如果看不到斯密对休谟的尊崇,就无法理解他许多主要学说的来源。

而如果看不到斯密对休谟的修改,看不到他如何持续而执着地拒绝全盘接受休谟的东西,那就会错过斯密身上与众不同、也最有趣的一点。”
休谟和斯密两人思想之间,有深厚而广泛的亲近关系,但是一系列常见的简单化描绘掩盖了这种联系。
根据这些简单化的描绘,两人的思想存在这样一些差异:在研究主题方面,休谟是一个对抽象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问题感兴趣的哲学家,而斯密则是一个专注于俗世且务实的经济学家;在政治主张方面,休谟支持保守的托利党,斯密则支持自由的辉格党;在宗教信仰方面,休谟对宗教持怀疑态度,甚至算得上是个无神论者,而斯密则是虔诚的信徒。
这三个简单化区分中的第一个很容易反驳。休谟学术生涯的开端的确始于研究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问题,而正是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使得他至今仍然受到学院派哲学家的关注。
即使如此,在他的第一本著作《人性论》中,休谟已经从这些相当抽象的研究,转向了对心理学和道德的更具体和现实的讨论。此外,他还就各式各样的主题撰写了大量文章,从政治到一夫多妻制,从经济学到辩论术,还有一些关于宗教的论述,以及不朽之作《英国史》。
的确,不论是在休谟的年代还是后世,人们首先认为他是历史学家,其次才是哲学家。同样,虽然斯密经常被誉为资本主义“之父”,但是斯密的现代阐释者总是不厌其烦地指出,他实际上远远不仅是一位提出“看不见的手”理论和倡导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
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位道德哲学教授,而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他众多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分而已,而且他清楚认识到了商业社会潜藏的危险和弊病,其认识程度远远超过休谟。
斯密讲授伦理学、法理学和修辞学课程,并撰写了关于语言发展和天文学史等问题的论文。人们的视野一旦超越了休谟《人性论》的第一卷和《国富论》中最著名的几页,就会发现休谟和斯密两人的兴趣有大量重合,这部分是因为他们的兴趣几乎无所不包。
20世纪的很大部分时间里,斯密的哲学著述通常被认为不过是休谟思想的一系列脚注;而作为经济学家,休谟长期被视为斯密的一个不重要的前辈,更多时候会被直接忽略。

大卫·休谟(左)和亚当·斯密(右)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将两人的思想并置,斯密对道德哲学的贡献和休谟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斯密追随休谟,提出了基于人类情感的道德理论,但他的道德情操理论是对休谟著述中相关思想的完善改进。
反过来,早在《国富论》出版几十年前,休谟就已经在为自由贸易辩护,并且强调商业对道德、社会和政治的正面影响,而《国富论》里面借鉴休谟之处,简直多得让人惊讶。
上面提到的政治主张的差异也同样是误导。休谟的政治思想确实有其保守的一面,而斯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中的重要一员,但是反过来说也仍然正确:就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休谟也是自由主义者,而斯密的自由主义也有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
更具体地说,这两位思想家都拥护自由主义传统的核心理想,强调法治、有限政府、宗教宽容、言论自由、私有产权和商业活动。因此,总的来说,他们都赞成当时英国出现的现代、自由的商业秩序。
另一方面,他们都不信任政治上突发的重大变革。他们认为,鉴于人类理性并不可靠,加之政治世界复杂多变,我们应该时刻警惕企图彻底改造社会的宏图大业。
因此,虽然他们主张自由贸易改革,并提倡更多的宗教改革,但他们始终坚持认为,这些改革应该以一种渐进而有计划的方式实施。如此看来,斯密和休谟都不能用“托利党”或“辉格党”来简单标签:他们都不完全支持18世纪英国的任何一个主要政党。
苏格兰启蒙时代的一位知名学者从休谟的一封信中得到了证据,称他们二人都是“持怀疑态度的辉格党人”:说他们是辉格党人,是因为他们都支持光荣革命促生的宪法,认为该法为个体自由和安全提供了保证;而说他们是“持怀疑态度的”,是因为他们刻意回避了往往同辉格主义相关联的意识形态包袱。
因此,将他们称为“务实的自由主义者”也许更加名副其实,因为他们虽然拥护自由主义传统的核心思想,但是也强调在运用这些思想时,必须注意适度性、严谨性、灵活性和承上启下的重要性。
总而言之,二人之间的政治分歧其实不大,主要体现在关注的重点和细枝末节的问题上,而不在于总体的观点。上述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差异,涉及他们的宗教观点,是由对这两位思想家的一般印象生发出来的。这一点的确值得认真思考,尤其是它将在本书所述故事中起到主要作用。


休谟、斯密与虔信宗教的同时代人
宗教是休谟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他所有的著述几乎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涉及这个话题:讨论宗教观点的可信度、心理起源和后果、发展历史,及其对道德和政治的影响。
虽然在细微之处存在争论,但他的立场基本上比较清楚:休谟既不是虔诚的信徒,也不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而是我们所说的不可知论者,或者18世纪所谓的怀疑论者。
他从来没有彻底否认过神力的存在,但也认为论证其存在的主要观点很难令人信服,而且他认为宗教的影响大多是有害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休谟对宗教和宗教信仰的批判是……微妙而深刻的,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方式破坏着宗教。”
休谟时常用一种巧妙或隐晦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论点,例如让一场虚拟对话中的人物说出这些观点,或者将怀疑论的结论披上信仰主义的外衣,但是这些烟幕通常很容易领会。
同时代的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愚弄,而他的确也并非出于愚弄之意。相反,休谟常常为在狂热者中引发的“窃窃私语”而感到高兴。斯密则喜欢将自己的宗教观点秘而不宣。
在他的作品和个人生活中,他总是竭尽全力避免暴露自己的宗教信仰——或者说缺乏宗教信仰——并且避免与虔诚教徒相对抗。同时代人经常指出,当谈论到宗教问题时,斯密的“谈话非常谨慎”。
他论述宗教的文章远比休谟的少,而且他即便是写,他的文章也指向了多个方向。一方面,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间或会引用天赐秩序的概念,而在述及宗教冲突时,他也总是使用人情味十足的词汇。在远超休谟的程度上,他为对神力的信仰赋予了现实意义,尤其是在为人类提供安慰和道德支持方面。
另一方面,斯密关于道德、政治或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其根本前提均非来源于宗教;在每一个他借助“造物主”加以讨论的问题上,他都提出了一个更为世俗的解释。

事实上,斯密道德理论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要表明道德来自人类本身,而不是来自上帝的话语或意志,因此,宗教不是德行的先决条件。这和休谟的说法如出一辙。斯密后来修订了《道德情操论》,为了缓和早先版本的宗教含义,但即使是在第一版中,其论述也暧昧不明,让许多读者无法确定他的根本信念。
例如,在该书出版后不久,斯密先生的一位学生詹姆斯·伍德罗牧师就向朋友推荐了这本书,并态度不明地评论道:“作者似乎对邪恶有着强烈的反感,因而歌颂美德。也许他对宗教是尊重吧,至少在我看来,有关宗教主题的内容看起来不像大卫·休谟那样肆无忌惮。但也许他们二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但在另一部著作《国富论》中,斯密的语言和观点却非常世俗化,而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一些论述中,却有很深的怀疑论色彩。直到今天,学者们关于斯密的宗教观点依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
从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到深柜的无神论者,各种猜测不一而足,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斯密是在居中的某个位置上,将斯密解读为一个自然神论者。对斯密与休谟友谊的长期反思,让人们的解释不得不走向了怀疑的一端。
埃玛·罗斯柴尔德评论说,他们的通信显出一种“亲密和共谋”的感觉,似乎“难以推断出宗教上的严肃差异”。他们经常在信中拿宗教开玩笑,斯密在宗教问题上的嘲讽和休谟一样显而易见。
诚然,斯密拒绝承担出版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的责任,在休谟最后的日子里造成了两人之间些许的嫌隙。人们经常以此认为,斯密不同意或不赞同休谟的怀疑论,但是我们将在第10章看到,这段插曲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尖锐,也并没有那么多哲学色彩。
此外,在休谟去世仅仅几个月之后,斯密在写给斯特拉恩的公开信中,高度赞扬了休谟的智慧和美德,这足以否定人们认为他因为朋友缺乏信仰而深感不安的猜测。两个多世纪之后,我们依然无法确定,到底是什么促使斯密在宗教问题上比休谟远为缄默,尽管我们很容易就能想象出许多可能性。
例如,斯密可能只是性格更加谨慎;或者他更加关注自己的声誉和事业上的成功;或者他认为宗教不是一个那么重要而危险的现象;或者认为沉默是金,具有比公开对抗宗教更强大的力量;或者他不想冒犯身为虔诚信徒的母亲;或者,他看到休谟因与虔诚信徒对抗而遭遇的不快,从中吸取了教训。
无论如何,由于他的审慎,在考虑斯密的个人信仰时很难避免一定程度的猜测。如果一定要给斯密的宗教观点贴一个标签,也许只能是持怀疑态度的自然神论者。斯密几乎肯定不是一个基督教信徒,例如他没有表现出接受耶稣神性的迹象,而且他似乎对大多数形式的宗教崇拜表示怀疑。

然而,他显然可能持有一种对遥远的,也许是仁慈的,更高的神力的信仰。
当然,在斯密的时代,这对于虔诚的信徒来说无足轻重:无神论、怀疑论和自然神论都暗示对基督教的怀疑,本质上别无二致,所有这些术语都时常被用作责难的污点。休谟的直率敢言和斯密刻意保持的缄默,是实际操作上的巨大差异;而休谟的怀疑论和斯密持怀疑态度的自然神论,在理论上只有微妙的区别。
就同时代人如何看待他们两位而言,前者远比后者重要。这两种不同的姿态带给了他们不同的声誉:休谟被称为“大异端”,被认为没有教育年轻人的资格,他曾两次寻求教授职位,但神职人员均果断否决他的候选人申请;而斯密则被看作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道德哲学教授。我们将会看到,所有这些都引起了他们之间的戏谑和玩笑,但却丝毫无损于彼此间的尊重和感情。

现代文明的三原则:财产的稳定占有、经同意的转移、遵守契约,被冠以“休谟三原则”而被世人熟知,但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这仅仅是休谟思想大树上一个小小的枝节。
亚当·斯密被认为是经济学的鼻祖,他的《国富论》则被认为是经济学中的圣经,对人类社会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在亚当·斯密以前,学者多研究经济现象,所称经济学不过是特定时代、特定场所的经济政策,亚当·斯密以”人性”为出发点,把普遍性带入了经济学的领域,使之成为社会科学。
休谟和斯密被称为“苏格兰的双子星”,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再读他们的作品,不仅丝毫不过时,反而非常紧迫。因为只要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就必须理解文明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误解休谟斯密,会导致我们以为人性是割裂的,市场和社会是不同的。进而,为强权打着善意旗号强制干预“自私”的经济留下了隐患。
为此,先知书店诚荐“休谟与斯密”专题书单,重温两位塑造现代思想的大师的智慧与美德。
众所周知,市面上关于休谟与斯密的作品版本众多,翻译、装帧等良莠不齐,先知书店从中精选出翻译精准、装帧考究,极具收藏价值的版本。
休谟与斯密的思想,不仅为现代人性认识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还为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奠定了伦理基础,更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圣经”。读懂休谟与斯密,可以理解现代文明的内核与国家持续繁荣的关键所在。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延伸阅读

关键词
思想
问题
社会
道德
《国富论》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