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吴正中篇小说:爱伦黄(之一)

做公众号里的《纽约客》
戳蓝字一键关注渡十娘
转发也是一种肯定
文字|吴正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
吴正,著名作家,诗人。1948年9月生于上海,现定居香港。1984年开始在国内外发表和出版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上海人》、《长夜半生》(香港版为《立交人生》)、《东上海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后窗》、《情迷双城》、《叙事曲》,诗集《吴正诗选》、《百衲衣诗选》、《起风的日子》,散文随笔集《黑白沪港》、《回眸香岛云起时》,译著《猎鹿人》等20余种,约350余万字。最新著作《北港岛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二)即将出版,正致力于写作《一个人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三)。
相关阅读:
《爱伦黄》选自著名沪港两栖作家吴正中篇小说集《后窗》,由吴正独家授权《渡十娘》公众号推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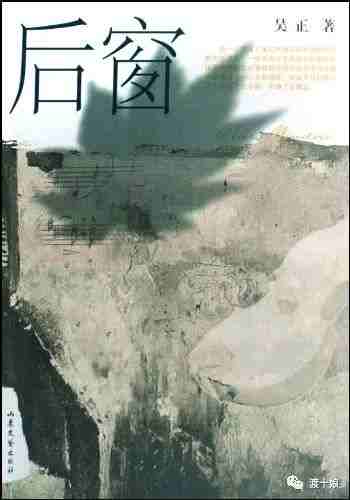
《后窗》,吴正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
(一)
每次,我从上海返港后去公司上班的第一个早晨,总会遇到那张脸,那张搽白了粉的老女人的脸:我托你的事办了吗?办事?为什么事?记忆从一个不显眼的角落提醒说,好像真有一件什么事她要我办的,但我已忘得彻彻底底,竟连立马找一个诸如此事我也真是在某一天去办过,不巧那次正好如此这般的借口来搪塞一下也缺乏服人服己的理据,于是,我只得讷讷地站着,想来脸上的表情也已清楚地告诉了她:此事我已忘却。
唉,白脸叹口气说,我知道你也记不住,这种小事……不过你是经常回上海去的,下次摆在心上就是了,辣菲德路马思南路口,只要你有便经过——
“噢,我记起来了!”我迫不及待地抢下了她的话头,“那是‘美专’的旧址,还有卡尔登戏院侧边的国立音专。”经她这么一提,记忆便立刻带我回到了那个她曾郑重拜托我的瞬间。
“美专在法租借,我在她的音乐系学钢琴;而音专在英租借:梅白克路,大光明戏院后面的那条路呢——晓得伐?”粉脸笑了,为我能准确地说出一家戏院遥远的英文原名而笑。但由笑容犁开的皱沟令白粉光滑的边缘出现了塌方式的肉红色隐纹,倒叫她的面对者感到了些许难堪。
“那条马路现在叫作黄河路,”我将目光避开了她的那张脸,说,“这是上海有名的食街,开满了个体饭店,一进入晚上便灯红酒绿地通街点亮,人来车往,水泄不通,霓灯歌舞,通宵达旦。”
“我可不管它现在叫什么,黄河也好,长江也好,反正那时叫梅白克路,是一条很安静的马路。周围有不少外国人经营的酒吧和咖啡馆,大光明戏散后,雅座里便坐满了对对情侣。”说话声停顿了有一刻,但在我还没能收拾起勇气来面对那张面孔之前,它又重新响起,“每星期三和六的下午,当我结束了声乐课走出校门时,他总站在路的对面等我,笔挺的条纹呢西服领上斜插着一朵白色的,而手中却握着一枝红色的玫瑰。见到我出现后,他便会横过马路走上前来,将花交给我,并轻声地说一句‘MYDARLING,I MISS YOU(亲爱的,叫我好想你)……’于是,两颗蓝翎脚踏车便一前一后地飞驰上了幽静的静安寺路。那时的上海路上人很少,树阴又特别浓,下午的阳光是柔和的,金黄色的——上海现在的阳光还那样么?”她的叙述突然没头没脑地转变成了一句对我的发问。
上海今日的阳光该怎么来形容,并不是一个我能立即答全面的问题;然而,这只故事,我却听过不下百回了。故事中的那位“他”便是她的首任丈夫——她的美专同学,一位来到上海学西洋美术的泰国华侨。至于时代背景,那是在孤岛期前后的上海。周围战争风云密布,处于飓风风眼中的上海租界却在享受着短暂的阳光的温馨。在法国公园的大草坪,在兆丰公园的碧湖面上,年轻的人们继续着三十年代上海繁华全盛期的记忆惯性,黑丝领结,白纱飘裙地沉浸在年华允诺给他们的奢侈中,浑然不觉岁月已在前方如何狰狞地等待着他们。
爱伦黄便是他们之中的一个。虽然她那条疲惫的人生航船现在是暂泊在我们公司的港湾里,担任一位收入稳定的钢琴师,但谁也说不定的是:她哪一天又会一咬牙一跺脚地将船驶出港湾去重经风浪。其实,爱伦黄这个名字就有些古怪,这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件中西合璧的产物——时代以及姓名的拥有者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性格的痕迹。爱伦是西洋女子名ELLEN的译音,“黄”当然是姓,但却模仿着西洋习惯倒过来念的。然而有一天,公司却收到了一封收件人为“黄凤仙”的信函。函件寄自香港的一家专打遗产官司的律师行,且还是急件。正准备退邮,我说:“先问问爱伦黄吧——看看同她有没有关系。”
我如此提议的原因是:大半年前她的第三任丈夫刚刚去世,虽然他是个据说会是经常对她犯点儿精神虐待症的丈夫,但她还是又挂黑纱又戴白花地折腾了好几个礼拜,而让全公司的人都知道,如今她死了丈夫,她很不幸,她很悲伤,同时,她也因此而恢复了自由身。
爱伦黄之所以说所为经常是藏有某种双重涵义的,有时别人一点即通,她却仍要执意地演绎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见听者们都忍受得实在不能再耐烦下去,而终于在某次将她的隐义彻底捅穿,她才肯停止表演。但有时,涵义却模糊不清地把旁观者的思路都不知引向了哪条理解的死胡同里,她却煞有其事地一经声明之后便从此守口如瓶。比如说此回的“黄凤仙”,没人特意去琴房将函件交给她,她是在课隙的时间里出来走动一下时才发现了那封并不太显眼地摊放在了收发柜面上的律师楼函件的。
她随即一把抢在手中,并迅速地将信的封面翻了个倒转,周围一阵环视,之后又悄悄地潜回琴房里去了,据说脸色都有些发白。好就好在这么多年同事,大家对她性格的脉络与分布多少也有些份数,再说在香港,谁也不会有对她隐私产生兴趣的必要和时间。然而,几个时辰之后,她却重新补了妆,再次自琴房中神色淡定地露了面,并趁着同事们也有不少个在场的机会,郑重其事宣布说:黄凤仙不是谁,黄凤仙正是她本人的原名——但哪又怎样?哪没啥可大惊小怪的!这一天也快到了,你们不要以为我爱伦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秘,到时间大军一到,工会党组一成立,就会有人去告密……
告密?告谁?又向谁告?再说,“黄凤仙”与“那天”又有什么关系?“那天”又是指哪天?同事们面面相觑,等她再度回琴房上课后,才捧腹了好一阵。
但对于我,承蒙她总还另眼相看。这不仅因为我是这里的老板,而且还可能因为我不常笑她,总认定她那性格与举止的背后应该是藏着些什么可靠理由的。
“黄凤仙”信件后的没几天,果然,她又找了个午休的机会来向我作出当面解释了。她是个一旦作出了解释的决定后,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她都要将准备好了的话吐完而后快的人;然而对于我,这只是对她曲折的人生故事又增多了一节发黄了色彩的伸展部而已。
她说,她是姑苏人,却生在上海。那是二十年代之初的事了,租界刚成立,人口还很稀少。她童年的记忆是有一条叫作“四明里”的石库门弄堂,刚造不久,簇新的朱红色砖墙上镶饰着整齐的水泥灰线。弄堂很宽敞,还有大铁门与看更人。那时的她大概只有三、四岁,净面乌发,伶俐乖巧,十分逗人喜爱,而“凤仙”就是她的乳名。再之前?再之前,他们应该也是从上海某处搬来这里的,反正,她只是听说自己在半岁的时候死了生母,而这,可能便成了她日后坎坷人生的始端。尽管她可爱,活泼,但早已被深深烙刻上了“克母”的罪名。父亲再娶,四明里可能就是他再筑的爱巢。当律师的父亲那时还不足五十,但已是缎袍瓜皮帽,手杖山羊须地呈现出一副准老人的模样。继母当然还很年轻。她所记得的是父亲的那对老不敢正视她的无奈的眼神以及继母的那条嫩白粗壮的手臂,拧着她的耳朵,将她像小鸡一样地扔锁进一间晚上不着灯的亭子间里,任她哭喊,没人感应答或伸以援手——这是在许多许多年之后,当她第一次读到夏洛蒂的《简·爱》时才放声大哭出来:她,实在太像那个可怜的小女孩啦!
她便这么地长大了,且升入高小班了。那年的深秋,在一个冷雨淅淅的晚上,她被从梦中轻轻摇醒。父亲就站在她窗前,极其温柔地望着她,无言。“爹爹,……”
他摸出一包银元,沉甸甸地塞到她的枕底下:“……都已经交了钱了,从明天起,你将搬到学校去住……”
“搬到学校去住?住几天哪?”
“不,这是……是寄宿学校。”
她睡梦惺忪的眼睛困惑地望着父亲,两颗豆粒大的泪珠从父亲的眼眶中滚出来,她突然明白了一切,疯了一般地抽身拔被而出,扑进父亲的怀中。她无力的小手死命地掐进父亲瘦骨嶙嶙的肩胛里,像溺水者抓住了一条漂浮而过的稻草:“爹爹,你别抛弃了我啊,你别……!”
她嗅到一股强烈的油脂味从父亲的领颈间蒸发出来,父亲的两块胛骨剧烈地颤动着——这是他无声抽泣的背部动作。
第二天一早,一辆挂着黄铜马灯的人力车便将她连同一只小皮箱一起载去了学校。她从此再没回过家,也没再见过他——直到她快近二十岁了,连第一次专场音乐会都轰轰烈烈地开过来;甚至在泰柬边境的那片农庄里,接到一份“父亲危速归”的加急电报时,她都抗拒这样做。她恨他,当然她也爱他;但她对他的爱平衡不了对他的恨。多少年后,那种脆弱的父爱,那种自父亲那儿缺给了的安全感都转化成了另一类需求而向她伸出了始终不肯缩回的,索讨的手。她渴求通过婚姻来满足,来获取——这便是她一生都在寻找,都在选择,而又都不快乐的原因,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二)
认识爱伦黄的第一幕至今仍清晰地保鲜在我的记忆里且看来今后的岁月也很难再使它变得朦胧。
那是在九龙亚皆老街窝打老道汇流处的一家琴行里,当时我也才来港定居刚半年。白日的正职干完后,傍晚与礼拜天的业余时间就去琴行里教提琴,并在其中体味摸索一番假如有机会,在香港经营一项商艺事业的可行性。
年过半百了的她浓脂厚粉地飘进店来,而一股太强烈了的香水味先她而到达,而后她又留在了他人的鼻孔中。天气炎热,她十指蔻红点点外,十只露趾也一样,仿佛要在人体所有的肢端上都开放一盏醒目的霓虹灯。她四周围点头地向人打招呼,问候午安与“你好”之类——甚至也包括素无谋面的我。她说的是广东话,但却明显着沪式的语腔,而这,正是来港不久的我的听觉最易从他人的发音之中鉴别出来的一种特征:上海人!这更令我产生一种离凳而起与她作一番自我介绍的冲动。但一位已在店里侯她许久的西洋学生已先我而起立:“GoodAfternoon, Miss Wong……(午安,黄老师)。”“Hello, How are you? Ok,please follow me to the studio room(你好,请随我上琴房去)。”她流利的英语之中含有一种属于纯粹英国语音的齿声,当然,这令我对她更刮目相看起来。
这就是香港,颓王败族,孤臣孽子,遗老遗少——而眼前这一位又算是何方神圣?一团疑云扩散着,还未及细想,已到了课隙的时间。我打开琴盒,拉一段巴赫还是门德尔松,想抓紧时间练练手指,就听得有敲门声传来。
“请进。”
半边粉脸自推开的门缝中挤了进来。“大音乐家,能与你谈谈吗?”——这样,我们便正式认识了。
倒不是她那么一句空洞的恭维话就让我得意了,连音乐家都沾不上边的我,更何来个“大”字?其实,她第一眼见到我的印象并也不佳,胡须拉碴,一派颓废提琴手的模样。她一向喜爱高尚,喜爱干净,喜爱富裕以及显赫,但她一样真诚地喜爱艺术。当时不是我,是巴赫们旋律中的那种不可抵挡的魅力将她拉进了门来——这是多少年之后,当她已成了我们公司的一名雇员后方才告诉我的话。“聪明人一个装得比一个笨,有钱人一个装得比一个穷,嘿,这就是我们老板给我上的第一课!”——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算为一句变了形的恭维话?
并不像你经常在结识了一位普通的点头朋友后从此就不再有下文,直到你在某天意外遇见他(她)时才记起,与爱伦黄的相识带给你的常常是一连串出其不意的惊奇故事。
一天,她的课正好与我的又排在了同段时间内,我于是又能有幸目睹她上琴行来上班的一幕。脂粉香水蔻红自然不用说,这回她的身边更多了一位二十岁上下的欧陆青年。金发碧眼,皮肤白皙,挺拔的鼻梁教人联想起小时候地理书上曾经读到过的阿尔卑斯山脉。他挽着她的手臂,样子十分亲昵。“来,叫UNCLE(叔叔)。”
“UNCLE,你好。我系欧文(IRVING)。”青年用幽蓝的眼眸望着我,说的竟是一口极其标准的广东白话。
惊奇第一击。被一位比自己也小不了若干岁的人叫作UNCLE的感觉效应本已令我相当地局促不安,再说,连预先准备好的英文问候语我也在刹那的惊讶时流失得精光。“这位是……?”
“我儿子。”?——惊奇第二击。而惊奇的第三、四击则是在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后,她才陆续向我揭开的。
“你看欧文的人品怎么样?”有一次,也是在课隙间,她在走廊中遇到我,便停下来这样问,神情有些自豪。
“很好——真很好。”我急忙回答,“漂亮又有朝气——他现在在哪儿?我的意思是……是说,他现在是读书呢,还是工作?”
“他在酒店任公关。”她表情突趋冷漠,但下一句的表达却又将另一种热情在她脸上被点燃起来,“他就像他的父亲,像极了!简直就是他父亲年轻时的化身——”她略作停顿,似乎在等待一个我会询问有关“他的父亲”之种种细节的可能性,但我只“哦”了一声,并无下文。
“——他是英国人,”她只能再追加一句。
“谁?”
“欧文的父亲。”
但我也只是用“噢”代替了“哦”——英国人,美国人还是德国人并不重要,反正,这样一个儿子的父亲,或者说,这么一个儿子的母亲的丈夫当然不会是中国人。这在香港是件很普通的事,也是我在知道她有这么个儿子时一早已在心中肯定了的事实,再说,打听他人私事从不是我的习惯。于是,谈话便这么中断了。
一星期后,我又在琴行门口碰见了她。我们在路边站定,亚皆老街上的双层巴士来回驶过,废气噪音之外,更有一种歪歪斜斜地好像随时准备冲上街来的趋势。“我们去喝杯咖啡,好吗?”她指指琴行隔壁的一家灯光幽暗装修别致的咖啡馆,而我看了看表,觉得推托似乎有点缺乏理由。
“听说你家很有钱,住半山区。”刚坐下,点了饮料,她便单刀直入,眼中勃勃着兴趣的光彩,“怎么不去开一家琴行?去,去开一家!开了我来帮忙——”
“假如真有那一天,一定找你。”我淡淡地推挡了一句,想回避转一个话题,“你就这么一个孩子吗?”
“什么?”她抬起眼来望着我,“我……还有个女儿。”
“女儿?那一定很漂亮啦。”
“为什么?”
“你儿子都已经那么帅,就甭说女儿了——混血儿一般都很漂亮,不是嘛?”
“但她是中国人。”
我沉默了,明显地感到触及了一条无形的禁区线。我把目光他望别移而去,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屋角的一盏壁灯上,一股浓浓的咖啡香漫溢在屋内,一个戴红领结的侍者托着盘子,直挺挺地走过。
当然,这一切一切的谜底后来总是会有那么一回被揭开的时候——我们毕竟相识了这么许多年,而且还反复又反复地同过事。只是每一次与她谈话内容的出其不意常叫人有一种从钢丝一端走向另一端的惴惴不安感,这使我产生出了一种可以回避就回避她一下的欲望。但对于她,或者就因为了我的这种对他人隐私毫不感兴趣的个性而滋生出一种莫明的信任来。这,便是其中的某一次。
“欧文他爸爸死了,是心肌梗塞……”有一天,她突然在一种极不协调的上下文中向我宣布这么个消息。
“是吗?”我震惊非常,并下意识地为自己调节好了一种向她示哀的极端姿态,但她的脸部表情并不显示有一桩惊天动地事件发生后的强烈症状。“在哪儿过的生?”
“伦敦。”
“几时的事?”
“二十五年前。”
“啊?!——”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而这,又是另一次。那会儿,我太太也已从上海申请来了香港定居,她怀孕了,挺着个大肚子请爱伦黄一同出来去帝苑酒店(ROYALGARDEN)的LOBBY(大堂)内厅咖啡座消耗一个礼拜天的下午。周围人造喷泉淙淙,一株绢织的桃花树正“怒放”出一种如火如荼的形势。一个菲律宾乐手坐在大理石人工岛的一架三角琴旁,正掀背俯身地弹奏着RICHARD的《水边的阿蒂丽娜》。飘忽的琶音流动出一种人生经历,爱伦黄弹开了她硬质手袋的金属环扣,取出一张发黄的135型照片,递到了我们的眼前。
照片上一个着短袖香港衫的青年人正叉手张腿地站立在马路中央,微笑地等待着相机快门按下的那个瞬间。他脸膛黝黑手臂也黝黑。周围是一派上海的盛夏景象,背景中写着英文彩字的大光明戏院的玻璃楼壳就矗立在他身后。几个着仿绸衫戴白礼帽的行人刚巧在此时迈开了匆匆的脚步。而一行模糊的铅笔字迹留在了相片的背面:1943年8月,摄于沪上。“就是他。”
“谁?”
“我女儿的父亲。”
我们当然知道这便是那位每个星期三六都要持花等她放课的泰国侨生,当时他正在国立美专攻读油画。他苦苦追求了她五年,在消耗了不知多少朵红白玫瑰之后,终于在1947年的5月,才能扶着一个大了肚子的她登上一艘美国游轮,途经东海、南海、南中国海、暹逻湾地踏上了泰国的土地。之后,再一路长途车程,他们又疲惫不堪地来到了一片接近柬埔寨边境的农庄里,那儿是他的祖业,他在那儿出生。
而她,同样也在那儿生下了她的第一胎,这是个女儿,她为她取名叫丽莎(LISA)。这些,都是我们在见到那帧发黄照片之前已了解了的事。然而,一个画家与一个音乐家的结合并没能写成一部有始有终的爱情长篇,她在一年之后便离开了他,而且是在某个朗月之夜突然消失的。她说,她忍受不了那种寂寞,更忍受不了那里的风俗:在终年是炎夏的泰国,为了多子多孙,主人与女佣间的私通,据说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与她私奔的是一位曾参加过二战的英国飞行员,而他的照片我们也是在那同一次才见到。他更年轻,年轻得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大男孩。他额上佩戴一副航空镜,身上穿一件皮茄克,细顺的鬈发柔软地贴在头顶上。他像欧文,但更像某位黑白片时代的,颇觉眼熟了的男主角,正准备告别情人,驾机冲霄赴前线。
她不顾一切地与他一同来到了香港,这是她生命之中最浪漫的一个时期。碧天澄沙,棕榈风帆;星斗海潮,烛光晚餐;有时在墨绿的有轨电车上摇晃过湾仔古朴的街市,有时则嬉笑地奔跑上中环石板街的陡陡台阶,一个弯腰以及气喘的动作之后,便是闪电般的拥抱与烈火样的炽吻——他们,只是生活在梦中!
在那个改变了她一生生活轨迹的月夜之后的多少年,其实,她也曾回去过,回到过那片靠贴在泰柬边境的农庄去。而到了那时,她才知道,原来那位油黑肥胖的女佣已替代了她的位置。他与她,或者再加上一打其他女人,已有了十三个孩子。他老了,他望她的眼神令她记起了当年她自己父亲望她的那一种。而最可怜的是那个被她遗弃了的丽莎,一扔就是二十多年。她已变得怪癖而内向——她始终没曾结婚,直到现在。她说,她既怕女人更怕男人。而所有这些,爱伦黄应该都是理解的。她毕竟是她的母亲,她爱她,她也爱她。但她们中间却永远相隔着一座不可逾越的关系的高墙。她想推翻它,她也想;但她推不倒它,她也一样不能。
爱伦黄的身世故事到此暂告一段落。我们款步走出帝苑酒店的大门,两个穿金红制服的后生,拉开大门,笔挺地站立在了两旁。
门外已是七十年代末的香港了,阳光猛烈,照射在人背上立即产生一股热辣辣的渗透感。从刚落成不久的尖东休憩区放眼而去,对岸港岛参参差差的楼厦的森林正隐隐约约在一层浅蓝色的午雾里。我扶着怀孕的妻子慢慢地行走在傍海的漫步径上。走在另一边的她也挽住了我妻子的另一条胳膊:“我也有过两次类似的经历,女人在走过这段历程时的感情最脆弱也最复杂。”她冲着我莫名其妙地笑了笑,完了再向我妻子肚腹上的那条动人的曲线丢去了理解的一瞥。“而且,两次都是登船离开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一次是从上海去泰国,由他扶着我;而另一次则是从香港回厦门,孤单一人,时间是在1950年的2月。
(未完待续)



你是我的阅读者 我做你的渡十娘
昨日更新:
热文链接:
栏目:
读完请点"在看"让更多人看到
图片 I 网络
整理 I 编辑 I 渡十娘
清单内容来自 I 吴正
版权归原作者 I 如有侵权 I 请联系删除
生活中
总有些东西值得分享



渡·十·娘
DES
IGN
发现 I 家庭 I 乐趣
想每天与渡十娘亲密接触吗?
喜欢?粉她!

有话想说: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