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与他未曾谋面的老师



德鲁克与他未曾谋面的老师
文:世纪鹏信 编:
李强
从年代上说,德鲁克出生于1909年,去世于2005年;而克尔凯郭尔出生于1813年,去世于1855年。克尔凯郭尔比德鲁克早生近百年,而他去世时间比德鲁克早150年。
克尔凯郭尔虽英年早逝,但他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力正好是19世纪后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而那时正是德鲁克人生中学习吸收与自我精进的关键阶段。
在德鲁克看来,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具有“机智与现代感”,具有“早生百年”的卓越感;在德鲁克眼中,克尔凯郭尔是帮助20世纪的人们看清整个时代的局势、个人的美德以及生死关系的“先知”人物。
Kierkegaard在丹麦语中是由“教堂”和“园地”组成。《恐惧与颤栗》写于1843年,作者用笔名“沉默的约翰尼斯”;按照克尔凯郭尔的习惯,通常状况下,用笔名写的作品多为美学作品,而用真名实姓写的作品多为宗教作品,作者宣称自己“绝不是哲学家”,也“不懂哲学体系”。
因此,我们可以大致理解《恐惧与颤栗》实际上是一部哲学美学或神学美学的著作,而不是纯粹的神学作品;但是,从整体上讲,《恐惧与颤栗》所讨论的核心是个人信仰,而非名义上的宗教;主要以旧约圣经中“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创世纪》第22章)展开解释;所用的“恐惧与颤栗”是信仰的心理状态描写,有哲学、神学以及美学的内涵。

克尔凯郭尔
德鲁克的名篇“不流行的克尔凯郭尔”原稿写于1933年。1942年德鲁克任教于本宁顿大学,1943年他在该大学曾经有过题为“人类存在何以可能?”的精彩演讲,其中德鲁克就曾引用克尔凯郭尔的许多哲学神学观点。
比如“人因不愿成为独立个体而深陷绝望”、“绝望成为生命的本质”、“人可能存在于信仰中。罪的对立面不是美德,而是信仰;信仰是指相信上帝具有‘不可能的可能性’,相信在上帝里面,时间与永生合而为一,生死皆有意义。”这些名句后来都出现在他的“不流行的克尔凯郭尔”一文中。
1949年,“不流行的克尔凯郭尔”正式发表于《赛望尼评论》;在1985年写给朋友的信中,德鲁克声称这篇文章是他写得最好的一篇论文;后收录于1993年出版的《生态愿景》,独立成章(第30章),德鲁克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短文附上一个大标题:“为何只有社会是不够的”,真是意味深长。
从孩提时起,德鲁克在犹太-基督教价值体系和基本认信的熏陶下成长;年轻时,他阅读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时被深度吸引,以至于“顿悟”,按德鲁克自己的话说:“I Understood/I Knew immediately”。
哲学与神学的探索成了德鲁克后来管理学领域突破与创建的根基,在此意义上说,克尔凯郭尔的神学思想对德鲁克的学问和后来管理学思想的影响功不可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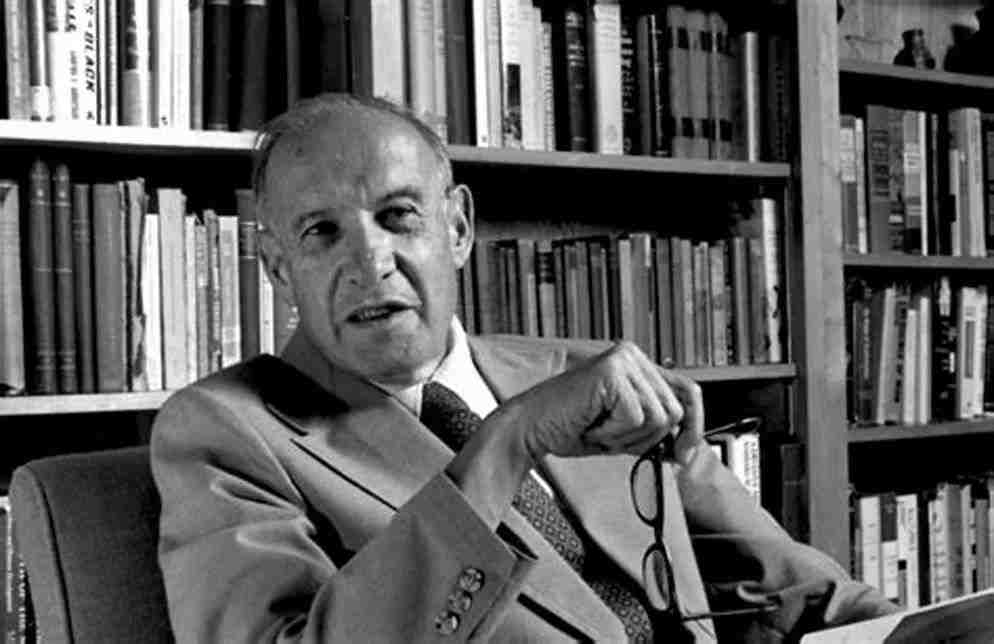
德鲁克
德鲁克认为克尔凯郭尔有以撒一样隐藏的意义——亚伯拉罕象征着克尔凯郭尔他自己,牺牲以撒象征着他自己最深沉的秘密。亚伯拉罕百岁得子,130岁时献以撒,也就是说以撒是30岁时被亚伯拉罕献祭的,而克尔凯郭尔是在30岁时完成《恐惧与颤栗》一书。

首先是19世纪的欧洲现实。从政治到文化乃至精神价值(信仰)出现深度危机,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性危机”,那是19世纪的通病,指人类真实的生存危机,包括现实性(社会、经济与政治)危机与精神性(道德、价值观与不断涌现的思潮)危机。
最为典型的有两点:
一是,一切以科学和量化为准,生命质变与终极价值被肆意忽略。表面的体现是“社会运作不正常”或者说“社会功能严重失调”。人过度依赖自己的理性与自由主义,从而怀疑和贬低原有的精神传统和灵性启示。
二是,人们疏离甚至抛弃了固有的信仰传统,转向崇尚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道德主义。
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高度膨胀摧毁了人对精神价值和启示信仰的依赖,但此二者依然解决不了人的生死问题和世界朽败的问题;甚至最受追捧的道德主义也没能驱逐邪恶和朽败,也阻止不了现实的痛苦;相反,道德主义盛行导致人的情绪不稳和多愁善感,以至于连道德立场的选择都会转变成为可怕的相对主义。
其次是,关于存在主义(哲学)神学在20世纪的影响。1855年,克尔凯郭尔去世后,他的哲学神学思想才被德国人关注并深刻影响20世纪,尤其是对经受过纳粹法西斯蹂躏过的欧洲;当社会瓦解、人的精神状态崩溃时,人的痛苦是不能被淹没、不能被视而不见的。
谎言长久不了,因此人不能因谎言自欺欺人;痛苦太真实,因此人不能对痛苦自我麻痹。人们更不能对信仰无动于衷,所以有些人宁可说“上帝不存在”或“没有上帝”;实际上,其目的就是为自己作恶提供方便,为自己的邪恶行为自圆其说。

纳粹集会,人们被激情的洪流所裹挟
20世纪上半叶,人们被激情和洪流所欺骗。存在主义哲学指出人的存在的真实性,信仰的真实性,具有很强的入世思想,因而存在主义神学便具有了医治人心的作用。
因此,德鲁克受此影响不足为怪,在《经济人的末日》、《工业人的未来》以及回忆录《旁观者》中多有流露。我记得德鲁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那个时代的人,不可能成为乐观主义者。

德鲁克试图寻求“人何以存在?”的哲学解释,直到阅读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神学时,他说:“只有克尔凯郭尔给出了答案”。
他想要说的是:人不只是活在社会之中,社会不是人生存的所有真实性,甚至即便是人只为社会而活,那也不是存在的全部真相,因为社会只是人生存的一个维度而已;人作为被造者,人的存在、灵性(精神)、个体等维度的确定性来自人对上帝的信仰。
人不只是“社会人”、“经济人”,还是“属灵人”,还是“孤独的个体”甚至是“绝望的人”。在上帝的眼里,不存在社会;在上帝的永恒里,个人才是存在。这些话与其说是为了引导读者,不如说是他自己的信仰的觉悟与希望的笃定。
克尔凯郭尔的“存在”到底何意?首先必须理解对存在的认知问题。克尔凯郭尔认为黑格尔哲学“扭曲了人对现实性与实在性的理解”,因此他提出:人的个体生存状态,每个个体都在进行自我认知的变化、不停地面对多种可能性、必须做出个人选择,在选择中做出决定,最后必须承担责任——活生生的人、真实的个体对存在现实的思想。

在上帝眼中,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德鲁克继承克尔凯郭尔的思想,有反黑格尔哲学的倾向,比如他认为黑格尔“要求个体去思想而不是存在”。在德鲁克看来,人最难的不是“毫无选择”或“可以不选择”,也不是“有多个选项可以挑选”,而是“明知不好而必须做出选择”。
当然,在理解人的真实困境与人性的痛苦中,克尔凯郭尔也反对柏拉图把人性假设成为积极的——“如果我们了解善,我们就会行善”;克尔凯郭尔认为,即便是人拥有道德和伦理的知识,依然“不得不深陷善恶之间选择决定的困境”,伦理道德的真实困境让人无法自拔。
德鲁克在这方面也很像克尔凯郭尔。他强调管理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管理要以人为基础,要正确理解人性的真实,以及人在困境中的实际体现和需求,这些都是管理者的必修课。
关于“I am/we are” and “I should be/we should be”的认识。“我是、我们是”和“我应该是、我们应该是”——从“本质”到“存在”的运动。
人是有限的,并且人都在缺乏安全感与不确定性中生存,因此每个人都试图“说点什么”或“做些什么”来克服自己的有限性、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越是如此,人就越觉得焦虑、失望、甚至绝望。
德鲁克讲管理学也是如此,比如政府对企业、组织、社会、经济以及个人的管控,源自于对自身的有限、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因此政府的管控越严、越多、越紧,说明政府面临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性越强烈;从而暴露出政府管理职能的有限性越大。管控得越细致、越繁琐,社会中的个人、企业和各类组织的责任感被削弱得就越严重。

德鲁克:创业既不是科学
也不是艺术,它是一种实践。
存在主义者都强调人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和行为负责任,人是自由的,因为他会选择,但人的自由选择和自由意志难以摆脱人的处境困境和人性的自我囹圄。
当人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存在时,人就会深度地感知到这种困境,因此,人只有重新找到自己,他才能意识到自由的难能可贵,从而恢复人的尊严。以自由来承担责任,以责任来赋予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也是真正的责任。
你的责任是你的自由意志。故此,德鲁克在“不流行的克尔凯郭尔”中指出,不能运作正常的自由就等于否定自由的存在,丧失正常运作能力的社会,自由便沦为某种政治阴谋和个人特权,自由的实质与重要性便失却了;他甚至在《旁观者》中感叹“自由不好玩”。

最重要的是,德鲁克管理学中很强调信仰、知识、实践、行动的合一,我认为德鲁克不是“知行合一”,而是“信知行合一”。实践与行动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关键。
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是“行动的哲学”,强调人要做个“行动的清醒者”和“清醒的行动者”。大家都熟悉这个比喻:两种马车驾驭者,一是手持缰绳却在睡觉,一是完全保持清醒,结果可想而知。“真正的马车驾驭者”是“有意识地参与到行动中”。
一个人只有真正参与在有意识的意志行动中,才能算得上真正存在。德鲁克的管理学是“实践派”或“行动派”,比如管理是工作,领导力是工作,是认真做事等。

克尔凯郭尔
人的终极价值在于回归个人对上帝的信仰与灵性的成长。总体而言,克尔凯郭尔认为人对生命的认识历程有三个阶段。
第一是美学阶段,也就是人按照自己的本能、冲动、趣味、激情和情绪行动,处于美学阶段的生活原则是享乐,特征是绝望。越追求享乐,越感觉孤独和绝望。
第二是伦理阶段,理性接受现实,勇于承担责任,把道德视为理智标准,一个伦理的人持守道德自足的生存态度。处于伦理阶段的生活原则是选择,基础是道德判断。
第三是信仰阶段,树立对不可见者的信心,放弃自以为是的“客观、理性、伦理”标准去探求与揭示上帝的真相,转向信仰与依靠,实现生命的“不可能的可能性”。处于信仰阶段的生活基础是人的负罪感,特征是甘愿承受苦难。
存在主义哲学神学是鼓励人正视个人的孤独、内心的痛苦、焦虑、心灵的不得安息、精神的无家可归感,因为所有生命最痛苦的时刻都是极其个人的,从而鼓励个人的自我回归信仰、皈依仰赖上帝,勇敢做“信仰的飞跃”、做“看不见的跳跃”。
这不是悲观主义,是具有节制和谨慎的乐观主义。德鲁克在“不流行的克尔凯郭尔”说到:
“只有通过绝望,通过苦难,通过痛苦和无尽的磨练,才能达至信仰。信仰不是非理性的、伤感的、情绪化的、自生自发的。信仰是经历严肃的思考和学习、严格的训练、完全的清醒和节制、谦卑、将自我服从于一个更高的绝对意愿的结果……每个人都可能获得信仰。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绝望。”


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是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中所分析的实例,德鲁克文中也多有提及。在这个故事中,至少有如下关键点需要把握。
首先,信仰是超道德价值。在哲学与神学领域,强调信仰是超道德价值,并不是说信仰不讲究道德,也不是说信仰脱离或放弃道德价值。
克尔凯郭尔认为,在伦理学上,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行为被描述为“亚伯拉罕意图谋杀以撒”,这是违背道德伦理的事件。
在圣经故事描述中,亚伯拉罕与爱妻撒拉的爱情是美学、道德和信仰的完美结合,况且亚伯拉罕是百岁得爱子;按照人伦,“父亲对儿子的爱应该胜过对他自己的爱”,因此,当亚伯拉罕愿意把以撒献祭时,实际上作为父亲身份的亚伯拉罕已经牺牲对儿子负有的道德责任。
道德与伦理都要求坦诚、要求公开隐秘性,才能树立人伦榜样。但伦理道德的局限性在于它本身的多愁善感、容易激动也容易厌倦,因此道德伦理不会永久保持不变,也无法达到救赎的目的。
因此,亚伯拉罕意欲献以撒,只能在信仰上加以解释。在信仰上,这个事件被描述为“亚伯拉罕定意献出以撒”,亚伯拉罕的行为“超越了整个伦理范畴”,他以信仰为“更高的目的”,因此对伦理道德提出了质疑;按照克尔凯郭尔的话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包含了一种对伦理学的神学怀疑”。

信仰超越了道德伦理,至少是当亚伯拉罕定意将以撒献给上帝的那个瞬间,体现出超伦理价值。这就是为何克尔凯郭尔批评黑格尔在论及信仰问题的错误,他说道:
“当黑格尔讨论到信仰的时候,他是错误的:他的错误在于,当亚伯拉罕应当被揭示和表明为一个凶手时,他没有大声而又清楚地反对亚伯拉罕对自己作为信心之父的荣誉和快乐。”“要知道,没有亚伯拉罕,伦理和道德就是人最高价值,而黑格尔没能从希腊哲学中学到这点。黑格尔本人对亚伯拉罕的理解未必清楚。”
其次,在爱与牺牲的层面上理解亚伯拉罕的伟大。克尔凯郭尔对亚伯拉罕是非常崇敬的,崇敬到“恐惧与颤栗”的程度。
克尔凯郭尔多次强调说:“亚伯拉罕令我景仰,可他同时也使我毛骨悚然”;“人若不知恐惧,也就不知伟大”;“我不能理解他,而只是敬仰他”;他“既不是悲剧英雄,也不是美学英雄”。
那么克尔凯郭尔到底为何敬仰亚伯拉罕到如此惊恐的程度、到膜拜的地步呢?对亚伯拉罕的伟大的崇敬,实际上是在具体的“献以撒”事件上得以升华和确认,这种确定性的本质是信仰。
克尔凯郭尔说:“有人靠力量而伟大,有人靠智慧而伟大,有人靠希望而伟大,有人靠爱心而伟大,但亚伯拉罕则是这一切之中最伟大的…”
因为他克制了“悲伤”、超越了“人之常情”,他拥有对上帝的真正的信仰,而信仰正是一切事情中最伟大、最艰难的事情,没有人有权引导他人去信仰某些次要的或容易的事情。

他把信仰奉为激情,而且是奉为最高的激情,正如他的名言所说:“人的最高的激情就是信仰。信仰是人的最高的激情。”在克尔凯郭尔的眼中,亚伯拉罕就是这种最高信仰激情的完美体现。
他献以撒是“为上帝,也为自己,二者完全同一。他为上帝而这样做,是因为上帝要求这一关于他的信仰的证据;他为他自己而这样做,是因为他能证明这一点”。
在此意义上,亚伯拉罕真正地做到了“上帝所要求的绝对的爱”,爱的绝对性程度甚至到了“去恨”的程度,“亚伯拉罕要真恨以撒,他就会确信上帝不会向他提出那一要求,因为他和该隐完全不同”。
而这正是耶稣呼召门徒时提出的要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路14:26),这里原文“去恨”,就意味着“爱少一点、尊敬少一点,礼遇少一点”,这就是“信仰骑士”不能屈从于凡俗事物、不能迁就于普通伦理规范的原因。亚伯拉罕既然拥有这种令人崇敬的信心,那就注定与众不同了。
最后,我们必须理解信仰的悖论或信仰的困境。信仰不是没有困境,也不是毫无悖论;相反,只有在信仰里,人们才能看清生存的困境和存在的悖论。在这个意义上说,信仰的确需要有冒险的勇气,即“往看不见的深处飞跃”,实现人生终极的质变。
克尔凯郭尔认为,信仰本身的困境正在于:独自性与个体性远高于任何普遍性。这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件中可见一斑:亚伯拉罕个体的孤独、绝望和信心是他同一时代甚至后世至今无人能够超越的。亚伯拉罕作为“信心之父”所具有的独特个体性与我们的普遍性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亚伯拉罕被弃绝在先,但他的信仰非但没有因为被弃绝而丧失,反而更加笃信不疑、坚贞不屈;这种激情与信仰,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他内心的冲动,而应该被理解为生存的悖论。

亚伯拉罕得爱子以撒,又牺牲以撒,最后失而复得以撒,这一连串的事件发生都因为他拥有真正的信仰;换言之,他是凭着信仰百岁得以撒,也因为信仰放弃以撒,再凭着信仰复得以撒。
这个故事体现亚伯拉罕“有信心的行为”与“有行动的信心”的完美结合。克尔凯郭尔是按照神学(哲学)美学的逻辑来解释亚伯拉罕敬虔的内心以及他对上帝的恐惧,特别是他忐忑不安与躁动恐惧中举起刀杀害以撒的那个瞬间。
人们理解不了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因为人们摆脱不了自我的捆绑、道德的束缚和柔弱的心灵。
在克尔凯郭尔对“亚伯拉罕献以撒”事件的解释中,德鲁克看到了“生与死都有意义”的道理。这里涉及“时间与永恒”的关系问题。时间是人造的概念,仅仅适用于衡量简单的存在区间与分隔;在上帝那里,根本没有时间可言。
信仰者正是凭着信心或者是信仰中与上帝的交谈和对话,将时间与永恒合一,至少亚伯拉罕就是如此,因此我们理解不了亚伯拉罕的恐惧与颤栗,理解不了他“在无限的弃绝中”享有“平和与安宁”;亚伯拉罕在此无限的弃绝中意识到永恒的有效性,因此他把握了存在的实质。


德鲁克说:“亚伯拉罕就好比克尔凯郭尔自己,牺牲以撒象征他自己最深沉的秘密——伟大而悲剧的爱”。
克尔凯郭尔从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件中学到的东西正是德鲁克从克尔凯郭尔那里所学到的。亚伯拉罕找到信仰中最令其激情澎湃、忠贞不渝的上帝;而德鲁克找到了克尔凯郭尔——一生难以忘怀的师者。
我们还必须重申另一个要点:“亚伯拉罕献以撒”不是理性事件、道德事件、伦理事件,而是“信仰事件”;亚伯拉罕的信仰不仅是内心真信,不仅是“有信心的行为”,也是“有行动的信心”。
有人是“看见了才信”,但更有福气的人是“先信,而后清晰地看见”。爱看得见的人不苦,爱看不见的上帝才苦;爱看得见的人难,但爱看不见的上帝最难。
在宗教学或神学上,德鲁克宣称自己是个“克尔凯郭尔主义者”,他强调生死的连续性及其相互依存关系,主张人可以“在一个尚可忍受的社会中”,有信仰、有尊严、有自由且有成就地活着。

克尔凯郭尔是德鲁克未曾谋面的老师,只有他给了德鲁克“人何以存在”的答案,让德鲁克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活着;德鲁克自己也是一位真正的老师,他致敬克尔凯郭尔的方式,就是将他的思想,作为后来自己在管理学领域突破与创建的根基,不但启发了全世界无数的管理学习者,更能启发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更深刻的认识。
为此,李强好书伴读诚意推荐克尔凯郭尔和德鲁克的作品。收藏、阅读这套书的几大理由:
◎实用:克尔凯郭尔和德鲁克都注重行动的力量,他们让我们对世界有了深刻的认识,清楚的知道自己是怎样学习新知识和与别人共事的,以及自身的优势何在,从而做到卓尔不群,让自己重新认识自己。
◎权威:克尔凯郭尔是“存在主义之父”,德鲁克是“现代管理学之父”,存在主义影响了整个二战前后的世界,德鲁克的思想也已经影响了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读者,我们今天使用的许多观念都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
◎思维提升: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是行动的哲学,德鲁克的管理思想,是最顶层的思维晋级攻略,读他们的著作,探索和发现自我和组织内在的渴望与动力,并以此创建更好的行动方案,最终能实现叠加式的进步。
感兴趣的书友,可识码收藏,通过克尔凯郭尔和德鲁克,完成思维层次的跃升。


▍延伸阅读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