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顿的美发师
平均阅读时长为 114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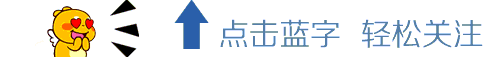

(一)
在曼哈顿, 找个满意的美发师和寻情人一样的难。
寻找美发师的路程曲曲折折 – 30多年的都市生活, 20年的觅求搜索, 与发型师的相遇和离别,数不胜数。
初到纽约时, 留着长发, 披肩梳起反反复复, 都不满意。急需位能整治管理的美发师, 打造出一头配得上摩登城市的发型。
曼哈顿的发廊沙龙遍地都是, 令人眼花缭乱, 难以分辨好坏。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不停地弃旧迎新, 挖掘那理想的一个,好似大海里捞针。
那些被抛弃的美发师, 好像都缺少些什么。完美的那位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后来发现, 不能全怪人家。有头发自身的毛病, 发质硬如枝杈, 不易修剪。瞧瞧那些金发女郎们, 细软的头发象丝绒。
一位菲律宾华人朋友炫耀她新剪的高雅时尚短发。忙问她是谁的创作, 是Vidal Sassoon。VS的电视广告立刻像过银幕一样地穿梭飞闪 - 模特们前卫惊艳的bob (短式的) 发型, 让人痴呆迷醉。跃跃欲试去预约。

朋友认真地传教, 告诫预约时必须提出的条件,最重要的细节是, 一定要找会 “剪亚洲头发” 的人。无怪我屡战屡败, 原来不知道这个关键。电话预约时, 小心谨慎地背着台词要: “一位会设计修剪亚洲人的黑、硬、直、长发的美发师” 。使劲地强调 “亚洲人的黑、硬、直、长发”, 直到预约男子重复了要点为止。
当他问要什么档次时, 价格吓我一大跳。想要取消, 可是嘴巴说不出“不”。只怪那个虚荣心。于是, 挑了一个中等价: 120多美元。这个数字死死地烙印在脑子里。毕竟, 那是90年代初,刚刚逃离了穷学生的日子, 来纽约工作才一两年, 在剪发上花这么大笔钱, 还是头一次。自我溺爱一回吧! 心疼喜悦各参半。
Vidal Sassoon的创始人是出生于伦敦贫民窟的犹太人。在欧美开有沙龙, 也创办了培训美发师的学校, 还出售自己品牌的护发美发产品。多年前, 有人专门拍了部有关他的纪录片。
上世纪90年代仍然是 VS的鼎盛时期, 它在曼哈顿有不止一家店, 都在繁华地段, 耀眼门牌。预约的那家, 坐落在热闹的 Greenwich Village (格林威治村)第五大道上的十字路口的街角上。
提前到达沙龙, 刚进门, 前台的男士立马起身, 热情地打招呼。还没等自报姓名, 他就说: “你的头发不黑、也不直” 。我愣了, 以为他是跟别人说。回头一看, 身后是位金发碧眼的女士。心想他怎么知道是我呢? 请他重复一遍, 耳朵没听错。只是不敢相信他的定论。
坐在等候处, 不停地自问: 头发怎么不黑也不直了? 难道垮跃大平洋后, 变质了? 是南橘北枳?
一位年轻漂亮、比我的头发还长的爱尔兰女人走过来, 是我的美发师。引我穿过一个又摩登又黯淡的长厅, 昏黑的像是夜总会。因为蒙暗, 长厅显得更加深窄, 一条线的理发椅子站立在那儿。走到尽头, 助手帮我洗头发。完后被带回到长厅, 安置在美发师的椅子上。
我迫不及待地问美发师我的头发是不是黑和直,回答是: “No。” 我紧追不放要她的鉴定,她说是浅栗色, 还有儿弯。“就是brown (棕色)”? 我又问,她点点头。
一辈子都以为自己的头发是黑的直的。专业人士揭穿了原型。没提放这个剪发前的序曲, 心里也没有接受新裁决的准备。
但是, 还要话归正题。问美发师要不要剪个象朋友那样的时髦bob。她不赞同, 和蔼可亲地解释了为什么 — 根据身材、脸型和发质等等。她夸头发光泽健康, 应该继续留长发, 多显摆一下, 否则以后想显, 都没的可显。头次听说这种理论, 自然铭记不忘。理解她的话为: 头发也有不幸的时候, 迟早有不能显摆它丽质的那一天。又觉得她有点儿杞人忧天。“那一天” 是何年何月?不过, 听从她的建议, 任她修整。
以后回想起来, 不得不佩服她的远见。她预示的 “那一天” 真的来了, 还来得那么早。
美发师一丝不苟, 按部就班地修剪。其实, 主要是修整刘海儿和长发末梢, 花了快一个小时。说心里话, 看不出她剪的好坏。因为装饰昏灰, 镜子里的头发和深色的背景混肴一体。
总觉得沙龙的发型主要是靠吹风机吹出来的。美国人从小就爱吹头发, 好像还没见过不吹风的人。自10几年前起, Drybar (干吧) 在大城市中流行。与发廊不同的是, 它只做打湿头发、吹风造型, 有的还供酒饮料。吹风是好赚钱的生意, 普通发廊早就提供这个业务。沙龙和顾客都吹上了瘾。而我是最烦吹头发, 热乎乎的风把脑袋吹得起鸡皮疙瘩, 真难受。每次, 都问美发师能不能不吹。这是难为人, 不吹就出不来型。发型师为了满足我的要求,最多是把吹风机的热气调到最低档。
VS的美发师也是靠吹风整治了我的头发。不同的是高价吹出的-加上小费快200美元, 心疼死了; 再有, 她给我头发做了诊断, 打翻了这一生的自我认知。不由地想, 有多少对己和事的误解, 需要一场扭转乾坤式的推翻。
VS算是独特的经历, 有惊讶, 有领悟。不过, 从没复返过。
亚洲人可能更适合剪我的又硬又不直的头发。抱着这个想法, 上路继续寻找那位绝妙的美发师。
有位日本朋友介绍东京来的Hair Mates (丝发伴侣)沙龙。它在曼哈顿有两处, 门面大的那家有近20把理发椅, 在东村的St. Marks Place, 又叫 “小东京” 或 “日本城”; 小的那家在东边的40街上。

发型师是位小巧玲珑的年轻人, 留着一层层精修过的、染浅的披肩发。好像在发廊干得比较久, 同事们都挺尊重他。做事兢兢业业, 毫不马虎, 从头到尾要一个小时左右修我的头发。有时觉得他的认真是浪费时间。
他的敬业精神, 让我想起曾经在日、韩和美生活过的朋友的话: 要雇东方人的话, 第一选择是日本人, 其次是韩国人, 第三是 。。。
师傅的价格在发廊里算是偏高的, 加上小费上百美元。经历过VS, 任何价钱都像是捡了便宜。
说实话, 美发师除了认真仔细外, 没有炫示出拿手戏。跟他的最大原因是预约便利,可以在两家选。后来, 两边预约都碰了壁, 只好改用他的同事。这到触发了再去寻找优秀发型师的念头。
在上东城的美国朋友, 收到一家沙龙在中城开幕的促销优惠, 邀我同行。她在白人中, 皮肤可谓白上白。可是, 头发却比我的还深还硬。一直钦佩她的灵敏嗅觉, 跟她走, 不会错。新的尝试又开始了。
狭窄的沙龙装饰得简洁大方高雅, 显露出的红砖头墙壁有着老城loft (阁楼) 和brownstone (褐沙石联排别墅) 的味道。因为只有四把剪发椅, 起名叫 Salon Quartet (四重奏沙龙)。好艺术!
美发师是希腊裔, 年轻美丽热情。40多分钟后, 新的发型横空出世。惊美的合不拢嘴, 朋友也赞不绝口。有生以来第一次爱恋上刚出炉的发型。因为促销折扣, 只花了60多美元, 还包小费。那一天都变得阳光灿烂。这大概是10多年前的事了。
梦寐以求的美发师从天而降, 头发总算有了归宿。

第二次预约时, 得知她转到新开的Brooklyn分店去了。Brooklyn是纽约市的五个Borough (郡) 之一。乘地铁去分店, 一趟要30多分钟。还是渴望待在曼哈顿。预约女士听出了我的犹豫不决, 建议我留下来, 答应给我一位好的美发师。
新的发型师是位年轻英俊的亚裔, 象个高中生。他说和那个希腊裔同事师出同门。这话让我兴奋, 也抱有更高的期望。他显得有点拘谨, 花的时间比他的同事长, 效果令人遗憾。没了优惠, 价格上涨, 质量下跌。
正想追随希腊裔去Brooklyn时, 有朋友提起唐人街的一家发廊。它恐怕是那儿最大的美发店, 从路边上就可以望见那一长排的大玻璃窗。进门后, 入眼的是无所谓的随随便便, 进耳的是粤语、普通话和点点英语混杂的高喊声。好一幅 “无政府主义” 场面。
师傅是马来西亚的中年华人, 高个子, 烫过的长发过肩。说是在伦敦学的美发。不明白为什么在唐人街干。他性格怪癖, 爱搭不理的样子。不过干活儿时很投入, 把满头加上夹子, 一层层地慢慢修。花了50分钟, 可收费才28美元, 再加小费。都说唐人街的生意经是价低量多。可这个价, 也太低了!哪个发廊比这家更便宜?
剪出来的头发可以接受。除了价廉, 跟他的好处是, 每次可以在唐人街吃一顿; 另外, 去马拉西亚前, 从他那儿得到了不少信息, 特别是他家乡槟城的游景小吃。他谈起故乡时, 像换了个人, 眉飞色舞, 滔滔不绝, 比对我的头发更感兴趣。
发廊令人失望的地方就是它的环境; 其次就是师傅动作缓慢。即便如此, 也没有另换门户的打算。
人生往往是你不想的事, 它倒是来敲门。
介绍“四重奏沙龙”的朋友又来诱惑我。惊讶地发现了她保持一头美发的秘密。她的头发是分别由三个不同发廊承包管理:一处剪发, 一个染发, 第三地只做打湿吹型, 就是dry bar的那套。怪不得她那比我的还黑还硬的茂发, 根根都老实地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发尾都朝着好像是GPS标定的指向。都这么完美了, 她还是寻摸不停。我和她比起来, 真是小巫见大巫。

她带我来到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开的家庭店。母亲和儿子做业务, 先生管钱预约。一位年轻友好的黑人负责洗发和扫地, 一两个美发师轮流烫发剪发。妈妈J高头大马, 头发眼睛漆黑, 看着有点凶, 不爱说话。儿子随母亲, 高壮的像个运动员。爸爸相对白净矮小, 也是一副严肃样。
与以前的发廊比, 这家最旧, 面积也不大;两把洗头的椅子, 五六把剪发的椅子。
也许是体大力足的缘故, J用劲猛烈, 我要不时地调整脑袋的方向, 适应她的手劲, 否则头皮恐怕会被拽下来。好在只需忍耐10分钟。价钱才20美金, 另加小费。谁能料到, 最便宜的剪发是在唐人街之外, 还是在犹太人家?
J有自己的生意经,她把一个精小的时钟摆在她的理发镜台上, 时间对准她和顾客。她花10分钟左右剪我的头发, 从没超过15分钟。我给她算了本账,她每一刻钟赚20美元, 另加小费。除了无法与VS的美发师比外, 她一小时的收入要比唐人街的师傅高好多, 也比希腊裔的高, 和那位日本人的差不多。J不是以我这种短发赚钱的。但是, 她也不拒这类小生意, 只不过是快刀斩乱麻地把它收拾打发走。
新发廊有不少优点, 也有不如人意之处。J的最大缺点, 就是缺少一贯性。这次修剪的发式可能令人喜气洋洋, 下次就出来个让人半尴尬的怪样。跟她耐心说时, 她还不高兴。不过, 她是个好人。时间久了, 也不怕她的 “凶相”, 还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触。
从未料到, J让我放弃了见异思迁的行为, 与她共处至今10多年;脑袋适应她的强拉拽扯如此之快;她的神速节约我那么多的时间;发廊离家和办公室比过去任何沙龙都近;预约也方便。更没料到, J从没涨我的价 (这是后话) – 可能跟我是名好顾客有关: 不毁约、提前赴约、剪短发、付现金、给好的小费。
(二)
30余年光阴, 单指一挥间。天地千变万化, 品味走高走低, 想法涌入涌出。。。发廊在变, 头发也在变, 还变得更快。随着阅历的增加, 追求也在变, 越大 (不是”越老”) 越觉得时间飞速划过。为了省事, 更是因为发质的改变, 头发留的越来越短。留短发后, 才真正体会到头发的难以驾驭, 明白了VS美发师说的 “小弯儿” 的意思 – 就是该直的不直, 横冲直闯, 东倒西歪。更懂得她预料的 “想显也显不了” 的含义。
也逐渐明白, 十全十美的美发师从来不存在。就算是跟了那位一见钟情的希腊女郎, 她也不会次次令我满意, 可能会像J那样, 有不一致的时候。简单的道理要折腾这么长的路后, 才悟出。
生活在通货膨胀的都市, 美发费却是步步低。昂贵的曼哈顿也显出让人负担得起的一面。如果不 怜新弃旧 , 尝试冒险, 可能现在还出没于高价的沙龙。
数年的长途跋涉, 找遍了半个曼哈顿, 才发现最适宜的发廊就在家后院; 最贵的最有名气的, 不见得就是最投缘的; 最便宜的也可能是最合适的。
(三)
沙龙有开有关, 兴衰巨变意外非常。
上个世纪, 魅力风靡的VS在曼哈顿只留守了一个动荡不安的小店。当年在第五大道上的招摇门面, 早早就被狭窄巷子里的小门脸取代。上个月, 无意间路过那儿, 看到玻璃窗上贴着店面出租的海报。店里还留着几张它的模特大照。VS临时搬到了一家多功能的活动场所 - 画廊和社交共栖的地方。沙龙和画廊在一起, 别有意趣。据说VS特别想留在老的店。可是, 房东不但不降价, 反而提高了租金。疫情期间,满市的空房, 怎么还加租? 不可思议。
VS现在的价目栏标出, 120美元是它的起价。这是我快30年前时付的中等价。
去年夏天, ”丝发伴侣” 也撤出了”日本城”, 只剩下在40街的那个小门面。

”四重奏沙龙” 在经济兴旺时就关闭了。猜想与涨租有关。欣慰的是, 它的Brooklyn发廊(使用不同的名字)仍在营业。三天两头儿地 Email诱人的美发广告。可惜, 从未登门拜访过。
唐人街的大发廊, 也是几年前经济红火时就停业了。店面一直在出租。新冠让租赁不容易, 想必它至今仍然空着。
疫情以来, 自己在家对着镜子, 拿着推子剪刀修修剪剪。常常是坑坑洼洼, 参差不齐。去年11月, 实在憋不住了, 全副武装后去J的发廊。
发廊规矩地遵守新冠期间的指令, 塑料帘子隔开每把椅子, 本来就不大的地方看上去更拥挤。顾客寥寥。J和过去一样, 10分钟拿下了我的头。
J的先生收取25美金, 多出5元, 不算小费。自从10多年前来他家落户后, 这是他们第一次涨我的价。比预想的要低。
祈求他们生意继续, 快速复原, 守住曼哈顿。这样我也不必再寻下家。听起来有点自私, 不过是心里话。
注明:照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曼哈顿的阮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政专业,美国教育硕士,在美国从事大学招生和服务工作20余年,现在曼哈顿做教育咨询和美国学校申请顾问。


推荐阅读其他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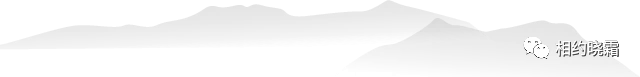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