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刊征稿 | 别了,爱情


对,没错,《三联生活周刊》纸刊向你征稿啦!
这是一则稿件征集启事。
本次征稿的主题是别了,爱情
。在2月中旬,我们即将发布一期关于爱情的杂志,被选中的稿件会刊登在这期杂志中。
截稿日期
1月25日。字数3000-5000字。
来稿格式:
别了,爱情+标题稿件请发送至

在任何一个时代,爱情都是奢侈品。真爱难寻,获得更难,维持则难于上青天。它如此之难,以至于几乎所有的爱情喜剧凡想成其为“喜剧”,就不得不在“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时刻有自知之明地打住。
对美好爱情的想象往往先于现实的爱情而存在。这种想象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与人对自身的理解、对自身与他人关系的理解有莫大关系。

《红楼梦》里宝黛之间的古典爱情固然绝美,却只能存在于古人的宇宙中。“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黛玉常挂嘴边的话“我为的是我的心”,不仅是说出来的话,她也是这么做的,这才有她与贾宝玉一往情深的纠缠和悲欢生死。可这样的一颗心,在现代社会中哪里有空间呢?首先那“灵河之畔一颗绛珠仙草”和“神瑛侍者”的前世想象,在只有现世的世俗现代社会中就从信仰上泯灭了,所依托的爱情想象也随之不复存在。

再以民国时期为例,爱情展开的方式也与今人所理解的有所不同。
沈从文的小说《边城》里,每一个人为的选择都造成了时间上的错位,最后导致爱情的悲剧。
天保大老喜欢翠翠,托一个熟人来问老船夫的意见。老船夫说,“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大老走的是车路,应当由大老爹爹作主,请了媒人来同我说的。走的是马路,应当自己做主,站在渡口对溪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
这两条路,一条是绕路,一条是近路,交通工具不同,速度也各不同。带话的人对爷爷说,“那好。见了他我就说,‘笑话吗,我已说过了,真话呢,看你自己的命运去了’。当真看他的命运去了,不过我明白他的命运,还是在你老人家手上捏着的”。
老船夫爱翠翠,想通过这个智慧的安排为翠翠找到真爱;可这个安排本身,就是悲剧的起源。这一“触机”,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人人出于朴素良善与单纯希望的言行,却是各种不凑巧。

天保大老和傩送二老轮流来给翠翠唱歌,天保不擅长唱歌,弟弟唱了一晚,他不愿意让弟弟代唱,就离开了边城。待到二老在对岸唱歌时,翠翠在梦中听到歌声,老船夫知道是二老在唱,但不知道二老爱翠翠,“只道是河街上天保大老走马路的第一招”。大老离开边城,命丧水中,二老因此失去了对老船夫的信任。老船夫对二老说,“翠翠说,在梦中被一个人的歌声浮起来”,而那晚二老是代大老唱的。
沈从文通过老船夫的心思意识到,“一开始自己叙述这段事情时,方法上就有了错处,故反而被二老误会了”。最后老船夫在愧疚中死于雷雨之夜,二老也离开了边城,与翠翠未能相遇。
沈从文所理解的爱情是发乎情感与灵魂的爱,且顺乎天意,人为的计划和目的性正是爱情悲剧的根源。他将希望寄予“明天”:时间成长翠翠,似乎正催促她在另外一件事情上负点责,可她却不知道是什么,只是“欢喜看扑粉满脸的新嫁娘,欢喜说到关于新嫁娘的故事”,“孤独时向天空的一片云一颗星凝眸”。在爱没有到来时,翠翠“只是想得很远,很多,可不知想些什么”。这就让翠翠的命运有了开放性。
看别国人的爱情,这其中既有普遍人性的东西,也离不开文化背景。伊朗电影《一次别离》讲的是婚姻中的摩擦与裂痕,妻子意欲离开丈夫移民。在人情义理古风犹存的伊朗家庭中,导致“别离”的因由是什么?这“别离”不仅是家庭的别离,实则是政治选择的隐喻:每一个人的选择都出于信仰或情理,都有道德上的理由和纯洁性,但为何无罪之人,命运最终全是悲剧?罪究竟在何处?“别离”何由?原本相爱的人是否还有重聚的可能?导演没有明确给出答案,却又将之化为看不见的动机蕴含其中。

又来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表面上,这是一个“婚内出轨”的冒险故事,可安娜的爱情悲剧却绝非出于一个简单的道德审判。
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写道,托尔斯泰深深关注的是道德问题,这不是随便哪个读者能够轻易读出来的。这个道德问题当然不是指通奸,安娜为此付出了代价,但这不是托尔斯泰的关切。在小说里,只要安娜隐藏她与沃伦斯基的私通,她就不会拿自己的幸福和生命做代价,但她没有隐藏。“安娜遭受惩罚,并不是因为她的罪,也不是因为她离经叛道,社会的习俗与其他惯例一样都只是暂时现象,她的受惩罚也与道德的永恒要求不想关”。

纳博科夫从中读出来的是:列文的婚姻是建立在形而上的爱情基础上的,不仅仅是肉体概念的爱情,而是相互作出心甘情愿的牺牲和互相尊重的基础;安娜-沃伦斯基的结合仅仅建立在肉欲基础上,这就注定了它的劫数。现代读者也许已难再接受这样的劝诫,但这的确很可能是托尔斯泰想要传达给世人的:爱情不能仅仅是肉欲的,这样的爱情是完全的自我中心主义,而自我中心带来的是毁灭而不是创造。多么老套,却又多么深刻!
爱情的模样或许有其永恒的一面,却始终随时代变化而变化。
到了英格玛·伯格曼的《婚姻场景》,对婚姻虚无的烦恼首先来自于每天不得不追随的“时刻表”,时间早已不再是自然的,而充满了人为计划,被分割成一个个时间段充塞在现代人忙碌的日常生活中。爱情成了一件与“时间管理”相关的不自然的事。许多当代爱情故事里,飞机载着情侣各自飞往不同的目的地,频繁地变换着地点,频繁地与不同的人相遇,频繁地离别和异地,相聚不再有阻力,移情别恋也变得只是平常。

在这层扁平化的表面下,再也没有徒步时代“桃花潭水深千尺”和“一期一会”的深情,速度让一切加速成形,也让一切加速解体和腐朽。况且,如果说感情是流动的,婚姻则不再具有这种灵动性,成为一份社会契约、一个约束性的框架、一个规范精神和肉体的制度——在这个近乎固定的制度里,我们有多大的空间腾挪,又有多少不背离道德和责任的自由的可能性?
《三联生活周刊》每年在春节期间或之后都会推出一期爱情特刊。这是个永恒的话题,编辑部可以提前准备,这样能在过年时放个假。过去几年里,我们做过《天上的爱情,人间的婚姻》《说吧,爱情》《读吧,爱情》《听吧,爱情》《看吧,爱情》等,更多是对美好爱情的讨论。
今年我们想讨论一下爱情的另一面:不那么美好甜蜜、不那么亲密无间的爱情
——随着时间流逝或在外力内力作用下褪色和出现裂缝或罅隙的爱情,变得失去信任或激情的爱情;爱情的疏远或背叛,爱情的疲惫或枯萎,灵魂与肉体不再统一的爱情,坠入凡尘的不知是否还能够称之为爱情的爱情……
我们终将面对爱情里一切尴尬的、不堪的、沮丧的、破碎的、令人黯然神伤的一面。我们能否弥合这些缝隙,跨越这些沟壑,重修于好?或者,当这些不美好乃至疼痛接踵而至时,我们该怀疑的是当代爱情本身?在怀疑之中,我们又是否能够对未来仍寄予希望,探索爱情“聚合”的新的可能?也许一个更高的要求和更深的渴望是:我们是否能找到当代爱情的新的叙事,已让这种想象引导我们前往幸福的爱情未来?

如果你有这样的爱情故事愿意分享
欢迎投稿
截稿日期1月25日,字数3000-5000字
。
来稿格式:别了,爱情+标题
稿件请发送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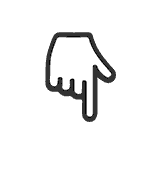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转发到朋友圈,转载请联系后台。
点击封面图,一键下单
「图像社交时代」
▼ 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周刊书店,购买更多好书。
阅读原文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