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于晏:练习|谷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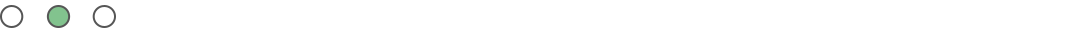
撰文丨魏玲
采访
丨魏玲 葛佳男
编辑丨王天挺
彭于晏38岁了。在一家海滩上的老五星酒店,他主动介绍自己。前一天夜里他飞来海口。像以往一样,他早起跑步10公里。
大堂连结海洋。绿树环抱,椰子林、三角梅和大叶油草从海岸线尽头升起。
“跑步就是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他揪着头发,努力把思想转化成语言。不成功时他会用那双干净、全神贯注的眼睛看着你。
新电影《紧急救援》里他没化妆。有时年龄帮到人,彭于晏不用只拍那种英俊小生的电影了。不工作时,他过着正常、传统的生活,围绕家庭运转,家庭指母亲与姐姐。她们陪他读剧本,母亲有时会把原著小说也读完,打理起居,为他能多睡一小时反复改期航班。他则在每份工作结束后带她们去世界各地旅行。他不介意承认,工作上多辛苦危险的要求都不拒绝,一个大原因是渴望换取更多能用在家人身上的钱与时间。
“经济能力好转了,我的时间有限,我妈妈时间也有限。真的。大家时间都是有限的。”彭于晏说,“没有东西能改变这个。如果去想,越想就是越悲哀。”
拍新片这一年他都住在海边的酒店。太平洋另一侧的水抽到影棚蓄水池,七十米深,可以放几架飞机那么大。墨西哥海水重度污染,眼睛接触发炎,刺痛,好莱坞演员全部拒绝下水。每天他跟导演说,导演,我先去马尔代夫等你,然后跳下去。溺水那天也是。上来之后所有人都不说话。奇怪的是片场有那么多人,那么多机械,却可以一点声音也不发出。
晚上健身教练陪他喝了几口威士忌。教练没说什么。他也没说。第二天又是下水。
噩梦也没有做。绳子在水下70米卡住,岸上拉威亚的人使了全劲,不知道他卡住,还在拉。机器一直往下沉,他被两头拽着,没有氧气瓶,像拔河游戏中间那块红色标布。打浪机做的浪非常大,他觉得比真海还恐怖。忽然就呛水了。喉咙被水顶开,每咕咚一声,水挤出一节身体内部的空气。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溺过水,知道后面是什么,挤光需要30-40秒,胃先灌满水,然后鼻子进水,肺部缺氧,脑缺氧,就死了。
海底等着六个水肺潜水员,出问题他们会给他氧气,但他们上来的时间他能不能撑到?如果他们以为他的挣扎是表演的一部分呢?他伸手够工具包,想拿刀划开绳子,但摸到的工具是假的。剧组怕演员出危险,往工具包里装的全是道具。他感觉出不对,扔掉刀,潜水下去解绳扣。黑暗使人完全失明,一失明就恐惧,恐惧加速缺氧,能依靠的只有你的两只手和求生欲。绳扣开了。上到水面才发现手指被什么锋利边缘削掉一块肉。
每次上岸他有五分钟时间洗眼睛,泡一个小水池暖身子。“当年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斯莱特拍《泰坦尼克号》泡过的,”彭于晏说,“跟好莱坞一样(待遇),给巨星泡的。”
“之前拍《破风》的疤,《阿信》摔的伤口,现在晚上还会痒。你问我碰到这些危险、负面,有没有一个很好的管道排解掉。你知道吗,溺水那天拍完以后,我还要再拍一个月,一个月天天泡在那个水里。我就告诉自己,我在马尔代夫,天气很好,喝杯咖啡,开工。”他用那双干净的、全神贯注的眼睛看着我。“就是一种信念,真的。人的意志很难解释。意志可以超出自己的想象,去决定你的行为。”

拍水戏上岸后,彭于晏和王彦霖在温水池中补给。手被海水侵蚀受伤,变得粗糙
我知道但没说的是,一个演员一旦开始做付出型演员,那他的问题是后面每一个找来的导演都准备好了苦给他吃。而这个问题的麻烦在于,后一个准备的总会比前一个多。我知道他也知道这一点。
他们希望他穿过火场,不带氧气潜入水下飞机遗骸,撞破玻璃同时格斗、射击,从高楼纵身一跃(毋庸多言,务必同时保持身姿和表情好看)。有时他们希望他的动作比高危职业的真实情况更惊险——荧幕里太小了看不清,但新电影每一帧画面直升机下吊着的小点都是彭于晏。还有部分愿望是即兴的。
工作人员提着防火浆过来,“导演要烧你,没问题?”
“OK,OK。”他说。
在墨西哥湾每个早晨,彭于晏与导演林超贤一起跑步。他们跑8公里。多年来林超贤渴望一个真正的搭档,不是“执行命令”,而是“并肩作战”。他说要把“所有懂的东西、我的功力全部传给彭于晏”,“我希望他是‘唯一’的。”
32岁那年春夏,彭于晏每天练习骑车6-7小时,为林超贤拍职业自行车公路赛的电影做准备。练体育项目和练乐器一样公平:练了就是练了,没练就是没练(骗子不管多巧妙也装不出精通乐器的样子)。他练“破风手”,一个有意思的、像从希腊神话中移植出来的工作:速度越快,风阻越大,风阻越大,越耗体力,于是需要一个家伙人肉挡住风阻,消耗自己体能以保住身后伙伴体能,助他人赢得比赛。
最后阶段的赛坡,运动员只冲刺一次,但拍摄要求彭于晏一天冲8到10次。林超贤说他相信破了纪录,“我是说演员被折磨和付出的程度,那是演员为电影能付出的意志上的极限”。
“有时灯没好,有时其他人没好,你跟他说,再冲刺一遍。他都说好。”林超贤说。“他的意志力没有一次掉下来。”

彭于晏和健身教练在剧组跑步
彭于晏对意志力的日常检修保养从每个早上跑步开始。像乐器校准音。他说你必须一直训练你的意志,每次都付出一样多的努力,看上去是体育锻炼,实际是精神练习:“你反复去训练:我规定我自己做的事情我做到了。”
谈这些时他的表达更清晰有力了:“即便重复再多次,每一回你的脑子也会告诉你,下次再做就好,下次再骑吧,休息一下再骑。但我会想,如果连这个都做不了,我怎么告诉我自己我可以在这个职业往深处走,走到我想去的地方呢?连骑个脚踏车,骑到这个山,或者跑个10公里,我都放弃,那我拍戏演不好,算了,下次再拍。不行。我必须做到。”
《奥德赛》里,特洛伊战争之后,奥德修斯要回家须经过海妖塞壬的水域。塞壬歌声妖异,瓦解掉驾船者的心神,叫他们撞向冰山。奥德修斯想听听这歌声。他用蜡封住除自己外所有船员的耳朵,然后把自己锁起来,捆在桅杆上。这样无论发生什么,他的头脑都无法命令肉体做出毁灭之举——人的精神没有强大到能固定在曾达到的程度上,像钢水冷却成型(“奥德修斯知道,光凭意志力不足以抵御塞壬的诱惑”),通过每日练习,你帮助它回忆,再帮助它重新做到。你和你的精神就是这么个关系。此前的都不算,每一天都是新的。
他脚踏实地学到的知识是那12个字:跑步就是左脚右脚,左脚右脚。无论多难的目标,只要动作能被拆解,都能成为一种练习:
1 提前知道塞壬的歌声在哪儿;2 设定目标,把愿望变成承诺;3 保持警觉,不被环境临时变化干扰;4 公开目标,让自己呆在他人视线的监督下;5 练习,重复这个练习,像戒酒协会标语说的那样:一日一次,直到变成人格的一部分。
当演员上他从没觉得安全过。十多年前他为一部电影的男配角色练习两个月拳击,男主角没来,电影流拍,无事可做只好又练一个月,三个月天天去拳馆,结果几年过去《激战》找演员,他的练习匹配上去刚好吻合,为《激战》多练的功夫又在几年后匹配了《黄飞鸿》——至今每天走进片场,他都带有迷信色彩地担心,命运是一款打点连线游戏,这一部演不好,下一部就不会连上了。一个点连结下一个点。一条想象的、虚构的旅程,你必须使自己感觉在不断前进,练习是能抓住的唯一绳索。
有时他想这些能一层层想下去。流量很好,拿奖很好,有钱很好,“赢”很好,样样都是好东西。你表演肯定希望演的东西被看见。就像他也喜欢画画,一个画画的人,没人看也会画,但有人看好开心啊,画完还能赚钱,太好了可以以此生活了。梵高就没有样样都要到。但梵高是他的偶像,他的一生是他的选择。
样样都是好东西,但如果不是样样都要得到,你会怎么选?他特意去了梵高最后那个精神病院,去了瓦兹河畔(Auvers-Sur-Oise ),普罗旺斯,站在他画那些画的地方。梵高住的房间很小,布局有一种医院风格、不舒适的整洁,家具全是直角,铁丝床硬且窄,椅子也是。清醒时梵高在这里作画,疾病发作会被带去旁边一间屋子,浸泡进冷水里,直到恢复平静。他努力想弄明白在这里度过生命最后一程的感觉。不可能会愉快。他想以生命为比例尺大概是这样,最终决定你成为哪种人的并不是你的能力,而是你的选择。
拍摄这年他经历了两次“万一”。一次是溺水。一次是他的朋友高以翔的死。他们都是台湾人,去加拿大念书,又回内地拍戏,在同一段时间被雪藏。无所事事的日子,两个男孩凑在一起打篮球。
“你碰到的所有人都是‘乘客朋友’,他下车了就是下车了。”彭于晏说。
世界变动不居,他庆幸自己还有一个平行空间可以去。电影的空间里,电话费、水费都不用缴,只需专注地体验:精疲力竭,命悬一线——导演说cut,喝酒,烤肉,抽水机把恐惧抽光。这个空间既短暂又虚幻,你可以在其中停留一会儿。然后独自走向更深处。
1982年至今彭于晏只见过父亲四次,每次不超过几小时,男人或人该怎么面对世界他靠自己学习。他看重持续不断的练习,相信付出比得到可靠。拍《翻滚吧阿信》时陪练的小孩当时五六岁,长大了,准备出战东京奥运会。他们的努力是真的,他的也是。
这是彭于晏的练习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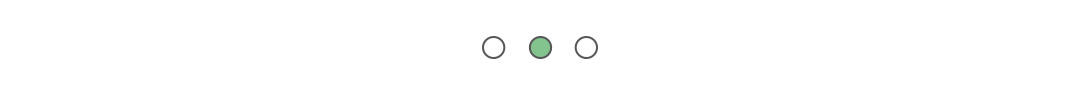
口述=彭于晏
我想如果真被巨浪压到水中,拍到的话不是更好的、更真实的镜头吗?
有一场戏我被火烧,500度的气泡火直接扑到脸上。太烫了,烫死我了。我姐姐就站在下边看。
那天导演一直加加加,我要爬上楼梯,楼梯正在倾斜、歪倒,一面爬那个平台一面倒,我还要救底下的人,反正很复杂,船已经要倒了,导演要再往上加爆炸,炸在我身上,凌晨他们又说涂一下防火浆,我说为什么,他说导演要烧你。

在涂防火浆的彭于晏
全身涂防火浆,脸,皮肤,衣服,涂完非常凉,凉到我想赶快烧我吧,太冷了。我的衣服能扛800度。危险的是进气口灌烟,涂防火浆的大哥跟我说你闭气,不能吸,不然没烧死肺也坏掉。
我没有准备,非常害怕。你会想,被烧了会有什么后果?是真的要烧很久,还是直接脱,还是有人上来帮你灭?如果我被烧了,我还能演什么戏?会想到有些演员受过伤。脑子转很多,心跳非常快,力量也非常大,因为肾上腺素上升。而且会很集中。我就想,哦,这是救援队的人每天碰到的感觉吗?
真正糟糕的感觉是你得等待。来了没有,来了没有,要来了吗。
500度火扑到脸上是什么感觉?非常非常烫,火从身上滚过,不像你突然摸开水壶,哎呀好烫,是热气碰触衣服,十几秒到三十秒到一分钟里,温度在你身上一直一直升高。你意识非常清楚,知道如果没有衣服你肯定烧化了。讲的深一点,那一刻最难过是想到家人。你害怕还有很多事没在这个生命里完成,我怕我走了,我母亲、我姐姐……这些东西涌上来造成了恐惧。因为你没被烧过,对痛的恐惧是不存在的,你恐惧的原因在于你的羁绊。
那就是你为什么干这个。做演员的信念是什么?看的人只觉得是动作嘛,大片。你可以选我安全一点,也可以选我要试,都是你一念之间。都不说做演员,那做人的信念是什么?
是我选择了做这个。
你只有做了,只有自己站在那儿,才有这个体验,如果你做都没做,你不够了解自己的内心。如果没有过去拍的这些电影,我今天不会这么了解我自己。

很多场景我在直升机下面悬吊,荧幕里太小了,一个小点,也看不出是谁,一吊吊一整天,加起来十几个小时。那个救援队的直升机长总是问,怎么还不放他下来,说我们平常下去一次就十分钟,他怎么一下去四十分钟不上来。因为电影要抓到最好的角度,不是五分钟、十分钟能拍到的。
绞车手是我的教官,他一直帮我控绳索,很厚的手套都磨破了,有天他跟我说,这种高度他们专业的人其实不太下去,我说为什么,他说太高了,毕竟有万一,万一机器怎样,绳子断了,这个高度你就再见了。
另外一场水泵连抽几天,把225吨海水抽进蓄水池,一下子炸掉,我在水前面跑,跑不掉就被水拍挂了。那是真船舱,225吨水惊涛骇浪一样压进来。他们说,你只有一秒钟。我自己练一下,除非被卡到,应该可以。我想如果真被巨浪压到水中,拍到的话不是更好的、更真实的镜头吗?
他们叫我做,可以做我就做。我想如果一秒钟没跑到,那就没跑到。后来我跑到了。
陪练的小孩当时五六岁,现在长大了,准备出战东京奥运会。他们的努力是真的,我怎么可以不是?
我并没有非要怎样,其实是你一定把身体练成那样,你才像你的角色,你像了以后你才能演他。
我演体操选手林育信,他是个真人,我如果不把自己变成那样,怎么对得起林育信?怎么对得起愿意陪我一起训练的所有体操队的小孩?那个小孩当时五六岁,现在他长大了,准备出战东京奥运会。他们的努力是真的,我怎么可以不是?
像《紧急救援》,又是火,又是水,但是中国救捞队天天干这个,那我为什么不真下去?
我不会复习这些技能,拍完就忘了。但那段时间跟人的相处会留在你生活里。前几天在台北带我妈吃饭,旁边一桌人打手语,如果你不练手语你是看不见的。拍《听说》之前我从没发现在街上有那么多听障朋友。
刚从东京带我妈回台北时,包括昨天飞来海口,飞机抖得非常厉害,我现在每次坐飞机都会想,如果真的出事了,真的crash(坠机),要做什么,有没有可能救人?我一听到baby哭,马上找逃生门在哪儿,下意识就数飞机上有几个老人,多少轮椅。
我知道他们在哪儿,如果真的出事了,我的个性,那我应该能比一般的乘客多出一份力,告诉他们往哪里走,先带谁——但也会拉回来觉得彭于晏你有病吗,想太多了吧,你是谁啊(笑)。但你本能的意识自动就开始转:等一个那个baby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在珠海训练吊挂时,突然接到电话说有船出事了。船要沉,救捞队只能带着我们下去救,那时我才体验到真的状况:被救上来的每个人都很“空”。你以为他们会说“谢谢你救了我”,会很感动,没有,上来就是惊恐,没有任何情绪。
这好真实,如果这是个剧本给我,我不可能想到我要这样演。
浪这么大,救生员下去,用钩吊装两个人,如果他只能吊一个呢?他就要选择。另一个他可能没时间救。每周你碰到一两次要选择生命:“你,我能救”,“你,我不能”。那你回到家,面对自己正常人部分的生活,你的老婆、小孩,你能跟他们分享吗?你跟他们吃饭还能保持跟早上起床一样的心情吗?
所以我觉得水里火里的,我就应该自己去,我如果不去,救援的人看了觉得彭于晏演的不对,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们的家人,还有那些根本不知道救捞队是做什么的人。

《紧急救援》中的交通海上应急反应特勤队
《黄飞鸿》第一场动作戏就从三楼往下跳,那时我没想过要变动作演员。第一个镜头是三楼摔下来落地再接一个长镜头打。“咚咚咚”下去以后,安全,没事,还可以继续演,你还在那个感觉里。那个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就是会上瘾。像你今天吃了一个很好吃的东西,你记得味道,你就还想再吃到。
但让你满足的阈值会越来越高。这个就是人性。对人性我很好奇。
喝咖啡,从速溶,到星巴克,到手冲,你会觉得喝不回去了,你的大脑会一直追求它被刺激到最难忘、最特别、最美味的东西。这个叫贪食基因。它记住,它就会一直想要。拍戏是一样的。试过之后你发现这种感觉是你从未有过的,是你平常在家里,在彭于晏自己的生活里绝不会碰到的。你只有做演员才能碰到,于是你越走越深。
你说观众真的非要你本人在上面吗?吊挂在直升机下,荧幕里那么小,看不出是谁。还是导演百分百要求演员本人上?都未必,到最后变成你自己和自己的事。如果全部能够我自己做,我一定要全部自己来。
溺水那次就是“万一”发生了。我没跟任何人倾诉。我游泳很好,以前是参赛的,但这个戏拍完我未来一年都不想下水了。我洗澡都不想泡太久。
你碰到的所有人都是“乘客朋友”,他下车了就是下车了
38岁我常常告诉自己,没有下次,就只有这一次。人生只有今天。
我不想让跟我一起工作的人觉得这就是一个明星来赚钱,我很踏实去练体操,训练六个月,付出让我踏实,我认识的体操朋友是真的朋友,教练,武行兄弟,我们真的相处。
我认为我们只是来这个世界体验的。我们离开以后,就会回到另一个世界。过去这一年教给我对周遭的人尽量真实,有什么话尽量说,真实地爱他们,花时间在他们身上。而道不同的人就不要浪费时间。因为你碰到的所有人都是“乘客朋友”,他下车了就是下车了。
Godfrey(高以翔)是我见过最谦逊的一个艺人。
他去更好的地方,我们还留在这个空间,以后我们也会走。做演员会给人一种感觉是你的付出别人会看见,努力不会白费,其实很不容易,你来一个新的地方工作,要被认可,他花了很长时间,他中文练了很久,口音学得很难,好不容易才有了这样的露出。
我会想如果今天我要走了,我还有什么事没做。我还没结婚生小孩,也没照顾好家人,我跟我妈还有好多地方没去,还有两个姐姐。我外婆一直想环游世界,但我妈妈没有能力,她一直在努力赚钱养三个小孩,一直说等赚够了钱就带我外婆去。
我外婆希望家里有一个人可以当明星,这就是我做演员的原因。我外婆很喜欢看发哥(周润发)。后来我真的跟发哥演了《寒战(二)》。我常常梦到外婆,她还是我小时候的样子。我跟她聊天,说我的状态。火烧水淹这些不讲,但她应该是有保佑我,每一次。
我做这行17年,如果外婆都有看见,她应该会非常高兴。她每周六做炸酱面,加上好客,家里来很多人吃面,然后打麻将。我最想回到小时候,小学一年级,我负责排麻将,大家吃完炸酱面,过来打麻将。

彭于晏和妈妈一起旅游
2019年我带妈妈去南法和南意,去了十几个城市。不是旺季,没有游客,非常棒。当地人不太用手机。还在种葡萄、橄榄、番茄。还住在古城里,有人用油灯。环游世界也要有能力,为什么坚持下来,除了喜爱演戏,我相信还有远远比那个大的东西推动你去做你觉得不可能的事。
经济能力好转了,但我的时间有限,我妈妈时间也有限,真的,大家时间都是有限的,没有东西能改变这个,如果去想,越想就是越悲哀。不要为了工作把你的生活给(覆盖掉)。
以前我觉得,工作就是工作,工作最重要,女朋友都不用交,因为没有工作就没有更好的生活,我要让家人过更好的生活,为了这个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没问题。但这一年让我有更多体验。你看得到“生命”。就是你真的要开心,工作也一定要开心,那样你就不会觉得你的工作是工作,你的时间就不浪费了。
我常常在脑子里想这个。但是没有人讲,就留在脑子里。
稻子长出来,淹水没有了,怎么办呢?人在短暂的生命里,就是要不停地克服困难
作为演员的安全感我一直没有过。比如现在这部戏,我会想如果我表演不好,是不是我就没有下一部戏了?
就流量说,我不觉得我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我还是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天在,稻子长出来,淹水了,没有了,怎么办呢?那重新再耕。人在短暂的生命里,就是要不停地克服困难。
我为什么会拍我现在拍过的戏,因为这些东西代表了我。市场喜不喜欢,流量喜不喜欢,那是他们考虑的事。每一天,拍戏的过程,在这个空间里跟导演,跟大家,创造一个moving picture,这是我喜欢的创作。外面讲你是偶像明星/实力明星/动作明星/流量明星,那是虚拟世界给你的分类,对我一点都不重要。对我重要的是我花出去的每一分钟。
我演《听说》是我这辈子最不开心的时候,每天要打官司,可能要被告,这个戏上不了,我觉得我会不会害了导演,害了团队、投资方。投资方也会问你是不是有问题,要把你换掉。郑芬芬导演坚持要用我。我非常感谢她。
那时我就明白,你没办法知道后面的东西,你只能做你此刻手中这个。

我常常检视我自己。在我没名的时候,人家不觉得你帅,不觉得你是任何“担当”,今天把你放进去,是因为你的名气。这是很实际的。等你又没名了,不是什么明星了,最终留下来的是什么?是电影院里面你拍的那个DVD里的你。
想清楚以后,其他都随便、无所谓,我只要有我拍过的作品。我希望我成为一个“我觉得的好演员”。“我觉得的好演员”就是能演什么像什么,把那个角色创造出来,让观众得到、带着离开电影院。你收获的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有你的积累,当下的付出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等你回头看,它连成一个轨迹,是你做的每一个点连结到下一个点,所以你一定得做。你害怕、恐惧,你放弃,你就没办法连到后面那个点。
所以每一个当下的戏、每一个当下的角色对我的人生都很重要。我只有此刻这一部戏。这一部戏做完做好才能连结到下一部戏。我的经历是这样的。
如果一分耕耘之后,田没了,你的收获是什么?你再碰到同样的困难你可以克服了,这是你的收获,所以我常常把自己逼到比较紧绷,以备应对更难的情形。
未来有没有电影都不知道,这是现代社会的事实
2020年我38岁了。现在的行业环境跟我刚出道时很不同。未来有没有电影都不知道。在小屏幕上竞争注意力,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事实。没法改变的东西。
以前微博我会自己发,现在世界变太快,大家好像要用这些平台宣传、塑造自己,博得外界喜欢。大家在乎“是不是最新的”超过“是不是真实的”,我发现以后,觉得很复杂,没办法反应。
环境变太快,有时讲什么都不对,而且你如果能检视自己,平衡工作与生活,照顾好你爱的人,你才有可能真的对他人感同身受。每个人都有他很艰难的人生要过。
这一年我学会了修冷气。还有自由潜水和急救,开放式骨折第一时间怎么正确包扎,每个器具怎么应用。拍《紧急救援》我不化妆,因为它讲的是真实的上班。重要的是像你的角色,想好看可以去拍把自己弄得很好看的戏。
其实我想过,我是真的喜欢演戏吗?可能不是,我好像是喜欢体验。因为我觉得自己的世界很复杂,好多人际关系,好多事。但电影的世界不一样,电话费、水费都不用去缴,很多人帮你打理,你只要专注地体验,这个世界比现实世界来得开心。

我一辈子只见过爸爸四次,男人该有什么,我靠自己学习
有很多戏我家人觉得要拍我就拍。因为我也没其他人,除了经纪人帮我接case,《听说》就是妈妈觉得要拍,《邪不压正》我妈还把书看完了。妈妈对小孩是永远的担心,她还担心我两个姐姐,不停地担心。她可能希望我有一个好的家庭,希望我工作能够顺利、安全。她看那些幕后花絮都会哭,不敢看。
拍《热带往事》那晚,我拉着我妈散步,我要跑步,叫她出去走,结果她摔伤了。休息了一整年。我非常后悔。如果能改变人生中发生过的一天我希望是那一天。我不会那么晚拉她出去,她看不清,走路拐到,两个膝盖髌骨碎了。
这是最后悔的,那几天我都内疚到睡不着。拍戏带着她来本来希望她开心,结果变成这样。我非常内疚。
我一辈子只见过爸爸四次,每次不超过几小时。所以对他没太大印象。当我拍戏演跟父亲的戏,我都会有新鲜感,因为我不知道跟父亲相处的感觉。
最早是刘松仁,拍《恋香》和《我只在乎你》,他演我父亲,跟梁家辉演过四次父子,《邪不压正》里面也是到处在找爸爸,这个蛮有意思,我的戏丰富了我的人生,通过跟这些演员交流,我揣摩父亲的角色。

彭于晏和松仁老爸
我不想母亲不开心,所以家里基本不会谈论他。我小时候看到过他两次,后来看到过他两次,就这样。这是上一代的事情。当我更长大,更成熟,我更觉得有责任照顾我母亲和姐姐,女性对我来讲非常地了不起。
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觉得要靠自己,因为我没有一个Role model,或者说一个人教我怎么做。男人该有什么,我靠自己学习。我不知道自己身上哪一部分来自爸爸,硬说我与他有什么连结,那可能是这个。
找另一半,如果把它设定成一个目标,就可以做到
我根本没去找,而且说起来我也不会,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如果说我的缺点,可能我是不那么浪漫的人。
纯粹的感情和交流我相信可以有。因为身份和工作,也许会比别人辛苦。而且一工作起来可能就没那么积极,就随缘吧,一随缘就……可能我找另外一半,如果把它设定成一个目标,就可以做到。
可能会吧,孤独。尤其有时落差特别大,你在片场,大家是这样,突然回到自己家,不拍戏的时候,你就是自己,好像离开角色特别空虚。那我就明白我不能待着,我要做个什么,我学画画,练琴,学做手冲咖啡、拉花……而且久而久之,你确实会跟以前的朋友没什么可聊。有时一年不见,两年不见,三年不见,你再聚要讲什么呢?

隔离期间,练习钢琴演奏和书法
所以我常常自己出去跑步,跑到以前上学的地方。有一次我去找了自己的小学老师。我就在小学问,碰到校长,校长说,哎你是校友,要不要来参加校庆,我说呃,不太方便啊,我问那个老师在哪里,问到他在别的学校了。我自己坐车去那个学校找他。他吓一跳。他请我去山上喝咖啡,他已经从老师做到训导主任,换了学校做到校长,女儿也念了名校,他很高兴地给我看照片。
精神力
其实我有花很多时间练习,大家感受不到,大家看到结果,觉得你做到了。我真的只有在拍戏时,才能够坚持到那种程度。
每天早上跑步是我面对自己的时候。每一秒都在想事情。有时有负面新闻,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的,你看到得面对。你跑步跑完,跟自己聊完,你知道没那么大件事,它会过去的。
只有跑步的时候会想,因为看电视你不会思考,看书你是在另一个世界,你跑步,或者骑脚踏车,然后告诉自己,今天我要跑8公里,今天我要骑过这个坡。中间你会一度要放弃,然后你告诉自己,我一定骑过,骑过以后发现,哎,中间本来想放弃三次,都没放弃,现在骑到了,接下来就是很顺很顺的下坡,很舒服。
你必须一直训练你的意志,每次都付出一样多的努力。在一天开始的时候,我规定今天看20页书,跑10公里,我如果做到,会有一个自信,有一个成就感,然后再面对当天工作的时候——拍戏有很多状况,你自己准备好,别人没准备好,或者灯还没好,都可能影响你。但你已经有一个准备好的精神状态。

通过运动,看上去是体力锻炼,实际上是意志和精神的练习,你反复去训练“我规定我自己做的事情我做到了”。像我和林超贤,每天开工前跑8公里,就是要有个好的“起始moment”。跑步其实就是左脚右脚、左脚右脚而已。做到了,再做什么都有一个很好的状态,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
所有的运动都是这样,相比较身体的训练,更接近思维练习。刚开始大家看到是外观的改变,但核心是你精神上的力。所以运动员看上去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他们的“力”与我们不同。
每次拍戏,如果是演这样的角色,我就会看他们的气质和“力”在哪里。我要去找到这个。当我找到了,我觉得不在于我演什么台词与动作。不是。是你知道他内心真正在想什么。这是我追求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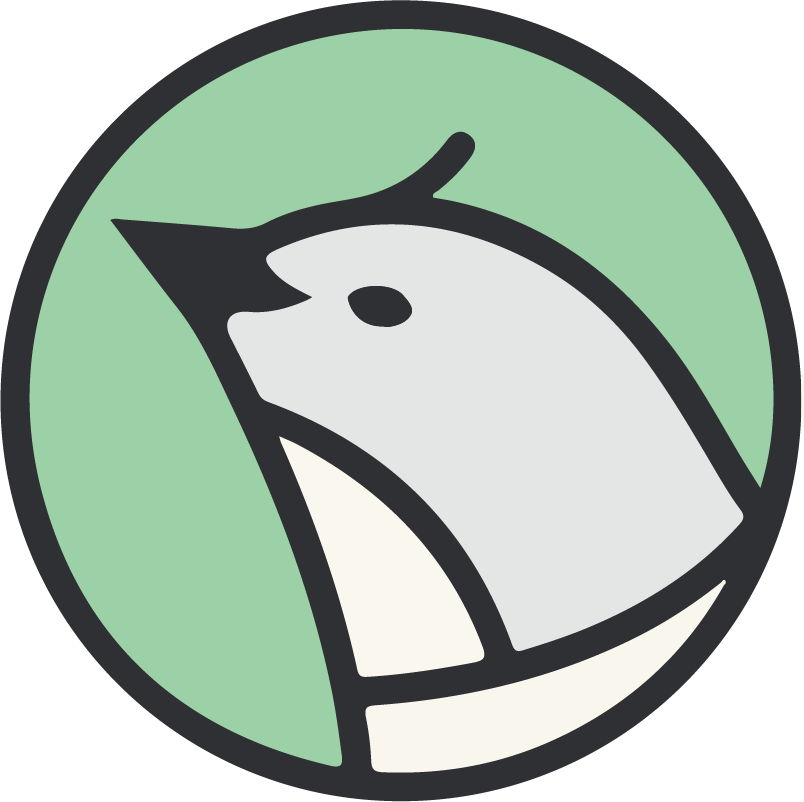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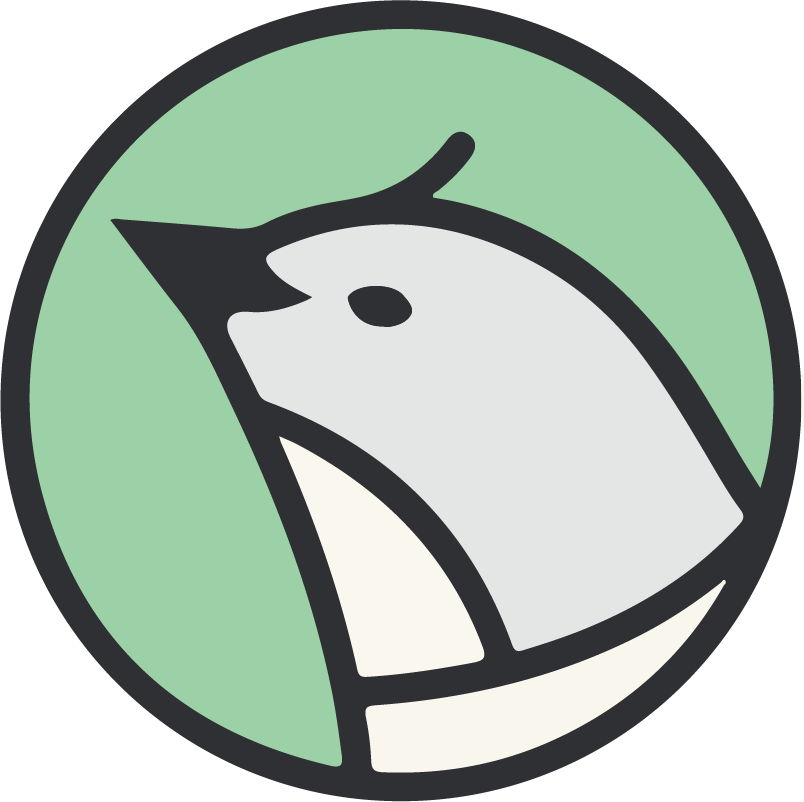
◦ 如无特殊说明,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 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腾讯新闻出品。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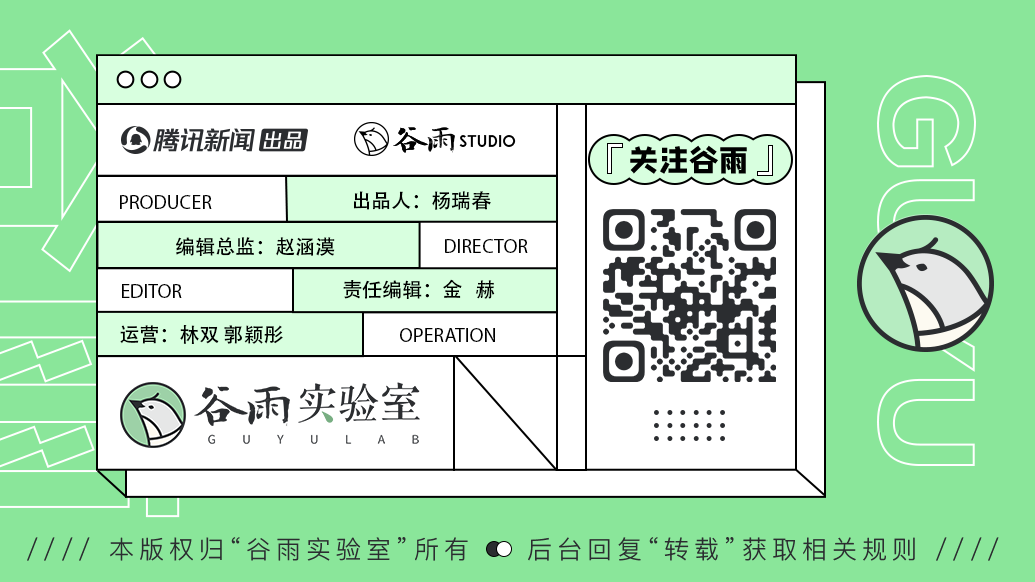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