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70岁,不想枉人生一场丨谷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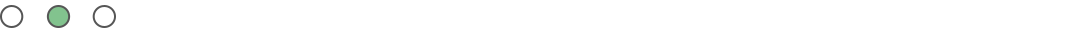
撰文丨刘洋
编辑丨糖槭
出品丨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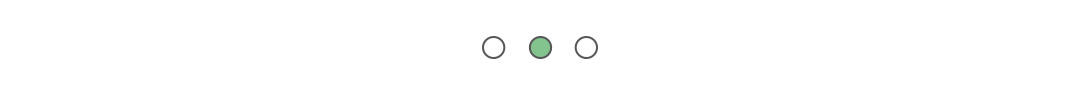
不辜负、不耽误这个时光
通常,每天结束工作的后半夜,张艺谋要花四五个小时看片做资料,凌晨五六点睡,上午十点起(电影拍摄期间,睡眠时间会缩短到三小时),睁眼便开始看新闻、小说、剧本,吃早午餐这全天唯一一顿饭,之后又进入不同的剧本会、筹备会、创作会……其间仅有的停顿,是为了维持“革命的本钱”快走6公里,日日如此。
《一秒钟》首映礼后,70岁的张艺谋转头扎进冬奥会四个仪式的创作会,电影《悬崖之上》的后期制作也没有停下,新片《最冷的枪》已筹备多时,半个月后就要在东北开机。他每天拿着一张满当当的时间表,进出一间又一间会议室,从上午到后半夜,大脑在不同的频道切换。那张时间表通常用不到10天就要换新的。这样的节奏也不算超常。筹拍《一秒钟》时,他同时推进9个项目(包括电影、舞台表演、大型演出等),每天工作20小时。
《一秒钟》的故事,就是他一边快走锻炼一边讲给制片人庞丽薇听的,不到一小时,故事就大体成型了,那是2017年底。张艺谋很兴奋,回办公室后立刻让助理把故事记下来,马上给远在洛杉矶的编剧邹静之打了电话。数日后(2018年1月)又郑重地给邹静之写了一封信,“不知为什么,几天来这个故事总在脑中盘旋,突然有了很强的创作冲动,想把它在今年7月拍了!……恐怕不能等到5月交,3月拿初稿为好。一个好汉三个帮,我特别渴望得到你的帮助。”
那时,他突然生出一种强烈的时间感,电影拍摄全盘数字化,中国又是改弦更张最快的,胶片生产、洗印工厂都消失了,他蓦然觉着改朝换代了,“哎呀,就没有了”。他拍电影以来的点点滴滴、许多记忆,以及所经历过的青春时代,慢慢也都成了历史,被碾碎消失了,“赶紧拍了吧”。他需要套一个故事,拍出那逝者如斯。于是,有了一个劳改犯逃出农场穿越千里黄沙去看电影,寻找死去女儿一秒钟影像的故事,胶片大循环,一遍一遍回放女儿的脸。
这是他第一次自己构思出整个故事,急迫地和邹静之轮流写,三个月完成了剧本。

其实,张艺谋擅长借题发挥,而非白手起家。早些年,他靠着一部部小说读下来,从中寻找可以改编的故事。去趟洗手间,一本《小说月报》或者《收获》就看完了,出差时,一个拉杆箱里全是小说,返程时再换一箱子书。即便如此,也觉得发现题材的速度跟不上创作欲,“吃不饱”。
近几年,行业内信息越来越开放,庞丽薇逢人便讲:谁有好的剧本拿来,不限题材。有人问张艺谋接不接科幻片。他说,“我是个科幻迷啊。”接不接动画片?“当然没问题了,只要剧本好。”
两年来,他连拍三部电影,《一秒钟》是500多个镜头的文艺片,《坚如磐石》是涉案题材,赛博朋克风格,用琉璃般的滤镜去呈现灯下黑的纸醉金迷,切现实脉搏的尝试,《悬崖之上》则是快节奏2800个镜头的谍战片。
年初因为疫情全国大停滞的几个月里,张艺谋也一天没歇着。当时《悬崖之上》正在拍摄,和剧组一起在酒店隔离的时间里,他就把拍完的素材剪辑好了。冬奥创作会也在推进,他每天和国内、国外的艺术家们开视频会。“没觉得难熬,因为一直在工作。”
“我特别喜欢几条腿走路。”张艺谋说,“我的工作速度很快,而且我的效率比较高,不浪费时间。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如果身体很好,如果一直有好剧本能续上,我都不止一年拍一部。我总是想多拍一点,希望能不辜负、不耽误这个时光,不枉人生一场。”
总有人质疑他拍电影太快了,不能耐下心来“五年磨一剑”。《一秒钟》的声音指导、和张艺谋合作了40年的陶经却嗤之以鼻,“说句老实话,大部分你们听到的五年磨一剑,眼泪花花的,不要完全相信,他们不少四年半都在玩。而老谋是,几个题材他感兴趣、有感觉的,一块往前走,哪个先成熟哪个先来。”
对张艺谋来说,拍出一部好电影的必要条件里,也不包括“时间”这一项:第一,要碰到一个好剧本;第二,碰到一群好演员;第三,你做的所有决定全是对的,没有跑偏。有很多次,他拿到一个小说或剧本,觉着要奔着好电影去了,但走着走着就跑偏了,或者力不从心,或者眼高手低,甚至犯了错误,尤其方向错误,再加上“客观原因”,佳作一直没有出现。“至今我仍希望我的下一部电影能更好,这也许就是我一直前进的动力。”张艺谋在首映礼那天深夜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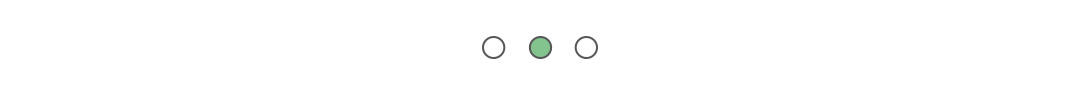
“否则你就被淘汰了”
《一秒钟》上映前,张艺谋深夜里去短视频平台宣传电影,从一个直播间到另一个直播间,很雀跃。因为没有录屏,回程路上他一直问庞丽薇评论里都说了些啥,觉得难得这样实时地贴近年轻人。他常说“与时俱进”,语气紧迫而诚恳,“电影观众都是年轻人,他不等你啊。”
《一秒钟》让许多人以为他在留恋胶片时代,像诺兰、昆汀、斯皮尔伯格一样。拍《长城》时他见到斯皮尔伯格,被问及“开始拍数字了吗”,他说早就开始了,他是中国最早的。
胶片时代,拍完的镜头要先送到洗印厂,洗好后剪接师粗剪,导演要过好些天才能看到。也是效率问题使然,张艺谋等不及,于是把DV连在摄影机上,同步录下影像,当晚再把DV连在电脑上剪辑素材,之后发给外地的剪接师对照着剪胶片。白天拍,晚上剪,在工作方式上他很早就进入了数字时代。
他一直在问,“有没有更新的东西”“有没有更新的技术”。近几年,连续三季执掌《对话·寓言2047》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张艺谋最初是为了了解全世界新的科技手段比如机械臂、激光、4D、裸眼、120帧等等如何运用到创作上,如何跟影像和人互动。在新技术领域,他相信自己比谁看的都多,“你看一百个,可能才有一个能用在创作上”。他想象未来甚至影像的载体也要被抛弃,指纹一晃,空气成像。
他毫不松懈,紧紧跟着,觉得观念、美学、技术、表达方式方方面面都得跟住了,“否则你就被淘汰了”。

电影《一秒钟》剧照
在编剧史航看来,除了紧迫感,张艺谋享受不停歇地创作。他对张艺谋不聊创作时的闷印象深刻,那是他最没劲的样子,像充电宝关掉了。剧本会上用全部五官传达兴奋感的张艺谋,则是他这个充电宝在放电给别人充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小亮灯,那个高兴,眉飞色舞。“比如有的哥们儿,不管你几点去见他,他都已经喝大了。而我有数的几次参加剧本会,都看到一个嗨大了的张艺谋,永远不闲置的一个充电宝。”
他想起北京奥运开幕式前期策划会结束后,作为顾问的陈丹青告诉张艺谋:后期你什么时候喊我什么时候来。史航说,“像陈丹青这么葛的人,他用不着给张艺谋面子,就是看到一个人跟工作之间如此如胶似漆的这种状态。而且电影表达不足以承载他的想象、创作激情、对影像和奇观的迷恋,就跟下雨,盆接完了用碗,碗接完了用桶,歌剧、演出、开幕式都是他不同的容器。”
和张艺谋一起工作的20年里,庞丽薇常常听着他的“倒计时”:人这一辈子,我还剩多少多少天,我还能拍多少部电影,你不要浪费我的名额,我的每个名额都很珍贵,我要拍不同的东西……
而谢东告诉庞丽薇,自己30年前给他当执行导演的时候他就在倒计时——那时张艺谋才40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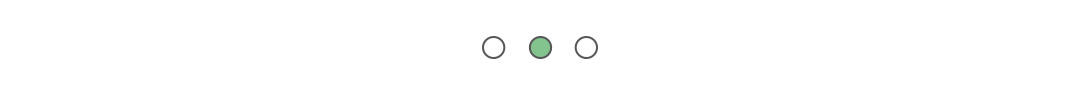
“人在时代里都必须先生存”
《一秒钟》故事里的时代,也是烙上他心理印记的时代,“那时候人是不能左右命运的,我自己深有体会,不敢想自己能上大学,更不敢想自己能拍电影。”父亲和两个伯父都毕业于黄埔军校,母亲是皮肤科医生,他自然“出身”不好,在恐惧里练出画巨幅宣传画、写超大美术字的特长。
他曾对作家方希说,“我一开始就有这个意识,让自己迅速工具化。工具化你就会对别人有用,人有了用,有些东西就不会找到你身上,你就会有空隙生存。工具不是个坏词儿,有用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价值感……恐怕我今天也有这个嫌疑。”
被北京电影学院破格录取前,张艺谋甚至考虑过去西北农学院念畜牧专业,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工厂的老师傅抓着他问:“艺谋,放电影还要学四年吗?”
从农场考上北影的陶经也和张艺谋一样“懵叉叉”的,以为电影录音就是配音,是童自荣。四十多年前,他们同在北影78级,那是“文革”十年后电影系录取的第一届,不少同学出自电影世家,见多识广,看张艺谋没看过的禁书和“内部电影”长大。顾长卫买了一堆音响碎零件让陶经给拾掇,弄好后放在窗台外用大喇叭放,奇特的、先锋的、前卫的,什么音乐怪放什么,放的吱儿哇乱叫。
张艺谋经常不吭不哈坐在床上鼓捣相机或作业。他的床铺在310室门口,脚后端放着整幢楼一百多号学生唯一的电话,张艺谋与这部电话几乎是绝缘的,但他应该绝躲不开电话这端的喜怒情愁,“老谋平时基本不说话,但他特别善于观察和发现,每个人打电话都是一个故事,跟家里人的,谈女朋友的,吵架的,哭泣的,他都默默看了。”让陶经印象最深的是张艺谋贴在床边的摄影习作,很强烈,很另类,像《黄土地》那种,天地之大,有运动感的线条、有冲击力的情绪,很有力量。
张艺谋后来多次谈及过当年的自卑,因为出身不好、比同学大十几岁、没有任何艺术家庭的背景,只能吭哧吭哧用最笨的努力奋起直追。连从摄影转导演都是迫于年龄焦虑,如果他按部就班从四助做起,要40多岁才能碰摄影机。
《一秒钟》初上映时,一段纪录片《2000年冯小刚的一天》在网络热传,“像我、像张艺谋这样的人,这都是属于生是自个儿砍杀出来的,没有什么太多的人帮你,别人你也指不上。”冯小刚在片子里说。
20多年前,张艺谋和陶经一起到日本做后期,在电视上看到一档综艺节目不约而同地喊起来,“这不是大岛渚么!在卖相机啊!”那可是大导演啊,日本“新浪潮”旗手啊!张艺谋很感慨,感受到生存焦虑。陶经相信张艺谋至今也一定记得那种震动。“他就是一部一部地拍,很珍惜。也从来没有身段。”
赵小丁觉得张艺谋的思维方式不同于常人,一般人做事都想着怎么能做成,一二三四几个要点,但张艺谋反向思维,先罗列出各种不可能,不断质疑,想出个点子,一转头又推翻了。“他老说自己不是天才,他知道哪样是肯定不行的,就不会犯那种致命的错误。”
然而,每次跟张艺谋谈剧本、谈创意,史航都感受到“第一流的才气”。法国人曾经找张艺谋拍《巴黎圣母院》,他想拒绝,又不好直说,赶上剧本会,就跟史航商量,想个特别忽悠、特别飞的点子把他们吓跑。俩人就坐着现想。史航说:卡西莫多是个机关大师,整条街都被他变成他的抽屉,一个大boss嗨翻巴黎圣母院以及巴黎街区的故事,蒸汽朋克。
张艺谋想的嗨多了:卡西莫多呢,他丑,他跟克罗德主教商量,想借用一天腓比斯卫队长漂亮的脸,于是把腓比斯麻醉,把脸揭了下来。到午夜时分,卡西莫多不想还了,因为这一切太享受了。之后,克罗德主教跟卡西莫多,就像科学家跟他的造物,开始了夺面之战。卡西莫多要夺下那张脸,要公道,因为上帝欠他的。
史航觉得里面有张艺谋对这个世界的很多感慨。“他这个岁数,那种沧桑,说这个世界公平吗?不公平。像把自己一生‘啪’扔进去了一样。”史航把那些很嗨的点子说给瞧不上张艺谋的年轻电影人,人家说那不可能是张艺谋想的。

张艺谋在片场
张艺谋很少回应批评,但极重视批评。他一直保持着开“神仙会”的习惯,剧本完成,请一波又一波的业内“大神”来提意见,一坐一屋子,一个个提,张艺谋自己拿着纸、笔,一条条记录下来,只记批评,之后让助理打印出来,一打十几页。他再跟编剧一起对着屏幕上的剧本,一条条讨论,一条条修改。片子粗剪完,他再请“大神”们来看,再听一轮批评。
在史航看来,张艺谋常常用许多拍摄条件的平均值覆盖在自己那第一流的才气上,后期剪辑时,又把这个时代基本的容忍度和审美覆盖上,“给小鸡崽盖了三层棉被,这不是孵化,这是活埋。”他跟几位大导演都讨论过剧本,有的导演会把自己的彩蛋随意抛洒在森林里,认为观众会有耐心和乐趣找出来,而张艺谋会忍不住在森林中标出好多箭头,指向他抛洒的地方,他怕你错过,他怕晦涩,怕别人觉得没劲转身走开。“他是极端尊重观众的导演,但不见得是足够信任观众的导演。”
而张艺谋有他作为手艺人的生存哲学,如果你拍一部变成地下了,再拍一部又赔钱了,那你以后也就没有创作空间了。“人在时代里都必须先生存,在生存中保持个性,保持清醒,保持头脑拼命运转,根据形势和感觉,表现出独立的思想性。你打定主意就是要拍一部十全大补的电影,既要通过,又要赚钱,还能表达自我,你就是好样的。”(《张艺谋的作业》)
他曾在《十三邀》里说,他不太爱惜自己羽毛,不太精心打造自己的品牌。许知远问他,没有超越时代的欲望吗?“没有。你还想超越时代?你能把你这事儿做好就不错了,你超越谁时代?你放心,人走茶凉。(年轻时候)也没多想,真没多想。人的命运常常就是这样子。”
庞丽薇常想着帮张艺谋把手稿留好,他手一挥,“不用留着,我没有那么伟大,等我死了以后这些东西也没有人看。”庞丽薇说,“他成就感极低,永远觉得自己还没有达到标准。”
他守的理儿也是手艺人的理儿,他相信,如果当初考上西北农学院畜牧专业,他如今可能在内蒙古,是个兽医,也会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很专注。
老辈儿人所谓的“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他只挣导演片酬,不对赌,“印象”之后也没在上市和股票上挣过一分钱。当年筹备北京奥运开幕式,有个品牌想找他代言,给1个亿,“绝对是天价”。庞丽薇兴奋得凌晨两点跑到办公室等他开会到天亮,等来的是他瞪着眼睛喊,“我不为五斗米折腰。”“导演,要是五斗米,我就不在这儿等到天亮了。”“那他们现在不就是觉得我是奥运开幕的导演吗?”“那当然是了。”“那不行,这是国家给我的,我不能拿这个去做这事,大家都会认为我是为了钱。”“那谁接广告代言不是为了钱呢?”从那以后庞丽薇再没跟他谈过任何广告代言的事儿,至今将近15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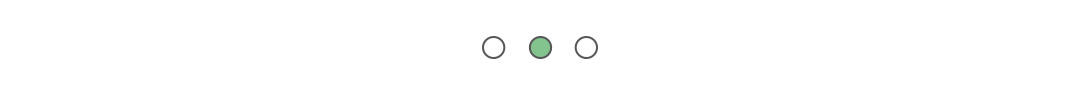
春非我春,秋非我秋
“在中国拍电影,就是会有遗憾。开玩笑。其实,全世界导演都会有遗憾,商业的,或者眼高手低,各种原因条件限制,总是有遗憾。我也经常会想,电影如果能重拍一次,当然是很棒的。下一次,下一部电影也许遗憾会少一点。”张艺谋说。
在庞丽薇看来,张艺谋是个自审性很强的导演,不会恣意而为,也特别为投资方考虑,一直提醒她控制预算。有时候面对各方来的意见,庞丽薇坐那儿想哭,“哎呀,我们怎么改啊”,而张艺谋早开始去想怎么能四两拨千斤的方法。
史航提起大气候,觉得张艺谋和国外的导演不在同一片天空下,对于人家来说,可以飞到一万米、九千米,而如果他永远是十米之内低空飞行,会撞到多少东西,也更容易遍体鳞伤。
他被视为开了中国电影的两个时代——“第五代”获得国际三大电影节最高奖,以及商业大片时代,但也在许多时间里处于骂声中。“你能征服全世界,但不能征服自己的家乡”,这是黑泽明的话,他的遭遇和表述,很让张艺谋触动。但他最常念叨的,还是黑泽明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时说的,“我今天还在学习拍电影”。
头些年,张艺谋对庞丽薇说,等我70岁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老导演”了,就对你没有那么多要求了,就都是夸了,毕竟“老艺术家”们都是被夸的……如今,他70岁了。
和舆论批评相比,时间是更让人敬畏的对手。
去年,斯科塞斯拍了《爱尔兰人》,有影评说,电影纵然好,但终究和当下的时代没什么关系,也就不会有《好家伙》《教父》当年的影响。联想到《一秒钟》的语境,史航觉得,春非我春,秋非我秋。光线变了,阳光普照的时候,你的作品纤毫毕现,斜阳时,就是为知音所赏,没有那么多人来。达斯汀·霍夫曼演的《杜丝先生》里,剧作家有句台词:我他妈以后就开一个只有在下雨天才开放的剧场。“冒着雨来的才是我的观众,这很傲娇。张艺谋可不这样。但是,雨毕竟已经下了。”
“好的电影是一个礼物,但是观众有权决定是否拆开。以往的观众喜欢接别人给的礼物,surprise,它超出你的想象,你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去观赏,还要看说明书。但是现在的观众更习惯收快递,我自己下的单,知道是什么东西,我昨天在吃,今天再要,我在我的舒适区里头,一步不挪,一动不动地继续享受。所以,收别人礼物的时代和拆自己快递的时代,是两种时代。”史航说。
到了《一秒钟》,一部关于“看电影”的电影,背景是他和这些老伙伴们共同经历过的“文革”时代。张艺谋对邹静之说,“格局很小,没有流行的那种戏剧性,贫瘠年代看电影的兴奋和满足,通过‘胶片’的不断‘转动’,传递一份情感,让我特别迷恋。”
“这是我第一次有一点儿想给自己拍部电影。”70岁了,拍电影40年,这样的个人心声由张艺谋口中说出来,仍透着十分的克制和慎重。
张艺谋找回了与他合作最久的主创们,合作40年的声音指导陶经、合作20年的摄影指导赵小丁、合作13年的编剧邹静之、合作15年的文学策划周晓枫、合作31年的剪辑师杜媛、合作31年的剧照师白小妍、合作20年的场务组长徐孝顺……
对于一个日常生活稀薄、没有娱乐、没有饭局、不擅唠家常、只有在工作中才喋喋不休的人来说,友情与陪伴也是在工作中实现的。庞丽薇理解张艺谋那种疏于人情世故,大脑被工作挤满,又在合作上极度长情的情感方式。这种性格也许随了生活中少言寡语、说一句是一句的父亲。23年前,父亲跟他说把烟戒了吧,他就再没抽过。
张艺谋曾对史航分析自己,“我想谁吧,就希望大家都在这儿,但我凭什么让大家都在这儿?我又不会开party。那我就一个办法,我就赶紧再弄一个电影,一个电影完了赶紧再弄个电影,大家就过来了。”忙下一摊,是跟他想见的人相见的唯一理由,而相聚也统统被他变成了工作。

张艺谋在片场
拍摄的时候,张艺谋盯着监视器的那种眼神,让赵小丁确信“一幕一幕的,都在他脑海里边儿”。赵小丁觉得,合作20年来,《一秒钟》是张艺谋拍得最笃定的一部电影,没有任何的犹疑和反复的试验。他拍得很克制,把颜色的饱和度抽掉了30%,一个接近自然的色彩还原。沙漠的光线、明暗很容易拍得很美,但张艺谋不要沙漠的美感。电影里放映《英雄儿女》,他不要数字投影,而要那台松花江5501型35毫米老放映机放出的胶片影像,观众们脸上的光影也只要荧幕的真实反光,不要任何打光。在剪接室看张艺谋一场一场顺镜头,赵小丁也感受到微妙的不寻常,总之“很有感觉”。
对陶经来说,这次是用最高的声音技术和老哥们儿一起做一部文艺片,全景声,64个声道,有的声道做风声,有的做草声,有的是虫子,有的在切菜,有的吃面条,十几个轨是近处的群众,十几个是远处的,摩托车、大卡车、自行车、拖拉机的声音,农妇训孩子的大嗓门,远远飘着的天气预报的声音、敦煌电视台的广播、新闻简报的声音蒙太奇、不断变化的与电影内外观众共情的《英雄儿女》歌声……最特别的是胶片大循环的声音,用肥皂盒、线轴、小板凳等很多声音元素做出来。“张艺谋是靠非常具体的东西来释放一种电影语言,人生当中的一秒钟一圈一圈地循环转(电影里张译饰演的逃犯一直在追寻死去女儿一秒钟的影像)。老谋就跟我说,轴,它一直在转,做出反复在心里‘咯噔咯噔’挥之不去的声音。”
拍摄间隙,张艺谋难得地和场务组长徐孝顺聊闲天,“小徐(其实他已经50岁了),你必须要跟到我最后一部戏,哪怕我那时候90岁了,你70岁,拍完最后一部,我请你一家人到北京来玩一趟。”20年前,徐孝顺从农村出来打工,在片场搬东西,张艺谋把他带成专业的场务组长。几年前,徐孝顺在老家重庆开了个养猪场。张艺谋听说后嘱咐他:你猪也养,电影还是照常跟我拍。后来听说《悬崖之上》的场务组长就是徐孝顺的儿子,他很开心,“那好那好,小徐不想干了,也后继有人了。”
史航相信,张艺谋拍电影有点像燃起一堆篝火,让人寻着火光而来,而《一秒钟》是找最久的朋友,一起致敬最初的恋人——就是电影。“老朋友都来了,发现‘你还惦记她呢’,是这种感觉。”
有人看完《一秒钟》想起托纳多雷的《天堂电影院》。但张艺谋的青春时代显然迥异于《天堂电影院》的况味,如他所说,是“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政治和苦难都是既远又淡的背景,有一点《活着》的意思,也有点儿冷幽默”,也是他为《一秒钟》配曲所写的歌词的况味:一个回家的人在路上,他看到黄河很长,他看到长城很长,耳边的花儿伴着他回故乡……半客观、半主观地远远飘在电影的风沙里。
而张艺谋更喜欢的电影结局,应该定格在胶片被沙子埋掉的那一刹那,一切戛然而止。黑屏,开灯,电影回到现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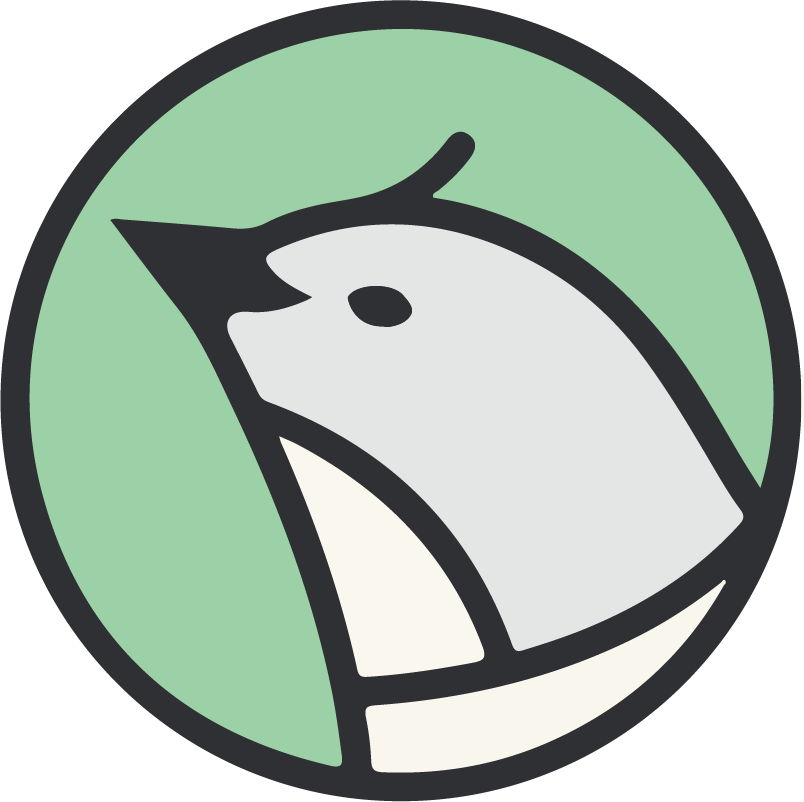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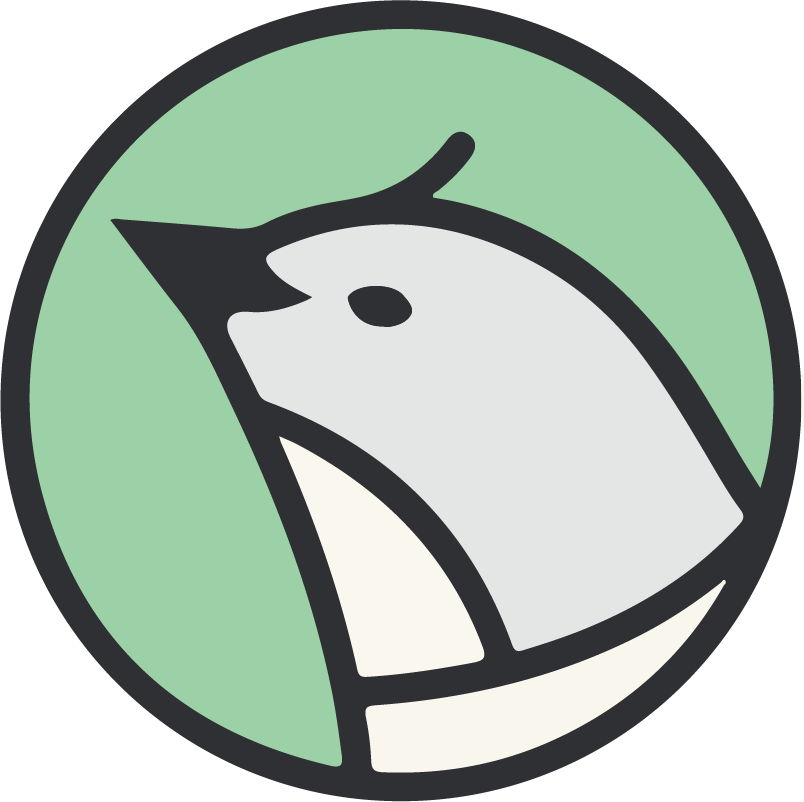
◦ 封面图源自视觉中国。如无特殊说明,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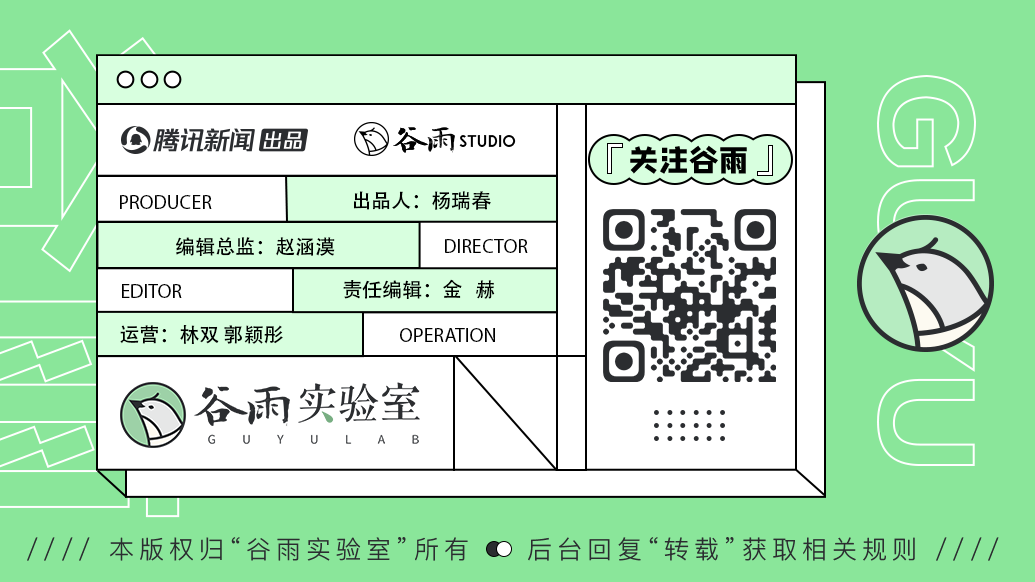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