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禽归来,致敬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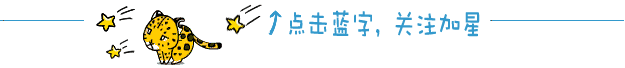
写在前面:
无论何时,尤其是春天,不要忘记,生的壮阔。
生命,会在绿色中一次次站起。
今天,借最自由的灵魂,向守护森林的人致敬。
4月2日百望山监测记录
总数:270只
猛禽种类:
普通鵟、雀鹰、红隼、黑耳鸢、灰脸鵟鹰、白尾鹞、鹗
大家好,我叫宋晔,我是北京猛禽监测项目的负责人。今天我来跟大家聊聊这些年北京猛禽监测,我究竟都看到了些什么,正在做什么。

大家知道其实北京上空是有鹰的,我们在多年前就发现北京其实是一条“鹰道”上的重要节点。

我们设置了两个监测点用来观察记录老鹰的迁飞。上图这座山看上去特别高,但其实海拔只有700米,我们一个监测地点就设置在这座山上。另外一个点在百望山上面,海拔更低,仅仅有200多米。你们可能要问,为什么海拔仅700米的山上都可以拍到云海呢?
那是2010年9月下旬的一天。大雾,能见度非常低,我们的原计划是要上山做调查,看一下猛禽迁徙的情况。
但是这个突如其来的大雾让我们有点犹豫。对于飞鸟来说,空中的能见度也是低得吓人,它们应该不会选择在这样的天气迁飞才对。但是,既来之则安之,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开车上去看看。
沿途能见度只有2、3米远,大雾中开山路很危险,大家都有些提心吊胆。我们车上有一个海拔表,海拔表过了400米的时候,大概就在那么1-2分钟的时间里,忽然一下,云开雾散,金色的阳光洒下来,我们看到了图片中的云海和云海上方湛蓝的天空。
原来是个大晴天!
一个“千猛日”,1300只鹰都在云的上面,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可如果我们位于市区的低地我们将什么都不会看到。所以,从那以后我们知道了一件事,无论是有霾、有雾、沙尘、下雨,我们的人都会上山做猛禽迁徙监测工作。因为我们生怕错过这样的日子,一千只猛禽从我们头顶上掠过,而我们却一无所知。

猛禽迁徙,旅途艰辛
这是我在山上拍到的一张照片。飞机和两只鹰,这两只鹰是凤头蜂鹰,距离比较远,两个剪影。对于我们有经验的监测员来说,辨认不是难事。不过究竟这只“铁鸟”属于哪个航空公司,是空客还是波音,我则完全不知。
上次有个对飞机感兴趣的朋友来到我家,看到这张照片曾经告诉了我一次,对不起,现在我又忘了。我是想说,我们认猛禽和我朋友认飞机一样,其实也没那么难,只要多去熟悉,慢慢就可以办到。

给大家看一张我收藏的邮票,这张邮票上面写着“琉球邮便”,是一张日本琉球冲绳地区的邮票。
这枚邮票上画的是东亚迁徙通道上猛禽跨海的壮观景象。我们可以看出正在飞翔的除了有黑耳鸢外还夹杂着一些雕属猛禽,这是一张1963年的邮票。

黑耳鸢
我们在监测点也可以看到这种叫黑耳鸢的猛禽,有时能看到两三百只集群迁徙的景象,和邮票很类似。

这张小地图是一张最近这些年发表的亚洲春季猛禽迁徙的走势图。
图中绿色的实线代表猛禽迁徙的主干线,绿色的虚线是可能存在的其他迁徙主线。
图中粉色的线是猛禽迁徙的支线。猛禽春季从南方的越冬地起飞,要向亚洲东北方向挺进去寻找繁殖地。我们看图,左边绿色实线的起点,这一批猛禽从印尼西部开始,过东南亚的中南半岛,经过越南、老挝等等这些国家进入到中国的西南地区,飞过广西,然后再不断地往东北方移动。
另外一批猛禽则从印尼东部起飞,路过菲律宾,然后进入到台湾地区。在台湾兵分两路。一路去了日本,然后继续向北,到北海道,库页岛,再去俄罗斯内陆。
为什么这条线路的老鹰飞日本时不是沿着直线飞,而是要拐一个弯?因为跨海迁徙,它们要寻找一些岛屿歇脚,这一片岛屿大家都知道,钓鱼岛、冲绳都在里面,也包括刚才那张邮票所在的地区。
另外的一路猛禽则跨过台湾海峡继续向北迁徙,到山东这个地方,和刚才说的印尼西部那波猛禽汇合,然后“兵合一路、將打一家”,一起飞向中国的东北。北京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大概是在汇合点向北一些。所以我们在北京看到大量猛禽迁徙过境是非常正常的。


灰脸鵟鹰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种非常常见的老鹰,叫灰脸鵟鹰。在南方很多地区数量很多,在北京以中等偏少的数量规模进行迁徙。
台湾其实前些年做了灰脸鵟鹰GPS监测,他们在垦丁跟八卦山那附近捕获了很多只,选了5只在身上装了GPS装置,并且把它们命名为海角1号到5号。监测的当年,海角3号、4号这两只便不幸坠海。3号是在从菲律宾飞往台湾的巴士海峡中信号失联的。海角4号是在跨越黄海的时候信号消失的,它已经到达中国内地,接着向朝鲜进发,很遗憾它没有飞过去。
而海角1号走的路线还特别绕。它本来想跨越台湾海峡到达福建,但是它迁徙的时候正好遇上东北方非常强烈的季风,等了几天,它实在等不及,就开始强行起飞跨海。结果被大风一直刮到了广东那边才登陆,好歹算是上岸了。当年走了一万多公里才到繁殖地,比别的鸟晚了很多。但是秋季返程时它走得特别快,成为这几只鹰中当年第一个完成了完整迁徙的个体。
我想说的是,其实猛禽在迁徙过程中遇到的危险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除了要跨越千山万水,还要面对食物短缺和人类干扰等等很多问题。
一个印度的保护组织在2010年左右发现在印度当地有大量的阿穆尔隼被猎人集体捕杀。捕杀的规模大概是一个季节10万到12万只。
迁徙是猛禽面临的一项相当凶险的挑战,但是它们非常勇敢地履行跟大自然的约定,做着每年两次的迁徙。冬天到西南方,比较温润的地方过冬。夏天到东北方,比较凉爽的地方繁殖。
北京的猛禽监测项目

下面我来说一说我们的北京猛禽监测项目。我们平时在山上的画风大概是这样的,站在视野开阔的地方等待天上的猛禽过境,我们会用拿望远镜扫视观察,然后端起长焦相机给猛禽记录存证。当然大多的时候大家是在无聊地等待。

尤其我们的监测期很长,基本上在猛禽没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人在山上等待了,在猛禽基本走光的时候,我们的人还在山上。
我想今天来自广西、重庆的同行也有相同的感受,等鹰的时候是很难熬的,我们在北京有烈日、雾霾、大风,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雨,但是我们的监测员一直都在山上。

这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这个项目在北京能够坚持7年的时间,绝对离不开这些监测员。今天可能到场有我们的监测员丁老师、舒老师,宋健是今年刚刚加入我们这个项目的新血,我们这些监测员会把这个事情一直做下去。

这是我们目前监测的一个总结。我们一共有监测员26名,是可以独自上山的监测员,大家单次排班分别上山,然后完成猛禽迁徙的监测,最终数据会在我这里汇总。
我们从2012年开始,一直到去年2018年,已经进行了7年的监测,到现在为止超过了1000天,累计已经超过了8000小时,超过9万只次的猛禽飞过我们的两个监测点。
这些年我们系统地记录在北京迁徙猛禽的种类,一开始是26种,但是这些年这个数字一直在不断增加,因为我们覆盖的监测时段非常长,哪怕某种猛禽只在山上出现一只也会进入到我们监测的视野中去。新的猛禽纪录包括松雀鹰、凤头鹰、黑耳鸢,蛇雕已经是第三次出现。也包括高山兀鹫,包括毛脚鵟,它们在去年10月双双出现在了我们眼前。
目前,我们总共记录到了33种猛禽,这个数字已经是亚洲之最,监测组相信北京地区可能还会有1种到3种的潜力可以被挖掘。

给大家简单看一下,数字大概是这样,这些年基本比较稳定,一年总共记录到的春季加秋季综合是1万多只左右,峰值出现在2015年达到17000多只。最近两年数字没有那么多,开始往下降,这些是我们这些年在相同的监测频次下获得的数字。
这样累计下来的数字比较具有对比、参考的意义,我们可以拿出两年的数据就进行对比寻找规律。

凤头蜂鹰春秋两季迁徙数量对比
比如说凤头蜂鹰,图中红色的线代表的是2012年的数据,绿色是2013年的数据。我们从一张简单的表格可以看出,凤头蜂鹰在春天迁徙的时间比较晚,在春季监测后半段出现在了监测员的视野中。
但是在秋季很早的时候,凤头蜂鹰就出现了,在迁徙的中期它们就消失了。有了坚持不懈的数据积累,要进行迁徙的对比会比较直观,这些东西在我们7年表格中都有比较充分的体现。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刚才说过的灰脸鵟鹰,蓝线是灰脸鵟鹰春季迁徙路过监测点的只次,绿色是秋季的数字。我们看到一个问题,春季迁徙来北京的很多,秋季数字很少。春季最多有662只,最少也有282只。秋季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是240只,比春季最少的时候还要少。
所以,这些数字可以证明一件事情,一个相当大的灰脸鵟鹰种群春季跟秋季走的不是同一条迁徙路径,春季路过北京的一部分在秋季选择了别的通道,原因不明。
不过根据现在对于灰脸鵟鹰的了解,国际上普遍认为灰脸鵟鹰的春季秋季的迁徙路径是比较一致的,无论是台湾的GPS和日本的GPS都印证了这件事。因此,北京的灰脸鵟鹰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又是怎么离开的,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清楚,2019年或许我们项目即将开展的GPS监测会揭秘路过北京的灰脸鵟鹰种群更多的细节。

再来看看另外一种猛禽,从我们这些年监测数字中可以简单拉出一张表来——普通鵟。这是2012年到2017年的春季迁徙的数据。2018年的数字还没有出来,不过我估算可能有1万3、1万2只左右。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年普通鵟的春季迁徙呈现一个倒U型的曲线,在2015年达到峰值紧着慢慢下滑。甚至我们在观察像雀鹰、凤头蜂鹰这种影响北京迁徙数字的大户猛禽时,也在它们中发现了这条倒U型的曲线。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只能说我们监测时长还是太短,如果我们做到10年、15年、25年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长、更可信、更完整的趋势图。我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做更多是描述,还无法得出一个定论。因为离作出一个结论性的东西,还差太远了。
我们其实从2002年韩冬老师探索出这个监测点开始做大量的猛禽调查,2012年开始每日不间断监测也只有7年的完整数据,对于猛禽的了解还是远远不够的。

这些年来,我们在山上发现的新种,我列了6种,分别是2010年两种,蛇雕和松雀鹰,2013年黑翅鸢和凤头鹰,2016年的白尾海雕跟2018年高山兀鹫。我说的并不是北京地区的新种,而是在迁徙点上新被记录到的新种。当然其中也包含北京新种,像黑翅鸢跟凤头鹰出现的时候,包括蛇雕出现的时候,当时也都是北京的新纪录。
迁徙季常见的猛禽们



凤头蜂鹰的三种色型
最后请大家简单看一看北京天空中有特色的一些老鹰。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刚才提过的凤头蜂鹰。体型很大,而且颜色很多样。第一张是中间色型的凤头蜂鹰,第二张是深色系的,身体更加黑一些,第三张是浅色系的,背景就是北京的楼宇,这条红线就是北京的五环路。这就是凤头蜂鹰在北京上方迁徙的状态。

凤头蜂鹰
这是台湾的朋友拍到的凤头蜂鹰在攻击蜂巢的照片,特别有意思。

鹗
这种抓着鱼进行迁徙的鹗,是鱼类爱好者,它也是北京比较常见的。

游隼
这是地球上运动速度最快的生物——游隼,俯冲的时候可达到300多公里的时速。因为山上有人养鸽子,所以我们时不时能看到游隼抓鸽子,游隼抓鸽子速度很快,你实际观看的时候可能看不了太真切,但是纪录片里面有展示,双爪攥拳,拳击鸽子,打落猎物,翻身抓住,带走吃掉,差不多是这么一个过程,非常精彩。

游隼抓鸽子的场面
我们在山上也拍到了游隼抓鸽子的画面,不光是游隼,有不少猛禽都具有空对空的非常强大的战斗力。

猎隼
比如说猎隼,我们在山上也拍到过猎隼抓鸽子的画面。也见到过雌性红隼抓鸽子。

红脚隼
这种猛禽就是我刚才说的在印度每年有10万到12万只被捕杀的小可怜,阿穆尔隼又叫做红脚隼,以长距离迁徙著称,从东北乃至西伯利亚,一直会迁徙到非洲南部,一年往返接近3万公里,这是一个非常壮阔的迁徙旅程,距离远远超过其他大量的迁徙鸟类。

阿穆尔隼
我们看阿穆尔隼,雄的身上颜色相当多样:白色的覆羽,黑色的飞羽,灰色的身体,鲜艳的爪子、嘴巴和尾下覆羽,是一种非常漂亮的小型猛禽。每次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尤其是知道在印度发生的那样的事情之后,我们都会祝福它,希望它能够一路走好。


鹊鹞
我们在山上见到的鹰里,黑白分明的鹊鹞也是相当光彩夺目的。它因为背后有像海神三叉戟那样的花纹而著称,像玛莎拉蒂的车标。

靴隼雕
这个是靴隼雕,有着非常醒目的肩羽。

草原雕

短趾雕
草原雕也会路过北京,短趾雕在北京每年的数字都不少。

金雕
这是金雕,金雕这一两年路过北京的数字不太多,但是前些年路过北京的数字还是比较多的。它们是整个北半球战斗力最强悍的一种老鹰,捕食大型猎物。在秋季非常晚的时候,11月份,或者10月下旬才会驾临我们的监测点。
寒冷的天气,启动比较晚的一些猛禽比如白尾海雕、毛脚鵟,都有可能在这个时间出现,猎隼和苍鹰在这个时间出现的概率也会比较大。
除了一只一只的猛禽,最喜闻乐见的事情莫过于看到漫天猛禽组成的“鹰河”。当你置身于上千只鹰隼之中的时候,你能清晰地感觉到生命带给你的震撼以及大自然的脉搏跳动。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鹰组成的“鹰柱”,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所有的老鹰都在螺旋状的飞行攀升。整体看过去就像是一根天神的拐杖,那个场面会让人觉得记忆犹新。
最好的团队,最好的坚持
除了动物带给我的感动外,人也同样让我很触动。我天天都能看到我们监测员的记录表。我都会看这些表具体在写什么。我看到其实很多监测员,在我们一个非常窄的叫备注栏里面的地方,写了很多东西。我给大家读一条。


我觉得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团队,大家能够把这样一份看似非常枯燥的工作用热爱坚持下来。这些年来我想我们大家心中想的可能都是同样一件事——希望猛禽在北京上空飞得轻松,希望它们能够顺利地路过这个区域,也让我们发现越来越多更多关于它们不为人知的奥秘。我们也同样欢迎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我们这个项目,大家一起把北京猛禽监测高质量地继续完成下去。

谢谢大家。
- END -
.........更多关于猛禽,你还可以读.........

两个月后,数万只猛禽飞掠山城……

太师说,你即将迎来和天空最接近的时刻

更多:
金猫 | 云豹 | 老虎 | 豹猫 | 宠物豹猫 | 黄喉貂 | 香鼬 | 猛禽 | 毒蛇 | 救助 | 北京华北豹 | 荒野 | 西双版纳 | 山西马坊 | 新龙 | 猫盟 | 长耳鸮 | 刺猬 | 长耳鸮 | 狍子 | 鬣羚 | 带豹回家 | 豹吃人吗 | 乔治·夏勒 | 个体识别 | 寻豹启事 |猫盟周边 |

长按二维码关注猫盟,记得给我们标星哦

还在等什么?
赶紧拿起你的望远镜出门吧!
阅读原文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