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埃博拉到新冠病毒,人类进步了吗?


通过对比这两场疫情的流行和人类的应对,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没做好准备。
经历过2014年埃博拉在西非的大暴发后,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对于应对严重的流感大流行和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世界并没有做好准备。”
不幸的是,6年之后,当新冠病毒现身的时候,这个世界依然没做好准备,甚至在某些方面做的更糟,因为这一次,病毒席卷了全球。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拥有着人类史上最先进的科技和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但新冠病毒造成的破坏,正在直追100多年前的“大流感”。
美国非虚构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在《血殇——埃博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忠实记录了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大暴发,和医务人员与之抗争所付出的巨大牺牲。通过对比这两场疫情的流行和人类的应对,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没做好准备。

2013年12月26日,一种“神秘”疾病在几内亚一个小村子里静静传播开来,但直到2014年3月21日才被确认为埃博拉。在这段时间内,病毒已经广泛传播,少数病例从几内亚输入进了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但这些病例都没被发现,也未经过调查或正式报告给世卫组织。在病毒静静传播了数周之后,感染人数多到再也难以追踪之时,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埃博拉疫情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非洲赤道地带的国家,已经有近40年处理埃博拉疫情的经验,那里的卫生系统虽然脆弱,但由于对这种疾病非常熟悉,而且疫情多发生在偏远农村地区,在世卫组织和国际伙伴的帮助下,所有发生的埃博拉疫情都在三周到三个月内得到了控制。
但西非国家从未经历过埃博拉疫情,临床医生从未管理过这种病例,实验室从未诊断过这类病人的样本,政府从未经历过埃博拉疫情的考验,当地的文化信仰和风俗也为病毒传播提供了巨大便利条件。
根据几内亚卫生部2014年8月份的报告,该国60%的病例,可以联系到传统的殡葬习俗。11月,世卫组织驻塞拉利昂的工作人员估计,该国80%的病例是与这类习俗相关。
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葬礼上会有一些秘密团体进行的仪式,部分送葬者用冲洗过遗体的水沐浴自己或膏抹他人。有些人还会在传染性极高的遗体近旁睡上数晚,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将能力移转到自己身上。这些参加埃博拉致死患者葬礼的人,后来把病毒带回了各自的家庭和村庄。
此外,传统医学在非洲历史悠久。由于政府所办卫生设施的服务难以获得,使得传统治疗师的护理和通过药店自行用药成为许多人尤其是穷人更青睐的卫生保健方式,许多激增的新发病例也都可追溯到与某一传统治疗师发生接触等原因。
同时,村民对前来调查的公卫人员充满敌意,他们带着病人和调查人员玩起了躲猫猫,欺骗、攻击公卫人员,并且拒绝遵守防疫建议。疫情开始后,高病死率使得人们把医院看作传染和死亡之地。此外,许多治疗设施外筑起高墙,有的还挂有铁丝网,看起来不像医院,倒更像监狱,这都进一步加重了不遵照建议及早寻求治疗的情况。
《血殇》中重点记述了塞拉利昂凯内马政府医院在对抗埃博拉疫情方面作出的巨大牺牲,这家医院的医务人员所感染的埃博拉病毒并非来自患者或社群当地居民,其病毒源头可以追溯到一位传统治疗师的葬礼。
麦宁道是一位广受爱戴的传统治疗师,她为埃博拉病人进行治疗被感染而死,至少200人参加了她的葬礼,悼念者趴在她的身上哭泣,用沾染了病毒的手擦拭眼泪,互相拥抱。
凯内马政府医院的一位救护车驾驶员违反了规定,没有穿防护服,去探望朋友,但那里有人感染了埃博拉马科纳毒株,是埃博拉毒株中毒力最强的一种,那人与麦宁道的葬礼有着紧密联系。
驾驶员被感染后入院治疗,他在卫生间里跌倒,撞破了头,好心的护士露西·梅为他清洗伤口,随后也被感染,露西·梅怀有身孕。护士长姆巴卢·方尼决定孤注一掷尝试拯救这位护士,从她体内取出死亡的胎儿,这次拯救行动感染了包括方尼在内的四个护士,最终方尼和其中一位护士死亡,而露西·梅也未能被拯救。
病毒遗传密码显示,凯内马政府医院的院长胡玛尔·汗也感染的是马科纳毒株,他也是在照护自己的团队成员时被感染,胡玛尔·汗医生最终死在无国界医生的凯拉洪医疗营地中。
当时对抗埃博拉一线的医务人员缺乏防护装备也是被感染的主要原因。在利比里亚,有一位名叫法图·科库拉的年轻女性,她正在学习护理,由于医院缺少床位,她不得不在家照护四位被感染的家庭成员。
科库拉没有任何防护装备,她用垃圾袋、雨衣、外科手术口罩和多层橡胶手套武装了自己,在她的照护下,她的父母和姐姐都活了下来,而她没有被感染。当地医务工作者把科库拉的防护做法称为“垃圾袋法”,并向无法去医院的居民进行传授。

图片来源:无国界医生网站
值得一提的是,在胡玛尔·汗医生死去的无国界医生的营地中,就存放着一组可能会挽救他生命的名为ZMapp的药物。这种药物只在猴子身上实验过,并且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疗效,但从未应用在人体,而且当时全世界只有6组ZMapp药物存世。
对于要不要把ZMapp应用在胡玛尔·汗医生身上,无国界医生进行了激烈辩论。
书中介绍,无国界医生组织毫不动摇地坚持“分配正义”的伦理准则,这条准则认为,所有人类都应该平等地得到有可能得到的最好的医疗服务,从分配正义的准则出发,每个人都有资格得到相同的服务,无论贫富、贵贱。假如医生和药物短缺,那么必须在所有患者中平均分配。
此外,药物也有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而营地中没有氧气供应,这会立刻杀死汗医生。因此,不论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分配正义原则,最终无国界医生决定不把药物给汗医生使用,同时不把这种药物存在的消息告诉汗医生。
这组药物后来被取走之后,拯救了两名参与埃博拉救援的美国医生。一组药物本来只能给一个患者使用,并且必须遵照检伤分类法给病情较轻的患者使用。但做决定的兰斯·普莱勒医生几乎违背了所有原则,他先是把药物给了病情最重的一位医生,在发现另一位医生病情急剧恶化后,他又做出了两人分享一份药物的决定。
他的决定为这两位医生赢得了时间。两人先后被送回埃默里大学医院,得到了后续的ZMapp药物治疗同时,也获得了最好的医疗护理。
然而,2014年西非埃博拉的战争不是通过现代医药和科技打赢的。当病毒在城市内爆炸性传播的时候,无国界医生凯拉洪营地的临床护理管理者安雅·沃尔茨探访了马科纳三角洲的基西村镇,这里就是马科纳毒株的名称来源地。
沃尔茨看到当地的村庄已经开始施行反向隔离,切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防止病毒进入村庄。对于每一个要进入村庄的人,他们都会进行仔细检查,看有没有疾病的症状,并且要用漂白水洗手,才被允许进入。
“感觉像是回到了旧时代,”沃尔茨说,“他们不去参加葬礼,不再互相亲吻,不触碰其他人,行为模式彻底改变。”
“暴发就是这么终结的。”无国界医生组织驻布鲁塞尔的官员阿曼德·斯普莱切说,“永远是因为行为模式的改变。”
1976年,当埃博拉病毒第一次在扎伊尔中部以北的低地热带雨林中现身时,比利时驻扎伊尔医疗救助组织的主管卢泊尔博士站在邦巴镇市场的一个台子上,告诉民众,要避免接触已经患病的人,绝对不要拥抱死者,除非带上橡胶手套,绝对不要触碰死者,必须尽快埋葬死者。
然后,卢泊尔告诉公众:“你们必须用远古法则处理这种新疾病。”
“远古法则”是人类在对抗传染病的历史中,总结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曾经在对抗天花的暴发中,疑似患病的人和他们的孩子会被送到村庄外建造的茅屋中,里面有饮水和食物,禁止与外人接触。如果茅屋里的人活了下来,就会被允许再回到村庄,如果都死了,村民就会把茅屋连同尸体一起焚毁。
卢泊尔博士反复提醒民众:不要接触患者,不要触碰死者,死后立即埋葬,遵循远古法则。
在2014年,医务人员能够提醒西非人民的,依然是这些内容:学会辨别症状,不去触碰体液,避免接触出现症状的人,放弃处理死者,交给专业处理的人去做,保住自己不被感染。

图片来源:无国界医生网站
到了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中国能够快速控制疫情,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也可以联系到远古法则。和埃博拉暴发时的非洲村庄一样,中国也封闭了疫区的村庄和社区。而在反对隔离和不肯戴口罩的国家,疫情至今势不可挡。
哈佛大学和布洛德研究所的基因组科学家帕尔迪斯·萨贝提博士将毕生精力都用在了研究病毒如何演化、突变上。多年来,她一直提醒同事,应该在公寓或住宅里储存一个月的食物和基础医疗物资。她将此称之为“一个小小的预防措施”,以防真的遇到四级事件,要像非洲村民一样,不得不反向隔离自己一个月。
在《血殇》一书的尾声,作者普雷斯顿预测了一场四级事件的全球性暴发:由某种生物安全四级的新发病毒引起,能够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没有疫苗,现代医药无法医治。
他在书中发问:假如一种四级新发病毒扩散到北美或任何一个大陆的百万级人群中,医院是否有能力处理这么多的患者并照护他们?假如感染人数超过百万,流行病学家是否有能力追踪并打破传染链?
“既然病毒可以突变,那么我们也能改变。”普雷斯顿最后写道。
普雷斯顿不会想到,他在书中的预测这么快就成为了现实。今天,他还有信心写下“那么我们也能改变”这句话吗?
PS:普雷斯顿另外一本关于埃博拉的非虚构著作是《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他凭借这本书获得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颁发的防疫斗士奖,是该奖有史以来第一位非医师身份获奖得主。
校对:臧恒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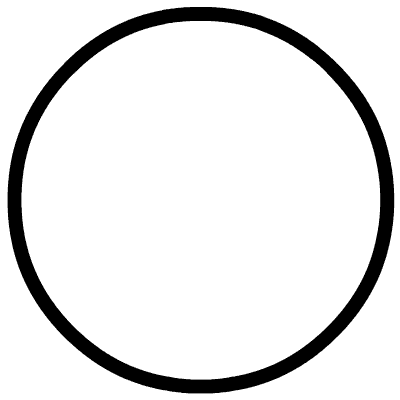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更多资讯~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