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对冲Trader袁玉玮:精析当前全球危机下的宏观博弈
平均阅读时长为 3分钟


我听说袁玉玮的名字很久了,朋友告诉我他是一位很有故事的交易员。也是一名十分优秀的宏观对冲基金经理。2020年3月,我终于有机会采访到袁玉玮。正值全球股市动荡时期,袁玉玮每天只睡4小时忙交易。
在2015年回国创立自己的私募基金前,袁玉玮曾经在法国和伦敦工作十年,担任宏观对冲交易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他与索罗斯的CIO交锋,并建议对方做空风电,太阳能。他的客户还包括德意志银行Prop Desk的CIO,JP Morgan伦敦的明星交易员等。
欧洲的工作经历对袁玉玮影响至深,他告诉我很多大基金所谓“明星交易员”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厉害,并且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欧洲十年,袁玉玮经历了许多办公室政治,对自己的能力和定位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虽然钱和名不是交易员的直接目标,但是成功的量化指标。袁玉玮后来确认了自己的战场在中国,他渴望回到中国大战一场。
袁玉玮在河南长大,作为一名70后,他从小就不太喜欢权威的束缚。他认为无论是价值投资,成长,宏观,量化,都有自己擅长的场景,也都有自己不擅长的场景,不能过度崇尚任何一个,也不能过度贬低任何一个。他说:“神话巴菲特、索罗斯,神话量化我都比较反感。我是70后,见识过人群集体运动的后遗症,所以天生对神话和崇拜反感”。
2020年年初的全球市场动荡,让袁玉玮摩拳擦掌,也兴奋不已。怎样在如此复杂的宏观环境下成功博弈,这也成为我们这次采访的主要话题。
宏观对冲就像在全世界下三国
精析当前全球危机下的宏观博弈
提问人: 春 晓
访谈者:袁玉玮
当前的宏观博弈,我的预测都一一兑现
春晓:玉玮,最近全球股市大震荡,听说你每天只睡4小时,净值一周就Up了5%。能介绍下最近你的策略和思考吗?
袁玉玮:中国的疫情发生前,我们已经认为市场内在的泡沫严重,风险度上升,所以做好了风险对冲的准备。所以疫情爆发后,组合的表现反而上涨。跟着,我们在全球做了布局:做空法国的汽车股,因为法国车在中国主要分厂在湖北。另外,传统汽车本身就受特斯拉移植到中国后成本和价格降低,产销量上涨的挤压,空法国车胜率就大了。所以在汽车行业,我们买特斯拉产业链/空法国车、美国车企和配件厂。两边方向同时受益于疫情和特斯拉效应。
另外,我们认为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受到破坏,所以做空依赖中国和亚洲供应链的Inditex(ZARA母公司), H&M。多中国物流公司中通(国家保民生政策)/做空国际物流Deutsche Post (DHL母公司),Fedex, UPS 。甚至我们还做空了Apple和巴菲特的Berkshire,因为Berkshire重仓Apple,导致风险传导。
还有基于疫情防控导致的消费者行为改变,买流媒体Netflix,B站,做空IMAX, Disney。做空星巴克,Yum!(KFC母公司),航空公司,邮轮公司,Uber...
基于中国工业需求降低,做空铁矿石制造商BHP, Rio Tinto, Vale,做空澳大利亚,巴西。
基于疫情诱发欧洲债务危机,做空西班牙,意大利,欧洲银行。
基于工业需求导致石油下跌,做空产油国俄罗斯,中东,拉美市场和货币;因为石油下跌对这些国家造成债务危机。
这些逻辑一环扣一环,和破案一样。这个是做宏观交易最有乐趣的地方。这就好像地球突然变得很小,可以掌上观纹,所有国家变成了棋子,我们在地球上下三国演义。用宏观交易表达观点时,我们眼里没有权威,任何别人崇拜的势力在我们眼里都是可以拿来当工具,大到国家,小到巴菲特的Berkshire, Dalio的全天候,都是工具。
春晓: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你会判断错误吗?
袁玉玮:肯定有判断错的时候。比如,今天(3.2)我们本来以为A股可能大跌,但大涨4%。但我们从来不赌一个场景,而是分散到几个场景里去分散风险。我们现在观点,对经济不乐观,但也不极度悲观,做交易表达观点,控制好风险,小心求证。我们的宏观交易和大多数人以为的交易大类资产期指、期货赌方向不同:我们会把宏观的逻辑往微观里去拆,去验证,拿微观来重新组合自己的宏观世界观 —— 就像魔方,我们调整每个微观的方向,博弈,不赌单边。而且每个行业,每个场景我们从来不重仓,不求毕其功于一役。我们的目标是交易里活的时间长点,好让自己的组合有时间去验证宏观观点。
我们的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基于不确定性的容错系统。我们也不相信投资世界里有标准答案,一个事件,在不同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多空都有道理,关键在于根据自己的交易系统找到适用的风控系统。
另外,我们既然反对崇拜权威,肯定要做到知行合一:不能己所不欲,而施于人,更不能严以律人,宽以待已。
春晓:怎样总体考虑今年疫情期间的投资呢?
袁玉玮:我们节前就做好风险管理了,节后下跌也实现了给客户资产保值增值和盈利。
在国外做了一些分散。但我们没有一把梭满仓A股科技股和创业板,虽然我们从去年也很看好。我们的利润是从多空对冲来的。上周全球暴跌,我们靠分散对冲也增长了6%。
在我看来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有如下:
1、一、二月放了很多水,因为疫情管控措施,很难进入实体流通,但很可能间接进了虚拟经济。这为未来金融系统孕育了不稳定风险,需要警惕。
2、节后的股市快速上涨,尤其科技股的上涨,已经进入反射(理论)形态:科技股开始涨,有宏观基本面支撑——为了和美国博弈。我们从去年也一直看好。但科技股越涨,买的科技股公募和ETF的人越多,买的人越多,科技股越涨,科技股公募和ETF发行越多、越快,这变成了击鼓传花的游戏。这个行业,以后可能会出现局部的2015年股灾的风险。科技行业长期我们比较看好,但短期泡沫太大。
3、债务风险。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疫情可能没那么严重。根据历史经验,等5月份气温升高可能就结束了。很多人也是依据这个,认为经济里的消费只是向后平移3个月。但就像我们认为随机漫步理论认为风险在金融市场里平均分布是一个错误一样,在实体经济里,很多风险也不是线性的。中小微企业停工2个月了,3月底前全面复工概率目前看也不大。用电数据也不支持50%以上的复工率。企业供应链上的短板效应也限制复工率。长期不复工,可能会导致企业生存困难上涨,员工收入下降,尤其中小微企业,这些消费能力如果失去了,很难再回来了。而且可能会导致风险从微观向宏观发展 —— 2007-2008的次债危机大海啸可能就是从某个不起眼的还不起房贷的低收入者家庭开始的。

很多人误解了技术分析
春晓:我知道您1995年就在炒股票了,能介绍下当时的情况吗?
袁玉玮:我1995年读大二,学的是电气自动化专业。那年一个朋友的姐姐刚好毕业在机构做投资,有一些消息,跟我推荐了几次股票都涨得很厉害。我就想去试一下。父母当时给了我几万块。那时内地人很保守,邻居和家人都批评说这炒股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又拖了几个月才去交易。
刚开始交易前两笔还赚,但第二笔盈利没几天就套牢。一直到96年初很多股票跌破净资产。我买的是沪市股票,96年大牛市是深市的。深圳很多股票翻了几倍,但上海很多50%升幅都没有。后来刚解套没几个月,跟着就是到96年底十二道金牌导致的跌停板,再次套牢。那时我就决定自己学习,靠听消息,盈亏都不知道为什么,还不如自己从教训里学习。
春晓:那个时候主要是通过哪些渠道学习呢?
袁玉玮:那会儿内地买报纸都买不到。股市大厅就一个大显示器,门口小贩卖投资咨询。乱七八糟的资讯报告,学习资料很少。所以我就去图书馆看报纸,主要读《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优先看的还是基本面的东西,纯属瞎子摸象。正好看了彼得林奇的书,很受他坐了灰狗巴士就去买灰狗股票方法的启发。
春晓: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技术分析呢?
袁玉玮:靠读报研究基本面从1997年到1998年上半年都很管用,但1998年下半年国企股重组、垃圾股借壳行情盛行之后就失效了。经常按基本面新闻和数据买入(比如银广夏、东方电子)很快套牢了,套了几个月刚解套卖了就连续涨停,翻几倍。心里就崩溃了,发现原来的体系没用了。最讽刺的是,后来发现这几个股票是窜通坐庄的机构财务造假、操纵股价。那时更下决心要重新换一套体系。刚好有个擅长技术分析的朋友带我入门。他原来学哲学的,很擅长把技术分析和哲学连起来,所以对我影响很大。
春晓:为啥很多人说技术分析不管用?大部分人对技术分析的误区在哪里?
袁玉玮:因为进入门槛低,使用的人基数大,最后跑出来的赢家比例肯定很低。技术分析不像基本面分析门槛高,开始就过滤掉一大群人。索罗斯,包括他最好的基金经理Stanley Druckenmiller说他80%的信号都是技术信号。还有另一个宏观大师Paul Tudor,亲自在大学教技术分析,国内人对他们了解的很少。
后来我在国外的工作中发现,国际上很多优秀基金经理和交易员其实都使用技术分析,虽然很多人对外都说做“基本面分析”,但实际上,他下决策的那一刻经常用技术分析。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历史上最好基金经理Stanley Druckenmiller说他的投资体系里,技术分析占80%比重。Wellington基金旗下有一只20亿美金规模的对冲基金,2个基金经理是Bollinger(布林线的发明者)的学生,以前是我的客户,他们所有的交易信号全部基于技术分析,而且是长线投资。
春晓:能讲讲你怎么接触到索罗斯的吗?
袁玉玮:我2000年偶然第一次读到有人介绍索罗斯的反射理论,对投资看到另一个境界 —— 它打破了技术分析和基本分析的藩篱,把它们糅合在一起。不久后,就有了实践机会:2001年6月,A股迎来了国有股减持大事件。当时A股市盈率在56倍左右,政府想参考市场价减持一些国有股用以补贴社保。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公开表†达:按市场价减持是错误。当时股市的估值偏高,是因为只有1/3的股票流通,这是合理的“流动性风险溢价”;而对非流通股,大多是按净资产,甚至低于净资产转让,按当时平均利润率,净资产大约对应16倍的市盈率;那么A股实际的“加权市盈率”是30倍左右,对于当时中国GDP每年10%的增长速度,30倍的“加权市盈率”其实并不高。所以当时我参照反射理论的原理提议:应该按净资产减持国有股,不应该参照“流动性风险溢价”后的市场价。如果按净资产减持,会降低市盈率,促成牛市;反之,会提高A股市盈率,投资者将被迫用脚投票,导致熊市。
事实上如我们预期,2001这波熊市一直持续到了2005年国有股兑价股改,当时大量股票价格跌破或近似于净资产(还没计算不少公司为了MBO在这个大熊市期间隐藏利润);放弃与民争利的股改之后,就是2005-2007轰轰烈烈的大牛市 —— 熊牛交替的结果证明市场是聪明的。
欧洲10年宏观实战:只有人,没有神
春晓:你曾经提到在法国工作时,发现很多大公司基金经理平庸,能介绍下当时的情况吗?
袁玉玮:我在巴黎读完商学院后开始工作。进了法国第二大的独立投资顾问公司。我凭借着自己的投资框架,一进公司就做到了业绩第一。
我策略中使用技术分析信号,就连很多之前完全不信技术分析的机构客户也被我的业绩说服,其中包括当时德意志银行旗下最大的对冲基金ArrowGrass的投研总监。还有一家Dalton基金的CIO观察我的组合一直以为我是价值投资派(证明在多空充分博弈的欧美市场,宏观+技术分析的输出结果也受基本面支持,一般没有太大矛盾)。由于工作中积累越来越多通过技术分析印证股票并购,基本面数据的成功案例,发现三者并不矛盾,也就逐渐建立起自信,和自己的交易体系。
到后来,我就专门做买方的“Alpha Capture”策略投顾业务 —— 有些大的对冲基金或投行自营部会专门划出一笔资金来配置/交易我们的策略,除了没有直接下单权限,交易信号产生,策略组合如何配置以及资金的风险管理都由我们来定(当时德意志银行的整个自营部都是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客户包括德意志银行Prop Desk的CIO,JP Morgan伦敦的明星交易员,还有索罗斯的CIO等。合作中接触多了以后,觉得他们90%都很平庸,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比如德意志银行一个PM跟我合作,要求我不但给他每天发交易策略,还不能提前发,要在价位触发前5分钟跟他电话提醒,很缺乏敬业精神,这个人在2008被裁掉了。还有一个美国最大的自营交易公司主观要求每天提供1-2个策略,达到每周盈利8-10%目标,且最大回撤1%。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没有任何逻辑:初中生都可以算一下复利,即使100美金本金起步,4年多点就可以超越巴菲特800亿美金身家了。
还有当时索罗斯的CIO,金融危机中间我跟他建议做空风电,太阳能。他问我原因,我说一是技术分析和量化有卖空信号;二是宏观基本面,2008次债危机全面爆发后,政府财政肯定缩减,对依赖财政补贴的新能源行业是致命打击。他说要去看看公司财务报表再决定。结果还没看完就跌了20%,错过了开仓最佳时间。我认为他错过这个交易机会不是错,但错在作为Soros宏观基金的CIO,应该是自上而下风格,却变成自下而上依赖财务报表,是严重的风格漂移。不出所料,那个CIO在2008年被索罗斯拿掉了,老人家亲自出马,在2008实现盈利。索罗斯在2000年后,量子基金CIO Druckenmiller离职,任人唯亲,让儿子接班,用外聘CIO或兼职CIO的模式管理量子基金,导致了风格严重漂移 —— 没有核心人才和策略,这对一家对冲基金是致命打击。
所以我当时工作2年后,就已经不盲信投资界的神和光环了。所有人都是凡人,没有神。
从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国外,基金管理公司(和国内不一样)并不依赖明星基金经理,而是一套完善的投研和风控体系,来管理人才,扬长避短。基金成功关键是管理团队的体系和文化。
春晓:什么时候有回国发展的想法的呢?
袁玉玮:2008年,我个人代表公司,拿了《Investars》全球143家投行alpha capture业务比赛业绩第一名 —— 其他公司都是几十到上百人的团队参赛,JP Morgan, Morgan Stanley, UBS这些大投行都参加了。我们是实打实地比拼业绩,不像某些奖项机构排名靠销售拉票。

而且2006-2009,我们连续三年期也是Investars前3。我在2009年换了工作,又用了6个月时间,把新公司做到Investars前3。
但做投资顾问时间长了,也就腻烦了。我的职业目标是自己做基金经理,不是给别人(客户)当背后默默无闻的影子枪手,尤其见了那么多平庸的基金经理之后,尤其整个组合的建立,策略,调仓,风控都是我替客户做。客观上,实际是我在做基金管理的工作,客户在做证券经纪的工作。
我做投资目标不是为了钱和名声,但收入和荣誉是对职业成绩认可的量化指标之一。
中国1个月,法国十年
春晓:你2015年就回到中国,迄今情况怎么样?公司的目标是什么?
袁玉玮:回国发展也学习很多。我发现自己做公司和在公司做交易研究是两码事。自己做公司要被很多运营募资工作浪费精力。国内金融圈整体还很浮躁,会被很多没意义的会议浪费时间和精力。
我们目标打造一支真正的全球宏观基金和alpha capture团队。真正的全球宏观策略和所有资产低beta,而且有抗尾部风险能力,对资产配置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
全球宏观这个领域,在国内和国外都比较空缺。我们和国外机构投资者交流,也说我们的策略逻辑很少见。索罗斯之后,做全球宏观的人越来越少了。
春晓:回国之后投资理念上有哪些丰富?
袁玉玮:中国变化快,每天都要向市场学习,向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学习,投资理念丰富得更快了。个人认为,中国的交易员基数大,土壤野蛮,所以活下来的天分和勤奋都比欧美好的很多,但欧美人更擅长风险管理,这一点中国人还有很大差距。两边擅长不一样。
2015年刚回来就赶上大牛市,又是索罗斯反射理论模型的实践。有个客户2015年4、5月问我怎么看股市。我反问他:现在宏观经济有没2007年好,他说没有;2007年有没有资金滥用杠杆?没有。那么2015年的A股这么多人使用杠杆配资,甚至用信用卡融资作本金,股市涨的比2007年快。我说这样的大盘只要涨速低于预期或资金成本,随时都会因为丧失流动性跌停。要离场,就得左侧,右侧想走也走不掉。跟他说完不到一个月,市场就崩溃了。
这样的场景每年都有。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日新月异;行业牛熊周期切换很频繁;人也浮躁、急功近利。虽然有很多缺点,但你在中国1个月,比在法国10年观测到的变化都大 —— 法国十几年,一个面包店或土耳其烤肉店都会一成不变地开着,在中国很多城市一年不去就不认识了。这对我们考查人性,观测宏观的变化,是很好的视角,每天都在学习。欧洲的社会波动很小,几乎静止的,对老百姓很安居乐业很好;但对我们,相对在中国,思维空间相对保守、狭小。在中国,你每天都在看巴尔扎克的史诗 ——《人间喜剧》实时上演。
春晓:投研上有发现什么问题或者教训吗?
袁玉玮:有。过去策略没有发现的缺陷在2016年暴露了。粗略地说,宏观策略,怕波动率衰减。2015年到2016年,波动率放大。我们做宏观多空对冲,盈利很稳定,而且越来黑天鹅,业绩越好。2016年是教训最多的一年。业绩前高后低:首先运营分散投资精力,另外是宏观策略怕波动率衰减这个经验历史上第一次遇到;还有就是那年演讲、会议很多。出去天天讲,讲多了无形对自己强化自己的观点,你的动作会变僵硬,对自己有心理暗示。所以后来的演讲我一般都推掉了。那时没掌握好节奏,谁请都去。最多的一天4个会,快变成娱乐圈的了。
还有一个教训,即便宏观全都判断到了可能还会造成负面影响。2015年,我判断石油危机,并且基于贫富差距扩大,预测2016年英国脱欧,川普上台是大概率事件。现在很多人讲贫富差距。那时讲这个逻辑的人很少。而且我们提前连节奏预测对了:预测英国脱欧会先跌后涨,川普上台也会先跌后涨,因为他们都是对前人错误的纠错。但结果我们业绩反而连续阴跌回撤,因为我们判断的是先跌一、两个月再涨一两年,结果是只跌了跌一、两个星期就直接涨。因为我们几乎所有都预测对了,所以认为市场是错的,我们是对的。结果虽然宏观趋势,方向和节奏几乎全都预测对,但一两个小细节的错误,反而对业绩负面影响。
春晓:你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吗?
袁玉玮:我觉得还比较单纯。我认识的做得好的交易员人都很单纯。人单纯,才能从复杂的市场化繁为简,抓主要矛盾。人太复杂,想得多,想面面俱到,想挣钱还不想承担风险,就会化简为繁,很难做好交易。
复杂还能做好交易的,大概几种情况:一是运气太好;二是业绩有水分,存在幸存者偏差;三是公司投研风控体系很好,弥补了个人缺陷。除了第三种,前两个很难长期维持。
宏观对冲就像实盘三国演义
春晓:你说对冲流派里只有宏观对冲具备抗黑天鹅的能力,能诠释下这个观点吗?
袁玉玮:这个不是我的观点,是Credit Swiss的研究结果。他们在次债危机后2009年专门发了篇报告,借用Paul Simon的歌名《Global Macro -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标题。他们统计,历史上,金融危机中和后,包括2007-2008次债危机,盈利能力和Sharpe比率最高的是全球宏观基金,而且宏观基金的盈利不依赖市场方向,牛市和熊市都可以盈利,和所有资产保持低相关性。
2007-2008次债危机中亏损最大的60-70%是量化基金,包括最近几年的黑天鹅中也是。比如最近,国内吹捧的量化巨头Winton上周亏损9%,Renaissance亏损7%,盈利的大都是宏观基金。
我认为,价值投资,成长,宏观,量化,都有自己擅长的场景,也都有自己不擅长的场景。我们不能过度崇尚任何一个,也不能过度贬低任何一个。神话巴菲特、索罗斯,神话量化我都比较反感。我是70后,见识过人群集体运动的后遗症,所以天生对神话和崇拜反感。现在国内对“量化教”和“茅台教”过度神话,国外对巴菲特和量化都反应平静,没有狂热。
崇拜,就是一种主观,无论崇拜神,崇拜权威,还是机器,都是主观。
和主观对应的是客观,不是量化。把哲学和工具对立 —— 崇拜量化的人犯了一个很基本的逻辑错误。
春晓:你把 “技术分析”可以分成四个派别,能简单介绍下吗?
袁玉玮:“图形派”:这个属于初级阶段。说技术分析不管用的人,很多还停留在图形分析的初级阶段;
“量化统计派”:通过技术分析的信号形态可以做一些归纳;
“哲学派”:“K线”实际是从日本的兵法演变而来的,追根溯源就是《孙子兵法》里的“风、林、火、山”四个形态,再演变成各种的K线组合。K线图中实际包含了很多中国的古典哲学理论,比如K线里面的“阴阳转换”,跟太极图有很密切的联系,因为《孙子兵法》本身就来自于道家的理论。如果对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化继承太少,会阻碍把技术分析应用于交易;
“博弈派”:“反技术”算是博弈的一种。博弈派包含一些兵法,比如你可以“跟庄”,也可以做“流动性分析”。打个比方,之前的“新疆德隆”,还有今年的“上海莱士”,为什么会突然连续暴跌?其实很正常。因为它的“日换手率”每天都只有0.2%,还能维持在那么高的价格,肯定是被庄家控盘了,随时会产生流动性风险。看似稳定的股价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很不稳定的变量上的。我们从机中看到危,就是利用反技术。
所以,“技术分析”应用中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大道至简”,要做“减法”,做“大概率事件”和“模糊控制”,因为越精确的东西反而是越危险,纠缠于细节越多,越容易一叶障目,而忽略宏观风险。
春晓:宏观对冲吸引你的是什么?
袁玉玮:交易的不确定性和博弈,需要我们不断思考,不断学习。
做宏观对冲感觉在现实里面实盘三国演义一样。和宏观经济学家的东西不一定能交易不同;宏观交易员要把观点用交易表达出来。我们的投研目标是要交易的观点,或者如何把宏观观点落实到交易。比如我们在2018年发文,基于地产、医疗、教育三座大山,对居民消费能力的挤压,给宏观经济带来风险,建议宏观调控应该压制这三个行业,释放居民消费能力,才能对抗宏观风险。我们会择时做空三个行业的资产。这些对信息处理能力,分析能力,博弈能力,反应能力很多考验,这也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还有,上个星期(2.24-2.28),我判断科技股的风险度上升,主要用的是三十六计里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连价格和技术指标都不用看。中兴通讯是大市值,行业壁垒也不是特别高,不具备高成长特征,常规形态应该是震荡式慢牛。但它却在科技股板块整体高度泡沫化、滞涨的时候连续两个涨停加速拉升,这种悖离常理的现象大概率是庄家手法,提振人气,转移散户注意力,让你们都觉得科技股崛起,好掩护其他科技股的出货。这种博弈,又不能完全量化的场景也很有意思。
袁玉玮现已入驻交易门非公开社群
欢迎大家入群和袁玉玮切磋交流
请添加小编微信咨询非公开社群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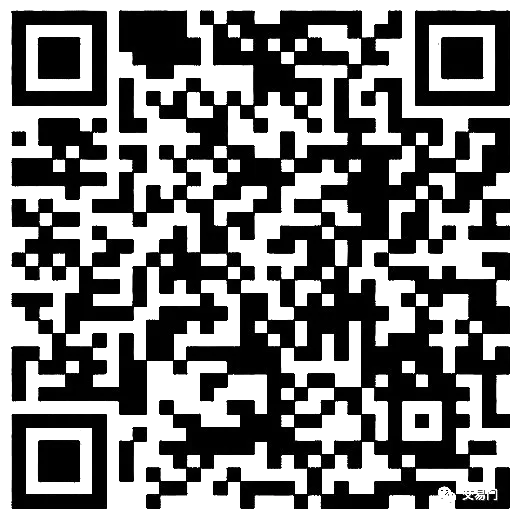
(18123353165)
加入交易门非公开社群还可以和
(点击查看人物报道)
交易门主角:汤立将于3月14日
(点击查看人物报道)
与交易门读者线上分享美国对冲基金运营实操
欢迎添加小编微信报名
(18123353165)
非公开社群成员可以免费获得活动回放
包括上周日交易门主角:华尔街老孙线上分享
美股自营交易系统实例音频资料
以及活动视频
周翔:波动率交易及风险管理
请添加小编微信购买深度精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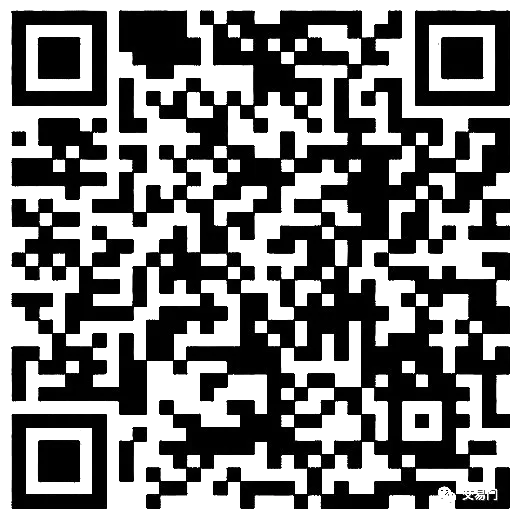
(18123353165)
从零到一打造自己的全自动交易系统
年赚6亿美元的期权交易员
职业牌手、资深基金经理
高收益债资深大佬
宏观对冲基金经理
二级市场母基金和一级市场股权投资
柯南
美股基金经理
携程国际火车票CEO
全球科技股捕手
资深期货从业者
资深债券交易员
王丰
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总编辑
……
了解更多精粹内容请点击下面图片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