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本是南开美女学霸,却中年丧夫丧女,65岁赴美,还成为了英美最有名的华裔女作家(附视频)

英语演讲视频,第一时间观看

看过下图这么一位老者的照片,已然90岁高龄的她,穿着蓝调旗袍,头发花白。一双老年人罕见的、幽邃晶亮的眼睛,温柔而有力,那种透过岁月尘土夺目的美,令人过目难忘。

《一代宗师》里有这么一句台词:“一门儿里,有人当面子,就得有人当里子。”行当如此,人生亦如此。人活一世,不外乎也是“面子和里子”的双重选择。
有人要面子,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有人要里子,腹有诗书,虚怀若谷。但还有第三种人,既要面子的精致,又要里子的沉稳,将人生活成了大写加粗的“体面”二字。
郑念,就是第三种人,被誉为中国最后的贵族、最后的名媛。
很多人知道郑念,是因为她那双眼睛。在很多老照片里,八十多岁的她,头发花白,面容沧桑,那双眼睛却深邃晶莹,有星光,有大海。
体面的人,有一种向上生长的姿态。纵使被时光侵蚀了容颜,那周身所散发高贵气质,仍无法被尘土掩埋。
今日,我们就来聊一聊,郑念渗透到骨子里的人生观——体面。
专访郑念
扬名世界的英文自传《上海生死劫》
“将永远离开生我养我的故土,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只有苍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贞于我的祖国,可是最终还是完全失败了,但我是无愧的。”
——郑念《上海生死劫》
纸醉金迷里的保持优雅得体,不算什么;
日常生活里保持优雅得体,也不算什么。

她被媒体称为“中国最后一位贵族小姐”。
人们纷纷感叹,她就是中国版的唐顿庄园大小姐。
更有人称赞她是东方的超级名模卡门·戴尔·奥利菲斯。

民国时期的“大家闺秀”,家境优渥,书香门第,但多给人留下交际花、娇小姐、少奶奶之类的印象,在历史上留名,也多因为她选择的男人,比较有名。
印象中,女子的贵族风范,似乎只是一出纸醉金迷的私生活、无休无止的交际和挥霍祖上财产做支撑的皮影戏。
没了虚浮的奢华,便没有没落的贵族,却只有郑念一人独占鳌头,受人青睐且毫无诋毁之意。
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出生于北京,后在天津长大。
她的祖父姚晋圻,曾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参与过戊戌变法,极重教育,曾任湖北教育司司长。
她的父亲姚秋武,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在中华民国革命海军舰队任职,是少将军衔。
当时的天津名流云集、名门望族纷纷置下房产,玩乐风尚渐渐兴起,形成上流社会。
许多名媛都曾在交际场合,大出风头。
《北洋画报》更启用富家闺女做封面,为这股名流之风推波助澜。
家世显赫,再加上她天生美貌,还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的她,就曾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成为京津卫地区的“风云人物”。
一般来说,只要在北洋画报上露了面的人,都能成为社交界最红的明星,无限风光。
在郑念之前,因在画报上露了面而名噪一时的,是赵一荻。
就是那个16岁与少帅张学良私奔,成就一段爱情传奇的赵四小姐。
可郑念的美,却像流星过境,嗖嗖四下,一闪而过,没有成就什么传奇姻缘。

她懂事,也聪明,安心听从家里的安排,读完了中学,考上了燕京大学,之后就出国了。
在与牛津、剑桥齐名,号称G5超级精英大学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
在天津,她追求者众多,到伦敦才遇到真爱。
20岁,她与正在学院里苦读博士的郑康琪相恋并结为夫妇。
多年后,她谈到女儿梅萍时曾评价说:
她还明确表示,虽然女儿当电影演员她不反对,但她打心底里希望她能从事以文化知识为资本的工作,而不是靠她的外貌。
郑念懂别人,更懂得自己。
她知道自己的家世不只是钱财上的富有,而是学识、眼界上的充盈。
像她这样的才女,应该享受的绝不只是交际场上出风头。
婚后,郑康琪在外交部任职,远赴澳洲任职。
夫妇两在澳洲生活七年,女儿也在澳洲出生。
1949年春,郑念随夫从香港回到上海。
她说:
郑康琪受聘为陈毅市长的外交顾问,后来成为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这是一家大型的跨国公司,也是1949年以后唯一留在内陆的西方石油企业。

当时的上海,百废待兴。
多事之秋的季节里,很多富人都变穷了。
很多工厂撤出上海,工商业者也一起搬到内地安家。
而郑念在丈夫去世多年,生活质量依旧。
靠墙排列着书架,上面是中英文书籍都有。
台灯下,还安置了皮沙发,供闲来无事,多多阅读。
一位经常拜访她家的英国友人称赞说:
郑念不愿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她家里依旧有仆人,管家,厨师。
对此,她自豪地说:
在上海,私人很少有像我这样的居住条件。
这个一千万人口的城市里,大约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家庭仍旧保持着老的生活样式。

家,是丈夫去世后,她与女儿生活中的避风港。
然而,一场风暴就要来临了。
无形的威胁正悬在空中。
1957年,郑康琪因病去世,郑念接替了丈夫的工作,担任英籍总经理的顾问。
郑念起草无数多家公司与内陆之间的重要通信。
总经理回英国,或者出差去北京,她代行总经理的职权。
她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因为她是享有在世界著名公司里从事高级职位仅有的女性。
似乎生活中的一切,与郑念自身,都是想匹配的,丈夫的身份、工作的体面、当然还有她自己的日常。
她家里有唱片,经常邀朋友一起听;女儿回家时,解闷的事,是弹钢琴、聊国内外局势。

1966年春天,壳牌石油公司关闭了在上海的办事处,郑念正打算用这段空余时间,与女儿一起去香港旅行。
可那年的一天清晨,家里来了两个陌生人。
郑念很爱看报纸,对社会上的风云变化了如指掌。
她知道,这次来的两个人,一定与那场即将到来的大风暴有关。
仆人向她描述了那两人的外貌,其中一个是郑念的同事。
她琢磨了一会儿,决定用磨洋工来让自己思考该如何应对。
冷静中,她还不忘让管家给两人上冷饮与香烟。
下楼时她走得慢极了,竭力显得镇静、沉着。
刚走进会客室,便打量起他们来。
一个小时后,她被拉去参加了批斗会。
晚上,她选择步行回家,让自己有多余时间思考。
她拉来了好几个朋友,分析如遇困难,个人该如何行事。
就在这种时候,她居然用当年胜任高级职员的经历来安慰自己。
想起自己三番五次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赢得了员工的尊重和信任,让一个女人去管理他们。
她对自己说:
可是,这一次,生活给她的挑战是进看守所。

这是在1967年。
理由是郑念因为过奢华的生活,走资本主义路线,长期在跨国公司供职,有很大的间谍嫌疑。
可刚一进去,就因为自己可能有机会用另一种方式来体验生活,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度过一生中的某一段时间而激动。
她居然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危险境地。
可是她立即警觉起来了。
因为看守所太脏了,蜘蛛网自上而下垂着,床上满是污垢,不怎么亮的小灯泡彻夜不熄。
郑念请求关灯,要求被驳回,不过午夜过后,灯光还是熄灭了。
黑暗掩盖了污秽。

郑念后来回忆起看守所的时光时,总觉得熄灯后黎明前的片刻黑暗始终是她恢复自尊、感到新生的时刻。
那时,她暂时摆脱了看守戒备的目光,拥有了片刻的自由。
尽管如此,她还是无法忍受白天里,四处可见的肮脏。
就在向管理员申请生活必需品时,她申请了一小盒面霜,还希望能有水打扫牢室。
要求被驳回,她便振振有词背诵毛主席语录:“以讲卫生为光荣,不讲卫生为耻辱”接着温言款语来了一句:
等啊等,她终于等到了足够的水。
女看守说她这样做,是想把资产阶级生活带到看守所来。
郑念不为所动,她靠背唐诗三百首打发时间。
不久,她还看起了报纸,尽管灯光微弱。
她可以哭的,但她没有。
她说哭会让她给别人留下软弱的印象。
其它时候,可以哭。
但在看守所这样的艰苦环境里,坚决不能哭。
一哭,人就没有斗志了。
她活着出去见女儿,这是她努力生存下去的唯一念想。

后来,她双手被手铐反扣在身后,手腕被磨破了,手也肿了起来。
仅仅十一天的时间,她的手就麻痹了,举不过头顶。
她只能靠坚持锻炼来恢复,数月后,她的手才能举过头顶;而整整一年过去后,手臂才能重新伸直。
未来的两年之内,她的手背依然没有任何知觉。
然而,六年来,她拒不认罪,也没有揭发任何人。
别人的恐吓,从未将她吓倒。
因为天冷,她请求添加衣物,可她坚决不穿囚衣。
一来,她没有罪;二来,囚衣套上之后,她仅剩的一点尊严与独立就没了。
最终,她的坚强为她赢得了自由。
出狱前,一个医生对她说:
让她挺下去的不是自己的好斗,而是她确信出狱后就能见到女儿。
正是确信一定能见到女儿,所以1973年出狱前,她还做了一件事。她反对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刑满释放,竟然拒绝出狱。
她说:
看守觉得好笑,只好骗她说女儿在外头等着她,成功转移她的注意力后,就一边一个把她架出了看守所。

六年来,她第一次照镜子。
一看镜中的自己,她大吃一惊。
脸色苍白,双颊深陷,体重只有77斤。
一缕缕干枯的灰白头发黏在头上。
唯一显得特别明亮的,只有一双眼睛了。
她端详自己很久,许下愿望:希望不久脸色能红润起来。
而眼睛,她最美丽的眼睛,能以宁静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副惊弓之鸟的神情。
她积极地“修缮”身体,也修缮新住所。
别人告诉她女儿自杀了。
她不信,因为女儿的性格像她,是不会自杀的。
这时候的她,又有了新的生存目标:追查女儿的死因,让真正的罪犯伏法。
这个想法是相当天真。
可是,郑念的许多想法都是天真的。
出狱后的她,依旧善良,从不因为自己遭了罪就随意践踏他人。

一位阿姨被安排进来照顾她生活。
起初,阿姨监视她。
后来两人关系好了,给花园砌墙时,阿姨就主动请缨要回苏州老家,让老公帮忙买砖头。
郑念觉得阿姨是个头脑简单的人。
阿姨却整天乐呵呵的,给郑念的评语居然是:
后来,朱太太一家搬来了。
郑念对朱太太很是头痛,经常讽刺她,可是两家总是一个屋子进出,郑念后来还经常帮她去国营小卖铺里买高级香烟。
来监视的人中,还有一个叫大德的男生。
他听说郑念的英语口语是全上海最好的,前来向她讨教。
结果,大德虽然依旧在监视,却经常陪郑念出去购物,代她排队,人多时就把人推开,给她让路。
大德人高马大,一眼就能看见货柜里在供应什么食物。
他对郑念说:
两人约着一起去吃大餐。
郑念说:
聊天时,大德的个人主义让她觉得惊讶,而大德则觉得她笨得可以。

生活宽裕后,她觉得对每个人都要慷慨。
新年时,她孤单一人,有朱家、阿姨和大德作陪,她很高兴,居然一次性买了一个大蛋糕和两斤巧克力送给朱家。
后来朋友到访,竟说,
福楼拜曾经说过:
命运对她不公,她却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六年的牢狱生活,没有将她打垮,因为她觉得出狱后,见到女儿时一定要体面。
得知女儿已去世,她再次披上战衣,四处奔走调查。
最后,她决定离开祖国。
两个妹妹都在美国生活,她六十五岁了,也应该享受姐妹团聚的幸福了。
到了异国,她很快适应了现代化的生活,超级市场的购物、银行自动存取款等等。
她开始随心所欲的安排生活了。
家族存在海外的钱,够她生活了。
她对物质并不避讳,每天都享受着丰富商品与第一流的服务带给她的安全感。
可是,她似乎还剩下一点斗志,她总觉得似乎有一种东西在强迫着她,要把心中的话一吐为快。
她开始写作。
一个人坚持不住的时候,身旁的挚友就鼓励她写下去。
1987年,她出版了全英文写作的《上海生死劫》,追溯那段悲痛的经历。
出版的当年,就成为超级畅销书,享誉多国,再版多次。

书的开头写了几个字:献给梅萍。
这是她死去女儿的名字。
而作者的名字,也从姚念媛变成了郑念。
这,纪念的是丈夫郑康琪。
这本书以其细致入微的洞察力,朴质的叙述打动了很多读者,其中就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
给《纽约时报》写书评时,他称赞道:
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忆录最伟大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对自己抵抗心理和身体的压力的记录。
信息多,充满了勇气的,吸引人的书。
这本书,记录的是一个女人的一生最灾难性的时刻,也记录下了她无尽善意的时刻。
经历了诸多苦难,她最后是认命的。
她觉得女儿的死是命中注定的,她抗争不了。
可是她的命,也是注定的。
她是个基督徒,她觉得既然上帝让她坚强的活着,把她对生活的要求,把她一直尊崇的优雅,说成好斗不驯,那她就这样活下去。
2009年,她因病离世,以94岁高龄走完一生。

朱大可说:
《上海生死劫》的出版让她的生活再次忙碌起来。
她开始了全美巡回演讲,还设立了“梅萍基金会”,专门资助中国内地的留美学生。
她的善良让人铭记于心。
加拿大歌手柯瑞·哈特就专门写了一首钢琴曲向郑念致敬。

她的美,是有风骨的。
她,一辈子都是传奇。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
到了郑念这里,试问苦难是否配得上她?
美,对她来说,是一种责任。
纸醉金迷里的保持优雅得体,不算什么;日常生活里保持优雅得体,也不算什么。
遭受苦难时的优雅与善良才最可贵。
Nien Cheng obituary
郑念讣告



Several years before Jung Chang's Wild Swans (1991) proved a sensation in the west, the work of another Chinese woman who suffered badl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 years of turbulence had become the first bestseller in English about this period.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1987) is a memoir of huge sorrow and triumph by Nien Cheng, who has died aged 94; it could be read as symbolic of the story of modern China itself.
She was born Yao Nien Yuan into a rich landowning family in Beijing and was studying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in 1935 when she met her future husband, Kang-chi Cheng. A supporter of the Nationalists, on the couple's return to wartorn China in the 1940s he joined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hey lived in Australia briefly, setting up an embassy the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meant that Kang-chi's political affiliations were potentially a problem. But he was to die, of cancer, in 1957, while serving as a general manager for Shell, one of the few foreign companies that maintained a presence in Mao's China.
After his death, Nien took up the position of political adviser to Shell and lived with their daughter, Meiping, a successful actor, in a large house in Shanghai, with antique furniture, servants and a good standard of living. But as Nien was to explain vividly in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all that was brutally ended one day in 1967 when a visit by one of the newly created Red Guard rebellion groups heralded her own initiation into the terrifying worl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had started formally months earlier in Beijing.

Her memoir documents her house arrest and the many hours of interrogations, in which she used Mao's words and slogans back at her own captors, and showed a proud, unbreakable spirit. She was placed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for more than six years, and was released in 1973, a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winding down. She was told almost immediately that Meiping had committed suicide in 1967. Nien did not believe this and was to find subsequently that she had been murdered by Red Guards. This shattering revelation, and further attacks from leftist activists, meant that, in 1980, she applied to leave China, and went to Ottawa, Canada, and then, in 1983, to Washington. She was to be based there for the rest of her long life.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her memoir she received acclaim. The book was reviewed warmly, partly because it told the inhuman and incomprehensible 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a human, comprehensible voice. But the trauma that the events in the late 1960s had left on Nien were not so easily erased. She told Time magazine in 2007: "In Washington, I live a full and busy life. Only sometimes I feel a haunting sadness. At dusk, when the day is fading away and my physical energy is at a low ebb, I may find myself depressed and nostalgic. But next morning I invariably wake up with renewed optimism to welcome the day as another God-given opportunity for enlightenment and experience. My only regret is that Meiping is not here with 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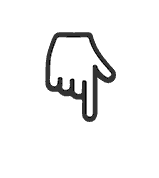
防止未来失联
请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备用号

想第一时间接收英语演讲文章&视频?把精彩英语演讲设置为星标就对了!操作办法就是:进入公众号——点击右上角的●●●——找到“设为星标”点击即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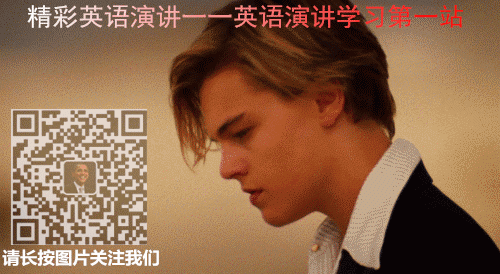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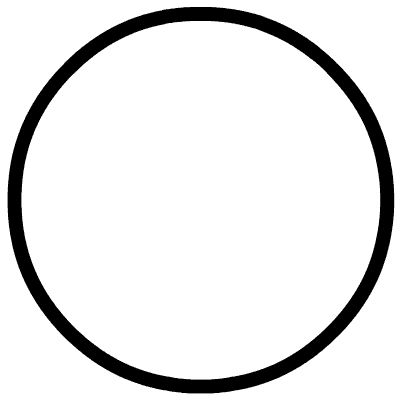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