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于「佛国」龟兹,鸠摩罗什的身世有多神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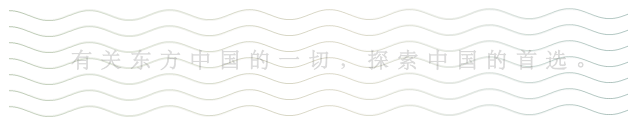
这就是从佛国来的那个和尚吗?弘始三年,当长安的信众们越过摩肩接踵的人群,望向高座上讲经的身影时,心中想必这样揣度着。
这时,距离第一位皇帝立誓要将鸠摩罗什迎入长安,已经过去了20年,而当初发下宏愿的帝王苻坚未能活着看到这一切,他死于一场争雄之战,胜利的一方接替了他的雄图霸业。
然而,苻坚希望迎佛法东来的心愿,并没有随着身死国灭而化为泡影。新任帝王随即发动了另一场战争,刀锋直指凉州——高僧鸠摩罗什被羁縻的城市。

△《真禅内印顿证虚凝法界金刚智经·三卷》明·沈度写、商喜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战争的结果显而易见,随着一座城池的覆灭,高僧鸠摩罗什踏上了东来之路。长安城西南,原本由姚氏王族营造的华丽非凡的逍遥园很快覆盖上茅草,摇身一变而为讲经译经的所在。
草堂寺,这座至今仍保存着鸠摩罗什舍利塔的寺庙,成为了龟兹高僧生命中最后一个驿站,以及长眠之所。
长安距龟兹,1280里。事实上,在鸠摩罗什之前,来往这条路上传佛的沙弥、居士和学者早已不绝于途。他们携带用婆罗米字母书写的龟兹文、焉耆文佛经东上,再倾数年、数十年之力将它们译成汉文。
近百年间,这些无名的信徒燃尽自己身为凡人短暂的寿数,使得三藏精义在汉地传播。其中不乏将名字留在了经卷结尾处的高僧大德,然而,他们是否还有机会回归佛国故土,则再也无人知晓。
龟兹王世子帛延就是其中的一个,在鸠摩罗什入长安前十年,帛延的名字出现在汉地的译经场中,他领衔翻译了《首楞严经》,在这部佛典的后记中,人们特别记下了他「善晋胡音,博解群集,内外兼综」的风采。
但他此后的行迹无人能知,结合另一条史料,如果他与曹魏三年在白马寺译经的帛延是一人,那么,此时的他应该已经垂垂老矣,几乎没有可能再回到龟兹。帛延很可能在某座无名佛塔下结束了一生。

△《真禅内印顿证虚凝法界金刚智经·三卷》明·沈度写、商喜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独特的姓氏「帛」表明,帛延与鸠摩罗什一样来自龟兹国的王族。
长安城里的信众也许很难想象,为何世俗富贵丝毫没有牵绊住这位王族的青年,却令他在信仰驱使下,不远千里、横穿黄沙来到燃烧着战火的异国。
但很快人们就会释怀。因为他来自龟兹,那是传说中的「王宫焕丽,与寺无异」的西方佛国,是佛陀的一颗明珠。
诞生了帛延和鸠摩罗什的龟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龟兹的佛法何时传入,这个问题恐怕不会有确切答案。中原人注意到的那一刻起,龟兹已经作为一个知名的弘法的驿站而备受瞩目,先是在塔里木盆地、葱岭内外的西域小国中声名远播,再逐渐向东传递。
当我们打开地图,试图勾画出佛教东传的轨迹时,历史会带领我们勾勒出两条线路,一为南线,僧人们由印度出发,途经大夏,也就是后来的大月氏,向东折去,途经于阗,继续向敦煌前进,抵达中原内地。
另一条则需要僧人以更加非凡的勇气,绕过塔里木盆地北上,再向东行去,一路串联起龟兹、高昌、楼兰等小国,如同串起一串明珠。而龟兹就是这串明珠上最为耀眼的一颗。

△《真禅内印顿证虚凝法界金刚智经·三卷》明·沈度写、商喜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由于语言、社会习俗、人种构成都与印度较为接近,在2世纪左右,龟兹迅速地接受了佛法。如果我们爬梳史料中的寥寥记载,也许能将这未经考证的想象边界推至公元前。人们曾在梁朝文士刘之遴的收藏中发现一只澡罐,上有铭文:元封二年,龟兹国献。
很难解释,龟兹为何会不远千里献上一只普通的澡罐,一种普遍的猜测是它与礼佛仪典有关,是专门用来洁身的佛器皿。
元封二年,那是公元前109年,就在不久前汉武帝还雄心勃勃地封祭了泰山,属于大一统王朝的光芒正喷薄欲出。而光阴如逝,到了鸠摩罗什的时代,400年泱泱大汉已归乌有,中原沦落为野心家的战场。
但是,龟兹的佛光却从未熄灭,甚至愈加明朗,3世纪,营造佛窟的斧凿之声在木扎提河两岸响起,同时,被称为雀离大寺的一代名寺也开始动工兴建,濒临着河水,佛寺的建筑蔓延到斜坡之上。

△《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上下卷》明英宗正统四年泥金写绘本
龟兹逐渐展现出了属于佛国的繁盛,高僧大德们聚拢于此,西域诸国的王族们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翻度葱岭,来到龟兹求法。
鸠摩罗什的父亲鸠摩罗炎就是来到龟兹求法的一个,他出身于天竺宰相世家,却果断拒绝了本应承接的政治担子,也许这就是他被传者评为「倜傥不群」的原因,然而,这位看似自由的年轻人,转而挑起了另一副更长久、更沉重的信仰重担——佛法。并发愿前往龟兹。
然而,在这座佛国里,他很快就经受了信仰与世俗的双重挤压。龟兹国的王妹耆婆一见之下,倾心于他。
「王闻大喜,逼炎为妻。遂生什。」
在混杂了神异与春秋笔法的记载中,人们已经放弃了探究这桩婚姻的原委,而是把它视为鸠摩罗什传奇的一部分。
诞下罗什后,耆婆随即出家修道,当罗什长到7岁时,也跟随着母亲的脚步,去雀离大寺出家成为沙弥。
雀离大寺并不亲近红尘,它位于龟兹王城以北20余里,从王城出发去雀离大寺,路途所见,便是一个孩子眼中的佛国。

当罗什12岁,游学归来回到龟兹时,他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有一万多个僧人,占据了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这之中有印欧人、龟兹人、西域诸国人、汉人,也许还有更遥远的西亚人,比如叙利亚人——5世纪,人们在龟兹佛窟壁画的题字上发现了他们的手迹:「来自叙利亚的画家摩尼拔陀绘制了此画。」东西方的触角在此交汇,正是他们构成了这座佛国的底色。
当车辆驶出王城,沿着河流去向西南方时,在靠近佛寺的山坡上,数以百计的洞窟开始显现。这是无数凡人倾一生劳力和虔诚造就的奇迹——龟兹石窟。
两千余年之后,它们之中的代表克孜尔石窟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对古龟兹文化的纪念。然而,在罗什受戒这一年,石窟们正发挥着自己的实际用途——不仅仅作为艺术,从建筑、雕塑、绘画三个方面来诠释三藏义理,同时,它也是僧侣们持戒、修行、演讲教义的实用场所。
供养佛像,用来礼拜的支提窟,供僧尼静修的禅窟,以及容纳修行者肉身起居的寮房,收纳骨灰的罗汉窟,等等,生、老、病、死,以及凌驾于其上的信仰,在这些佛窟里奇妙地并行、共生着。

△克孜尔第38窟·5至6世纪·柏林民族学博物馆
那个时代的龟兹人,也努力将自己的印记留在石窟里,以壁画或者雕塑的方式与佛同在。
在克孜尔石窟的供养人中,甚至能发现某一代龟兹王和王后的形象——脸庞浑圆,五官集中,国王用发巾包头,手持十字长剑;王后则穿着腰肢高束的长裙。两个人眉目弯弯,神色愉悦,如果不是圆形光头昭示着非同寻常的身份,人们可能会错把他们当作一对寻常的夫妻供养人。
事实也的确如此,两千余年后,佛法中所说的流转的业力抹去了一切,使得丘陵变为低谷,佛国变为尘埃,而王与凡人无异。
那年,去往雀离大寺的9岁的鸠摩罗什所看见的一切,如今都不复存在。龟兹更名为库车,销金的墙壁倒塌,佛窟前放牧羊群,塑像和壁画被割裂烧毁,或运入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博物馆保存。雀尔达格山的红色仍如火不退,但远处是大漠萧条、大河奔涌,两岸绝迹无人。

△《敦煌石窟》伯希和著·1920-1924年出版
很难想象,鸠摩罗什曾在幼年和少年时走过无数次的地方,数百年来无数僧人怀着炽烈信仰,赤足履过的佛径,此刻落得个大漠天荒,无知无识。
而淡金色的太阳仍悬在中天,似乎暗示着这片土地仍然是被佛光笼罩的土地,坏与空亦是轮回的一部分。
长达千年的佛盛世之后,业力继续推动这片土地滑入毁坏衰败的进程,寿数短暂的凡人闻风而喜,闻风而叹。唯有佛的目光注视着它,不悲不喜,这目光之中,也有当年那个初受沙弥戒的孩子——鸠摩罗什。
本文节选自知中ZHICHINA
017特集 《幸会!鸠摩罗什》
撰文 | 李冰洁
C O N T A C T
商务合作及投简历请发邮件
☞ 推荐阅读 ☜
点击下方图片即可阅读
为了汉字启蒙和美育,我们呕心沥血做了这件事
知中ZHICHINA秋招 | 童书策划编辑与营销编辑
宋代文人都沉迷的香文化,到底有多吸引?




点击👇阅读原文👇
快速获取《幸会!鸠摩罗什》
阅读原文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