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悲剧:比灾难更可怕的是谎言,比谎言更可怕的是遗忘


切尔诺贝利悲剧:
比灾难更可怕的是谎言,比谎言更可怕的是遗忘
来源丨网易新闻 文丨枕猫
1986年,凌晨1点23分,如果你在苏联乌克兰的普里皮亚季,你可能是20世纪最不幸的那一批人。现在是2020年,三十多年过去了,切尔诺贝利还是东欧人们心中魔鬼的代名词。
这次核泄漏事故,一共有1700多吨石墨爆炸燃烧,释放的大量放射性物质甚至一路飘到了法国,相当于“小男孩”核含量的400多倍,足足造成了9万多人的死亡,切尔诺贝利也一夜之间成为了一座空城。

而在34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这个事故?我想,追究泄露的原因,应该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考虑的事情,倒是应该用一个审视的角度,去看看,当事故发生的那一天,他们在做什么?
泄露发生之后
人们在深夜里熟睡。
突然有一束幽蓝的光,伴随着一声巨响,从切尔诺贝利发出,很多人从梦中惊醒,一副茫然。在附近的消防员瓦西里在半夜接到了核电站失火的消息,简单地穿好衣服,就像往常一样去了火场。
他的妻子一向是习惯了丈夫的这种作息的,不过这次她好像是预料到了什么,一语成谶的多说了一句话:“这颜色看起来不对劲啊。”见惯了失火的瓦西里还反过来安慰自己的妻子的过分担心,他不以为意地说:“这只是屋顶上的沥青,会烧一个晚上,而且臭得要命,这是最坏的情况了,别担心。”

然后这次出去,他再也没回来了。
同时在核电站的控制室中,警报就一直没有停下来,“撕拉”的声音让很多工作人员都没睡好觉,一个副总工程师也惊醒了,他听到技术人员的惊慌失措,还嚷着“爆炸了”之类的话。
他并不相信,想了一会之后,他呵斥道:“他吓傻了,赶紧带他出去!”他并不想听到这些动摇军心的言论,他坚信设计组设计的堆芯一点都不会有问题,只是在用最严厉的语气指责技术人员的粗心导致了水箱爆炸,然后一直让手下人往里面灌水。
他们都没有穿防护服。

辐射测量仪因为量程的原因,上面一直显示的3.6伦琴,这已经是最大的量程了。但核电站管理层此时都醒了,但是他们告诉手下人,辐射量只是恰好3.6伦琴罢了。他们直接忽视了自己身边人的痛苦,有人已经直接渗出了血液了,有人捂着脸痛苦的在地上打滚。
他们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
瓦西里到了,他顺手拾起了因为炸裂而破碎的石墨层,很快的,他的手直接腐烂掉了。在距离切尔诺贝利三公里外的普里皮亚季市,居民们也听到了这声巨响,然后他们看到了远方霓虹一样的烟火,他们觉得很美。

这是1986年4月26号的凌晨1点23分,爆炸已经发生,没人意识到,东欧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因为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普里皮亚季的43000名居民还是像往常一样过着自己的日子,孩子上学,大人工作,在路上甚至遇到熟人还会打个招呼。他们只是感到奇怪,自己为什么比平常困倦了好多,他们归结为可能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罢了,毕竟那声巨响,确实太响了。
而此时,无数的辐射尘埃,就这样通过空气,就这样触碰着这些这些无辜的人。

而厂长在开会商议之后,给莫斯科的报告里,只是说现场发生了火灾罢了。所以在时任能源部长马约列次的办公桌上的报告里,只是说切尔诺贝利发生了一起小事故,还觉得问题不大,不过在时任库尔恰托夫核能研究所第一副所长的列加索夫院士的据理力争下,戈尔巴乔夫还是派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谢尔比纳带领人员去切尔诺贝利进行检查和观测。
在有人冒着死亡风险的测量下。厂长的谎言自然是不攻自破,谢尔比纳所带领的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了现场领导权,开始指导反应堆清理任务,并开始根据自己现场的测量结果,做出了撤离普里皮亚季市全部市民的决定。

而此时已经是当天晚上八点了。
医院里已经人满为患,大街上的人也已经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并伴随着口吐鲜血和腐烂。从事故发生,到决定撤出全部市民,而这个过程,整整经历了18个小时37分钟。
而真正的撤离还是要等到4月27日11点。一千多辆大巴与3列火车到达普里皮亚季,普里皮亚季开始实行撤离,下午三点,才全部撤离完毕,此时已经过了38个小时了。
整整38个小时,我们既可以作为一个事外人,说处理的还算快,但是如果你是切尔诺贝利的居民,我们不妨要问一问,是不是还可以更快一点?
如果如实上报,如果高层没有派人来视察,还有很多如果,而只要有一个如果成立,这个故事的结局,都会大不一样。
我们所记得的切尔诺贝利
我们记住的,不只是上面的,我们还动容于这么几个瞬间。

像瓦西里这样的消防人员,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第一批到达切尔诺贝利的消防员中,在明知危险的情况下,还是冲上了屋顶,尽管他们知道,那里是爆炸的中心,辐射量直接就超过了2万伦琴。
切尔诺贝利空城之后的7个月里,苏联动员了足足有50万人参加了救援,他们干的是最危险的活动,负责清理那些散布了高污染高放射性的石墨的区域,他们有一个光荣的名字“清理人”,清理完毕之后,2万人死去,足足有20多万人成为了残疾人,他们的后代也因此很少有健全的。

一位士兵讲述自己的经历,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他们直接就被迫退役了。而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在高辐射环境下,从反应炉中搬石墨,有的时候甚至一次搬下来要换30只口罩。
他们感觉自己在切尔诺贝利,就感觉像全身的血被吸血鬼吸干。

空军战士们则开着直升飞机直接飞到反应炉的上方,对着辐射最强的部分,投下了沙袋,因为用水救火会污染地下水,从而影响几千万人的饮用水。有时候直升机驾驶员因为受到强烈辐射后,直接失去了意识,撞上吊塔,四名机组成员当场死亡。
最要命的是反应堆地下室的积水,高辐射的水如果遇到沙袋融化的岩浆,很容易造成二次爆炸,剩下来的三个反应堆都会成为一片废墟,但是如果要把水放掉,就要有人亲自下去,在高辐射的水中,拧开水阀。为了苏维埃,为了几千万的民众,尽管明知此行必死,还是有三名志愿者深潜入高辐射的水,打开了那个关键的水阀。
这样的悲壮英雄故事,并不是个例。
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抢险英雄群像

我们也许很难理解这样的故事,也很难相信这样的人物存在,但是他们就是发生了。真的有人会舍弃自己的家庭,从离切尔诺贝利很远的西伯利亚不远千里的过来,只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崇高的理想。
这些故事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你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伟大的人,有纯粹的人,有高喊着“为了苏维埃”奋不顾身的人。

除了伟大值得被铭记之外,我们同时也忘不了,这样一群人。他们被叫做切尔诺贝利人。
因为撤离的时候,官方还没有发布消息,为了一些愚蠢的理由。那些天真的人还以为自己可以回家。他们几乎是什么都没有带,甚至是自己的宠物。直到瑞典检测出了空气的核辐射超标,苏联政府才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个消息,很多人看到了新闻,才感觉到,自己一生可能永远都回不去了。
那些离开得居民,包括50多万参与救援的科学家,消防员,士兵,医生,平民,他们幸存之后,统一的有了一个名字“切尔诺贝利人”。他们被统一安置到了距离切尔诺贝利30公里外的 “隔离区”。

白俄罗斯作家阿列谢克耶维奇在《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中写道:
“你要知道,那不是你的丈夫了,不是你心爱的人了,而是有强烈辐射、严重辐射中毒的人。你如果没有自杀倾向,就理智一点。”
我们上文提到的消防员瓦西里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切尔诺贝利家庭”。
瓦西里去世得很痛苦,像一个随时随地渗出血液的活尸,一开始是皮肤龟裂,后来是全身流脓水,因为细胞全部死亡了,几天之内,他就掉光了所有的头发,一碰他,皮肤就会粘在别人手上。
医生就告诉他的妻子上面的一段话。

而在瓦西里痛苦地离开之后,他的妻子把他们的孩子生下来了,因为受到了强辐射,孩子出生时就有肝硬化和先天性心脏病,在4小时后,孩子也去世了。
这就是“切尔诺贝利人的家庭”,他们之中有参加救援行动的英雄,有的战士甚至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役,勋章挂满了衣服,也有一个个年轻的生命,他们有自己的爱人,然而在切尔诺贝利之后,往往只能注定孤独到老,没有人敢和他们结婚,有的战士,甚至被家人拒之门外。
切尔诺贝利,改变了太多。
结语:
至今为止,我们还见过天生血癌的女孩,只是因为她的父亲是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英雄,还有无数像这样的小孩子每年出生在东欧地区,他们的父辈祖辈,或多或少都和切尔诺贝利发生过接触。这无疑是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魔幻情节。
切尔诺贝利辐射所改变的基因,可能要很久才能消除。
而我们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就是无法得到任何教训。
我们不知道之后那些英雄是不是得到了自己应有的那一份补偿,我们也不清楚核电站的责任人是否被追责,我们更不清楚那些瞒报的官员有没有得到处理。

最后还是想对那个厂长说一句,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用谎言去代替正义,真相,那么对任何人都是灾难,说谎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博弈。谎言的代价并不是我们会把谎言误认为真理,谎言真正危险地方在于,我们听多了谎言,便很难分辨出真理了。我们会沉醉于我的幻梦多美丽的枷锁里,很难听得见那些不是很动听的真话了。
索尔仁尼琴说过,一句真话的分量比整个世界还要重,而中国的一位很厉害的医生,也在他去世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一个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让更多的人被听见,这是我们阻止灾难应该做的。
文/枕猫

《天涯连线》往期热帖

深度阅读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天涯连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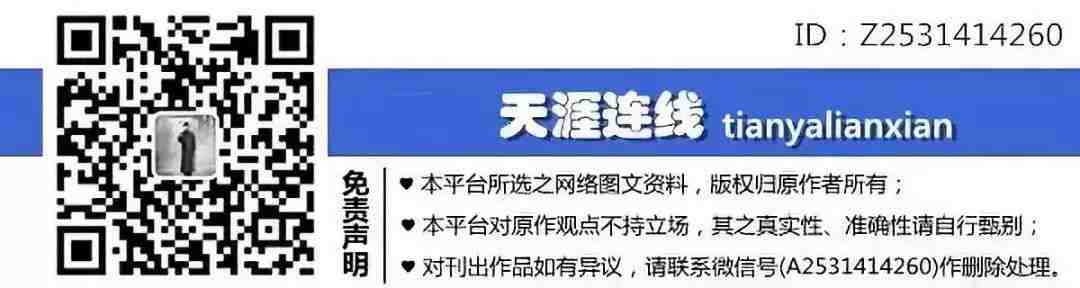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