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重现时,你会看到自然最精妙的魔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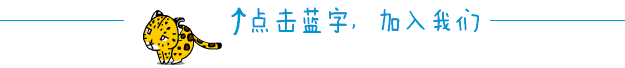

“修复荒野,带豹回家”这八个字翻译成英文是“Rewilding Taihang Mountains for homing leopards”。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动词,rewilding到底是啥?
在TED演讲上,乔治·蒙比尔特(George Monbiot)做过一段动人的讲述。我们就以此作为开端,说说修复荒野以及Rewilding的这些事儿。
首先,这哥们儿是谁?

乔治·蒙比尔特:畅销书作家、环境记者。现任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城市规划客座教授,1995年他获得尼尔森•曼德拉颁发的联合国全球 500名环境贡献杰出人士奖。
他的座右铭是:“我对人类的爱并不少,只是对自然的爱更多。”他自嘲:“我的工作就是跟别人说些他们不爱听的话。”(其实并没有)

稍微年轻一点的乔治,图片来源:thegardian
翻译:吴越,秦卓敏,范明睿
我年轻时,曾做过热带地区的调查记者,那是在世间最迷人的几片土地上,一场为期六年的荒野探险。当时的我还挟着青年人特有的愚鲁,是那种历来让战争一触即发的青年人的莽撞。然而自那以后,我身上便再不曾感到彼时的健旺活力。及至回到家乡,我看着自己的存在图景日渐黯淡,到后来往洗碗机里塞上几个碗就简直算得上有所作为了。我感到自己似乎一下下挠在生活的坚壁上,似乎挣扎着要从墙里逃出来,逃入墙外广阔的空间去。我想,我对于这一切诚然是做不到生态适应了。
相比起直面獠牙利爪的世界,我们如今在更加危机四伏的时代中逡巡向前。当然,远古的恐惧和胆魄还在,当年让我们得以幸存的必要攻击性也还在。但身处这样一个舒适安全又颇拥挤的家园,想要继续锻炼上述本能而又不去伤害别的什么人,根本没有机会。这正是我冲不破的那道藩篱。各个工业化社会的主导性目标几乎都是要克服不确定性,预测短期的未来;如若业已达标,亦或是胜利在望,我们就要面临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新需求。人们重视安全甚于体验,这种倾向的确让我们受益良多,但我觉得,也让我们付出了代价。
我并不打算透过玫瑰色镜片去看演化的漫长历史。我的年岁已经长过大多数狩猎或采集部落成员的一生,而如果是我挥舞着石镞长矛四处游荡,与一群被激怒的野牛狭路相逢并来个殊死搏斗,胜算也可想而知。演化的真实性也不是我所追寻的,我觉得那没什么实际意义,甚至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被阐明的概念。我不过是想要一种更加丰富和自然的生活,这种生活在大不列颠无以为继,或者说几乎在整个工业化世界中都无以为继。
所追寻的目标开始明朗起来,源于我偶然间瞥见的一个新词。就在这个词进入我视野的那一刻,我便知道我的余生将围绕它展开。

乔治在TED演讲现场。
这个词是“修复荒野”。虽然“修复荒野”是个很晚近的概念,它也已经有了好几个定义,其中有两个特别让我动容。先说其一,大规模修复生态系统。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最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之一就是广泛的营养级联。营养级联是个生态过程,从食物链顶端出发,由上自下传达至底。
这方面的一个经典实践案例是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在1995年对狼群的重引入。我们都知道狼会猎杀多种动物,但或许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狼也为很多其他物种带来生存的机会。这听起来有点奇怪,没关系,请继续听我讲。此次东山再起之前,狼群在黄石已经缺席了七十年,在此期间这里的鹿群没有了天敌,鹿丁一再兴旺,即使人们有意地控制种群,它们还是风卷残云,让公园里的植被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然而狼群甫一到位,虽然数量还不占优势,还是立即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当然啦,它们捕食了一部分鹿,但这并不是主要的影响,更为意义深远的是,它们使鹿的行为方式剧烈改变了。

被重新引入的狼。图片来源:daryl-hunter.net

黄石国家公园的鹿,照片来自网络
鹿群开始有意避开容易遭到伏击的特定区域,比如河谷和峡谷,于是这些地方很快重新萌发了生机。某些地带的树木高度在区区六年中增长了四倍,光秃秃的河谷两侧密布起白杨、垂柳、三角叶杨的树林,而随着这一切的发生,鸟儿也开始入主森林,鸣禽和候鸟的数量显著增加了。有树木提供佳肴,河狸的家族也繁盛起来。和狼一样,河狸也是生态系统的工程师,为其他物种创造出新的生态位,而河狸在河流中筑起的堤坝无论对于水獭、麝鼠、野鸭、鱼群还是两栖爬行类动物来说都是良好的栖息地。

构筑新生态位的“工程师”河狸也开心了。图片来自网络
狼群还消灭了一些郊狼,兔子和鼠类的数量随之抬头,而这又意味着更多的猛禽、更多的鼬、更多的狐狸、更多的獾子。乌鸦和白头海雕落在狼群吃剩的尸体上大快朵颐,熊也会捡腐肉果腹。当然,熊口增长的另一部分原因还有繁茂灌丛中兴盛起来的野莓;它们不时还会猎食幼鹿,这又进一步巩固了狼群的战果。

熊口也在默默地增加。图片来源于网络
事态的发展越发有趣——狼群竟也改变了河流的“行为”:河湾的曲折减少了,河岸的侵蚀弱化了,河道变窄了,沿河形成更多水潭和浅滩...... 所有这些变化对于动植物栖息地来说都棒极了。河流用变化对狼群活动做出了响应,究其原因,则是重生的森林加固了河的堤岸,河岸不再像以往一般频繁崩塌,于是河流走势也就稳定下来。同样地,将鹿群驱离使得河谷两侧植被复生,根系固化了土壤,这里的水土流失也减少了。总的来说,狼群并不庞大,但它们在幅员辽阔的黄石国家公园中却不仅改变了生态系统,还改造了地理形态。

狼的重引入启动了黄石国家公园荒野修复的自然程序。图片来自网络
南大洋的鲸群也同样有着广泛的影响。为了给捕鲸产业擦屁股,日本政府找过这样的借口:“(捕了鲸)海里的鱼虾数量会增多,更多老百姓就有得吃了嘛。”这借口够蠢,但听起来又有那么一点道理,不是么?因为你会觉得,鲸既然要食用巨量鱼虾,那么把它们除掉,鱼虾显然就能更多地为人类节省下来。然而这却适得其反。海洋中的鲸群被削减了,磷虾的数量反而暴跌。为什么会这样?
研究表明,鲸群对于维持整个海洋生态系统至关重要,部分原因是,鲸类常常潜入深海觅食,其后又浮上海面排泄,释放出大量被生物学家文雅地措辞为“羽状排泄物”的粪便。这些喷薄而出的巨量粪便划过海洋表层,冲入海水的透光带。这一区域的浮游植物得到来自深海的肥沃养料的洗礼,同时这里的光照也足以支持它们的光合作用,处于食物链底端的浮游植物由此增殖,又促进了其它浮游生物的生长,并进一步供养起鱼类、磷虾和其他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生态网络。
鲸类起到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藉由牠们在海面与深海间的自由穿梭将浮游植物带回海洋表层,让它们得以繁衍生息。另外,我们都知道海洋中的浮游植物会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海洋表层生长着越多浮游植物,它们就会吸收越多的二氧化碳——它们终将携着这些碳元素离开大气,经过食物链的层层渗透沉入深渊之中。这样说来,另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在鲸类曾经兴盛的时代,它们每年曾以独特的方式将数以千万吨计的温室气体从大气层中分离开来。

除了和食物间建立的平衡关系,鲸鱼这种海中巨兽还在改变大气的构成,这便是我们极难想象的生态平衡的微妙所在。图片来源:look.huanqiu.com
如果用这样的视角观察世界,你就会思考:等一下,既然我们前有狼群改造了黄石国家公园的地理环境,后有鲸群改变着大气层的分子组成,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生态层面上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詹姆斯•勒夫洛克所提出的盖亚假说——世界就是一个浑然一体的、能够自我调节的有机体?
营养级联理论告诉我们,自然界甚至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和精彩,这个理论告诉我们如果将大型动物剥离,留下的生态系统将会与先前截然不同。在我看来,要支持对缺失物种进行再引入,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对我来说,“修复荒野”意味着将一些失落的动植物种带回原位,意味着拆下樊篱,意味着封住排水沟渠,意味着在某些大范围海域杜绝商业捕捞,而如果不采取这些行动,就等于在错误的路上渐行渐远。“修复荒野”并不纠结于什么是“正确的生态系统”,亦或是“正确的物种间共生关系是什么样的”。“修复荒野”不是去打造一片原野、一片草场、一片雨林、一个海藻牧场,或一片珊瑚礁,而是将决策权交还给自然——而自然往往精于此道。

将决策权交给自然。图片:四川林业&猫盟
我先前提到过,关于“修复荒野”的概念有两个定义引我入胜,剩下的一个,是修复人类生活的荒野。我并不认为这与社会的文明进程相悖,我相信人们可以一如既往地享受先进技术带来的便利,但与此同时,只要我们愿意,就有机会去探索一个更丰富、更有野性的生活,因为我们将拥有已被修复的、美好的生态栖所。
这样的机会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飞快增长着。据估测,美国有三分之二曾遭开垦的林地如今已随着农夫和伐木工人的撤离而再次被覆生机,在这个国家的东部尤为显见。而在欧洲,另一项估测表明,有三千万英亩的土地会在2000年至2030年间退耕还林,这个规模相当于波兰的国土面积。
面对着这样的机遇,如果“物种回归计划”还囿于狼、猞猁、熊、河狸、野牛、驼鹿这些已经开始在欧洲快速扩散的物种,是不是显得太小家子气了?或许我们也该开始考虑迎回那些失落已久的巨兽了。
巨兽,你指的什么?这么说吧,除了南极洲以外,每一个大陆都有过巨兽。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开工动土的伊始,在河床沙砾中发现过河马、犀牛、象、鬣狗和狮子的骸骨。是的,诸位,远在纳尔逊纪念碑修建之前,特拉法尔加广场上曾有狮群漫步。上述物种全都曾在间冰期栖居于此,那时的气候和我们如今的家园十分相近。这个世上巨型物种的失佚大体上不能问责于天,而该引咎于人。正是人类的狩猎行为和垦荒工程让它们走入绝境。
即便如此,你依然可以在现今的生态系统中看到这些巨兽投下的影迹。为什么大多数落叶树木能够在任何枝干折断的伤口处萌发新芽?为什么它们可以安然承受那么多树皮的剥落?为什么林下叶层的树木虽然承受的重力与风力摧折明显弱于冠层乔木,却长得远比后者更加坚硬,更难以折断?大象就是答案。它们适应的是大象的撼动。比方说,亚洲象的远亲——长着直通通獠牙的古棱齿象曾游荡于欧洲内陆,它们是温带动物,温带森林中的生物,体型远比亚洲象还要庞大。适应古棱齿象的存在正是欧洲树木的演化动力之一。再举一例,为什么有一些常见灌木只消抵御鹿的啃食,却生出了牛刀杀鸡式的棘刺?或许在演化之初,它们需要抵挡的是犀牛的攻势。
想想看,无论是漫步于公园里还是穿行在林荫道间,我们都能看到这些巨兽遗留的印痕。不觉得很美妙么?古生态学,这门着眼于旧时生态系统的学问,对我们理解当今的生态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就像一个入口,引你进入一个奇幻的王国。审视那些即将拥抱荒野的土地,如果它们当真能达到我所描绘的规模,为什么不考虑重新引入那些一度绝迹的巨兽,或至少是与那些业已绝灭的物种有密切亲缘的动物?为什么不能在我们的庭前拥抱自己的塞伦盖蒂草原?

乔治·夏勒的家人在塞伦盖蒂草原,与一只被救助的小非洲狮在一起。图片来源:网络
或许这就是“修复荒野”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东西,我们生活中丧失了的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一点希望便能激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和维护,这就足以抵消掉几万倍的绝望。“修复荒野”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态变迁之路并非不可回头的独木桥。它带给我们这样的希望——我们寂静的春天会被一个喧闹的夏天所取代。
谢谢。
PS:
关于Rewilding的翻译,我们和大牛讨论了许多次,是更学术严谨的“再野化”还是修复荒野?见仁见智,然而本质却是一样。
因为生态系统精微的平衡,巨兽的消失与环境恶化互为因果。带豹回家,豹不是唯一的目标,而它所影响的太行山、完整的食物链才是。因此,我们不会天(nao)真(can)地把豹子直接空投进京,而是让荒野重现,努力修复一个生机勃勃的动物王国。
这是雾霾、沙尘暴之中一盎司的希望,是喧闹的夏天,大自然喜欢的大自然。
以上。
欢迎扫码了解支持带豹回家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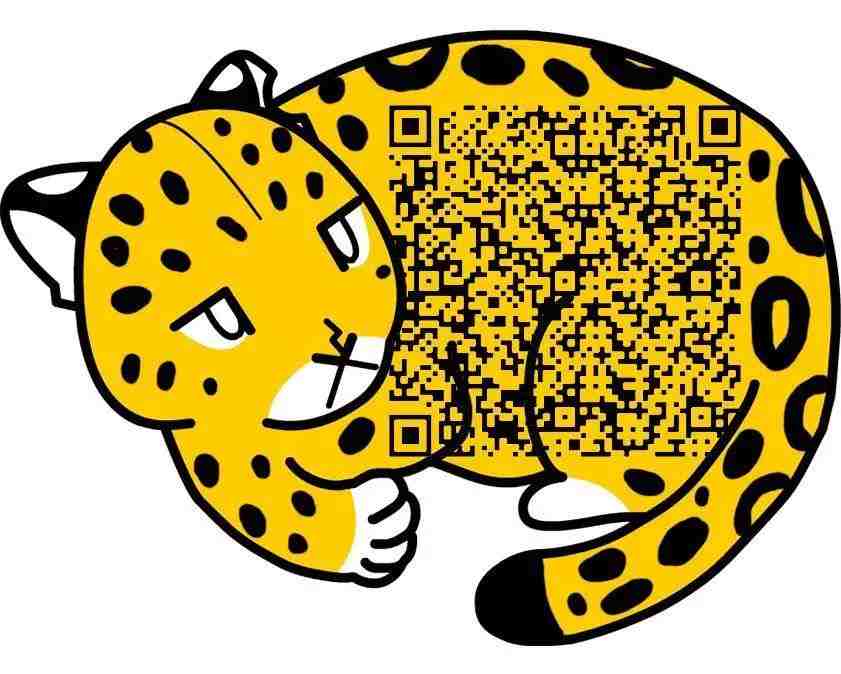
我们一起,修复荒野和人心


川西荒野中的金钱豹。图片:四川林业、新龙环林局&猫盟
阅读原文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