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不知家乡历史的八零后,却都能细数家乡美食|大家



6月去了趟陕北,走了榆林、延安、绥德、米脂、吴堡、佳县,同样这些地方,在1999年的秋天都曾经来过。20年过去,山川沟壑没变,绿色多了些,国道210陕北路段来来往往满是大货车,不同的是,这次见到的是另外的人。

一、前货车司机
从延安去绥德这一路,记忆里是幽静的山路,现在大货车一辆接一辆,源源不断的掀起尘土,没节制地按喇叭。由北向南的,是从神木出来的运煤车。由南向北是往神木方向拉石子的车。
陕北的地下究竟藏了多少煤,看迎面从神木来的车阵,也许可以造一条超级传送带了。
榆林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我们榆林现在是资源地区,GDP全省排第二,仅次于西安,都超过宝鸡了,我们地下有煤有石油有天然气,这些可都是钱。

傍晚在吴堡县城黄河边遇见他,大个子,瘦而结实。他说他是开货车的,从神木拉煤到山西吕梁,再拉上石子到神木,两个人倒班开车,一天一来回。
今天没出车?
现在不干了,辛苦,但是开车挣得多,一个月一万五。
那怎么不再干了?
这不是好喝两口吗,不安全,不干了。
今天喝了吗?
刚喝了半斤,一会回去还得喝点。
能喝多少?
三斤吧。
陕北的黄米酒挺好,还有西凤酒。
喝不起呀,太贵,西凤也贵,一瓶20多,我喝散酒,8块一斤。
不开车了,还干点别的?
在小区扫街,挣得少,一个月1000。
他始终笑眯眯的,虽然喝了半斤,走路很沉稳,跟没喝一样。不过不能再开大车,让他露出明显的不舍得。这位前大货车司机,1966年出生,今年53岁。
8点多了,西部的天还没全黑,头顶上有几片长的火烧云,不远处是一座黄河桥,一侧在陕西,另一侧在山西。桥上货车不断,可能是桥架得格外高,一点声响也听不见,好像移动的积木块,好像脱离了人世间。
和他一起向亮了路灯的河堤走,偶尔抬头看一眼远处黄河桥上的车流。

二、坐在墙根的女人们
我们的车下高速,拐进一个叫乔沟湾的小镇。它紧挨着包茂高速公路,街道空空,没人没车,非常非常寂静,很像西部片中某个暗藏无数诡秘的角落。每隔十几分钟会有载重的油罐车从一条斜的小路上速度极快地往下冲,掀起的尘土要落几分钟。
路边有间孤立的小饭店,门帘在风里卷着底边,几个世纪都没人进出的样子。
饭店背后拴了条肮脏的小狗。一大块空地,再远一点是高的黄土坡,土质紧密细腻。空地边上有一堆大煤块和一把看来是专用砸煤的斧头,乔家湾这地方好像就这么多了。
忽然发现路对面一排平房前有四五个人,挨着墙坐成一排,都是老太太,一动不动,正盯着我们这边。平房前有个四角高翘的露天摊,高台子上面睡着一男一女,应该是弹棉花的。走近才发觉,本以为在睡觉的女人正眯着眼和我对视。
老太太中间有人说话了,是个穿花衣服的,她比另外几个显得精神也衣着鲜艳:你们是旅游的,咋没去看主席旧居?不远。
我们说这一带旧居好像不止一个。
花衣服说:那时,一个沟一个沟的跑吗。
又说:你们是想看看煤呀?
可能从我们的车一进镇,一直被他们注意着。

当地现在的煤价是500元一吨,小饭店后空地上的那堆不到两吨,价值900元。
花衣服指着对面小饭店说那就是她家,又说上个月她一家人刚去北京旅游,从榆林坐飞机去的,坐火车回来的,北京坐到延安。
说到北京榆林延安,明显带着炫耀,而她身旁不出声的老太太们没任何反应,始终用迷茫的眼神望着空空的马路。这个下午连风都没有,除了细到看不见的土末在飘落,让这小镇连土墙上的裂缝都是干黄干黄。
上网查了乔沟湾,这地方的地下蕴藏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天然气已经进入开采利用阶段。主要农作物有玉米、洋芋、荞麦和土葱。

三、除草的和卖杏的
他有60多岁,正在清涧县的路遥纪念馆外一块狭长的花圃里除草。一看就是从小在地里做的,干活一点不累。
这天是周末,附近有人在下河抓鱼,有人在下钓竿。太阳一露出来,天气有点热,他拖着锄头离开花圃。
问他除一天草能拿到多少钱?
他说不按天,在景区按月领钱,一个月能拿1200元。
他指了指对面山上说,家里有老婆,半身不遂,得有人管着,不能去远处干活。不是他提醒,很难注意到对面黄土梁上面还有人家,果然,山坡顶有人露半截头,正朝下面望着呢。
他家在山上种了三亩苹果:瞅不见的,在山后,到秋天,苹果熟了,有大车从外面来收。说这些时,他有点心急,总抬头看景区中心那排房子。
看他走远,腿上是有残疾的,微微的瘸,他快走过去,直接把头探进一只大垃圾箱,翻出一只塑料瓶,夹在胳膊下。

一辆农用车下山坡,经过景区停车场前,被钓鱼的人给喊住。
开车的老头下来,灰白头发,灰眉毛,面善,木讷,爱笑。周围玩的人过来围住他的车,揭开蒙被,露出几筐很新鲜的杏子。两个品种,软的是黄杏,硬的是红杏。大家都想买杏子,可他既没有秤,也没有装杏的袋子。
有人去自己车里拿出塑料袋,大家装好杏,凭他钩子一样的手提一下,估个重量,说个数,就拿钱给他,还都说不找零了。
他不说什么,只是笑眯眯的接钱,好像一切都本该这样。
又有刚路过的人围上来,他忽然急了,说要赶路,给杏子蒙上被,开起车就跑。
难道他摘了这一车杏子不是想卖了换钱?

四、看寺庙的老白
出绥德县的义合镇,过满堂川,往三十里铺方向路边搭有戏台子,唱戏的是附近佳县古城晋剧团。听说已经唱了两天,我们经过的这天是三天大戏的最后一天。
隔着公路有个小杂货店,屋里六七个上年纪的男人齐刷刷坐着,像刚散了牌局,只等着对面唱戏。老白就在他们中间起身说,带你们看看山上的小庙。原来他就是守庙人。
抬头能看见那庙,几乎是垂直的陡立在坡上面,路陡峭,在陕北,好像很多这种折叠向上的便道。他说你们慢走,他是每天无数次上下,脚步飞快。
居高临下看戏台子稳稳窝在山坳里。他说原来村里想搭个临时戏台,后来才决定建个长久的。
下面已经在放流行音乐,有老人夹着板凳过来。
三天庙会,要筹八万块。唱戏三天剧团拿三万五。老白说:贵。村上每人交30,现在钱还没全收上来。
小庙新修复的,神像彩绘都过于鲜艳。不知道供的什么神明,最中间的那个披红布,赤脚,手捧八卦图,侧旁一个脚上穿鞋手持长剑的侍卫,面目如生,简直就像拍电影的山西人贾樟柯刚钻到这位置刚站下。

庙的院子不大,周边地上丢着鸡或鸭的小骨头,发出难闻味道。
老白说他年轻时候很能唱,能蹲在这个山上往对面那个山上唱。说着张口就唱了一段“兰花花”,嗓音高亢,已经不很像唱歌,像搏命像撕扯。他会的曲儿多,但是老忘词,老感叹自己老了。
他建议我们去附近的大庙,说那地方要开发旅游了:那地方好!
怎么好?
平。
就凭这一个平字,就是好地方了?
一起下坡,老白要去戏台子帮忙。
最后一天的戏,中午11点开始唱两出:《王莽篡位》、《宫门挂袍》。晚上8点最后一场唱一出:《双官诰》。
戏班子不少人,都画好了脸,穿了袍子,在后台的屋子里等待,那儿地上还铺了条挺新的红地毡。戏台子背后是剧团的露天厨房,盆盆碗碗都敞着,切菜吃饭的痕迹都在,只有苍蝇飞,两个炉灶各个头上一缕淡淡的烟。
而老白正跟几个人一起用力拉一幅大布,给看戏的人们遮阳。非常巨大的布,是平时苫菜棚的那种黑塑胶布。风刮得尘土四起,大布一角耷下来兜住他的头,整个人灰头土脸的,完全没有唱小曲时的豁亮。

五、香炉寺守门人
佳县县城建在绝壁上,特别狭促。这个县最出名的是两个寺庙,一个白云观,一个香炉寺。
香炉寺的一部分建在一块孤立的石头上。
20年前,我来这儿见到的守庙人叫李树旺,60多,做这个十几年了,问他堂上供的什么神,他说十几个呢,都记在小本本上了。然后这个老汉拿他的小本子比做土地,一根圆珠笔比做革命事业,他特别有底气地说:革命设立在佳县。
理由是佳县当年给革命做过大贡献:1947年秋天,正和胡宗南队伍周旋作战的红军陷入极度缺粮,毛泽东找到佳县县委书记,书记动员佳县老百姓收割没成熟的青玉米青谷子,杀驴杀羊,支援部队开战三天。事后毛泽东给佳县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
现在,刻有这个题词的碑还立在县城。前后20年,小县城里几乎什么都变了,这石碑还在。

有点期待这次上香炉寺,也能遇上李树旺老汉一样能说会道的。
上午的香炉寺没游人,门口一张躺椅,看门人斜靠在上面看手机。
一人20,他一动没动,没抬眼皮。即使接钱,也没起身,眼睛还在手机上。
他脚边一只拴在鸟笼架上的八哥倒是蹦跳得欢。交了钱就可以进去了,好像也没有门票的。
香炉寺低矮可爱,神像也都质朴低调,从这里直直地往下,能看黄河就在下面缓缓地流。
出来时候,那人还躺在躺椅上。忽然手里电话响了,他被迫起身,半撩起上衣,卷在胸口,到边上去听电话。
那只八哥很热情,隔十几秒钟就喊一声:你好。又喊:多多关照。反反复复就这两句,声音有点哑。
讲完电话,那人又躺回去,懒得理周围这一切的样子。
不知道教八哥学说话的人是不是他。

六、三皇原则村的白家
这个名字有点怪诞的村子在吴堡到义合镇之间。在大货车不断的陕北公路上能看到的村庄不多,更没见过田地,满眼都是山坡山坳。
沿着小路往山里走,仔细看那些山梁上,其实零星的建有房子。每一户人家都孤零零,像是勉强才在山壁上找到块落脚地,大家都没邻居,一户户都在独自面壁。
先听到说话声,才见远处坡底有人,还有一辆小型货车。走近了见一个小伙子正在戴白手套,准备从车上往下卸石子。
他叫白富平,他家就在几十米外的坡上,家里有母亲和两个哥哥。
问他可以去做客吗?
他赶紧说可以。
白富平的母亲和他二哥在家,他们的房子所在的山坡平台不小,看来曾经花不少力气,才有了平整敞亮干净的院子。
20年前来陕北那次,当地正盛传就要不种粮改种树种草了。对这说法,世代务农的人们将信将疑的,见人就说:“今后真不种粮了?听说粮食统一从外面调,中央说我们陕北人以后的任务就是种好树,保护好黄河。”讲这话的已经不只是乡村干部,连牵驴磨面摆摊卖枣的都知道了。
这些年确实在种树,种下的多是枣树,树都不高,一路都没见过大树,但绝壁沟壑间有绿色了。即使离开高速公路和国道,沿小路向山里走二十公里,也常见山坡被低矮植物遮盖,不过,不同地方的百姓都说管不住那些放羊的,羊把山上的树苗啃得厉害。
现在,白富平家有30多亩山地,地块零碎,都不连着。他二哥带我们上到他家的房顶,往远处指一下说地在那边。不知道指的是哪儿,不知道有多远。他说,十几年都不种粮食了,枣太多,不好卖,不值钱。
问起当年盛传农民能得到“不种粮补贴”,白富平二哥说,原来一亩地每年补贴90块,现在调整成40—50块,不够买口粮的,可粮食这些年都在涨价。他指给我们看山坳里的小块地,大概20几棵玉米苗,是农民自己开荒种上的,这块不是他家的。
在这个家里见到三个女人。

白富平母亲,1954年出生,属马,老头已经去世,家里墙壁上贴一份贫困户表格,老头的名字还在表格中。她身体结实,嗓音豁亮,我们进院时见她正搭个架子。她有三个儿子,都曾经去外面打工,现在都回来在家附近干活,主要是拉石子。
白富平二嫂给婆婆做帮手,她戴眼镜,有点斯文,像个小学老师,她在县里加油站上班。因为孩子在县城读书,所以,她平时住县城。
另外有个姑娘可能是白富平妹妹,笑眯眯手里捧着三个鸡蛋到处给人看,说刚从鸡窝里摸的。真正的农家土鸡蛋,在村子里也要两块五一个。
三皇原则村有200户人家,家家都不相连,各自在山坡上寻位置。
细看白家的日常用水是个巧妙的微型生态工程:屋顶和院子抹得特别平整,下雨天可以集结雨水,分别流入专门的储水窖。屋顶收集干净的雨水,做全家的饮用水,院子里的雨水进入下一级水窖,浇周围的菜地。随着房屋周围的山势开辟的菜地,上上下下,好多小块,辣椒黄瓜西红柿都结了水灵灵的果实。
靠屋顶雨水,够你们全家吃吗?
老太太连着说够用。
白家的饮用水水龙头装在屋子里,龙头下面直接铺木板,没有洗脸池,可见每一滴落下的水都会被再收集利用。
这些山崖上的人家,只有走近细看,才可能发现其中的智慧,味道和乐趣,而那些苦事难事,不会轻易对外人透露。

七、在黄河滩里种菜
黄河流到陕西和山西,成了这两个省的自然分割线。
20年前,陕西人告诉我,看迎面来人是陕西的还是山西的,要看包着头的羊肚子手巾(白毛巾),扎在前额的是陕西的,扎在后脑勺是山西的。这次在陕北走了十天,这种古老的装扮几乎绝迹,只有一次见到个毛巾扎在前额的老汉,坐在佳县县城电影院门前的水泥台阶上。
陕西沿黄河一侧多峭壁,现在修了一条800公里长的沿黄观光公路,路两侧一面是河一面是山。但是,这次遇到了一大段封路,因为峭壁落石,正在赶工加固加网。
黄河在吴堡县城这里修筑了很高的河堤。傍晚的黄河滩里,有两个年轻人蹲在水边发呆。问他们发现了什么新奇,他们有点不好意思,起身说在学习“放空自己”。

河滩上遇见的第三个人正弯腰拔草,是个女人,50上下。
如果不是她指点,不容易看出稀稀拉拉种在河滩上的是蔬菜:生菜、香菜、豆角、葫芦瓜、小白菜,东一棵西一棵,实在是种得太随意了。
她说,都是种的,人家不让,大铲车给推了一些,就剩下这点,推的时候都长得不小了。河滩上确实有履带车留下的急转弯印记。
她指着远处的河滩说:前面文化广场那边也能下河滩,那边种菜的比这边多,那边也不让种,铲车也去推。尽管这样,她还是每天晚上都来伺候她的菜。说话的时候,她手里始终攥着两棵刚摘下来的豆角,一只手浇水拔草,另一只手握着豆角,像握住珍宝。
问她还上班吗?
她摇头。
没有再问,也许她从乡下搬进吴堡县城没多久。早20年或者30年,不是人人都有资格进城工作,农业人口不能自由迁移,只能留在乡下种田。再早些年,人们的饥饿记忆顽固而清晰,见到土地就想播种,就想种植和收获。
太阳快下去,她拿上一个铲子和一个喷水壶,一边往岸上走,一边说如果黄河发大水,滩里这些全都能淹了。
你的菜也都泡在水里了?
是,水来了,就都跟着水跑了。
听她说得那么轻松,同样是毁掉她的菜,好像很气愤铲车,却很能容忍黄河涨水。

八、河水和菜价
那天离开绥德县义合镇的集市,经过一座简易桥,桥边两个老头在歇脚,地上放着他们刚买的菜。
桥下的河道完全是干的,只有淤泥和垃圾。
一个老头说:合作社时候,这条河的水还能喝,现在,你看看。
另一个说:合作社以后就不行了。
这一路上,在绥德和米脂两个县城都见到河,几乎都是干的,河底变成垃圾堆积场。

他们生着和南方人不同的狭长的脸,额头是刀刻似的皱纹。记得20年前,这个年纪的老头都戴一副大框黑镜片的水晶眼镜,说是保护视力,现在没见人戴了。
从河水说到菜价。
高个子老头说,土豆平时在镇上卖两块钱一斤,今天是集,他刚买的便宜,一斤一块。
就在第二天我在米脂遇上集市,专门去问了,土豆一斤只要九毛。可见如果不是自己种菜,在陕北乡下生活要比在县城消费高,除非少吃菜。
米脂县城的集市上,猪肉一斤13到14块。羊肉一斤35块,整只羊大约1200块。临街的羊肉摊位上明晃晃摆开几只刚割的羊头,每颗羊头的长相和神态都不同,个个栩栩如生的,只是眼睛都闭着,没见有睁眼的。

两老头说现在粮食也贵呀。义和镇的集市上,高粱米十块三斤。小米五块五,陈小米五块,绿豆六块。
从菜贵说到粮食贵,两个人摇头叹气一阵后问:你们是干啥的,检查环保的?

九、看守天主堂的老刘
从吴堡走沿黄公路向佳县方向,接近佳县县城时候,会有指示牌提示说这里有个谭家坪教堂。网上能查到:谭家坪村的天主堂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由西班牙籍聂长春、魏向阙、乐因神父督建,如果想了解更多,也能从只言片语的概述中得知它后来的一些境遇。
我们走过了,重新又兜回去找。
谭家坪村仅靠沿黄公路,好像空无一人,安静得像被人忘了,一点声响没有,一块能移动的物件也没有。贴着路就是黄河,垃圾顺着陡峭的斜面拖拖拉拉垂进水里。
猛然抬头,黄土坡的高处,灰的,一对直立的双尖顶,一定就是它,暗暗的灰配着山坡的黄,搭配得有点和谐,也有点神奇。
教堂建在平坦的高坡顶上,庭院的铁栅门开着,正对着院门的是一块不高大的石碑,好像临时立在那儿的,却有一个遮雨棚。石碑上面刻有跟这座教堂的历史,有前面说的三个神父的名字和建造教堂的简要经过。

从窗口见到窗帘,是有人常住的。院子不是很大,非常整洁,几棵对称生长的大树。
教堂里面有个白衣人低头祈祷的背影,门上有小纸条,留有一行电话和人名。
可能是听到声音,白衣人走出来。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个子不高,走路缓慢,身体有点虚弱。
他说神父这两天回家了,留他一个人守教堂,门上就是他的名字和电话,他姓刘,父辈就信教了。
他颤颤地带我们上到教堂的顶层,从高处看见了更低更远的黄河像一条亮黄的长布带。河面上除了水的波纹,别的什么也没有。老照片里的黄河才有帆船,有羊皮筏,记得萧红写过的山西风陵渡。
他指给我们看他的家,低处一排五六间房子,只在房屋表面那层贴白色瓷砖,俗称“砖挂面”。
一百多年前,在陕北佳县这么偏僻的地方建一座居高临下看黄河的教堂,多不容易。听我这么说,他苍老的眼睛里一下子满是眼泪,但是没流下来,水汪汪,就那么打转。

问当年建教堂时,叫聂长春的神父是怎么死的。
他说,是伤寒,人就埋在教堂大殿中心的地下。他一直带我们走到那位置,指了指脚下的地砖。
停留了一个多小时,他流眼泪好几次,不断从旧的白衬衫胸前口袋抽出一块灰色手绢擦眼睛。身上带着手绢的人,好多年没见这样老派的人了。
他1945年生人,今年74岁,读到小学四年级后辍学。有四个孩子都大了,都在外地打工,他的白房子里现在只有老伴。说到老伴,他连说了几次,要我们“上家吃饭”。

十、绥德吕布
从延安去绥德,临近县城了,按导航的指引离开国道,顿时逃离了大货车,走上一条新修的盘山小路,弯多路窄但是像误入世外桃源,全程没见一辆车一个人。车走了半小时,前方闪出几座古式建筑,有牌楼,有小庙,有石狮,没想到直接走进了南宋名将韩世忠故里。眼前的建筑有新有旧,参差不齐,最早的是清道光年间,也有明显是后建的。无论新旧建筑,都和它背后的山色一样黄,黄土高原上特有的灰头土脸。
路边停了两辆车,七八个大人孩子围着景区的石桌正聚餐,小孩子手里举着烤鸡翅在跑。我们问路,顺便也问他们知不知道谁是韩世忠。
几个大人们都笑了,摇头。他们是带刚考完试的孩子们来过周末的,随后自嘲是一群没文化的八零后。有人说孩子们可能知道,叫过一个女孩,女孩说韩世忠,好像是个英雄吧?
离开前,随口问了句绥德有什么好吃的。
这下子,所有人都来了热情,大人孩子都在嚷嚷,每个人都能报出一串菜名。
最热心的小伙子很怕我们错过绥德的美食,坚持找纸找笔,要给我们列一份清单,列出从这天晚上到第二天的三餐,每餐吃什么,在哪家吃,哪些是必点菜。
纸笔来了,他有点不好意思,原来提笔忘字。换了另一个来写,也是写不了几个字就卡壳,最后还是喊来猜韩世忠的小姑娘,她端端正正坐下写菜名。
热心找纸笔的小伙子长得有点英俊,穿红衣服,我们就叫他绥德吕布。

当地的民间传说里,把吕布和貂蝉都说成是绥德本地人,虽然东汉人吕布据说生于五原郡九原县,就是现在的包头,而貂蝉是个虚构人物。
热火朝天介绍美食时,他们中间有个没说话,始终靠后站的女人,30多岁。他们说她吗,她不是绥德的,贵州那边嫁过来的。
一下山很快进了县城。
没想到绥德这个小地方这么热闹,聚拢了这么多人。天黑以后,中心城区的霓虹灯都亮起来,完全不理会信号灯的人在多车的街上来回穿过,到处都有人在吃东西。
拿出吕布他们热心推荐的菜谱,郑重点菜,每道菜上来都凑近了细看,哎呀,绥德美食,好多就是变着花样做熟了的土豆。
第二天一早,接到吕布的电话,很快他跑来酒店,提着一袋刚从朋友家地里摘的甜瓜,说让我们尝鲜,还说这种瓜在当地叫芝麻瓜,匆忙放下袋子就骑摩托车走了,吕布在绥德城里是开修车行的。
这是偶然遇上了一群多喜爱自己家乡的人,虽然年轻,身上却带点超越常态的古老农耕文明的遗存,热情和义气。

大家一周阅读排行榜
3.刘远举 | 80后指望以房养老,是在刻舟求剑
5.孙佳山丨《哪吒》成爆款,在今日中国是正常还是反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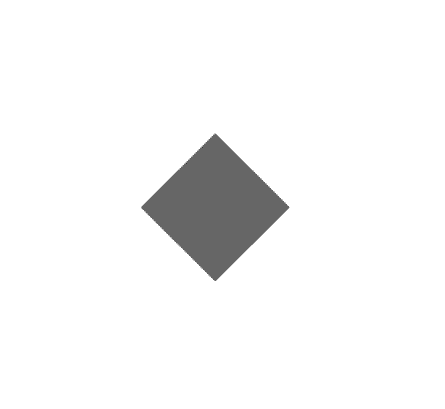
点击文末在看,帮喜欢的文章冲榜
原标题:《那么荒凉的地方,那么鲜活的人》
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