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这是我迄今最好的投资


作者 Bill Gates
在科技行业,成功和失败都是常事,而大多数都是失败的。我总假定,我在科技领域的投资里,10%会成功——而且是大获成功,剩下的90%则会失败。
当我离开微软,转而在慈善领域开启我的第二段职业生涯时,并不觉得成功率会有多大变化。如今,我投资于减少贫困和疾病的新方法。我发现,发现一种新疫苗就像发现下一个科技行业的独角兽一样困难。(事实证明,发现疫苗难得多。)
然而,投资保健领域20年之后,一种投资方式令我大为讶异——因为它不同于投资新疫苗或新科技,成功率居然非常高。这就是全球卫生行业从业者所谓的“筹资与送达”(financing and delivery)。数十年前,这些投资确定性不高,如今却总有丰厚的回报。
在人类与疾病的斗争中,发现新药等重大突破是很引人瞩目的,这是理所当然的。青霉素和麻疹疫苗等新发明拯救了数亿人的生命。

2013年3月,在加纳奥武图森亚区,本文作者看着一名卫生工作者给儿童接种疫苗。图片来源:PIUS UTOMI EKPEI/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然而,仅仅研发有效的新药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让这些药从实验室去到医院、诊所和需要它们的家庭。药并不会自己行走。购买医疗用品,再送去需要它们的地方,听起来似乎容易,甚至有些无聊,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发展中国家,拯救生命往往意味着把药品运送到偏远山村和战区。
20年来,我和妻子梅琳达(Melinda)投入了100亿美元,支持从事这项艰巨工作的组织,其中规模较大的三家是:Gavi,即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Vaccine Alliance),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简称:全球基金)以及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组(Global Polio Eradication Initiative)。每家机构都非常成功,然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它们,也不了解它们的工作。
相比关注它们,为它们提供资金和支持的人就更少了。未来的18个月内,如果没有更多资金支持,这三家机构将不得不大幅缩减抗击疾病、维持人类健康的工作。这种事不该发生。这些机构并非无关紧要或可有可无。事实上,它们也许是我们基金会做过的最佳投资。
20年前,国际社会开始意识到,尽管自二战以来公共卫生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人们的死亡率依然高得惊人,其罪魁祸首主要是疾病,而这些病用一些基本药品就能轻松治疗。相关机构建设的浪潮由此开始。
浪潮的起点是2000年Gavi成立(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其宗旨是购买疫苗,然后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孩子接种。两年后,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成立,其目标也与前者相似:提供药物,对抗被视作低收入国家头号杀手的这三重疾病。

接着诞生的是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组,或称GPEI。它最初成立于1988年,根据当时的卫生工作者记录,世界各地有35万多例脊髓灰质炎症。然而到了21世纪00年代,全球只剩数千病例,并且人们还在继续努力,让这种疾病从地球上永久消失。
全世界早已拥有抗击困扰贫穷国家的疾病的工具。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问世已有30年了,而在我出生前,Jonas Salk就发明了第一种脊髓灰质炎疫苗。然而,20年前,这些药物多数都很昂贵,而且我们也没有一个有效的网络把它们运送到贫穷国家及其周边地区。
这些新成立的机构帮助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们汇集美国、英国等捐助国的资金,创造了规模经济。许多药品的价格暴跌。这些基金与近100个国家合作,建立了大规模的供应链来运送货物:Gavi去年为1亿名儿童接种疫苗;全球基金发放了2亿张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来帮助人们抵御传播疟疾的蚊子。
这些举措对疾病的影响是巨大的。自Gavi成立以来,中低收入国家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人数下降了40%。同时,脊髓灰质炎几乎已经消失。去年,全球的脊髓灰质炎病例数是31。
艾滋病方面的进展也许最为惊人,尤其是若你记得2000年左右这种疾病传染的情况。新千年伊始的一期《新闻周刊》(Newsweek)封面上,“1000万孤儿”的标题赫然在目,杂志报导称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艾滋病如同残忍的镰刀收割着生命。”两年后,全球基金成立。四年后,死亡人数达到峰值,此后,数字下跌了一半以上。
2000年,当我和梅琳达开始投资这些基金时,我们的目标是拯救生命,让人们不再受折磨,从这个标准来看,这些机构取得的成就早已超越了我们最美好的设想。但即使是从传统的投资角度考量,它们也是成功的:它们创造了大量财富,因为人一旦不再卧病在床,就可以去上班或上学了。

智库“哥本哈根共识中心”(Copenhagen Consensus Center)使用精密复杂的算法和最佳可用数据来比较备选扶贫策略。通过他们的方法,我们得以测试一个有趣的假说:假设我们的基金会没有投资Gavi、全球基金和GPEI,而是把那100亿美元用于跟踪标准普尔500指数,并承诺18年后将所有结存送给发展中国家。那么,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截至2019年年初,这些国家应该会收到约120亿美元,如果把股息再投资也算进去,那就是170亿美元。
如果我们把100亿美元投资到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项目上呢?回报是1,500亿美元。投资基础建设,回报是1,700亿美元。然而,我们投资全球卫生机构获得的回报远超于此:我们用100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药品、蚊帐和其他用品,创造了估计2,000亿美元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每三到五年,这三家机构都需要筹集新的资金。大多数时候,它们的“资金补充”在时间上是隔开的。然而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了。十分凑巧,在未来18个月内,Gavi、全球基金和GPEI都需要更多资金。就我所记得的,2019年和2020年是为抗击疾病提供资金最重要的年份,捐助者面临的紧要问题是:你会继续投资吗?我的回答是:会,一定会。
我的回答并不仅仅基于过去的成功。这三家机构中,没有一家是一直一帆风顺的。给我信心的是它们的学习能力,通常来说是互相学习。
举例来说,由于脊髓灰质炎症从1980年代的几十万例下降到2000年代的几千例,GPEI也就要随之改变抗击这种疾病的方式。消灭最后这些负隅顽抗的脊髓灰质炎症很不容易,因为它们流行之处是全世界最难到达的一些地方,例如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偏远角落。尽管如此,GPEI还是设法建立了一个监控系统,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都能获取样本(脊髓灰质炎通过粪便传播)并检测这种疾病的踪迹。
现在,全球基金就在尝试将脊髓灰质炎小组的经验应用于抗击疟疾。他们建立监控系统,跟踪是哪种蚊子在传播疾病,又传播到了哪里,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分发带有对应杀虫剂的蚊帐。
在接下来两代人的时间里,我们预计人类与疾病的斗争范围会缩小,但也会更剧烈。发展中国家整体上变得更健康了,但也有更多儿童出生在世界上最欠发达的角落。面对新疾病的出现,旧疾病的发展,以及这些人口的增长,能拥有这些与时俱进的机构,我们何其有幸。
2017年9月,我和妻子梅琳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时,很担心总统特朗普会把美国对外援助的预算削减30%。幸运的是,在国会议员的努力之下,此事并未发生。但我们的隐忧仍在。2019年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总统再次瞄准了对外援助,称其支持者“甚至不知道自己把钱给了谁”,并表示将削减资金。

并非只有特朗普总统那样想。如今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像Gavi、全球基金和GPEI这样的机构,然而给予他们的帮助却是其史上最少的。
我们对这些机构捐赠的100亿美元仅占全世界投入的十分之一。绝大多数的资金并非来自慈善机构,而是政府。
20年来,说服立法者和国家领导人投资这些机构一直是一项艰巨但尚可掌控的任务。哪怕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经济衰退期,美国对全球基金的捐款也是在增加的。然而从那以后,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
孤立主义的浪潮继续席卷了许多西方民主国家。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欧盟的立法部门——的选举将于5月举行,更多的极右政治家有可能会前往布鲁塞尔。至于英国的对外援助预算,无人能预料到它在英国脱欧的动荡中会有怎样的结果。即使是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等倾向于支持对外援助的领导人,也面对着重重压力,需要将资金优先投入与本国相关的其他项目上。
在这种情况下,要为这些重要的全球卫生机构维持原本的资金注入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随着最具挑战性地区的人口快速增长,维持原有的投入是不够的。事实上,年初全球基金正式要求捐助者在未来三年内提供140亿美元,比过去三年的全球认捐额多了10亿美元。
当然,也有好事。尽管总统颇有微词,美国国会还是始终坚定地支持对外援助。另外,印度和中国等快速发展的国家逐渐转型,从接受全球卫生机构的援助转变为为其提供支持。只是资金状况并不稳定。
全球基金的年度预算约为40亿美元,在三家机构中是最多的。20年来,德、法、日、英、美五国的援助资金占了其中的65%以上。Gavi和GPEI的数字略有不同,但情况极为相似: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在鼎力支持它们。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启动了一个名为“全球消灭疟疾计划”(Global Malaria Eradication Program)的项目,成功地消灭了欧洲、南美洲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疟疾。但该项目几乎完全由美国出资支持,1963年,美国决定撤回资金后,该项目在没有别的支持者的情况下只好停止,于是该疾病卷土重来:从巴西到土耳其,疟疾到处肆虐。即使是少数富裕国家削减援助预算,我们今天也很有可能目睹类似的结果。
数十年的数据和经验表明,抗击疾病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金钱。针对医疗保健的对外援助水平与某些最致命疾病的死亡率下降之间密切相关。捐助增加,死亡人数就减少。现在,全世界的人们需要决定,是否还要延续这种显著趋势。
在全球卫生体系的某些领域中,数据参差不齐,我们不清楚投资是否会有回报,也不知道如果完全不投资会怎样。但上述投资不属于此类。如果我们想减轻苦难,拯救生命,那么Gavi、全球基金和GPEI这类机构是我们最有成功把握的事了。它们是这20年来我与梅琳达做过的最佳投资,也是整个世界在未来几年中所能做的最佳投资。
本文作者比尔·盖茨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联席主席。文章为作者个人见解,不代表本报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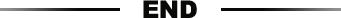
你可能还关注 ▼
未来厕所什么样?比尔·盖茨掀起马桶革命
比尔·盖茨夫妇的一封信:美国为什么应该继续帮助穷国
大家也在读 ▼
“废品荒”来袭,中国企业赴美淘宝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