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医学领域“多数研究成果都是假的”


图片由Doug Chayka绘制。
作者 Richard Harris
4月28日,HBO电视网将播放一部由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主演的电影,讲述1951年死于宫颈癌的马里兰州非裔美国女子海瑞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的故事,她的癌细胞至今仍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里。
电影根据瑞贝卡·斯克卢特(Rebecca Skloot)的畅销书《海瑞塔·拉克斯的不朽人生》(The Immortal Life of Henrietta Lacks)改编,深入展现了虽然拉克斯为科研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她是无意的),但其家人却难以因为她的贡献获得认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从拉克斯身上提取并培养了肿瘤细胞,将之命名为“海拉”(HeLa),于是“海拉”成为首例用于医学研究的“长生不死”的癌细胞。
关于海拉细胞,引人注目的除了拉克斯的个人经历外,在生物医学研究方面也有一个严重问题。由于繁殖速度太快,再加上这些年来处理不当的情况屡屡发生,所以海拉细胞已被证明是严重污染物之一。它们毁掉了无数个实验,愚弄了一代又一代对它们悄然钻进烧瓶的行为毫无察觉的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就能让海拉细胞乘虚而入,挤走其他细胞。例如,科学家自认为在研究肝癌,但实际上大错特错。

海瑞塔·拉克斯。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 实验结果再现性危机
这种细胞污染只是生物医学研究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科学家指出,生物医学研究如今面临着“再现性危机”,也就是说,研究结果无法再现,即使不是无效,也靠不住。这个问题不只是浪费时间和金钱那么简单。很多观察人士现在认为,“再现性危机”令全球生物医学研究受到大幅拖累,以至于放缓了寻找新疗法和新药物的速度,使之偏离了正轨。
有证据显示,“再现性危机”已有10多年之久,解决这个危机成了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当务之急。不过,第一步先要认识危机的源起,例如培训不足、糟糕的实验室技能、经费紧缺诱发不良的职业晋升动机等等。
失败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环节,没人要求研究人员第一次做实验就顺风顺水。科研成果通常是一个长期自我修正的过程,期间会不断补充进来有用的信息,以及甚至来自失败实验的疗法和药品。然而,要是头开错了,实验进程却可能因之放缓。
▶ “已发表的多数研究成果都是假的”
有多少生物医学研究确实有错?2005年,斯坦福大学流行病学家、卫生政策研究员John Ioannidis在同行评议性质的全科医学周刊PLOS Medicine上发表文章,带头敲响了警钟。他的文章认为,小样本实验设计和实验者偏见是存在于该领域的长期问题,这两个因素可严重高估实验结果的积极性。最后他得出的结论竟然是,“已发表的多数研究成果都是假的”。
这个问题在动物实验里尤其突出,因为科学家常常只使用为数不多的几只动物,且没有对它们进行随机选择。这类错误难免会导致偏见。药品测试采用的大规模人体实验虽不大可能如此离谱,但亦有自己的弱点:和所有人一样,科学家也忍不住希望得到想要的结果,而为了获得想要的结果,他们可能会对数据进行“筛选”或修改。
法国波尔多大学的Estelle Dumas-Mallet与同事今年2月在科学期刊PLOS One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跟踪了解了156项被主要英文报纸报道的生物医学研究。他们发现,初始结果积极的研究中,有一半被后续研究推翻,而这种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媒体则鲜有跟进。那156项研究涉及的主题十分广泛,包括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生物学原理、新乳腺癌易感基因、暴露在杀虫剂下与帕金森病之间的可能关联、病毒对自闭症的影响等。
制药公司的评估数据同样不容乐观。2011年,拜耳公司(Bayer)科学家在《自然综述:药物发现》(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上发表的论文显示,对于林林总总的各项研究结果,他们只能复制出其中的25%。2012年,安进(Amgen)癌症研究负责人C.Glenn Begley在科学期刊《自然》(Nature)上称,53个看似乐观的研究结果,他和同事只能复制六个,这还是在求助了参与研究的一些科学家的情况下。
由于人体临床试验的成败攸关数百万美元,所以科学家遵循高标准的动机更强。这类研究常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合作,研究结果最终由后者复审。即便如此,大多数临床试验的结果也都令人失望,这往往是因为试验所依据的实验研究本身就有缺陷。
▶ 造成危机的罪魁
造成“再现性危机”的成因有很多,但正如海拉细胞的例子所展示的,受污染的研究材料是主要罪魁。大约有20个科学家的志愿者组织国际细胞系认证委员会(International Cell Line Authentication Committee)一直在记录被错误辨识的细胞系数量。目前的统计结果为,(生物医学研究中)逾450个细胞系被错误辨识,其中113个细胞系被海拉细胞系污染,但海拉细胞系并非唯一污染物。
1976年,休斯顿市MD安德森癌症医院和肿瘤研究所(MD Anderson Cancer Hospital and Tumor Institute,当时的名称)从一名患乳腺癌的女性身上分离出一组细胞系,命名为MDA-MB-435,曾连续多年被视为研究乳腺肿瘤最重要的工具之一。2000年,科学家用基因指纹法对这个细胞系进行鉴定,发现它实际上是黑色素瘤。这一发现被广泛报道,但即使这样,之后的科学家仍用这个细胞系发表了900多份“乳腺癌”报告。

一个海拉细胞的电子显微图像。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另一个导致错误的重要来源是糟糕的实验设计。太多科学家要么实验设计不严密,要么没能正确进行实验分析。他们在实验中使用的动物往往太少,且没有采取减少偏见风险所必需的所有措施。
想想寻找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亦被称为葛雷克氏症,此病患者会逐渐失去移动和呼吸的能力)治疗药物的一连串失败吧。过去几十年,科学家花了纳税人数百万美元,经过种种试验,选出了貌似有望治愈这种神经肌肉退行性疾病的药物。
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研发出有效的治疗方法。马萨诸塞州剑桥ALS疗法开发学会(ALS Therapy Development Institute)的科学家下决心查明原委。2008年他们在《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期刊上称,几乎所有基础研究都存在重大缺陷。在研究过程中,每个实验所用小白鼠的数量常常不到12只,且没有采取专门措施来避免明显的偏见来源,如实验小白鼠的遗传变异性。ALS疗法研发学会重新做了一遍相关基础研究,各项环节都适当把控。他们发现,尽管初步结果较为积极,但是那十几种药物无一带给人们真正的希望。
ALS疗法研发学会目前就有望成功的疗法展开了自己的实验研究,每个测试组有32只小白鼠,每个对照组也有32只。若每个步骤都严格把控,那每项实验的花费都在10万美元以上,学术研究人员大多无力为一项实验筹集这么多钱。
但现在不仅仅是钱的问题。研究人员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过严谨实验设计的培训。年轻的科学家可能上过一两节统计课,但在接触实验设计方面却往往是以特定的方式——基本上是在实验室里被导师用作廉价劳动力的时候。2014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立综合医学研究所负责人Jon Lorsch为了提高实验设计的培训水平,曾设法复制他能找到的最佳方法类课程。他给大学打电话,询问建议,但却一无所获。此后,NIH便开始给研究实验设计方法的课程提供资金。
令培训不足问题雪上加霜的,是科研人员希望一鸣惊人的学术压力。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竞争十分激烈,这主要是因为经费难搞。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14年的数据显示,美国高等院校58%的生物医学研究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只有4%由州和地方政府资助,其余由大学基金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资助。
可是,支持生物医学研究的公共资金规模呈现出了急剧下滑的态势,并且这一态势已持续了一段时间。美国联邦政府称,按实际货币计算,2003年至2015年NIH提供的资金金额减少了22%。特朗普政府的预算案若获得通过,NIH的预算将随即再减18.3%。不过国会不太可能接受如此大手笔的减支。

NIH表示,时下项目经费十分紧缺,实验室负责人平均为一个项目须提交五份经费申请报告。可想而知,他们的压力有多大。拿不到经费的科学家最终不仅可能会失去员工、实验室,甚至可能搭上自己的职业生涯。
明尼苏达州非营利研究机构HealthPartners Institute的社会学家Brian Martinson说:“大多数科研人员工作起来都很拼,所以要想占优势,想领跑,想成为第一个冲刺过线的人,还能怎么办?只能抄近路,这是唯一的选择。”
科学家如想获得好工作或拿到大学终身教职,亦得在屈指可数的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没在著名杂志《自然》(Nature)上发过论文?没有面试机会。这就让他们有了更多“美化”研究结果的动力。美化的方法多种多样,可以剔除不合适宜的数据结果,增强影像,甚至绕开那些可能会引出一个意外结论的实验。
▶ 亡羊补牢
科学家和科学机构管理人士已经认识到,不能再忽视这些环环相扣的复杂问题了。Ioannidis与同事Steven Goodman及其他几位研究员目前的工作重点是完善生物医学研究实践。他们在斯坦福大学成立了元研究创新中心(Meta-Research Innovation Center),旨在寻找转变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工作方法。
Goodman表示:“我绝不会说,我们解决了临床研究的所有问题,但在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上,至少我们有了一个像样的模板。”他认为,现在要迈出的关键性第一步,是提高研究过程的透明性。
美国开放科学中心(Center for Open Science)执行董事、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Brian Nosek也认为,研究人员应该无偿提供所有方法和数据,这样可以更快地修正工作中的错误,敦促研究人员从一开始就应更加认真细心。Nosek创立了一个名为开放科学框架(Open Science Framework)的免费在线资源,旨在让科学家有机会免费提供自己的假设、方法、计算机代码和数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率先启动了一个项目,在实验室研究成果为生物制药公司所用之前,验其真伪。
有些公司也开始介入其中。位于加州伯克利的Protocols.io是一个科研方法资源库,科学家可精确复制往期实验,下次做研究时使用同样的公式,或与他人共享那些具体方法。加州奥克兰的Ryffin也是这样一家专业公司,它用软件帮助科学家设计实验,管理分散的数据集,还能整合数据集用以分析并与其他科研人员分享。
高校院系和院系负责人也可以改变扭曲了大量研究的不合理的激励制度。他们可以在一开始就告诉科研人员,职称晋升将只与两三项重要的研究成果挂钩,无需提交一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这会鼓励他们注重研究的质量而非数量。
技术上的一些简单措施也能排上用场。NIH规定,从2016年1月开始,获得联邦经费的科学家要对研究所用的细胞系进行检查,以免不小心错用海拉细胞系或其他冒充者。现在有一项价格低廉的测试,可解决细胞污染问题。研究人员须把这项测试纳入到研究计划中,但还不清楚NIH如何保证研究人员遵守这一规定,违规者又作何处罚。
关于科研经费和望眼欲穿的科学家人数之间的不匹配问题,则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这个生态环境从根本上说是失衡的。经费再充裕也杜绝不了浪费。甚至在研究启动前,同行评议就已淘汰了80%的经费申请,包括那些研究方法站不住脚的。
天下没有任何方程式能预测出,哪个研究项目可以产生下一个神奇药物。如果能预测,就没必要做实验了。但从严的标准和规定至少可以减少很多没必要的错误。研究的透明性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不可避免的错误更快地曝露出来。
改变生物医学研究的职业习惯和文化不是易事。对于最新研究的轰动性成果,心存谨慎还是有必要的。但是,真正的改变就要到来。加快新药和更佳疗法的开发速度还是大有可为的,所有人都愿意看到这一幕,只是过去几十年科学界迟迟没有做到。
Richard Harris是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新闻频道负责科学栏目的记者。本文改编自他的新书《尸僵:粗心大意的科研造出毫无价值的疗法,碾压希望,浪费巨资》(Rigor Mortis: How Sloppy Science Creates Worthless Cures, Crushes Hope and Wastes Billions),基础读物出版社(Basic Books)出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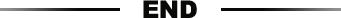
你可能还关注: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