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地方,哪怕回不去,也时常念起

故乡是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3918期
▾ 点击收听 ▾
《峡河西流去·自序》(节选)
我不过是个写信的人,我以文字歌哭、悲喜,以晨起暮歇的有用无用功为世界、为人们、为看见和看不见的事物写信,又以同样或不同的方式接收来信。我不知道我写出的信你们是否收到,而你们的所有来信,我都认真读过了。
马提雅尔说过,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我有时候在其中活一回,有时候死一场。
谨以此书献给我形已消失的故乡,以及风尘里赶路的、风流云散的人事。
故乡消散的年代,愿我们都有故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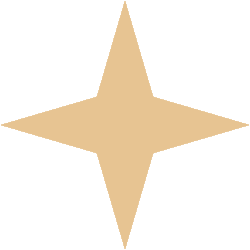
朗读者根据朗读习惯略有改动
「留言」:聊聊故乡的变与未变
峡河西去 漫天的云层里
他辨认出了童年 少年 以及
来自地心的铜 铅 金 银……
——陈年喜
比如一条河的枯荣兴亡。“峡河七十里,七十里的地理与风烟,包含了多少秘密,我似乎熟悉,又一无所知,就像我们对于自己,更多时候,也像老死不相往来的亲戚。”(《峡河西流去·峡河七十里》)
比如“一把弹弓”的出现与消失。“年轻的瓶子变成了老瓶子,他弹弓的绰号人们慢慢都忘了。是啊,这世上,多少人,多少事,谁还记得呢。”(《峡河西流去·弹弓》)
比如一人同一地的缘起缘灭。“他的妹妹嫁到了南方,父母和哥哥因病都作了古,他已没有了牵挂。就是说,峦庄镇再也没有白毛,白毛也再也没有峦庄镇,像彻底破裂的婚姻,一拍两散。”(《峡河西流去·峦庄镇的白毛》)
时间待故乡温柔又残酷,故乡于游子亲近又疏离。然而无论它如何变化,都盛满了教人难以放手的回忆,那里往往藏着最初的人间印象,和最深的生命底色。
故乡还早早就将某些生存的真相暗示出来,留待人们日后去感悟:
“峡河地方穷,没有剧场,没有舞台……剧团为什么要费力地来唱戏……他说,唱戏的人,喜欢唱戏。
后来的生活和人生给了我一些答案,很多事,很多人,因为没有目的,而达到了很美很远的目的,而我们后来的很多事物,因为太有目的,结果离目的越来越远。”(《峡河西流去·峡河七十里》)
在变化与不变、记忆与遗忘、离别与返还之间,我们同故乡彼此打量。秋往春来,物是人非,时间落在故乡的人、物、事上,也让我们从中更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形状。
你后来一定见过许多花开、尝过各色美食、走过不同街道,它们却常常难敌记忆深处的一片草地、一缕炊烟、一条土路。你可以说故乡是回不去的远方,也可以说它如同无处不在的月亮。
背负故乡和回忆行走的人或许要辛劳些,但这未尝不是幸运。“故乡消散的年代,愿我们都有故乡!”
撰文 | 一条小路 审校 | 西格玛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