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养老院里当“网红”,偶尔忘记变老|谷雨

作者| 崔一凡
编辑 | 唐槭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全中国平均年龄最大的“MCN”
这里是全中国平均年龄最大的“MCN”。“MCN”设在天津一家养老院。你或许已经看过他们的视频了。一群老爷爷老奶奶在镜头前,告诉你“不听老人言,开心一整年”,安慰你“坚持不自律,其实也是一种自律”。他们教你如何面对阴阳你的同事,如何怼占你便宜的朋友,末了还会告诉你,这是生活中的基操——他们年纪加起来超过400岁,任何话都显得很有说服力。
视频里的他们擅长玩梗,甚至不回避死亡。“化学课”系列中,常见的情节是,在化学老师的教导下,倒霉学生误吸了某种“有毒气体”,当场翻车,躺在担架上被人抬走,上了南天门。评论区称之为“化学逝验”。演员们,也就是这些走路都颤颤巍巍的爷爷奶奶们还觉得挺有意思,生死有命,问题不大,谁还没收到过张病危通知书呢?在一条点赞转发均突破10万+的视频里,有人评论,“谢谢爷爷奶奶们将毕生功力传给我们!!!”
我到达这家养老院时,这些网红老人们正参加一场活动。一群初中生来养老院,和他们一起联欢。学生们在台上表演节目,他们在台下看。学生们提问人生问题,他们给予解答。一位母亲也带着得了抑郁症的初三孩子一起来,她看了视频之后,觉得心里很暖,希望孩子能跟爷爷奶奶互动,或许对孩子的病情有帮助。
他们的账号叫做“养老院里的春天”,账号火了,老人们过上热闹的生活。一位艺名鲍勃的演员表示,他甚至走在街上都能被人认出来。艺名卡尔的演员说,红了也没什么感觉,就是采访稍有点多。
中午1点半,到了开始拍视频的时候。演员们在18楼的活动区集合。两位演员坐在轮椅上,一位90岁了,另一位半身不遂——他右手拄着拐,像是随时要站起来。轮椅和轮椅之间隔着距离,他们放大声音聊天,且只称呼彼此的艺名,卡尔、爱丽丝、鲍勃……听起来像互联网公司的同事。
此时,卡尔正坐在一旁的沙发上,仔细研读今天的剧本。视频平台上,卡尔几乎是最受欢迎的角色。他叫陈家伟,80岁,脸方方的,鼻头挺大,一头银发向后梳,如果戴上黑框眼镜,跟《飞屋环游记》里的卡尔一模一样。卡尔把剧本,也就是一张A4纸,捏在右手虎口的位置,他身患格林巴利综合征,一种罕见病,直到现在也无法弯曲手指。
今天的剧本很简单,拍的是“心眼子训练”系列。你在公司得奖了,同事撺掇你请吃饭,你该怎么办?卡尔扮演得奖的同事,另外几位扮演让同事请客的人,以及心眼子教官。剧本用黑体大字印在纸上,只占了A4纸的三分之一。
演员们默默熟悉台词,一位戴着棒球帽的年轻人则在四处寻找合适的拍摄场景。他叫陈卓,29岁,是短视频的导演,也是“MCN”的真正核心。来到养老院之前,他在广东做服装生意。疫情让他开始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去年三月,他回到老家天津,和他的爷爷——也就是卡尔——住在养老院里。拍视频最初是为了记录,逐渐地,他觉得拍视频不管对老年人还是对自己都是件有趣的事。他希望用视频传递自己的理念,比如不需要把死亡看成多么可怕又悲伤的事,它是必然,又或者是一种新生。陈卓并不准备用这个号盈利,他更希望每天跟老人拍视频这件事是纯粹的。但视频爆火也并非没有任何好处,最近他开始承接起其它养老机构的起号业务。
陈卓觉得,这些视频是个乌托邦,他把角色塑造成老人们希望成为的样子,饰演化学老师的余幽芳原来就是老师,现在她继续做老师;卡尔就是个显眼包,所以总让他在视频里整活儿。之前还有位演员,喜欢当领导,于是视频里他总是演领导。
视频里,爷爷奶奶们头脑灵光,金句迭出,像是长着一张老年面孔的年轻人。面对阴阳怪气要求请客的“同事”,卡尔回怼,“我说你们怎么不拿奖,原来是怕请客啊!”“同事”不甘示弱,“就这点儿小钱还计较!”卡尔说,“那等我再攒攒,一人给你们买套房!”
拍摄时的节奏却并非如此,即便剧本非常简单,演员们还是很难完整地记住一句话,并把它表演出来。拍摄时,陈卓说一句,让演员们重复一句。有句台词,卡尔老说不顺溜,陈卓不急,把一句台词拆成两句,分别拍。说了几遍,有进步,“非常好!”陈卓说。
对于这些老人来说,拍视频成了他们每天的念想,一种生活的寄托。聊天时,90岁的余老师问我,“你说这视频,能拍下去吗?”她担心剧本总有拍完的一天,她不希望有这么一天。
那天正拍着视频,刘学霞拎着布兜走过来,她穿一双枣红色小皮鞋,袜子卷着花边儿。“睡过了,”她笑了笑,看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今天的脚本里没刘学霞的台词,但她还是要了一张台词纸看。
刘学霞83岁,在养老院里住了不到一年。前些天陈卓他们拍视频,刘学霞在边上看,看得多了,陈卓就叫上她一起。刘学霞年轻时是工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与外界的接触越来越少。2015年,老伴儿离世后,她总独自在家,坐在沙发上,对着电视打盹。
后来我再次见到她,聊天过程中,刘学霞手里一直攥着一张A4纸。她知道今天有人采访她,怕有些事情记不住,说不好,就提前让女儿写下来:
“我是在天津空调器厂退休的,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多次被评为过劳动模范,我喜欢参与各项文娱活动,感谢节目给我参与演出的机会,我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和指教,我愿意成为你们当中的一员。”
养老院里的春天
陈卓的第一个演员是卡尔,卡尔天生有表演欲,退休之后又学过唱歌,唱帕瓦罗蒂,意大利语。但拍多了总得有点新意思。那时陈卓看到短视频平台上,有博主用搞笑的方式讲课,他第一时间想到余老师。
余老师叫余幽芳,90岁,人瘦小,头发银灰,梳成一丝不苟的四六分。她原先是耀华中学的化学老师,1990年退休。她不想让自己闲下来,上了八年老年大学,学画画和书法。但衰老意味着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弱。她的腿脚逐渐不行了,连去老年大学都成了难题。女儿给她买了个iPad,她白天独自在家,用大把的时间玩对对碰和俄罗斯方块。2015年的某一天,女儿女婿出门买饺子,她想去厨房准备碗筷,手里的拐棍没拄好,人摔在地上。她爬回床上,等人回来。
摔了一次之后,她不敢拄拐棍儿了,换成四个腿儿的助行器,需要两只手扶着走。“拿着拐棍还能动换,热点东西(饭菜),一拿这个(助行器)我没法热了,这可怎么办呢?”她说去养老院吧,女儿们没有反驳。
余老师虽然会用智能手机,但原先对短视频没概念。陈卓邀请她,说一起玩,她就加入。有时候拍摄不明白的内容,她也不在意,看了成片就明白了。她不知道怎么在App里看他们的视频,陈卓就会每次发布后再给余老师单发到微信,她再把视频转发给女儿。
现在,拍视频已经成了余老师每天生活的重心之一。每天拍视频之前,她都要先问陈卓时间。大约是午休之后,她要提前半小时开始准备,主要是上厕所,她担心因为自己耽误了拍摄的进程。
陈卓会注意那些不怎么快乐的人。比如鲍勃,陈卓曾无数次讲过鲍勃,也就是王力的故事,且从不厌倦再讲一次。王力63岁,在养老院里算年轻人。13年前,他因糖尿病引起脑梗,之后半身不遂,三年前住进养老院。
那时陈卓看王力总是憋在屋子里抽烟,想叫他出来活动活动,他招呼王力过去。王力表现得害羞极了。“我不方便,”他是指自己的身体,“我怕耽误你们。”王力说。话虽如此,他还是被这个新玩意儿吸引了。他喜欢表演,小学就演过智取威虎山,后来商海浮沉,中年重病,这些闪烁的东西早被消磨殆尽。
拍摄对于王力来说很艰难,他得努力按着拐杖,试图从轮椅上站起来,但不行。有时,73岁的爱丽丝过来帮忙,双臂夹在王力腋下,用力把他架起来。但王力脑袋灵光,也擅长证明自己的灵光。我看他们的第二次拍摄,王力和卡尔一人负责一个长难句。卡尔总是记不清,索性拆开说,分别拍。王力不行。陈卓让他断句,他坚决不从,“我不用!”他说。
据说王力是个毕业于南开的大学生,学的化工。七十年代开始做生意,八十年代开上奔驰。什么赚钱干什么,去国外进口电视机,进口家具原料。之后干过国企,南海治过沙,在香港,他管理过几百人的大厂子。
“这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亦真亦假。”陈卓说,“但是通过他的描述,我能感觉得到他曾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
但当我见到王力,想听他自己讲讲往昔光辉岁月的时候,他只轻轻摇了一下头,“不提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觉得它们不重要,没意义了。他离那个王力太远。年轻时,他过着喧闹的生活,12点之前没回过家。转折发生在2011年11月的一天上午,他骑车去办事,突然手脚不听使唤,把人车后视镜给撞了。到医院检查才知道,他的身体已经垮了。
半身不遂之后,他扎了6个月针灸,每天143针,他觉得自己像个刺猬。后来大夫看不下去了,说别傻了兄弟,你再扎一年也没用。“要不现在谁要说扎针就能好(治好偏瘫),我能跟他抬(杠)一宿!”王力说。
有一天夜里,他从床上滚下来,他撑不起自己,妈妈80多岁了,也扛不动他。他只能打电话给儿子,儿子开车过来,抱他上床,然后回家。从那时起,王力开始接受,自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残疾人”。那时他已经离婚了,妈妈照顾他。他躺在家里,不断地抽烟,他抽一次,妈妈就拿痒痒挠抽他的背一下,但他依然抽,不抽不行。
直到开始拍视频之后,王力变成了鲍勃。在陈卓看来,他变成鲍勃的证据是,他的烟量从一天四包变成了两三包。他重新变得爱吃了——就像一个热衷用口腔探索世界的婴儿。他让陈卓去几公里外的玉泉饭庄,给他打包苜蓿炒肉和八珍豆腐,这是原先从未发生过的事。至于他们拍的视频,鲍勃从来没看过,点赞粉丝什么的他更不关心。“我只是抒发一下我郁闷的心情。”鲍勃说。
成为短视频小组的成员,并不需要什么条件。只要有意愿,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曾经有一位叫刘国霞的演员。她84岁,患抑郁多年,每天要吃四种药。刘国霞不识字,拍视频的时候,陈卓说一句,她跟着说一句。
刘国霞年轻时是纺织工人,退休后拉扯孙女,孙女拉扯大之后,她发现已经拉扯不动自己。抑郁也在此时进入她的生活。医学领域有个专门的名词,叫老年性抑郁,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精神障碍,起因多为退休、空巢、独居及慢性病。陈卓觉得,老年人的抑郁源于丧失感,身体机能的丧失,社会能效的丧失,甚至亲密关系的丧失,也就是说,“他发现他不行了”。
在陈卓的讲述中,之前刘国霞总是推着自己的助行器,从不主动与人聊天。但后来,她连药量也减少了。
生死之间
或许出于对衰老的恐惧,人们渴望看到快乐的老年人和快乐的老年生活。他们在短视频中呈现某种样貌,得到年轻人的喜欢和夸赞。心态是重要的,活力是重要的,这些都是好的部分。但别忘了陈卓说的,这是个乌托邦——而衰老就是衰老。看看卡尔爷爷僵直的双手吧,想象一下每根手指只有第一关节能够稍稍弯曲的样子。他双掌夹起水杯喝水。他穿上那件黑色呢子外套,却怎么也拉不上拉链。他喜欢抽烟,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等烟灰长到摇摇欲坠时才去弹落——不是真的弹,而是用手掌边缘锤打桌面。
卡尔早已习惯了这些,并用一贯乐观的心态面对命运无常。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我能跟你讲两天两夜不重样的!”他确实能做到。他的声音洪亮,我坐在他左侧(“我把好耳朵留给你!”),声音也必须洪亮。
在养老院里,你能感受到一种安乐祥和的气氛,比如大堂广告屏上欢迎新入住老人的海报,屋子里展示的老人们的书法作品,还有他们的照片墙。每一张照片里都是笑脸。当然,你也会发现,一些内容被刻意隐藏了。养老院的电梯没有4、13和14层,为了让这几个数字彻底消失,连显示楼层的电子屏都被贴纸覆盖。
但老人们或许对生死的问题并没有那么敏感。短视频的其中一期,饰演化学老师的余老师,让卡尔闻一氧化碳,卡尔当场“中毒”躺倒,被担架抬走。屏幕上的花字写着,“一逝便知”。另一期,还是化学课,卡尔又吸了有毒的硫化氢。卡尔站在南天门上,背景音问,“你是怎么来的?”卡尔说,“化学老师让我来的”。
总有记者问卡尔,孙子拍视频,让你上南天门,你怎么想?
卡尔觉得,“无所谓,生老病死不可抗拒”。他总用自己在ICU的经历回复,他患的病叫格林巴利综合征,发病率十万分之一,发病原因未知,且没有相应治疗手段。卡尔被下过两次病危通知书,同病房的七位病友,只有他自己活下来。“老天爷说你罪没受完,不收,就这么着,所以我多活一天都是赚的。”卡尔说。拍摄这些题材之前,陈卓并不需要给老人们做过多解释。他们有时明白,有时不明白,解释之后也不觉得有什么。余老师告诉我,她最喜欢的就是卡尔上“南天门”那一集,“他还真躺在担架上让人抬走了!”余老师说。
有时,演员们也会给导演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他们拍过一集视频,叫《生死簿》。笔记本上记录着一些人的名字,余老师挨个给这些人打电话,不在人世了,就用红笔把名字勾掉。到鲍勃拍的时候,他说陈卓我给你加句词儿。“我要把这生死簿撕了!”镜头里的鲍勃说,“我的人生我做主。”陈卓大受震撼,作为一个看着《西游记》长大的90后,他很清楚撕掉生死簿的象征意义。
见到鲍勃时,我询问他关于生死簿的事,“都进过ICU了,你还在乎生死吗?”他说。至于为什么要加上那句台词,鲍勃觉得,他在表达一种不在乎的感觉。“我都不在乎了,这生死簿还有用吗?那我跟孙悟空一样,撕了就完了。阎王也要不了我的命。”鲍勃说。
但当死亡在身边真实发生时,就是另一种情况了。鲍勃记得,住在之前那家养老院时,正赶上疫情扩散。晚上死个人,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就全知道了。问怎么死的?新冠,大家点点头,就都不说话了。据鲍勃说,那时殡仪馆来抬人,还总赶到吃午饭的时候。殡仪车停在门口,人从房间拉走,经过饭厅过道,老人们抬眼瞧瞧,然后埋头吃饭,吃完赶紧回屋。所有人都保持沉默。
在养老院里,陈卓也必然会拉近和死亡的距离。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一位老人正吃着,突然倒在陈卓怀里,后来发现是睡着了。两个月后,老人离世。还有一次,他跟爷爷卡尔在外面吃饭。正吃着,卡尔突然栽倒。幸好十几秒后,他醒过来,说就是眼前一黑,没事。
死亡当然是件重要的事,但陈卓更愿意将之理解成一种新生。或者说,更重要的是,每个人还活在世界上的时间。“卡尔爷爷被罕见病困扰,鲍勃半身不遂,爱丽丝心脏搭了桥,余老师也是一样。从他们每个人身上,我们都能看出来,生命苦难重重——这是世界上比较伟大的真理了。这是谁也没办法避免的。但是他们今天不都还完完整整地站在你面前?不也都幸存到今天了吗?”陈卓说。
乌托邦之外
在视频评论区里,最常见的评价是“人间清醒”,人们乐于看到老年人为年轻人解开疑惑。刘学霞的女儿之前就关注了这个账号,某天看视频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妈妈在里面,十分惊喜,立马把视频转给亲戚朋友。更多的评价是,“可爱的老人”和“正能量”。陈卓很理解视频为什么受欢迎,“当一群爷爷奶奶站出来,摸着你的头说,乖不要焦虑,不要有压力,你会觉得好治愈。”视频里的老人是人们心目中最好的老人,就像卡尔戴上那副大大的黑框眼镜,就真的是《飞屋环游记》里的卡尔了。那副眼镜专门为拍摄准备,平时他只戴小框的。
下午两点,拍摄结束后,卡尔回到房间,取下黑框眼镜,准备睡一觉。他的生活看起来很充实,拍视频、下象棋、唱歌,原先的养老院附近有家卡拉OK,10块钱唱一下午,他总去。卡尔有很多朋友,他翻出手机相册,跟我介绍,谁是发小,谁是早年演出时认识的。但对于更熟悉和亲近的人,他总表现出不愿多打扰的敏感。他和鲍勃、余老师们早就成为朋友,但在养老院,卡尔并不主动找他们聊天,“你怎么知道别人方不方便呢?”
我们见面的那天晚上,卡尔要去看望儿子,儿子最近做了个小手术。在平时,他与两个儿子较少联络,“尽量不麻烦他们”。至于孙辈呢,卡尔说,他人生中最快乐的几年,就是大病初愈之后,在家带孙子陈卓和孙女。他带他们去儿童乐园、游戏厅,一玩一下午。他从不喊他们的名字,只叫“宝儿”。后来,孙子和孙女长大了,去了很远的地方,很想他们,觉得他们忙,也不多打扰。陈卓说要回来,他非常开心,“至少能每天见到了”。
我请卡尔带我去找鲍勃。鲍勃住在5楼护理楼层,这里是行动不便的老人住的地方。他的房门总是半开,传出超乎一般人承受能力的电视声响。跟老年人接触多了,你会发现,电视是他们最好的伙伴。鲍勃屋里的电视24小时不关。
鲍勃正在坐在马桶上抽烟。他自封厕所所长,为了不熏坏墙皮,现在他只在厕所里抽。见卡尔过来,鲍勃慢慢从厕所挪到卧室,打开衣柜,给卡尔扔了一包荷花烟,“儿子给送的”,他说。
鲍勃总喜欢摆出一副倔强的表情,他也有自己的坚持。比如坚持24小时开电视,即便他的电费要比邻居贵三倍。坚持每天吃一个苹果,虽然他身患糖尿病。坚持不用智能手机,互联网上的纷纷扰扰与他无关。还坚持不玩任何棋牌类游戏——就算是跳棋——在半身不遂之前,他牌桌上得太多了。他还坚持不麻烦别人。刚来这家养老院的时候,陈卓发现,鲍勃有半个多月没洗澡。正常情况下,护工每周都会帮老人洗。陈卓问他为啥不洗,他说怕麻烦,不是怕自己麻烦,是怕麻烦别人。
“因为自己不行了,就特别怕麻烦别人。自己越不行,就越怕麻烦别人。”鲍勃说。
正因如此,他也要付出更多努力。冬天的衣服里三层外三层,不好穿。别人五点起床,鲍勃就四点起。“因为什么啊?”他撇了一眼自己不能动的左手,“咱们笨鸟先飞。”洗漱也一样,拧不了毛巾,就用另一只手捏,一点点把水挤干。“人必须得自己干点事儿,我得证明自己还是有价值。”鲍勃说。
孤独是显而易见的,他承认这些,但并不准备解决。他离了婚,前妻有时来看他,短暂的,时间久了必然吵架。他爱他的儿子,但除非有什么要紧事,从不主动打电话。“人家两口子二人世界,我不打扰他们生活。”
“多难受,我忍着,”鲍勃说,“不单单我这么想,你把这些老人都叫出来,问他们哪一个没事叫儿子女儿过来,都不会。”在关于儿子的问题上,鲍勃构想了很多“万一”。“现在孩子本身生活工作压力就大,他有事儿怎么办?他来了能不给你花钱吗?万一他最近手头紧怎么办?儿子愿意来,万一儿媳妇不乐意,两口子闹矛盾怎么办?现实问题。”
在养老院里,老人们从不互相询问儿女来没来。这是一种忌讳。如果没来,人家心里不舒服,如果来了,你家的没来,你自己不舒服。“说句良心话,盼着他来,又不盼着他来。”鲍勃又说,“养老院这些老人,都恨不得自己的孩子来看看。”
“所以说,孤独,我宁可自己咬牙,我就面壁思过,电视开着,演的什么不知道。我就敢面死过去,我也不想(打扰儿子)。”鲍勃说。
在养老院里,或者养老院之外,老人们的需求总是很简单,但也最难满足。陈卓为老人们构建了一个乌托邦,或许这个乌托邦也是属于观看视频的年轻人的。但在乌托邦之外,老去就是老去,老去本身无法被浪漫化表达。
坐电梯的时候,我遇到一位被护工推着的老奶奶。她坐在轮椅上,头发近乎全白了,背有些佝偻。她自下而上盯着我,时间久到让人有些尴尬。她缓慢转头,向身边的护工说了几句,声音微弱,然后继续看向我。
护工向我翻译,“她说,你长得像她儿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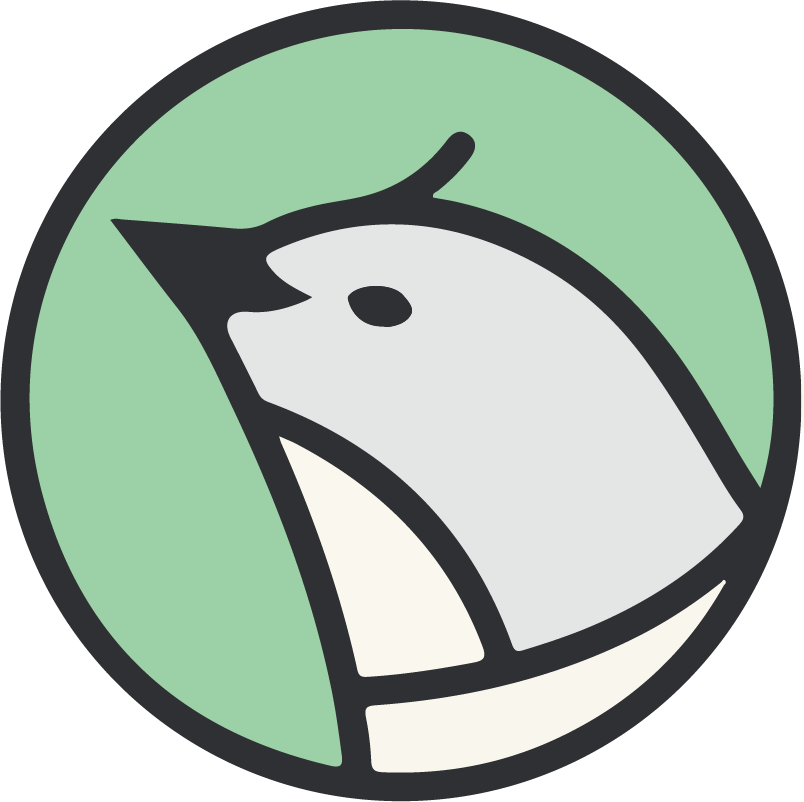 (来源:腾讯新闻)
(来源:腾讯新闻)
◦ 图片均来自作者。
*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为了不错过每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将谷雨实验室设为星标🌟哦,期待每次第一时间与你相遇!
关键词
老人
养老院
时候
老人们
就是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