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在义乌,日结向左,直播向右|谷雨

作者| 肖途
编辑 | 张瑞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高薪挑战
这真是一家空空如也的招聘网点,一面没有贴满招工启事的墙,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一个搓手御寒的中年男人在里面踱步。“想找什么工作”,他说不用手续费。
多绝望的求职者才会在这个看上去只存在于上个世纪的地方找工作,而我是第十六个。
中年男人让我填写求职意愿,在包装工和质检员旁,我还写下主播。中年男人拿起登记薄,满怀信心地说,很快就会有人找你。
那时,我已经在义乌呆了十天。我住在朋友K位于外环的房子,这里因为有大大小小的加工厂而被称为“厂区”,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其中一间PP棉加工厂做计件工。第一天,一个女工向我示范,将3克棉花、两种胶布塞进包装袋,扯下防粘条裹紧,然后扔进桌边的空纸箱。她对我说:“这个(活)傻瓜都会做。”她能一天包完3000个棉花包,折合成薪水150元。而我从早到晚只包了1000个,拿到50元。
我包棉花的工作台,这份工作只能500个起包,要么包500个,要么包1000个
我还体验过质检员的工作。K的母亲在离住处2公里外的出口贸易公司当质检员,我和K有时会在周末去帮忙。这是一家专门出口日本的商贸公司,我们剪掉衣服上印有中文字样的标签,或是用空白的贴纸隐掉中文说明。虽然岗位是质检,但除了不要弄错鞋码的标签,我们没有任何动作是为了检查质量。
在义乌,我干的最后一份日结工是包发夹,一包7毛钱,比包棉花(5分钱)划算,但包发夹把我手包肿了,我开始琢磨找一份新的工作。在义乌,我在不同场合见过拿着支架对着手机滔滔不绝的人。直播电商卷过这座城市,在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留下招主播的启事,就连烧饼摊上也没有错过。如果说厂区里的计件工代表着“旧义乌”的底色和韧性,那么直播电商就回荡着“新义乌”的喧嚣之声。再粗心的人都会发现这座城市的变化,比如四年前冒出来的北下朱直播电商小镇。
包发夹,把三个发夹夹在纸板上,每12个纸板一包,7毛
于是,我在中年男人那里留下求职信息,他言之凿凿,但当然没有人打来电话给我工作。
我在主流的招聘软件上搜索主播,就薪资而言,工资在5000-20000之间。我任意点开一条,岗位要求是吃苦耐劳,学历不限,经验不限。更寡言的招聘者只留下“直播带货,有老人带,想要高薪的来挑战下”。我随机发了几个沟通邀请,附上了两张我最体面的照片。收到的第一个回复是,“你身高体重多少”。回过去自己的信息后,招聘者遗憾地表示,他们对主播的要求是100斤以下。我点进招聘信息发现,这个岗位招的是穿版主播,就是在直播间里展示服饰穿戴效果的人,招聘要求里有明确的体重要求,80-100斤之内。按照要求只有微胖服饰可以接纳我,他们写着“体重在100-140,身高165cm以上”,长得矮也不行。
好不容易,有位粗心的招聘者答应让我去面试。这家招主播的公司位于义乌市郊的苏溪镇,以制衣闻名,直播间就设立在服装工厂的生产车间里。
招聘者让我试穿他们最小码的样衣。我问他,为什么要求主播的体重在100斤以下,消费者不是个个都苗条。他拿出手机给我展示模特图,“我们想要这个效果。”图片上的女孩把运动风的套装穿得松松垮垮,我猜她不会超过90斤。另一种女孩把紧身套装穿得凹凸有致,没有一丝赘肉。没错,在购物时,模特的穿着效果是我的主要参考标准,但不代表人人能像严格身材管理的模特一样穿得合适,我不想跟招聘者讨论“身材羞耻”的话题,因为他主动告诉我退货率是60%。我想这说明了一些问题。不出意外,我穿不下S码的衣服。
放弃穿版主播的岗位后,我在一家卖拖鞋的公司接受培训。第一天,老板张总带我到直播间,一位女主播正对着一面巨大的镜子介绍拖鞋,她的激情就像有一万个人在翘首以待,实际上只有镜子背后的我,和直播间里200个在线观众。张总向我介绍,镜子是他研究出的辅助工具,主播可以看到自己的状态,还不容易在来回看摄像头时让观众觉得主播在翻白眼。
这是一个24小时直播的账号,业内叫“日不落直播”。卖得最好的单品是定价9.9元的棉拖鞋,我看到前一天的成交总额是20万左右,结合实时在线人数,平均每10个人就有一个人下单,而综合7天的退货率不足10%。张总自豪地说,夏天洞洞凉拖一天最多能卖100万。我不明白怎么有那么多人买拖鞋,我的凉拖穿了5年都没坏。张总的解释里有着小商人的直觉和消费者的质朴,“你不可能带一双拖鞋去打工吧。”
干呕的主播
张总绝不会告诉我关于成本的秘密,他只说:“市场是畸形的。”安徽人张总在3年前来到义乌开始做直播电商,那一年直播电商的商品交易总额突破万亿元,他是赶上风口的一批人。他讲述自己的故事是从身负50万元债务开始,自己做主播卖出了第一个爆款,做成一个百万粉丝的账号,之后就一路顺风顺水,扩张规模,招募团队直到现在。他坦率地说,初中毕业就没有再上学,做过销售,开过网店,吃了很多苦……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桌上的保时捷车钥匙说明了一切。
接下来的几天,我在主播们的休息室里背话术。即便我常常走神,也不难发现所谓“直播话术”就是不断地说谎。“今天最后一波福利价格,两分钟后截单了”——每2分钟重复一次。“三层加厚的羊羔绒”——人造纤维,和羊没有任何关系。“4.0版本的实心橡胶大软底,三五年不断跟不断底”——被展示的样品鞋底已经开裂,4.0版本的说法用以替换掉之前“真正的4cm鞋底”,因为出于成本考虑,已经做不起厚底。办公室里堆成山的退货是证据。
直播间的背面是不同版本的拖鞋,张总早期卖过鞋底最厚的版本,现在卖的是薄的
主播们教给我的话术只有两页纸,3分半钟的内容,但购物车里有数十款产品。主播们告诉我,义乌的直播都只卖单品和爆款。所以,虽然有玲琅满目的拖鞋,但她们只喋喋不休地来回介绍1号和2号链接。这和动辄介绍几百个产品直播间的盈利模式不同,不依赖主播影响力,不用花高昂的费用购买流量,而是利用24小时的直播时长抢占平台免费流量。张总曾告诉我,流量好的时候(自然流),放只狗在直播间都有人买。说到底,我们主播的存在就是比AI稍好一些的工具人。更关键的是,单品的进货成本低,也无需依赖固定的工厂,只要单量足够大,就会有工厂找上门,况且品控要求不高。单品模式是一种草根生意,和义乌的很多生意人一样,不需要你是一个厂二代和富二代就能开始。
这间公司有12位女主播,虽然职位描述中不曾写到只招女性,但主播多是女性。张总告诉我,直播电商的消费者主要是女性,女主播更懂消费者心理,就像传统零售业的女售货员。但他没有提到,在女主播为主的行业,李佳琦这样的男性才是其中翘楚。我们这个公司的基层女主播,有小学语文老师、短视频演员、电商客服、娱乐主播、护理专业的毕业生,被三年前一阵无形的大风卷到了这里。
主播们休息的时候常把婚恋当作闲聊话题,如果你不主动说起,她们绝口不提过去,每份工作都如此短暂,人们不在工作中交朋友。一个女主播说自己最近掉头发厉害,另一主播随口问她原因,她就把自己即将结婚的烦恼倒豆子一样说出来。她的父母在年初给她找了一个同乡相亲,对方在见面两小时后就问她要不要订婚。她连对方的样子都记不住,但对方说,相处不合适可以退婚,所以还是勉强订婚。她不确定要不要嫁给这个人,但她已经29岁,在长辈的催促下,他们一个月后就会结婚。我问她结婚对象是怎样的人。她显得十分不满意,个子比她高一点,但是个大胖子,家里条件还没有她家好,但对她言听计从。我说,那为什么要嫁给他。她像是没有听见,她说,她发誓结婚5年内绝不要孩子,“生个孩子两三年没有办法工作,到时候哪还找得到工作。”她很勤奋,上一份主播工作的时长不多,她还找了一份夜班主播的兼职干。她希望在自己能赚钱的时候多干点,“谁知道主播能干几年”。过了几天,我又碰到她。她说自己刚打了除皱针,兴高采烈地为婚礼做准备,半个月的时间拍婚纱照,找好婚庆,一切都很仓促,因为她想少请几天假,预备过完年就恢复工作。我总算明白为什么人们不谈真正重要的话题,他们只需要一些情绪,而不是建议。
有几天,东方甄选的主播董宇辉是热门话题,我顺口问休息室里躺着看手机的主播,职业目标是什么。对方很犹豫地告诉我,人人都想成为董宇辉或者李佳琦,她从前也这么想过,但那需要一些复杂的手段,资本的推动、运气。拖鞋公司的主播都对现在的工作感到满意,她们一天工作4个小时,每个月有2天休息,薪水是一万元的底薪加上提成,按照总成交额的0.1%算,一个月能拿到几千块。就连我,一个新人主播,张总也大方地开出8000元的底薪。这是我在义乌面试过的直播公司里得到的最高待遇。
主播的工作看上去比包棉花轻松多了,可以说,除了当老板,这是义乌最高薪的工作,但我不能假装辛苦的劳动不存在。每个主播的嗓子都是哑的,她们告诉我,“公鸭嗓”是主播的职业特征。一位主播在连续说了3个月同样的话术后,在直播时发出了干呕。前不久,她介绍拖鞋时又一次干呕。主播们被要求在两小时内将同一套话术说34遍,每一次重复都像第一次饱含热情地手舞足蹈,我光是看着都累。只有金钱为这份工作缔结了稳固的关系,虽然抱怨,但没人想过辞职。
一周后,张总考核我的时间到了,我表现得很差。虽然我努力去模仿其他主播的语气,但说出来全变样了。张总说,没有人会下单。
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在义乌,我听到许多暴富的故事。比如,一位市场的送水工,他每送一桶水只赚2块钱,但他会留意哪家的生意好,后来他发现了医疗配件的商机,发了财。还有一些以负债开头的故事,就像张总,最后都是苦尽甘来,赚了大钱。但只要我问做生意的人,今年过得怎么样,他们就会说,今年生意不好做。好像失意的人都去开滴滴了,我在搭车时遇到了几位负债的司机,其中一位告诉我,他和妻子统统是失信人。他的三家餐饮店在熬过疫情三年之后还是倒闭了,他不仅亏光所有积蓄,还把全部的房产卖掉了。妻子和朋友合伙在拼多多上开店,光是仓库就租了上千平米,挺了两年,债务比他还多。一想到欠了还不清的钱,他就没法睡觉,只有开车后的疲惫能治好失眠。
市场卖衣服的老板没事干也会做计件活,
她在给耳钉套针帽
我在常去的咖啡馆认识了刘哥,他自称“贷款中介”,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最了解老板们经营状况的人。刘哥的工作是给小加工厂老板放贷,过程常常是一位急需用钱的小老板找到他,他根据客户的信用向银行递交贷款申请,一个星期后银行给客户放款,他收取佣金。虽然刘哥说自己的职能相当于银行的外包业务员,但没有哪家正规银行有“中介”的职位。
放贷的关键在于关系。刘哥和银行的信贷经理建立友谊,他将佣金的大部分献给对方,以获得客源,也就是那些被银行拒绝的客户。大部分小老板不容易获得贷款,他们的经营规模小,流水达不到标准,就算银行降低门槛,也很难在短期内拿到钱。但贷款的老板们往往急需用钱。刘哥解释道:“如果一个老板接到了大单,他的生产规模达不到,账上也没有钱来买原料,他做不做?他肯定要做,还要借钱做,谁有钱不赚。”有了关系,一切就好办了,那些资质不够的老板能拿到高于银行信用评级的贷款金额,还能在一周内收到钱。
我住的厂区常常可以见到晚上还在干活的小加工厂
刘哥每天到咖啡馆报到,他不时举着手机支架到室外录上一段介绍信贷业务的小视频发在朋友圈和抖音,他和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聊天,挖掘潜在客源。他告诉我,现在一个月能贷出去100万都算是好的状况。六七年前,他在义乌做P2P网贷业务,手下最多有80人,一个月最多能放出2000万。但两年后,这种贷款形式被取缔,公司原地解散,刘哥作为主管在派出所扣了一天一夜,出来后他就离开了义乌。2021年底,他回到义乌,开始做银行直贷的助贷业务,他发现连愿意贷款的人都不多,贷出去的钱也都是30万、50万。我找出一份高校对义乌的调查报告,上面整理了义乌海关公示的2020年-2023年前三季度的数据,我告诉刘哥:“报告上说,三年疫情义乌市场全球性辐射能力的韧性经受住了考验。”他推开了我的电脑。
我想他的意思是与其看数据,他更相信自己的观察。刘哥说现在越来越难,“赚不到钱”,但不肯透露自己的收入,他只告诉我他的手续费是3%。他说,经济状况好的时候,人们有信心贷款,因为觉得自己能赚回来,但现在的贷款人都是被动的,“最多的一类客户是做了一两年没有赚到钱,他又不肯放弃。贷款是和未来博弈,让自己今天能活下去,明天才有机会。”
人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我常常被问到为什么要来义乌打工,我准备了两套话术。一种是说,我来义乌找朋友,没事做就找点活干。另一种是,我逛了义乌的各种市场后,震撼于里面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货物。十几元一双的鞋,五元一条的牛仔裤,一元的帽子和围巾,耳钉和发夹像炒货店里的干果被堆进格子柜,从几公里外的工厂被日夜不休的制造出来,又像破烂一样按重量收到库存市场转手卖去对潮流不敏感但对价格敏感的县城,在直播间里滚动轰炸。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认为找份工作是最直接的了解方式。
义乌市场
但我一般只说第一种理由,因为解释成本更低。后来,我发现在找工作时,这点担忧是多余的。每一次可以被称为面试的谈话中,老板们只象征性地问我的工作经历,说明完薪水和工作时间就问:“能干吗?如果能接受就开始。”
如果说生产和销售也需要激情,那么义乌就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地方。这里讲究实用和效率,每个人既为财富做梦又为财富行动,在包棉花的工厂,老板的女儿开着凯迪拉克到来,然后和我们一起坐在工位上操作压缩机。一个河南女孩曾经在流水线上工作,她在一间黑屋子里检查显示器的分辨率,看亮着的显示器在眼前流走,工作清闲,但她受不了黑暗和孤独。于是来到义乌打零工,但包完500个棉花后,老板问她第二天会不会再来,她干脆地说:“不来。”第二天她就找到一份时薪19元的工作,还包一顿饭。在简陋的氛围中,仿佛一切都可以随时开始和结束。就连面试主播时,招聘者都对我说:“假如公司没了,你出去再找别的。”
五爱库存街是库存尾货市场,但在一筐耳钉里,
我还翻到前不久在小红书上看到的款式
在义乌,工作和生意就是这样变动不居。但我不能说一切都如此,至少打工者的工作总是机械重复,无论是主播们干呕着直播,还是棉花厂的工人将包棉花的工序一天重复3000遍。
每个打工人都要扮演好工具人,他们被要求像一台不必休息的机器一样高效、准确,那为什么不能让一台真正的机器来干?我曾在一间智能化的便利店打工,我了解人工的价值在于灵活性,但包棉花的工作完全不需要。我把问题转述给在义乌做外贸员的朋友K,她的工作常需要对接玩具厂完成订单。她告诉我,大型玩具厂包棉花的工作早就由机器完成,但问题是大型玩具厂不接数量小的订单。被拒绝的订单流向小型加工厂,不需要过多的机器,依靠廉价的人力灵活经营,我一刻不停地包棉花,这个动作不仅意味着无技术门槛的工作不值钱,还表示在灵活的商业模式中,总有人要做机械而疲累的工作。
和义乌的生意人打交道越多我就越疑惑,我为了一个繁荣的市场而来,抱着说不定能找个生意做的心思,但这里的人告诉我的却是他们的艰辛。我在义乌见过各种政府宣传欠薪维权渠道的横幅和海报,它们不仅出现在厂区还有高级写字楼里。我遇到的每个主播都遇到过倒闭的直播间,运营卷款跑路、老板嫌累不想干了,更多的是做不下去关停的。一位主播告诉我,公司倒闭前没给她结算提成,这不在劳动保障内,她只能认倒霉。当我问她,如何判断一家公司是否稳定时,她断然回答我,“干这一行就不要想稳定了。”
连已经发财的张总都说,生意不如前两年好做,但他还能暂时靠薄底子拖鞋来控制利润,所以没有影响他在新工作室里为自己装修“董事长办公室”的热情。人们说着一年不如一年,但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好像只要在义乌,就是安全的,永远可以和未来搏一搏。
直播不能停
离开义乌的前一周,终于有位老板通过招聘网点联系到我,给了我一个面试机会。公司在北下朱,一进门我就闻到满墙隔音棉散发的气味,接待我的人说,他们才搬来义乌两天。随后我就看到一位电信公司安装宽带的员工找老板结钱离开。办公室坐着5个人,他们都是这家公司的经理和主管。听到我是新人后,他们好像很开心,“那你来对地方了,我们不仅教你怎么直播,还给你每个月5000块钱和提成。”然后指着角落里的人说,“她花了7000块钱去上直播课,还不如在这里播一天。”被指着的女人对此表示赞同,她告诉我,来这里的每一天都很开心,她有严重的抑郁症,现在都减药了。她向我展示完手上被割伤的疤痕,就带我参观直播间。
新人主播去上电商课的资料,
虽然她说没什么用,但也没丢掉
这家公司的品类是油锯,用于伐木和造材的五金器械,可能对普通人最直观的联想,是《电锯杀人狂》中的凶器。她打开一扇直播间,一个看上去超过50岁的大爷对着手机说着“老铁们”,他面前是一地被排列整齐的器械。他是我在义乌见过年纪最大的主播。女人告诉我,油锯公司的直播分为露脸和不露脸,她和大爷都是不露脸直播的,但她偶尔会在镜头前展示拉油锯。说着,她就要到另一个空着的直播间里拉给我看。油锯不规律地响着,我真怕她伤到自己,但她说很喜欢拉油锯。
老板终于出现了,他领我到写着“总经理室”的房间。他问我,之前是干什么的。我说,做文字相关的工作。他用了然于胸的语气地评价,“赚不了几个钱”。他又把主播工作的好处说了一遍,免费教学和发工资。接着他介绍了这家实力雄厚的公司,20年经验的五金制造工厂,在东阳、义乌、金华和山东都有直播基地,如果我去东阳还可以包食宿。我问他,每天能卖多少。他说,直播业务刚开始做,一天也能卖十几万,但油锯这个赛道的竞争者少。言下之意是做到头部很容易。我不小心在办公室参观时看到直播后台上的数字是1万出头,退款是7千。他问我,要不要干。语气好像只有傻瓜才会拒绝这么好的工作。我说,我考虑考虑。回到大厅,先前接待我的人拿着相机在拍产品图,他让我拿油锯试试,我举起十几斤的油锯,他说这样很好,给我拍下一张照片。
我再没有遇到比油锯公司更奇怪的直播公司,说谎的总经理(当然所有的老板都说过一些谎)、一箩筐的高管、有抑郁症和超过50岁的主播,但每一个人都表现出一种昂扬的信心,我只在电影里见过。几周后,我在老板的朋友圈里看到一连串的视频,用宏大的开场曲展现出这家公司的蓬勃态势,好像没有人能阻止他们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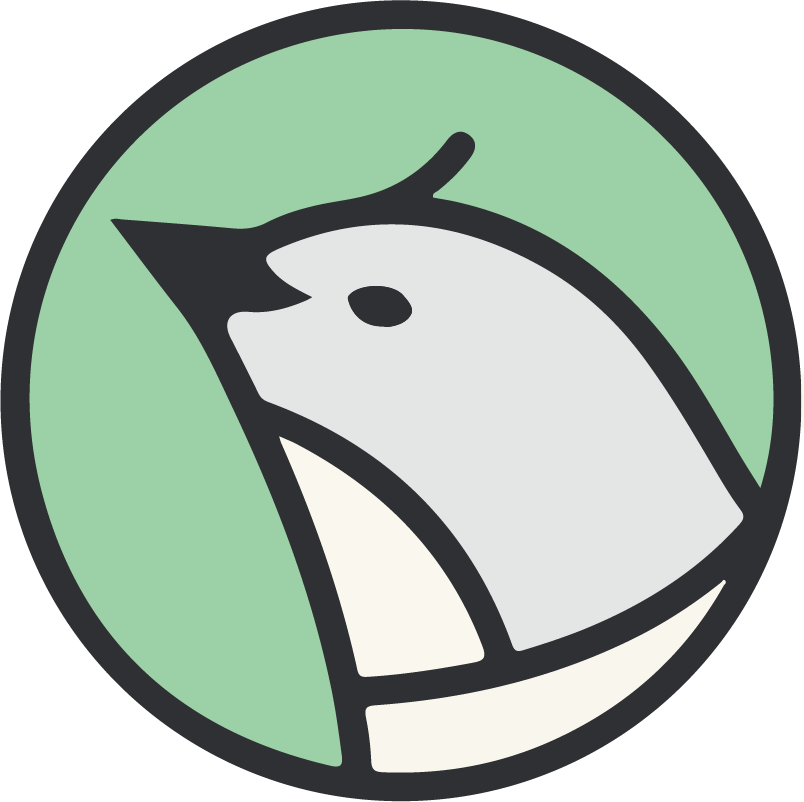 (来源:腾讯新闻)
(来源:腾讯新闻)
◦ 插图均来自作者,头图、封面图为AI作图。
*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为了不错过每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将谷雨实验室设为星标🌟哦,期待每次第一时间与你相遇!
阅读原文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