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上的山里娃,和毛不易“写年” | 谷雨

作者| 语冰
编辑 | 方奕晗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如果故事以“95后回家乡支教”作为开头,就难免陷入一些庸俗的框架。比如,在艰苦环境里励志的故事,乡村教师李柏霖凭借一己之力带学生们办起了一个诗社;再比如,逆袭的故事,这个既不“骨干”也不“先进”的姑娘,带着她的学生们出现在春晚舞台上,和毛不易一起表演节目。故事的结果大同小异,屏幕内外的人,陷入短暂又匆忙的感动。
春晚歌咏节目《如果要写年》
毕业6年,乡村教师李柏霖不觉得是在坚持。教孩子写诗的一开始,她只是为了提高他们的语文素养,以诗歌作为方法。写着写着,她被他们在诗里自由的创作和表达感动。
六七年的时间,一层质疑黏着一层质疑,李柏霖总要回答同样一个问题,“写诗有什么用”。
说环境不艰苦都是假的,山区的风,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李柏霖脸上留下痕迹,青春痘叠着青春痘,山路连着山路,困难接着困难。我问她,来这里教书甘心么?她说,刚开始,看着同学在市里逐渐成为教学骨干,而她还在一点点纠正孩子的坐姿、带他们梳理知识结构,并且发现没什么效果时,说不焦虑也是假的——她因此陷入一段漫长的自我怀疑。
李柏霖与孩子们 ©李柏霖
李柏霖曾布置过一个阅读作业,让孩子们把视频发在群里。手机画面的背景是他们各自的家,昏暗的光顺着木质房子嘀嘀嗒嗒地流下来。李柏霖发现,对这片土地背后的肌理,自己的理解还是太浅了。
村庄皱巴巴的,是一个留不住爸爸妈妈的地方。它的官方名字,叫会同,隶属于湖南省怀化市,新闻里对它的印象是,有很多留守儿童、一个刚刚摘掉国家贫困县的地方。大人们像候鸟一样,飞到浙江,或者更远的广州,再在一些被称为年节的日子里,匆忙地飞回来,短暂停留。大山里流淌着多重时间,孩子们漫长的成长时间,和爸爸妈妈在夕阳里飞快穿梭的时间。
一次,快过年了,李柏霖让孩子们给大人写一封信。在一堆歪歪扭扭的字中间,埋了这样一句话,“爸爸你不yao再打妈妈了如果你再打妈妈的话我就不要你zhe个爸爸了。”
逗号和童年一起迷失在这句话的世界里。李柏霖突然意识到,这些情景,正是他们的日常。有孩子会在课间,平静地告诉她,“老师昨天我爸爸去世了”。他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人们在这里被生死和宿命抽打,这是他们正在经历的最真实粗砺的生活。
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像野草一样生长。等待幸福的过程太乏味,而困难又是那么寻常。只有诗歌是个意外。
山上的云好看,在天空突然聚积,一朵挨着一朵,金光和红光在上面翻滚追逐。李柏霖把孩子们带到大自然里,让他们观察,记录下今天值得记下的事。有孩子写,“在黄昏下,我伸了伸懒腰,趴在奶奶背上,黄昏学着我的样子,也伸了伸懒腰,趴在了山上。”
央视导演被“黄昏趴在山上”的句子戳中,把夕阳、月亮,和老师孩子们一起,打包带到了春晚。
月亮怎么不见了?
春晚导演第一次去会同,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施工队横七竖八地驻在学校里,校门口堆着铁皮,身高不足一米的小女孩,穿着自己身型一倍半的衣服在学校里逛。茶话会上,孩子们在抢板凳,一个小男孩摔到地上,板凳被其他同学抽走了,周围乱糟糟的,但他一直在笑,豁着一颗小虎牙。导演们被这种自然喜悦的生命状态吸引,告诉他们,或许可以上个节目。
那个节目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春节联欢晚会》。在这个被数亿人关注的舞台上,李柏霖要带着孩子们,和歌手毛不易一起,表演一个叫《如果要写年》的节目。
《如果要写年》©春晚剧组
最开始的创意,来自传唱颇广的一首歌《如果你要写风,就别只写风》。歌词写道:如果你要写风,就不能只写风,你要写柳条轻轻柔柔飘入你心中,你要写纸鸢摇摇晃晃飞舞晴空中。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句式,创作一些关于“年”的表达?这个创意最开始被推到春晚技艺节目组组长毕波面前时,他有点拿不准,觉得艺术性不太够。于是导演组找了身边的小孩,加了一些小朋友念的还不错的关于年的诗,插到demo里,“有了那么点意思”,节目被保留下来。
海选从10月持续到12月,导演组从各地学校收集了一万多首诗,它们整整齐齐地趴在执行导演何中石的excel表格里——他也因此被同事嘲笑是干统计的。
在这三个月里,何中石一直在避免把学生当成学校的宣传工具。春晚的总导演也跟他提过,在创作过程中要考虑清楚一件事,这样的节目到底能带给孩子什么。
李柏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她的答案是,希望孩子们可以被看见。班级里有从外校转过来的小孩,刚来的时候,天天欠作业。李柏霖读到他交上来的诗,他说,影子是一个特别粘人的家伙,踢它打它都不会走,“我想要影子这样的好朋友。”
转校生的融入是漫长的跋涉,李柏霖从诗里读到了孤独。她把这首诗在讲台上读了5遍,带着大家一起读。那个男生的脸,嗖地一下红了,第二天,好久没写的作业主动交了上来。诗歌发表那天,男孩高兴地和老师说,如果写诗都可以的话,我也可以写故事,还能做好多别的事。
这里的孩子往往承担着很多年龄之外的责任。比如,要照顾六七十岁的奶奶,要照顾刚学会走路的弟弟妹妹——生活的重担,理直气壮地压在他们身上。在新闻报道里,他们被统称为“留守儿童”,他们的“被看见”,也往往带着同情、怜悯、审视和高高在上。而李柏霖想要的,是这些孩子“可以作为熠熠生辉的个体被看见,而不仅仅是同情”。
毕波导演对我说,他印象最深的一首诗是《月亮怎么不见了?》“你知道么,在大年三十这天晚上,是没有月亮的。”他说自己活了30多岁才发现这件事,这群孩子,在十多岁的时候就观察到了。
关于月亮去哪儿了,孩子们给出的答案是,在这一天,“月亮被新年请来当灯笼了”。
观察月亮,是大山给这个距离县城6小时车程的小学校,最最慷慨的礼物。夜里的操场,一抬头,一整片星空都是你的,可以慢悠悠地看时间从头顶划过。中秋节那天晚上,李柏霖带着孩子们出去玩,他们在后面一边蹦一边叫。有女孩看到月亮挂在天上,想把它摘下来尝一口。但遗憾的是,她觉得不好吃,又放了回去。
从一万多首诗里,李柏霖和她的学生们脱颖而出。导演组又让他们以“年”为主题,创作了几首诗,用在节目里。
就这样,李柏霖带着12个孩子,坐了六七个小时车,从会同来到北京。
孩子们在春晚后台 ©何中石
水土不服混合着来到大城市的兴奋,把孩子们砸晕了,有的人还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流鼻血。央视演播厅太大了,一开始,他们找不到机位,坐在凳子上一声不吭。让他们对着镜头笑,一个孩子笑着笑着就哭了,李柏霖赶紧问怎么哭了,孩子说,我笑哭了。
舞台好大,他们不知道该干嘛。
何中石试着让孩子们和台里的哥哥姐姐打招呼,带他们去自己负责的另一个节目《看动画片的我们长大了》的后台去串门,努力让他们和现场建立连接。他问他们,长大了想做什么?有人说,想当飞行员,有人说,想当画家,有人说,想当设计师。现场的一些叔叔阿姨很开心,告诉他们,自己就是设计师。
《如果要写年》是春晚上的一首歌,毛不易在前面唱,孩子们和李柏霖在舞台上表演。为了适应表演节奏,李柏霖带着他们做游戏。规则是,嘴要闭上,通过动作和眼神来告诉别人自己要什么。他们慢慢发现,原来不说话时,还可以用身体和眼睛表达自己。
李柏霖与孩子们在春晚舞台上
孩子们写的关于“年”的诗,也被做成立体书,在节目中展示。这是一个很少在电视上呈现的道具。但负责节目舞台呈现的视觉导演江宇昊觉得,他们日常写诗就是写到本子上,与书的形象很贴合,也可以让诗和歌里的所有意象,都有立体化的呈现。于是江宇昊找到给《宝莲灯》设计立体书的岳向辉,花了半个多月,立体书被做了出来,上面一页一页都是孩子们写的诗,包括那首《月亮不见了》。
这本书有二三百公斤重,从通州运过来,一路上免不了磕碰。又要把它搬上舞台,装上轮子,让孩子们可以拉动。要不要减配重?要不要多加一些轮子?道具来来回回磨合,每次排练之前,都要花大量时间检查,是不是一下能拉开,孩子能不能拉得动?
排练了一个多月,节目、人、道具,反反复复地调,舞台地屏还被压碎过好多次。何中石向我形容,屏幕碎一次,心也跟着碎一次,“十五六次吧”。
至少,我们可以做一个
把春天带给别人的人
写诗的故事,是从“棉花吐出了丰收”开始的。
二年级的语文考试,李柏霖让孩子们写比喻句,要对“葡萄像一串紫色的珍珠”进行仿写。
有孩子写,“棉花吐出了丰收”。这不是一个标准意义的可以被判为“正确”的答案。
“谁能觉得丰收是棉花吐出来的?”李柏霖反问,它白白的、胖胖的,一张嘴,什么都被它吐出来了。
在试卷上,李柏霖打了叉。但后来,她把这句话抄在黑板上,让大家读,说写得好,说离开了这个题目,这句话值100分。
“棉花吐出了丰收”像一颗石子,击中了湖心,让李柏霖看到孩子们藏在水面之下的想象力。涟漪就是,她开始教孩子们写诗,把它当作提高语文素养的一个抓手。
写诗还是从仿写开始,但这种方式很快被李柏霖抛弃。仿写只能跟着别人的思路去写,她不想这样。
她带孩子们读诗,读胡适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告诉他们大诗人也会写这样的口水诗。她想让孩子们知道,写诗不是那么难的事,那就试一试吧。
还是写不成句子,那就把课堂变成主题课。比如春天,李柏霖让他们依次说春天的特点,有人说春天是唱歌的蛐蛐,有人说春天是散发香气的桃子……到后面,一些有趣的词开始蹦出来,有人说,春天是刚睡醒的桃花,还有人说,春天是浑身是汗的爷爷。
一些班级之外的孩子觉得好玩,也加进来,李柏霖索性弄了个诗社,一开始20多人,后面变成40多人。
李柏霖希望他们能从日常琐碎中,捡拾起美好的碎片。她写过一句话,说她喜欢秋天里,太阳落下的时候,像天空角落挂的红灯笼。她读给孩子们听,让他们也去秋天里,去找最能代表这个季节的东西。孩子们找到了天空、河流,还有枫叶,把时间和季节,凝固在巴掌大小的叶子纹理上,说秋天的落叶,像一面红色的镜子,照着春夏两个季节。
学校后面有片小树林,李柏霖鼓励他们去找落叶,把诗写在上面。于是有人找到了一团燃烧过的芭蕉叶,歪歪扭扭的黑色的字,在上面蜿蜒地爬,“小小的叶子上,睡着一只毛毛虫,睡着睡着就有蝴蝶飞出来了。”
也有孩子写,“我是一棵树,只有叶子陪我,到了秋天连叶子也陪不了我。”
孩子们在落叶上写诗©李柏霖
“现在是谁在家里?”李柏霖找到写诗的孩子。
孩子低着头,搓一搓脚,“爷爷和奶奶在家,爸爸妈妈打工去了。”小女孩几个字几个字地往外蹦,这是她能说出来的最长的句子了。
诗歌成了情绪的晴雨表,李柏霖会根据孩子们的情况,设计一些游戏。在搭桥的游戏里,几个人并排在一起,组成一座桥。哪座桥最先摆到操场的另一边,他们的队伍就赢了。这个游戏要相互配合,孩子们尝试着迈出关于友谊和合作的第一步。
诗歌越写越好,里面也装下了越来越多的字,和秘密。
孩子们的诗 ©李柏霖
李柏霖有一个什么都知道的纸壳箱。孩子们写在本子上的诗,撕下来,参差不齐地折叠成小方块,塞给她。李柏霖挺开心,一抓一大把,放到箱子里。
“我每天都不想回家,因为家里有不爱我的后妈。”李柏霖读到这首诗,去和孩子亲妈沟通,说孩子挺想你的,说他现在特别不适应。妈妈这才有所觉察,时不时地把孩子接过来住。在妈妈家的那一周,小朋友会开心很多,李柏霖能感受到。
“我的妈妈很可怜,她没有房也没有车,但她还有我。”有人在诗里写。
生活的黑暗,似乎在一点点地变淡。
一个清明节,李柏霖收到一首诗,“奶奶带我去见外婆最后一面,那天我哭了,像被大火烧坏了眼睛,但外婆再也没有哄我。”外婆是家里唯一一个会把糖留给他吃的人,生活把外婆和糖一起带走了。
李柏霖知道,一些问题诗歌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诗歌解决不了。她只是觉得,如果现实一定包含一些黑色,至少可以改变看待和解释它的方式。文学,有时可以成为我们为数不多的武器。
有一个春天的故事,李柏霖挺喜欢,老讲给孩子们听。班里组织春游,有个孩子生病不能去,其他人有的带回来一片叶子,有的带回来一朵花,给那个不能去的同学。她知道,除了像铅一样沉重的黑,生活中还有很多温暖的力量,可以被信赖。
李柏霖对孩子们说,“至少,我们可以做一个把春天带给别人的人。”
坦荡地接受阳光,也坦荡地接受阴影
“你们觉得伤仲永,伤他的有哪些人?”春晚排练间隙,李柏霖把这个问题,抛给一起来北京的同学们。
有孩子说,是仲永自己,因为他放弃了学习。也有孩子说,是他的父母。
还有么?李柏霖问。
隔了很久,一个小孩说,“还有那些宾客。”
“对,请他去这儿去那儿的宾客,但是好像他们也没关心他究竟有没有进步。你们也是这样。”
春晚临近,节目表演完马上就要回去了。李柏霖担心孩子们见到了外面的世界,适应不了自己的小家。她更不希望春晚之后,孩子被当成频繁表演的工具,“还是要回到正常的成长上。”
见到李柏霖这天,距离春晚还有三四天时间,导演给他们放了假。毕波担心过度排练,孩子身上的纯真会被榨干。
在李柏霖住的宾馆里,她给我看手机里存着的一幅画,是班上同学画的大山。
山上,一层绿色交替着一层褐色,深浅不一地拼接到一起。
一座山,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颜色?画画的小孩说,绿色是爸爸的爱,褐色是爸爸的缺点,褐色很多,但爱会掩盖它。
孩子画的大山 ©李柏霖
“看待世界的视角变了,生活就会变得浪漫。”李柏霖解释。诗歌让孩子在不同的世界里短暂居住,告诉他们,怎么坦荡地接受阳光,也如何坦荡地接受阴影。
不少升到六年级的孩子,来诗社的时间变少了。留在家里上学还是进城去找父母,他们需要面临更严峻和逼仄的选择,未来要去哪里。
周末的时候,李柏霖买来空白风筝,让他们把理想写到上面。理想随着风筝,被带到天上。这个想法来自《红楼梦》,黛玉她们放风筝,风筝飞到特别高的时候,把它剪掉,烦恼就都被放走了。
孩子们把理想写在风筝上©李柏霖
在风筝上,有孩子写,想当老师,也有孩子写,想当宇航员,把诗写到太空里,让外星人也看见。
这些文字,被李柏霖一个字一个字敲在电脑里。她自嘲这几个月的word水平越来越高。投了几个出版社,没啥回应,她就自己把诗集打印下来,发给孩子。
李柏霖向我说起余华,那篇《包子和饺子》她一直记得。“我活了三十多年,不知道吃下去了多少包子和饺子,我的胃消化它们的同时,我的记忆也消化了它们。”
李柏霖努力记录下生活中这些“包子和饺子”,帮她和孩子们,对抗一部分“胃酸”和遗忘。
六七年的时间里,她总是不得不回答“写诗有什么用”的问题。有时质疑被简化为:“写诗可以提高成绩吗?”如果功利的看,写诗的孩子成绩不比别人差,甚至,他们的成绩变得更好了。但李柏霖始终觉得,成绩只是成长的衍生品,孩子成长了,成绩才会变好。
她知道,哪怕上了春晚,在这样的时代,写诗也不构成一个职业,更不能完整地养活自己。孩子们还需要迎接诗歌之外,更广袤的生活。“但如果有一天,他们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也在写诗,保存浪漫看世界的角度,这有多棒!”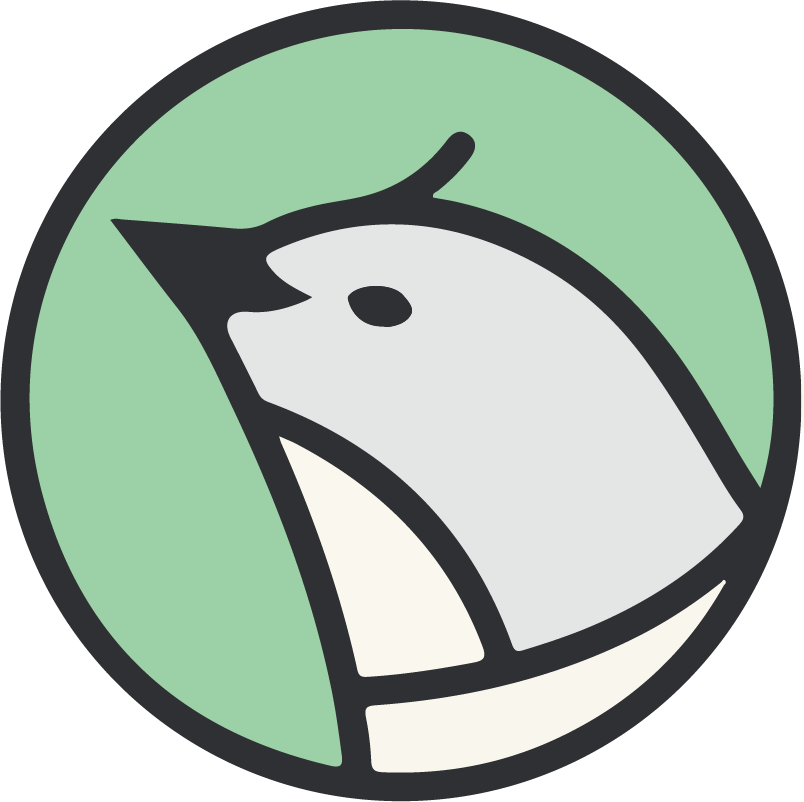 (来源:腾讯新闻)
(来源:腾讯新闻)
*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为了不错过每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将谷雨实验室设为星标🌟哦,期待每次第一时间与你相遇!
阅读原文 关键词
时间
一天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