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咨询行业的源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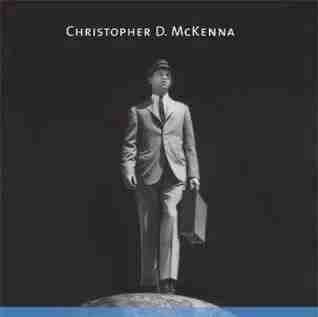
来源 | 陈果George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管理咨询直接源于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 W. Taylor, 1856-1915)发起的“科学管理”运动,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牛津大学副教授麦肯纳认为,它的起源完全不同。
19世纪末,美国大企业已经发展到需要外部建议的程度。这些建议大多来自大型银行,它们与企业客户的联系比今天的银行密切得多。他们拥有企业股份,向其借贷资金,并且经常在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有时还包括在董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银行开始雇佣专业顾问:提供工程咨询的化学工程师,如阿瑟·D·利特尔(Arthur D. Little),提供外部审计和财务咨询的会计师事务所,如安达信(Arthur Anderson)和安永(Ernst & Ernst)以及大型企业律师事务所。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和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成立终结了这一切,迫使银行在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之间做出选择,并切断了与企业客户的密切联系。1930年,大约有100家独立的“管理工程”公司(当时这样称呼它们),十年后,这一数字增长到400家。公司的规模也在扩大。
麦肯纳认为现代管理咨询行业发展的动因是 30 年代出台的银行分业法案,使得咨询服务脱离银行得以快速发展;上世纪初银行雇佣工程专业人士产生了最早的“管理工程师”,早期的咨询顾问(包括 ADL、麦肯锡、博思艾伦等)都具有会计和工程的双重专业背景。此外,对 IBM 反垄断法规限制, 还促成了IT 咨询行业。
法规推动专业服务业发展最近的例子,是 2005 年后的 SOX 404 意外推动了美国上市公司里ERP的深度渗透。
我觉得中国管理咨询和企业软件行业发展需要政策推手,实际上中国ERP 萌芽就得益于会计电算化的政策,然而,中国当前在反垄断、知识产权保护、扶植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的各种立法不健全,使得管理咨询和企业软件行业缺乏良好的土壤,例如,对企业技术开发外包形式的规定、对软件厂商的源代码权益保护、对企业软件的产品和服务的商务分离、对数据要素的产权归属确定等。
这本书其他内容还叙述了管理咨询公司在现代全球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今后继续分享。
知识经济 -
管理咨询的理论
◎现代管理咨询的先驱 George S. Armstrong
1930年,《商业周刊》向读者介绍了一种新的专业服务:管理咨询。正如《商业周刊》的作者所解释的那样,现有的商业专业人士体系已经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麦肯锡(James McKinsey)表示,一种新型的专业人士“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在增加……顾问告诉企业何时使用其他顾问。”尽管《商业周刊》继续记录管理咨询在接下来的70年里的兴起,但咨询师们很难向公众解释他们提供的是什么服务,尤其是当这个世界上最新的职业比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还要快的时候。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观察家们一再对管理咨询的增长感到惊讶。1965年,《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惊讶地评论说,每100名职业经理人中就配比了一名顾问。到1995年,这一比例达到了13比1。人们常常会问:“当每个经理都雇佣自己的私人顾问时,咨询业的增长最终会停止吗?” 如今,咨询师的数量之多或许令人吃惊,但当人们追随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观点思考“为什么要有管理咨询师”时,咨询师数量的相对增长就显得尤为有趣了。换句话说,高管们为什么要经常聘请外部人士就他们自己可能是专家的企业管理问题向他们提供建议呢?或者,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为什么高管们要聘请外部顾问来跨越公司的边界?
分析人士试图解释管理咨询的惊人增长,传统上把该领域的扩张与美国经济的整体增长、国际竞争的影响以及现代管理的复杂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解释并没有错——咨询公司在经济扩张时期兴旺发达,在经济衰退时期遭遇难过。但是,关于全球竞争加剧和管理复杂性的概括并不能完全解释咨询相对于其他管理角色的增长。例如,考虑一下一位知名咨询师对咨询业增长的解释:“你必须看好咨询业。它在变化中茁壮成长,而这是一个变化正在加速的时代。”对于1999年咨询业的增长,许多咨询师可能会同意这种解释,但这种说法在1969年也是正确的,当时咨询师说出了这些话。在此之前30年,也就是1939年,马文•鲍尔(Marvin Bower)重建了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mpany)。麦肯锡公司惊人的增长(1939年至1944年间平均每年增长47%),如果不是因为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中,对顾问的需求不断增加,以帮助高管们,那该怎么解释呢?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对管理咨询增长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对经济的外生变化和全球竞争的影响敏感,但学者们不能仅仅通过经济复杂性和全球变化来解释管理咨询的显著发展。相反,为了理解他们对国家和国际经济日益增长的影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咨询师存在的原因以及咨询师如何战胜他们的专业竞争对手。本书的后续章节将以这种方法为基础,描绘20世纪管理咨询兴起对制度的影响。在我描述顾问的广泛影响之前,我必须首先说明外部顾问存在的原因。
彼得·德鲁克的问题:“为什么会有管理咨询师?”呼应了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著名问题:“为什么会有公司?”这两个问题彼此平行,因为从本质上讲,它们挑战了经济学家的传统观点,即“企业可能被设想为市场关系海洋中,刻意协调的岛屿”。因为这两个问题如此相似,它们的解释也相互关联也就不足为奇了。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对自己问题的回答是,企业家创建公司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学家将交易成本定义为:管理相互独立的公司之间合同以及其他关系的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高管们如此愿意聘请外部顾问。正如科斯所言,早在管理顾问被广泛接受之前,企业不仅经常面临“制造还是购买”实物商品的决定,而且“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所有的建议或知识都是按需购买的。”就像驱动制造商从成本较低的供应商那里购买材料的过程一样,管理信息的供应商享受着大量的“知识经济”,而这些“知识经济”反过来又传递给了他们的客户。在交易成本的框架内,管理层在决定从顾问那里购买建议时,并不比决定购买机床而不是自己内部制造机床更奇怪。事实证明,公司的性质决定了顾问的性质。
外部顾问的效用
数千年来,行政管理人员一直聘请外部顾问,但他们的建议传统上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商业性的。正如弗朗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在1597年所写的那样,“参事与国王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说以国王忏悔的告解者的形式、被神圣化的政治顾问是司空见惯的事,而亚里士多德到伊拉斯谟等政治哲学家,也一直在警告过分信任外人是危险。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为政治顾问辩护的文章中指出,因为国王的行为而惩罚顾问参事是错误的,但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一直是现实主义者,他在著作中专门用了一章来讨论“在任何企业中担任参事的显山露水的危险”。包括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内的政治理论家在他的论文《论参事》中一直承认,尽管聘用外部人士存在固有的危险,但外部顾问为未经检验的想法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发声委员会。这种务实地接受顾问价值的模式,加上对其强烈政治性质的持续关注,已成为400多年来对专业和管理知识的看法。在战后的美国,政府资助的专家激增,历届总统创建了国家咨询委员会,如原子能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经济顾问委员会,尽管人们普遍担心这些专家服务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公众的利益。不管是好是坏,政府官员、非营利组织经理和企业高管开始依赖这些新的“官场”精英,尽管怀疑这些顾问的动机,但也勉强接受了这些专家的效用。
高管们已经接受了顾问的优点,因为专家已经证明他们能够掌握、操纵和扩展复杂知识的新领域。自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对劳动专业化进行分析以来,经济学家们就明白了知识专业化带来的经济利益。通过专注于一项任务,或者专注于单一的经典,那些专门化的人士可以享受个人的规模经济。尽管人们担心过度专业化,但即使在传统职业中,这种经济也很明显,因为官僚组织中的专家逐渐取代了通才。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最有可能大声疾呼要求通才回归的批评者,往往自己就是最高度专业化的专业人士。在这种情况下,使顾问与众不同的不是他们的专业化,而是他们继续独立于公司。
因此,让评论家们感到困惑的并不是外部顾问的功能,而是其形式。一般来说,批评者并没有问为什么高管需要聘请组织再造、信息技术或公司战略方面的专家,而是问为什么这些专家留在公司外部,而不是内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担忧反映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假设,用管理理论家约瑟夫·巴达拉科(Joseph Badaracco)的话来说,就是“公司有边界,而且应该保持清晰。”但是,即使公司逐渐形成了商业联盟,模糊了公司的传统界限,越来越多地使用外部人员也使大型官僚组织将管理咨询内部化的期望(在20世纪70年代被广泛预测)变得混乱。相反,随着外部顾问的使用增加,对内部顾问的需求却减少了。管理咨询公司的蓬勃发展主要是因为他们脱离了公司的传统界限。
与政治顾问不同,从19世纪80年代到50年代,早期管理咨询顾问不是作为告解者,而是作为公司的分包商。外部顾问为面临内部人员无法轻易解决的问题的组织,带来了其无法获得的专业知识。特别是,高管们根据两个截然不同的先决条件决定是否聘请外部顾问。首先,潜在的问题是简短的、专门的、不重复出现的,而对这个课题进行内部分析既缓慢又昂贵。其次,这些潜在的咨询师在之前的行业任务中有过类似案例的经验,要么是因为咨询师对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要么是因为咨询师曾为竞争对手进行过类似的研究。因此,在首要化身中,管理顾问是解决管理问题的主意或知识的经纪人,不是通过他们对不寻常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而是通过对已知问题的现有知识的应用和重新表述。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对管理顾问及其客户的研究总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客户主要是根据顾问在行业中的声誉和他们在类似任务中的经验,在竞标候选者中进行选择。例如,1958年,金融家兼外交官乔克·惠特尼(Jock Whitney)选择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mpany)而不是博思艾伦(Booz Allen & Hamilton)来重组《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主要是因为他的商业伙伴向他保证,麦肯锡通过研究《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和密歇根州的一家大型连锁报纸,“在报纸工作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通过他们内在的“知识经济”,这必然是基于他们作为局外人的地位,管理顾问为他们的客户提供了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在对相同问题进行同等的内部研究时,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管理技能、技术和过程。
当知识经济的收益超过外部合同的成本时,咨询师就会蓬勃发展。在每种情况下,高管决定是使用顾问还是内部解决问题,都取决于顾问的增量费用:对相对交易成本的估计。高管们面临着“自制和购买”的抉择,迫使他们在外部供应商的规模优势与内部管理的合同效率之间进行权衡。正如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在科斯(Coase)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的那样,组织之所以得以创建和维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内部化生产降低了交易成本,抵消了从外部承包商那里购买产品的潜在回报。如果大型现代公司可以被最好地理解为最小化交易成本的组织适应,那么咨询顾问代表的是相反的——一个尽管合同成本高、但仍然繁荣的机构。
因此,交易成本决定了咨询师的生计。实际上,咨询师是在管理/交易成本计算的边际收益中获得成功的。从制度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顾问对外部专业知识的增量销售是一种特别有效的经济结果,因为那些拥有更好知识的人可以很容易地“出售(他们的)建议或知识”,而无需“自己积极参与生产”。此外,用经济学家J·M·克拉克的话来说,因为“知识是唯一不受收益递减影响的生产工具”,所以向一方出售知识并不一定会减少,实际上可能会增加其竞争价值。在单一行业内反复传播管理最佳实践对顾问来说可能相对便宜,但对竞争对手来说却具有无价的战略价值。因此,考虑到聘用外部人士所固有的巨大优势,人们可能会逆转彼得•德鲁克最初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会有管理顾问?”,并反过来想知道,为什么大多数公司选择不把所有的管理问题分包给外部专家。
对于企业为何不将所有管理知识的生产、管理和传播都转包出去,最直接的答案是,独特的知识是企业在试图在市场中脱颖而出时,获得竞争优势的唯一最佳途径。在不断发展的“知识经济”中,如今被誉为最有价值的企业资产的知识差异化是必要的。
但是,对于企业为何不将其所有的管理知识转包出去,还有一个相关的解释,或许不那么明显:大多数企业也作为隐性(有时是显性)的客户顾问,在出售实物产品的同时,出售关键知识。公司不会把他们所有的知识生产转包给顾问,因为反过来,公司也经常充当顾问。因此,咨询师为企业客户提供服务所依赖的“知识经济”同样也被企业方所采用,比如他们向竞争对手授权新技术,教零售商如何推销他们的产品,或者向顾客介绍他们的产品。事实上,查尔斯·梅里尔(Charles Merrill)认识到,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的股票经纪人实际上出售的是知识,而不仅仅是股票;西格拉姆公司(Seagram)的高管决定向零售商传授烈酒的正确营销方法,这两个例子都是大公司通过将有形产品与无形建议结合起来销售有形产品的例子。企业高管,就像他们聘请的顾问一样,明白知识不仅仅是一种内部资源,也是一种外部产品。
近年来,大型制造和服务公司以顾问的形象重建一直风靡一时。无论企业高管是否效仿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mpany)对共享企业文化的重视,埃森哲(Accenture)在知识管理方面的技能,还是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Group)在团队合作方面的专长,管理理论家都将咨询公司誉为不断发展的知识经济中的终极机构。华尔街分析师尤其赞扬了IBM和EDS这样的公司,它们创建了成功的咨询部门,适应了新的全球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制造产品已经成为大路货,知识现在是最珍贵的产品。然而,这种企业转型引发了进一步的问题。如果说分析师们现在能更好地理解高管们为何聘用咨询顾问作为知识经纪人,那么他们似乎就不那么清楚,为什么咨询顾问会主宰这一至关重要的经济职能。如果外部信息可以通过任何制度渠道传播,包括行业协会、政府贸易团体、商业报刊、智库和专业网络,所有这些都享受“知识经济”,为什么在新的知识经济中取得胜利的是顾问?
作为卓越的知识经纪人的咨询师
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将企业的性质解释为交易成本的解决方案,为管理咨询的一般理论提供了概念基础,但单靠交易成本并不能直接回答“为什么要咨询顾问”这个问题。虽然交易成本框架解释了对外部知识的潜在需求,但它没有解释知识必须通过的制度网络。事实上,企业高管总是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收集外部信息,包括战略联盟、地理集群、政府贸易集团和大学合作伙伴关系。由于几乎所有的外部知识提供者都表现出实质性的“知识经济”,交易成本本身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咨询公司比竞争对手扩张得更快。相反,我们必须超越经济学,从法律的角度来理解咨询公司在制度上的成功。正如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可能会怀疑的那样,美国管理咨询的制度化不仅仅是交易成本不断增加的必然结果,而且是20世纪30年代旨在限制公司之间串通信息流动的美国立法的意外后果。相比之下,在日本和德国,立法者从未禁止组织知识转移的替代机构,管理顾问从未在企业经济中发挥同样程度的影响力。美国长期以来的反垄断传统无意中导致了对管理顾问的制度性依赖。
管理咨询作为一个独特的专业领域的兴起,是1933年国会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Glass-Steagall Banking Act)的直接结果。《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分开,在此之前,商业银行家经常监督会计师和工程师的工作,这些会计师和工程师进行的“调查”后来由管理顾问进行。1933年的《银行法》不仅迫使商业银行放弃承销和股票经纪业务,而且立法人员还禁止银行以前从事的咨询和重组活动。与此同时,1933年的《证券法》要求“任何融资都必须经过尽职调查”,华尔街的律师将其解释为所有后续交易都需要“由有能力的(管理)顾问公司对标的公司进行调查”。此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要求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围绕公司审计重组其专业团队,以保持会计师的专业“独立性”并避免潜在的利益冲突。一些知名的会计公司,如安达信公司(Arthur Andersen & Company),以前专门从事“工业和金融调查”,现在他们的业务仅限于有限的(尽管利润丰厚的)财务审计。《银行法》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一种复杂而并不总是完全预料到的方式,禁止律师、工程师和会计师等竞争专业团体继续担任顾问,并促进了独立管理咨询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的迅速发展。
管理咨询并不是通过一个渐进的线性演变过程发展起来的,而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被监管变化打破的竞争平衡中产生的。1938年,经济学家乔尔•迪恩(Joel Dean)宣布,“不为人知、几乎不为人注意的专业管理顾问已成为我们商界的一个重要机构。”这并非巧合。因为,正如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所解释的那样,“当管辖权空缺时,职业就会发展起来。”联邦政府通过规定要求银行家对管理层进行尽职调查,并通过规定防止会计师和律师从事可能造成利益冲突的活动,使公司调查领域中除了管理顾问之外,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结果,乔治·阿姆斯特朗、詹姆斯·麦肯锡和埃德温·博斯等相对年轻的咨询师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并在短短几年内成功地将管理咨询领域公司化。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通过后,专家咨询的法律意义上的重配置在乔治•阿姆斯特朗(George Armstrong)的职业生涯中得到了体现。1921年至1932年间,阿姆斯特朗是国民城市银行(现花旗银行)负责工业调查的副总裁。在20世纪20年代,国家城市银行聘请阿姆斯特朗对银行向阿纳康达铜业提供的不良贷款进行研究,对棕榄、卡夫和好时的拟议合并进行分析,并应彭尼公司的个人要求,对其连锁百货公司的相对费用比率进行了比较。然而,1932年,在他叔叔的内部确认下,富兰克林·D·罗斯福打算分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阿姆斯特朗辞去了国民城市银行的职务,于1933年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阿姆斯特朗的新公司,乔治·S·阿姆斯特朗公司,立即获得了成功。在20世纪30年代,这家咨询公司受雇于一系列投资银行公司,调查琼斯劳克林(Jones & Laughlin)、西格拉姆(Seagram’s)、Birds Eye Frozen Foods和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等企业巨头。因此,乔治·阿姆斯特朗从组织研究的银行监管到管理咨询制度化的转变中获利,尽管他进行的研究类型并没有改变。George S. Armstrong 公司发展迅速,不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新的组织建议,而是因为Armstrong创立了一家符合新监管要求的独立公司。
在詹姆斯·O·麦肯锡公司(麦肯锡公司和科尔尼公司的前身)和博思·艾伦&汉密尔顿公司,情况都差不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极大地促进了这个相对稳定但增长缓慢的领域的业务。1926年,在经营了12年之后,埃德温·博斯仍然只雇用了另外一名顾问,但到1936年,博斯·艾伦&汉密尔顿公司已经有了6名顾问。同样,麦肯锡1926年在芝加哥创立的詹姆斯·O·麦肯锡公司(James O. McKinsey and Company),到1936年已经扩大到超过25名员工,并在纽约设立了第二个办事处。这两家咨询公司都从银行业与其组织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中获利。1933年加入麦肯锡咨询公司的马文•鲍尔(Marvin Bower)写道,这些调查类似于鲍尔年轻时在众达律师事务所(Jones Day)管理的债券持有人委员会的企业组织改革。事实上,由于投资银行家在20世纪30年代经常雇佣顾问,詹姆斯·O·麦肯锡公司的合伙人开始把他们的工作称为“银行家的调查”。
管理顾问很快就忘记了上世纪30年代的监管变化对他们职业发展的重要性。因为这些联邦法律并没有直接管理他们的活动,而是禁止来自专业对手的潜在竞争,咨询公司很容易忽视间接立法的直接后果。此外,咨询师们忘记的不仅仅是咨询作为一个专业领域的时序和结构演变,而是咨询师作为交换潜在“反竞争”信息的法律渠道的出现。毕竟,《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广泛的国会调查的结果,这种调查是在公众普遍恐惧的推动下进行的,针对当时被称为“货币托拉斯”的机构。长期以来,公众一直担心,以摩根大通(J.P. Morgan & Company)为代表的华尔街银行家不仅控制着资本流动,而且还通过银行家在大型工业公司董事会的席位,监督着迷宫般的反竞争卡特尔和协会。当国会制定了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为核心部分的监管金融市场的新政(New Deal)立法时,政客们不仅拆分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还对银行家传播反竞争信息设置了限制。20世纪30年代末,随着“公开价格”运动、银行家主导的卡特尔和《国家工业复苏法案》等几项价格垄断策略遭到拒绝,咨询公司成为了满足高管们分享某些形式的“内部”信息的内在需求的独特的美国解决方案。社会学家尼尔·弗莱格斯坦指出,美国政府“通过排除公司之间垄断和勾结的可能性”,迫使公司采用另一种方式来共享知识。企业高管们意识到,新政法律禁止他们雇佣行业协会、行业卡特尔或银行家来创建行业基准和学习管理创新,于是转而求助于管理顾问,作为他们获取组织间知识的主要来源。
反垄断法规不仅在20世纪30年代使管理咨询制度化,而且还在50年代塑造了计算机咨询的发展。正如管理咨询是大萧条时期反垄断监管的副产品一样,信息技术咨询是战后反垄断监管机构的副产品,后者试图限制垄断的力量,并重新引导组织知识的传播。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官员认定管理咨询与公司审计存在利益冲突,像安达信公司(Arthur Andersen & Company)这样的会计师事务所是输家的话,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司法部禁止IBM提供计算机咨询建议,会计师们象征性地得到了回报。1956年,IBM总裁小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 Jr.)的一项决定,解决了联邦政府长期存在的反垄断诉讼,这意味着IBM实际上将新兴的信息技术咨询领域割让给了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信息技术咨询巨头安达信(Arthur Andersen)的合伙人后来想知道,为什么他们的会计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退出了管理咨询领域,而且这些合伙人也没有意识到,为什么安达信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计算机系统咨询领域如此容易。认识到反垄断监管是20世纪50年代信息技术咨询出现的核心,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安达信没有面临更多的竞争对手,以及为什么IBM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张旗鼓地进入这个潜在利润丰厚的领域之前,在这么长时间里一直置身于这个领域之外。
特别是安达信,因为1956年政府不允许IBM提供安装和使用计算机的专业建议而获利。尽管安达信公司(Arthur Andersen & Company)在20世纪20年代曾向纽约和芝加哥的投资银行家提供“财务调查”,但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后,他们转而专注于企业审计。直到20世纪50年代,安达信才重新进入管理咨询领域,而且是最初通过一个似乎与精英管理咨询公司服务的组织关心课题相去甚远的狭窄专业:电子计算机系统的安装。20世纪50年代,安达信公司(Arthur Andersen & Company)的合伙人确信电子计算机将彻底改变企业内部的成本会计和收账管理,于是开始向他们的企业客户提供如何安装和使用计算机的建议。他们的建议是安达信自己的会计业务的合理发展,因为高管们希望使用电子计算机来加快会计信息的产生,但安达信的建议是创新的,因为在1953年之前,只有科学家和军队使用电子计算机。然而,1953年,安达信公司管理了通用电气公司第一台专门用于商业目的的计算机的安装,并很快开始以商业电子计算机系统安装专家的身份推销自己。
如果美国政府允许IBM进入咨询咨询领域,在托马斯·沃森的领导下,IBM可能很快就会阻止安达信公司进入计算机系统咨询领域。毕竟,IBM一直雇佣专家为其客户提供安装、维护和使用IBM打卡机和制表机的建议。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索贝尔(Robert Sobel)所观察到的那样,“经过 IBM培训的技术人员将安装设备,如果出现任何问题,服务代表将随叫随到,并就如何在业务变化时最好地修改或增加机器提供建议。”很少有 专门的顾问为购买或安装IBM制表机提供建议,因为IBM的销售人员确保他们的客户没有任何问题。
然而,IBM的寡头垄断力量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沃森父子(父亲和后来的儿子)不得不在美国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反垄断行动的持续威胁下管理公司,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然而,1956年,小汤姆·沃森说服他的父亲与司法部和解,并接受了一份同意令。这项法令在35年内限制了IBM的竞争能力,它不仅要求IBM出售而不是出租其机器,并向公司的竞争对手提供IBM的专有技术,而且还禁止IBM就购买和集成计算机系统提供建议。司法部禁止IBM提供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因为律师们认为IBM会推荐自己的设备而不是竞争对手。在进行反垄断监管时,司法部要求IBM将自己的知识和实体产品的销售分开。由于领先的计算机制造商IBM被禁止进入咨询领域,安达信公司(Arthur Andersen & Company)很快在信息技术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合法领先地位。安达信的“管理咨询服务”部门稳步增长,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几名会计师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的数万名顾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IBM的垄断力量可能间接导致了独立信息技术咨询的兴起,正是对 IBM力量的削弱,推动了该领域的快速发展。随着IBM的市场份额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下降,以及计算设备市场扩展到每个企业桌面,对集成这些系统的顾问的需求急剧增加。尽管1982年司法部撤销了长期存在的反垄断案,IBM赢得了几次得不偿失的胜利中的第一次,但直到1991年,该公司仍受制于1956年同意法令的最后残余部分。当IBM最终成功地解除了同意令后,由郭士纳(一位前麦肯锡顾问)领导的IBM立即创建了一个信息技术咨询集团。到1996年,也就是IBM成立其咨询子公司仅仅四年之后,IBM咨询集团的年收入就达到了110亿美元,几乎是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并且已经成为安达信咨询公司的一个重要竞争对手。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银行业监管机构和美国国会在很大程度上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为银行家再次以新的制度形式重组为管理顾问铺平了道路。大多数咨询顾问,虽然敏锐地意识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废除对保险、商业银行和华尔街重组的影响,却很少意识到这一变化可能对他们自己的公司产生的战略影响。如果不了解过去的工作情况,咨询顾问就无法预见像摩根大通这样的老对手,或者像德意志银行这样的国际竞争对手,会再次构成竞争威胁。而且,由于缺乏关于咨询是如何成为一个独特的专业领域的制度记忆,大型管理咨询公司可能会发现,他们正在与60多年前通过立法意外击败的同一专业对手重新开始竞争。
******
1962年,顾问乔治·阿姆斯特朗(George Armstrong)在自传《华尔街工程师》(An Engineer In Wall Street)的开头引用了桑塔亚那(Santayana)的一句陈词滥调:“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阿姆斯特朗不善罢,他还引用了密西西比州维克斯堡旧法院的一句铭文:“忘记过去的人没有未来……”阿姆斯特朗似乎认为,他从管理咨询的早期历史中了解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未来几代咨询师需要了解的。奇怪的是,他是对的。
阿姆斯特朗知道,作为一名顾问,他的职责不是设计新颖的组织设计或实验性战略,而是重新配置他周围的组织知识,以适应他的企业客户的需求。正如他在国民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工作时了解到的那样,乔治•阿姆斯特朗(George Armstrong)是一位知识经纪人,高管们向他求助的原因是,咨询顾问可以让经理们通过之前的咨询任务获得关键的组织知识。虽然“交易成本”一词比乔治·阿姆斯特朗的自传晚了十年,但阿姆斯特朗会欣然同意,他的咨询业务依赖于知识经济,因为他是20世纪中叶贯穿企业经济的信息网络的核心人物。
然而,在乔治•阿姆斯特朗的自传中,他并没有试图向咨询顾问解释他们工作的潜在经济原理,而是警告他们警惕正在沉睡的竞争对手。因为他知道,知识经济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高管们选择购买外部知识,而不是简单地自己创造知识,但这种“制造或购买”的分析无法解释为什么企业更青睐顾问的增长,而不是其他信息来源。阿姆斯特朗特别记得,咨询顾问的广泛雇佣是上世纪30年代反垄断立法的意外后果,该立法将咨询顾问的使用制度化,并禁止竞争对手的专业团体(尤其是银行家)提供类似的服务。咨询可能只是体制内最佳做法转移的许多可能解决办法之一,但在美国,大多数其他方式都是非法的。管理顾问提供了另一种合法的方法,在竞争对手组织之间转移知识,而不会招致监管制裁。
最后,阿姆斯壮认识到,他自己的历史给未来几代咨询师上了重要的一课。乔治·阿姆斯特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听从了叔叔的建议,创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从政治驱动的银行法变化中获利。管理咨询和信息技术咨询的发展并非源于咨询公司有意操纵反垄断法规,而是源于他们利用政府禁令造成的专业服务的司法空白。事后看来,我们可以看到阿姆斯壮从监管改革中获益的经验,可能会为后继几代咨询公司提供宝贵的经验。当IBM无法提供计算机安装方面的专家建议时,安达信(Arthur Andersen)填补了空缺;但一旦司法部撤销了同意令,IBM就重新成为咨询服务的领先提供商,尽管安达信已经领先了30多年。如果没有禁止银行家提供咨询服务的规定,阿姆斯特朗的老东家花旗银行很可能再次成为咨询业的重要竞争对手;或者至少在监管环境出现下一次彻底转变之前是这样。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