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人的精神不死 | 谷雨

过去一年,疫情终于不再是生活的主题,感染、核酸、封控这些旧日名词烟消云散,生活重回正轨,我们盼望回到旧日的好时光,但2023年过去了,过去的却并不平静:
新的战争与冲突、经济的颓境、世界的分裂,新的动荡以新的方式呈现;千年一遇的暴雨、史所未见的高温,我们身处的地球也在暗流涌动;AI崛起了,一个新的世界加速到来。
所谓现代人,即是每个人心中自有风暴。我们对未来不证自明的信心正经受拷问:生活会越来越好吗?当未来不再是一条没有尽头向上的直线,而是震荡成为乱麻。
在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邀请谷雨的朋友们,回溯过去一年他们最重要的经历和感悟。回溯是私人的,也是公共的,是感受,也是体察。而最深刻的感悟,无不关乎行动。我们的年终栏目命名为《地球来信》,既是因为谷雨的朋友们身处四面八方,也是因为个体的生命经验,才是时代乱流之中,独属于每一个人的锚点。其中,项飙教授谈到了他在疫情后回国的故事,谈到了他所体察的我们共同的焦虑;王笛教授一如既往的珍视普通人的日常,他写书、论述,将之作为过去一年最重要的行动;记者周轶君则奔波于几国之间,探寻什么是好的教育——孩子是未来的主人翁,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在探寻什么是好的未来。我们的讲述者各有身份,但同一的是,作为个体,他们都将自己作为方法。就像项飙所说,无论时代如何变幻,他相信人的精神不死。
过去一年是我们理解过去的钥匙,未来将如何到来,过去一年也在埋下线索。我们每个人要做的,就是和谷雨的朋友们一起,去思考、去感受、去行动。
作者| 张月
编辑 | 张瑞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在绝大多数场合,项飙是那个被提问的人。作为也许是当下中国最负盛名的人类学家,他被冀望能够给充满焦虑和不安的人们提供答案与方法,他也习惯了像一个学者一样思考和回答问题。但2023年对他来说最意义非凡的事情,是这种身份和方法都失败的时刻。
2023年9月至10月,他回中国待了两个月,上次回国,还是在2019年。在严肃的学术交流之外,他花了更长的时间和普通人待在一起,希望了解四年后人们的焦虑到底发生了何种变化。在北京他去看了浙江村的老师傅,在广州和一些身份各异的年轻人待了七天,有时会从早上聊到深夜。在家乡温州,他见了当地的老师、学生和一些社群。
在经历了已经被当做历史纪年单位的三年后,项飙对中国的观察是,人们对焦虑已经不再陌生,与它长久相处变成了新的现实。那种曾被集体相信的成功和增长叙事破灭了,但这不完全是坏事,当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个体的意志和选择才有了更多的机会浮现。
项飙在浙江村 ©傅梅溪
在广州的一个夜晚,项飙切身感受到了这种丰富性。他和那群年轻人坐在地板上聊天,大家讲述各自的生活和苦恼。有人是学生,有人是工人,还有的人无业,项飙记得,大部分人说的是一些司空见怪的琐碎小事,并不剧烈,也不深沉,但每个人都认真回应,坦然分享。那形成了一种极其温柔的氛围,某个瞬间,项飙觉得自己摸到了生活更真实的质地。在那种氛围中,项飙察觉自己“学者式”的方法失败了,或者说,他不愿意再用那种方法来面对这些庞大、具体、细碎、深刻的个体经验与感受,如果把它们仅仅视作“素材”,那显得过于粗暴和傲慢了。
这个瞬间,项飙称之为2023年的“开窍”。无论如何,人精神中那些丰富复杂的部分始终不能被理论的手术刀精准解剖,它们在人的头脑中永恒闪烁,不能被任何力量所抹杀,不管在何种境遇,真实的感受和思考始终是人可以为自己保留的庇护所,“我是相信,人的精神不死。”项飙说。
以下是项飙的口述:
“开窍”
这次回国既不是一次出差,也不是简单的一个探亲,而是想沉浸式地感受一下,现在时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也去看看自己应该怎么样去进一步思考,所以是希望看到具体的生命体验。
上次采访咱们说共同焦虑(编者注:项飙的人类学研究强调从普通个体的苦恼和焦虑入手,为此提出一个概念,共同的焦虑,详见《与项飙对话:在不确定的世界,建设自己的大后方》),那么就得对共同焦虑有非常具体的把握。比如说人们觉得经济下行找不着工作,他具体是怎么感知的,他对自己未来是一种什么想法,还有来自家庭的压力,你会看到各种现象:去演唱会,特种兵旅游,淄博烧烤等等。这些看起来好像不是焦虑,但是真正的焦虑都是通过这些非常具体的事情表现出来的。所以你必须去看,跟他们混在一起,有一个浸泡感,你才能够理出具体的焦虑长什么样,是什么样的感觉。
但是你知道要浸泡到一个群体里面是很不容易的,我以前做实地调查最少有8个月,现在大都市里面大家都很忙,隐私感也很强,我这次回去两个月,一般情况下不可能达到这种真正地混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在过去这些年通过公共交流,认识了不少网上的朋友,他们都非常的慷慨,愿意接纳我,因为大家这种的开放、信任和慷慨,让这次回去就成为我2023年最重要的事件。
这次回去主要见了三个群体,一个是我浙江村的老朋友,1992年我开始调查,这个算是回访,大家都很熟。第二个群体是在温州,主要是中学老师和其他的领域的青年人,包括一些学生,第三个群体是广州“看见最初500米”工作坊的参与者,大概将近20人,他们主要在广州的周边,也有从其他地方来的。
跟经典的人类学不一样的是,我没有住到他们家里去,但也不是说我去做访谈,我问他们答。大家就跟朋友一样见面讨论,聊很长时间的,比如说在广州那几天,大家是从早上10点一直聊到凌晨一二点。
在广州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场景是,10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到工作坊的两个学员家里,大家在地板上坐成一圈,大概有十几个人。大家都讲自己具体的经历、故事。聊到大概是十一二点的时候,我突然会有一种感觉,自己的身体被很多很具体的生命经验和情绪所包围、所拥抱。
这种感觉对我是比较奇特的,因为我的年纪比他们大,同时我是一个长期做思考的人,还是一个情绪上很不丰富的、比较单根筋的人,所以一直以来,我对信息和材料的处理是非常头脑化的。我看到一个信息,我会去想这个里面主要的点在哪里、线索在哪、起源是什么、中间过程是怎么样,我会把一个原生团一样的情绪和经验转化为一个可以解剖、可以分析、可以理清楚的材料。这个是我的工作方式,也成为我的思维方式。
那天晚上,我觉得我这个办法失败了,不是说那种行不通了,而是说,我自然而然地觉得我不能够用我熟悉的方法来处理大家讲的东西。因为大家讲的太具体太丰富,情感太重,它是一个一个的原生团,没有清晰外形,但是很有力量!你很难简单地去从外部一把刀切进去要对它解剖,那就变成一个非常粗暴的行为了。
每个人的故事本身都不是特别激烈,其实非常寻常。比方很多人讲他和父母的关系,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它很具体。比方有一个学员跟妈妈不讲话,很长时间没有联系,突然有一次,妈妈牙疼的时候打电话给他,问他上次牙在哪里看的,说到这一刻他就开始哭,他说我知道牙疼是真的很疼很疼的,我知道是什么样的。这个经历分析起来是很复杂的,为什么关系疏远的情况下,母亲会在牙疼的时候给孩子打电话,也许是一种潜意识的求助,也许是母亲想借这个机会重新跟孩子说话;孩子当时赌气没有告诉妈妈在哪里看的牙,但是他现在和我们讲这一段经历,讲的时候又有不可遏制的痛感,怎么理解他此刻的痛?这个关系里头,当事人和我们都是很难去信息化的,但就让你感觉到它的质地。
很多这种故事,有时候不是真正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之后引起的感受的波澜,逼迫你要面对它,要去处理,要去消化,其实这是一种责任。许多事情没有太清楚的对错判断,但是你必须面对,这种面对,是一种在地的责任。这位学员讲妈妈的牙疼忍不住哭,是在处理自己对生活的责任。
慢慢的,它们(这些讲述)就包围你。我就有一种头脑被架空的感觉。那种感觉是很美好的。平常我要说头脑架空,听起来有点紧张,好像迷失了,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些信息。但那天,身体被包围着包裹着,我的感觉是很安心的、很有着落的,你一点都不迷失。
你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下一个问题是什么?你不这样说话了,你会搅在具体的经验感知里面,搅在里面的感觉是很好的。也会有新的问题冒出来,包裹着我的那些经验故事也不断让我回想起其他的一些经验,所以它不是说一种崩溃式的,好像失去了回应的能力,不是的,反而是我的回应变成是更加多方位的,更敏感了。
我有一点点感觉,是那一刻开窍了。对,就是开窍。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它,2023年是我的开窍年。
和稀泥是一种背叛
“看见最初500米”这个工作坊是2022年我和广州建筑师何志森和在奥斯陆的段志鹏一起发起的,我人在德国,只能通过线上参与。这是一个社会艺术项目,通过三个月的大量的讨论交流想法,同时每个参与者选一个课题,用一种艺术的方式,去观察自己的周边,并把它用艺术表达出来。
最初500米这个概念和我之前提出的“附近”有关,说的是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这个世界。我们当时觉得我们的认识太两极化了,一方面大家很担心个人的情况,比如学业、亲密关系、工作等等,这是一极,另外一极就是手机上告诉你的世界大事。然后你的周边完全变成空洞化,谁是你的邻居,谁在清理你的垃圾,每天你去吃早点,开早点铺的那个人是谁,他们在担忧着什么,他的孩子在哪里上学等等,这些是我们生活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但是对它们我们基本上是无感。这种无感造成了很多焦虑,因为你在一种好像很不稳定的状态里面生活,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托着,可能会有一种很强的孤独感。同时你又老关注所谓大事,这些大事都是通过很多意识形态化、具有很强烈情绪色彩包装出来的话语,很容易造成意识上的断裂对立。“最初500米”是说,生活里那么重要的一块其实在我们的意识里是缺失的。
来参加的学员都不是搞艺术的,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是学生,有的是搞计算机的,有的是做财务的,有的是无业。
很多学员最后的作品都和亲密关系有关。前面提到的那位学员做的是他和母亲的。他会说家庭像犯罪现场,要不断逃离。这背后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本来家庭不和,有他母亲的精神不稳,有相对贫困,这是一种城市贫困,城市贫困跟农村贫困情况不一样,因为城市贫困造成的精神压力是特别大的,更加难以疏解的。他的项目是把自己和母亲吵架的声音录下来。他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但是和母亲的吵架是最让他压抑和心烦的事情,他可能就想处理一下心头的这块大石头。录完了,要做出项目,他就要剪辑。在剪辑的过程当中,他突然听到了新的东西。他听到母亲的很多谩骂,其实是在渴望他的注意力。母亲有的时候会讲很不好听的东西,其实是在表达她的担忧。他发现在吵架过程当中之前完全没有体会到的东西。最后他的作品就是在快递柜(工作坊里形成的所有作品都装到一个快递柜里)的一个盒子里放着录音,播放器连着一条脐带形状的塑料管,观众可以通过脐带听到他和母亲对话的片段,你听到的是吵架、是痛、是冲突,但是通过脐带传出来。
我很难判断这个工作坊究竟发挥什么作用,但是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没有这样的讨论,没有几个月的这种浸泡观察,我就不可能和他们一起感悟、开窍。
开窍不容易的,特别像我这个年纪,脑子里心里很多东西都堵死了。而且不是说通过什么理性思辨去转弯去开窍,而你是把自己打开,让身体放松,让别人的经验来浸泡你,包裹你,这不是容易的事情。
这全靠大家的信任。有了信任才会有深度的理解和坦诚。不同意就是不同意,因为在那个情况下和稀泥是没有意思的,而且和稀泥讲严重一点,是背叛。因为基于信任,我们觉得是有责任向对方讲你真实的感受,这个东西也许会伤害到你,但是说你假装一切都好,这是一种背叛。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种信任,比方说我们有一个学员,她参加工作坊的时候已经两年不去工作了,在交流上有障碍,她说话不能成句子的,她也基本不怎么出门,呆在家里,线上讨论会的前一天,她会紧张得睡不着觉的。这次我们相聚的时候,她每天都来,还带了点心,她说话声音还是很低,但是看得出来她很开心,不时地会讲很幽默的话。她说,“我要让自己重新长出来”。这样的话,一般哲学家讲不出来的。
我这次“开窍”以后,再看世界的时候,你一下子就对人的具体的经历和感知更加敏感了,会比以前更加细腻,更加关注情绪和人的心理过程。
清高与佩服的消失
在温州我跟很多中学老师聊,你还是能看到中国社会的一些变化。
比如说我发现清高和佩服的消失。在我读书的时候,中学里面总是有一些老师,一般都是40岁到将近60岁左右,校长说什么他就唱对台戏,但是大家很佩服他,因为教书教得好。有的时候他的意见也是为怪而怪,大家都知道不可行,但是大家都很高兴有这样的老同事用这种方式唱唱反调。反正是有那么一批人是这样的,清高,傲气,有群众佩服。这样的人就在消失。
在大学就更明显了,当时我们上大学,什么样的老师讲话最有吸引力?一般的都是那些比较傲气的、看不起行政的那些人讲话是最有吸引力的,大学里头系主任经常是被欺负的(笑)。行政权力是被清高、傲气、佩服这样的民间话语制约的。没有佩服这个事情的话,你也就没有那些学校里面比较刺头的大师级的老师,去保护我们传统和风格。因为佩服它是一种口碑,是一个民间自发形成的评价标准,它告诉人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它会给人很多力量。
在浙江村也有这种现象,比如我去看的老先生,他就会讲到自己是当时最好的裁缝,大家是佩服的,他说话算数。但是年轻人越来越关注的,不是去追求傲气和别人的佩服,他是在追求体面和别人的认可,所以傲气被体面取代,佩服被认可取代。原因当然是跟整个生活的商业化、行政化、等级化等都是有关的。归因不是特别难,难的是说人心为什么会这么变化,有没有可能再变回来,我也在思考。
生命力的争夺与摧毁
还有一个让我担忧的问题是青少年的抑郁和自杀。我不太能够讲它的细节,有些对我情感上是个很大的冲击。
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青少年问题、教育问题或者医疗问题,青少年抑郁是全社会的问题。
在德国,年轻人也有一种绝望感。气候问题是非常大的一个焦虑,这个国内年轻人可能有点难以理解,为什么气候焦虑会影响个体到抑郁这个程度。有些事情是很具体的,比如我们这一代就到处出去旅游,看不同的文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感的来源,但现在欧洲新的年轻人就不敢了,因为他会考虑到他的碳足迹的问题,考虑到他的访问会给其他的地方带来的影响,比方说要去西藏的话会不会给它的文化带来损害,他就觉得他自己没办法在世界上行动。另一方面他们觉得老一代现在掌握政治经济权力的人不愿意拯救地球,感到很绝望。
但是从青少年的抑郁和自杀这个情况的上升来讲,中国还是有一点特殊。因为德国年轻人不会说到一种极度抑郁和自杀,但对于中国15~25岁之间的年轻人来讲,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了。
你知道给我影响很大的一个哲学家是阿伦特,她说,人存在的一个意义基础,就是我们不断把新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每一个新的生命都会是一次革命,我们觉得生命是重复,但对一个孩子,他一切都是一个新的起点。动物也不断出生新的生命,但那是简单的重复,每个个体是物种的一个分子而已。但是人有意识,不仅是物种的一份子,而且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每个人的生活不可能是对另外一个人的简单重复。每一个孩子的到来,每一个新的生命的起点,都是我们人类去探索新的可能的一个机会。
但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很多新的生命在16岁17岁就选择结束,这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存在意味着什么?
人为什么终结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我们的发展是很大程度上是对生命力的一个争夺。抑郁症就等于他的生命力被耗尽了。生命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能够不断地自己延伸自己,这种自我持续、通过内在机制吸收外来养分,使得自己成长的力量,就是生命力。生命力怎么体现出来呢?那是当生命主体要对外界做反应的时候。生命力的最主要的表现可能就是劳动,再加上各种行动、意识、情绪等。生命力不是外在给予的,是生命自己拥有的,但是是在和外界互动时体现出来的。当人们觉得对外界“无感”、对别人“爱无能”,那就是生命力受到损害了。环境不仅可以耗尽他的生命力,而且摧毁了他自己重新产生生命力的能力。这样就会有抑郁或者是自杀这样的情况。我们的教育、我们各种的评比、各种对成功的追求,从生命力的角度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比如说家长,不断地告诉孩子你为了将来,要好好学习,要成功。父母不断的说教和暗示,让孩子觉得,为了父母的面子、为了父母以前吃的苦、为了父母现在投入,他们必须努力,他们要对2个成人甚至说是6个成人是有责任的,他要去创造一个未来去“赎”父母和祖父母的苦。一种在自主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责任感是会激发生命力的,比如父母有了孩子,往往生活更累了责任更大了但是觉得也更有意义了。但是父母强加给孩子的责任感,是要击垮孩子的生命力的。孩子就早早失去了那种享受那种漫无目的的、当下的、即刻美好的能力。
具体可以很深刻,抽象可以很肤浅
在温州的时候,我还去参加了一个叫慢来生活的社团,他们是从2017年开始一直做到现在,就是周末请陌生人吃饭,做得也很低调,但是能够坚持那么多年做下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不容易。
在和慢来生活社团的对话中,当时现场有人提了一个问题,“怎么和保安说第一句话”,这样的问题其实是非常好的,很具体,激发大家的思考和智慧。这样的问题比很多学术性讲座里听到的问题要好很多。学术讨论里提的问题都是怎么给这个事情下定义,理论上怎么理解等等,而不是说从他生命经验出发,不是说我这里有一个纠结、我怎么跟保安说这句话等等。这些问题非常的具体,然后你要引申开来的话,意思是非常丰富的。
比如说什么叫第一句话,这就会联系到很深刻的道理,第一句话要有一种吸引力,让对方觉得很容易接得住,第一句话不能是凭空来的,你呼啦走到保安面前跟他说一句和他所在的场景无关的话,那就很奇怪。所以你一定要对这个场景有一个感知,要有对话的流淌感,你的第一句话应该是流淌中的一部分。流淌感这个东西应该是一种半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感知,但这就是“附近”。
问题是现在这个感知变得很弱。现在教育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把学生和生活切割,整个教育做的工作就是切割,住校,一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这样等等,学生是在泡泡里面做非常机械的活动,他对生活、父母在做什么,都不知道。刚刚提到的场景感、对话的流淌感,他没有机会去触摸这些东西,所以提的很多问题变成像教科书上的那些如何定义什么的,我觉得没有太大意思。
所以我可能更愿意跟非学者交流,因为非学者会更容易从他的生活经验里面提出一些问题,生活经验是具体的,但是会很深刻。
具体的事情是不容易说的,因为你要对具体的情况很熟悉,知道人在那个场景下,究竟是怎么感受怎么想的。我们的思考往往被抽象和肤浅的东西绑架了,具体的生活丢在那里好像总是一地鸡毛。所以你如何在这样非常具体的场景里面提出新的问题才有特别的价值,你才能够以具体的方式帮助具体的人。
人的精神不死
整体上,我感觉中国的common concerns有一些变化。变化之一是大家是对焦虑不再陌生了,觉得焦虑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很多人开始想从里面走出来,但是怎么走出来不清楚。
走出来是需要很勇敢的,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你要跟过去的很笃信的东西决裂,这不是很容易的。这需要一个社会环境,需要一个圈子互相打气。很多青年人的行为上,他有比方说对考公、对要不要辞职的反思,包括我之前讲到的演唱会,以及所谓的发疯文化,其实都是在表达说我们要重新定位,要重新估价很多事情。
在广州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这种要重估价值的渴望,当然参加工作坊这批人本来就是比较敏感的,这批人他一开始就是有反思的。我现在是感觉越来越多的人会加入到这个反思里来。以前很多人会觉得,这些要反思的不都是一些文青废物,找不到好工作什么的,现在可能就是那么想的人不会太多了,大家会觉得去重新探索生活的意义是一个正当的事情。
“附近”这个概念受到那么多关注,也说明了这个趋势。我自己一开始也有点愣,我说这个概念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强的、大的深意,怎么会激起那么多反响。现在看来,它可能确实触到了大家的一些痛点,激发了大家的一些思考。所以这个概念引起反响,不是因为它本身,而是大家给了这个概念一个新的生命,给了它新的力量和底色。
关于未来,我是比较乐观的。我是觉得我们很多人在重新思考,提出了很多很好的问题,至少在相当一部分的年轻人里面,我觉得对话变得越来越有意思。
也不能说所有的年轻人都改变了,至少在相当一批年轻人,他的思考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着地。我觉得这可能会对整个社会的变化是有好处的,我是相信,人的精神不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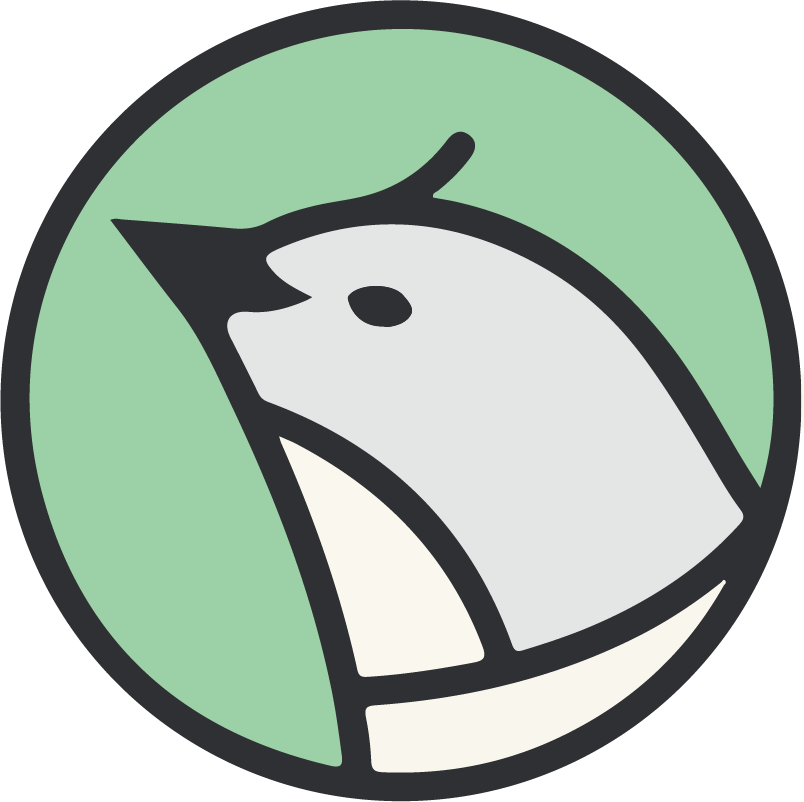 (来源:腾讯新闻)
(来源:腾讯新闻)
◦ 头图、封面图均来自项飙。
*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为了不错过每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将谷雨实验室设为星标🌟哦,期待每次第一时间与你相遇!
关键词
就是
时候
事情
就是
中国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